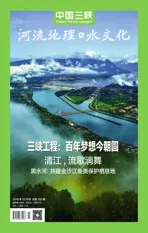理性之外,需要想象力、诗意与神秘
2018-03-15兰川
文 | 兰川

切今之事
作者: [英] C·S·路易斯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原作名: Present Concerns
译者 : 邓军海 译 叶达 校
出版年: 2015-3
丛书: C.S.路易斯作品集(精装新版)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切 问而近思”原本是说做学问要心不外驰,不泛问远思,以免劳而无功。那么,对现代的“切问而近思”,便是对现代进行切中要害的发问,对身处现代的现代人进行近取诸身的思考。“切今”有一种为当今诊断的意味。《切今之事》囊括了路易斯19篇原作。所涉话题有理想、平等、民主教育、文学等。
何谓时代势利病?路易斯在《惊喜之旅》中说:“不加批评地接受我们自己时代共同知识气候,认定大凡过时之物便不再可信。”现代人大都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既然处在时间的最前端,无疑是最好的时代。科技如此发达,生活如此富裕,宇宙对我们而言也日渐透明。这时候,赞美过去,是落伍过时的,除非这种赞美是为了衬托现代“更 美好”。
自17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理性的旗帜得以高扬。这时的理性已经不是奠基于古典哲学和信仰的向善、向神的理性,而是首先关注效率的理性。所有符合理性计算的就是好的善的,与效率冲突的部分大可阉割、舍弃。
路易斯对现代人的这种“时 代势利病”十分警惕。这种病让人只拘泥于身处的时代。这不是现代人的明智,而是现代人的自大。他们信任理性,信任逻辑,不相信一切无心的、无缘由的事情。他们同时具有两种特征:逻辑完整和心灵萎缩。他们会用逻辑和理性将一切不确定杀死。
与此相反,健康的人应该允许在逻辑、理性之外,有想象力、诗意与神秘。而诗意和神秘正是古典所保存的那部分。很可惜,时代势利病一发作,现代人便将古人放在被告席,将上帝放在被告席。他只相信,有了理性,就可以做一切事物的审判官。
启蒙运动之后的种种理论和社会现象又加剧了这一病症的发作。比如教育革命。现代工业文明之前,教育奠基于古人。西方有基督教传统,中国有一脉相承的古典教育。现代工 业文明之后,凡是在时间上被划定在“古代”一方的,都因古而废。现代教育的去神圣化,让神和圣贤人物不再可能。
现代教育提倡民主、自由、平等、独立、解放,这本身无可厚非。然而,这些理念的提倡是要有保留神圣维度的前提。否则,当我们在说民主、自由的时候,其实是在说自己有理由从被“管教”中释放出来。而当我们说“管教”的时候,我们指向的是宗教的教条、古人的教训、家长的约束等等。凡是在上者,诸如神、圣贤、长辈,我们都视之为仇雠。凡以神之训诫、道之义理要求我们的人,必定是早就应该埋入历史尘土中惹人厌烦的清教徒、卫道士;凡以圣贤之言、长辈道理教育我们的,必定是压迫、束缚我们的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落伍者。
势利病的危险还在于,妄图运用理性打破传统,对人类的未来,以精心策划代替自然生成。他们相信,理性策划将更符合人类利益,将在更短的时间内让人类过上物质极大丰富的绝好生活。这种“相信”建立在一个“自圆其说”上——一切损害眼前利益的都不算损害,因为那一定符合人类长久利益。
路易斯对现代切脉诊病,所立足的是古代。在多数人礼赞现代的时候,他毫不避讳自己是好古之人。他提倡今人读古书,并非因为古人皆对,而是因为古人可正今人之失。他说:“每一时代有其识见。它善于看到特定真理,亦易于犯特定错误。因此,我们所有人都需要那些可以纠正我们自身时代标志性错误的书籍,这意味着古书”(《人 之废》)。
读路易斯的书,是审视自我,也是审视自我身处之时代。正如译者后记所言:“真 正的阅读,给我们带来的往往是冲击,而不是抚慰;是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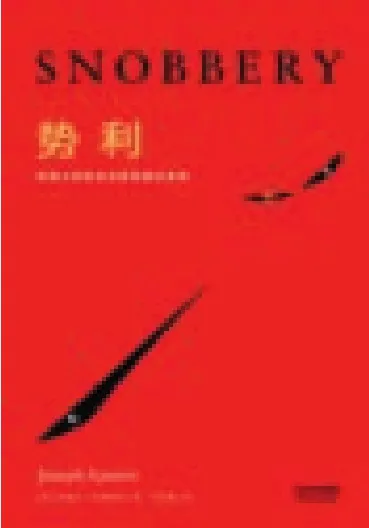
作者: [美] 约瑟夫·艾本斯坦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所谓上流社会及势利眼众生相
译者: 马绍博
出版年: 2017-5
C.S.路易斯的《切今之事》讲的是整个时代的势利病。而具体到人,势利就是一个关乎每日生活的病症。这种情况,被约瑟夫·艾本斯坦写在了《势利》一书中。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很多大名人都有势利病。伍尔夫亲自撰文写自己的势利病——《我是势利眼吗》。据说她曾攻击天才作家乔伊斯毫无教养,势利成了她打压对手的武器。和她一样患有势利病的大名人还有普鲁斯特、安迪·沃霍尔等。据本书编辑介绍,苏珊·桑塔格的魅力就在于她将势利心态和自我推销的技巧成功地结合了起来。桑塔格的出版商将她精心包装成一个深邃、美丽、前卫、法国化的严肃知识分子,只有在美国这个追捧欧洲文化的势利心态以及文化自卑感挥之不去的地方,她才能够获得成功。此外,无论是豪门出身还是贩夫走卒,无论社会名流还是市井小民,都被纳入了作者考察的群体,他们的势利心理毫发毕现、无所逃遁。作为读者,读这本书的时候也一样心有惴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