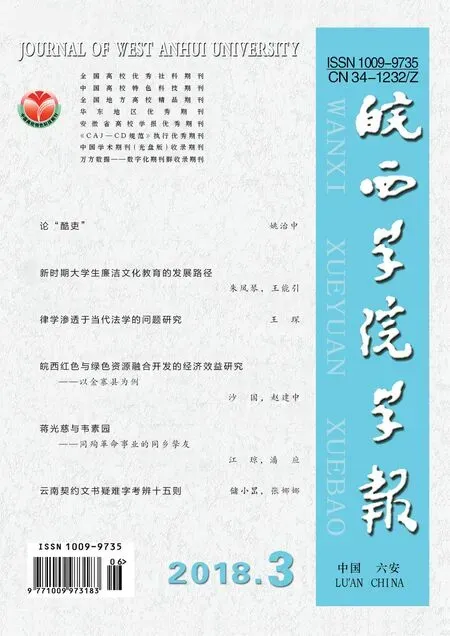论“酷吏”
2018-03-07姚治中
姚治中
(皖西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华夏国家萌芽同时也萌生了世卿世禄制,各级官职由部落贵族世袭。一直延续到西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世卿世禄制逐渐被官僚政治代替,官僚制度形成。古代把管理国家事务,统治平民百姓的人叫吏,听命于君主的吏叫官,官吏的群体叫僚,《尚书·皋陶谟》称“百僚师师”,即此。司马迁作《史记》,首次将统治手段严酷的官吏列入《酷吏列传》[1],到《金史》为止,二十四史中有九部编列《酷吏传》。2002年版《辞海》说酷吏“指滥用刑罚,残害人民的官吏”,只以“酷”字的原义为本,过于笼统,说“后世史书因之”,也不够严谨。
一、“酷吏”是一个历史概念
尧舜禹时期,确立了“以德治国,以刑辅德”的治国理念。皋陶“迈种德”,所以得到舜的任命,担任“士”(司法官),在建立华夏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王朝——夏——的过程中,皋陶坚决地贯彻了这一方针,“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史记·夏本记》)
李耳总结尧舜的德治观念,总结为“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结成完整的体系。作为考察国情的根本[2]。儒家学派在这基础上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突出以德治国的主导地位:“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司马迁也认为严刑是德政必要的补充:“民信(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刘向则认为,严刑苛罚忽视德教的主导,“非皋陶之法也”。(《汉书·礼乐志》)
我们不应忽略,中华治国理念的古代认识是在5000—4000年之间开始形成的,其中有很强的原始性。如上述之“刑”是皋陶之法的主体,其实就是刑罚,即《尚书·大禹谟》所说之“刑期于无刑”。它只是“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皋陶等的治国理念“以德治国,以刑辅法”,它只有关于法治的因素,到西汉初年,刘安等提出以“法籍礼仪为治国之准绳”。(《淮南子·主术训》)才是比较成熟的“以德治国,以法辅德”理念,但是,它没有成为主导治国理政的方针[3]。汉武帝时确立了董仲舒思想的主导地位,“王者欲有所为,宜求端于天。天之道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使阳出布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汉书·董仲舒传》)“德主刑辅”成为封建王朝治国的指导思想。前引《史记·太史公序》说明司马迁也是持同样观点。但一旦偏离,以刑罚为主体,即是酷政。“酷吏”政治是当时封建专制统治的一个方面,它的本质是被认为代表“天”的皇帝的人治,各个时期皇帝的意志决定不同时期“酷吏”的表现,所以欧阳修说:“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新唐书·酷吏传》)
西汉王朝正当中华封建社会早期,唐朝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这两个王朝的酷吏表现出不同时期酷吏政治的典型性。
二、西汉时期的酷吏
西汉的基本国情是,它还处于封建社会的前期,从5000年前(距西汉3000年前)开始的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但是还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存在多方面的残余,妨碍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基本完成了渔猎畜牧向水利农业的过渡,但水平很低,各地发展不平衡。如邻近中原的淮河流域都还没有普及牛耕,养蚕技术也不成熟。官方不支持养二次蚕。
夏商西周基本完成原始部落向地方性国家(方国、诸侯)的转型。到西汉时仍有严重的残余。刘邦镇压了异姓王,同时也册封同姓子弟为王,到前157年景帝即位时,诸侯王领有42郡,而中央王朝仅领有15郡。前154年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基本扭转了局面,但并没根本解决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4]。
一是部落氏族转型为各地的“豪猾”,“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汉书·王尊传》抵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破坏小农经济的巩固。还与诸侯王的残余势力相勾结,企图武力夺取皇位。“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齐孝王孙刘泽交结郡国豪杰谋反,欲先杀青州刺史。”(《汉书·隽不疑传》)“豪猾”这一诸侯割据的社会基础,直到西汉后期都未清除。
二是以皇权为核心的思想意识并不牢固,严重影响皇权的巩固和国家统一。它多方面地表现于社会生活中,对此贾谊有全面的论述。其一,“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其二“……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的道德伦理还不完备,“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其三,以淮南为例,交租赋服劳役要远赴中原京城长安,加重了经济负担,而且倍加辛苦,“其苦属汉而得王至甚”。不少民众从中央的郡县逃亡到地方诸侯国去。其四“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义,捐廉耻,……”急须“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汉书·贾谊传》)贾谊认为,这些都不是“俗吏”所能胜任的。
总之,两汉酷吏政治的出现是继承“德主刑辅”传统的必然,出于巩固封建经济政治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阴柔的刑治向阳刚的严酷偏移。汉武帝(前140—87年)时期,承祖辈解除异姓王之余烈,基本解除了同姓王的威胁。同时“独尊儒术”,确立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指导思想。前135年,其祖母窦太后死后,大力提拔公孙弘、张汤等以儒学缘饰刑、名之术的新一代官僚,汲黯说他“用人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汉书·汲黯传》)《史记·酷吏列传》收酷吏12人,武帝朝占其九,《汉书·酷吏传》收酷吏13人,加上另立传的张汤、杜周,共15人,武帝朝占其十。这一批官僚,在西汉巩固封建专制制度的关键时期,基本起了正面的作用。班固说这些人“虽酷,称其位矣”。(《汉书·酷吏传·赞》)其主要活动如下:
第一、致力于铲除同姓王割据势力,巩固皇权。景帝朝,御史大夫晁错顶着父亲的反对,致力于“削藩”,郅都“行法不避贵戚”,被列侯和宗室称为“苍鹰”。武帝时,张汤追究淮南、衡山、江都诸王,“皆穷根本”,对出入诸王“禁闼腹心之臣,……交私诸侯”的人物,即使武帝“欲释之”,他坚持“如此弗诛,后不可治”,从皇朝根本出发,武帝最终同意他的做法。(《汉书·张汤传》)
第二、打击“豪猾”,从社会基层清除破坏封建制度发展的障碍。“汉承战国余烈,其并兼者则凌横郡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后汉书·酷吏列传》)一般地方官(从二千石郡守以下)都不敢招惹,平民社会中盛行一种观念:“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汉书·酷吏传·严延年》)这些“豪猾”藐视王朝法令,如涿郡西高氏、东高氏等,“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还“宾客放为盗贼”,俨然是地方上的第二政权。西汉的“酷吏”列入《酷吏传》者,15人中有十人都以严酷手段镇压“豪猾”,淮南王刘安的表兄弟周阳由,当过几处郡守,“所居郡,必夷其豪”。(《汉书·酷吏传·周阳由》)酷吏之所以得名,严酷镇压“豪猾”是主要原因,在2000年前,不如此不能巩固封建国家。严延年任河南太守,“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根据法令严办)迫使“豪强胁息,野无行盗”。为小农经济的生存与发展营建安定环境。
第三、镇压黑社会。西汉黑社会活动猖獗,其形成原因很复杂,大致以某些诸侯王或“豪猾”为首领(主使人),豪猾为骨干,破产农民、市民、手工业者为群众,破坏涉及多个方面。公元前150年,汉景帝立刘彻为太子,梁王刘武的愿望落空,他收买刺客,暗杀反对立他为皇储的“议臣”袁盎等十余人。有的官商勾结,囤积居奇,茂陵“富人”焦氏、贾氏……汉昭帝驾崩。囤积殡葬物资,抬高物价要挟朝廷,大司农田延年没收了这批物资,他们出钱网罗田延年的“罪状”,买通了丞相和大将军霍光,迫使田延年自杀。(《汉书·酷吏传·田延年》)汉成帝(前32—7年)时,长安“闾里少年群辈杀吏”,接受某些人的收买“受赇报仇”。大家一起“摸丸”,摸到红丸的杀武官,摸到黑丸者杀文官,摸到白丸的为作案死亡者料理后事。没有这种“买卖”时,就趁“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汉书·酷吏传·尹赏》)京都长安尚且如此,地方上如何安宁?尹赏担任长安令“视事数月,盗贼止,郡国亡命散走,……不敢窥长安”。这些“闾里少年”究竟是什么人?“……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鲜衣凶服被铠杆持刀兵……”显然与起义农民沾不上边。为什么尹赏的举措产生了巨大的震慑?手段极其残酷,一次就活埋数百人。
西汉酷吏政治表现出封建官僚政治的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违背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权观念。《尚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道德经》第25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有版本作“王亦大”)尊重人的生存权。西汉酷吏对付“豪猾”的残忍,司马迁、班固等都持批判态度。《汉书·酷吏传·严延年》写严延年之母到儿子这里过腊八,听说儿子又杀囚犯,不愿到儿子官府,只住在“都亭”中。严延年去拜见母亲,母亲说:“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滥杀人者自己也会遭报应。)
第二、酷吏执法是封建“人治”的一个侧面。酷吏的头脑中,皇帝的意志就是唯一的“法”。杜周当廷尉,有人批评他“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他答道:法律是怎样制定的?前朝君主认可的就是律,后代君主认定的就是令,当今皇帝所需要的就是标准,哪来什么必须遵循的法律?(《汉书·杜周传》)其次,执法时,揣摩君主的意志,张汤执法,“所治即上(皇帝)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史记·酷吏列传·张汤》)杜周基本仿照张汤。最后,照执法者本人喜恶办案,而且变幻无常,使别人难以揣摩。严延年竭力“摧折豪强,扶助贫弱”,但是“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汉字·酷吏传·严延年》)他认为这样才能使“吏民……战栗不敢犯禁。”生与死全决定于他的一念之间。
第三、酷吏中的大多数对于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集中表现为忠于君主。景帝时,晁错力行“削藩”,他父亲从家乡赶到长安,劝他不要“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得罪权贵。晁错答道,不这样做,“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亲说,你这么做,“刘氏安矣,而晁氏危,……”气得服药自杀。(《汉书·晁错传》)郅都当济南太守,走马上任就杀掉“二千石莫能制”的土豪家族,常对人说:“我离开父母当官,这条命自然死在皇帝交给的职位上,根本顾不上老婆孩子了。”于是他“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和宗室都怕他,又恨他,叫他“苍鹰”。(《汉书·酷吏传·郅都》)
第四、《汉书·酷吏传·赞》:“其廉者足以为仪表”。郅都“公廉,不发私书,问遗(礼物)无所受,请寄(委托)无所听”。拒绝拉关系走后门。武帝时,赵禹当御史、中大夫,“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不搞吃吃喝喝拉扯勾结。(《汉书·酷吏传·赵禹》)张汤当廷尉6年,御史大夫7年,职位仅次于丞相,死后家产除皇帝赏赐俸禄之外,一无所有。(《史记·酷吏列传·张汤》)死后“有棺无槨”,与当时流行的厚葬截然不同。尹赏在成帝时当长安令,从朝廷到地方腐败成风,他临死时告诫子弟:大丈夫当官,面对官场起落而不能正直应对,“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赃”。切勿患得患失而陷入贪腐。(《汉书·酷吏传·尹赏》)
根据汉代史实,“酷吏”的界定并没有客观科学的标准。如“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界定他为“酷吏”的依据是“刻轹宗室,侵辱功臣”(《汉书·酷吏传》序)。再如晁错,景帝还是太子时,被认为是太子的“智囊”,贾谊死后,他继续“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是个改革家,太子(景帝)很赞同他的意见。景帝即位,晁错提升为御史大夫,他将理论付诸实践,削诸侯之“支郡”,并“更令三十章”,引起“诸侯喧哗”,爆发“七国之乱。”景帝把他腰斩。(《汉书·晁错传》)他并没有“滥用刑罚”,他所针对的也不是人民群众。“酷吏”中确有滥用刑罚的,人民群众也被涉及,但酷吏所打击的“豪猾”及黑社会与“人民”应该有所区分。有的“酷吏”还打击侵害百姓的恶势力,如张汤,“排富商大贾,……锄豪强并兼之家”。因为这些人使“百姓不安其生,骚动。”他了解到封建政权的休养生息没有让百姓获得,原因是“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绝以罪”,痛下决心惩罚这些贪官污吏。(《汉书·张汤传》)严延年注意惩办“其豪桀侵小民者”。(《汉书·酷吏传·严延年》)酷吏,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应该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评价。但不管如何“具体分析”,都应注意一个最基本的历史本质:“酷吏”政治的本质是以皇帝为核心的人治。有史实为证。
汉武帝重视吏治,除了提拔并支持坚决维护皇权的酷吏之外,从公元前106年起,将全国分为13个大区,派刺史巡视检察,其内容有六个方面,主要重心是:打击“强宗豪右,严禁二千石不遵皇帝意志,侵渔百姓,引发天降灾异,背公向利,旁诏守利”。酷吏的行政必须贯彻皇帝的意志,并受皇帝的检察。武帝除设置十三部刺史外,还派遣“绣衣直指”,加强监察,其指导思想是民本主义,西汉严谨行政者以酷吏为代表,贯彻了民本主义思想,反之,从西汉的吏治也可发现民本主义与当代的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不同。也可以史实为证。
汉宣帝(前73—49年)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必须依靠良好的吏治才能达到,常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汉书·循吏传》序)赵广汉被当地长老称为”“汉兴以来治京兆者治莫及”,“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职。(各得其所)”却因公平执法得罪了贵戚大臣,诬告他“摧辱大臣,……逆节伤化,不道。”宣帝要杀他,“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愿代赵京兆死,使得牧养小民。”宣帝还是将他腰斩了。(《汉书·赵广汉传》)这一史实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民本主义的本质。
三、唐代的酷吏
唐代(618—907年)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夏王朝开始王位世袭,夏商西周时兄终弟及还是常态。秦汉嫡长子继承确立,成为封建社会专制帝制的核心,外戚(后族)、宦官、官僚集团的运作都围绕这一核心而开展,延续近2000年,清末还出现那拉氏(慈禧)的专权。唐代武则天掌权半个世纪(655年十月立为皇后,至705年十月,复国号为唐)上承“贞观之治”(627—649年)下启“开元盛世”(713—741年)是唐代繁荣的关键时期,武则天又是我国古代唯一的正统王朝的女皇帝,以皇权为中心的各政治势力的斗争极其激烈。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政治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特征。新旧《唐书》所载酷吏,大多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以《旧唐书》为例,共收酷吏18人,武则天时期占其中之十一。作为一个有相当见识与才干的专制君主,武则天遵循贞观年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主义治国理念,维持唐代国力的继续发展。作为异姓又是女性君主,她必须培植并使用酷吏为爪牙,清除挡道的李氏皇族及其亲信臣工。作为女性,她跳不出存在千余年的宗法制度,既不可能成为武氏家族的宗主,也否认不了李家媳妇这个名分。这些是我们考察武则天时期“酷吏”必须注意的客观存在。
第一、唐代酷吏政治由武则天一手策动。“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旧唐书·酷吏传》)684年之前,她与唐高宗并称“二圣”,依靠皇帝这个靠山,排除异己。683年夏历十二月(公历684年初)高宗“驾崩”。中宗李显即位55天即被废,睿宗即位当年被废,软禁。684年夏历九月,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司马光写道:“太后(武则天)自垂拱(武则天垂帘听政时的年号之一,685—688年)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害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赌徒来俊臣,以告密东平王李续为敲门砖,从一个“凶险不事生产”的无赖,不到两年就提拔为御史中丞(从五品上)。武则天特设“推事院”,专门侦查审理“制狱”(皇帝认定的案件),由来俊臣负责。胡人索元礼,顺应武则天奖励告密的意旨,“告发”了一些人,一下子被提拔为游击将军(从五品下),他审理一人能株连几十、几百。酷吏恣横,造成一派恐怖气氛,武则天以此震慑反对她的唐宗室及官僚。
第二、这些酷吏的“执法”有个基本“流程”:第一步,揣摩武则天意图,窥探形势,选定对象;第二步,罗织“罪名”,逮捕入狱;第三步,严刑逼供,锻炼成狱;最后,根据皇帝意向,决定“罪人”生死。整个过程有两个关键:一是告密,不只是一人举告,而是收买众多暗探及告密者,从多方面罗织“罪状”,造成“众口一词”的假象,对上欺瞒,对下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酷吏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手下都有长期豢养的流氓无赖群体,作为他们罗织诬陷的工具。二是刑讯逼供,使用花样繁多,骇人听闻的刑具,仅枷号就有十种,只要将这些刑具在“罪人”前面一摆,什么“罪状”都会屈打成招。来俊臣会同党羽,将以上流程“理论化”,写成一卷制造冤假错案的经典《告密罗织经》。睿智勇敢如狄仁杰也难过这一关。692年,身为地官(户部)尚书的他被诬“谋反”,没等动刑他就“招供”,承认“谋反是实”,使来俊臣等放松监押,趁机让儿子带出申诉状,武则天问他,你为什么要承认谋反?狄仁杰答道:我如果不承认,早就死在刑杖下了。(《旧唐书·狄仁杰传》)
第三、唐代酷吏,道德败坏,品质恶劣。他们的首要目标是“盗官”,就是盗窃一部分政权,下一步就利用手中的权去贪财、贪色,谋财(色)而害命。大到诬人“谋反”,小到鸡鸣狗盗,荒谬绝伦。王弘义当了御史,还经常白吃邻居老乡的瓜,老乡给少了,就带一帮手下,命令他们到瓜田“抓兔子”,将老乡的瓜田糟蹋得一片狼藉。上下级及同僚之间的关系,难以想象的卑劣,御史大夫魏元忠卧病在床,御史们都去探望,郭霸去迟了,怕大夫怪罪,向左右索取魏元忠的便尿给他品尝,尝过后“大喜”,对魏元忠说:如果大夫的粪甘甜,病就难治了;如今您的大便好苦,病很快就会痊愈的。魏元忠鄙视这种“恭敬”,将此事揭露了。(《旧唐书·酷吏传·郭霸》)
大致655年唐高宗李治死后到690年九月,“以唐为周,……上尊号曰圣神皇帝”。《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为了夺权和巩固地位,武则天策动了酷吏政治,一时“酷吏恣横”,酷吏的放肆,危及王朝的根本,武则天开始约束它的“度”,主要措施有二:杀掉索元礼、来俊臣“以慰人望”,将周兴流放岺南(在中途被仇家所杀),此其一。其次,遏制告密,揭露告密者的卑劣。692年,她下诏禁止屠宰及捕鱼 。左拾遗张德生了个儿子,杀了羊宴请同僚庆贺,同僚杜肃吃过后,抹抹嘴就到武则天驾前告密,第二天早朝,当着众臣,武则天对张德说:“闻卿生男,甚喜。……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杜肃恨不得地上裂个缝钻进去,文武大臣都向他吐口沫。(《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一》)七世纪末(大致692年后),武则天策动的酷吏政治逐渐降温。698年,她与宰相姚崇谈心,问道:近来处死周兴来俊臣之后,再也没听说有造反的了,难道以前杀掉的,有冤枉滥杀的吗?姚崇直言,从她掌权以来,酷吏横行,受害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冤假错案泛滥,动摇朝廷根本和社会安定。武则天赞扬他敢于说真话:“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旧唐书·姚崇传》)次年,武则天朝最后一个载入《酷吏传》的吉顼死。唐朝酷吏政治的高潮过去,开元(713—741年)中,唐玄宗清算武则天时的酷吏政治,先后处理23人,其中开元二年(714年),玄宗敕令:“涪州剌吏周利贞等十三人,皆天后时酷吏……宜放归草泽,终身勿齿。”(《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天宝年间(742—755年)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操纵政权,又培植酷吏作为工具。《旧唐书·酷吏传》赞:“王德将衰,政在奸臣。鹰犬搏击,纵之者人。”唐代酷吏政治是统治集团争斗激化的表现,封建统治腐朽的一种现象。
四、酷吏政治违背中华民族传统
中华民族国家萌芽之际,已产生初步的“以德治国,以刑辅德”理念,秦汉之后发展为“以法辅德”,但两千年来都是“以德治国”为主。酷吏及酷吏政治的出现,是古代历史中对“以德治国,以法辅德”传统的干扰和偏离。
第一、“酷吏”的出现与演变是一个历史过程,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它的认识也有个过程。中华民族历代王朝都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都由王朝主导撰修历史。“二十四史”中对酷吏的评价准确地说明了“酷吏”在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传统中是被否定的。
《史记》否定酷吏的“酷烈”,肯定其中“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汉书》基本承袭《史记》的观点,酷吏“虽酷,称其位矣。”《北史》同意《史记》《汉书》对汉代酷吏的评价,对以后各朝的酷吏前后一概否定,批判他们违背“天道”。《金史》是编列酷吏传的最后一部正史,仅收酷吏两名,批判他们“咸尚威虐,以为事功,而谗贼作焉。”破坏社会安定,毒化社会氛围。酷吏违背以德治国的传统,正史中不再为之立传,可视之为某种警戒。
第二、酷吏的行为违反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权观。早在中华国家初建之时,皋陶就提出“天工人其代之”,人的生存和活动是自然规律,“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尚书·大禹谟》)应尊重人的生存权。“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酷吏“残人肌肤,同诸木石,轻人性命,甚于刍狗”。(《北史·酷吏传·论曰》)违反了“天道”,即践踏了人的生存权。1991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人权状况》,说明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继承并科学地阐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权观。
第三、酷吏政治的本质是以封建专制皇帝为核心的人治。西汉刘安所作《淮南子》批判了专制帝制的局限,主张以法籍礼仪为“治国之准绳”,以“法籍礼仪”限制君主的“擅断”(《淮南子·主术训》),即将皇权关进法制的“笼子”。中华历代史家对酷吏的批判与《淮南子》的思想相辅相成。中华民族的人权观首先是承认并尊重人的生存权,对酷吏的批判也是对传统人权观的维护,彰显了“以德治国,以法辅德”的传统。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李耳.道德经[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3]姚治中.重评“淮南狱”[M].合肥:黄山书社,2015.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