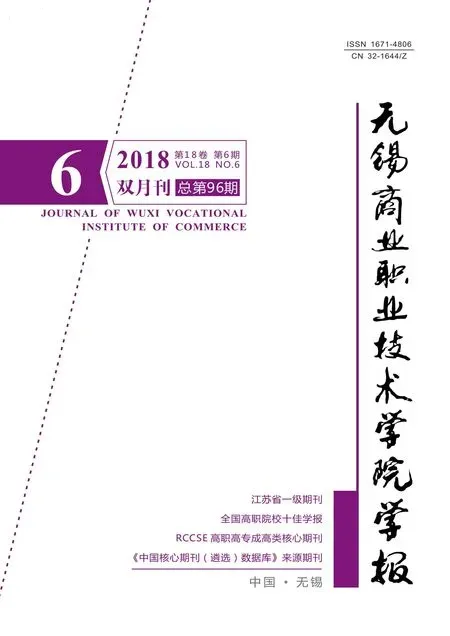认知生态批评视野下罗斯金的三种想象力
2018-03-07迟秋雅
操 磊,迟秋雅
(1.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1;2.金陵科技学院,南京 211169)
认知是一种心智加工处理过程,它使人的行为方式得以被理解。人文学科研究的认知转向是当代研究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虽然认知学与神经科学密不可分,然而它的诸多内容方法和研究课题却源于人文学科。认知学中的“blending”概念即源于经典修辞学中的“conceptual integration”。对文学的认知研究本质就是对文学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2004年,认知文学批评研究者Alan Richardson认为:“Perhaps the most accurate definition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then,would be the work of literary critics,and theorists vitally interested in cognitive science and neuroscience,and therefore with a good deal to say to one another,whatever their differences.”[1]由此可见,连接文学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重大桥梁就是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认知文学研究发展至今,分支众多,包括认知酷儿研究、认知后殖民研究、认知历史主义研究、认知叙事学研究、认知生态批评研究、认知后结构主义研究以及认知女性主义研究等。
Lisa Zunshine在《认知文化研究导论》中指出:“认知科学家每天都在跨越学科边界,把新的学术领域吸引进他们的轨道。”[2]运用多种认知理论与方法侧重研究文学艺术的文化及生态蕴涵,即认知生态批评(cognitive ecocriticism),尤具新意,值得关注。生态批评着重于文学艺术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而认知生态批评则在文学艺术对生态场景的文化沉思中,强调人的心智构建及再现。
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认为,想象是对事物的构思和简单的理解。罗斯金反对这一定义,认为其过于简单含糊,忽略了想象力的真正目的和实际意义。随后,罗斯金在其百科全书式的文艺佳作《现代画家》第二卷中引出了想象力的概念:“然而,这些美之源泉并不以一种纯粹的摹本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们在传递到那些艺术工作者头脑中时会得到不同的反映,并且被它们头脑中所呈现出来的印象修改或加工。这种修改和改变就是想象所做的工作。”这里反复出现的“头脑”“修改”“加工”等词语无不赋予想象力一种认知意味。根据其功能及运作方式的不同,罗斯金将想象力分为三类:联想性想象力、洞察性想象力以及沉思性想象力。
一、认知生态下的联想性想象力
认知科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就是“blending”(整合),也就是认知文学批评中的概念整合理论。概念整合作为一种经常发生的心智构建机制,选择性地将两种独立不同的图形框架知识或场景组合在一起,生成一种意义崭新的心智结果。马克·特纳曾经举了一个“复活的亚里士多德”的例子来解释概念整合理论。“如果现在亚里士多德还活着,他肯定会受到现代认知研究的影响而修改自己之前的作品。”[3]这样的话一经说出,便激活了两个场景:“现代认知研究”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个场景在认知整合的加工下生成一个崭新的故事:知识渊博而又不懈追求的亚里士多德还活着,他在最新文学研究的影响下,修改自己之前作品,为当代认知研究做出贡献。“现代认知研究”和“亚里士多德”作为两个毫无关联而又相互独立的场景通过概念整合理论变成了一个新的场景概念,并传达给读者一种崭新的知识或阅读体验。
而联想性想象力(imagination associative)通过联合不同的事物或概念以产生新的表现形式。罗斯金当时惊叹于人类的这种思维能力,并感慨道:人脑中这种认知原理至今未被精神学家们所发现。但现在看来,这种认知原理即为“概念整合理论”。在联想性想象力的运作下,总会出现两种概念或想法,他们各自独立开来是平淡无奇、苍白无力的,但一旦集合在一起就会唤起某种强烈的情感。罗斯金认为人类心智拥有的最伟大的能力就是联想性想象力,这种崭新的人脑认知机制引领人与自然万物达成有缺陷的和谐,而非完美结合的和谐。“联想”“结合”的审美认知机制暗合了“blending”(整合)这一概念内涵。罗斯金在《现代画家》中非常认同Fuseli的文学创作理念:“Second thoughts are admissible in painting and poetry only as dressers of the first conception;no great idea was ever formed in fragments.He alone can conceive and compose,who sees the whole at once before him.”[4]在这里,Fuseli所说的碎片整合即为概念整合的雏形,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就是因为他们对图景或概念的认知不是单一独立的,而是进行了完整有序的整合。罗斯金在“联想性想象力”一节中还反复列举了对一棵树的整合性认知及绘画创作。“由于树的所有部分独立开来都是不完美的,且这不完美又有无穷的源泉”,而在认知概念整合的加工下,各个部分都能对号入座且难以被取代,每个不完美的部分都跃然纸上,形成一个耀眼的整体——一棵生机勃勃的树。而不具备这种联想性想象力的画家则会使每一片树叶树枝都极尽完美,却发现每一处都很相似而显得虚假乏味,失于真实。原因就在于过分强调了单一场景概念的存在,而忽略了场景整合后的整体效果,无法生成令人满意舒服的新场景。因此,联想性想象力的欠缺本质上是概念整合能力的认知缺失。
认知生态批评强调艺术与环境互动中创作者心理认知的角色。伟大的作品通过这样一种认知整合的心理过程将各个部分不尽完善的自然环境再现为一个和谐一致的整体,这种认知活动在罗斯金看来是“催人奋进的,充满活力的和完整有序的意识活动”。Nancy Easterlin认为,传统的生态批评者过度迷恋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浪漫主义书写,强调了自然环境,忽略了人脑本身的认知机制对创作的影响[5]。而认知生态批评反对这种厚此薄彼的作为,认为作品由环境在创作者心智构建下整合生成。这种一味浪漫主义的创作生成有悖于创作者真实的认知机制,除了概念整合能力,人脑认知能力还包括环境协调、思想随机、信息归化、目标定位、问题解决、智能合成、社会偏好等,这些都会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留下痕迹。如果只注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颂扬,而忽略了人脑本身的认知加工角色,那文学的生成及批评因有失于真实或完整,所以是片面的。
除了忽略创作者真实的认知构建机制,传统的生态批评理论还倾向于作品中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认为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人类罪大恶极,难辞其咎,却忽略了人与自然作为整个地球环境的两个独立场景,互有损耗却又动态平衡,并最终生成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环境整体。罗斯金认为人类心智拥有的最伟大的能力就是联想性想象力,关联性想象力反对事物的孤立,强调事物的真实集合,而这个集合体唤起人更加热切的情感。对应到生态环境中,这种崭新的人脑认知机制引领人与自然万物达成整体和谐性,哪怕和谐中还包含着缺陷、错误、丑陋,而非一味强调美丽的、完美的结合与和谐。
二、认知生态下的洞察性想象力
罗斯金认为,每一位诗人和画家都被想象这种心智功能所操纵。譬如埃斯库罗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等等诗人和作家的作品都是他们内心“神之源”的展现,受到宗教信仰影响。罗斯金并未对“神之源”做出进一步解释,但坚信它永远存在于人的心中。得益于“神之源”的存在,那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也为读者开辟了一条通往他们内心世界的通道,引导读者深入他们内心世界,去发掘更多的信息。而洞察性想象力的功能就在于能够突破事物的外部特征,直击事物的本质和真相,深刻展现事物带来的情感力量和体验。心灵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便是情感的表征,创作主体和客体在情感的融合下实现身份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斯金所谓的“神之源”或许是人脑与生俱来的心智或认知能力。
因为幻想在功能上和洞察性想象力十分接近,所以罗斯金认为诗人约翰·弥尔顿也经常将二者混用。具体如诗行所示:
早熟的樱花草开了,又孤独地死去(想象)
丛生的百脉根,苍白的茉莉(无用表达)
那白色的石竹,有深黑色斑点的三色紫罗兰
(幻想)
这容光焕发的紫罗兰(想象)
那麋香玫瑰和形似鹿角的五叶地锦(粗俗的
幻想)
和那苍白无力的低垂着脑袋的报春花(想象)
和每一朵带着悲伤的花朵(想象与幻想混用)[5]
弥尔顿的这首诗想象与幻想并存,因此行文力度时而如钢铁般坚硬,时而又如瓷器般脆弱。基于此,罗斯金对洞察性想象力和幻想进行了区分。首先,幻想只关注外部世界,并能对其做出清晰、精彩而详细的描绘;而想象则探寻自然和内心,使两者均能通过图像或文本的形式被读者所感知。在这里,罗斯金举了两个例子来对比说明。“她的红唇,薄厚有致/和她白皙的脸肤相比/就好像刚被蜜蜂叮了一口。”这很形象地展示了红唇的红艳和生动,然而缺乏思想和情感,只停留在了红唇的外在形象上。“随着他闪电般的一拳击中她的双唇/两片樱唇顿时被血染红了/冷酷的心施予了打击/柔软的唇流血了”。柔软的樱唇和冷酷的心灵形成强烈的力量碰撞,带来一种直击内心的情感冲击力,这才是洞察性想象力的魅力所在。
其次,因为幻想总是着眼于外部世界的表面特征,因此它只是一种纯粹和简单的心智功能,无法庄重严肃,更无法发人深思。而想象则遥远、幽深、庄重、严肃,让人无法停留表面,只能深入其内,惹人深思。正如拜伦评价但丁的作品,没有哪部作品能够比得上但丁作品中的紧张、严肃、认真,因而也成就了但丁作品恢宏磅礴的气势。
最后,想象是平静而安宁的,而幻想则是躁动不安的。想象着眼于内心世界,自我平衡,并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洞察性眼光透视外部世界。而幻想则专注于外部世界以及外部世界的表面特征,游走不定,空虚多变,不能持久而全面地展现本质的内涵力量。正如罗斯金所说,幻想像一个圆形监狱里的松鼠,故步自封而又无知地快乐生活着。而想象则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他的终极家园是天堂,他拖着苦难庄重而又坚定决绝的步伐不懈前进,不断接近他的家园。
洞察性想象力生成的每个词都有一种现行通行意义之外的解释和表征。这一表征虽然晦涩难懂,但是如果对其进行稍加揣测并寻根溯源,就会发现精神意识的主导地位,进而就会茅塞顿开,如沐春风。洞察性想象的内在功效在于凭借直觉与凝视等方式,也就是一种真切可信的开启和揭示能力,而非一般的推理能力,透过事物的表层来把握其内在的“更具本质意义的真实性”。罗斯金生活于十九世纪,彼时正值英国浪漫主义的鼎盛发展时期,受浪漫主义诗学的影响,罗斯金较多地关注了人内在的情感心智力量对文学及艺术创作的影响。洞察性想象力就是情感认知机制的产物。在自然环境与浪漫主义诗学文本的互动中,罗斯金总结并提出了“pathetic fallacy”(情感误置)的人脑认知机制概念,认为其是浪漫主义作品最为突出的创作特征。
三、认知生态下的沉思性想象力
《现代画家》第二卷最后讨论了沉思性想象力[4]。这一想象力处理的对象无法用视觉感知,因为这些对象抑或是抽象的想法,抑或是记忆中的事物。沉思性想象力的运作机制也分为以下两种:展现事物的一部分以代指整个事物;用其他事物代替来展现原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沉思性想象力恰如暗喻的能力,其功能也类似于象征主义。
著名认知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在《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一书中提出了全新的哲学理论:体验哲学。体验哲学的认知基础包含三个方面:心智的体验性,思维的无意识性以及概念的隐喻性[3]。就概念的隐喻性而言,lakoff和Johnson认为构成人类思维模式的基础是隐喻结构。隐喻是身体、大脑、心智和经验的产物,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文艺创作领域。
概念隐喻的运行机制是把内容相对具体、结构相对清晰的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内容相对抽象、结构相对模糊的目标域之上,以期实现明确的认知体验,这是一种用源域的结构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的认知手段。基于认知参照点理论,目标域是认知主体想要理解的目标对象,而源域是认知主体选取的辅助对象,由辅助对象到目标对象的定位便实现了认知的隐喻性飞跃。概念隐喻作为一种跨域映射,是将两个事物并置,借助某类具体事物来表达并认知另一类抽象事物,本质上源于两种事物间存在着相似性和关联性。譬如:“The wind is a cat”一句中,“the wind”作为目标概念,是无形的,抽象的;而“a cat”作为源概念,生动形象,可感可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在于“风”和“猫”都是无声无息,来无踪去无影,并且都会发出声音:风的呜咽声和猫的鸣叫声。通过这样的认知构建,读者便能通过猫的形象进一步认知“风”的概念。
罗斯金举例说,羽翼丰满的公鸡雕塑已经被当作富商的标志性肖像,原因就在于公鸡这样一种源概念,桀骜不驯而又斗志昂扬,很好地象征了富商们一掷千金、财粗气傲的气场。沉思性想象力通过概念隐喻的象征性构建,在众多文艺作品中均有表现,最为典型的就是一系列动物形体的抽象或象征表达,如大英博物馆《埃及的狮子》、米开朗琪罗的《约拿的鱼》、佛罗伦萨的《公猪》、丁托列托的《金牛》等。这些作品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动物形象来隐喻创作者的某种主观意识,以实现对某种抽象概念或对象的无缝认知。
四、结语
罗斯金一生都执迷于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真实的探索中,并找到了自然之美投射于艺术之真实的媒介:人的想象认知能力。通过罗斯金对想象力三种形式的内涵阐释,不难发现他所谓的“imaginative faculty”(想象能力)就是现代认知学有关“cognitive faculty”的某些元初形式,如概念整合、概念隐喻能力。无论是联想性想象力,洞察性想象力,还是沉思性想象力,都是伟大的文艺创作者不可或缺的认知能力。在这些能力的构建下,自然之美才得以再现于艺术作品中,并为世人所理解、欣赏和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