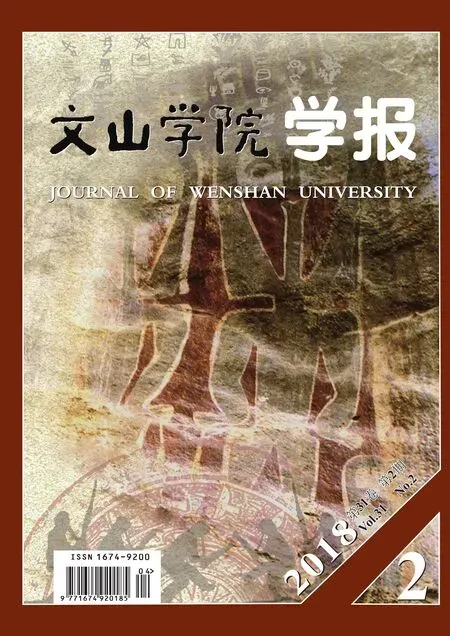略论西北行记中的西北开发思想
2018-03-07孙彦红
孙彦红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300384)
《西北行记丛萃》共有两辑,其中第二辑共辑录图书12种,这些作品的写作年代集中于民国初至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多为民国时期各级政府官员和科技、文化、教育各界知名人士,其著作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作品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20~40年代中国西北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经济、民族、宗教、历史、自然等方面的情况,并且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建议和构想。本文选择《西北行记丛萃》第二辑为分析文本,在细致深入地了解西北社会全貌、认识西北开发的重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全面考察所收录行记中的西北开发思想,能够从这些主张之中为西部大开发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做出更正确的时代选择。
一、西北地区之重要地位及开发西北之重要性
作为我国领土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极为重要的边疆地区,这些西北游记的作者均对西北地区之重要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纷纷呼吁开发西北、建设西北。
林竞认为西北地区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并呼吁全力经营西北:“国人须认明,西北之政治、经济地位,均具有牵动世界之价值,差可比拟于已往之巴耳干,而重要又过于现在之东三省。前途吉凶休咎,虽听命世界大势之所趋,而明辨机微,取决从违,完全由吾之自主。……根据上文之情势,则西北者乃全国之西北,亦全世界之西北。故国人应以全国之资力才力,从事于经营,并应在外交上尽力避免国际上之冲突;而于经济方面,则诚意予各国有善意投资之机会。”[1]1李烛尘则具体指出了新疆、西藏、蒙古等地区在我国地理位置、国防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性,并主张用政治力量解决边疆问题:“试披览中国地图,新疆……而地处神州大陆之脊,实为中国西北部之首,西藏、蒙古为共两披肩,青海、宁夏为其左右臂,尤其是河西走廊,更为内外息息相通之咽喉。总之新疆一隅,居高屋建瓴之势,得之足以屏卫中国,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历史俱载,斑斑可考。……但就地理环境以策将来之安全,吾人以为新疆之国防不在新疆之本身,而在新疆之侧翼与后路。……均须用政治力量以解决之。”[2]130-131高良佐在指出西北地区重要性的同时,还殷切呼吁西北地区的青年人积极投身西北建设:“西北为中国之一部分,而屏障西疆,地势险要,历史悠久,天产丰富。从全国而言,固应努力于西北之开发,从西北本身而言,尤应积极建设,直接以促进西北本身之繁荣,间接尽国民救国之责任。……西北青年应凛于责任之重大,充实人人之智识能力及品性,俾得为民族复兴西北建设预备之一员,以挽回国运,洗刷国耻,恢复我民族历史之光荣。”[3]31
西北行记的作者对于开发西北的紧迫性以及重要性也都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游记中多次阐述。杨钟健认为,西北地区的危机不亚于东北,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便是外蒙古已不属于我国领土。他还指出,从商业上看,西北地区大部分沦为了苏俄的殖民地,其余部分又被英国夺去,因此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化了”[4]171;从边防安全上来看,由内地至新疆,交通极为困难,而由新疆至英国、俄国的交通却十分便利。并且“据说一旦有事,莫斯科的兵,一星期内可到塔城,这是多么危险的事。……东北边事,固可痛心,但沿中国边界,无一处没有不发此等同样事件的可能”[4]172。别国努力建设边疆至此,我国岂能坐以待毙。自助者天助,因此他强烈呼吁应努力建设西北。马鹤天也在其西行游记的序言中表明了西北开发之必要性并积极呼吁开发建设西北:“吾国西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虽为古代文化发源之地,而近代落后。无论在国防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均应积极建设。……为救中国,救西北,则西北之研究与开发,实为必要。”[5]145
二、开发西北之主张
在亲身体验并详细描述西北地区的落后与贫困的同时,西行游记的作者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对于开发西北地区的建议和主张。总体来看,这些主张涉及农业、交通、教育、移民屯边等多个方面。本文选择了在所选游记中论述最多的交通和教育两方面的具体主张进行重点考察,以便真切感受游记作者的爱国热情,全面了解这些主张的可行性与建设性,从而对这些主张做出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交通
在所选择的西行游记中,很多作者主张发展交通为开发西北之第一要务。他们在阐述发展交通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的同时,也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主张。
顾执中认为,发展交通是解决西北地区问题的前提和保障:“从大体方面言之,假使陕西的水道和交通问题一日不解决,那么全省的实业,将永无发展的希望。所以陇海路线如能延长至西安,无形中就给陕西民众一种生命之路,西北的开发也加上了一种稳定的保障。”[6]14谢晓钟认为发展交通为开发新疆之第一要务:“今不急谋交通,缩短南北程途,以便商旅往来,出师转饷,一旦有事,南路八城,恐非我有,喀什噶尔尤必先亡,而新疆危矣。盖全国精华,悉在斯土,无喀什则无新疆也。”[7]119他指出,若将来不幸发生战事,本省需要调兵应敌,关内也需派兵前来支援,输送军队及弹药均需火速到达前线。若以新疆至内地此时的交通状况而言,路途遥远而交通阻滞,则只能坐以待毙。因此他主张“便利交通,为开发新省第一急务”[7]122。刘文海在阐述其对于甘肃发展之意见时,论述了发展交通对于运输粮食、改良吏治及发展商业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发展交通可以便利粮食运输,可以将粮食运往所需之地以补救其灾荒。另外,其他一切补救粮食缺失的举措均有赖于便利的交通。对于发展交通之举措,他指出:“欲谋交通事业发展,一方面在促成交通媒介,一方面在取消交通障碍。提倡邮电事业、汽车、火车、飞行等,为促成交通媒介;免蠲各项苛捐杂税,为取消交通障碍。”[8]43在论述交通对于改良吏治之作用时,他指出“故欲根本改良甘肃吏治,首在便利交通及消息之传达”[8]44。因此他竭力主张发展交通,并认为此种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此外,刘文海还指出“然欲求商业发展,首须便利交通”[8]99,并且提出了铲除商业运输原有的积弊陋规、开辟新的交通事业等详细举措。
对于在不同省市、不同地区发展交通的具体措施,所选西行游记的作者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和主张。林竞在其《蒙新甘宁考察记》中提出了在西北地区发展交通的具体举措,他主张因地制宜,发展不同的交通运输种类:“……开发西北首宜从交通入手,而交通之先后及种类,则宜因地而异。余意黄河上游各地域,与其建筑铁路,不如先疏浚黄河,盖轮船之利远胜于火车也。沿岸各市镇,辅以长途汽车,伸水陆衔接,则各地之脉络灵活矣。况河道既修,则水灾永免,其所得又岂可胜数乎!至于蒙古、新疆、青海,无舟楫之利,而有广大之平原,及宽长之驿道。以今日国家情势言,欲待火车完成,河清难俟。惟有创设长途汽车,而辅以飞机,此事简而易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惟在当局者诚意为之耳。”[1]92其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具体的发展举措对今天的西北大开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林竞的观点类似,杨钟健针对西北开发问题也主张以发展交通为急务:“西北的危急,既如上述,图补的方法也很多……但惟一的基本问题,不能不郑重略述的,就是交通问题。交通便利,一切都有办法,否则一切都是徒费。我们现在要办的……乃是民众化的交通。基本要图,当然是铁路。”[4]172-173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情形,他以为办理铁路交通困难重重,于是也提出了因地制宜的解决办法,即汽车交通与原来的运输方式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既便捷又省时的运输方式。李烛尘在《西北历程》中也建议开发西北之第一步工作为发展交通,并且提出了自己发展铁路和航空业的主张:“ 第一步工作完成,建设之事,经纬万端,而交通第一,则为普遍之意见,‘铁道一条通迪化’,固盼提早完成,眼前急务,希望西北空航,增加班次,使内地人士有企业之热心者,得以前去观光。”[2]137他认为,有了交通,则人方可到西北地区去,因此可以给西北地区带去大量优秀人才;有了交通,而后机器可运到西北去,从而使得西北地区拥有先进的生产工具。他指出,“交通之于国家,如人身之有脉络,通则行动自在,滞则麻木不灵”[2]138。其对于发展交通事业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针对在西北地区发展交通的具体举措,不同的作者针对不同的地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主张。从上述所列举的例子来看,这些西行者的个人主张都是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的。他们都从中国当时具体的国情出发,在充分考虑具体地区的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二)教育
以发展教育为开发西北之第一要务是这些游记作者讨论次数最多的另一个问题。这些游记作者同样是认识到了发展教育对于开发西北的重要意义,同时针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主张。
关于发展教育的重要性,这些游记之中有较多讨论。此处试举几例:马鹤天在《甘青藏边区考察记》中指出:“惟余以为生计、教育,宜兼筹并顾,一方生活安裕,一方知识增进,方为治本之法。望回教领袖与地方当局,注意及之!”[9]22谢晓钟在《新疆游记》中也指出发展教育为国家要务:“孔于曰:‘夫政也者,蒲芦也。’蒲芦者,蜾赢之谓也。……尤望就其教俗,大兴教育,进浑噩诸缠于似我之域,使免苛虐于乡约之下,则又仁者之用心,抑亦国家之要政也。”[7]245高良佐在《西北随轺记》中呼吁加强民族教育,以此复兴西北:“教育目的在于养成生活的能力,要充分发展文化,必使文化不离生活。现在中国之教育,应趋重民族教育,以求复兴。……青年学生与教授青年学生者,应注意关于德智体方面之努力。甘肃为西北中心,地位重要,应以西北作复兴民族之基础。”[3]47
在充分认识到发展教育的重要性之后,针对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教育类型,这些游记作者也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侯鸿鉴在《西北漫游记》中阐述了发展师范教育的注意事项以及发展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具体举措。他指出,要注重师范教育,从而造就大量人才,并教育其以服务外县及贫困山区为志向;同时要注重培养小学教员的研究能力,这样能使得受教儿童学到课本以外的基本常识,而不至于成为死读书的书呆子。同时,他指出师范教育所用之教材应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尤应选择适当之教材以应用之为要;所以乡土教材更为小学应用必需之物。故师范教育,似应令师范生先采查本邑风俗、乡土产物、地理历史、民族宗教种种不同者,编为乡土教材,以为小学之应用。”[5]106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他主张要重视学生到工厂进行实习,这样才能体现职业学校设置的本意,才能够锻炼学生的操作能力。关于发展社会教育,侯鸿鉴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使民众识若干字,为最低限度之社会应用”[5]57。二是“使民众知中国今日所处之地位,及国难国耻之相当认识”[5]57。此外,他还具体针对甘肃省的教育发展问题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教育经费问题应及时解决,否则迁延拖欠,教育则始终停滞不前。关于教育设备问题,他也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在能制造简单仪器的教员的教授下,自己制造各种应用仪器;二是请一名掌握生物学和地质学的教员教授学生采集标本、认识矿产,此举既能节省购置机器的教育经费,同时也能教授学生感知本省的物产丰饶。马鹤天在《青海考察记》中就甘肃省的教育发展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余以为消弭之法,不在兵力而在教育。故余极力劝回教人多入学校,并劝将清真学校一律改名,招收汉生,并入汉人学校,以期根本上消除意见,融合感情,统一思想,泯灭界限。……总宜不分民族界限,期达各民族一切平等之目的。”[5]174其字里行间流露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但其具体主张似乎并不是最适宜的,隐约有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色彩。在《甘青藏边区考察记》中,马鹤天也就发展教育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第一,他认为西北地区的小学校应以同校为宜,这样可以统一语言、联络感情、更改习惯,从而消除民族隔阂。同时,他又极为反对专编蒙、藏、回文教科书,他认为这样会增加儿童学习困难,引起民族情感疏远。此外,他还提出了带有教育与宗教分离色彩的主张:“故余在甘教厅任内时,提倡回民教育,但主张教育与宗教分离,学校不必以清真为名,回、汉子弟一律同收,无宗教民族之别,至宗教另有寺院,可于清真寺中举行也。”[9]198他的这一主张尤其具有进步性,其对于宗教信仰的尊重态度也是值得称赞的。刘文海在《西行见闻记》中提倡在蒙古施行教育,并且就如何发展教育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教育之道,贵在基础。因此主张“中央须及早选派专门教育人材,就蒙古境内实地提倡小学、中学教育,先由蒙古儿童做起工夫”[8]129。谢晓钟在《新疆游记》中也提出了发展新疆教育之建议:“今宜权由国库岁拨款十万元,以充新省教育经费,普设汉语学校,多方奖诱缠生(于阿訇乡约子弟,尤宜多令入学),利用宗教信仰,特订教科专书……或可望其永作藩篱。”[3]346-347
就以上发展教育的建议及主张来看,这些游记作者均认为应在西北地区大力发展教育,既要发展师范教育,也要发展民族教育,还要发展社会教育等不同的教育类型。同时,他们也都注重对于少数民族的教育,他们中有的人主张在少数民族地区专编适合其学习的“乡土教材”,有的人则主张将各民族学生置于同一学校以方便其相互同化。无论其主张是否切实可行,他们都在表达自己理想的教育发展方式,试图让汉族与与其他少数民族消泯隔阂、和睦相处,都希望能达成各民族大团结的局面。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游记中所阐述的西北开发的举措还有很多。比如刘文海提出了在新疆实行殖民实边政策的建议,谢晓钟则提出了对军人实行退伍与屯田(军屯)的主张。只因上述两种主张和建议不是本文介绍的重点,故此处不再详述。
三、总结与评价
从《西北行记丛萃》第二辑所辑录的这些西行游记来看,这些奔赴西北地区的人,在民族危机的压力下,在民族使命感的召唤下,在实地考察西北地区社会面貌的同时,对西北地区社会的黑暗给予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对民众生活的水深火热也表达了自己的同情和悲愤。通过他们的描述,我们能够真实且全面地审视西北地区的全貌,能够将他们开发建设西北的主张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下予以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也能够从他们的建议和主张里寻求新的时代背景下西部大开发的正确政策选择。此外,他们的民族责任感以及积极探索祖国边疆建设的民族意识和使命感,对于今天的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是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由于阶级以及时代的局限性这些游记作者的建议和主张也并非是完全正确的。比如,刘文海在《西行见闻记》中认为蒙古人民自动努力之方向,即提倡民族主义以对抗帝国主义,提倡民权主义以对付王公贵族及宗教势力、提倡民生主义即改换游牧生活。其对于提倡民生主义的建议不免有些不合时宜,他认为蒙古民族“惟有提倡民生主义、增加土地产力、发展工商业、规定财产之均机,可以救济厄劫。一俟人民有固定住所,方可言‘文化’二字。”[8]126这就表明他没有做到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没有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认识西北问题,而是生搬硬套了汉族的发展模式。此外,《新疆游记》的作者谢彬也在其游记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了其认识的局限性。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民国官员,历史的局限、阶级的烙印,决定了他必然会在一些重大的政治观点上存在错误。在他的游记中,他将起而同反动统治阶级作反抗斗争的少数民族,称之为“蒙匪”“回寇”等。他虽然也肯定各民族的长处,但同时又将其存在的一些短处上升到了不应有的高度,如将西北地区不好的卫生习惯,归根于“种性卑劣”;还把妇女缠足,说成是“等于禽兽”;甚至还认定吐鲁番缠民“刁顽,好犯上作乱”;哈萨克布鲁特诸部游牧人“性愚而多诈,俗不可采”;蒙民“悾而愚,寡识鲜智,蠢然一物”等等。
由是观之,对于这些西北行记中所阐述的种种观点,我们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以全面了解时代背景及作者本人的立场和态度为前提,用公正审慎的眼光全面进行考察,用明辨是非的理性从中进行借鉴和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求经验,才能在创造崭新历史的道路上,在持续不断地上下求索中,为祖国的未来开辟更辉煌灿烂的天地。
[1] 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2] 李烛尘.西北历程[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3] 高良佐.西北随轺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4] 杨钟健.西北的剖面[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5] 侯鸿鉴,马鹤天.西北漫游记·青海考察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6] 顾执中.西行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7] 谢晓钟.新疆游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8] 刘文海.西行见闻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9]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