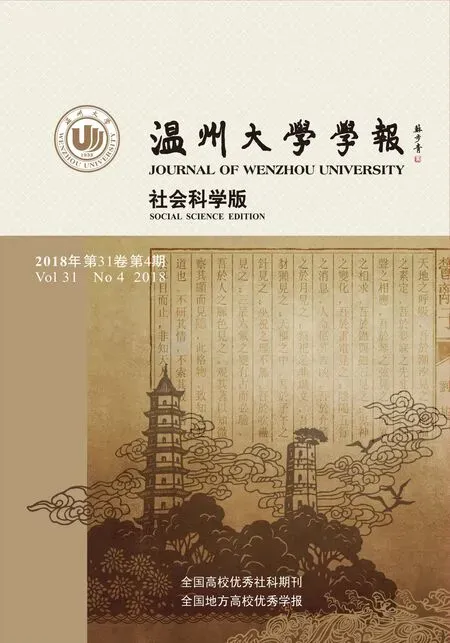一次华丽的转身
—— 反东方主义话语下的《长城》
2018-03-05蔡贻象
蔡贻象,余 音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一、“东方主义”恶梦缠身的张艺谋
在“张艺谋电影”批评史中,尤其从上世纪 90年代到本世纪初期,贯穿始终的批评主题之一就是“后殖民”或“东方主义”批评。当90年代前后张艺谋的《红高粱》《活着》和《菊豆》等在国际上先后获大奖,其独特的民俗展示方式及其创造的获奖神话,激发了文化、文学批评工作者深入探究其缘由的浓厚兴趣——戴锦华就指出,在张艺谋的电影作品中,中国历史、文化均成为西方文化视域中“一只纤毫毕现、钉死的蝴蝶”,并为中国电影提供了非常典型的后殖民文化的批评范本。批评家王干认为“这些电影投西方观众所好,尤其是适应了目前在西方理论界颇为风行的所谓‘东方主义’的虚幻建构,从而为一向以‘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论’为基点的西方学术理论界制造出有着或然性的‘他者’形象。”[1]张颐武在《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中首次拆解了张艺谋电影的后殖民性:在他的电影中,中国被当做一个特殊的代码,提供着“他性”的消费,让“第一世界”的人们看着这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张艺谋电影的“隐含读者”不是中国大陆的观众而是西方人——这一现象正表明了中国的第三世界处境和在全球化秩序中的边缘位置[2]。
事实上,后殖民理论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有着一体化的密切联系,本质上就是西方中心论,“东方几乎是欧洲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代表了罗曼史、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是欧洲最深奥、最常规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后殖民”简言之就是“文化殖民”,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文化侵略,它以一种友好的、温情脉脉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方法,使“落后”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的快感抚慰下俯首就范。
在“张艺谋电影”被后殖民或东方主义电影批评无情拆解剖析的同时,其批评本身也遭到批评界的质疑与反对,这也包括了张艺谋本人。他对自己被称作“后殖民”有无辜的自嘲和无奈的辩解:“我至少无意去拍所谓的丑陋”,“我坚持我的电影是要让外国人为中国喝彩”,迎合西方的说法“是发展中国家的心态”,“如果我们的国家更加开放,我们有更高的文化修养,我们有更强的民族自信心,我们有更加繁荣昌盛的局面……大家还会不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评价艺术作品应该用文艺批评的方式,一部电影就是一部电影,绝对做不到祸国殃民的程度”[3];“我们不可能先从理论上设定……作为创作者,我越来越重视的是情感(理论可能过时或错误)”[4]。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张艺谋遭遇后殖民主义或东方主义批评,著名电影史家丁亚平认为有两方面的语境原因,一是“张艺谋电影”超越了批评的历史性短视,引发了后殖民的反民族性和反艺术规律的围观讨伐,他实际上守住了自己的自尊,却遭到了极大的误解;二是和 20世纪最后十年这个阶段前后及其中的中国电影节文化的繁荣和开放带来外来电影资本的出现有关,一方面张艺谋之所以获得西方电影节的认同,确实和题材上的原始、落后、边缘有关,另一方面,从更宽容的心态看,第五代和“张艺谋电影”走向世界,是在政治性的接受背景下的艺术性的接纳,“不能过于在乎张艺谋们占了什么媚外的便宜,很多时候是历史借助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政治兴趣,而成就了张艺谋电影”[5]。
确实,正如历史与现实所明证的那样,西方对于东方的理解是存有偏颇的,在西方人眼中,“西方是主体,东方是客体。西方关于东方的学问,是西方这个主体企图征服东方这个客体的产物。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不管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文艺作品中,都严重扭曲了其描述的对象。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了,被丑化了,被弱化了,被女性化了,被异国情调化了。”[6]而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所获得的欢迎与荣耀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些华人导演对西方主流意识的准确把握。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东方导演对东方世界他者与异化形象的塑造,不仅获得了来自国际上的肯定声音,也成为了国内票房的保证,进而成为中国电影市场资本运作的来源与保障,使得中国当代电影无法摆脱并将长期困陷于东方主义的窘迫语境中。
但电影批评的历史语境不再,“东方主义”恶梦缠身的张艺谋的自我辩解也无能为力,仍有巨大创造力的张艺谋只能通过新作品来回复历史的疑问,《长城》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中诞生的。对于屡获国际大奖且对于电影市场动态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张艺谋而言,想要让《长城》在新的电影趋势面前抢占市场,就不得不摒弃旧有的传统电影观念,自觉适应新生电影的创作环境。然而,以象征性军事建筑长城为名来表现主题,若要去除厚重感和神圣感并非易事,于是,张艺谋另辟蹊径,选取大牌明星、实力演员与当代中国最热的“小鲜肉”进行结合,一方面勾起普通观众的观影期待,另一方面也抢占了粉丝化、低龄化、青年化、女性化受众的市场;聘请新西兰著名特效制作公司维塔工作室制作逼真与流畅的特效,加以漫画式镜头的穿插,以满足日趋视觉化、平面化的观影习惯;除此之外,他更是找准了中外合作、文化输出、反东方主义等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都不乏热度的话题,以中国元素为主要支撑点,怀着借助西方先进的电影技术开创中国电影票房新纪元的勃勃野心,打造中外合作的商业性大片,其在技术手段、运作模式、展演方式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创新与突破,尤其在祛除“东方主义”梦魇方面。《长城》的出现无疑是包括中国导演在内的东方导演对东方主义话语进行的质疑与批判,它是一次华丽的转身。
二、以东方元素为支撑的“华丽转身”
根据弗兰兹·弗农的观点,“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中,‘殖民者创造历史,他的生活是史诗,是伟大的航程’,而和他对立的‘被热病所折磨、被祖先的传统所困惑的迟钝的生物为殖民者重商主义的创新动力构成了一幅有机的背景。’”①参见:陈犀禾,吴小丽.影视批评:理论和实践[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419。弗农虽然未正面提及“东方主义话语”的概念,却描绘了某些西方电影乃至中国当代电影的特征: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世界是先进的、文明的、史诗级的,值得赞誉与令人向往的,而东方世界是受折磨的、困惑的、愚笨迟钝的,只能成为西方世界的背景与垫脚石。在当代电影史上,东方世界里那苦难的景观、压抑的传统总被放大与凸显,而积极正面的元素却只能成为好莱坞大片的点缀。然而,《长城》却打破了这样的表现格局,将宏大的而非狭隘的,唯美的而非丑陋的,开放的而非闭塞的,悲壮的而非苦难的中国元素从幕后搬向了台前,使其成为该部影片的主要支撑点,向世界展示了不一样的东方大国。
(一)长城形象的唯美和象征
“长城是世界伟大的奇迹……”,《长城》开篇即向世人展示了与天齐高,与地同阔,极具中国意味的长城,以上帝视角从高处俯瞰长城全貌,奠定了影片恢宏的气势。除此之外,影片在描绘军队抗击饕餮时,多次采用大仰角、大俯拍,快速拉近镜头以及俯冲式的镜头来拍摄长城,一方面凸显了战局的激烈,从侧面也映衬了出长城的宏伟与高大,此时,长城已不仅仅是作为抵抗饕餮屠城的坚强的壁垒,更成为了众将士获得勇气与力量的精神支柱。当由张涵予饰演的殿帅被狡猾的饕餮袭击身亡之后,上万名将士身着白色素衣在长城上点燃无数的孔明灯,飞向远方的长长的犹如白色丝带般的孔明灯将混沌的苍穹映照得清晰无比,也让无垠的长城尽览无余。长城作为中国所独有的建筑,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的巨型标志,而影片更是通过多处的场景与气氛的渲染使长城散发出独属于东方的气质与韵味。
所以说,影片最大成绩就是“以宏大语调讲述了关于长城的古老传说”,把“长城”精神化了,从而展现了“他者”眼中的中国英雄——“终于轮到中国英雄拯救世界了”[7]。我们有无数的电影出现过长城和长城英雄,但《长城》确实是第一次将“长城”以中国英雄的象征性主角,展现在西方主流电影观众面前,使我们对片名的理解,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作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和影响最深远的文化遗产、文明见证类型的长城(至今存留 21 196.18公里),是和战国时期残酷的兼并战争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春秋时期的 170个诸侯国,最后只剩下7个,战争促使中原的农业诸侯国将封闭的城墙变成长长的高大的墙体以抵御侵略,使长城成为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和体系。但长城“不是中华大地上一道道自然的、物理的、僵死的、割裂的、逐渐消失的人工堆砌物,而是一条条连贯的、前后相续的、始终涌动的、奔腾的、鲜活的、与历史交融的、蕴含文化意义的伟大遗存”[8]。这个伟大遗存,越过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被张艺谋想象成中西文化的碰撞点,成为影片中真正的东方元素的亮点。
(二)民族符号的去神秘化
军队中五颜六色的战袍曾被视为影片的一大败笔,眼花缭乱但井然有序的场景甚至被不少人诟病为以为在看奥运会宣传片。然而,换个角度也可以看成是张艺谋的“勃勃野心”,他是在向远古的中国传统文化取经问道,试图借此揭开中国民族符号的神秘面纱。“对西方来说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神秘,那样不可理解了。甚至于一听到中国这个词,马上想到的就是远古仪式,极富异国情调的茶还有迷信。”[9]在张艺谋过去所导演的多部经典影片中,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总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京剧、皮影、放鞭炮、出殡、挂灯笼都被精心的调用为‘美’的神秘而诡异的文化寓言。”[10]这是一种刻意渲染的美与神秘,也正是这样的神秘感使得以“他者”形象存在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中国影片得以在西方世界中拥有立足之地。《长城》也向西方观众展示了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特色服饰,主要表现为用五种动物(虎、鹰、鹿、熊、鹤)及五种颜色(金、红、紫、黑、蓝)加以区分的五支无影军的战袍,这些动物与相应的颜色对应,也与相应的兵种勾连:金色的虎代表负有军队工程保障职责的工程兵,金色与虎的肤色相近,也与金属的颜色一致,让人倍感凶猛与凌厉;红色的鹰是善于射击的弓弩兵,他们需要的是如同鹰一般深邃的眼光与鹰的速度;紫色的鹿代表持盾的步兵,他们有着鹿一般的安舒与敏捷;黑色的熊是近战部队的标志,是充满力量的代表,与饕餮直面相击;蓝色的鹤是飞索兵的化身,她们与天相融合,化作轻盈的一缕风烟。影片中所展示的动物、颜色和兵种的灵感源于极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功夫“五禽戏”,它汲取了被誉为中国传统水墨画中的“墨分五色”的作画技巧。派兵布阵也彰显了中国传统兵法的智慧,同样是融合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长城》中的无影军和阵法摆脱了《功夫熊猫》中“禅”和“气”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感。
正如张艺谋自己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这种中国传统对中国人来说,是常识性的东西,把它用进去,美国人就会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他们没有接触过,觉得很特别”[11]。这一次,传统的东方文化不再被遮上一层又一层厚重的面纱,而是以知识性的表达方式呈现于西方世界。
(三)东方价值观的呈现
也许是张艺谋急切于在为数不多的机遇中大展身手,恨不得将有关东方的一切都倾泻而出,影片中的意象显得过于繁杂。各种杂乱的意象相互拼接,所有的暗示都点到为止,似乎值得深思的点都处于一个平行的状态,导演想说的很多,最终的结果却变成了什么也没说,这的确是影片的一大弊病。然而,与过往张艺谋导演的影片中所展示的一种鲜明的强调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同,《长城》向人们展示的是与西方崇尚个人价值观相对立的东方集体主义价值观。影片从多处细节向西方观众推出集体主义观念。长城,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影片中它却更多地充当了依托无影军与饕餮进行殊死搏斗的战场,成为表现军队骁勇善战、英勇无畏的大背景。长城的屹立不倒不仅仅是因为建筑方面的坚定牢固,更得益于常年驻守边疆的无影军队的守护。在面对来势汹汹的饕餮的凶猛进犯时,无影军队表现得毫无畏惧并且井然有序,这不仅表现在由林梅领导的女子鹤军即使知道生途渺茫也义无反顾地跳下长城与饕餮搏击的一幕,也表现于在这样庞杂躁动的打斗场面中,每一支队伍都能自觉听从主帅的指挥,有序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然而这样的大义凛然并不是中国人的天性,影片借助由鹿晗出演的小兵的胆小懦弱向观众展示了人类惧怕的本性,在危难面前,没有人天生就是强大的,但是为了保全家园、保全集体,就需要大无畏的精神。影片在作战的大场面中奠定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框架,在林梅与威廉的对话中体现了两者对军人的不同理解,点出了以保家卫国为主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以个人利益为主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正面交锋,更在影片的最后,让胆小懦弱的小兵与智谋无双的军师纷纷为保全最后胜利的机会而舍身取义,集体价值观念的传输顺理成章地达到了高潮。集体主义观念的反复强调与突出,正凸显了张艺谋传输中国文化与主流价值观念的意图。
同样的,正是影片重中之重的“饕餮”设计,直接导致了其奇幻大片的性质和中国符号中隐喻价值观念的输出。从神话或艺术看,1981年李泽厚的名著《美的历程》重点分析其形象的文化特征:虽然是艺术,但有浓郁的宗教巫术性,是那个时代标准的符号,代表了战争、屠杀,呈现了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感,既是恐怖的象征,又是保护神,有理想性和童年气派的美丽。王小盾教授认为李泽厚对“饕餮”明显是理想化了,“饕餮”只是上古智慧的符号。他在《经典之前的中国智慧》的“艺术”单元中专门谈到了“饕餮”的符号特征:“饕餮”就符号艺术的特点看,本来是贪吃的著名的想象的兽类动物(幻想动物的某种集合体),形象常见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面,最奇怪的是没有下颌和身体,以突出其“饕餮”的不同处(无身体和虎食兽),于五千年前产生,母型主要是牛和老虎,有时是图腾,其本质是兽面纹。从智慧角度看,“吃人特征”只是表面的,其内涵在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是“超凡能力的神兽”——借助吃人(兽神)仪式性地表达生命的更新,是人、兽互相转换的神话和艺术[12]。现在出现在影片中的“饕餮”,是西方人乐闻所见的像大白鲨一样的怪兽形象,对应着我们关于“饕餮”的最通俗的理解:抽象的狂野动物,不可控的邪恶的、恐怖的、黑暗的、贪婪的隐喻。剔除了吉祥、保护神、神威乃至生命等意义,只留下贪婪意义,是符合电影作为大众娱乐文化性质的,也方便简约性的影像传播。其在影片中的存在意义,一方面激发了人们对野蛮的斗志,通过信任和团结战胜非理性、非文明的唯利是图,另一方面是在数字技术和特效手段中,给观众提供实体和视觉化的娱乐巨兽形象。
三、反东方主义表达的种种尝试
从故事的设计来看,《长城》是好莱坞故事的中国版,特别容易进入“东方主义”的批评视野。来自欧洲的雇佣军加林与托瓦尔来到东方,意欲盗取中国人的黑火药,却意外发现长城竟然是为了抵御怪兽饕餮所建,由神秘的精锐部队无影禁军常年镇守,在多次抵御饕餮的惨烈的战斗中,他们为中国军人的勇敢、互信、牺牲精神感召,决定留下来为人类而战,最终凭借其独特的技艺帮助中国人战胜了饕餮。但张艺谋“不愿重蹈东方主义的窠臼”,站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对话”的角度,“聚焦于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新东方视觉元素”,通过三个欧洲人的视角“讲述了东方的传奇故事”,反对东方主义电影“占据着居高临下的启蒙位置”,“接受了勇敢、无私、守纪、创造等中国式精神美德的再教育”[13]。这种“再教育”在影片中表现得非常清晰。
(一)反东方主义的女性主义
赛义德曾指出:“在讨论东方之时,东方是完全缺席的,人们感到出席的只是东方主义者和他的言论;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东方主义者的出席恰恰是由东方的实际缺席造成的。”[14]缺席与沉默使得西方对东方进行了随意的想象,按照自身的需求建构了属于他们的东方世界。这种缺席与沉默同样适用于东方女性,而她们除了承受来自东西方差异的“他者”身份,还要忍受因性别歧视而带来的普遍“失语”。在张艺谋导演的影视作品中,女性主义的表现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张艺谋主要将视角放在了女性为争得自由与解放(尤其在性方面)而与中国传统中泯灭人性的旧约陈俗进行的顽强抵抗,而在这些抵抗之前,女性的地位与身份往往是被预设的:或是大户人家中饱受苦难的小妾或是被迫失去自由而成为交易的筹码。在《长城》中,张艺谋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存在由一群女子组成的鹤军,为什么最后的主帅是交给了唯一一位女将领而非其他男将领,然而,没有解释就是最好的解释。《长城》中的女性是无影军中冲锋陷阵的前驱者,她们与军队中的其他男性士兵一样是军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林梅虽是女性,却是军中唯一一个和军师一样可以用异地语言与外邦人进行流利交流的智者,是在面对牺牲与背叛之后能沉着反思、冷静应对的强者,有着与其他男性将领一样的理性与力量,甚至有着超越他们的智慧与坚韧,她成为主帅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说张艺谋以往的影片以先抑后扬的手法赞扬东方女性冲破束缚的胆量与勇气来表现所谓的女权主义,那么《长城》则以平淡无奇、水到渠成的方式展示了东方女性与生俱来的意念与力量,这是对女性主义的反观,也是对东方主义的诘难。
(二)东西文化的平等凝视
有学者认为“《长城》比过往呈现出更为浓烈的东方对西方‘东方主义’的反凝视性,但这种‘反凝视’仍然是建构在西方‘东方主义’的框架之内”[15]。的确,影片中堆砌了不少东方元素,却给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混乱感,想要极力表现的是东方集体主义价值观,却将最后拯救东方的大任交给了西方的人与物,难怪它被看作“仍然是东西对抗中一种东方民族自我确证的审美幻象”[15]。然而,我们无法否认其主流是一次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提升与尝试。整部影片大体呈现出以东方文化为载体,以西方技术为支撑,将东方价值观融入好莱坞式的叙事结构与英雄主义情结的中西合璧格局,用美国大片的视觉技术塑造了中国古籍《山海经》中的饕餮形象,营造了形象逼真而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而在细微之处,更有西方布料与中国古代针法完美交织的精致戏服,既有中国古典乐曲中的鼓声、秦腔,也有充满西域风情的电子琴声。影片中灾难最终因为西方人与磁石而得以消解,但仍是东西方携手共战、相互合作的成果。影片中的三位同行却志向迥异的外来客是西方人所熟知与推崇的个性化与个人主义的表现,与东方军队的整齐划一与为国捐躯的集体主义相互对立,影片在表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时,并没有向天平的任何一边倾斜,片中的领导者对三位外来客总保持着包容的态度,男女主人公对于军队意义的探讨也没有压倒性的倾向,而是一次平等的对话,显示着东西文化的平等凝视的尝试。在这部影片中,没有东方导演献媚般的对东方主义的极端的认同与积极主动的附和,也没有极端的反抗所导致的极端民族主义、本土中心主义,甚至是模仿东方主义营造出来的东方的“西方主义”。这种平等的对话与凝视方式为重塑东方形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东西文化冲突的消融
东方将领林梅与西方外来客威廉关系的变化是影片发展过程中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作为一名在军队中长大的东方女性,林梅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括影片中强烈凸显的为国捐躯、勇于牺牲的爱国情怀,以及在长年累月的军队训练中所习得的服从与集体意识,但同时,林梅又有着不同寻常的身份与思维方式。她从小就接触学习异域文化,对于新异的事物带有包容与探寻的态度,饱含着女性独有的温情与柔韧;而威廉却无论在外貌、言行、思维方式等各方面都渗透着西方人的气质。林梅与威廉两人从对立冲突到携手共战,从相互敌视到相互珍视的关系的微妙变化,已不仅仅是人性的使然,也是他们背后的两个国度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念的缩影。
萨义德研究的东方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控制不仅仅满足于政治上的操控,还在不断进行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导演张艺谋对林梅与威廉这条线索的演绎在警惕文化霸权方面,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影片从一开始就在不断渲染两者之间的矛盾和碰撞,金发碧眼,奇装异服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奇特的语言造成的交流障碍,不行跪拜之礼而被误解成对主将不敬的文化冲突,都在表达着东西方文化的疏离与排斥,但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影片最终让两人冲破了隔阂和障碍,逐渐走向联合,甚至产生了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这不仅是两人内心分歧的消解,更象征着东西文化冲突的消融。这样的消融并不建立在权力的压制上,也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入侵与代替,而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让西方男性得到东方女性的爱慕和身体,没有庸俗的滚床单,而是“战士的惺惺相惜,英雄的心心相印”。值得令人回味的是,尽管林梅在大权在握后获得了留住威廉、占有他甚至改变他的权力,然而她并未阻拦威廉的离去,这不仅是林梅的豁达,也是导演张艺谋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包容和豁达。
四、结 语
《长城》在以中外合作的科幻商业大片为噱头,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元素为定位的同时,也在试图冲破和摒弃萨义德所揭示的,直到今天仍然阻碍着东西方平等交往,久久无法抹去的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智慧与愚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屏障。它是张艺谋致敬《功夫熊猫》、《变形金刚》等本土文化与全球化的混血儿,孵化出中国元素与国际化元素糅合的新型文化基因的温暖胚胎。“有时候高票房的商业电影业具有优质的文化基因,历届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就是一例。”[16]虽然《长城》在电影艺术表现方面还远未达到获得奥斯卡奖项的标准,但其文化正确性的有意识的弥补,是令人敬佩的,这不仅是一次将商业电影打造成传播本土优质文化的重要媒介的大胆尝试,也是东方导演对东方主义进行批判与质疑的尝试,更是张艺谋运用融合思维平衡电影艺术、网络资本与本土文化的一次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