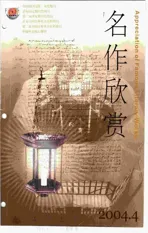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忆余光中先生
2018-03-05美国张凤
美国 | 张凤
我在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及台湾师大读书时就很爱读诗。我们读罗曼·罗兰、莫泊桑、契诃夫、福楼拜、加缪、吉本、房龙、杜翁、托翁,也读司马迁、刘勰、金圣叹、曹雪芹、叶嘉莹、洛夫、郑愁予、周梦蝶、叶珊、杨牧、翱翱、张错、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当然也捧读余光中的诗文。余先生早年的《天国的夜市》《莲的联想》我甚至还有手抄本。我尤其喜欢他的散文《幽默的境界》《听听那冷雨》等。欣赏一个作家,重要的是用心读他文贯中西的作品。后来,他多篇诗文被选入台、港及大陆教科书,作品被译为英、韩、日、德、法文等,影响了几代人。
我的哀乐中年多艰辛,经过三十年多年哈佛大学的历练,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益发体会到,少年爱做的事,哪一样不是梦的延长?于是总有些意犹未尽。
2008年11月,我回台北剑潭参与世界华文大会,趁便,应邀到几个学校演讲。应允23—24日去高雄中山大学演讲,主要为见南台诸友,最大的吸引力还是余先生——余先生曾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时任院长的黄心雅教授和曾在哈佛开过会的张锦忠教授,悉心安排了一段不短的时间,让我与诗人欢叙。

张凤女士2008深秋高雄中山大学演讲之后,与余光中先生欢叙
余先生听我脉络分明地梳理他的美国留学讲学历程,讶然并愉悦。我还说到他1958—1959年去爱荷华大学随李铸晋教授研读硕士,与我后来申请到该校奖学金的渊源。1964年,他为“亚洲教授计划”,到伊利诺州枫城(Peoria)的布德里(Bradley)大学及中密西根大学、宾州盖提斯堡学院、纽约州等巡回教学。1969年,他受美国教育部之聘,第三次赴美,任科罗拉多州教育厅外国课程顾问和寺钟女子学院客座教授。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了两年。
他谈那次赴美,发现自己与杨牧还有同一项爱好:摇滚乐。他因对鲍勃·迪伦(Bob Dylan)——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琼·拜雅(Joan Baez)以及披头士、民谣诗人有所感触,写了《民歌手》,仿照迪伦的诗句《江湖上》。
我留神的是1974年,余先生的《乡愁四韵》分别被杨弦、罗大佑谱成民歌,于胡德夫演唱会发表。更有李泰祥,将《海棠纹身》和《民歌》两诗谱了曲。翌年,杨弦续谱余先生诗集《白玉苦瓜》内的多首诗歌,1975年初夏,在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发表。当时余先生正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返回登台朗诵诗作。听众对乡土渴望的迷思,与既亲又疏的现代音乐交织,引起了热烈的共鸣。由此也引发了民歌运动、“以诗入歌”的创作,并引发了学院派音乐家的论战。
杨弦本名杨国祥,是外子担任台大合唱团团长时的男高音之一,低一届农化系学生。将余先生诗歌铺衍成类似异乡的诗乐,为《我们的歌》引领先声。
余先生爱旅行和开车,还幽默。他书中多有信手拈来、涉笔成趣的事。如在美国漫长而无红灯的四线高速公路,他曾以七十公里的时速疾驶,越过九个州,想突破重重的秋色。他笑说:“我现在还天天开车。”我闻之甚喜,禀告他与我们哈佛的赵元任教授一样,学到老开到老。
他谢我到校演讲,非常鼓励地说,绝对是应该听的讲座。他送了我他的诗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藕神》《凭一张地图》,亲自勾勒签赠。墨宝点画势尽,力透纸背,让我喜出望外。他又为我珍藏几十年的作品《左手的缪思》《掌上雨》《逍遥游》《五陵少年》《望乡的牧神》《敲打乐》《白玉苦瓜》《在冷战的年代》《焚鹤人》等,一一签名。
在西子湾西望神州,我也论起了他于1972年1月21日写就的《乡愁》。余先生离乡,是与父母跨海来台。他说:“乡愁是人同此心、举世皆然的深厚情感……我离开大陆,已经二十一岁,汉魂唐魄入我已深,华山夏水,长在梦里。”日后更远赴美国,乡思尤甚。他的诗上千,乡愁之作大约十占其一,但他所向往的,实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与兰香”的故乡。
细品他编辑《蓝星诗页》的1960年前后(他也编过《现代文学》),为准备一期女诗人专号,安排良久,仍缺一首,他便以“聂敏”的笔名,虚拟了《第三季》一诗,在蓉子和敻虹之间,秘密地公开出来。聂敏者,匿名也,曾引得周梦蝶几位有想入非非。他写《乡愁》等诗,写他在重庆悦来的青年会中学,写信给居住在朱家祠堂的母亲倾谈旧事,也有与母亲分隔的语境虚构。
《乡愁》本指淡淡的哀愁,但听到朗诵,常是激动,甚至凄厉,有样板戏的风味,令他很难为情。夏志清教授论及他时,曾说:“台湾散文创新最有成绩的要算余光中。”台湾散文在余先生充满刚柔之美的文字的熏染下,渐渐孕育成恢宏的气度。千禧2000年,他与我皆入选《世界华人学者散文大系》。
中山大学别后,他就由助理与我代通电邮。2011年冬,在香港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大会期间,他都曾畅谈近况,津津乐道诗画、音乐,或共同的师友夏志清伉俪等。他也谐趣横生地谈起书,“腹有诗书气自华”,架上的书,永远多于腹中的书;读完的藏书,恐怕不到十分之三。尽管如此,书确是可以“玩”的。他“玩书”的毛病始终没有痊愈。“玩书”则是玩书的外表,七色鲜明、设计潇洒的封面令人一见倾心:企鹅丛书的典雅,现代丛书的端庄,袖珍丛书的活泼,人人丛书的古拙,花园城丛书的豪华,瑞士史基拉艺术丛书的堂皇富丽,尽善尽美……
约翰生曾说,既然我们不能读完一切应读的书,我们何不任性而读?余先生说他的读书便是如此:大学时代,自勉自励地读完八百多页的《汤姆·琼斯》、七百页左右的《虚荣市》,甚至咬牙切齿、边读边骂地咽下了“自我主义者”。自从毕业后,这种啃劲愈来愈差了。他独到地分析:“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刘邦会用读书人,汉胜楚败,也是这个原因。苏轼这两句诗倒也不尽是戏言,因为一个人把书读认真了,就忍不住要说真话,而说真话常有严重的后果。这一点,坐牢贬官的苏轼当然深有体会。
读书其实只是交友的延长,吸收间接的经验。生活至上论者说读书是逃避现实,其实读书是扩大现实,扩大我们的精神世界,因不只生活在一种空间。英国文豪约翰生说:“写作的唯一目的,是帮助读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过来说,读书的目的也在加强对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对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据说《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生平只熟读《圣经》。弥尔顿是基督教的大诗人,当然也熟读《圣经》,不过更博览群书。结果,班扬的成就,也不比弥尔顿逊色。真能再三玩味善读智慧之书者,离真理总不会太远。这种智慧之书,叔本华说:“只要是重要的书,就应该立刻再读一遍。”考验书是否不朽,最可靠的试金石当然是时间。一切创作之中,最耐读的恐怕是诗。
就余先生而言,“峨眉山月半轮秋”和“岐王宅里寻常见”,读了几十年、几百遍了,却并未读厌;所以作《廿二史札记》的赵翼所谓“至今已觉不新鲜”,说错了。其次,散文、小说、戏剧,甚至各种知性文章等,只要是杰作,自然也都耐读。卷帙浩繁、读来废寝忘食的武侠小说,依赖厚重情节,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最不耐读。
朱光潜的试金法:拿到新书,往往先翻一两页,如果发现文字不好,就不读下去了。余先生要买书时,也是如此。因为一个人必须想得清楚,才能写得清楚;反之,文字夹杂不清的人,思想一定也混乱。偶尔有一些书,文字虽然不够清楚,内容却有其分量,未可一概抹杀。有分量的哲学家,却不一定成为清晰动人的作家。作家如果表达上不为读者着想,那就有一点“目无读者”。
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记得余先生说,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炉中,炼出一颗丹来。他尝试把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拆开又并拢,折来且叠去,为试验速度、密度和弹性。理想是要让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余先生和我都同意中外文坛很少认真批评散文。散文包容广,易写难工,需具诗才;小说家的本领,真何止一把刷子。晚年他写诗臻入化境:咏物诗、环保诗,能把全球化的现象、国际和个人问题入诗,或带进节气……提醒“冰姑”“雪姨”不忘神农的期待,具民族感性。他在中年就曾说过:诗人过了四十五岁,居然还出诗集,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例举华兹华斯等西方诗人为例。但文友晚近厦门提问:都说诗歌是属于年轻人,您现在是怎样进行诗歌创作的?有着皎白银发,机巧又悠阔的他,顿成怒目!
他早就洞彻生死,诗文中常牵触死亡。在1963年冬,儿子诞生,仅三天早夭。死亡随着生之喜悦接踵而来,使他猝然体会生命之单薄和瞬息……一眨眼,“死就在你的肘边”。三十岁那年,母亲在台去世,三十五岁子殇又得暂瞒爱妻,令他尽历凄凉的岁月。
他感伤:“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雨在海上落着。雨在这里的草坡上落着。雨在对岸的观音山落着。雨的手很小,风的手帕更小,我腋下的小棺材更小更小。小的是棺材里的手,握得那么紧,但什么也没有握住,除了三个雨夜和雨天。潮天湿地。宇宙和我仅隔层雨衣。雨落在草坡上。雨落在那边的海里。”北台湾的潮天湿地,深化了他儿子凄凄切切丧礼的高渺,转而宣讲莎翁和附王文兴先生的邮笺阐发:超脱一己的锥心之恸,而为沉甸哀悼千古的死亡。当时看似颇为完满齐全的我,也移情成为忧郁的文青,撼动非常!不忍心再问他:是否想过这是表亲近戚结合之故?常思不知他究竟如何向咪咪师母(范我存夫人昵称)忍痛明说。那个阶段,他常将诗与文一题二奏,将折射散文《鬼雨》的诗《黑云母》献给未见亡儿的妻。他将私情浪漫化,写诗意真意切,又多过百首。最多的是给妻子,一生恋着的江南表妹。
人心千头万绪,有人明哲保身选择噤声不语,或栖栖惶惶。而他发表乡土文学论战等的执念衅端不赘,也同各类人生的自由抉择,在文学创作,他总卓尔不群!
他是自我淬砺的诗人,要提升自己,同时还要身外分身,比昨天的我更加高明客观。要能看透,他指在文学上的经验越丰富,功力越高而能脱胎换骨。
厦大2014年秋举行女作协大会,纵使在师母右腿跌伤,住院开刀才两个月,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刻,余先生依然排除万难光临,做主题演讲。也使我得以与余先生再相会。10月24日起,头尾餐会都幸同坐,他对我感叹:本来我存夫人会陪他从高雄直飞,如今女儿幼珊正照料,女婿手续未成……唉!
他依然生气勃勃,以自嘲嘲人的冷诙谐,在盛况空前的听众前,逗人倾倒欢笑,着实具有耀目的辉煌。今竟然骤去,真叫人难以相信。就此天人永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