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八十年代
——读冯骥才《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
2018-03-05禾刀
文 禾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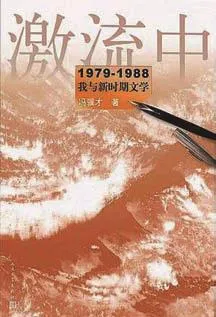
《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
作者:冯骥才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简 介:在本书中,作者记述了他亲历的新时期十年的文学活动,以及对整个新时期文学现象的反思。
这既是冯骥才的八十年代个人传记,也是中国文学八十年代的一次素描。
从冯骥才个人角度来看,本书是他计划书写的五部五十年精神史的第三部,其书写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是他个人创作的丰收期。十年间,他先后创作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等极具影响力的优秀作品。也是在同一个十年,中国文学迎来了一个井喷期:伤痕文学出现了《伤痕》《班主任》《血色黄昏》等,改革作品涌现出《花园街五号》《人生》等,寻根文学则有《钟鼓楼》《棋王》等……优秀作品辈出的背后,是刘心武、张贤亮、李国文、路遥、韩少功、贾平凹包括冯骥才等人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作家的喷涌而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华夏大地春潮涌动,处处焕发出久违的勃勃生机。刚刚走出十年劫难的文学界迅速觉醒,但同时又显得有些小心翼翼。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在上一个时代末终于得以出版,并且创下了新时期我国小说发行量的新高。《第二次握手》的意外爆红,对于文学界无疑是莫大的激励。然而,时代变革的潮流虽然不可逆转,但守旧僵化的传统思维惯性依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也所以,作家们的大胆探索既可能一鸣惊人,同时也可能成为一些人质疑乃至批判的对象。
毫无疑问,文学创作从来离不开批评的声音,但如果批评只是来自于对僵化思维的深深眷恋,那么这样的批评非但无法促进文学的进步,反倒可能成为文学发展的绊脚石。时间终于表明,那些违背时代潮流的落伍声音,最终不可避免地湮没于时代前仆后继的浪潮之中。
当然,文学界的小心翼翼不单单表现在创作方面,还表现在刚刚开启国门后文学界对于国际文坛显得过于陌生。由于长期封闭,不仅仅文学界还包括许多中国人对于国门之外所知甚少。冯骥才在书中不乏调侃自己初出国门时闹过的诸多笑话,这些笑话既有自己对西方国家社交礼仪惯例的不了解,也有一些国外高校在时隔多年后初次接触中国作家所表现出的仓促。显而易见,这些笑话也是打开封闭而必不可少的成本。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开放,中国文学才得以打破过去单一“向北看(苏联)”的惯例,许多优秀的西方作品得以进入中国,比如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两位文学大家就成为影响那个年代中国作家的重磅级人物。
冯骥才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一方面当然是指那个年代中国文学界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优秀作品永远是文学创作的晴雨表。另一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是中国文学“四世同堂”的时代,即“五四”时代的作家茅盾、巴金、郭沫若、冰心、曹禺等健在,革命作家丁玲、艾青、臧克家、刘白羽等等一大批作家也都在,王蒙、李国文、邓友梅、从维熙、刘绍堂、张贤亮等等“右派作家”当时并不老,“再有便是我们(冯骥才自指)一批‘文革’后冒出来的一代”。当然,每个时代的作家群体都有四世乃至五世同堂的现象,但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经历各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作家汇聚一堂的现象并不多。
在 历史的大浪淘沙下,历经历史变革的作家思想更加成熟沉稳,这与新生代作家的锐猛形成猛烈碰撞。各年代的作家在相互交流中砥砺奋进,许多时候,正是因为老一代作家的呵护,新生代作家才得以排除干扰,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

在中国文学作品喷薄而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也弥漫着浓郁的文学气息。清楚地记得,那个年代的年青人常常会因为读到一部好小说而彻夜难眠,会因为读到一首好诗而激动万分,会因为读到几句醍醐灌顶的名人名言而争相传颂。各种传抄文学作品和诗歌的现象屡见不鲜,情书成为年轻人展现文学素养的重要载体……“文青”在那个年代还是一种赞誉,而不像今天这样带着某些鄙夷的“穷酸气”意喻。倒不是说今天我们要开历史的倒车,回到那个年代。正如冯骥才所言,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文学。但对于在今天这个读图读频日益泛滥的时代,文学界能否迎来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的创作井喷期,这或许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