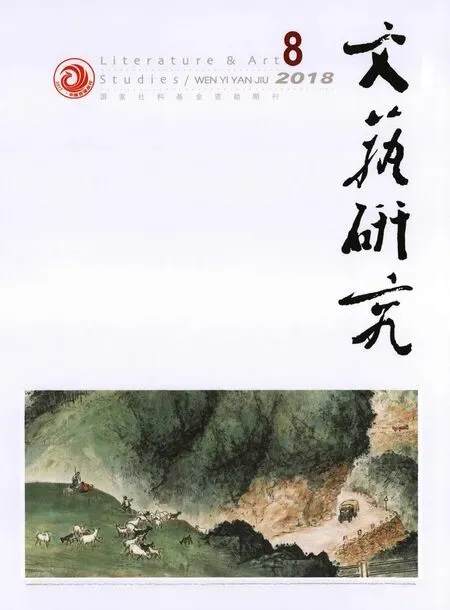作家的中产阶级化与21世纪长篇小说乡村想象的几种方法
2018-03-03雷鸣
雷 鸣
如何把乡村书写得真切而生气淋漓?我们自然会想起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那些为完成自己的创作而深入生活、落户农村的作家。柳青为写《创业史》,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十四年之久;周立波为写《山乡巨变》亦从北京回故乡湖南益阳安家落户,与农民生活在一起。虽然他们由于时代语境之囿,创作难免带有理念化的痕迹,但是他们对那个时代农村现实生活的深入体验和细致描绘,颇多可圈可点之处。
当下的中国作家却极少有人真正深入乡村,大多在城市里过着稳定富足的中产阶级生活,正如作家韩少功所说:“现在的作家都开始中产阶级化,过着美轮美奂的小日子,而且都是住在都市。”①韩少功此言并非虚妄。按照社会学家陆学艺的观点,中产阶级群体主要以脑力劳动为主,工资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稳定、高额的收入给中产阶级带来相当的消费能力、一定的闲暇时间及较高的生活水准,并且这个阶层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公民意识②。因此,当下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自然可归于中产阶级的行列。一是他们大多收入稳定,要么是“专业作家”,要么供职于作协系统的大报、大刊,一些知名作家甚至跨入了“新富阶层”。二是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如“60后”作家毕飞宇、韩东、李洱、邱华栋都毕业于知名高校,年轻一代的“70后”作家,如徐则臣、付秀莹,更是京城名校的研究生毕业。尤其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大学,如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等纷纷在知名高校担任教职,其生存方式之“学院化”,似乎也表征着作家的“中产化”。
当然,作家的身份、社会地位、所处阶层与文学作品的风格特征,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绝非一阶层只有一阶层之文学。事实上,列夫·托尔斯泰出身贵族,亦不妨碍他访问贫民窟,深入了解城市底层生活,写出人道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鲁迅彼时作为教授和作家的收入,完全可归入富人阶层,但丝毫不影响他的作品表现对弱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写作者生活环境(或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世界观、艺术观、个性、气质的差异,还是会或显或隐影响到作品的内质与样貌。当下中国作家的中产阶级化的生活方式、世界观、艺术观必然带来与之相应的美学话语。诚如程光炜所言:“中产阶级时代造就了中产阶级文学,而中产阶级文学又以特殊的形象符号描绘了中产阶级时代的价值观念、思想感受和心理情绪。”③
综观21世纪长篇小说之乡村叙述,已经中产阶级化的作家书写对他们而言隔膜、遥远的乡村时,总是以深浸于都市所养成的中产阶级趣味,预设种种观念定制、覆盖他们“看不见的乡村”④,表达他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感受和心理情绪。由此,形成了几种流行的“套路”,亦暴露出21世纪中国文学乡村书写的诸多隐忧。
一、高密度知识的填充术
现代以来,中国作家对乡村的书写形成了几种固定的叙述方式:一是鲁迅的决绝批判式,勾勒乡村的破败与众生的愚昧,以启蒙、唤醒民众;二是沈从文的缱绻怀恋式,叙述浪漫的湘西记忆,建立人性美好的“希腊小庙”;三是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的革命理念规划式,改写从前鲁迅的“哀歌”与沈从文的“牧歌”式乡村形象,塑造清新、明朗的红色乡村;四是莫言、陈忠实的民间与传统观照式,试图考察乡村社会之变迁并反思历史。上述几种格式的乡村叙事,由于各自视野的局限性,难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真实的乡村生活。但不管怎样,他们展开的乡村想象的基底,是乡村人伦风情的描述与鲜活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没有抛弃对乡村生活丰富细节的描摹。
那么21世纪的中国作家如何书写当下的乡村呢?显而易见的是,居住在都市的作家过的是同质化的生活,乡村生活经验极其贫乏,即便有些乡村生活的体验,也是多年前挤牙膏式的童年记忆,新的生活经验基本上来自各类媒介。如莫言曾坦言:“对于我们50年代出生的这批作家来说,想写出反映现在农村的作品已经不可能。我们对农村已经疏离,很难去体验它真实的变化。”⑤阎连科也曾自我批评道:“连我自己,做小说的时候,对于乡村的描绘,也是不断重复着抄袭别人的说法……而实际上,村落真正是个什么,沟壑的意义又是什么,河流在今天到底是什么样儿,我这个自认是地道的农民的所谓作家,是果真的模糊得如它们都沉在雾中了。”⑥因此,不难发现,近些年来,写乡村的小说出现不少雷同、撞车或“抄袭”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作家对乡村的认知、叙述,依赖于书斋里获得的媒体信息,缺乏脚踏实地去感知与体验。如刘继明2004年发表于《山花》的小说《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与李锐2005年发表于《天涯》的小说《扁担》,素材皆来源于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一期节目“千里爬回家”;贾平凹《高兴》据农民工千里背尸回家的报道改写而成,阎连科《丁庄梦》的“本事”亦是见诸媒体报道的河南上蔡县的“艾滋病”村。
雷同的都市生活处境,对作家创作构成极大挑战,如何在都市逼仄的书房内闪展腾挪,表现斑斓裂变的中国当代乡村呢?“中产阶级却又并不仅仅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资产,不仅仅意味着物质生活上的小康,还意味着有文化,有教养,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知识文化水平。”⑦于是,对从乡村生活抽身而退的“中产化”作家来说,在文本中表现自己“有文化、有教养,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知识文化水平”,或许是本阶层的趣味所致,亦是一种对乡村隔膜之后无可奈何的选择。广西作家鬼子道出了自己的心曲:“你们说乡土文学城市化,符号化了,你要使写作逃脱这种模式,最后无非也是发现或发明另一种‘乡土’,我估计走着走着,还是另一种符号。可能关键是哪种符号更可爱。”⑧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作家来说,或许选择文化知识来发现或发明一种“乡土”更可爱。
因此,21世纪以来,中国作家似乎更愿意展示自己的专业修养、知识水平,好以炫耀的笔致表现自己的知识与文化优势,借助所掌握的民俗、历史、宗教、经济、地理等专业知识,搭建乡村叙述的框架或道具,以弥补对当下乡村生活的陌生造成的缺漏。由此,21世纪小说的乡村书写出现了一种悬置乡村故事、抛弃乡村生活质感的趋向:不屑讲述乡村现实,复现乡村人生,对乡村生活细节的编织也没有耐心;乡村不再是一个生活的空间,而变成了涵纳高密度知识的容器。
先以郭文斌的《农历》为例,虽然作者试图以农历节日为切入点,描摹诗意氤氲的乡村生活图景,以此唤起传统文化精神,但也正是由于极度迷恋于此,小说不惜大段引用传统文化经典,如孔子和老子的经典著作、《朱子家训》《孝经》《心经》等,还大量插入民谣、古诗、对联、议程词和一些剧本。作者似乎难以逃脱掉书袋之嫌疑。再看李锐的《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由系列小说构成,姑且视为长篇),贩卖知识之嗜亦非常明显,系列小说以元代县尹王祯所著的《王祯农书》中提及的十六种农具为主题,每种农具作一篇小说。除《颜色》《寂静》两篇以外,其他小说都包含农具图片、王祯写的文言文、引自《中国古代农机具》的说明文等知识性构件。尽管小说试图通过书写农具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命运,来借喻农民传统生活方式所遭遇的尴尬和现实处境的无奈,但小说中的图片与文字、文言与白话、史料与虚构,以超文本的方式拼贴在一起,仿若古代农具博览之解说修辞。同样,阿蛮写土家族聚居地石柱县有关蜀绣的小说《纪年绣》,也是一部高密度的知识化小说,如贺绍俊所批评的那样:“我在读《纪年绣》时,一方面感到知识量非常大,另一方面又感到阿蛮对于自己的储藏太不吝啬。”⑨
此外,关仁山的《日头》亦有夸耀知识、文化元素过多堆积之弊。小说多次写魁星阁、状元槐、天启大钟等意象以象征中国传统的精神,连人物的命名(如金沐灶)、人物之间的冲突(金家与权家)也暗含了中国文化中的五行(金沐灶:金、木、水、火、土)及运行规律(“金”克“木”)。小说还不断使用《金刚经》《道德经》《圣经》等文化经典来表达主题,有时借人物之口直接讲解文化知识,比如金沐灶作如此思考:“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因果轮回;道家的清静无为,追求长生不老,得道升仙;基督教追求信、望、爱。我看来,这些宗教在最高宗旨上意见不一,甚至争得厉害。可是细想想,入口不同,最终的道理是一致的。”⑩不得不说,这般高密度、高浓度文化内涵的注入,必然会冲淡乡村生活的质感。与此类同的,还有孙惠芬的《上塘书》。这部小说采用地方志的文体,确有其新颖与独特之处,但缺陷也十分明显。作者把上塘村按照“地理”“政治”“交通”“通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和“历史”等九个方面进行划分和叙述。正是这种地方志的书写方式,使文本中充斥着大量的有关解释、说明上塘村的风俗民情、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社会状况的文字。尽管作者也试图表现乡村生活的日常状态,但由于解释、说明的知识性文字过多而遭遮蔽,此时的作者仿若全知全能、喋喋不休的上塘村“导游”。
正是由于对知识、文化符号的过度追求,这些小说类似于民俗学读物、地方志、古代文化知识汇编。阅读它们,你几乎看不到当下乡村绵密细致的日常生活,很少能见到真实的充满血肉与肌理的乡村生活样貌,很少能触摸在21世纪乡村裂变期,农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变迁。读者看到的只是知识层峦叠嶂的“七宝楼台”,却没有丰盈摇曳的人伦情感以及乡村生活的绵密针脚与生动韵味。这种依靠知识、文化填注的乡村小说缺乏文学所需要的明敏、鲜活的感性维度,文学性自然会大打折扣。
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认为:小说可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确实在企图再现人生……不消说你如果没有对现实的感觉,你就不会写成一部好小说⑪。确实如此,作家只有企图再现乡村人生、有对21世纪乡村现实的感觉,才能写出好的乡村小说。贾平凹在21世纪的长篇小说给了我们正面的启示,《秦腔》《带灯》等作品或书写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遭遇的溃败,或叙述当下乡村基层政权的百态,虽然也有小说地域背景的知识性成分,但作者致力于还原乡村生活本然的“肉身”状态,以密实的生活细节洪流,勾描着当下乡村的细密纹理。何以能如此?事实上,贾平凹不只是处于书斋、纸上写作的状态,他不时体验、融入当下乡村生活,感知乡村生活之枝枝蔓蔓的变动,如他在《带灯》“后记”中所说:“几十年的习惯了,只要没有重要的会,家事又走得开,我就会邀二三朋友去农村跑动,说不清的一种牵挂,是那里的人,还是那里的山水……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了,即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两旁的树和一些小区门前的竖着的石头,我一眼便认得哪棵树是从西安原生的哪棵树是从农村移栽的,哪块石头是关中河道的,哪块石头来自陕南的沟峪。”⑫
二、寓言化表意的妆容术
除以知识作为乡村叙述的填充料之外,还有一种明显的趋向,即同样不屑忠实地表现21世纪乡村的复杂现实,而热衷于运用理性思维和哲学思辨的方法改写或重构乡村,借助寓言化的方式,对乡村的历史与现实加以变形、扭曲,以便阐释某种理念。“所谓寓言性就是说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因此故事并不是它表面所呈现的那样,其真正的意义是需要解释的。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述或再写一个故事。”⑬也就是说,寓言化的乡村书写,背后隐含着作家想要强烈表达的思想观念,内置着作家智性思考的隐喻功能。简言之,乡村成了作家意念的“酒杯”,以浇作家个人智性思考的块垒。
这种回避当下现实,或致力于现实之夸张、变形的寓言化写作倾向,阎连科近年来创作的小说可为代表,其《日光流年》《受活》《炸裂志》等长篇小说均可以视为寓言化文本。《日光流年》里见不到乡村生活的丰富肌理,多的是各种荒诞的情节:这个叫三姓村的地方流行着名叫“喉塞”的可怕疾病,村人都活不过四十岁;村民为活过四十岁翻地换土,年轻的男人去卖自己的皮,女人出去卖淫;为了巴结公社领导,村主任鼓动村民献出黄花闺女。毫无疑问,这部小说是一个现代寓言,旨在反思中国政治文化与民众生存状态的关系:愚昧导致对权势的崇拜,权势又更加剧了民众的愚昧。《受活》同样具有寓言性质,小说重点描述残疾人的生存世界“受活庄”,是如何一步步地纳入现代性体制的过程,又如何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失乐园的痛苦。小说展示的生存图景极具特异性:受活庄是由残疾人组成的世界,村民个个身怀绝技,要成为受活庄人的前提是残疾;县长柳鹰雀要购买列宁遗体,在县里建纪念堂,并以此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以便带动全县经济发展……不难看出,故事基于对乡村历史、现实的有意变形与荒诞化,暴露出作者过于明晰、强烈的表意焦虑:即对建立理想生存方式与形态的“乡土乌托邦”的思考。《炸裂志》虽然借用志书这一似真模式,但依旧采用寓言化的写作方式,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而所谓‘炸裂志’,表面上看是‘炸裂’这个地方的市志,而实际则是中国之‘炸裂’的‘国志’,也就是说,《炸裂志》以‘寓言’的方式表现了整个中国的‘炸裂过程’。”⑭当然,上述寓言化写作也显示出阎连科不囿于现实主义的传统写法,试图追求审美变革的叙事野心。从他提出的“神实主义”概念亦不难窥见:“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事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⑮客观地说,这种“特殊臆思”的寓言体式,的确扩张了小说的话语内涵与艺术张力,但一味以寓言化作为小说表达意义的唯一手段,未免让读者厌恶并产生精神疲惫,也表明作者在小说创作上存在着满足于自我复制、自我循环的短处。
范小青自《女同志》之后就潜心于乡村叙事,无论是《赤脚医生万泉和》还是《香火》,虽然都充满荒诞感,但写实仍是主脉,而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却是现代主义色彩浓厚的寓言式写作。小说的开头就有卡夫卡《变形记》的色彩:“我弟弟是一只老鼠。当然,这是妄想出来的,对于一个精神分裂病人来说,想象自己是一只老鼠,应该不算太过分吧。”⑯作品的情节非常简单,就是扔掉与寻找的过程,隐喻着现代人的身份迷失与悖论式生存。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弟弟不但祸害乡邻,还影响了“我”(王全)的婚姻,整个家族便做出决定:把弟弟扔掉。扔掉之后,“我”内心却萦绕着深重的罪恶,父亲见“我”魂不守舍,就让我外出寻找弟弟。在“我”寻找弟弟的途中,乡村百态逐一暴露,但完全是荒诞不经的。同时,“我”在寻找弟弟的过程中也被当成精神病,“我”说不清自己的身份,也说不清弟弟的身份。范小青表示:“这样的设置是想通过侧面来写人生的疑惑与不确定,在人的一生中有许许多多解不开的迷惑和疑团,有许许多多的未知和不确定,如果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不正常的世界,显得无趣和苍白,所以,试图用不正常的眼光来看这个不正常的世界,会产生双重的变形的效果,荒诞、离奇,写起来更有趣味。”⑰这一哲学命题被嫁接到乡村故事中,绵密的乡村生活细节在追求所谓思想深度与普遍寓意的文本中失去了踪迹,乡村故事成了包裹作家理念的外衣。正如有研究者所论:“这也显示出作者的精英主义立场,她恐怕早已失去了感受真正乡村的能力,只能避实就虚地写作‘借乡村的酒杯,浇个人心中的块垒’的现代故事。”⑱
如果说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是一个披着乡村外衣的有关现代人身份迷失与悖论式困境的寓言,那么赵兰振的《夜长梦多》(第一部)则是一个借村庄叙事,表达有关个体存在的荒谬与虚无的寓言。小说中主人公翅膀替父亲在塘边守夜,看守等待分配的鱼堆,他鬼使神差地抱着那条传说中的大红鲤鱼睡着了,竟然被亲戚正义当成了向上爬的梯子,被人挂上“社会主义淡水鱼强奸犯”的纸牌游街示众。多少年后,翅膀回到故乡依然痛不欲生,心里唯一的那份美好,在他回来时,亦顷刻崩坍,感觉世界一切虚无,因为他看见了令自己魂牵梦绕、宛若仙女的女孩何云燕,在一场吵架中,从自己的裤裆里,拽出血呼淋啦的纸巾,像糊膏药一样贴到了男人的头顶上。在这里,作者书写了个体的孤独、异化、忧郁、破碎,有明显的加缪、卡夫卡、博尔赫斯的气息。小说很难看到村庄的现实面影,有太多马尔克斯、福克纳式的写法,作品中的嘘水村,又叫南塘,被作者描写得充满神性又阴森可怖:南塘边上有指缝结着冰碴,穿着棉袄的无头鬼;南塘的夜空飘着神出鬼没的绿莹莹的灯笼;南塘的湖底有神秘的洞穴,有喷血的大红鱼……小说中人物亦有着奇诡怪异色彩,项雨迷恋婶子的豪乳,楼蜂最喜阉公鸡,以锤子敲猪崽的脑壳,正义患有血腥气冲天的血手怪症。
新疆作家刘亮程当年以散文《一个人的村庄》《风中的院门》描写诗意乡村的丰富肌理而蜚声文坛。2006年,他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虚土》却陷入了寓言化写作的窠臼。小说通过描写一个虚拟、灵异的乡村世界,表达着孤独与死亡的主题。林白的《万物花开》通过脑袋里长了五个瘤子的乡村少年的独特视角,呈现乡村生活的荒诞怪异。小说的寓言意味十分明显,表现出作家对未经规约和压制的生命本能的思考,其寓意正如小说标题“万物花开”所示——任何事物都有其自然存在的方式与生长权利。
以寓言化的方式书写中国乡村并非始于21世纪。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寻根文学是这一创作模式的始作俑者。韩少功的《爸爸爸》即是有关民族文化思考的现代寓言,小说刻画的白痴丙崽具有象征意义,他是一个永远保持童稚状态、退化返祖的怪物,是集肮脏、蒙昧、粗鄙、丑陋于一身的民族文化劣根的象征体,作者通过这个形象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批判。莫言的《红高粱》、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亦是如此。公允地说,小说的寓言化倾向是对中国当代小说中那种教条化、平面化现实主义的矫正,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文本的思想容量与意蕴张力。但寓言化也容易为了一种预定的思想“深度模式”,而舍弃“生活原则”,把丰富的生活场景限制在理念的框架之中,人为地将多维度的生活符号化、仪式化。在这一点上,寻根小说之弊很明显。
时至今日,上述寓言化的21世纪长篇小说,在处理生活上以先在的理念预设,步了寻根文学的后尘。这些作家或无法廓清层出不穷的新的复杂现实,或缺乏直面当下的勇气,只好粗暴地悬置了乡村现实的丰富性,以所谓哲学沉思、微言大义,把对世界的智性思考看作小说的首要目的,乡村的现实情态仅仅是作者表达理念的道具与锚地。
如果说寻根小说将乡土叙事带上寓言化的轨道,乃是当时出于对加快改革步伐的热切盼望,用隐喻的方式反思传统文化,那么21世纪作家的乡村寓言化书写,除了追求自己创作上的美学变革外(虽然这种现代主义寓言式隐喻的方法已经非常老旧),笔者以为,似乎还有更复杂的原因。首先是以思辨之长补经验之短。当下大多数作家居于都市,远离乡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穿插于世界繁华都市,浏览于名山大川之间,参加各种笔会、座谈会、评奖会、演讲会大概就是他们书斋以外的生活。偶有回乡,恐怕也是‘省亲’式的荣归故里。这样‘高居云端’的写作,怎么可能触及底层‘新的现实’和‘深的现实’”⑲?虽然他们缺乏乡村生活经验,但理性、思辨却是其所长,以“怎么写”(寓言化)来掩蔽“写什么”(乡村现实)的苍白与单调,成了很多作家扬长避短的策略。有些作家也意识到了在乡村生活现场的重要性,如写有“神农架系列小说”的陈应松表示:“以为远离我们视线的存在就不算存在,远离城市生活的生活就不算生活,是极其糊涂的。我宁愿离开那些优雅时尚的写作,与另一些伏居在深山中的劳作者殷殷的问候和寒暄。”⑳其次是中产阶级化的精神趣味使然。正如前文所述,21世纪的中国“专业作家”或“职业作家”已经跨入“中产”之列,已经超越了追求基本生存需要的阶段,更在意心灵体验等精神层面的满足。以寓言化小说表达哲学思辨,进行对世界的智性思考,正是“中产化”作家这种精神需要的文学化表现。费斯克指出:“中产阶级趣味和大众趣味的区别,不仅在于前者对距离和绝对性的看重,也在于它缺乏乐趣和某种共同体的感觉。”㉑这样一种夸示智性、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写作逻辑,或许正是作家与大众趣味拉开距离的原因。
三、都市视野的移置术
正如前文所述,当下书写乡村的作家大多定居于都市,即便过去有乡村生活经验,也早就成了遥远的、不再更新的记忆。深受都市文化浸润的他们,少有直接而鲜活的乡村生命体验,摆脱不了以隐性的都市视野作为观照乡土的方式。与此同时,乡村小说的读者也大多是城市读者,出于商业逻辑,乡村书写也必须契合都市人的期待视野,把他们的价值观摆在优先位置。因此,21世纪很多作家笔下的乡村想象,大多寄寓着都市主流阶层对乡村的情怀与记忆,镜像般地映照着当下都市主流群体(或曰中产阶层)的现实处境与精神诉求。
一是将都市欲望化想象植入乡村现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文化逐渐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欲望是消费主义发生的动力源和最终诉求,“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令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㉒。这种追求欲望满足的消费文化,被当下的一些作家植入乡村书写中,文本里大量堆砌着物欲崇拜、享乐主义的符号景观,欲望被裸呈于乡村大地之上。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许多文本不约而同地写到了乡村男女的偷情故事。贾平凹的《秦腔》虽被评论家誉为“废乡”之作㉓,但小说所写的偷情之事却反复出现,淋漓尽致地写了夏庆玉与黑娥、三踅与白娥、翠翠与陈庆之间的偷情场景。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也大肆渲染高爱军与夏红梅的偷情。付秀莹2016年的长篇小说《陌上》虽然在表现乡村生活的丰盈质感方面很突出,其笔下的芳村氤氲着乡村生活的气氛,但叙事功效不大的偷情元素却在文本中被多侧面地展示,似乎作者在有意炫耀和展览作为看点的乡村“性趣”。如小说中多次写到香罗、望日莲、瓶子媳妇、春米等女人在办公室、小汽车、庄稼地与男人偷情;小说中有权有势、敢闯敢干的男人,如大全、增志、村支书建信、秘书刘银栓,则无一例外地都喜欢“偷腥儿”。
何以在乡村现实的描写中,男女偷情的局部元素被强化与放大呢?这种满载偷情元素的乡土叙事背后,其实隐藏着都市中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的愿望,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实生活中中产阶级就关注自我欲望的极大化满足,就追捧炫耀性消费和富有刺激性的偷情——因为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炫耀性消费和偷情频率是中产阶级文化身份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是中产阶级显示财力、能力和地位的最佳形式。”㉔此言得之,21世纪中国作家之所以热衷于书写乡村偷情故事,实际上是在兜售情欲,乃中产阶层都市人心态的投射,只不过是把都市情欲的幻梦挪至乡村野地,更添几分新奇、刺激的色彩。
二是以都市人的怀旧心态把乡村伊甸园化。乡村总是被刻意塑造为都市的对立面,当作矫正和平衡城市文明的一种力量,这实乃都市发展建构的产物,更多是都市人的视野与心态使然。赫伊津哈指出:“幻想着回归自然的怀抱,憧憬着牧羊人式的纯真生活,这一梦想最为强烈也最为持久。”㉕尤其当工业化、城市化日益加速之时,这种梦想更为强烈。因为,对于久居都市的人而言,乡村仿佛是一个可以寄托美好情感和回忆的地方,是一个逃避现代性恶果的“桃花源”,可以缓解焦虑、弥合创伤。为此,文学作品就着力书写乡村的纯洁静谧,其中的乡村没有贫困、劳作、污秽,只有令人神往的田园风光、闲情逸致和美好人性,乡村生活被完全理想化、诗意田园化。这种写作路向,在中外文学史上一直未曾间断。早在英国伊丽莎白时期,著名诗人西德尼和斯宾塞便对乡村生活的恬静、淳朴予以赞颂,后来的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济慈等亦是把乡村视为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的救治之方。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而言,沈从文、废名、汪曾祺、迟子建等作家的创作都在这一思想脉络上。
21世纪以来,一些长篇小说或将乡村复杂现实彻底诗意化,唯有民风淳朴、人心善良、生活宁静、温情氤氲;或将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张力和伦理道德深层裂变,化约为一首清澈动人的牧歌,只有自由、和谐与静穆;还有的倾向于挖掘边地乡土世界的传统风俗和生活方式,以构建都市人难得一见的文化奇观。方英文的《后花园》凸显了这方面的主题,小说写一个大学教师宋隐乔因解决内急下了车,被启动的火车遗弃在陕南农村的青山绿岭中。装有他各种身份证件及手机的行李都留在了火车上,作为现代性符码的身份证和手机的遗失,暗喻着他与现代性的告别。他来到了一个叫娘娘窝的村庄,那里纯洁安详、美妙和谐,人置身其中享受着诗意的安顿。赵本夫的《无土时代》设想了一个具有乡村诗意化的木城:“月牙儿落得很快,紧接着就是满天繁星。天也一下子暗下来。大地上的一切都变得朦胧而神秘了。荒野的风漫进木城,大大小小的树木和玉米地都发出簌簌的声响。”㉖更多的小说则书写诗意浪漫的边地乡土世界,如安妮宝贝的《莲花》、党益民的《一路格桑花》、杨金花的《天堂高度》、七堇年的《大地之灯》等文本也都极力渲染边地乡村原生态风景的美好,是奇异、纯洁、神圣、充满着浪漫气息和脱俗气质的“香格里拉”,是产生纯美爱情或升华精神格调的天堂。
21世纪中国作家这种将乡村伊甸园化的写作方式,除了是对过去文学传统的惯性沿袭外,还与满足当下中产阶级的审美需求相关。恰如温迪·J.达比所说:“具有审美愉悦的田园风光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把农业过程、农业劳动者,甚至整个村庄从视线里清除出去,留下无人的、如画的风景,使特权观赏者能够观赏纯粹的画面。”㉗因此,21世纪长篇乡村小说构建这种伊甸园式的乡村神话,其实隐含着当下中国都市中产阶级的精神境遇与心理代偿愿望:期望乡土世界的纯净美好,作为逃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信任断裂等现代性恶果的避难地,同时亦期望文本中的乡土世界成为“故乡”,以疏解他们远离故土的失落和怀念。正因如此,作家就很难顾及全面洞悉乡村现实的绵密肌理,也无暇剖析农民精神世界的幽微了,唯有提供与都市景观截然不同的“诗意”或“奇观”景象,供都市人把玩。
结 语
显然,21世纪长篇小说以文化展演之“知识填充”、智性夸示之“寓言表意”、心理代偿之“都市置换”,作为想象和书写乡村的三种方法,无疑是中产阶级的审美逻辑和话语体系建构的审美程式,表现出创作主体强烈的中产阶级趣味。这种躲在象牙塔里以精英主义心态来书写乡村的弊端很明显:以这种方式书写乡村,只能是一种无关痛痒的“自己和自己玩”的纸上游戏;作家笔下的乡村只能是一种苍白而空洞的观念化乡村,与鲜活而实在的乡村相去甚远;作家也无法体察当下农民生活与精神的本然状态。
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恩格斯曾有过精辟的忠告:“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㉘虽然今天要求已经“中产阶级化”的作家们住在农村,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不太现实,但他们完全可以接续现实主义令人尊敬的“体验生活”之传统,从书房走向村野,对21世纪的中国乡村投以深情的关注,以扩张自己对乡村新的感知,而不是每天沉迷于都市中产阶层生活之安逸,依赖媒介化的农村信息,自恋地意淫远方的乡村大地。
① 韩少功:《作家的创作个性正在湮没》,载《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8期。
② 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③ 程光炜:《中产阶级时代的文学》,载《花城》2002年第6期。
④ 何平:《新世纪乡村文学:文学乡村与现实乡村的偏离》,载《文艺报》2012年10月31日。
⑤ 田志凌、孙晓骥:《新乡土文学:文学离今日乡土有多远》,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3月15日。
⑥ 阎连科:《返身回家》,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⑦ 王彬彬:《“中产阶级气质”批判——关于当代中国知识者精神状态的一份札记》,载《文艺评论》1994年第5期。
⑧ 参见《2004·反思与探索——第三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纪要》,载《人民文学》2005年第1期。
⑨ 贺绍俊:《阿蛮〈纪年绣〉:典型的知识写作》,载《文艺报》2016年1月25日
⑩ 关仁山:《日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2页。
⑪ 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杨烈译,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11—512页。
⑫ 贾平凹:《带灯》“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6—357页。
⑬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页。
⑭ 刘汀:《〈炸裂志〉:书写中国现实的另类文学标本》,载《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4期。
⑮ 阎连科:《发现小说》,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182页。
⑯ 范小青:《我的名字叫王村》,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⑰ 周韫:《范小青谈新作,每个人都可叫“王村”》,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8月27日。
⑱ 徐刚:《小说如何切入现实:近期几部长篇小说的阅读札记》,载《南方文坛》2016年第1期。
⑲邵燕君:《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由阎连科〈受活〉看当代乡土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失落》,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6期。
⑳ 陈应松:《靠大地支撑》,载《小说选刊》2003年第8期。
㉑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㉒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7页。
㉓参见《秦腔:一曲挽歌,一段情深——上海〈秦腔〉研讨会发言摘要》,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㉔ 向荣:《想象的中产阶级与文学的中产化写作》,载《文艺评论》2006年第3期。
㉕ 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刘军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㉖ 赵本夫:《无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页。
㉗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红英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㉘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