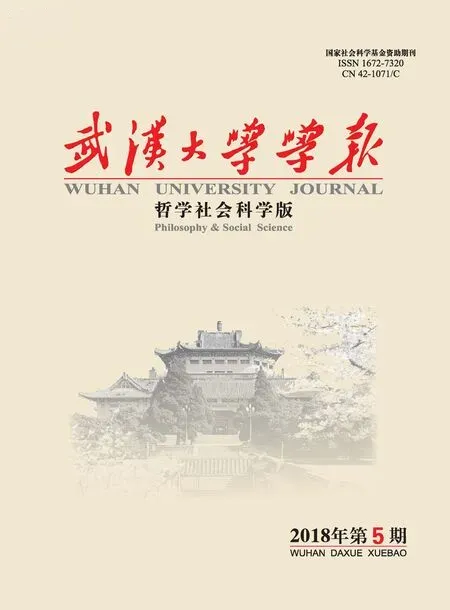从清华简《诗》类文献看先秦楚地《诗》教特征
2018-03-03禄书果
禄书果
先秦儒家“六经”之学尤以《诗》教影响至为深远,《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以《诗》。”可见《诗》教在先秦时期之盛行。儒家《诗》学传播与楚地《诗》教构建存在诸多关联,楚地对《诗》学的接受,一方面是出于提升政治、文化、外交影响力和发展贵族教育的需求而主动接受周王室“礼乐文化”的结果①西周早期,楚地与中原的交流仍处于被动状态:“周王朝对楚蛮的统治和影响是强制性的,同时也有歧视性,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物质文化的生产方面,对荆蛮都是采取限制态度”。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楚国在军事实力提升和地域版图扩张之后,开始明确表达其政治诉求:“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史记·楚世家》),甚至觊觎王权并“问鼎”于周王室(《左传·宣公三年》)。至春秋战国时期,提升政治、外交影响力成为楚国主动学习接受以礼乐之道和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的主要动因。[1],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儒学和“六经”在楚地传播的深刻影响②先秦诸子之学在楚国皆有传播,其中尤以儒学及“六经”传播最广。据史籍记载,不但孔子曾经“游楚”,七十子及其后学中,馯臂子弓、吴起、陈良及荀子等都曾先后在楚地传播儒学思想。高华平先生对孔子及七十子后学“游楚”和楚地“六经”文献的传播情况皆有考辨,详见高华平《先秦诸子与楚国诸子学》及高华平、李璇《由楚地出土文献看“六经”在楚国的传播》。[2][3]。楚地《诗》学的确立是以楚人对“六经”和儒家诗学思想的接受为基础,而楚地《诗》学的兴盛和楚国统治阶层对“礼乐之道”与《诗》之德育、教化功能的主动施用,共同推动了楚地《诗》教的繁荣。刘冬颖指出:“从出土楚地简帛涉及到《诗经》的篇章内容来看,无论其作者为谁,是否楚人,是否在楚国讲学,都足以说明一个问题:楚国受到儒家‘诗教’思想影响很大,其对《诗》的接受与认同的程度可能还在中原各国之上。”[4](P127)从近年的大量楚地出土文献材料特别是上博简、清华简中的《诗》类文献来看,这一看法是符合事实的。
学界以往的研究多由于传世文献中缺乏可靠材料,无法深入全面地揭示儒家《诗》学在楚地的传播情况,但日渐丰富的出土文献特别是楚地简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新契机。刘冬颖结合郭店简和上博简对先秦楚地《诗》学的传播情况和楚地《诗》学特征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但未及采用清华简中的《诗》学材料。马银琴也关注到战国时期《诗》在楚国的传播情况,探讨了战国时期儒学在楚地的传播,遗憾的是同样未及采用清华简中的《诗》类文献材料[3](P143-162)。高华平、李璇结合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楚地简帛材料,较为全面地对儒家“六经”在楚国的传播情况进行了梳理,但在探讨楚地《诗》学时仅提到清华简《耆夜》篇收录的《蟋蟀》一诗[5](P126-139)。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对楚地《诗》学的研究多侧重于探讨儒家《诗》在楚地的传播过程和相关影响,却忽略了无论是儒学南渐传入楚地之前,还是儒家《诗》学和儒家思想全面传入楚地之后,楚地《诗》教都是不断发展且具有内在连续性的教育体系,具有相对独立的教育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渊源。那么,楚地《诗》教具有哪些文本特征和文化特征,先秦时期《诗》教在楚地发展历程如何,战国时期楚地《诗》教又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本文拟通过对清华简《诗》类文献的考察,尝试对以上问题加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清华简《诗》类文献的篇目范围与判断标准
学界一般认为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的楚地竹简,目前已整理出版的前7册篇目内容,涵盖类别有《诗》《书》《易》《春秋》等,其中所见《诗》类文献多为不见于今本《诗经》的“逸诗”,但学者们对清华简中《诗》类文献的具体篇目范围仍有不同意见。
关于清华简中《诗》类文献的界定,李守奎先生认为:“诗类文献以记录诗的内容为主,兼叙诗的创作和使用过程。《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之诗》(即《芮良夫毖》)3篇已经公布了。其他叙事作品中也有唱和的诗,但以叙事为主。”[6](P291-298)黄甜甜在博士论文《清华简“诗”类文献研究》中将《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耆夜》等 3篇作为《诗》类文献加以阐释研究,讨论了儆、毖之诗的文体源流[7](P106-138)。还有学者从《诗》学研究视野对《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耆夜》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显然都是以这些篇章属于《诗》类文献作为研究前提。江林昌先生则注意到清华简《祝辞》与先秦巫术咒语诗的相似之处,认为《祝辞》是特殊的楚地巫祝诗歌,这一判断扩大了清华简《诗》类文献的认识范围。此外,清华简《金縢》篇记载有“周公乃遗王诗曰《鸱鸮》”之事,虽然没有详细记录《鸱鸮》的文本内容,学者一般认为就是今本《诗·豳风·鸱鸮》,则《金縢》似可看作是关于《鸱鸮》的“诗本事”,但也有学者认为“清华简《金縢》表明《鸱鸮》并非周公所作而为周公所用”[8](P30),《鸱鸮》当作于周公之前,是周族居豳期间所作。据《尚书·金縢》记载:“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毛诗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古代郑玄、孔颖达、朱熹等学者皆认为《鸱鸮》乃周公所作,崔述、傅斯年等学者则认为不必拘泥于陈说,《鸱鸮》乃周公援引豳地风诗以明己志。今人曹胜高通过对考古资料的考察,指出鸱鸮是商族战神符号,《鸱鸮》是周族居豳所作而非周公所作,旨在表达对商族的不满。清华简《诗》类文献的争议集中在《芮良夫毖》的文本性质上,赵平安先生认,为从文本结构和韵文特征方面来看,《芮良夫毖》应属于《书》类文献而非《诗》类文献;陈鹏宇也主张应将《芮良夫毖》划归《书》类文献;李学勤、姚小鸥、马芳、马楠等学者则倾向于认为《芮良夫毖》属于“毖”体的《诗》类文献[9][10][11]。
综合来看,李守奎先生关于“诗类文献”的判断依据是较为中肯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记载了周公在成王即位典礼上所作毖诗四句和成王所作组诗九首,《芮良夫毖》记载了芮良夫所作毖诗两首,《耆夜》记载了周武王和周公在伐耆凯旋的饮至典礼上所作诗歌五首,《祝辞》收录了五首用于巫祝仪式的咒语诗歌。清华简中记录有《诗》文本内容和记载《诗》创作背景的《周公之琴舞》《耆夜》,从文体形式和用韵特征来看属于诗歌体裁的《芮良夫毖》《祝辞》,作为先秦楚地用于《诗》教的文本,都应当视为《诗》类文献。
二、清华简《诗》类文献的文本特征与思想倾向
与今本《诗》对比,除了作为楚地咒语诗的《祝辞》性质特殊外,清华简其它《诗》类文献表现出以下共同特征:首先,清华简中所收录诗篇的创作年代集中在从武王到厉王之前的西周时期,且以武王、成王时代之诗居多。其次,清华简中提及的诗篇除了《蟋蟀》《敬之》《鸱鸮》见于今本《诗经》,其它诸如《耆夜》所录《乐乐旨酒》《輶乘》《英英》《明明上帝》,《周公之琴舞》所录儆毖组诗,《芮良夫毖》所录毖诗,皆不见于传世文献。再次,清华简中的诗篇多具有典型的“乐诗”特征,如《周公之琴舞》记载周公和成王作诗时分别“琴舞九絉”,并云“元内启曰”“再启曰”“三启曰”“乱曰”,《耆夜》记载武王和周公作诗皆称“作歌一终”,《芮良夫毖》记载芮良夫“作毖再终”“絉”“启”“乱”“终”都是用于乐诗的乐章结构和演奏顺序的文本符号[12](P51-61)。此外,《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诗前皆有小序,《耆夜》篇首关于饮至典礼的背景介绍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乐乐旨酒》等五首组诗的小序,这与今本《诗》所传《毛诗序》的形式是很相似的,也说明了“诗序”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
清华简《诗》类文献与今本《诗》的最大差异在于保留了显著的“乐诗”特征,这一方面体现在《周公之琴舞》《耆夜》中的诗篇皆以组诗的样式出现,而今本《诗》皆为单篇而无组诗;另一方面体现在清华简中保留了“琴舞九絉”“启曰”“乱曰”等乐章演奏的原始符号,而今本《诗》没有这些原始特征。从《诗》教的发展历程来看,具有音乐性是早期《诗》的典型特征,清华简中的《诗》是服务于“乐教”的乐诗,儒家所传《诗》则是服务于“德教”而侧重于解读“诗义”的纯文本。徐正英先生认为,“将《周公之琴舞》视为先秦时期有代表性的一种《诗经》作品原始存在形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它代表的是“未经孔子删定整理过传至战国中期的一组《诗经》作品完整形态”[12](P52)。由此观之,清华简《诗》类文献是早于孔子编订“诗三百”之前的早期《诗》文本,其来源可能是西周时期用于礼乐仪式的周王室“乐教”之诗,并传播到楚地成为贵族教育的《诗》类教材。此外,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又见于今本《诗·唐风》,虽文句略有出入,但二者显然存在共同的文本来源;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的《敬之》也见于今本《诗·周颂》,且文句基本相同,这些证据都说明楚地用于贵族教育的《诗》选本与儒家所传《诗》选本必然存在共同的文献来源,应当都是源自春秋之前西周王室所编《诗》类文本①马银琴认为《诗》在西周至少经过周康王、周穆王、周宣王、周平王时期的四次结集整理,这一判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由此可以推断,西周时期官方每次对《诗》的大规模整理结集都必然形成不同版本的《诗》文本面貌。此后,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传播中,经过不同地域、不同授习传抄途径,逐渐形成内容各有差异、版本复杂多样的《诗》文本,但这些《诗》文本的主体内容都是来源于西周时期官方历次整理结集的《诗》。春秋时期楚地所传《诗》文本,同样来源于王室整理结集的《诗》文本。[13](P135-295)。
三、从清华简看楚地《诗》教的思想主旨及文化特征
《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说:“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且夫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节义以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可知春秋时期楚国已将《诗》教纳入贵族教育体系,并且高度重视《诗》的德育教化功能。申叔时把《诗》教的功能主旨概括为“耀明其志”“诵《诗》以辅相之”“德音以扬之”,这揭示了春秋时期《诗》教的三个功能:一是学习《诗》义以提升道德修养,树立远大理想;二是通过诵读《诗》文来辅佐君王以及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来发挥《诗》的政治交往功能;三是发挥《诗》乐的“乐教”功能。《礼记·乐记》:“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申叔时所说“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的功能与此一脉相承,即通过音乐和诗歌来陶冶培养人的性格情志。
清华简《诗》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国《诗》教所用教材,从文本的思想内容来看,基本延续了春秋时期楚《诗》教的教育主旨并加以深化扩展,其教育主旨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以《诗》儆戒”。《周公之琴舞》记载周公和成王在成王即位典礼上所作组诗,所表达的最核心内容就是“儆戒”。在周公仅存的半首“多士儆毖”中,告诫群臣“无悔享君,罔坠其孝”,说祀奉君王和祖先要无怨无悔,孝道不要中道废弃。成王组诗也多次强调“敬之”,不但诫勉群臣而且用以自警。《芮良夫毖》是芮良夫在国家危难之时儆戒君臣的一篇长诗,开篇就反复呼吁“敬之哉君子”,篇末再次强调要“畏哉”,通篇都是谆谆告诫君臣要齐心谋政的忧患之辞。《耆夜》记载饮至典礼上君臣饮酒庆功,前四首诗歌皆为赞颂贺词,周公最后所作《蟋蟀》充满了忧患意识,强调“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儆戒君臣要在胜利中保持清醒头脑。
二是“以《诗》明德”。“德育”是楚地《诗》教的核心主旨之一,作为《诗》教选本的清华简《诗》类文献凸显了这一主题。《周公之琴舞》组诗中“德”字直接出现4次,反复强调要“文非易帀”(修养文德不改易)、“弼敢荒德”(为政不敢废文德);《芮良夫毖》中“德”字共出现 8次,芮良夫将“德”与“刑”并举,警告说“不秉纯德,其度用失营”。《耆夜》记载周公所作《英英》诗云:“毖精谋猷,裕德乃救”,将战争的胜利归因于“德”。
三是“以《诗》达情”。抒发感情是诗的一项基本功能。从《楚辞》可以看出楚地《诗》学具有悠久的抒情传统,上博简《孔子诗论》记载孔子说“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强调诗乐的抒情功能。“以情解《诗》”也是《孔子诗论》的特征。上博简是战国晚期楚简,说明楚地《诗》学的抒情传统接受了儒家《诗》学的影响。清华简《耆夜》5篇诗歌主题都是抒发战争胜利的喜悦之情,《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以儆戒为主旨,同时也表达了深刻的忧患之情。《金縢》中周公遗成王以《鸱鸮》之诗,实际上是在表达对王室的忧患之情和自身的孤愤之情。
总体来看,“以《诗》儆戒”“以《诗》明德”“以《诗》达情”从三个不同层面强调了《诗》的德育功能和政教主旨,并将“德政”作为政治教育的核心加以凸显。《周公之琴舞》和《耆夜》中的诗歌还带有显著的乐诗特征,通过语音和语义的双重层面实现其教育功能,以“诗乐”陶冶情操和以“诗义”培养德行都属于楚地《诗》教之宗旨。
关于清华简墓主的身份,李学勤先生认为:“清华简的墓主人,可能是史官一类的人。”[14](P105)从清华简的内容来看,不排除墓主人是接受过系统教育的楚国贵族或专职从事贵族教育的师傅之官的可能性,清华简应该是楚国用于贵族教育的教材文本,虽然抄录年代约在战国中晚期,但从文本内容多为商、周史事来看,其编订成书年代应当远早于此,在楚国经过了漫长的抄写和流传过程,烙下了楚文化的印迹。学界一般认为楚文化起源于长江流域,在发展过程中也接受了中原文化和三苗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东夷文化等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①俞伟超先生认为:“楚文化应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某一支所发展起来的……楚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曾不断地受到周围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见俞氏《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及《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等相关论述。[15][16],清华简《楚居》也证实了先秦时期楚族早期活动范围主要在江汉流域。从文学形式上来看,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文体上受到了夏商古歌谣和商周所传《诗》的影响,作为楚地《诗》学的产物,清华简《诗》类文献中也保留了一些楚文化元素的特征。有学者关注到《周公之琴舞》与《楚辞》之间存在的关联,如李颖认为,《周公之琴舞》的“琴舞九絉”与《楚辞·九歌》等篇在采用的文体形式上同属“九体”,并通过考证指出“九体”源自夏代用于祭神礼仪的古歌《九歌》[17](P19-29)。汤漳平认为,屈原《九歌》是楚国王室祀典[18](P19-27);李炳海则认为,《九歌》蕴含有东夷文化的基因[19](P101-112),与《九歌》所用“九体”相类似,在传播过程中经过楚人编订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在文体形式上同样反映出楚地诗歌的文体特征要素。清华简《诗》类文献中还收录了具有典型楚地巫术特征的《祝辞》,当是楚地用于祝祷仪式上的歌辞。《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五祀”之祝祷仪式自春秋至汉代广泛流行于楚地[20](P95-101),上博简《鬼神之明》等出土文献也反映出战国时期楚地仍颇为盛行祝祷之术,《周公之琴舞》与《祝辞》同在清华简中出现,说明战国时期楚地《诗》教具有一定的巫祀性质,《诗》与巫祝歌谣同属于贵族教育的学习内容。
四、春秋战国时期楚地《诗》教的发展历程与态势
《国语·楚语》中申叔时提到的《诗》等典籍是春秋时期楚国贵族教材,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从内容来看,很可能都属于楚国贵族教材选本,可知楚地《诗》教渊源久远,而且选用教材的文本范围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与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环境和政治导向变化密切相关。从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来看,楚地《诗》发轫于西周时期的礼乐之教,成型于春秋时期的六经之教,在战国时期接受儒学影响转型为德政之教。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清华简《楚居》也记载了楚族先祖世系和居处迁徙。
在楚国建立之前,夏商之际的楚族被称为“荆楚”“蛮荆”或“楚蛮”。《商颂·殷武》:“维汝荆楚,居国南乡。”殷商时楚为南方方国。但胡厚宣先生认为楚族本来居于东夷,后来才迁往南方:“金文中伐楚伯在奄,而奄在鲁曲阜之地,知楚之必在东方也,……惟其后,东方民族多相率南迁,而楚民族势力甚强,及渐扩土于南方之江汉流域。”[21](P54)
楚族经过与江汉流域各部落不断融合,在商末周初正式建立楚国。相传楚族先祖鬻熊曾担任周文王之师,《史记·楚世家》:“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鬻熊在担任周文王之师的过程中必然接触到文王所藏典籍,西周时期楚国开始接受周王室的礼乐之道和诗书之教。《史记》记载“鬻熊子事文王”,当是指鬻熊受封子爵于文王,楚国正式作为诸侯国受封于周是在成王之时,鬻熊的曾孙熊绎是楚国的始封君。《史记·楚世家》记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王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可知楚君熊绎曾历事成王、康王两朝。郑玄《诗谱序》云:“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周公“制礼作乐”是在成王之时。据史书记载,成王在位期间,周公曾经因为流言而奔楚避祸。《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史记》虽未记载周公奔楚的细节,但熟知诗书礼乐的周公必然为楚国接受礼乐文化和《诗》的传播提供了契机。
春秋时期,楚国国势逐渐强盛,对中原渐生觊觎之心。《史记·周本纪》载:“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兵乃去。”楚庄王自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591年在位,在位期间选贤与能,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最终名列“春秋五霸”之一。春秋时期楚国不但在政治、军事方面取得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开始有意识地主动接受和学习周王室的《诗》《书》等“六经”之教,春秋时期流行赋《诗》之风,《诗》教已经转入“以《诗》为聘问歌咏之手段的时期”[13](P249),教育和培养政治外交人才成为楚地《诗》教的现实功用,也推动了楚地《诗》教的繁荣。《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楚国以“上国”自居,这种文化自信显然源自对礼乐文化的接受和掌握。
春秋时期楚国《诗》教不但有了经过初步编订整理的《诗》文本教材,根据楚国官制,还设置有大师、师、少师、傅、太傅、少傅等专门从事王室贵族教育的职官。春秋之际的时代风气和列国之间军事、文化的碰撞交流,也促进了楚国《诗》教的发展。一方面,“赋《诗》言志”成为春秋之际流行的外交辞令,据《左传》记载,楚国在外交聘问等场合引《诗》、赋《诗》的频次在列国之间居于前列,并且有其独特的用《诗》方法和体系①关于《左传》中记载楚人用《诗》情况的详细统计和相关讨论,可参看王清珍《〈左传〉中的楚人引〈诗〉》及毛振华《〈左传〉赋诗研究》等相关论述。[22][23],楚国贵族对《诗》的娴熟是楚国贵族长期接受《诗》教的必然结果,这也说明楚地《诗》教之盛。另一方面,楚国与诸侯之间的频繁战争,促进了《诗》《书》等典籍的传播和文化交流。王室史官以及诸侯国贵族逃难至楚国,更带来了周王室和列国典籍文化。《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又《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桓公之子七人,为七大夫于楚。”此外,孔子曾经游历楚地传播儒学,《庄子·达生》记载“仲尼适楚”,《孔子家语·致思》也记载“孔子之楚”,孔子及其弟子促进了《诗》和《诗》教在楚地的传播。据《孔子家语·好生》记载,孔子曾对楚庄王表示赞赏:“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匪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孔子对楚王的欣赏可能源自楚地对儒家学说和诗书之教的接受,儒学南渐和儒家对《诗》教的推崇,客观上促进了楚地《诗》教的发展繁荣。
战国时期,受时代环境影响,楚地《诗》教进一步转向以“德政”为核心的政教功能。德育原是周代贵族教育的核心内容,《诗》是承载德育功能的核心文本。《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周礼·地官司徒·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儒家通过对《诗》的整理编订进一步凸显其德育功能,受儒学影响,清华简《诗》类文献反映出楚地《诗》教具有明显的德育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战争更加频繁,强国武力兼并弱国的形势加剧,政治形势的变化必然在《诗》教等文化层面产生影响,春秋时期盛于一时的《诗》教至战国后期开始在列国呈现颓势。刘毓庆、郭万金写有《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一文,略云:战国乃《诗》学危急时代,危急来自两方面,一为时代对诗礼的排挤,二为诸子的反诗学思潮。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马银琴指出:“战国时代《诗》的传授在官府与民间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当《诗》的教习失去了带来现实政治利益的功效时,《诗》必然受到统治阶层的冷遇。与此同时,由于儒墨等私家学派的传习,《诗》在民间获得了较为广阔的空间。”[24](P4)将清华简《诗》《书》类文献之间的数量略作对比,也能略窥战国时期楚地《诗》《书》之教地位的升降趋势。清华简中《诗》类文献共4篇,合计约64支竹简;清华简《书》类文献共15篇,合计约221支竹简,无论是篇数还是简数,《书》类文献都远多于《诗》类文献。尽管清华简目前尚未全部整理完毕,据整理者介绍《诗》《书》类文献已公布殆尽,已公布的清华简《书》类文献规模整体上远胜于《诗》类文献,而且《诗》类文献还杂入了诸如《祝辞》这类巫祝歌谣,战国后期《诗》教在楚地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呈现下降趋势。春秋时期盛行的“赋《诗》言志”之风,至战国时期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失去外交辞令功能的《诗》在楚地贵族教育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战国时期列国注重武力和事功的政治导向不可避免地对《诗》教产生消极影响,《诗》教开始淡出官方视野转为主要通过民间诸子私学传播。与《诗》类文献相比,《书》类文献更具政治功用和指导现实的价值,清华简《书》类文献就保留了大量商、周时期的王室政治文书和重要历史档案,《书》中记载的历史成败经验能够为争霸天下的列国君主提供更多政治借鉴,在选用人才和治国牧民等方面也能够从中获得政治智慧,这就使得《书》教在楚地教育体系中相对《诗》教更受重视。从清华简可以看出战国后期楚地《诗》教之下降和《书》教的相对上升,这也映射出整个战国时代《诗》《书》之教的历史走向和传播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