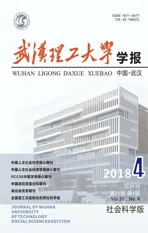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之灵魂与神的关系探析*
2018-03-03胡志刚
胡志刚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 广州 510053)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可以分为感觉灵魂和理性灵魂,人之所以是动物,在于和动物一样具有感觉灵魂,能够接受外在事物的刺激,形成对外部事物的认识。人有别于动物,是因为人具有理性灵魂,在他看来,理性灵魂可以划分为被动理性和主动理性,被动理性形成普遍的知识,主动理性虽有认识功能,但更多是要力求达成至善。感觉灵魂和被动理性与知识关联,区别在于从感觉灵魂中得到的知识不具有普遍性,被动理性能够形成可以被普遍传达的知识。主动理性是一种纯形式,能够进入永恒境地,并且能够认识神,神是不动的推动者,以自身为思考对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高的善是沉思,因而最好的生活是能够进行沉思的生活。
一、感性灵魂和理性灵魂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可分为两个部分,即感觉灵魂和理性灵魂。他说:“我们习以为常的措辞,‘我们生活(活着)而有所感觉’,这恰如另一措辞‘[我们活着而]有所识知’,都得有两个方面的命意:其一我们是在说[感觉或]知识,另一就在说灵魂(生命);我们所以[有感或]有知,就由于我们具有灵魂(有生),或由于我们[有感觉,或]有知识。”[1]92在他看来,灵魂使人类能够感觉和获得知识,认识有感性灵魂和理性灵魂两个来源,人的认识肇始于感性灵魂,如果没有感性灵魂对外在事物的刺激做出反应,认识就不能产生,感性认识以感觉、知觉、表象的形式保留住事物的刺激。感性灵魂就好比一块柔软的蜡块,事物的刺激如同外物刻印在蜡块上的痕迹,事物的形状、颜色、气味、硬度等属性分毫不差地被感性灵魂保留下来,对于认识产生的背后原因,感觉不得而知,它只是一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认识。亚里士多德把感性认识的形成机制形象地称之为蜡块说。感觉最根本的缺陷在于不能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不能满足对事物深层认识的需要。感性认识只能形成对外在事物的认识,认识往往因人而异。个别事物总在变化和生灭中,难以对个别事物进行定义,自然不能确定其本性。感性认识具有丰富性和生动性,却不具有普遍传达性。“可感觉的个别本体既不能有定义,也不会有证明,因为它们所具有的物质,其本性可以成‘是’,也可以不成为是。为此故,它们所成就的个体都是可灭坏的。”[2]174此外,感性无法对事物进行定义,对事物进行定义超出了感觉灵魂的能力范围,一旦涉及到界定或定义,就不再是感觉灵魂的领域,而进入了理性灵魂的范围。人寻求确定性,感性认识却不能满足此要求。感性灵魂给人留下了丰富多彩、形式各样的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材料,如果人满足于多样的感觉材料,只会使生活陷入混乱,无利于现实生活。感性认识还不能称之为知识,知识是理性灵魂导致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差异是这样的:操持感觉机能,着落之于一一个别(特殊)事物,知识乃为普遍性的表现。普遍性机能蕴在灵魂之内,所以其涵义与感觉的特殊性有别。这样,人们在任何时刻,都可自运其心识,操持理知,至于他的感觉功能则不然,这必须待之外物而后应用之以显示其所经验。既然可感觉事物全是各别的,外在的,我们于每一项目的感性‘知识’都得作如此相应的理解。”[1]106感性灵魂是对个别事物的认识,理性灵魂则是对普遍事物的认识。感性认识不具有普遍可传达性,不是认识的目的,只有普遍知识才是人奋力追求的目标。普遍知识具有抽象和一般的特性,它不源自感性灵魂,而来自理性灵魂。普遍知识是理性灵魂的追求,理性灵魂具有形成普遍知识的欲求,思维是理性灵魂的特征,通过思维能形成普遍必然的知识,理性灵魂内在包含着普遍概念的思维活动,能满足人类求知的意愿。
在《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把理性灵魂区分为被动理性和主动理性。对知识进行定义是被动理性的工作,被动理性和感性经验材料相关,被动理性赋予感性经验材料以形式,形成具有能够进行普遍传达的知识。定义对于普遍知识的成立至关重要,亚里士多德格外强调定义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能够进行定义的知识才能被普遍理解,才能确定事物的本质。他说:“我们必须注意到事物的怎是与其定义;若无定义,研究是徒劳的。”[2]134只有通过对事物进行定义,才能确定事物的特性,划定事物的范围从而作出区分。“定义之所以为人所重就在于它必有所指明;由名词组成的公式将所解释的事物划出了界限。”[2]91知识只有经过定义才能被言说和传达,定义确定了事物的本性,使知识能够被普遍传达,不再是个别的经验。定义直接和被动理性相关,被动理性通过定义对感性经验进行抽象概括,形成普遍知识。
亚里士多德说:“在作主体活动中的心识是‘(独立的)可分离的,不被动的,是单纯的(不含杂物的)’;主动要素总是优于被动要素,原因(本因与动因)总是高于物因(材料)。”[1]157主动理性由于比被动理性更纯粹,因而也更高贵和优越,同时,两者还具有内在的紧密性。罗斯对主动理性和被动理性的关系这样论述道:“主动理性所作用的是被动理性,被动理性是一种可塑物质,主动理性在它上面印记上可知对象的形式。”[3]165-166主动理性不具有感性性质,它以被动理性作为对象,是一种纯形式。被动理性是主动理性和感觉灵魂的中介,能够沉思本质和确定定义,使知识成为普遍可理解的形式。“主动理性已经认识所有可理解的对象,因此使本身具有潜能的被动理性可以现实地去认识,使可知物可以现实地被认知。”[3]166主动理性不掺杂任何经验成分,因而是永恒、不朽和神圣的。它是一种完全脱离质料的纯形式,可以完全摆脱人的身体而存在。身体是可灭坏的,主动理性却是不朽的,主动理性和人的身体无关,它是无质料的纯形式,如果主动理性依附于具有质料的身体,无疑是荒谬的。“我所称之为心识的这部分灵魂,(‘心识’这字,我的命意,专指灵魂中,思想,和由思想以成立信念的那个部分)在它从事于思想之前应无现实存在。所以,若说它是和合于躯体之中的某物,这就不通于理了。”[1]152-153被动理性不是纯形式,不能脱离身体存在,和身体共存亡,它没有完全摆脱感性色彩,是驳杂不纯和可灭坏的。“心识有时不考虑知识(不作理知活动),有时是全不活动(不行思想)的。心识,可是,只有在它‘分离了’以后,才显见其真实的存在。只有在这情况,它才是‘不死灭的,永恒的’。既然它不是被动体[而是主动体],所以它不作记忆[于以前的活动无所回想],作为被动体的心识,是要死灭的,而灵魂(理知灵魂)失去了被动心识就再不能思想(理解)任何事物(任何实用思想的外感客体)了。”[1]158被动理性的功能是概念思维,形成知识的基本原理和概念,如数学公理、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等。这些原理和概念都有其感性现实来源。被动理性和感觉、记忆和经验等感性认识存在关联,被动理性是不纯粹的,随着肉体的死亡,被动理性也跟着消失。理性灵魂中的主动部分却是不朽的,它可以超越生死而参与神业。
亚里士多德认为,主动理性和被动理性同属于理性,它们曾经一度结合在一起,由于肉体的死亡,被动理性和主动理性发生了分离,被动理性灭坏了,而主动理性继续存活。亚里士多德强调,主动理性能够完全脱离肉体,不含有未实现的潜能,以概念和自身为沉思对象。罗斯指出:“当被动理性还仅仅是潜在的认识时,主动理性是现实地认识。显然,这意味着尽管主动理性在灵魂之中,却超出个人范围;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说,主动理性对所有个人都是同一的。”[3]167亚里士多德认为,当被动理性和主动理性发生分离,不生不死的主动理性进入了永恒境地。主动理性不受现实状况的影响,它的认识不带有时空的痕迹,因而主动理性具有神性色彩。“它们(生物界)不能托自己的存在之延长,参预[宇宙的]永恒与神业,它们既是可灭坏的事物,这就不能以其数为一而相同的个体,以入于永恒,于个体而论,它们自己的存在虽或较长,或较短,却终是要灭坏的;它们企图进到永恒而参与神业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只有期之于与已有形式相类同的嗣承个体,这样的类同个体,当然不能其数为一,但在品种上确乎为同一。”[1]97-98理性灵魂以抽象的普遍事物为对象,是一种形式实体,是品种上的同一,而不是实存实体的多。
二、主动理性和神思
主动理性以被动理性形成的原理和概念为认识对象,也以自身为认识对象,它完全摆脱了感性和肉体的束缚,主动理性以自身为思维对象,实现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主动理性是一种理智之光,它使潜在于灵魂中的普遍原理成为现实的知识,作为一种“纯形式”的理智之光,它能使人领受到神的意图和愿望。神和主动理性都是一种无人身的“纯形式”, 亚里士多德对于主动理性的理解,和其在《形而上学》中对潜能和现实的理解存在逻辑一致性。在《论灵魂》中,他说:“知识与感觉两者对于其相应客体的关系,各分为潜在与现实两项,潜在的对应于潜在物,现实的对应于现实物。在灵魂的内部,知识机能和感觉机能,潜在地就得是各与相符的客体,知识合于可识知物,感觉合于可感觉物。”[1]166他认为认识的潜能和现实与客体的潜能和现实关系是一致的,这使得它的认识论和其本体论内在统一起来。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潜能和现实相互转化的结果使得宇宙成为一个等级分明的整体,处于等级底部的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质料,纯质料在潜能的驱使下,使自身拥有形式,成为一个包含质料和形式的个别事物。在宇宙整体中,低级事物成为高级事物的质料,高级事物成为低级事物致力于实现的形式,宇宙整体的最高点是纯形式的“神”。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神,黑格尔有一个精确的评价,他说:“神是纯粹的活动性,是那自在自为的东西;神不需要任何质料”[4]310。神是绝对的实体,是一种永恒且纯粹的活动性。神是一种纯形式,黑格尔说:“‘这个最高的实体并且是没有质料的;’因为质料作为质料乃是被设定为被动者,变化就发生在它身上,因此它并非直接地(简直)就是与纯粹的、本质的活动性相同。”[4]311正是由于神没有质料,它才成为纯粹的现实性,如果神还存留有质料,那它就具有还未实现的可能性,这和神的纯形式的本质是不相容的。从亚里士多德对宇宙起源的解释可以清楚看出其注重形式的倾向。形式是质料努力趋向的方向,纯形式的“神”成了万事万物的目的,宇宙论具有了某种目的。亚里士多德对“神”的理解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基督教的上帝,当然,亚里士多德的“神”的能力和上帝相比还具有相当大的距离,“神”不是全能的,而上帝是全能的。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神与上帝的区别,汪子嵩先生曾这样评价道:“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个‘神’,不是宗教的神,而是哲学的神。”[5]亚里士多德承认无任何规定性的质料的存在,并认为这种纯质料是宇宙形成的物质根基,它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却是永恒存在的。
主动理性和神皆是无人身的理性,都不具有“无中生有”的能力。罗斯对亚里士多德的主动理性有一个精确的评价,他说:“主动的理性不是从无创造的理性。”[3]164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中,神不能从“无”中创造出宇宙来,纯质料不是神的创造物。上帝能从“无”中创造出宇宙来,宇宙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创造,上帝是创世主。亚里士多德对“神”的理解和基督教对上帝的理解,充分表明了哲学和宗教之间的区别,哲学家再大胆也无法相信从“无”的世界中能创造出“有”来,“无中生有”对亚里士多德而言绝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哲学需要进行逻辑论证和理性推理,它不求助于狂热的信仰。正如康德所说:“在哲学的所有学科中,尤其是在形而上学中,任何一种能够进行的解析也都是必要的,因为无论是认识的明晰性还是可靠结论的可能性都取决于此。”[6]哲学对于宇宙产生的解释力度不如宗教,哲学的每一个前提都是不确定的,需要去不断寻求确定的理论前提;宗教的基本前提是确定的和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世界是上帝的造物。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神和基督教的上帝的区别,罗素说:“当柏拉图论及创世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由上帝赋予形相的原始物质;而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看法。他们所说的上帝,与其说是造物者不如说是一个设计师或建筑师。他们认为物质实体是永远的不是被造的;只有形相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与此见解相反,圣奥古斯丁像所有正统基督徒所必须主张的那样,主张世界不是从任何物质中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上帝创造了物质实体,他不仅仅是进行了整顿和安排。”[7]448西塞罗对纯质料有这样的论述,他说:“作为万物之源的物质实体不大可能是由神意创造的。这个物质的实体始终拥有一种自身的力量和本性。”[8]亚里士多德的神和基督教的上帝之间的差别,通过奥古斯丁关于上帝的描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奥古斯丁说,上帝是“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使骄傲者不自知地走向衰亡’;行而不息,晏然常寂,总持万机,而一无所需;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虽万物皆备,而仍不弃置。”[9]在基督教中,上帝是一种全知全能全善的化身,能从“无”中创造出世界来。
罗斯看到了《论灵魂》中的主动理性和《形而上学》中的神的一致性,他说:“上帝若是在《论灵魂》中作为内在于个体中的表象,则与它在《形而上学》中作为超验的‘他’的表象不一定不一致”[3]169对于《论灵魂》中内在于个体的主动理性和《形而上学》中的超验的神的关系,巴恩斯的这段论述很好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他说:“人区别于动物在于他拥有理性和思维的能力。人身上‘包含有神圣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智力的东西是神圣的’,并且我们的智力是‘内在于我们的神圣的东西’,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智力的人,因为这是我们至高无上的、最好的元素’。”[10]124主动理性和上帝实质上是一致的,却不意味着主动理性就是神。神和主动理性都能使潜在的认识对象成为现实的认识,使得对一切事物都成为可被理解的东西。神具有使潜在的事物成为现实的事物的能力,主动理性却不具备,主动理性只是一种认识能力,而不是实现事物的能力。此外,主动理性作为一种理智之光是神把它注入到人身中去的,神从来就不在身体之中,主动理性和神比较而言,神是第一性的,主动理性是第二性的。主动理性是人身上最神圣的东西,因而能感而遂通达于神。神是导致万物产生和消灭的原因和动力,是世界的终极目的。主动理性以被动理性为认识对象,其认识有善恶和真假之别,神超越真假和善恶,神本身即善,神以自身即以善为认识对象,所以神思自始至终是善。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神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神,它不高居于人类之上,也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人格神。亚里士多德把神理解为一种理性,也就是努斯,神不像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它是一种“纯形式”,不具有任何质料,世间的事物都是形式和质料的结合体。神不被质料所阻碍,它是完全能动的,既没有产生,也没有消灭,永恒如此,无始无终。它没有潜能,纯粹是一个现实,而现实中的事物由于潜能和现实的相互转化而生灭变化。世间万物都是外在原因导致的,神是努斯,它本身是能动的,它是自身的原因和动力,也是世间一切事物的原因和动力。神不动,却能推动万物,它是“不动的推动者”。它不在时间和空间中,时空只能用以说明现实事物。神是不动的,如果它运动的话,就会一会在此一会在彼,那么它就是处在空间中的,也就是说它具有质料,这和它的“纯形式”是矛盾的。如果神占据空间,它就是有限的,但神不可能是有限的,它必须无限,只有它才能使事物产生消灭,它力量无限。它又是超时间的,如果它在时间内,那么它本身就是被产生出来,它就不能化生万物。它以自身为认识对象,对自身的认识不能以真假来衡量,对它自身的认识超出真假之外,真假判断只适合于现实事物。它和它的思想本身是同一的,它是现实事物都趋向的最高目的,它本身就是善,对它的认识也就是对善的认识。亚里士多德的神,是自然的内在动力,是一种纯粹思想。神思只是对它自身的思,是一种纯粹对善的思。
三、神思与善
亚里士多德说:“宇宙间总该有一原动者,自己不动,而使一切动变事物入于动变。”[2]93神被他看成是一个不动的推动者,神自身不动,却推动世界万物。对于不动的推动者,有学者这样分析道:“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如果所有本体都是可变灭的,那么一切事物就是可变灭的,因为本体是基本存在;第二个前提是,时间和运动不可能既存在,又停止存在。这说明,有些东西是不变灭的。因此,必定存在着一个不变灭的本体。”[11]78这个不变灭的本体是纯形式,它没有一丝一毫的潜能,是纯粹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只能存在于纯粹的精神活动中,不处于现实的活动中,它是不动的推动者。“说不动的推动者的本质是纯粹现实性,这意味着什么呢?要成为完全现实的,永恒本体必须没有任何潜在的性质,它必须是纯粹活动。这种活动不可能是物理的,因为所有物质事物都是可变的,而不动的推动者必须是永恒本体。因此,它的现实性必定在于纯粹的精神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唯一可能的无变化的精神活动就是纯粹思想或沉思。”[11]79不动的推动者只是以自身为思考对象,是一种纯粹的沉思,他以精神活动推动世界的运作。不动的推动者本质上是善的。“亚里士多德开始称这个永恒本体为‘神’。因为他的本质是善,神的永恒思想必须被引向至善。至善就是他自身。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并不是说,神思考正在思考自身的他自身……也许,这个观念是说,对神来说,思想的对象和思想本身没有区别。神的思想不可能和它所思想的事物的存在分开。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神圣沉思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因为它牵涉到他关于人类本性的见解。”[11]80不动的推动者最大的特点在于对自身的神圣沉思,正是因为神圣沉思,他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两者之间呈现出了一定的关联,而不是两种不相干的学说,正是神圣沉思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伦理学有了共同的目的。罗素也觉察到了这种关联,他说:“他(指亚里士多德——引者注)的实践伦理学大部分的确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哲学性,只不过是观察人事的结果罢了;然而他的学说中的一部分尽管可以独立于他的形而上学之外,却并不是与他的形而上学不一致的。”[7]234正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主动理性具有神圣和永恒的特点,这种沉思的主动理性在其伦理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人生最大的快乐是幸福,幸福是人应当致力追求的最高目标,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内心的宁静,这种宁静是神圣沉思导致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神的描述可以作为其德性伦理学的一种论证。他的德性伦理学把幸福当成是最高的善,善的特性是神圣的沉思,在神思中,善与幸福合二为一,达到了完美结合。“是以思想(理性)所涵若云容受神明,毋宁谓秉持神明,故默想(神思)为唯一胜业,其为乐与为善,达到了最高境界。”[2]275-276神成为了人获得幸福和善的最终根据,正是因为人具有主动理性,才使得人有可能超凡入圣,进入永恒境界。“生命本为理性之实现,而为此实现者惟神;神之自性实现即至善而永恒之生命。因此,我们说神是一个至善而永生的实是,所以生命与无尽延续以至于永恒的时空悉属于神;这就是神。”[2]276主动理性灵魂能在人身死灭的顷刻,脱离尸骸,还入宇宙而得自由常在,也就是进入了圣域,与神为一,这就是至福。
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灵魂的论述和其在《论灵魂》中对灵魂的划分类似。在《论灵魂》中,他认为人同动物一样具有感性灵魂;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同样认为人和其他生命一样,共同具有一个无逻各斯的德性部分。“在无逻各斯的部分,又有一个子部分是普遍享有的、植物性的。我指的是造成营养和生长的那个部分,我们必须假定灵魂的这种力量存在于从胚胎到发育充分的事物的所有生命物中。这比假定后者中存在一种不同的能力更合理些。这种能力的德性是所有生物共有的,而不为人所独有。”[12]33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营养和生长这种无逻各斯的德性是所有生物都具备的。此外,除了营养和生长以外,人和动物都具有欲望,欲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也是无逻各斯的,相对于营养和生长的无逻各斯而言层次更高。“灵魂的无逻各斯的部分还有另一个因素,它虽然是无逻各斯的,却在某种意义上分有逻各斯。因为我们既在自制者中、也在不能自制者中称赞他们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这个部分促使他们做正确的事和追求最好的东西”[12]33正是由于欲望的驱动,生物才意欲生殖和繁衍,在人而言,欲望不仅是繁衍的内在驱动力,还是文明的驱动力,在欲望的驱使下,人才能致力于某种目标,去从事某种达成自身的活动,这样才导致文明的产生和形成。营养、生长、欲望这些无逻各斯的德性,是人同其他生物共享的,并没有把人同其他生物区分开来。对于理性灵魂、感性灵魂和无逻各斯德性之间的关系,巴恩斯有这样的论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思维需要想象力并由此需要感知力;因此,任何能思维的生物必然能够感知。感知力从未独立于生命的第一本能,即获取营养和繁衍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各种各样的能力或者说灵魂的不同官能形成了一个等级体系。”[10]105正如人是理性的动物一样,人也是一种知善恶的动物,这种善的依据不在于身体层面,而在于灵魂层面。“人的善我们指的是灵魂的而不是身体的善。人的幸福我们指的是灵魂的一种活动”[12]32,幸福是一种善,和人的灵魂密切相关,善是理性的进一步推演,灵魂中的善成为了人和其他生物的区别。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把理性灵魂分为主动理性和被动理性,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也采取了相似的区分方法,把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灵魂的逻各斯的部分就是分为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是在严格意义上具有逻各斯,另一个部分则是在像听从父亲那样听从逻各斯的意义上分有逻各斯。德性的区分也是同灵魂的划分相应的。因为我们把一部分德性称为理智德性,把另一些称为道德德性。智慧、理解和明智是理智德性,慷慨与节制是道德德性。”[12]34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两种德性中,理智德性高于道德德性,因为理智德性关乎智慧,是一种努斯和沉思,是最具神性的东西,正是沉思实现了德性,构成了完善的幸福。“我们身上的这个天然的主宰者,这个能思想高尚[高贵]的、神性的事物的部分,不论它是努斯还是别的什么,也不论它自身也是神性的还是在我们身上是最具神性的东西,正是它的合于它自身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构成了完善的幸福。而这种实现活动,如已说过的,也就是沉思。”[12]305努斯是一种精神性活动,是一种神圣的沉思,是人所拥有的最好和最高贵的东西,沉思的生活是最具神性的生活,也是最幸福的生活,它是德性的最高目标。“如果努斯是与人的东西不同的神性的东西,这种生活就是与人的生活不同的神性的生活。”[12]307此外,“属于一种存在自身的东西就对于它最好、最愉悦。同样,合于努斯的生活对于人是最好、最愉悦的,因为努斯最属于人。所以说,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12]308由于神圣沉思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连为一体,在精神实质上贯通起来。正如罗素所言:“他(指亚里士多德——引者注)只是相信就人有理性而论,他们便分享着神圣的东西,而神圣的东西才是不朽的。人是可以增加自己天性中的神圣的成分的,并且这样做就是最高的德行了。”[7]220罗素把握到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内在关联。“神是永恒活动的象征,思辨活动是永恒活动的表现。人通过思辨获得永恒的过程是最神圣的活动,所以当人能够追求永恒的时候,就能将自己与自然界永恒的理智结构融合为一。在思辨活动中,人和神得到了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二者得到了统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说亚里士多德的神是人的灵魂的理论理性活动的大写。”[13]沉思是人身上最好的部分,因而应当去寻求与之相应的生活,在所有物种中,唯有人才能进行沉思,正是沉思活动,人能努力追求不朽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如此推崇沉思,是因为沉思实现了人与神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的根基在于沉思活动能实现人和神的善,人在对于善的追求中,达到了与神共在的境况。“沉思似乎是惟一因其自身故而被人们喜爱的活动。”[12]306沉思是人类活动的最好方式,它具有神性。
汤因比曾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为一种强大而深入人心的思想工具,延缓了希腊社会的瓦解,并且有力地影响了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西方直到17世纪才从亚里士多德的魅力中解脱出来,这几乎已经是亚里士多德时代的两千年之后。”[14]可以说,即使到了18、19世纪,西方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神学思想和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就存在直接的影响。对于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和神关系的探讨,涉及到如何理解希腊哲学、基督教思想、启蒙运动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内在的精神关联,同时关乎西方哲学的内在演变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