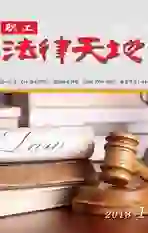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之主体研究
2018-03-01付洋郑晓虹李锦宏
付洋 郑晓虹 李锦宏
摘 要:近日新公布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稿》第777条规范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制度,该条款明确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制度的理论基础——近亲属权益保护,而此前,我国对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一直依赖于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法院对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究竟应采用何种理论基础也是摇摆不定,而征求意见稿第777条似有结束理论争议的局面。该条的保护范围包括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权益,由此可以看出其将死者人格精神利益和人格财产利益进行了统一规范。这样的规范方式在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理论支持?其次,该条款与《民法总则》第185条在适用伤存在重叠,为了保证民法体系的自洽性,建议将草案第777条进一步细化,将现有对英雄烈士特殊人格利益的保护与草案777条普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进行统一规范,对于《民法总则》第185条可以在民法典进行统编的时候予以删除。
关键词:死者人格利益;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近亲属权益保护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已于近日意见征求完毕,草案的公布意味着我国民法典的编撰又迈进了一大步,其中草案人格权编第777条很是显目,对于该条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对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到底应当采取何种理论基础?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与死者人格财产利益保护规则如何进行构架且理论基础是否一致?其中《民法总则》第185条与意见稿第777条的关系如何?接下来文章也将围绕着这几个问题展开。笔者对该条款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仍然需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对此我们应该从立法论的角度回归到解释论的角度,对该条文的适用与理解进行体系化阐释。
一、结合《意见稿(草案)》第777条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争议进行评析
1.学术界与理论界历来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争议
就死者权利保护而言,权利的存在是以主体的存在为前提,当主体消灭时,其身前所享有的权利也会随之消灭,人格权也不例外,否则将会与现行的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我国《民法总则》第13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为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甚至会动摇传统民法权利构造的制度基础——主体制度和权力能力制度。由此引出死者人格权是否能够获得保护,如果能获得保护,那么保护的是死者的人格权还是人格利益?《意见稿(草案)》777条:“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和父母的,其他近亲属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文意解释,该条款的用语是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字眼而不是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由此可见该条保护的是死者的人格利益而不是人格权。
1989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依法受保护的复函》:“吉文贞(艺名荷花女)死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母陈秀琴亦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1990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名誉权一案有关诉讼程序的复函》:“海灯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作为海灯的养子,范应莲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均是采取死者人格权利保护保护说作为其理论依据。
2017年通过立法的方式在《民法总则》第185采取公共利益保护说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加以规制,而今《意见稿(草案)》亦打算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该条草案采取是近亲属权益保护说。笔者认为无论采取何种学说对此问题进行规制,只要能在逻辑上、体系上做到周延二字即可。
2.对各家学说进行体系上的评析
死者权利保护说主张:自然人死亡之后,仍然可以继续享有人身权。该学说存在两大障碍,第一,该种学说主张的最大障碍在于其与现行法律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其基本上否定了我国已经采用并被民法学界所接受的主体制度和权利能力制度;第二,该学说无法解释既然自然人在其死亡之后仍然享有权利但却同時发生了继承法的继承。该学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会带来一系列在现行制度框架下无法消化的问题,如果以后相关法律的修改采取该种学说,这就难免要在现行的民法理论内“大动干戈”——修改民事权利定义,或者干脆直接废除这个概念,从而避免矛盾,而且还要调整好与继承法的制度衔接关系。
对于死者法益保护说而言,该学说同样也没有能够解决主体缺位的问题。法益和权利一样,利益总是以主体为依托,其表现的总是一定主体的利益。人因生命终止而丧失主体资格,不能再享有权利,亦不能再享有利益,因此,无论是死者的人格权还是死者的人格利益,都缺少承载的主体。
3.《意见稿》第777条的基本解读
该条在理论基础上采取了学界的主流观点,解决了主题问题,但是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以待在草案进行审议时有待改进;第一,该条只能顺利解决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护的问题,对于死者人格财产利益的保护缺乏法理上的依据,因为我过相关法律尚未明确权益的可继承性;第二,该条最大的限制在于:“通过对近亲属权力的保护间接的保护死者人格上的利益免受侵害,但是当该死者无近亲属时该法条则无用武之地,但死者的近亲属不愿意主张权利时,对于死者人格上的利益又该如何保护,该法条亦没有进行规制,最后,如果对近亲属不加层次化限缩,势必会造成滥诉等问题。”;第三,该条与《民法总则》第185条对特殊死者权益保护的规制属于一般与特殊的问题,在法律的适用上无需进行人为的割裂,完全可以对其进行统一的规制。
二、对《意见稿(草案)》完善的相关意见
根据我国历来的司法解释的态度转变以及学界的主流观点,我国在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属于一元论的范畴,但我一元论的有别于德国,德国的一元论采用直接保护的方式,而我国的立法更加倾向于间接保护的方式。虽然制度的构造方式不同,但是德国的立法对我国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完善有极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