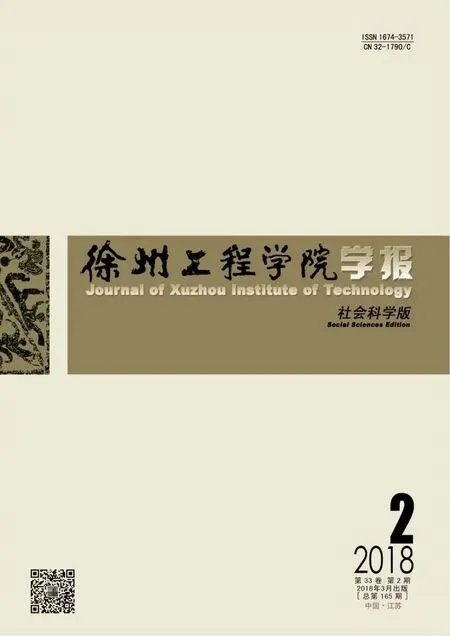方立天先生的华严学研究
2018-02-27韩焕忠
韩焕忠
(苏州大学 宗教研究所,江苏 苏州 215123)
作为当代著名的佛教研究专家,方立天先生对中国佛教华严宗有着非常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内容涉及经典校释、祖师传论、义理阐发、现代价值等多个方面。
方立天先生(1933-2014年),原籍浙江永康四路口中村。方先生晚年著《跬步记述》,概述其一生履历云:幼时沉静少言,喜好读书,但因日寇侵略,读小学时只能时断时续,1946年进入永康县立初中,三年后初中毕业,本欲投考浙江省立杭州高中,但因耽误入场而被取消了考试资格,1950年春进入上海华东税务学校(后更名为华东财政学校)学习,随后留校工作,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喜欢中国哲学,深受冯友兰、张岱年等人的影响;196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哲学为学术研究重点,为此曾到中国佛学院进修8个多月,虚心问学于周叔迦居士、法尊法师、正果法师、明真法师、观空法师、虞愚教授等人;返回中国人民大学之后,陆续撰写了《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等多篇论文在《新建设》《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不久因参加“四清”和爆发“文革”而被迫中断佛教研究十余年,直到1978年之后才得以继续,相继出版了《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华严金师子章校释》《慧远及其佛学思想》《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册)等多部著作,以及带有结集性质的《方立天文集》(十卷十二册),在教界和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244-259。方先生诸多佛学研究著作的发行量十分巨大,虽经一版再版,依然畅销不衰,这在学术著作向来滞销的中国图书市场上堪称奇迹。
方先生对华严学的研究虽然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但还没有形成比较全面的总结和概括,而十卷本《方立天文集》的出版则为弥补这一缺憾提供了便利。
一、经典校释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经典的校释和解读主要体现在《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和《华严金师子章今译》上。
《华严金师子章》是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贤首法藏大师为女皇武则天讲说新译《华严经》义理的记录,言简意赅,文约义丰,因此深受历代华严学者的重视。“藏为则天讲新《华严经》,至天帝网义、十重玄门、海印三昧门、六相和合义门、普眼境界门,此诸义章,皆是华严总别义网。帝于此茫然未决,藏乃指镇殿金狮子为喻,因撰义门,径捷易解,号《金师子章》,列十门总别之相,帝遂开悟其旨。”[2]732百余年后,新罗崔致远为法藏大师立传,仍对这部讲章赞不绝口:“此作也,搜奇丽水之珍,演妙祇林之宝。数幅该义,十音成章。疑观奋吼于狻猊,胜获赆琛于鹅雁。虽云远取诸物,实乃近取诸身。以颔下之光,为掌中之宝。则彼玉龙子之实玩,岂如金师子之虚求?启沃有余,古今无比。”[2]283因此《金师子章》自问世以来,弘讲传习,颇不乏人,古之注疏流传至今者,犹有五台承迁、晋水净源及日本景雅、高辨四家。
方立天先生所著《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堪称古今中外有关《金师子章》注解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部著作不仅运用了五台承迁《华严金师子章注》、晋水净源《金师子章云间类解》、日僧景雅《金师子章勘文》与高辨《金师子章光显钞》校订文字,诠释文义,而且还撰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华严金师子章评述》置于文前,收录历代有关法藏的传记及承迁、净源、高辨等的序文、题解、缘起及三人生平等十多篇资料附于文末。《评述》系统地介绍了《金师子章》的成书过程,深入地剖析了《金师子章》的思辨逻辑,从现象与本体、现象与现象、现象与主体三个层次阐释了《金师子章》的核心观念“无尽缘起”的复杂内涵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深远影响。该书出版之后,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亲自撰写书评,称赞该书《评述》“更有助于读者深入地了解这篇讲话(笔者按,指《金师子章》)的内容和意义”[3]29。这部著作后来成为中国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铂净法师将《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一书视为体现“方立天先生是较系统研究华严宗哲学的学者”的学术成果,认为“作者在书前的‘华严金师子章评述’中,对华严宗的学说及其实际创始人法藏的事迹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解说,详细地分析了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说’‘六相’‘十玄门’等的各种圆融的特点,尤其是从社会根源上考察了华严宗的产生与理论渊源,指出了它的社会意义和深远影响”[4]366。此后凡研究《金师子章》、贤首法藏及中国华严宗的著作,几乎都将《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列为参考文献。
方立天先生所著《华严金师子章今译》是《华严金师子章校释》的姊妹篇。在方先生看来,做好佛教文献的整理工作(包括对佛教文献的“校释”和“今译”),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就对方先生而言,他在《跬步记述》中指出,这“是一种良好的专业训练,在切实把握佛教思想方面,对我产生了重要的持久的作用”[1]253;就对他人而言,“今后能读古籍和肯读古籍的人会日益减少,因此古籍今译就显得更为迫切。古籍的今译如何保存原作的意味,是一大难题。应当承认,古籍经过翻译以后,是比较难以保存原作的语感与情味的,我们应当尽量做到符合原作的本义。我在《华严金师子章今译》一书中,力求使译文的意思与原文一致,力求语句通顺,以争取达到译文准确地表述原作的内容和有助于人们读懂原著的目的”[1]254。笔者在方先生门下求学时,曾多次听到方先生以《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和《华严金师子章今译》为例“现身说法”,引导弟子们进行深入细致的经典阅读和文本分析,以便在论文中避免讲一些没有经典依据的套话和空话。
《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和《华严金师子章今译》既是方立天先生研究华严宗的重要学术成果,也是方先生重视古籍整理和经典校释的集中体现。从这些成果中可以体会出方先生著述资料扎实、论证充分的奥秘之所在。
二、祖师传论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祖师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应傅伟勋和韦政通两位教授的邀请为“世界哲学家丛书”所撰写的《法藏》一书上。
《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在为中国古籍整理提供典范的同时,也奠定了方立天先生作为中国佛学界华严宗研究专家的学术声誉。当远在美国的傅伟勋和韦政通两位教授策划“世界哲学家丛书”时,方先生就成了为《华严金师子章》的作者即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法藏撰写传记的最佳人选。而方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确定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交叉结合、互动互补”的学术思路。在他看来,“一部佛教史就是佛教代表人物和广大信徒的信仰修持史,一部佛教思想史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成果史。研究历史上的佛教代表人物,就能展示佛教尤其是佛教思想演变、发展的途径和内容”[1]3。正是基于这一思路的指引,方先生曾经对道安、支道林、慧远、僧肇、道生、梁武帝萧衍等中国佛教的代表人物进行深入地研究。方先生接受了傅伟勋教授的盛情相邀,他在为《法藏》一书所写的《自序》中指出,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优秀哲学走向世界,也有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岸学者的同胞情谊”,因此他就“十分愉快地接受和承担撰写《法藏》的任务”[1]3。由此也促成了方先生又一部华严学研究重要成果的问世。
《法藏》是运用现代学术范式对华严宗祖师法藏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重要著作。全书共设九章,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法藏的生平与其创宗活动”及第二章“法藏创宗的社会背景和学说渊源”,叙述了法藏的身世、师承、出家、译经、著述、讲学、弘法、培养弟子及创建华严寺等情况,从唐代大一统政治局面、武则天大力支持、寺院经济雄厚、佛教自主性提高、《华严经》的流传及中国佛教进入创宗时期等多个方面分析了法藏实际创立华严宗的复杂背景。第二部分即第三章“佛教义理史观——判教论”,方先生“认为判教论是一种佛教文献次第观、佛教义理深浅观和佛教派别优劣观,并就法藏先前的判教诸说、法藏判教的具体内容(五教、十宗、同别二教和本末二教)、哲学意义、贡献与缺陷,尽力作出平实的叙述和论说”[1]4。对(华严宗的)判教学说给以如此的重视,这在中国佛教研究历史上实为首次,后来笔者撰写《华严判教论》的专书,即是深受方先生相关思想的启发和影响。第三部分包括第四章“法藏的宇宙观——法界缘起论的原由”、第五章“法藏的宇宙圆融论——法界缘起论的内容”、第六章“法藏的宇宙本体论——法界缘起论的本质”、第七章“法藏的人生理想论——行果论”、第八章“法藏的认识论——法界观、唯识观和还原观”,以“法界观”为核心对法藏思想展开了深入地论述,并充分照顾到这一思想体系的宗教实践品格。第四部分即第九章“法藏的思想影响和历史地位”,是对全书内容的总结。方先生认为,“法藏是唐代佛教华严宗的真正创始人、佛学家、翻译家、哲学家、宗教和社会活动家、书法家。……他的宗教活动和学术思想对当时与后世的社会生活、宗教理论,乃至文化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在佛教史上,法藏对于《华严经》思想的发展、判教和修行实践都带来了冲击、推动、分歧、变化,对于天台、唯识和禅诸宗的关系,也带来了正负的作用,并且推动了朝鲜和日本的华严宗的创立和发展。在哲学史上,主要是以独特的现象论、本体论、人生理想论、心性论和认识论,丰富了古代哲学思想的宝库,并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推动作用”[1]181。此处对法藏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又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的。
方立天先生在撰写《法藏》时对学术性和思想性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对于学术性,方先生“充分运用法藏的历史事迹和基本著作来加以描述性的介绍,并着重运用现代语言加以清晰的说明,以求客观而全面地论述法藏的生平业绩、哲学内容、思想作用和历史地位”[1]5。对于思想性,方先生“特别重视阐发法藏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和思想的哲学意义,剖析其所含的哲学思想内涵,总结其思维方式的类型和特征,并适当地与当代某些相关学说,如一般系统论、宇宙全息统一论等加以比观评价,从而力求呈现出法藏哲学思想的真实面貌、基本特征和时代意义”[1]5。这应是佛学界对于祖师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法藏》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在论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学研究的重大成就时,邱高兴指出,“方立天教授著有《法藏》一书,对法藏的生平与思想作了全面的研究”[5]25。对此书的学术地位作出了中肯的评价。此书的繁体字版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于1991年出版,简体字版则更名为《法藏评传》由北京京华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此后海峡两岸佛学界的学者凡论及法藏者,往往将方先生此书列为重要参考文献,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永革先生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丛书》所撰写的《法藏评传》一书所列参考书目中,在所列诸多方立天先生的著作中,就同时含有此书的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6]501。
三、义理阐发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思想有着精深的研究和准确的把握,其研究的范围涉及中国佛教思想的各个方面,因此他不仅在《华严金师子章校释》《法藏》等著述中对华严宗思想有着专门的阐发,而且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等著作中将华严宗义理置于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整体发展历史中进行考察和诠释。
《中国古代哲学》一书的原名为《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1990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分上、下两册,后来编入《方立天文集》时改为今名,是方立天先生运用“问题解析体”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而形成的一部专著。在“中国古代本体论”一章中,方先生指出,“法藏宣传理事无碍的学说,其宗教意义在于调和佛教内部各个宗派、各种修习方法和修习次第的关系,它们各自作为佛教整体的一部分而互相融通无碍;还在于宣扬世间和出世间、世俗世界和佛国世界是相即相入、无障无碍的。其社会意义则在于说明现实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美好的,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都是和谐协调,无矛盾、无斗争的”[1]80。宗密“站在中国佛教华严宗的立场,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印度佛教哲学所作的总结性批判,体现了中国佛教哲学的理论特色”[1]84。在“中国古代时空观”一章中,方先生认为,“法藏的时空观,承认大和小、远和近的相对性”,因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法藏空间理论的宗教实质是,论证虚构的佛国世界和现实的世俗世界是无矛盾的,相即相入的,给人一种可望又可即的精神满足,从而争取更多的佛教信徒,扩大佛教阵地”[1]129。在“中国古代矛盾观”中,方先生指出,“从理论思维角度来看,法藏的宗教哲学涉及现象与现象的矛盾,以及整体和部分、同一和差别、生成与坏灭的矛盾。应当承认,它已触及矛盾的统一性,其中也包含了比较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在中国古代辩证法史和古代范畴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地位”[1]210。方先生此书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写成的,那时在哲学思想研究领域仍然盛行唯心与唯物、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相互对立的研究范式,因此方先生将法藏、宗密等人的思想置于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的高度予以论述,自然是那个时代对华严宗义理的地位和作用所能给出的一种高度评价。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册)堪称方立天先生一生从事佛教研究的代表作,书中有大量章节涉及华严宗的思想和义理。全书共分总论、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实践论五编。总论部分对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历史演变及思想体系的论述,虽然不是专门论述华严宗义理的,但华严宗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却为方先生的相关论述提供了坚实的佐证。方先生在这一编中有不少地方对华严宗的思想特点作出了高度概括,如他曾说,“此宗以《华严经》的圆融观念为依据,与融中国固有的诸说于一炉的包容思维相协调,提出宇宙万物之间、现象与本体之间圆融无碍的宇宙观。此宗还直接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思想体系,并在一定意义上沟通了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规范”[1]19。他指出,“智俨首先以一与多(一切)相即相入的观点阐发成佛的境界——觉证的世界”,法藏“用‘十玄’‘六相’等法门,系统、全面地阐发了华严宗独特的世界观体系”,澄观“明确提出理(本体、性空)、事(现象)、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四法界说,阐明宇宙万物,相依相待,相即相入,圆融无碍,重重无尽,即世界万事万物大圆融、大调和、大统一的情景”,“还把华严宗终南山系和五台山系的学风结合起来,并开创了融合华严与禅的新风”。宗密“更加强调禅教的一致,并调和佛与儒、道的关系”,“提出以灵知之心为宇宙万物本原的观点,给宋明理学以重大的影响”。他认为,“唐代华严宗哲学广泛地涉及了宇宙生成论、现象圆融论、认识论和主客体关系论等内容,思想丰富、深刻,形成了中国佛教理论的一座高峰”[1]39-40。这些高度概括的语言对于读者从总体上理解华严宗的义理具有非常高的启发作用。在以后各编的具体论述中,方先生对华严宗的佛身说、自性清净圆明说、事事无碍论、真心本原说等进行了具体而深入地阐发,在全面展现了中国华严宗这一佛教宗派义理思想的深刻、丰富、伟美、壮观的同时,也在多个层次上梳理了中国华严宗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其他宗派以及儒道二家及现实政治、经济之间的基本关系。
单纯地对华严宗的思想和义理进行研究,虽然有助于引起教界和学界对华严宗的关注和重视,但却不易展现华严宗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方立天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和佛教哲学的语境中对华严宗思想和义理进行的诠释和阐发,则是在比较研究中自然彰显华严宗思想和义理的基本特征,从而使方先生的华严学研究具有了更为宏阔高远的历史和哲学视野。
四、现代价值
方立天先生从事佛学研究长达半个多世纪,晚年比较注重探讨中国佛教传统观念的现代价值,其中许多地方都涉及华严宗的思想和义理。对于这方面的内容此处无法遍举,仅以华严宗的圆融观和普贤行为例。
方先生认为,华严宗的圆融观应是处理不同文化传统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中国佛教,无论是天台宗,还是华严宗,都非常注重阐发圆融的观念。天台宗讲一念无明法性心即具三千世间,即空即假即中,三谛圆融;华严宗讲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六相十玄,相即相入,融通隐隐,缘起重重。方先生指出,“圆融是中国佛教宇宙观和真理观的重要理念,同样是能够相容和谐、调和适应的方法论基础。圆融要求尊重事物的不同因素,尊重差异各方的共存共荣。按照佛教圆融观来看待世界,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统一整体。按照圆融理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并无高下之分,也不存在相互冲突的必然性,各自不同的文化特性,都应获得尊重。我们认为,当前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保护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同文化特性尤为重要,这是建设和谐世界的要素之一”[1]367。如果具体到一般的行为规范,就是要“重视团结合作,互相让步,必要时适当妥协”[1]359,因此他认为,华严宗的圆融观具有“为建设和谐世界提供方法论基础”的重要意义。
方先生认为,对普贤菩萨的品格和精神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非常有助于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方先生详细考察了中国普贤菩萨信仰的发展史,他指出,在《华严经》中,“‘华严三圣’是强调普贤的大行和文殊的大智对彰显、庄严毗卢遮那佛(清净法身)的作用”[1]380。但随着《华严经》等经典在中国的流传及华严宗等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普贤菩萨在中国佛教信徒中拥有普遍而崇高的信仰”[1]381。一些佛教学者,如唐代李通玄居士和清凉澄观大师进一步发展了对普贤菩萨的信仰,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完善,明代以后四川峨眉山也逐渐演变成为普贤菩萨的道场。方先生将普贤菩萨的实践品格和实践精神概括为“正心”“向善”“求真”“反省”等几个方面,正心“就是正确确立修持成佛的主体性”,向善“体现了度化众生的利他精神”,求真意味着“透过现象看本质”,反省“对于防止一味追求感官享受、贪欲膨胀、邪思邪念都有警示作用”[1]386。因此他提出,“普贤菩萨的行法,作为中国传统佛教文化的一项内容,值得我们重视和认真总结,其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值得我们发掘和继续弘扬,这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有益的”[1]387。
应当指出的是,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现代价值的发掘和弘扬并不是站在佛教信徒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一位关注世界现实问题和人类未来发展的学者立场上进行的。正是这种立场保证了他所发掘的华严义理现代价值的真实性和可行性。
五、结语
总之,方立天先生的华严学研究对教界和学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一者,方先生在华严宗和中国佛教研究中起到了示范作用。《华严金师子章校释》被誉为古籍整理方面的典范之作,《法藏》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这些著作写作严谨、资料扎实,对于佛教经典的整理和祖师传论的研究具有直接的示范作用。二者,方先生为中国的佛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多年来习惯运用“哲学问题解析体”的研究范式,将佛教的重要哲学概念和范畴放在纵向的观念发展和横向的范畴体系中进行考察、分析和比较,非常有利于准确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含义和历史价值。三者,方先生为中国的佛学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他将华严宗视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佛教可以和社会主义相适应,特别是华严宗的圆融观和普贤行,在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之后,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四者,方先生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华严宗培养了人才。方先生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佛教哲学研究方向上的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一直坚持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尊重学生研究兴趣的前提下,鼓励学生对华严宗展开研究,门下弟子如邱高兴、张文良、胡建明以及笔者等人,都曾在他的指导下写出过华严学方面的专著。
[1]方立天.方立天文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M]//大正藏:第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3]李一氓.读《华严金师子章校释》[J].读书,1984(9):29-33.
[4]铂净.20世纪的华严学研究[J].佛学研究,2005(1):363-381.
[5]邱高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佛学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8(1):23-28.
[6]陈永革.法藏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