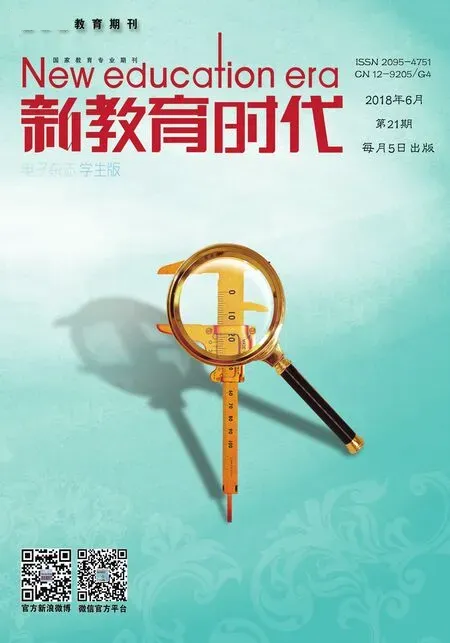大鹏因何挂左袂
——试析李白的仕途何以多舛
2018-02-26傅辰雪
傅辰雪
(浙江省杭州市第四中学 浙江杭州 310000)
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诗坛旷世的奇才,他继承了屈原楚辞的浪漫,谢朓山水诗的自然清新,一改前代文风的浮糜,且不拘泥于诗歌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被后人誉为“诗仙”。他像他笔下背嶪太山、翼举长云的大鹏,足萦虹蜺,目耀日月地飞过历史的天空,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仰望。
李白以一首《蜀道难》令贺知章惊为谪仙人,唐人钱易在《南部新书》中说:“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可见,在当年的盛唐李白就已声名远扬,在诗赋方面达到了千百年来常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但他却在临终的《临路歌》中却发出了“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这样的叹息。这是为什么呢?
李白是一个传奇,天赋超人,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从他留世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鹏是他的图腾,他以大鹏自喻,一生渴望自己像大鹏一样,一飞冲天,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他自云:“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但他一生并不以诗文的成就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在一篇带有自传性的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写到自己:“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在由此可见,他志不在文,那么他的远大志向在哪里呢?
他多次在诗文中表示,他的志向是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宇大定,海县一清。”可见,李白的目标是从政,并且是能够为国为民出一份力,济苍生,安社稷,达则兼济天下的重臣。于是他从青年到暮年,一直矢志不渝地走在干谒的路上。
干谒是唐代除科举外的另一条进入仕途的道路,即通过官员或权贵的举荐,不用通过科举考试就被朝廷直接录用的方式。在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是被绝大多数人认可的人生之路,因此,干谒也就成为当时士子们流行的入仕之路。李白一直坚信自己有王霸之略,纵横之才,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写道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像姜太公、贾谊一样为帝王赏识并重用,主要是因为缺少伯乐。因此他“遍干诸侯”,干谒过益州长史苏颋、渝州长史李邕、荆州长史韩朝宗等,并下了许多干谒的诗文,虽屡屡失败,但从未放弃希望,在《行路难》中他写到:“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总是满怀希望能遇到一个赏识自己的贵人,向朝廷举荐自己,从而实现自己入仕的理想。
纵然是李白有“日试千言,倚马可待”的才华,但他的干谒之路却从未顺畅。曾短暂地进入翰林院,也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是由于某人的举荐而达成的。李阳冰《草堂集序》中有这样的话:“天宝中,皇祖下诏,徵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这样看来,是皇帝听说了李白的诗名而招他入翰林。在这个时期,李白虽然没有官职,算不上进入仕途,但非常接近政治中心,期间他为皇帝起草过诏书、写过《和藩书》,但短短三年后却被赐金放还,这又是为什么呢?
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中这样写道:“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那么,李白的翰林遭贬很可能是被人陷害的。李白也为这一段经历抱憾终生,他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写道:“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更在《梦天姥吟留别》中表明自己的心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但我们在李白存世的诗文中也没有见到一篇类似《过秦论》的治世策论,而他干谒过的人中不乏识人善任的伯乐,比如韩朝宗,他就是一个“喜识拔后进”的人,李白也曾说“白问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那为什么韩朝宗不向朝廷举荐有远大抱负的李白呢?在翰林的日子里,李白为什么没有像贾谊一样,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为唐玄宗所赏识并委以重任呢?这应该说明了李白在治国的才能方面远不如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笔者以为,开创了开元之治的唐玄宗即便年事已高,也不算一位昏君,不可能分不清李白的才华在文还是在政,若李白真是难得的治世之才,即便有人进谗言,也不至于只把李白作为御用文人来看待,并且短短三年就赐金放还。
李白在年青时已经名满天下,那他为什么还穷其一生来谋求入仕的机会呢?为名、为利还是为理想?笔者认为,“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的李白,不可能为名气和金钱谋求入仕。李白的理想是像姜太公、管仲一样辅佐君王,安邦定国。但仅仅如此吗?他曾写道:“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这说明他谋求入仕的另一个原因是光宗耀祖。李白的身世一直是个谜,一直以来说法不一,但肯定不是名门望族。李白作为一个神童,应该是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光耀门楣,而他也将此作为了自己毕生努力的目标。文章的大成不能让他满足,在他看来文章只是一个小技巧,所谓“儿戏不足道”。他渴望的是出将入相。而干谒却屡试屡败,使李白从豪情万丈地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到满怀忧思地写下“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直至怅然地写下《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作为自己一生的总结。
综上所述,李白仕途的不顺是多方面的,一是他放弃科考选择干谒的方式谋求入仕,却每每得不到举荐;二是他个性张扬,与官场圆滑的风气格格不入,招致小人进谗言陷害,三是他在政治上的才华远没有他在文学上的才华耀眼,导致虽入翰林依然无法得到皇帝的青睐。但李白在文坛上不可争议地是最璀璨的一颗明珠,他像天外飞来的大鹏,“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千百年来被人敬仰,难以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