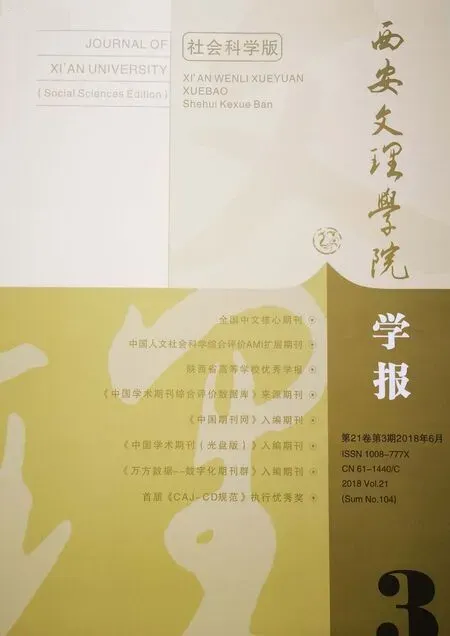石勒与魏晋时期史学发展的互动关系探析
2018-02-26陈俊川
陈俊川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石勒是十六国时期后赵政权的建立者,也是羯胡的一员。作为流寓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历来为人所关注。从羯胡小率到建国立都、从屠戮民众到招抚流民、从“两胡一枷”到威震宇内,石勒的人生充斥着武力征服,但落实到文化程度上便显得捉襟见肘,其文化水平远不如武力水平。纵然如此,在政权构建过程中,石勒在武力征服之外却不自觉地在践行另一条文化路线,推动着史学的发展。这不仅是后赵政权发展过程的一大特色,也是胡族汉化下的一大转变,更是当时史学独立过程中的重要表现。
一、石勒“不知书”下的文化偏向
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后赵的创建者,石勒的军事能力卓越,如吕思勉先生所言,“羯本小族,所以能纵横中原,几至尽并北方者非其种姓之强大,实由勒在诸胡中剽狡独绝”[1]。石勒的军事战斗能力毋庸置疑,但落实到文化上便捉襟见肘,连“石勒”这一姓名也不是他本来姓名。石勒原名,“石勒”一名是在投靠汲桑以后由汲桑所改。其自小缺乏系统学习,经历多是颠沛流离,曾为人力耕,又被东赢公滕“两胡一枷”掳往冀州,后被卖为奴,未曾发现有丝毫文化学习的经历。但就是这样一位无文化基础的胡人君主,最终建立了后赵。在称赵王后,首先做的事情是营建东西宫,继而便是“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2]2735。这种官职的设置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特别是“史学祭酒”的设置更是独见于此,是中国历史上“史学”一词最早出现的记录。[3]“史学祭酒”的设置促成了经学、律学、史学并立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创见。
除此以外,石勒更曾有听史书之好。《世说新语·识鉴》载:“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4]431-432石勒不知书,这是实情,但却愿意听史书了解史事。《晋书·石勒载记》载:“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2]2741两处描述,《石勒载记》更为细致,而且用“虽在军旅”来解释石勒不能亲自阅读的原因,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一种好学的表现。石勒勤听史书是从具体实际出发,史书之中包罗政治、军事谋略,因军事需要而强化对于史事的了解和研习。石勒论帝王善恶,其评价内容便是他们的行为与谋略,这无疑是一个相关的侧面。
《晋书·石勒载记》中对于石勒更是在“常在军旅”之前加以“雅好文学”。石勒“雅好文学”仅见此处,而且只是陈述,并无相关作品,或许是作品散佚,但更可能的是石勒所谓的喜好文学是一种非文学性的偏向,是注重历史的一种表现。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列有“僭伪诸君有文学”条,对十六国诸多君主的文学修养进行分析,这些人物包括刘渊、刘和、刘宣、刘聪、刘曜、慕容皝、慕容儁、苻坚、苻登、姚泓、李流、李庠、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等14人,涵盖汉赵、前燕、后燕、前秦、后秦、成汉、北凉和夏等八个政权,认为“此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5],而缺少后赵以及石勒,不书于笔端。赵翼对十六国君主的评价不可谓低,特别是他们兼爱文学层面,更是予以赞赏,即使如赫连勃勃所谓的“有文学”显得比较苍白而略显牵强,却仍被赵翼所认同,同是十六国君主的石勒,赵翼在其著作中却未提及。由此可见,赵翼对石勒“雅好文学”的事实并不认可。《晋书》为唐人所修,对于《世说新语》中所记内容不可能不了解,据《隋书》卷三四《经籍志》记载,隋朝时尚有刘义庆《世说》八卷本和刘孝标注《世说》十卷本存世。[6]1011弃《世说》而不用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世说》当时被视为小说类,“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6]1012,不足为正史所取。《晋书》以“雅好文学”取代“不知书”,这无疑是对石勒修养的一种修饰。赵翼对石勒的评价不高,更多是采取时间较为靠近石勒所处时代的《世说新语》作为参考。
《世说新语·识鉴》“石勒不知书”条下注引邓粲《晋纪》载:“勒手不能书,目不识字,每于军中令人诵读,听之,皆解其意。”[4]432此处的“书”应解释为“书写”。张万起对于“石勒不知书”的“书”解释为“字”[7],那便可以理解为石勒连基本的文字识读和书写都不能做到。这样一位羯胡政权统治者却“雅好文学”,“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石勒“雅好文学”的真实内容是什么?
二、石勒“雅好文学”的表现
石勒雅好文学,却并未像十六国其他君主一样能著述、吟咏,博览群书,而是习听《汉书》,“常令儒生读史书”,至于其他类别书籍的听或者阅读就不得而知。文学和史学之间,显见石勒更倾向的还是史学性质的内容。关于当时文史之间的关系,胡宝国先生认为刘宋时儒、玄、文、史四学并建,标志着在学术分化的大趋势下文与史的区别终于明确,[8]而此前,文与史是不分的。由此可知当时文、史联系较为紧密,文、史区别并不是特别明显。不过文所重视的是创作,能文是著史的前提,但史重在记事。因而石勒虽是“雅好文学”,他所学习和推崇的不是创作和表达而是史事,是在不自觉中对史学价值的认可,这可能便是石勒未曾设立文学祭酒而是史学祭酒的原因。详览《晋书·石勒载记》,石勒的文学创作基本为零,没有文学式的创作和学习,也不存在著述和吟咏,只是从史事中吸取具有史鉴意义的养分。文学式的创作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与研习,对石勒这般半路出家式的武将来说,文学创作极为困难。史学则不同,史学学而能用。
《晋书·石勒载记》载宴请高句丽、宇文屋孤使节,石勒问徐光自己作为帝王的历史地位如何,徐光认为地位仅次于轩辕帝。石勒却不这么认为:
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2]2749
石勒反驳的言论对刘邦是尊敬,视刘秀为对手,以曹操、司马懿父子为耻,这符合石勒听《汉书》时“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的表现。这当是学习《汉书》的结果,其对于刘邦、刘秀事迹的熟悉大抵来源于此。而且以汉家天子自比,鄙夷魏、晋开国君主,无疑也是向汉族靠拢、追求汉化的一种表现。
石勒不是唯一一位热衷史学的胡族君主,从上引“僭伪诸君有文学”条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胡族君主不仅“有文学”,对于史学亦多涉猎,如刘渊对《史记》《汉书》、诸子百家均有所览,刘宣读《汉书》、刘聪究通经史、沮渠蒙逊博涉群史等,十六国的君主对于史学的热衷可见一斑。就胡族群体之间出现数量如此之多的“有文学”、重视史学的君主而言,胡鸿认为十六国时期“君主的‘有文学’‘尚儒学’如同‘有神异’一样,主要也是史学文本上使用模式化叙事的结果,是利用专属华夏帝王的符号,来塑造十六国君主作为华夏帝王的‘史相’”[9]240-241。其认为文本上的描述实际上远超实际水平,即胡族统治者们并不一定完全具备史料中所描述的能力与才华,只是为与华夏文化接轨,构建正统性和移风易俗。胡族统治者进入汉族地区要想继续统治,便不可能固守原来的游牧方式,必须接受或者说融合汉族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最终由胡变夏才有可能实现更好的统治,因而不能高估石勒等胡族君主的文化水平,但对于石勒等人的努力我们不能忽视。
石勒重视史学与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变有关。《梁书》卷一四《江淹任昉传》文末载:“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10]江淹、任昉虽为南朝人,但“多由文史”中“史”的价值必是在魏晋时期已经出现并发展。当时社会中选官用人的标准已经与两汉不同,由经术转变为文史,这反映出魏晋时期社会学术风气的变迁影响到了政治领域,进而对于官员的任用也产生了影响,史学的地位在这一阶段因而也得到了提高。
由“经术”到“文史”之间尚有“经史”共称的情况,经术、经史、文史是魏晋时期史学地位变迁的几个重要表现名词,也是评价时人学问的常用语。石勒重用的谋士张宾便博通经史,《晋书·石勒载记》附《张宾传》载:“宾少好学,博涉经史”[2]2756。读史、通史、著史是魏晋时期的常见现象,如邵续“博览经史”[2]1703,后被石季龙俘虏,继而被石勒任命为从事中郎。荀绰“博学有才能,撰《晋后书》十五篇,传于世……没于石勒,为勒参军”[2]1158、虞预“雅好经史”[2]2147、谢沈“明练经史”[2]2152、黄泓“博览经史”[2]2492,等等。当时更有家学传史,《晋书》卷八八《刘殷传》载:“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2]2288-2289由此足见史学在魏晋时期已经逐渐摆脱经学的附属位置,在某一方面已与经学的地位相对等,也表明魏晋时期经史分离形势下《史记》《汉书》成为一种“师法相传,并有解释”的专家之学,和经学同样成为教授的对象。[11]
石勒不仅任用张宾、邵续、荀绰等具有史学研习经历的士人,更在设立史学祭酒的同时修撰史书,“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2]2735-2736。《史通通释》卷一二《古今正史》载:“后赵石勒命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又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12]332修撰史书是十六国诸多胡族君主基本上皆有的行为,可视为诸胡族所认可习得汉文化、向汉文化靠拢的行为。
石勒在政权构建过程中推进史学的发展是可以看见的,从设官到著史再到任用士人,这是十六国时期任何一位其他胡族君主所无法做到的。纵使如赵翼所论十六国君主多有“有文学”的表现,但在政权构建过程中皆不再有具体措施,因而这些君主的“有文学”便只是一种个人喜好,或者说是习得汉文化的一种方式,得其形而没有习得精髓。即使是拥有刘渊、刘和、刘宣、刘聪、刘曜等学通经、史、文学的成汉政权的统治者们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也没有给予史学以合适的位置,恰恰是石勒完成了由个人“雅好文学”或者说对史事的重视到对史学的推崇,进而转化为国家层面的官僚建构。
三、史学独立趋势下石勒重史的价值
石勒进行的关于史学国家层面的官僚建构,即任命“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的行为不是偶然的,它不但是对魏晋时期急剧动荡的社会变迁及特殊政治形势下所作出的积极有效的回应,也是对魏晋时期获得勃兴的史学的价值的认可,更是对政权构建的一种合理性的文化层面上的塑造。
(一)史学价值促进修身治国
两汉重经学,经学在两汉时期受到推崇,司马迁认为“《春秋》以道义……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13]3297。《汉书》卷六十《杜钦传》载:“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14]经学在当时可视为万事万物皆可应对,被人重视如此。但自汉末国家分裂以来,作为汉代精神基础的儒家思想失去独尊地位,儒家思想经长期凝结固定而失去原有的弹性,无法适应汉末魏晋社会剧烈的动荡与变迁,逐渐走下原来的神坛。由于经学自身解释的多样与繁杂,在魏晋时期弊端更显,“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2]923。
两汉时期作为经学附庸的史学,魏晋时期逐渐摆脱经学,脱离了束缚而获独立。同时,史学由于具有与经学不同的价值在当时被更多人所接受。
第一,言语精练,习得较易。《汉书》便是一个代表,不仅语言精练,记事也极为丰富,“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言皆精练,事甚该密”[12]20。《汉书》内容详略得当,且易于掌握,偏向具体史实,提供历史教训,较于经学抽象的义理更易学习。当时对于《汉书》注解较多,“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12]314。注解人数如此多,可见当时《汉书》流传之广*除研习人数之多之外,从流布地区看,目前在敦煌、吐鲁番地区发现有《汉书》的12件写本,其中两件是《汉纪》,十件是《汉书》,可以想见当时《汉书》的传播地区已经很广。参见余欣的《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2~44页。、研习之盛。从汉到陈将近六百年,其价值不断被人所认可,“兼采众贤,群理毕备……是以近代诸儒共行钻仰”[13]附《史记索隐后序》,9。无论当时是中原士人或者胡族地区,特别是胡族地区是极有可能存在《汉书》的流传以及士人进行研习的情况。吉川忠夫认为《汉书》是“作为实用的书籍而被阅读”,成为“帝王学之书”,并指出石勒使人读《汉书》的行为是“想从《汉书》中引出政治智慧的态度”[15],这是有道理的。《汉书》的精练、可理解性较于经学的复杂性、义理性对于当时人来说更易被接受和阅读。无论从《汉书》的流行度、注解的人数和研习情况看,还是本身的可读性,石勒常使人读《汉书》当与之有关,《汉书》对于石勒更易被接受。
第二,强化权谋,言传身教。把《汉书》与《孙子》《六韬》等兵书并列,是视《汉书》为学习军事谋略、提高军事素养的作品。《汉书》不仅是了解史事的典籍,更是蕴含诸多军事谋略的兵书。石勒所处时期社会动荡,想要不被兼并或屠灭,不仅要依靠谋士,也要强化自身的军事能力,无疑兵法谋略更需要。石勒子石弘“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但石勒在教子方面认知却不仅如此,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专以文业教也。’于是使刘徵、任播授以兵书,王阳教之击刺”[2]2742。乱世之间经、律固然重要,但想生存必须有实力,这是动荡之世存活的根本。要提升能力则需要学习,自然便要转向史学求经验,从而以刘徵、任播教授兵法一事便有特殊意义。任播曾任史学祭酒,兵法思想不排除来源于史书的可能性。任播曾任侍中,“侍中任播等参议……勒从之”[2]2746,由此可认为任播是石勒身边较亲信之人。更有学者认为任播即是石勒以及石弘的历史教师。[16]由此观之,石勒重史的行为是不无道理的,不仅自己重视史学,对于太子培养也不放过史学教育的环节。
《汉书》记录诸多军事事件,都具有借鉴之处。石勒读《汉书》,一方面可能是《汉书》相较于兵书理论性要弱化、情节性更强,更适合石勒的文化修养水平;另一方面《汉书》作为记录汉政权的正史,可以更多理解中原正统的汉室如何创业*仇鹿鸣认为无论是石勒使人读《汉书》,或者张宾自比张良,学习和掌握历史知识都有现实功用。详见仇鹿鸣的《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乃至构建政权以至于最终失败的功过是非,这是当时驰骋中原的羯胡石勒所必须而且紧要学习的。
(二)治国之下史学的辅助性
谈及正统,任何胡族政权建立者都无法回避,而且也在不断创设条件来实现正统性的塑造,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胡族自身缺乏政权构建经验,唯一有效且易于实施的政权模式便是中原王朝的构建模式,即模仿“汉晋帝国式的政治体”[9]204,而要构建这种模式,必须依赖汉族士人即通过胡汉合作的形式,既削弱民族间的敌视感,又依靠士人的知识与能力模仿华夏王朝构建胡族的政权组织形式。石勒在政权构建过程中不断寻求使士人乃至当时社会认可的方式,同时推动史学在后赵政权建构中的地位。
石勒重视士人的作用,拉拢士人,“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集衣冠文物别为君子营”[2]2711,不仅设立君子营,更曾设君子城。《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居处部》载:“石勒每破一州,必简别衣冠,号为君子城”[17]。无论是君子营还是君子城,都可以看出石勒对士人的优待。法藏敦煌文献《晋记》写本(编号P.2586)更记载诸多石勒政权中的士人,“晋人则程遐、徐光、朱表、韩揽、郭敬、石生、刘征,旧族见用者:河东裴宪、颍川荀绰、北地傅畅、京兆杜宪、乐安任播、青河崔渊。”[18]虽然诸多士人不是主动投靠,甚至被俘虏以后多有怨言,“卢谌、崔悦、荀绰、裴宪、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19],但如傅畅等人却深受石勒重用。傅畅被石勒任为大将军右司马、荀绰担任参军、崔悦曾任大官、续咸为理曹参军等,甚至在设官任事上设立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2]2735。衣冠华族或士人在石勒政权创建过程中备受重视,不仅与中原士族接轨,在石勒进行国家建构方面也是积极辅助者。士人参与是石勒能更多接触史学的重要来源,这些士人是石勒在国家层面建构过程中给予史学以一席位置的推动力量。
在石勒僭称赵王前,刘曜曾署勒“太宰,领大将军,进爵赵王……如曹公辅汉故事”[2]2728,张宾等人也曾请石勒“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2]2730建立赵国。两次事件所依据的“故事”都是魏晋时期近事,也是曹魏、蜀汉政权建立之初的典型事件,作为应援的事例为石勒称赵王提供依据。其后在太兴二年(319)称赵王时,“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2]2735。后在石勒僭称赵天王时,“侍中任播等参议,以赵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腊,勒从之”[2]2746。凡此种种,我们都可见石勒在利用汉文化为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张本,但也可以看到这一系列举动都和史学撇不开关系,无论是群臣援引事例亦或改元,我们都能看到史学的影子。诚然,石勒也依然重视经学和律学,如“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2]2720,“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2]2741,设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2]2735等,但重视历史这条脉络一直存在。
从“不知书”的羯胡小率到建立政权的一方霸主,石勒不仅重文化,而且在政权构建中给予史学以特殊地位,与经学、律学并立,这不仅代表史学地位和作用的抬升,也可以体现当时史学的独立倾向更明晰。石勒设立史学祭酒,乃至采用的一系列促进史学发展的措施既是为了拉拢士人、巩固统治,也受当时史学抬头、史学实际价值凸显的影响,使得作为胡族的石勒能接受史学,并把它运用到国家建构、官员设置和选官用人上。这种现象既是史学独立的产物,也显示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胡族对于史学的特殊态度。石勒所用促进史学发展的举措虽然不是那么完善,其文化程度也不是那么高,石勒的残酷暴虐我们也能看到,但石勒时期在文化路线上这种不自觉地推动史学发展却不容忽视,这种向华夏政权模式的转型不是单纯的模仿,亦有自身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