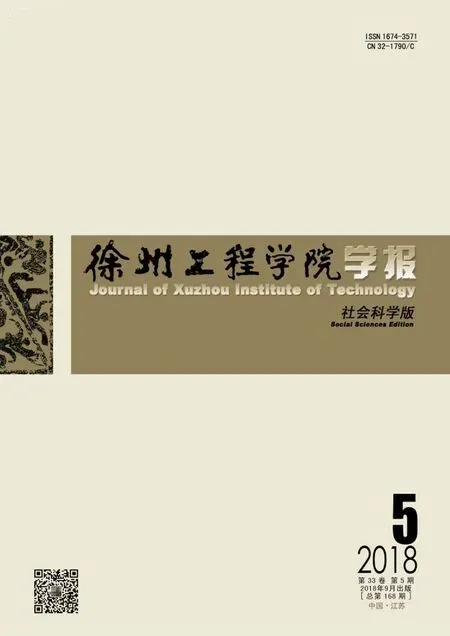魏晋时期王弼易学的发展与流延
2018-02-25吕相国
吕相国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前言
王弼《周易注》的横空出世,无异于在平淡不惊的两汉象数易学深潭中,掀起了一巨大波澜,其所及之处,无不受其影响,其影响之深广,旷超前代。然汉代象数易学并未因此而趋于消亡,而是仍然牢固地盘旋在当时很多学者的思维之中,甚至以玄学名士著称者,亦未能遽然接受王弼的“扫象”说。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王弼《周易注》的出现,无疑对当时及以后的学者有着深刻的影响,直接打破了固有的两汉象数学思维模式,对《周易》的解读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使易学重新获得了生命活力。
为了展现魏晋时期王弼易学的新发展,我们截取四个代表性的人物,对其易学进行分析,以见其流延之梗概。这四个人物分别是向秀、干宝、阮籍和韩康伯,时间不分先后,只是按照其易学思想的特征及其自身的学术倾向进行择取。向秀,与嵇康、阮籍等号称“竹林七贤”,是玄学派的代表,然其易学著作却带有明显的保守特征;干宝,作为两汉象数易学之殿军,被认为是京氏易学的传人,然却又受到王弼易学的巨大影响,并基于象数学的立场,对王弼玄学易进行了回击;阮籍作为玄学人物,顺承玄学的一贯立场,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虽然思想根核承王弼之绪,带有浓郁的老庄学气息,然又能有强烈的现世关怀,丰富了王弼易学的内涵;韩康伯能得王弼玄学易之旨归,补足了王弼《注》中《易传》部分的缺遗,使王弼易学得以完整呈现,于玄学易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然其在日常生活中,又极其注重名教,表现出了与其思想不相协的一面。
据黄庆萱先生言:“东汉之世,师法已坏,魏晋以降,家法又亡。研静之士,出入多家,异议纷起。”[1]14可知当时学术,百花齐放,新奇议论层出不穷。上所举四个代表性人物就是在这种自由思想的学术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虽然这四个人遗留至今的易学方面的材料有限,然透过这些不多的文献,我们对其学术特征及其学术取向尚能略窥一二。现不揣谫陋,对四人的易学思想进行分疏,既见王弼易学的影响,又见其新发展,更见象数易学对王弼玄学易的反击。
一、“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的向秀易学
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著有《周易注》,今不存,唯在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和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尚能窥见只言片语,笔者即据此以观向秀易学思想之大概。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秀别传》曰:
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以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后注《周易》,大义可观,而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未若隐庄之绝伦也。[2]243-244
从上文可以总结出两点。第一,向秀虽大畅玄风,然与嵇康、吕安趣舍不同。嵇康、吕安二子注重的是超脱性的精神境界,即身体力行之超脱,而非仅为思理上的超脱,而向秀则与王弼、何晏一途,注重纯粹思理上的超脱,于身体力行处尚谨守儒家礼教之规。由此可见玄学由第一个阶段的思想解放,流入了第二阶段之对礼教之超越的分界。第二,向秀的《周易注》未受到《秀别传》作者的肯定,仅许以“大义可观”。推测其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可能作《传》者本人基于玄学派求新的立场,不赞成向秀对旧的象数学持继承的态度;二则可能是向秀《周易注》在当时相较王弼易注,并无新义,故仅“大义可观”而已。但是从作《传》者以“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对向秀《周易注》的特点进行描述来看,似乎第一种理由更加合理些。
由上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向秀《周易注》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继承了汉代象数易学家的部分观点和理论。这可以从向秀对《乾卦》九二爻“利见大人”之“大人”的注释看出这个特点。
“大人”,向秀《周易注》以为:“圣人在位,谓之大人。”《释文》引王肃说,谓:“大人,圣人在位之目也。”[3]73究其源,王肃、向秀俱本之《易纬·乾凿度》“大人者,圣人在位者也”一说,则向秀、王肃应该不异郑玄之说,以为“利见九五之大人”。此种解释显然不同于王弼的注释,王弼认为“‘利见大人’,唯二、五焉”。可见向秀在对九二爻“大人”的解释上倾向于汉人的旧解,而不同意王弼的新解。
向秀继承汉代象数易学的另外一个明证,便是对《大畜·大象传》的注释,他认为:
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天为大器,山则极止,能止大器,故名大畜也。[4]277
此处向秀纯粹以取象说明《大畜》卦之义,深得汉易精髓,此与王弼“物之可畜于怀,令德不散,尽于此也”的纯粹说理方式相差甚巨,因此《秀别传》的作者认为向秀《周易注》的特点是“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当是确论。
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向秀在《周易注》中没有受到王弼的影响,从现存的为数不多的几条资料来看,他也受到了王弼玄学易的影响。
1.王弼对《豫卦》六三爻的解释为:“居下体之极,处两卦之际,履非其位,承动豫之主,若其睢盱而豫,悔亦生焉。迟而不从,豫之所疾。位非所据,而以从豫,进退离悔,宜其然矣。”[5]102
按:其中对于“睢盱”的解释,自古各有差异。孔颖达以为“喜悦之貌”,向秀以为“小人喜悦之貌”[3]85。焦循引庄、列之文,以为“睢盱之人莫敢与居”,“睢盱”者,自矜伐之义。又以为即王肃训“大”、郑玄训“夸”之义。并进一步认为:“睢盱而豫指九四,谓九四以一阳自贵于众阴之中,其睢盱之状,不可与居,今承而从之,必受其辱而生悔。……‘若其’二字明指九四。”[6]541故据此以为向秀、孔颖达俱不得王弼之旨*焦循在《周易补疏》中引《释文》向秀注为“小人喜悦优媚之貌”,不同于宋刻本《经典释文》,或所见本不同。。然观王注,“若其”接上文“居下体之极,处两卦之际”,明指六三爻无疑,其义以为:六三不得其位,又承动豫之主,若媚以求九四之豫,则是不以正求豫,故悔生焉;若迟退不求,又不符合豫时进求之义,故进退离悔。“睢盱”者为六三,不为九四,故据此而言,焦循对王弼注的理解颇显穿凿之嫌,而向秀、孔颖达的解释反而更加能合王弼之义,此见向秀受到了王弼新注的影响。
2.王弼对《大过卦》《彖传》“本末”的解释为:“初为本,而上为末也。”[5]148《周易集解》引向秀注为:“栋桡则屋坏,主弱则国荒。所以桡,由于初上两阴爻也。初为善始,末是令终。始终皆弱,所以‘栋桡’。”[4]290由上文可知,向秀“本末”之义或有借鉴于王弼之“初上”为“本末”义。
以上列举两条例证,可见向秀之易学博采古今,不寓封见,且其杂采众家的学术特色和为学理路,在南北朝时期易学的发展中得到了肯定。
二、干宝对王弼玄学易的批评
干宝(?―336年),字令升,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人,易学著作有《周易注》。干宝易学继承两汉象数学传统,以能明京氏易学著称,然际王弼玄学易汹涌之世,其易学思想自然难免受到王弼易学的熏染,但干宝于此之际,仍能基于象数学之立场,对玄学之弊病有所认识,并对其进行批驳,而不随波逐流,此足见其胆识。兹先述其与王弼易学的瓜葛处,再述其对玄学易的自觉反击和批判,以求能得干氏易学之整体概观。
就干宝易学与王弼易学的瓜葛言之,首先是干宝《周易注》采用了王弼本为底本,此可从黄庆萱先生的文本同异字数统计获证:
以干宝为例,其《易注》异文,同孟者四字,异孟者七字。同京者一字;异京者五字。同郑者四字;异郑者八字。同弼者十六字,异弼者九字。故知干宝《易注》,虽多棌京房象数之学,然其底本,则用王弼本,而偶以孟、郑本订弼本,不从京房本。[1]17
基于以上的同异,我们无法确定干宝的初衷,然据笔者推测,不外乎有如下两种情况:第一,王弼易学当时影响甚大,王弼本是最容易获得的本子,因此以王弼本为主,而兼采其他版本;第二,王弼本在版本上有一定的优势,即其相较其他本,版本内部矛盾更少,前后更加一致,错误较少,故采取此本。然而不管以上哪种原因,干宝的《周易注》以王弼本为底本却是事实,其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王弼易学的影响也是可以想见的事实。
除此之外,干宝受王弼易学直接影响的痕迹并不明显,然据有些学者认为,干宝受到王弼易学影响较为明显的的例证,还有《坤卦》初六爻“履霜坚冰”的注释,干宝认为:
重阴,故称六。刚柔相推故生变。占变,故有爻。《系》曰:爻者,言乎变者也。故《易》、《系辞》皆称九、六也。阳数奇,阴数偶,是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阴气在初,五月之时,自姤来也。阴气始动乎三泉之下,言阴气之动矣。则必至于履霜,履霜则必至于坚冰,言有渐也。藏器于身,贵其俟时,故阳有潜龙,戒以“勿用”。防祸之原。欲其先几,故阴在三泉,而显以履霜也。[4]76
王弼的注释为:
始于履霜,至于坚冰,所谓“至柔而动也刚”。阴之为道,本于卑弱而后积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阳之为物,非基于始以至于著者也,故以出处明之,则以初为潜。[5]32
仅从上引文,我们很难看出二者有什么联系,而清人张惠言却说:
以乾例推坤,始于令升,一变汉人师法。审如阴出为祸,在三泉而戒之,出地上而反无不利,何耶?此王弼之谬,而令升不察也。取象无实亦隐宗辅嗣,谁谓令升得京氏学乎?[7]539
而黄庆萱先生又批评张惠言有“门户之见”[1]406,尽管张惠言认为干宝受到了王弼的影响,然而就干宝解释的方式方法而言,他仍然秉持汉易象数学传统,绝不类似于王弼的说易方式,因此,笔者认为上面的材料很难作为论据以说明干宝受到了王弼的影响。
在上文论述了干宝受王弼易学影响以后,我们将更多地关注干宝对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易的反击和批评,就其批评而言,有直中要害者,亦有隔靴搔痒之论,当区别对待。
《周易集解》于《序卦传》“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的注释,引干宝《周易注》:
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止(按:“止”,原作“正”,依李道平《纂疏》改。)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圣人弗之论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还。《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上系》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春秋谷梁传》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而今后世浮华之学,强支离道义之门,求入虚诞之域,以伤政害民,岂非谗说殄行,大舜之所疾者乎![4]719
从上引文,我们可以看到干宝在对玄学易批评的时候,存在着偏见和真见两个方面。就偏见而言,认为“天地之先,圣人弗之论”,乃纯粹从汉代象数易学“法象”的角度言说,维护的是汉代象数易学的合理性,然却不知此非“真见”,乃是纯粹出于一种激昂情绪的不思之言。圣人若真不论“天地之先”,则“乾元”“太极”岂非空谈?天地万物之根基岂非无立定处?圣人岂能如此盲见无识?就其真见而言,他现实地观察到了由于玄学的激荡,整个社会和国家陷入了无序之盲动,能够识别出因“玄学”之流延而造成的“伤政害民”的坏影响。然至于为什么玄学对国家百姓有如此坏的影响,他却并不能从理论上加以说明,这从其反对探本求源之学就可以推知,其不可能对玄学有真正的批判,更不可能提出真正的解决之道。
然而干宝的批判并非毫无用处和见地,他通过经验观察作出的对玄学弊害之描述,起码起到了“触目惊心”的作用,直接触动了后来的学人对玄学流延弊害的原因和救济之道的探索与思考,且他提出的一些见解对后人亦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如干宝所著《晋纪总论》,描写了当时社会弊坏不堪、民风士风不堪之惨状,曰:
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昊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疾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察庚纯、贾充之事,而见师尹之多僻。考平吴之功,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悟戎狄之有衅。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将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8]2175-2191
干宝将社会残破、民生凋敝归罪于何晏、王弼倡导的玄学,认为正是玄学的流行,使整个社会尚虚浮之言谈,轻行身名检;名士玄谈在上,学士亦随风摇荡,不知道德礼教为何物,以放荡逐利为洒脱高致,从而使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虚名浮利,而不知礼教、国家、民族之大义。干宝深感于此,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儒学宗旨来提揭未来的出路,此的确能够中玄学之弊病。
魏晋玄学名士的学术,虽表现各有所致,然就其宗旨而言,俱蕲向超脱一途,就其知与其行之相符而言,却也能做到“知行合一”,然由于其以虚无之“道”为最终归宿,而“道”之无为和无用性质,直接体现在他们的行事上,则表现为两个特征:即对名教的超脱和对世事的不关心。这不仅破坏了既有的旧的名教系统,又以其超脱心而未建立新的名教系统,从而对整个国家社会贻害无穷[9]40。
当时对玄学痛批者,不仅干宝一人,凡稍有国家社稷担当意识的人都有此感触,如裴頠就是其中的一个:
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魏末以来,转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甚,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頠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世虽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之士,皆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有识者知其将乱矣。而夷狄遂沦中州者,其礼久亡故也。[2]238-239
由上可知,众名士据其虚诞之理以表现于行动中,身体力行其所遵奉的玄学旨归,可见其辈亦知行合一者,非徒尚口耳之愉悦,然因其所尚之理论本身仅仅只希慕超越之本体,就必然表现为不切实务,“以遗事为高”,故要对此种行为有所矫正,必须由虚理达实理,由超越落实到具体,此孔颖达之学术任务也。且必须彻底摒弃玄学名士所采取的“超越”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社会的建设中去,从现实中实现“道”,即秉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价值理念,才能最终挽此颓势,此对孔颖达的《正义》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三、《易》为“往古之变经”的阮籍易学
阮籍(210年—263年),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易学著作有《通易论》。阮籍思想形式复杂,如他既主张“礼乐”的教化作用,此相通于儒家之礼乐教化思想,观其《乐论》,俨然一个儒者形象;然他又主张道、德、仁、义、智之间存在优劣分别,则全本老子思想,观其《通老论》,又全是一个道家形象。但是,尽管他的学术思想在表面上呈现出如此多的复杂形象,然就其根本学术宗旨而言,还是一个本老庄思想为说的学者。何以故?如其与儒家思想最接近的《乐论》,根本宗旨,还是“定性命之真”,此不异于老庄提倡的“保真守性”之学。当然并不是说他的《乐论》一点儒学的影子都没有,如其对礼乐随时变化的认识,就秉持儒家思想的一贯看法,但是就其宗旨而言,还是道家的底子,如他将“乐”定义为“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其根本看法还是让人“精神平和”,这与儒家主张的“乐”是教人积极向上、激昂人的精神生命,追求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尚不完全一致。
阮籍作为玄学后劲,其易学思想受到王弼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事,然而阮籍易学思想在秉持王弼的义理易特征的同时,又对王弼易学有一定的发展和丰富,此亦影响到孔颖达的《正义》。
其受到王弼易学影响的直接例证,是其对《乾卦》上九爻“亢龙有悔”的解释。王弼的解释为:“但九五天位,有大圣而居者,亦有非大圣而居者,不能不有骄亢,故圣人设法以戒之也。”即认为之所以“有悔”,是因为上九之爻位被非大圣之人所居,其言外之义即认为,若是大圣,即便居上九爻也不会有悔。阮籍继承了王弼的这种看法,认为:“‘亢龙有悔’,何也?继守承贵,有因而德不充者也。欲大而不顾其小,甘侈而不思其匮,居正上位而无卑,有贵劳而无据,丧志危身,是以悔也。”[10]127其以为上九爻之所以“有悔”,乃是因为“德不充”的缘故,因此换言之,若是德充之大圣居之,即不应该有悔,此明显是截取王弼之义,而对其进行了重新理解和扩充。
然而阮籍在继承王弼易学思想的基础上,还对其玄学易进行了丰富。他在其易学代表作《通易论》中,主张对社会进行重新改造,这表现出了他对现实社会的关切。他认为:
《易》之为书也,覆焘天地之道,囊括万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极而“改”。“反”用应时,“改”用当务。“应时”故天下仰其泽;“当务”故万物恃其利。泽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以顺自然,惠生类也。富贵侔天地,功名充六合,莫之能倾,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10]116
可见,他主张《周易》是“往古之变经”,其中富含着改革的思想,而变革的理论根据就是“道至而反,事极而改”,且认为只有通过改革,才是顺自然之道,才能惠及万物生类,从而建立“富贵侔天地,功名充六合,莫之能倾,莫之能害”的万古不变之基业。
他接着认为,圣人在改制的过程中,以仁义为基本原则,并通过此基本原则,以祸福吉凶的形式来劝化民众。他说:“仁义有偶而祸福分。”偶者,合也。合仁义者,则得福;不合而别求者,则得祸。此乃逻辑之必然,非现实之实然也。此乃是价值取舍之原则。故其后又说:“故犯之以别求者,虽吉必凶。”通过这样一种劝化,圣人期许建立一套完整的宗法名教制度,即:
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别求者,虽吉必凶;知之以守笃者,虽穷必通。[10]130
可见,阮籍将王弼在《周易注》中表现出来的对超越本体的期许和追求,转变为圣人本“道至而反”的原则,希望通过改制,以建立国家社会新的名教宗法制度为最高追求的现实关怀,这无疑相较王弼的易学思想要落实了很多,而他这种急切的现实关怀精神也直接影响了孔颖达的易学思想,并最终通过孔颖达的《正义》实现了对王弼为代表的玄学易学的理论性改造。
四、“承王弼之旨”的韩康伯易学
据《晋书·韩伯传》记载,韩康伯,名伯,字康伯,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艺”,且以“思理伦和”著称于世,著有《辩谦》,并于文中提出了辩论所需遵循的基本原则,即“寻理辩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11]1993,由此可见其对“名理”研究颇深,能得玄学之要旨。又承王弼之后,补王弼所缺之《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传注,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载,韩伯为《系辞》补注,当是随顺其时代的学术风尚而作,因为除韩伯外,尚有谢万、荀柔之、顾欢等九人为《系辞》作注[3]24。
然韩伯注较其他注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被当时学者附于王弼注后,合称王韩注,必有其独到之处。笔者认为韩伯注有如下两个优点:第一,忠实于王弼玄学易本旨,能够得王弼易注之神髓,这也是为什么孔颖达认为“韩氏亲受业于王弼,承王弼之旨”[5]329的主要原因;第二,能够适时地发展王弼玄学易,即能够本玄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来完善王弼注,只有如此才能得玄学之正统。为了较为详细地证成上文笔者之意,现详论如下。
首先,就韩伯能得王注神髓而言,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在对《周易》中基本要素的认识上忠实于王弼义。如其对“彖”“爻”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就全本之王弼《周易略例》,他说“立卦之义,则见于《彖》《象》;适时之功,则存之爻辞。王氏之《例》详矣”[5]347“立本况卦,趣时况爻”[5]347等,此本之王弼“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又如,他认为“彖言成卦之材,以统卦义也”[5]356“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众之所归”[5]357“彖总一卦之义也”[5]310等,则本之王弼“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和“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义,如此者众,不一一举例。第二,对“言象意”关系的认识本之王弼义。他本王弼对“意”的重视,认为《周易》一书就是圣人说理之书,“非忘象者,则无以制象。非遗数者,无以极数”(《正义》,第334页),因此强烈地反对“守文”“守象”不“求意”的诠释方式。如他对“观象制器”的解释,纯粹从文辞上对《乾》《坤》《涣》《随》《豫》等卦释义,而不取传统的“取象”说,显示了他对王弼“取义”说的坚持*按:详细解释可以参看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史》第1卷。(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页)。又如他排斥汉代《易纬》以来对《序卦传》和《杂卦传》的看法,认为《序卦传》“非《易》之蕴也,盖因卦之次,托以明义”[5]396,《杂卦传》则是“杂糅众卦,错综其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也”[5]299,二《传》的根本旨趣都是为了“托以明义”,而汉人那种必从形式上求其义的做法是“守文而不求义”,故“失之远矣”[5]397。第三,对本体之“道”的认识与王弼相同。他认为“道”是“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5]315“有必始于无”[5]340“夫动本于静,语始于默。复者,各反其所始,故为德之本也”[5]368等,此本之王弼在《老子注》和《复卦》注中对“道”的基本认识。由上可知,韩康伯对《系辞传》的注释,不论从词语概念还是“易道”内涵的理解都本之王弼。
其次,就韩伯能适时地发展王弼易学而言,大致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他对《系辞传》中的一些特殊概念的理解,发展了王弼的思想。如对“几”和“神”的理解,就超出了王弼易学本身。他受《系辞传》影响,认为“几”是一种“去无入有,理而无形,不可以名寻,不可以形睹”[5]336的状态,是从虚无太极向阴阳二仪过渡的阶段,而只有圣人能够体悟及之,贤人则不得及之,故“在理则昧,造形而悟,颜子之分也。失之于几,故有不善”[5]364。他强调对“几”把握的重要性,此无疑要比王弼对“几”的理解要深刻得多*王弼在其《周易注》中“几”的内涵往往表现为:“进退之几”“不失其几”等,表示的是一种变化之几运,并没有明确的揭示“几”的内涵。。如果说他对“几”的理解受到了《系辞》的影响,那么他对“神”的理解就不仅仅是受到《系辞》的影响,还受到了郭象思想的影响,他说:
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曰“阴阳不测”。尝试论之曰:原夫两仪之运,万物之动,岂有使之然哉!莫不独化于大虚,欻尔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应;化之无主,数自冥运,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是以明两仪以太极为始,言变化而称极乎神也。夫唯知天之所为者,穷理体化,坐忘遗照。至虚而善应,则以道为称。不思而玄览,则以神为名。盖资道而同乎道,由神而冥于神也。[5]319
他将“神”理解为“道”生万物、使万物变化运动之过程的神秘状态,即不知所以然而“妙万物”的状态。他对“神”的这种理解,明显受到了郭象“块然自生”思想的影响,所不同的是他仍然秉承了王弼的“有生于无”的本体论思维模式,不同于郭象的“无不可以生有”的非本体论思维方式。第二,韩伯相较于王弼,对“占筮”有更深的理解。他在对“大衍之数”章“揲筮”过程的解释中,直接“抄录了陆绩的注”[12]18,表示他接受了象数学对“蓍数”的一些看法。又如他对蓍数与卦象关系的看法,受到了《系辞传》的深刻影响,认为:“明蓍卦之用,同神知也。蓍定数于始,于卦为来。卦成象于终,于蓍为往。往来之用相成,犹神知也。”[5]338“蓍极数以定象,卦备象以尽数。”[5]382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丰富了王弼易学对《周易》一书的基本看法,他认为:“作《易》以逆睹来事,以前民用。”[5]384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蓍数与卦象的作用,相较王弼,更加符合蓍数和卦象之真实作用,这也影响到孔颖达对蓍数和卦象的理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韩康伯的易学思想本之王弼《易注》,能得王弼易学之神髓,且适时地对其有一定程度的丰富和发展,然就根本旨趣而言,仍然是本之王弼玄学易。
结语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王弼易学在魏晋时期的影响,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是巨大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易学思想变更了易学在两汉时期的旧面貌,开创了一个易学发展的全新时代。随着王弼易学在魏晋时期的流传,基于王弼易学玄学性和说理性的特征,魏晋时期的易学家从正、反两面受到王弼易学或多或少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王弼易学的内涵,为进一步推动以王弼易学为代表的玄学易和义理易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造成了南北朝时期,随着玄学在社会上的普及和流荡,王弼易学作为这个学术潮流的开启者,走上了学术的神坛,被指定为当时之官学,供学者学习和研讨。而为了对王弼易学思想进行解读,新出现的“注疏”体被用来作为对王弼易学进行解读的基本形式,这种新的学术形式,一直延续到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而南北朝的众多学者在对王注疏解过程中取得的理论成果,又被孔颖达《正义》充分汲取,他们在注释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被《正义》最终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