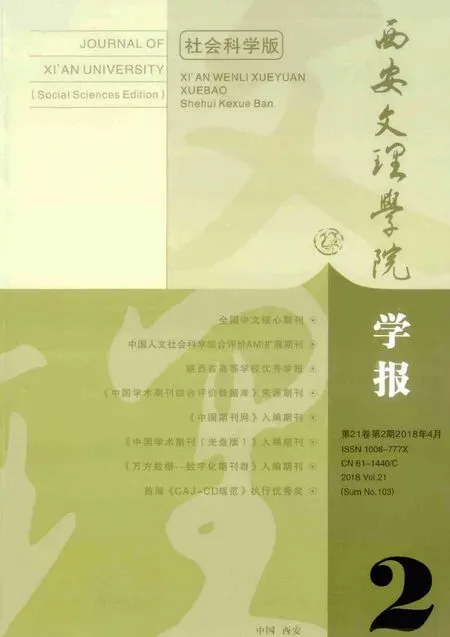周立波小说中的风景与抒情
2018-02-25钟凯丽
钟凯丽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周立波是“十七年文学”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他早年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从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司汤达、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了“浪漫主义者所有的想象力”[1]273。他于该时期创作的《牛》《麻雀》《第一夜》等短篇小说皆表现出浪漫倾向,承载着诗意情怀。1942年,周立波受整风运动影响,文艺思想发生了改变,并于1943年做了自我检讨:“我只能写写牛生小牛的事情,对于动人的生产运动,运盐和纳公粮的大事,我都不能写。……我只希望我们能够很快被派到实际工作去,住到群众中间,脱胎换骨,‘成为群众一分子’。”[2]此后他一直坚定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道路。今天学界对周立波的研究,多集中在他后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上,关注其创作的民间立场,却忽视了他从创作初就一直保持的抒情姿态。作为“茶子花派”的代表人物,周立波小说中清新迷人的自然风景和诗意情怀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但依然被纳入民间立场的角度进行分析。鲜有学者对周立波小说中的风景与抒情进行探源。有学者注意到了外国文学和地域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但在“十七年文学”中受外国文学和地域文化影响的作家不在少数,我们不禁发问:是什么使得周立波的小说在风景和抒情上迥异于该时期的同类作品,成为其小说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
本文以周立波小说中的自然风景为对象,试图对周立波文学创作的抒情倾向做由外至内的探源。笔者认为,周立波小说中风景与抒情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受到传统、地域和个人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该影响无法被作家创作的主观意识完全抹去。在文艺作品的情感抒发受到限制的大环境下,作家创作中难以掩饰的抒情倾向便更加熠熠生辉。
一、历史的风景:抒情传统
“抒情传统”的概念肇始于1971年陈世骧先生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认为,《诗经》和《楚辞》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源头,确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为主导的发展方向。高友工、蔡英俊、吕正惠等人进一步论述了“抒情传统”。普实克、王德威、黄锦树等人更是将“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联系起来,用以解释现当代作家的文学话语。其实在此之前,中国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文学中独特的抒情现象。朱光潜曾说:“长篇叙事诗何以在中国不发达呢?抒情诗何以最早出现呢?因为中国文学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偏重主观,情感丰富而想象贫弱。……因为缺乏客观想象,戏剧也因而不发达。”[3]
在围绕“抒情传统”的讨论中,也不乏反对之声。龚鹏程对“抒情传统”表示质疑。郑毓瑜则反对陈世骧、高友工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学中“抒情”的解释。学者们对“抒情传统”的争论,实际上始终围绕着它的含义和源头两个主题。即便是否认“抒情传统”的学者也无法避开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以抒情为主导的现象。中国文学中存在一个“抒情传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剩下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定义“抒情传统”?
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最初是在比较语境中提出的,因而要解释“抒情传统”需要与西方的浪漫主义进行对比。王德威认为“现代西方定义下的主体和个人,恰恰是传统‘抒情’话语说致力化解——而非建构——的主题之一”[4]5,并指出“中国抒情传统里的主体,不论是言志或是缘情,都不能化约为绝对的个人、私密或唯我的形式;从兴观群怨到情景交融,都预设了政教、伦理、审美,甚至形而上的复杂对话”[4]56-57。该言论将中国的“抒情传统”与西方的浪漫主义做了区分,与蔡英俊、黄锦树等人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中国的抒情不具备完全的主体性,这是中国“抒情传统”的特殊之处。
周立波深受中国古典诗歌和小说的影响,曾多次论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浪漫情怀。“人们需要美、幻想和激情以及对于这些东西的陶醉。所以现实主义必须要有浪漫主义的成分。”[1]447但他同时也说:“感情的纯粹的存在是没有的,感情总和一定的思想的内容相连结。……一切文学都浸透了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1]10周立波所言的“浪漫主义”一词来自于西方,但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他所指的“浪漫主义”与西方语境中的“浪漫主义”是有区别的。西方浪漫主义强调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而在周立波的阐释中,这种与思想内容连结的情感其实更偏向于抒情传统。
基于中国的抒情传统来看周立波小说中的风景与抒情,我们会发现其中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周立波早期的短篇小说如《第一夜》《牛》《麻雀》等充斥着浪漫的气息。但这些小说中的抒情,不同于西方张扬个性的浪漫主义,而与政教、伦理相关。小说《第一夜》中,我身处监狱,梦见了一片自由景象。“烟雾消散了,现出了蓝色的天空和青色的山野。山边有一条漂着茶子树的白色落花的溪水,溪岸上一个赶牛喝水的赤脚的孩子唱着他的快乐的山歌,向我走来。”这里的风景描写并非完全出于一个受禁锢的人对个人自由的渴望。在这个美好的梦境出现之前,“我”的眼前浮现的是“大老鼠,麻布袋和洋包探的红润的胖脸”。而上文提到,许多革命男女被装入麻布袋,投入海里。因而“我”梦中的景象不仅表现着“我”对自由的渴望,也饱含着“我”对革命胜利的殷切期盼。周立波在评价艾芜的《南行记》时说:“为了疗救眼前生活的凄苦,他要在近边发现一些明丽的色调,于是他向自然诉求……要赶走洋官和他们的帮办,要消除自然的美和人生的丑的巨大的矛盾……”[1]106-108在这里,自然风景已经不仅限于抒发个人审美感受,它作为灰暗生活的参照物,融合了作家对民族崛起、国家和平的向往。
1949年以后,风景描写被置于尴尬的境地,“乡土小说在“十七年文学”普遍表现出对风景画的“淡漠”,风景描写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此后的乡土小说“风景”工具化、操作化、重复化现象突出,特定意象更是概念化、公式化[5]149。该时期,周立波的文艺思想同样发生了转变,但风景描写并未从他的作品中销声匿迹。超越个人主体性的抒情传统在周立波后期的小说中有了更明显的体现。《卜春秀》中写道:“山顶上,阳雀子不住停地送出幽婉的啼声。温暖的南方的清夜飘满了草香、花气和新砍的柴禾的冲人的青味。她的心神又飞到了我们的勇士守卫着的、祖国的遥远的边疆。”这里的风景描写,不仅是对小说中美好恋情的烘托,也是对边疆卫士的赞美。
中国抒情传统与政教、伦理、审美等相关联的特点,使得周立波能够恰当处理情景交融与意识形态的矛盾。情景交融之所以能够成为他“十七年文学”小说中的一个亮点,是由于这并非完全来自西方的浪漫主义,也承袭了中国的抒情传统。
郑毓瑜认为中国文学中存在引譬连类的现象,而非纯粹的个人感怀。言下之意,中国文学作品中许多景物描写并非完全是作家处于情感而做出的选择。中国几千年来的抒情传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结构,如“春女思,秋士悲”这种自然与人情的联系成为一种常理常情。
周立波在《夏天的晚上》中写道:“月亮照上来,带着水样的光辉和烟样的思虑映进了房间。我们的心情飘动了。”尽管周立波在下文批判了这种低落的情绪,但小说中处处透露的乡愁是无法遮掩的。而“月亮”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月亮是一个重要的意象,而它最重要的寓意之一便是乡愁。周立波的小说中还曾多次出现“蛙鸣”,“田野里,在高低不一的、热热闹闹的蛙的合唱……”,“田里到处是蛙鸣”。这些风景描写烘托了欢乐祥和的气氛。前一选句还能借着“热热闹闹”“合唱”等词凸显这种气氛,而后一个选句却有点像空穴来风。然而这个句子的抒情效果并不会因为修饰语的缺失而大打折扣,因为在我们的传统知识结构中,“蛙鸣”与“田地”联系在一起,通常象征着农业的丰收,代表着喜悦的情感。
从“引譬连类”的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周立波小说中充满了这种基于抒情传统的景物描写。周立波小说中的风景与抒情其实是对中国抒情传统无意识的回望。
二、眼前的风景:湖湘风光
“十七年文学”时期,周立波小说中许多自然风景被社会主义风景遮蔽,但正因为如此,那些未被埋藏的自然风景才更可贵,那是地域环境打在作家创作灵魂上的烙印。
《山乡巨变》被视为周立波长篇小说中的最高成就。除了创作手法成熟外,地域文化也是《山乡巨变》成功的重要因素。茅盾曾评价道:“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确立起他的个人风格。”[6]《暴风骤雨》是周立波结合自己在东北参加土改的经历写成的,小说中虽然也有东北的风景描写,但所占比重很小,显然不如他在家乡创作的《山那面人家》一系列短篇小说和《山乡巨变》中的风景描写那般驾轻就熟。周立波借助自己最熟悉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了个人的艺术风格。
湖南秀丽的山水风景和少数民族文化成为湖南作家珍贵的创作资源。湖南作家群中,沈从文、周立波、古华、叶蔚林、韩少功等都曾受地域环境影响而创作了极具乡土特色的小说。作为湖南作家群的主力,“乡土作家在审美趣味,思维习惯,对题材的选择及处理方式,设定主题等方面,都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地域特征”[7]。沈从文曾说:“两千年前那个楚国逐臣屈原,若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魂动魄的景物,两千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了。”[8]沈从文此言显示了一个湖南乡土作家的文化自信和对故乡风光的深情。这种自信和深情也体现在同为湖南作家的周立波的身上。周立波曾写有《湘西行》《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雾里的湘西》,介绍湘西的历史和风俗,其中饱含着他对湘楚文化和湖湘风光的热爱。
周立波的家乡益阳地处湖南省中北部,南部以山地、丘陵为主,北部是洞庭湖平原。“中部丘陵岗地是楠竹、油茶、茶叶、果木等经济林生产区,益阳是全国著名的‘楠竹之乡’”[9]。在周立波的小说中,我们时常能看到那“茶子花”“阳雀子”“青松”“楠竹”等景物,这些都是周立波家乡的常见之物,是他最为熟悉的风景。《山乡巨变》中写道:“虽说是冬天,普山普岭,还是满眼的青翠。一连开一两个月的白洁的茶子花,好像点缀在青松翠竹间的闪烁的细瘦的残雪。林里和山边到处发散着落花、青草、朽叶和泥土的混合的、潮润的气味”。从季节、花期到景物的颜色、气味,都体现了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渗透着他对家乡一草一木的热爱。相比之下,《暴风骤雨》中大多数风景描写纯粹是为情节发展服务的。
水网密布、雨量充沛也是益阳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地理环境特点到了周立波的小说中则表现为一幅幅烟雨朦胧的水墨画。例如,“雨落大了。……在青翠的茅草里,翠绿的小树边,这一丛丛茂盛的野花红得像火焰。背着北风的秧田里,稠密的秧苗象一铺编织均匀的深绿的绒毯,风一刮,把嫩秧叶子往一边翻倒,秧田又变成了浅绿颜色的颤颤波波的绸子了”,单看这样的风景,我们感受到的是喜悦。奇怪的是,下文紧接着的是人们对大雨的抱怨和对农作物的担忧。“今年不会烂秧吧?”“这种鬼天气,哪个晓得啊?”人物口中的“鬼天气”显然是与作者笔下诗意的风景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在周立波的小说中并不罕见。小说《民兵》中,写到何景春被烧伤、前途未卜时,周立波居然插入了这样一段风景描写:“近山淋着雨,青松和楠竹显得更青苍。各个场屋升起了灰白色的炊烟。在这细雨织成的珠光闪闪的巨大的帘子里,炊烟被风吹得一缕一缕的,又逐渐展开,像是散在空间里的一幅一幅柔软的轻纱。”
1935年,周立波在《选择》中写道:“在小说和故事中,作者常常可以借用自然描写和环境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气氛,加强人物的个性。这种背景要和人物的气氛和个性配合。”[1]40可见,他在小说中运用环境描写时是有意识的,他小说中出现的风景与人物心理的矛盾并非作家创作的失误。
周立波也并非不能写狂风暴雨。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为一对逃难的母子安排了一场大雨。“西南天上起了乌云,密雨下黑了天地,老远望去,雨脚织成的帘子从天到地,悬在西南,真有些像传说里的龙须。带着湿气的大风猛刮着,把那夹着雷轰电闪的雨云飞快地刮了过来。”这里对东北自然环境描写与小说气氛是一致的。但在周立波回乡生活期间创作的作品中,我们很难发现这种较为阴沉或极端的气候描写。即使是家乡的大雨,在他眼里也是秀气的、充满诗意的。
周立波从湖湘风光中汲取养分,使作品具备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同时也寄托了他对故乡的情感,这使得文学能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保持相对的独立。
三、个人的风景:浪漫情怀
地域环境对作家的创作风格起到重要影响,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作家的主观因素对风格形成的作用。朱光潜在《谈美》中说:“美不完全在外物,也不完全在人心,它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10]周立波在书写湖湘清新迷人的风光时融入了个人的审美意识和文艺思想。
今天我们通常认为“十七年文学”的政治环境削弱了文艺作品的文学性。然而在周立波眼中,文学与革命、政治并非对立。周立波在评价歌德的《浮士德》时说:“我们要求有丰富的现实知识和激越的诗的精神的作家。”[1]156在文章的最后,他引用了歌德的诗句:“我觉得这样的人才算是幸福的人,或者是死在阵上头戴血染的荣冠,或者是狂舞之后抱在一位姑娘的手腕”,并说道:“要是我们的姑娘们也行将做人的奴婢的话,我们将更决定的爱了前面两行诗句吧?”[1]157在他眼中,战斗的理由甚至可以只是为了夺回姑娘们。这是多么浪漫的革命者!
在政治加紧对文艺控制的环境下,周立波对文学抒情的定位是十分准确的。他不反对文艺作品中的抒情,只反对伤感的流露。在他看来,积极的浪漫情怀能为现实提供动力。这种文艺思想在他的作品中具体表现为色彩明丽的风景。例如“桐树的丫枝还是溜光的。桃花却开了,红艳艳的,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好像一抹粉红的轻云,浮在淡蓝的天底下和深黑的屋檐边”。这幅风景画同时具备了“红”“蓝”“黑”三种色彩,极富视觉冲击力,给人一种明朗、生动的想象,预示着希望与成功。周立波正是借助这种“积极的浪漫”来表达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
此外,周立波还富有诗人气质。他除了创作小说外,也写有许多诗歌。他曾说:“形式不过是诗的骨骼,情意才是诗的血肉;技巧的工拙是诗神的末事。诗人们!到大自然中,到人间,去找你们的诗的印象和感兴罢。诗在人间,在自然里,不在笔端,也不在书上。”[1]59这种诗人气质使得他对自然环境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他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与何其芳、严文井等成立了一个名为“草叶社”的文学社团,这个社团名字正是取自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此外,他曾多次称赞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中的浪漫主义,也十分欣赏《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中的幻想。
对爱情的书写是周立波小说的一大特色,他笔下的爱情总是浸润着月的清辉,弥漫着花的芬芳。由于文艺政策的原因,周立波在书写爱情时是谨慎的,常常将其与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当两者产生矛盾时,爱情往往做出让步,但他常常忍不住迈出文艺政策划定的界线。在《山乡巨变》中,他借助自然风景,极力渲染了浪漫的气氛。“多好呵,四围是无边的寂静,茶子花香,混和着野草的青气,和落叶的沤味,随着小风,从四面八方,阵阵地扑来。他们的观众唯有天边的斜月。风吹得她额上的散发轻微地飘动。月映得她脸颊苍白。她闭了眼睛,尽情地享受这种又惊又喜的、梦里似的、战栗的幸福和狂喜。而他呢,简直有一点后悔莫及了。他为什么对她的妩媚、她的姣好、她的温存、她的温柔的心上的春天,领会得这样的迟呢?”在这段描写中,我们看不到政治的痕迹,只有作家浪漫情怀的肆意流露。
周立波的浪漫气质还在于他对社会主义抱有的几近于乌托邦式的怀想。“家家的屋前屋后,塘基边上,水库周围,山坡坡上,哪里都栽种。不上五年,一到春天,你看吧,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嫩黄的桔子花,开得满村满山,满地满堤,像云彩,像锦绣,工人老大哥下得乡来,会疑心自己迷了路,走进人家花园里来了”。这段描述令我们想起了桃花源。周立波既基于社会主义建设展开了展望,也表明了他积极、乐观的改革态度。这与他的浪漫气质是相符的。
周立波曾经对自己的浪漫气质做出检讨,但在之后的创作中,这种浪漫气质却并没有消失,它作为一种隐性的元素,潜藏在小说的风景描写和日常生活中。这说明作家创作的情怀、气质或许会被特定的环境所压抑,却无法被彻底改造。
在“十七年文学”时期,如何恰当处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成为作家创作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该时期许多作家或因为文艺超越政治界线而遭受批判,或因为过于突出政治的地位而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和抒情性。尽管周立波也因为小说中的抒情性遭到一些批判,但他作品的思想和内容依然紧扣时代的主题,符合他所坚持的道路——为工农兵服务。这与他的个人气质、故乡风光和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继承是分不开的。这三者消解了政治对文学的部分压力,使周立波在该时期还能创作出如山花带露般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 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6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2] 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65-66.
[3]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134.
[4]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5] 魏宏瑞.消失的“风景”线——十七年(1949—1966)乡土小说中的风、花、雪、月[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4):147-151.
[6] 胡光凡.周立波评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329.
[7] 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2.
[8]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9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81.
[9] 朱翔主编.湖南地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5.
[10]朱光潜.谈美[M].北京:中华书局,20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