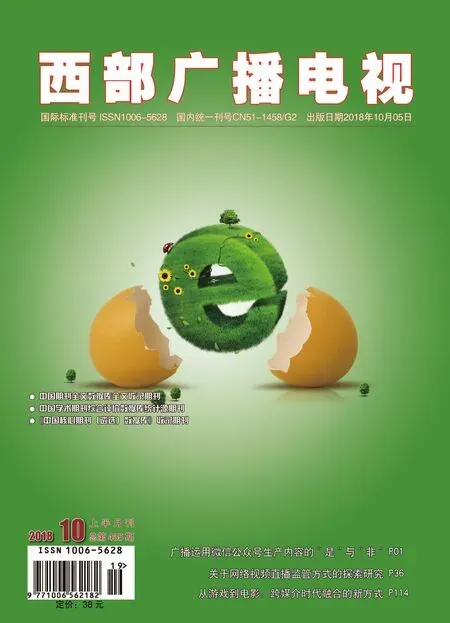江湖行走的守夜人
——电影《三峡好人》中的出走与寻找主题分析
2018-02-22李贞秀
李贞秀
(作者单位:西安培华学院)
从《小武》中的小偷、妓女到《任逍遥》中的混混、矿区模特,贾樟柯电影中塑造的人物大多为社会的边缘人,他的电影是中国当代底层社会的一面镜子。在电影《三峡好人》中仍然继续了导演一贯的风格,再次把底层小人物的故事搬上了银幕。然而,正是这些小人物却吸引了关注的目光,正如贾樟柯自己所说的那样:“当看到工地上那些挥土如云的工人,我觉得他们的生命不管放在哪里,只要能被看到,生命本身都是很美丽的,是非常感人的。”[1]
1 隐退社会矛盾叙事背景
《三峡好人》用写实的镜像语言了两个独立而又密切联系的故事,一个是为了找寻妻子女儿来到三峡,另一个则是为了寻找丈夫,虽然两个故事彼此分开,但同样的寻找主题使两段故事联系起来。与贾樟柯之前的电影叙事相比,《三峡好人》中的主人公从漫无目的的游走与惶惑中暂时脱离出来,而是开始了一种目标明确的出走与寻找,在这种出走和寻找的过程中完成了人物命运与环境碰撞之后的价值实现。由于三峡水库的修建,奉节地区成为中国当下的种种矛盾集结最为明显的地方,城市的淹没导致人们开始迁移,无家的漂泊又使人们产生无处寻根的文化失落,整个影片都把这种社会矛盾作为大背景隐退到叙事的后面,各种个体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大背景之下而产生。然而,正是这种社会矛盾在影片中作为叙事背景的隐退,使电影趋向个体矛盾激化的埋藏于内心的歇斯底里和末日的狂欢。无论是扬言烧船的工人还是斗殴的青年,在他们身上随时显露出来的暴力倾向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无奈与外化出来的极端反抗。
由韩三明这个外地人的视野中展现当地人们的现状更显得客观和冷静,从刚到奉节一上岸遭遇骗术、被摩的宰客到客栈的吃回扣,都是用一种冷静的视角展现,在舒缓悠长的镜头之下,这些生命个体不是面目可憎,而是一种利益凝结的卑微与无奈。在小马哥眼中,奉节是个失去江湖情结的江湖,从一开始的魔术诈骗到最后的莫逆之交,用小马哥的话,两个人都因为太怀旧而走到一起结成兄弟。在这里,怀旧这个个体的生命活动又对社会产生了隐喻的作用,三峡的兴建导致故土的淹没,故乡作为一种怀旧符号的最终消失导致人们精神的涣散与缺失,义气作为江湖的行为准则早已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取而代之的是当今社会失信的泛滥。韩三明来到陌生的奉节,同何老板语言上沟通的困难成为最基本的障碍,成千上万的奉节人们去广州、辽宁以后即将面临的也正是这种困境,由语言沟通的困难引申出来即是文化的失根。韩三明在等待中体验着身在异乡的孤独,天空中滑过的飞行物这个超现实影像成为看似充满希望的等待实则终究无果的表征。
2 多主体多角度凸显主题
随着飞行物的滑过,引出了影片叙事的第二部分,同样从山西来到奉节的沈红拉长了韩三明的等待。同样看到飞行物的沈红有着和韩三明同样的孤独,如果说韩三明作为拆迁移民最底层生活的见证,那么沈红则亲历了城市拆迁的变化。沈红的寻找从一开始便注定是无果的,在影片中出现的破旧工厂会让人不由得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在钢铁与机器包裹的城市中,人们的隔膜与疏离往往成为必然,压抑已久的沈红举起锤子重重的一砸,成为死寂中最具力度的宣泄。茶的出现极具讽刺意味,旧茶不像酒越放越醇,茶更像生活,平淡的清香带着自己才知道的苦涩。哀伤莫大于心死,沈红来到奉节不是为了寻找爱情,而是为了求证现实。沈红从始至终都是理性地一步步验证着自己的推断,在长时间的闷热过后,沈红打开风扇,晾出了自己贴身的内衣,这场仪式使得沈红的决定犹如莫名飞走的纪念碑一样决绝。飞走之后的纪念碑使奉节在导演的超现实臆想之中强行回到了过去,回到了那个“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奉节,也回到了那个夫妻情浓、父女团聚的曾经。然而,沈红的仪式并没有真正结束,她和丈夫在江边的一段舞蹈更加耐人寻味,原本可以促进情感交流的舞蹈在此成为最后告别的仪式,当她最后一个人坐船离开的时候,奉节的天在影片中第一次显得那么纯净。
相比沈红最终的孤单离去,韩三明似乎幸运了许多,在经过苦苦等待之后终于看见了自己当年的妻子。然而,此时妻子的颠沛流离与饱经风霜则更显示出生活本来的无奈,由于最基本的尊严使她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脱离了韩三明,生存的基本问题又使她再次被交易,当生存成为人们生活中第一本位的考虑因素时,女人的价值往往为男权社会所操控。当然,贾樟柯在此不是想讨论女性主义的话题,而是通过女性交易这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来揭示人生背后的无常与无助。最后,韩三明的遭遇依然归结到人生的苦痛之中,何老板被人强拆了房子后住进桥洞、小马哥最后的死、妻子再次被交易,这些边缘人物命运的背后是个体生命价值让位于金钱与政治操控的当代社会凸显的矛盾。韩三明见到妻子后却只能卑微地恳求妻子的主人,这一段戏的画面被导演赋予了表现主义的意味,妻子的主人坐在韩三明与妻子的中间位置,面向观众的主人成为画面的主导,韩三明背对观众则显示出无助与弱势,更为明显的铁窗在画面中成为隔离夫妻的重要象征,其中的隐喻仿佛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中小凯恩被母亲决定命运一样,妻子在铁窗外彻底成为了局外人,而妻子由于逆光对于韩三明只能成为一个含糊的轮廓。当韩三明与妻子相会在被拆的残破不堪的楼中分吃一块糖时,这种隐喻终于同远处倒塌的楼一样暴发了出来,几乎没于任何对白的自然音响在此时显示出来的是彻底的崩溃。
3 客观展示社会现实
在片尾韩三明的命运依看似幸运许多,但当韩三明同工友一起离开奉节奔赴山西的黑煤窑时则饱含了生死未卜的恐惧,如同在片尾出现高空走钢丝的画面一样命悬一线。电影在结尾依然响起刚开始时的一段川剧《林冲夜奔》,韩三明如同林冲一样被逼进绝路铤而走险,音乐苍凉悠长,仿佛是深渊中的回声,同时也暗示了韩三明同样作为底层人物对不公命运的无法逃脱。韩三明的出走与寻找最终逃不出命运的摆布,个体生命的失值、历史的失落、文化的失根,如同被反转过的人民币一样,最终都要让位于金钱和政治。然而,贾樟柯并没有有意在影片中权衡二者利弊,出走与寻找本身就没有结果,只是把个体价值/群体利益、历史文化/金钱政治这些二元对立在影片中尽可能客观冷静的展现,不否认后者的价值实现,只带着属于艺术家的良知来关注前者的弱势与流失。“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殖民文化的入侵、国内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新型城市地理景观的构建等多元因素影响下,文化环境与地理空间景观都处于一种快速的变迁进程之中,致使诸如‘小武’等边缘人物陷入一种集体式的焦虑与迷茫之中,‘怀旧’故乡的传统记忆成为其挥之不去的情结。”[2]这种对人性的探寻与呈现,一直都是贾樟柯电影中的主题,在这一种主题下,贾樟柯用摄影机对冷峻荒诞的生活进行客观记录,这些生活也正是他熟悉的地方,因此充满了乡愁,这种特殊的观察距离,使得贾樟柯的电影在冷峻之余,又充满了温情的人文关怀,也正是这种温情为那些寻找与焦躁不安提供了可供休息的空间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