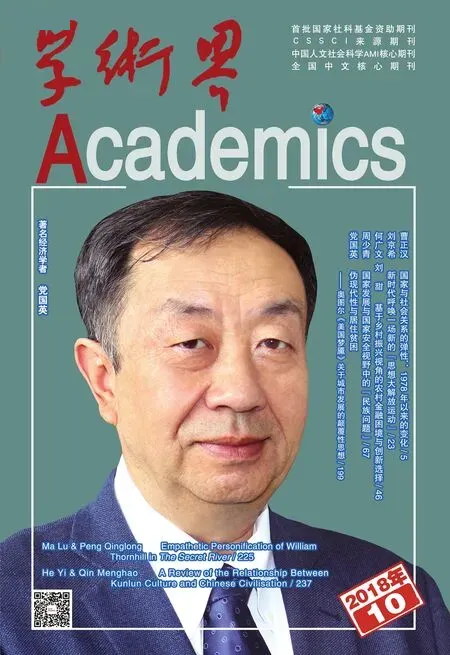日本诗话的文体史料与文体批评〔*〕
——兼与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比较
2018-02-20任竞泽
任竞泽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理论形式,中国历代诗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渊薮,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给予关注。日本诗话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文体史料和系统的文体学思想,而且与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有着极深的血脉渊源,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还是空白。其中,日本诗话与中国诗话的血缘关系及其影响比较研究,是中日学者关于日本诗话研究的核心内容,如王晓平《跨文化视角下的日本诗话》云:“日本诗话的兴盛得益于中国诗话的传播。日本诗话中体现的诗歌观念,大都来自中国古典诗论。”〔1〕孙立《面向中国的日本诗话》云:“日本诗话脱胎于中国诗话,内容也以论析中国古诗及诗论为主,是一种面向中国的‘外邦’诗话。”〔2〕同样,日本诗话中体现的文体观念,也大多来自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而论析中国古代文体及其相关的文体理论批评也是日本诗话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全面辑录分析日本诗话中的文体史料和文体批评,系统构建其文体学理论体系,将日本诗话中的文体观逐一与中国诗话中的文体论进行比较对照,加以印证,以见其渊源影响关系及“和而不同”的自身特色,这对于日本古代文论、中国古代文体学及其中日比较诗学等研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批评史意义。
一、欲学作文者,辨体之为急务
“辨体”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首要原则和基本起点。“辨体”范畴有多重内蕴,包括体制为先的尊体观、辨家数的辨析文体风格、辨白是非优劣高下以及辨体辨伪等,其核心观点是“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观,如吴承学先生强调:“以‘辨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首要原则”,〔3〕“古人首先在认识观念上视‘辨体’为‘先’在的要务”,“从而使‘辨体’成为古代文体学中贯通其他相关问题的核心问题。”〔4〕关于“体制为先”的辨体论,也是日本诗话文体学的核心理论范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辨体之为急务。关于“辨体为先”的理论,日本诗话中最具代表的就是长野丰山的“辨体之为急务”辨体论,如长野丰山《松阴快谈》:“有套语有歇后之语,用之诗尺牍小文辞犹可也,至作大议论、大文章,则必不可用也。世之陋儒,大抵不能辨文体,粗心读书,见西土人或用俗语,或用套语,或用歇后之语,不辨古今,不问文体,以为文章皆如此,遂妄用之。曰我有证据,是可笑之甚者。文体之不同,犹画工之于草木禽兽,各别体也。今若画桃施之以兰叶,画虎施之以鹿毛,孰不笑其谬戾也?故欲学作文者,辨体之为急务。”〔5〕他认为,文体不同,有各自特定的语言形式、写作要求和体制规范,即所谓“文体之不同,犹画工之于草木禽兽,各别体也”,比如套语、歇后语这类俗语的使用,在诗、尺牍这类“小文辞”文体还可以,但是在诸如制诰策论等“大议论、大文章”中“则必不可用也”,其错误之根源就在于“不能辨文体”,“不辨古今,不问文体”,也就是不辨古今文体,最后结论是“故欲学作文者,辨体之为急务”,所谓“辨体之为急务”,当然是说“辨体为先”,而这个辨体,就是要辨析并知晓古今各种文体的体制规范,使得“学作文者”在临文动笔时有所分别并加以遵守,也就是尊体,这实则就是中国古代的“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论。
需要注意的是,长野丰山所谓“辨体之为急务”的“辨体为先”辨体论,与“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论还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自刘勰《文心雕龙》至唐人诗格以来,中国古代“辨体”理论的主要言说方式是“文章以体制为先”或“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这类模式,并在宋代形成一股文艺思潮而达于极致,元祝尧则对此说法用“辨体”论进行总结和确立,〔6〕只有到了明代,直接以“辨体为先”进行文体批评的文论家才多了起来,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引明陈洪谟“文莫先于辨体”,〔7〕王世懋“作古诗先须辨体”,〔8〕车大任《又答友人书》:“诗文各有体,不辨体而能有得者,未之前闻也。”〔9〕章潢《图书编》云:“学《易》莫要于玩象,学诗莫要于辨体。”〔10〕其中,“辨体之为急务”之“急务”与章潢“学诗莫要于辨体”之“要于”更接近,当然也即“先于”或“为先”之意。另外,长野丰山活动于清中叶,正见出其辨体理论受明人影响更为直接。
我们说长野丰山直接受明代辨体为先理论的影响更为直接的证据,是其对王世懋辨体论的直接引用,如长野丰山《松阴快谈》:“画法与诗法通者,盖此类也。王世懋《秇圃撷余》曰:‘诗必自运,而后可以辨体。诗必成家,而后可以言格。故予谓:今之作者,但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此数段议论,皆与余意合,故钞出。”〔11〕其中,所谓“此数段议论,皆与余意合”最能看出二者辨体论的影响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长野丰山与王世懋及其明人辨体论的接受关系,我们也把王世懋“作古诗先须辨体”那段经典辨体理论完整“钞出”,以比较对照参看。王世懋《秇圃撷余》:“作古诗先须辨体,无论两汉难至,苦心模仿,时隔一尘。即为建安,不可堕落六朝一语。为三谢,纵极排丽,不可杂入唐音。小诗欲作王、韦,长篇欲作老杜,便应全用其体。第不可羊质虎皮,虎头蛇尾。词曲家非当家本色,虽丽语博学无用,况此道乎?”〔12〕
再如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云:“徐而庵云:‘今人诗,要见好,所以工于字句之间;古人诗,不要见好,所以妙于篇章之外。’洵知言也。今之追逐时好者,不辨体裁,不了章法,以好行小慧为能事,徒争巧于五字七字之间,琢镂凑砌,抽黄媲白,何作何由而得哉?以此博一日之名则可,而遂欲传后世耶?”〔13〕这与宋代学者倪思的那段广为当代文体学者引用的经典论断“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14〕之行文颇为相契。易言之,“辨体裁”就是“文章以体制为先”,“争巧于五字七字之间,琢镂凑砌,抽黄媲白,何作何由而得哉”对应于“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尤其“抽黄媲白”与“抽黄对白”的差无二致尤能看出二者的影响关系。津阪东阳生活的时代也大致对应于清中叶期间,稍早于长野丰山。
其二,先其体制,体制为先。日本诗话中的“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言论文献并不多,也不鲜明,但也能看出其影子。在论诗的诸多要素中,往往借鉴中国诗话诸如皎然《诗式》、严羽《沧浪诗话》之文体论,将“体裁”“体制”“体势”“俗体”列为第一位,可以看作隐在的“体制为先”辨体论,这也以皆川淇园为代表。如皆川淇园《淇园诗话》:“夫诗有体裁,有格调,有精神,而精神为三物之总要。盖精神不缺,而后格调可得高,体裁可得佳。盛唐之诗主兴趣,兴趣亦由此精神而出,要认此所在,须求之冥想中而后得之。”〔15〕皆川淇园认为“精神为三物之总要”,这个“总要”说明了体裁、格调、精神之顺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终点目标是精神,体裁为起点,是开始,也即“体制为先”,这是前所述其辨体理论的另一种形式或者说不同说法。
芥川丹丘则往往引用皎然、严羽这类文献以见其暗含的“体制为先”辨体理念。如芥川丹丘《丹丘诗话》:“四深:体势、作用、声对、义类。释皎然曰:‘气象氛氲,深于体势。意度槃薄,深于作用。用律不对,深于声对。用事不直,深于义类。’余谓:‘气之沛也易失检,意之放也易差运,律之用也易忘黏,事之会也易误类。’”〔16〕四深中“体势”排第一位,即“体势为先”。《丹丘诗话》:“五俗,俗体俗意俗句俗字俗韵:严仪卿曰:‘学诗,先除五俗。’”〔17〕五俗中俗体排第一,还是“体制为先”。再如《丹丘诗话》:“五法,严仪卿曰:‘诗有五法,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余谓:‘体制要正,格力要高,气象要宏,兴趣要新,音节要响。’”〔18〕五法中“体制”排第一,且称“体制要正”,所谓“正体”,与变体相对举,指“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的尊体观。再如《丹丘诗话》:“七德,释皎然曰:‘诗有七德:一识理,二高古,三典丽,四风流,五精神,六质干,七体裁。’余谓:识理贵不暗,高古贵不僻,典丽贵不浮,风流贵不乖,精神贵不露,质干贵不弱,体裁贵不邪。”〔19〕“七德”中“体裁”排最后一位,正说明了“德”作为文章根本是最重要的,是写作的最终目的,而“体裁”作为形式要素是创作中最先考虑的,其实质还是“体制为先”。
除了以上这类隐在的“体裁为先”辨体文献外,还有一种与“文章以体制为先”形式更为相近的说法,如“凡学作诗,须先多诵古人之诗”、“凡学作诗,先欲多诵得古诗”〔20〕、“凡学作诗,当先从七言始”、“其于体,当先从绝句始”〔21〕、“学诗须先多知诗家熟用文字”〔22〕、“学诗先要知调”〔23〕等,也主要以皆川淇园为主。如皆川淇园《淇园诗话》:“凡学作诗,须先多诵古人之诗,又须将其所诵之诗,一一皆领解透彻其意旨,盖诵以参其调,领解以参其格。格调既习,而后可得以参其法。未得参其法,则虽欲扬榷之,亦将何以乎?轻俊子弟,耳食相和,猥品千古,汉、唐必佳之,宋、元鄙之,以‘佳’‘鄙’二字,概而论之,不复究求其故,是以妄称妄举,权衡皆失矣。若此,何以进步?学者不可不以自戒也。”〔24〕其中,所谓“凡学作诗,须先多诵古人之诗”,其后是“格调”,即“盖诵以参其调,领解以参其格。格调既习”,结合上文之隐在的“体裁、格调、精神”顺序,可以看出所谓“凡学作诗,须先多诵古人之诗”中的古人之“诗”重点在“体裁,其“学作诗”中“体裁为先”的辨体观显露无遗。
其三,本色、当行说。宋人针对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的破体现象,往往用“本色、当行”的辨体尊体之论进行文体批评。所谓本色当行,王水照云:“强调的‘本色’即是文体的质的规定性”。〔25〕“尊体,要求遵守各类文体的审美特性、形制规范,维护其‘本色’、‘当行’。”〔26〕宋明诗话中严羽、胡应麟之论最为代表。如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云:“须是本色,须是当行。荆公评文章,尝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胡应麟云:“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27〕
日本诗话中此类颇多,如太宰春台《诗论》:“此诗徒记故事耳,非绝句本色也。”〔28〕指出绝句体制当简洁,不可叙事。再如《诗论》:“此一时者,孟子之言也。于鳞取而入绝句,恐非当行也。”〔29〕认为经史典故不可入于绝句,这违背绝句诗体的自然体格。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七言古诗,一韵到底却非本色。韵不转诗不活。盖波澜变化,顿挫开阖,韵亦随而转,斯见其妙矣。”〔30〕七言古诗在韵律体制上当转韵,不可一韵到底。再如《夜航诗话》:“《枕山楼诗话》曰:扼腕悲歌,风尘睥睨等语,尤不宜轻用。严沧浪曰:‘须是本色,须是当行。’”〔31〕引用严羽之论足见宋人诗话对其影响。它如小野招月《社友诗律论》:“达尝闻或说,诗言志,歌咏言。言志,诗之本色也。有诗而后有歌,盖当初作者,感物言志,咨嗟咏叹,自成音响。”〔32〕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锦天山房诗话:杏坪诗才宏深,远过二兄,七古最当行,虽痛快不及其侄,口所欲言笔能到焉,亦近世之雄也。”〔33〕此不赘举。
二、辨同异真伪是非高下:辨体批评实践
在辨体理论指导下的辨体批评实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最为典型的就是辨作家诗体风格之似与不似,辨不同体裁之间的体制同异,以及辨中、日之间文体同异,主要是和歌与汉诗文体之别;二是,运用辨体作为考据方法和手段辨析古籍诗文真伪,这是宋人欧阳修、朱熹、严羽等辨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诗话中也颇多借鉴这种考证方式进行辨体辨伪;三是,辨体的内蕴之一就是辨清浊、辨工拙、辨是非、辨高下、辨利病、辨雅俗、辨体用等,这在钟嵘《诗品》及严羽《沧浪诗话》中都是纲领性的理论文献,如钟嵘《诗品序》:“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诗集,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34〕其诗学批评方法或者说辨体批评方法就是“显优劣”“品高下”和“辨彰清浊,掎摭病利”。严羽《答吴景先书》所谓“辨白是非,定其宗旨”,〔35〕也是其辨体批评的核心手段。以下分而述之。
其一,辨文体之间的同异。日本诗话中这类辨体文献最多,也是与辨体尊体最为关系密切的一种辨体批评实践。可从如下四个角度来看:一是,辨作家诗体风格之似与不似。往往称“诗体似乐天”“虽类昆体”“而不类常建诸诗”“不类文公作”“格调气韵各自不同”云云,如林梅洞《史馆茗话》:“先是渤海大使裴颋与菅相赠答,谓其诗体似乐天,故御制云尔。”〔36〕安积澹泊《老圃诗膎》:“梁范云字彦龙,皆用事精切,虽类昆体,而气脉深厚。”〔37〕“余窃疑五言律诗中所载常建《泊舟盱眙》诗,虽格律平正,而不类常建诸诗,偶阅《唐诗纪事》,此诗作韦建,而云建与箫颖士最善,据此则韦建中唐诗人也。”〔38〕“今检文集无之,诗亦尖巧,不类文公作,盖嫁名也。”〔39〕芥川丹丘《丹丘诗话》:“宋名家王荆公、欧阳公、苏东坡、黄山谷、陈简斋、陆放翁之类,格调气韵各自不同。”〔40〕二是,辨不同体裁之间的体制同异。往往称“文体已异”“其体相似”“体裁各别”“文体各异”“有同名异体者,有同体异名者”“体制各异”“以诗体玄黄相判也”“不可辨其似与不似也”云云,如长野丰山《松阴快谈》:“有经语,有史语,有小说家之语,有语录随笔之语,论记、序书、尺牍之类,文体已异,语气自别,断断不可混用也。”〔41〕安积澹泊《老圃诗膎》:“《后夜闻佛法僧乌》诗曰……惺窝先生以为集中第一,罗山先生谓唐顾况诗……其体相似,韵亦偶同。”〔42〕虎关师炼《济北诗话》:“凡绝句、四韵,体裁各别。”〔43 〕林梅洞《史馆茗话》:“齐名、以言文体各异。”〔44〕津阪东阳《夜航诗话》:“古诗题目,歌、行、引等,本一曲尔。见少陵作,有同名异体者,有同体异名者,不必拘局也。”〔45〕芥川丹丘《丹丘诗话》:“夫选诗,时代不同,体制各异,安得混称乎?”〔46〕江村北海《日本诗史》:“盖其无信者,以诗体玄黄相判也。……是以万庵诗高华雄丽,百拙诗深艰枯劲。”〔47〕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假使能捉之摹之,亦但不可辨其似与不似也……而后庶几可与可言诗已矣。”〔48〕三是,辨诸家体格之别。辨析不同作家文体风格也即“体格”的不同,是辨体的又一重要内涵,也即严羽所谓“辨家数”,这是在尊体辨体理论基础上的辨体批评实践。如皆川淇园《淇园诗话》:“盛唐诸公体格各别,少陵状物,情态皆切……青莲置思于天地之外……王维如……李颀如……崔颢如……余别有律罫之书,精辨诸家体格之别。”〔49〕首先提出“盛唐诸公”杜甫、李白、王维、李颀、崔颢的“体格各别”,然后用美妙的比喻具体“精辨诸家体格之别”,把“辨家数”“辨体格”之辨体批评实践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属于严羽“诗体”篇的“以人而论”的“辨家数”辨体,其中包括少陵体、太白体、王右丞体。四是,辨中、日之间文体同异,主要是和歌与汉诗文体之别。往往称“夫和歌汉诗,异体同工”“夫和歌者,倭语也;诗者,中国之语也”“汉倭联句,以和歌句,间杂诗句,殊方异言”云云,如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夫和歌汉诗,异体同工,则我藩风雅之兴实胚胎于此。”〔50〕太宰春台《斥非》:“夫和歌者,倭语也;诗者,中国之语也。如之何相通?可谓违理也。好古君子所宜戒也。”〔51〕再如《斥非》:“联句自唐人为之,本有体裁,实诗之属也。虽今人仿古人为之,不失其体,何不可之有?惟倭儒所为联句者,别有一法,大非古制。且其为辞,鄙俚猥琐,去诗远甚。又有一种汉倭联句,以和歌句,间杂诗句,殊方异言,联缀成篇,动五十韵至一百韵,乖戾不伦,令人厌恶。”〔52〕
其二,辨真伪,辨体与辨伪。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辨体作为一种考据方法往往成为学者辨伪的工具和手段,这在宋代以欧阳修、朱熹、严羽最为代表。辨体作为辨伪的方法和工具时,主要是运用辨体内蕴中“辨家数”和“辨体格”,包括辨严羽“诗体”篇“以人而论”的作家风格和“以时而论”的时代风格。如东梦亭《锄雨亭随笔》:“鲍明远诗:‘归花先委露,别叶早辞风。’余谓此句入宋人集中不可得辨。”〔53〕鲍照作为南朝宋元嘉三大家之一,有独特风格,而此诗之哲理性有宋诗体格,故而称“此句入宋人集中不可得辨”。再如《锄雨亭随笔》:“六朝诗风一变,遂开唐人律诗之源。吕让《和入京诗》云……明余庆《从军行》云……此等诗,搀入唐人集中不可复辩。”〔54〕明余庆《从军行》与唐吕让《和入京诗》风格相似,皆悲凉放旷,故而称“此等诗,搀入唐人集中不可复辩”。其他如唐宋诗之争及唐体与宋体之辨尤多,下文再述。再如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况独出手眼,别裁伪体,定众作之权衡,揭诗道于日月者,自有其人。”〔55〕杜甫“别裁伪体”说最能体现辨体与辨伪这一辨体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友野霞舟的引用尤能看出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文体理论的了解和借鉴。
其三,辨工拙、辨是非、辨高下、辨雅俗、辨体用等。辨工拙是非,安积澹泊《老圃诗膎》:“明人不嫌其蹈袭,取而入选。世必有能辨其工拙者也。”〔56〕太宰春台《斥非》:“夫是非无定体,人之是而我以为非,我之是而人以为非,是非之争,虽历千载,孰能辨之?……为文辞者,苟效华人,则当以华人为法。此辨是非之公案也。”〔57〕
辨高下、尊卑、优劣。皆川淇园《淇园诗话》:“闻其所言,乃云诗寄兴而是,何必论体格之高卑?……据此,少陵未以绮丽为当行也。夫古今诗人,未有不宗少陵者,虽以元轻白俗,亦靡有异论,则‘何必论体格之高卑’之言,余恐虽元、白亦耻作此语。”〔58〕长野丰山《松阴快谈》:“柳子厚状段太尉逸事,咄咄如生,与马迁相上下,而其作南霁云庙碑,皆骈俪之语,盖柳文佳者绝佳,而不免驳杂,固不如韩文之篇篇皆高古绝妙也。”〔59〕再如《松阴快谈》:“秦汉古文,大抵粗枝大叶之文,气骨雄壮,豪荡不羁,所以为高也。清人之文,唯于枝叶上粉泽,是所以不及也。”〔60〕
辨雅俗难易。小野招月《社友诗律论》:“故谓词曲盛而律诗可废者,由不辨徒诗乐府也。怪词曲少而律诗多者,由不辨雅俗难易也。”〔61〕
辨体用。皆川淇园《淇园诗话》:“诗写情,须必有体,有用。体,则未入场前,心本已有蓄之者是也。用,则凡应物而感,触境而生之属皆是也。盖体为内,用为外。”〔62〕久保善教《木石园诗话》:“故诗之有三体三用,犹机之有经纬也。三体各交三用成之,而诗道备焉,是则学诗之第一义也。”〔63〕加藤善庵《柳桥诗话》:“帘动香满,以有微风也。无微风,则帘不动,香不满也。体用兼该。”〔64〕
辨文气之强弱、体格之清浊。长野丰山继承曹丕的文气文体论,主张辨析文气文体之平易和艰涩,这必须具备一定的辨体能力、眼光和识见,才能够辨别出“孰强孰弱,孰优孰劣,孰奇孰拙”,也即“具眼者必能辨之”。如长野丰山《松阴快谈》:“文之强弱在气,而不在辞。世有以艰涩为强,以平易为弱者。东坡之文,平易著明;于鳞之文,艰涩隐晦。然孰强孰弱,孰优孰劣,孰奇孰拙,具眼者必能辨之。魏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是千古之确论也。”〔65〕熟识并重视中国古代文气理论是长野丰山的一贯做法,如把韩愈的“气盛言宜”说看作“作文之要诀”,这与称赏曹丕的文气文体论为“千古之确论也”如出一辙。如《松阴快谈》:“韩文公论文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可谓作文之要诀矣。”〔66〕
辨析诗体用语之宜与不宜。辨析五言、七言诗用字方面关于字面、语短语长或语势曼促之语体不同,这属于辨体内涵之辨析语体差异的典型,如皆川淇园《淇园诗话》:“连熟字面,或有宜用于五言,而不宜用于七言。其辞意颇促急者,宜用于五言,不宜用于七言。大抵五言语短,用字不妨意急节促;而七言稍长,语势动苦弛散,若杂意急节促之字面,一句之间,一曼一促,调之甚难,不可不辨也。同是七言,而古、律、绝已异其体,则其调之之法,亦各有其所宜。律句要浑圆而有力,古诗句要流畅而宕,绝句要含蓄有响,五言仿此。”〔67〕不单要辨五七言诗体之别,而且即便同是七言,“古、律、绝已异其体”,也“不可不辨也”,可见“辨体”的重要,在创作和批评中是一时也离不开的。
以上辨体文献皆出于皆川淇园和长野丰山的诗话中,二者分别是文化和天保年间去世,约生活时代对应于清中叶嘉、道年间,但是这种辨体观可以追溯到日本第一部诗话虎关师炼《济北诗话》中:“诗赋以格律高大为上,汉唐诸子皆是也。俗子不知,只以夸大句语为佳,实可笑也。若务句语之人,不顾格律,则‘大言诗’之比也。‘大言诗’者,昔楚王与宋玉辈戏为此体,尔来相承,或当优场之欢嬉,盖诗文一戏也尔,岂风雅之实语与优场之戏嘲并按耶!近代吾党偈颂中,此弊多矣,学者不可不辨矣。”〔68〕所谓“戏为此体”“优场之欢嬉”“诗文一戏也”“风雅之实语与优场之戏嘲”“偈颂中,此弊多矣,学者不可不辨矣”云云,显然属于辨析雅体、俗体之别,这是宋代辨体的主要内涵之一,而虎关师炼生活于元初,其对宋代文体学尤其是辨体理论的了解和继承也显而易见。
三、唐宋诗之争与唐宋体之辨
自南宋以来,唐宋诗之争便成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经久不衰的学术论题,其表层意涵是辨唐诗、宋诗之优劣的问题,深层上是唐体和宋体何者为高为尊、何者为下为卑的辨体理论,而根本上则是关于辨体和破体这一对立的文体学核心理论范畴,即唐体是诗体尊体的典型,而宋体之“以文为诗”则是诗体破体的模范。大致有两类意见:一是唐体高于宋体,宋诗一无是处;一是唐诗高于宋诗,但宋诗也有优点,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甚至达到能与唐诗比肩的高度。
日本诗话中唐诗宋诗之争的文体文献极为丰富,故而我们在此辟专节来谈。很多诗话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如蔡镇楚《中国诗话与日本诗话》:“中国诗史上的‘唐宋诗之争’波及日本诗坛,或尊唐,或崇宋,亦相为论争。”〔69〕张伯伟《论日本诗话的特色——兼谈中日韩诗话的关系》:“释显常《诗语解题引》云:诗之与文,体裁自异,而其于语辞,亦不同其用。大抵诗之为言,含蓄而不的,错综而不直,而其所使之能如是者,正在语辞斡旋之间。诗文之所以别,唐宋之所以殊,皆以此。”〔70〕
首先,唐体宋体之辨、宗唐与宗宋。唐宋诗之争的本质是唐体与宋体之辨,这在严羽《沧浪诗话》中已经对此有了明确的定位。日本诗话中,久保善教是将辨体论与唐宋诗之格调体制论争结合在一起的重要文体学者,如久保善教《木石园诗话》:“学诗先要知调,唐宋自有唐宋之调,元明自有元明之调,岂可混乎?明之而后可以言诗也。余视近世名家诗,宋唐相混,元明相杂,夐然一调,是以一句肖少陵,一句肖东坡,一首之中,意味不接者,间亦有之。”〔71〕所谓“学诗先要知调”,正是“文章以体制为先”的翻版,这个“调”指格调、体调、体格、体制,这是辨体理论概括。接下来,具体指出唐宋之调间的辨析、元明之调之间的辨析及其唐宋之调与元明之调之间的辨析,都属于辨体批评,即所谓“唐宋自有唐宋之调,元明自有元明之调,岂可混乎?明之而后可以言诗也”,这也属于严羽诗体篇“以时而论”的时代风格辨体,也就是说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文体风格和格调,无论在学习创作时还是批评接受时都要具备一定的辨析识别能力,可见辨体已经成为一种学习、创作及批评的素养能力,必须要深入理解和明了并全面培养和训练,只有这样才有评诗言诗的资格,或者说评诗论文时才会更科学、更公允,所谓“明之而后可以言诗也”。可以说,久保善教的辨体论总体上为唐宋诗之争的辨体理论倾向定了“调子”。
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形。
其一,崇唐抑宋。在具体论述和辨体批评中或明确褒贬,或暗含是非。如太宰春台《诗论》:“……此诗全似宋人。《和答殿卿》曰:‘白眼风法一酒卮,吾徒犹足傲当时。’此一、二句非唐诗之调,只是宋诗之下调。‘吾徒犹足傲当时’只是平常言语,非诗语也。……谓予曰:‘于鳞绝句非唐调。’因举此二诗三、四句而曰:‘此似谜语。’予亦不能诘。……此皆太多,其诗大抵多用故事,饤饾成章,非以写情胜者,徒斗才而已,岂绝句本色哉?比之唐诗,见其实不如也。”〔72〕再如《诗论》:“蔡蒙斋《联珠诗格》所载宋人之诗多似此体,唐诗希有。末句‘声’字独平,亦为声病。”〔73〕太宰春台通过辨析,认为“于鳞绝句非唐调”,是因为“多用故事,饤饾成章”,“徒斗才而已”这正是秉持严羽以来指责苏黄为代表的宋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学问为诗”的批评标准,而“岂绝句本色哉”(按本色当行说是宋人以来辨体尊体的换一种说法,日本诗话中也颇多文献)则更说明了这是一种明确的辨体批评。唐诗是以“以写情胜者”,这也是诗体具有的最应遵守的体制规范,是从钟嵘、皎然、严羽以来批评家所普遍认可的,严羽推崇李杜为代表的唐诗来反对苏黄为代表的宋诗,就是认为唐诗具有“兴趣”“妙悟”和“吟咏情性”的本色当行特征。其中,“此一、二句非唐诗之调,只是宋诗之下调”,则明确体现了唐诗体格高于宋诗格调的崇唐抑宋倾向。
皆川淇园则从声律、声调着眼,并结合“诗本吟咏性情”的本色尊体特征,来辨析唐体宋体并品评高下,如《淇园诗话》:“唐人声律未甚严,而宋人已降拘束日甚,殊不知古韵多三声相通用。如宋礼部韵,本非唐人之旧也。后世乃奉之,殆如金科玉条,岂非可笑之甚?《诗话》载:宋秦少游诗律极严,当时讥其人小石调。据此,则宋人声律,尚未甚极其严,至明李攀龙辈,苛刻严急,不容细过,其意盖恐人或指摘之也,殊不知诗本吟咏性情,略调声律可歌则可矣。”〔74〕所谓“唐人声律未甚严,而宋人已降拘束日甚”“殊不知诗本吟咏性情,略调声律可歌则可矣”,都是继承了钟嵘、皎然、严羽以来的诗体本色当行说。
其二,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这是日本诗话的主流,以菊池五山为代表,他如津阪东阳、长野丰山、久保善教、皆川淇园、友野霞舟等都持这种通达观念,所言诸如“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唐宋皆吾师”“历代之诗,各有所长”“唐诗有唐诗之妙,宋诗有宋诗之妙,而唐宋诸家各有悟入自得处,都不一般”“譬诸饮食,各有所嗜”“我不必唐,不必宋,又不必不唐宋”“唐诗自有唐诗字面,宋诗自有宋诗字面”等等。如: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唐宋之辨,人动问及,余亦难言之。……诗云:“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宋人生唐后,开辟实难为。……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75〕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唐人诗不胜学,宋人学不胜诗。唐诗温润,有春水四泽之象;宋诗磊砢,有冬岭孤松之象。唐则满朝诗人,宋则不过数家,只斯数家,优足与全唐诗人抵敌,此宋诗所以称雄也。〔76〕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唐诗自有唐诗字面,宋诗自有宋诗字面,今人不择,随手混用,殊为欠炼。〔77〕
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余尝言:历代之诗,各有所长,择其善者可也,何必一概以世废言。元享以来,明诗盛行,宋诗则弃如粪土耳。……时风之所靡,好尚无定,如此不亦太甚乎?……予闻人论诗好争唐宋,必以先生此语晓之。〔78〕
长野丰山《松阴快谈》:唐诗有唐诗之妙,宋诗有宋诗之妙,而唐宋诸家各有悟入自得处,都不一般。如韩柳欧苏王曾之文,欧虞颜柳蔡米苏黄之书,莫不皆然也。学之者亦各学其所好可,其所好者,便其性情之所近也。譬诸饮食,各有所嗜。〔79〕
长野丰山《松阴快谈》:客问余曰:“子学诗,唐耶?宋耶?”曰:“我不必唐,不必宋,又不必不唐宋。”可见“不必”二字,是我宗旨也。〔80〕
久保善教《木石园诗话》:近世伪《唐诗选》行,绝无知宋诗之精灵者,尚却之为近偕语。璧之不知味者,犹未食大牢之羹,而论之味也,故轻视宋诗为唐之奴隶也。唐诗固善矣,然唐诗既为于鳞、元美见腐,则其陋极矣。〔81〕
从以上文献中所言诸如“唐宋之辨,人动问及,余亦难言之”“时风之所靡,好尚无定,如此不亦太甚乎”“予闻人论诗好争唐宋,必以先生此语晓之”“近世伪《唐诗选》行,绝无知宋诗之精灵者”等可以看出,“宗唐宗宋”或辨体唐宋是日本文化、天保前后文坛诗歌学习的取法对象和创作标准,也是批评界争鸣的核心论题,这可以说是中日文学之间尤其是文体学之间影响关系的一种折射和缩影。
其三,菊池五山的伪唐诗和伪宋诗之说,则从学诗的角度说明了辨体真伪及其“得体”“尊体”的必要。如: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解题:自山本北山排击伪唐诗,海内靡然向宋诗,然其所谓宋诗,非真宋诗。故五山入市川宽斋江湖诗社,又排击伪宋诗。〔82〕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山本北山先生昌言排击世之伪唐诗,云雾一扫,荡涤殆尽,都鄙才子,翕然知向宋诗,其功伟矣。余谓先生曰:伪唐诗已鏖矣,更有伪宋诗。〔83〕
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均之伪也。唯作伪唐诗者,刻鹄类鹜,其言虽笨,犹且不失君子体统;宋诗失真,则画虎类狗,其言庸俗浅陋,与徘歌谚谣又何择焉?竟使耳食者谓宋元诸诗率皆如此,而并薄之也。乃嘐然自称宋诗,妄不亦甚乎!其病坐不才无识而已。故学宋诗,必须权衡,唯有才识可以揣度,不然,则鄙俚公行,几亡大雅,不如作伪唐诗之为犹愈也。〔84〕
从以上三则文献可以看出,菊池五山从日本当时弃唐转宋的创作风气出发,认为唐宋诗之争的焦点不是何者高下尊卑的辨体优劣问题,关键是如何在学习中辨析真唐诗真宋诗,这涉及到取法对象的难易问题,他认为宗唐容易,即便学不好,“犹且不失君子体统”,但是,“学宋诗,必须权衡,唯有才识可以揣度,不然,则鄙俚公行,几亡大雅,不如作伪唐诗之为犹愈也”,这是由宋诗好用俗语谚谣的特点决定的,有才识的大家诸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虽运用但避免弊病,否则就会“画虎类狗,其言庸俗浅陋,与徘歌谚谣又何择焉”,其实质就是关于唐体宋体的辨体理论问题。此外,除了唐宋之争外,日本诗话学者还结合当时的创作和批评实际,对宋诗明诗的宋明之争有所反映和关注,此不赘举。
要之,日本学者对于唐宋诗之争这样的时代风格辨体问题所秉持的态度整体是通达的,而长野丰山所谓“辄以世代为高下,是耳食之言耳”“岂得拘世代哉”,以及友野霞舟所谓“于文不必汉,于诗不必唐,将集众美以成大者也”“文不必汉未尝不汉;诗不必唐未尝不唐。而二者杂诸宋,未尝堕宋”则更为宏通,可以为此论作结。长野丰山《松阴快谈》:“世儒论诗文,辄以世代为高下,是耳食之言耳。诗文之佳恶在人而不在世,在诗文而不在人,惟具明眼而能公判者可与论诗文矣。”〔85〕再如《松阴快谈》:“前人不必胜后人。如《列子》之不及《庄子》,左氏之不及司马,范晔之不及陈寿,《晋书》之不及《五代史》,诸皆是也,岂得拘世代哉?”〔86〕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余尝过其房,见几上有《端明集》,乃亦知其于文不必汉,于诗不必唐,将集众美以成大者也。退省其所为,文不必汉未尝不汉;诗不必唐未尝不唐。而二者杂诸宋,未尝堕宋。则虽所不必守乎,而竟未得不以家风矣。”〔87〕
其次,四唐体格之辨。不单是唐宋元明不同朝代诗体风格不同,需要辨析,而且同一朝代不同时期也要辨体,这以唐代初盛中晚为代表。初盛中晚之四唐文学史分期划分,自宋严羽、元祝尧就已开始,到明高棅而定型,成为现当代唐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学者的普遍共识。其划分依据涉及到时代政治哲学思想文化学术等复杂因素,但核心则是根据初盛中晚四期的诗体风格不同来划分的,如前所言,最初严羽“诗体”分初唐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及晚唐体就是证据。所以四唐之辨析大体都是关于体格风格之区别,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例子在在皆是,日本诗话中亦如此,常常用气格、体格、格调、声调、体制、气象、精神、繁缛雅健、神采生色、调峻辞急等语词概念道出。
此论以皆川淇园为代表。皆川淇园继承严羽“诗体”篇“以时而论”之“辨体格”的时代风格辨析,认为“初、盛、中、晚四唐之别,其风格各异,本不得相同。”针对“近有人欲混而一之”的不能辨体,称“可谓不能辨菽麦者矣”,进而指出明人模仿盛唐风格的“失之皮相”,其原因也是不辨四唐时代体格有别的缘故。皆川淇园《淇园诗话》:“初、盛、中、晚四唐之别,其风格各异,本不得相同。近有人欲混而一之,可谓不能辨菽麦者矣。明一代诗人,务模拟于盛唐,而优孟竟与真叔敖不相近,盖风度虽类,而精神大远。明人志气轻佻,而语皆促迫;盛唐之人志气安舒,而语皆优柔。虽言时风不同,而要之明人于唐诗,失之皮相故也。”〔88〕严羽“以时而论”辨析分别的不同时代诗体包括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其后就是初唐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然后是宋代的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89〕其中大历体和元和体就是中唐体。如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汉魏六朝,唐宋金元,以逮乎明清,靡不世有作者。一代自有一代之诗,指归虽同,气格各异。且以唐一代犹有初盛中晚之别,王孟韦柳,李杜韩白,皆异其撰。宋元以下,莫不悉然矣。此岂有法令驱之,赏罚导之哉?风气所趋,虽作者亦有自不知其然而然者也。古云:诗道与政升降,信不诬矣!”〔90〕所谓“一代自有一代之诗”的文学发展观,及其“且以唐一代犹有初盛中晚之别”,都是因“气格各异”,这个“气格”就是体格、体气,可见终是辨体。其他大致如此,罗列于下,以见大概:
皆川淇园《淇园诗话》:盛唐诸人作乐府诗,皆欲其入于歌咏,是以规模务宏远,……中唐此风尚盛,至白居易更欲其惬于俗听……于是诗体一变,鄙俚满篇,而雅响正音扫地而尽矣。然晚唐李贺七言歌行,尚入筚篥平调,则可见唐一代诗人,皆亦莫不以其入歌咏为主矣。宋元以来诗歌分行,而诗竟如哑钟,徒供观览耳。降至明人,竟巧于饰辞,夸博于用事,调峻辞急,意短气佻,殆所谓五降之后不容弹者矣。〔91〕
皆川淇园《淇园诗话》:其谈诗特于精神格调缱缱致意,而一以盛唐为标准。钱、刘以下则不屑,其论四唐之品,及明人之失,衡悬度设,不失平量。〔92〕
皆川淇园《淇园诗话》:晚唐之人,气象衰飒,……盛唐决无此等诗,……必能在此三字上更下一段工夫,而以成一篇绝妙佳诗,此乃盛唐晚唐之别也。〔93〕
皆川淇园《淇园诗话》:初唐七言古诗,辞虽过繁缛,而作者主意,率亦皆在以此写其神彩生色。盛唐去繁缛,尚雅健,而用笔稍兼有流动之态。中唐乃喜事流动,而不知写神彩生色之为善。〔94〕
芥川丹丘《丹丘诗话》:弇州《咏物》六十首,体格卑卑,中、晚色相。〔95〕
四、变体中变体与常极而变生
辨体与破体,或者说尊体与变体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的一组对立范畴,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辨体尊体是根本、是基础,但其弊端是循规蹈矩,拘执保守,这就需要破体变体,革故鼎新,创变出奇。这种文体上的变体革新规律,也是文学发展演变的必然,如同文学史上的正变观。与之最为相近的对立范畴有正体和变体,得体与失体,实则就是正与变、常与变或正与奇的关系。日本诗话中津阪东阳、太宰春台、芥川丹丘、友野霞舟等都崇尚变体变格,相关正变、常变、正奇关系的文体文献言论都很丰富。
其一,正熟而奇出,常极而变生,变体中变体耳。关于正奇、常变、正变关系中,更为重视变体出奇的,以津阪东阳为代表,两次提到“正熟而奇出,常极而变生”,其他诸如“变体中变体耳”“常法辄用奇法”之类肯定奇变的说法也很多。如津阪东阳《夜航诗话》:“凡诸学技艺者,正熟而奇出,常极而变生,盖不期然而然尔。《芥子园画传》所谓‘有法之极,归于无法’,不唯绘事也。若未习之常而欲试其变,变未可得,而先失其常。犹寿陵余子学步于邯郸,未得国能,而又失其故步,直匍匐而归耳。况夫艺文之业,尤宜守其正也。山谷云:‘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东坡云:‘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也。’此艺苑要诀,药石于时弊。学者才习操觚,未知常法辄用奇法,未问正路辄走邪路,务安僻字,肆骛险语,使人难诵而难解,亦将何用哉?徒贻笑于大方耳。”〔96〕再如《夜航诗话》:“钱虞山云:‘诗到真处必平平,到极处即奇。’善哉其言之也。盖至其上达,正熟而奇出,常极而变生,换骨脱胎,从心所适,亦莫之遏御也。”〔97〕
可以看出,津阪东阳反复提到所谓“正熟而奇出,常极而变生”,是认为由正入奇、自常达变是文体发展演变的必然规律,但这种演变是有先后次序的,所谓“若未习之常而欲试其变,变未可得,而先失其常”“未知常法辄用奇法,未问正路辄走邪路”,也就是说辨体尊体或者说正体常体是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所变化,进行一定的变体。这种创作中要遵循的正变关系及先后顺序,他还用学习书法的比喻形象地进行说明,如《夜航诗话》:“书法备于真书,溢而为行草,故学书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焉。有不善楷法而能作纵体者哉?今人多尚行草。未始学真而径习草,犹未能庄语而辄放言耳。”〔98〕关于正体与变体包括破体本是书法理论概念,真书为正体,行草乃真书之变体。必由正而变,“故学书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焉”,所谓“未始学真而径习草,犹未能庄语而辄放言耳”,正如“若未习之常而欲试其变,变未可得,而先失其常”。
其二,拗体,变体中变体。津阪东阳在先正后变的前提下,还指出破体是有限度的,不能入于怪癖奇险,要适度,不能“务安僻字,肆骛险语,使人难诵而难解”。但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可以允许出奇,如唐诗中的“拗体”“拗格”,这是“变体中变体”,如《夜航诗话》:“韵脚若三平相连,对句亦叠三仄以应之,唐诗拗格中往往有之,是鹤膝病之尤者,变体中变体耳,故非拗体者未尝见之也。……凡名贤高作,或不拘绳墨,如拗体、出韵等变格,以瑕不掩瑜不弃焉。”〔99〕这种拗体,正如津阪东阳前所引苏轼所云“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也”,可以适当允许保留,即“以瑕不掩瑜不弃焉”。
对于拗体的声律之变,小野招月认为唐人以来律诗声律有严格规定,但可以有所变化,不可拘执,即“有唐之人虽创定声律,而往往不拘声律,有变体,有拗体”,但是这种拗体之变,也是如苏轼所云“其变之,非误而犯之也,不得已而变之也”。如小野招月《社友诗律论》:“有唐之人虽创定声律,而往往不拘声律,有变体,有拗体,有当平而仄,有当仄而平,是变之也。其变之,非误而犯之也,不得已而变之也。”〔100〕
所以对于拗体的这种融通态度,无疑是一种文体通变观,即小野招月所谓“学者宜论声律,而不拘泥声律亦可也乎”,太宰春台所谓“故法不可不守,而贵通变”,如小野招月《社友诗律论》:“……加之自举业之学行,声律益严,是以失律拗体不入举场,……虽盛唐名家,间有失律拗体,……若杜少陵,包含汪洋,变化无穷,可谓诗中之天籁矣,孰知声律之外,别有一唱三叹之音也。学者宜论声律,而不拘泥声律亦可也乎。”〔101〕如太宰春台《斥非》:“今人固守声律者,虽无失于法,而诗亦不能佳,泥也。故法不可不守,而贵通变。是故诗苟及古人,虽拗体,尚可为,况失黏乎?”〔102〕
拗体显然是相对于“正体”的变体,即太宰春台所谓“拗体非唐诗之正也”,他通过辨体,认为五七言律绝中,“唯五言绝句不嫌拗体,以贵高古,故不必声律谐和也”。太宰春台《斥非》:“拗体非唐诗之正也,唯五言绝句不嫌拗体,以贵高古,故不必声律谐和也。五言律及七言绝句尤要声调。唐人间作拗体者,亦遇佳境时为之耳,是故拗体必得绝唱而后足采览。”〔103〕
日本诗话中只有芥川丹丘对“拗体”持完全否定态度,他引用皇甫子循所言“诗苟音律欠谐,终非妙境,故无取拗体”,认为“此最正论”,并强调老杜拗体变律不可为法,即“北地学少陵多变律,初学不可楷则矣”。芥川丹丘《丹丘诗话》:“皇甫子循曰:‘诗苟音律欠谐,终非妙境,故无取拗体。’此最正论。声律严密,莫如济南焉,其《选唐诗序》曰:‘七言律,诸家所难。子美篇什虽多,愦焉自放矣。’盖讥其多拗体也。北地学少陵多变律,初学不可楷则矣。”〔104〕
其三,关于文学史上文学的演变盛衰,其实质就是文体上的变体盛衰。如久保善教《木石园诗话》:“物盛必衰,犹四时之相循环,周道既衰,春秋变为战国之世。屈平起于楚国,始作骚辞,其体大变。及汉扬雄、相如之徒作赋,于是三百篇降而为辞骚及赋。……其后天下分为三国,又为南北两朝,为宋为齐,为梁为陈,为后魏、周、隋诗,于是诗道愈衰,仅不绝如缕。时至运开,天与诗道于唐,而使之又振,由之诗道复兴。……故诗风亦小变。遂为五代,其诗纤佻薄弱,日以沦胥。宋兴乃有四大家,范、陆、苏、黄之徒,皆经豪迈之气,卓识之见,脱李唐五代旧习,别开一家机轴,大唱清新之诗风,宋诗殆欲驾唐而上之。及元,虽诗风小变,率祖宋人,但作者尤少,元虞、范、杨之徒,仅仅可数耳。及明,作者互出,其最巨擘者,刘伯温、高季迪之徒也。加之李献吉、何仲默并起,以腐陈为趣,以剽窃为工,是以风格愈变愈衰。……其余教犹未变,施及清代,于乎,中郎之洪福,岂不亦大乎,是古今诗道之大变也。”〔105〕可以说就是一部自先秦至清代的文学发展史或者说文体盛衰演变史。文中所谓“其体大变”“诗道愈衰”“诗道复兴”“诗风亦小变”“虽诗风小变”“是以风格愈变愈衰”“其余教犹未变”“是古今诗道之大变也”云云,足见久保善教是有意识地将变体批评作为方法进行文学批评的。
太宰春台《诗论》也是从《诗经》、《楚辞》、汉赋、张衡七言、建安五言的文体变迁描述了先秦至魏建安文学的发展,既有诸如“四诗之体一变”“后又一变为赋”“而小变其体”之类的变体批评,又不乏“此等为辞短简,调近‘风’‘雅’”“则《楚辞》之体,非古诗之调也”“皆异于四诗之体”之类的辨析文体同异。〔106〕
江村北海《日本诗史》还指出这种文体变迁的原因是时代政治之治乱兴衰,即“气运”,所谓“而诗体每随气运递迁”“气运使之者非耶”“是古诗渐变为近体”,〔107〕友野霞舟也称“诗之随时运”、“体裁兴致随境而变”、“文体变迁须‘观世道之升降矣’”〔108〕、“夫诗之随时运”〔109〕、“体裁兴致随境而变”〔110〕,这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的文学史观很相近。
其四,作家诗体屡变及变体批评。关于作家诗体屡变,是说一个作家的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年龄、阅历及师法对象不同而改变。往往称“诗体屡变”“老年稍变格”“格调数变”“变幻百出”“不固守一格,愈变而愈妙”“中年变格”“一变而香,再变而剑南”“乃更体格”云云,这方面以友野霞舟所论最为丰富也最为精辟。如江村北海《日本诗史》:“余按:蜕岩诗体屡变,为唐,为宋元,为初明,为七子,为徐文长,为袁中郎,为锺谭。”〔111〕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安受道士)喜明七子体,老年稍变格。”〔112〕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原善公道曰:蜕岩以诗豪压一时,而意见屡改,格调数变,皆足以惊人。自言初学宋欧、苏,而旁放翁、简斋,中年学唐,祖祢李、杜,缘饰以钱、刘诸家,又退学明,甘为王、李银鹿,亡几,为袁中郎,为徐文长,而遂以初盛唐为表准。”〔113〕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角田简大可曰:蜕岩诗才高妙,变幻百出,奇正互用,而极力锻炼,兀兀不休,自少至老,诗体屡变。”〔114〕再如《锦天山房诗话》:“独蜕岩泛爱博纳,出入诸家,不固守一格,愈变而愈妙。”〔115〕诸家皆针对“蜕岩诗体屡变”,赞赏其“不固守一格,愈变而愈妙”。再如《锦天山房诗话》:“子静于学精敏,最长乎诗,篇什颇富,清丽奇峭,无所不有,其初为樊川,一变而香,再变而剑南,终又镕陶诸家,别出杼轴,亦非一体。”〔116〕再如《锦天山房诗话》:“最好诗赋,初从刘文翼游,后悟其非,乃更体格,专宗剑南,海内诗风为之一变。”〔117〕再如《锦天山房诗话》:“尊者诗初年犹作时调,中年变格,专出入于香山、剑南之际,其七言律有逼肖放翁者,晚年渐流颓唐。”〔118〕长野丰山感叹杜甫诗体之“千变万化”“出入纵横”,称赞韩愈“波澜横溢”“殆不可拘以常格”,更具辨体破体批评的通变观。如长野丰山《松阴快谈》:“杜诗长篇,或用一韵,短篇却屡换韵,千变万化,可以见其出入纵横之才矣。”〔119〕
其他各类相关的变体批评文献还很多,如津阪东阳《夜航诗话》往往称“故变态少,观其体格”〔120〕、“嘉隆伪体”〔121〕、“格局变化”、“篇篇体裁同一,机轴略无变易”〔122〕、“若用仄韵,变体耳”〔123〕,芥川丹丘《丹丘诗话》称“杜子美体制格式自成一家”〔124〕、“七言歌行,太白间用长语,亦是其变化处”〔125〕,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称“体裁虽合,意兴索然,乏变化故也”〔126〕等。
其五,定体无定体、定法无定法。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上,辨体与破体或尊体与变体的辩证关系,还常常用定体无定体与定法无定法的对立组合范畴来表示,其中辨体通变观与宋代吕本中“活法”论极为相似,且往往“体与法”并谈,也是正与变、正与奇的关系。日本诗话中学者对此理论的态度总体是变通的,首要的是要守法,但守法而不拘于法,要有所变化,以长野丰山为代表。
一方面,主张坚守法度,认为文章有定法和定体,创作中要严格遵守,不能失法、失体,秉持辨体尊体观。如长野丰山《松阴快谈》:“本邦儒者作文,多未知篇法而妄作也。太宰德夫《文论》曰:‘文有四法:曰篇法、曰章法、曰句法、曰字法,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四者皆有法,一失其法,则不成文矣。先秦古文,以至韩柳二家,森然法度,历历可考,近世古文辞家作,今观其文,非不工也,惟其字与句有法,而章与篇皆失法,故气脉不贯,不足观也。’善哉!太宰氏之言。……盖用力于文辞者,莫如徂徕之徒,而其所作,犹多失篇法如德夫之言,况他人乎?夫失字法句法,是小疵耳,至失篇法,则安在其为文哉!”〔127〕所谓“四者皆有法,一失其法,则不成文矣”,对篇法、章法、句法、字法都很重视。
再如反对“作古文者,不必拘法可”的说法,认为“后之学文者,不得不依其法,犹作诗者不得不依沈约之韵也”。如长野丰山《松阴快谈》:“客问曰:‘六经左国史汉皆古文也,篇章这间,固非无法,然岂一一合后人所说哉?作古文者,不必拘法可。’余曰:‘否。子欲知议论文法,且试读《孟子》《庄子》;欲知叙事之法,且试读《左传》《史记》。反覆以索其结构之法,久之自了然矣,不必须多辨也。今夫世人孰不读孟庄左史,但粗心读过,生吞活剥,不知其法之所在耳。且夫韩柳欧苏八家之文,已为千载之宗师,后之学文者,不得不依其法,犹作诗者不得不依沈约之韵也。’”〔128〕再如《松阴快谈》:“余谓学文者先学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犹学诗者先学平仄、排比、句法、韵脚也。”〔129〕
另一方面,长野丰山也提倡“有正有奇”,奇正相生,认为“正者,法度如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为法度所缚,千变万化”,才“是论文之尤善者”。如《松阴快谈》:“元吴莱论文曰:‘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如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为法度所缚,千变万化,坐作击刺,一时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还其队,元不曾乱。’是论文之尤善者。”〔130〕以用兵之法为喻,“譬犹军法,左右前后,坐作进退,皆有法度,而战开之际,变化不测,出奇无穷也”,来说明“文法甚严且明,而本无定法”。再如《松阴快谈》:“文法甚严且明,而本无定法。一篇之中,有起结、照应、波澜、转折、起伏、顿挫、抑扬等之法,可一一指示,而非有几句必转折,几段必照应之定局也。譬犹军法,左右前后,坐作进退,皆有法度,而战开之际,变化不测,出奇无穷也。善作文者,穷言竭论,如意已尽,忽又一转,更出人意表,而照右应左,结前起后,未尝出范围之外。”〔131〕
他处诸如此类的说法颇多,以长野丰山《松阴快谈》为代表,往往称“奇奇怪怪,不与法期而与之合”〔132〕、“明清人作时文有定法”、“古诗无定法而恰有法,然非如近体之平仄一定”、“古文无定法”〔133〕、“固守规矩,而不敢胡乱下一笔也”、“自首至尾唯是一法,少变化”、“所谓神明于法者”〔134〕、“一气流贯,纵横驰骋,不失法度,乃称作手”、“纵横驰骋,无规矩法度,则是风颠汉之絮语,岂成言语哉”〔135〕、“礼未始有定论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外,则亦未始无定论也。执其无定以为定论,则涂之人皆可以为礼”〔136〕、“则自然活泼不死矣”〔137〕等等。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则屡屡称“然其声律动失法度”〔138〕、“不墨守家法”〔139〕,小野招月《社友诗律论》称“夫律者有一定之法,而未始有一定之间法也。律者有一定之法,而聆之者未得一定之法也,聆之难也”〔140〕、“诗人不可无格调。但好谈书法,好讲格调,论者以为远乎韵矣”〔141〕、“而有恒变之别。如恒调,须固守常法;至变调,则纵横交错,绝无定则”〔142〕等等,林林总总,在日本诗话文体学中独具理论体系,因为篇幅关系,这里仅举其大端,笔者会有专文研究。
以上我们通过全面阅读辑录、分类分析日本诗话中丰富的文体史料并系统建构其文体学理论体系,同时与中国古代文体学尤其是宋以来诗话文体学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这种“影响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整体来看,日本诗话文体学脱胎于中国古代文体学尤其是宋以来诗话文体学,其后又逐渐本土化和日本化,形成与中国古代文体学“和而不同”的独立特色。这种“文体学”之间的“影响”关系及其“影响比较研究”,与著名诗话学者蔡镇楚、张伯伟、孙立等关于中日诗话的影响比较研究观点如出一辙,如孙立《面向中国的日本诗话》:“日本诗话在早期脱胎于中国诗话,在江户后期又逐步本土化的表现,说明日本诗话在面向中国的同时,为适应日本本土读者的需要而本土化的特色及过程。”〔143〕蔡镇楚《中国诗话与日本诗话》:“中日两国诗话之比较研究,属于影响比较研究。”“盛极一时的日本诗话,就诞生在中日文化交流的艺术氛围之中,它既是古代日本汉诗繁荣发展的产物,又是日本人善于吸收中国诗话这一独特的诗论之体,经过移植、模仿而逐渐使之日本化的结果。”“日本诗话公开承认其诗学渊源在中国从中古时代开始,日本就进入中国文化圈之内,日本汉诗及其诗话,都是中国儒学东渐的产物,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宁馨儿。”〔144〕以上结论都可以从文体学的角度进行观照甚至替换。
在这种比较研究中,日本诗话文体学的价值和作用主要在于:一是,日本诗话文体学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参照系。日本诗话不仅保存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大量文献资料,而且又从域外的角度价值标准而使这种文体批评别开生面。二是,通过中日诗话文体学之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文体学对日本诗话文体学思想的深远影响。三是,文体学比较研究的文化交流作用,如张伯伟《“文化圈”视野下的文体学研究——以“三五七言体”为例》认为“文体学的研究不只是一个语言形式问题,更需要拥有一个文化交流史的眼光”“考察文体的演变不仅需要有时间观念,同样重要的还有空间观念”。〔145〕四是,通过中日诗话文体学影响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日本诗话文体学“和而不同”的独立特色。如王晓平称“尽管如此,由于两者产生于不同的文化土壤,故日本诗话亦有不同于中国诗话之处。这些正是跨文化传播中的汉诗在日本文化中产生的独特价值”。〔146〕同样,日本诗话的文体学思想亦非亦步亦趋于中国诗话的文体学理论,其在借鉴汲取中国诗话文体观念养料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和而不同”的民族特色和风格。
注释:
〔1〕〔146〕王晓平:《跨文化视角下的日本诗话》,《南开学报》2016年第3期。
〔2〕〔143〕孙立:《面向中国的日本诗话》,《学术研究》2012年第1期。
〔3〕〔4〕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15页。
〔5〕〔32〕〔33〕〔41〕〔48〕〔50〕〔53〕〔54〕〔55〕〔59〕〔60〕〔61〕〔63〕〔64〕〔65〕〔66〕〔71〕〔79〕〔80〕〔81〕〔85〕〔86〕〔87〕〔90〕〔100〕〔101〕〔105〕〔113〕〔114〕〔115〕〔116〕〔117〕〔118〕〔119〕〔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马歌东编选、校点:《日本诗话二十种》(下卷),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317、220、11、199、109、293、275、105、16、21、323、41、94、11、11、43、24、27、42、13、14、180、103、318、320、42、166、167、167、223、234、235、31、11、13、13、11、11、12、13、14、16、18、22页。
〔6〕任竞泽:《“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论源流》,《求索》2016年第5期。
〔7〕〔14〕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于北山点校,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罗根泽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81、14页。
〔8〕〔11〕〔12〕〔明〕王世懋:《秇圃撷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黄宗羲:《明文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六一。
〔10〕章潢:《图书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一。
〔13〕〔15〕〔16〕〔17〕〔18〕〔19〕〔20〕〔21〕〔22〕〔23〕〔24〕〔28〕〔29〕〔30〕〔31〕〔36〕〔37〕〔38〕〔39〕〔40〕〔42〕〔43〕〔44〕〔45〕〔46〕〔47〕〔49〕〔51〕〔52〕〔56〕〔57〕〔58〕〔62〕〔67〕〔68〕〔72〕〔73〕〔74〕〔75〕〔76〕〔77〕〔78〕〔82〕〔83〕〔84〕〔88〕〔91〕〔92〕〔93〕〔94〕〔95〕〔96〕〔97〕〔98〕〔99〕〔102〕〔103〕〔104〕〔106〕〔107〕〔108〕〔109〕〔110〕〔111〕〔112〕〔120〕〔121〕〔122〕〔123〕〔124〕〔125〕〔126〕〔138〕〔139〕〔140〕〔141〕〔142〕马歌东编选、校点:《日本诗话二十种》(上卷),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80、141、62、63、63、64、142、144、145、43、145、54、66、327、372、18、29、29、30、80、31、10、17、389、76、115、148、40、40、31、36、144、154、143、2、54、54、144、243、240、248、389、192、193、198、144、146、141、148、153、81、297、297、297、323、45、44、60、48、126、104、229、203、126、269、294、296、346、366、65、76、180、179、181、321、322、326页。
〔25〕〔26〕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3、77页。
〔27〕胡应麟:《诗薮》内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11页。
〔34〕〔35〕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06页。
〔69〕〔144〕蔡镇楚:《中国诗话与日本诗话》,《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
〔70〕张伯伟:《论日本诗话的特色——兼谈中日韩诗话的关系》,《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89〕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62页。
〔145〕张伯伟:《“文化圈”视野下的文体学研究——以“三五七言体”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