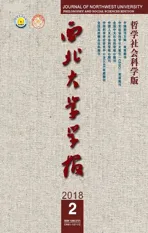秦始皇陵所见帝国文明宇宙观
2018-02-12段清波
段清波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是文化进步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历代帝王陵墓是不同时期社会治理体系、宇宙观、核心价值观等综合信息的承载者[1]。秦始皇帝陵园的设计理念,便是对“皇帝”这一中央集权制社会治理体系的再现[2]。其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设计思想,将帝国时代“盖天说”理念下天圆地方观念中最核心的阴阳、五行相克、水德等宇宙观完整地模拟在地下,在象征天圆的地宫顶部,绘制有四神二十八星宿,是阳的体现;在方形地面上,设计有以水银为江河湖海的帝国版图,是阴的体现;以水银象征水,表示五行中的水德,是秦人以水德代替周人火德的思想体现。这种宇宙观是对秦帝国社会治理体系和皇帝执政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论证。
一、秦始皇帝陵园所见社会治理体系
“战国”之名来自刘向的《战国策》。战国的开始不仅仅由一件或几件特殊的事件导致。不论以孔子春秋绝笔(前481)或《左传》记事结束(前468),周元王即位(《史记》)还是三家分晋(《资治通鉴》)等不同时间节点为发轫,影响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深层次因素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化,改变了历史进程。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治理体系和为社会治理体系提供支撑的宇宙观,与王国制时期相比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秦始皇帝陵园的陵寝因素,如以各类陪葬坑组成的外藏系统[3](P14-20)、内外两重城垣[4](P6-35)、高耸的封土和九层高台建筑、三出阙[3](P31-33)等,就是新时期中央集权社会治理体系的物化标志。
秦始皇帝陵园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园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陵园面积2.13平方公里,由南北向的内外两重围墙套合,地宫位于内城南部;陵区面积达60平方公里;陵园、陵区的地上地下分布着为数甚多的文物遗存。秦始皇帝陵园的学术价值和已经展示出来的文明价值,并不仅仅因为令人震惊的兵马俑等这些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文物遗存现象,更由于它是帝国文明理念的集中展示——这里所展示的制度文明,影响了古代中国2200年发展历程。
秦始皇帝陵园最富时代特色、最具文明价值的是大量的陪葬坑。
陪葬坑早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开始广泛流行[5],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诸侯们的大墓外均竞相以车马坑的形式来陪葬死者,并且形成以车马数量的多寡来象征生前社会地位高低和财富多寡的规律。正所谓“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6](P223)。秦东陵陪葬坑数量不多,从勘探出来的包含物和坑体的尺寸看[7],应该和东方六国诸侯墓葬陪葬坑一样,都是车马坑,这一现象到秦始皇陵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
秦始皇陵园中仍然使用陪葬坑这种埋葬形式,但数量和内容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目前已经发现将近200座形状大小各不相同的陪葬坑,他们分布在陵墓墓圹之外,内城之内、内外城之间和外城之外均有分布,面积大的有1.4万多平方米,面积小的仅几平方米。秦陵陪葬坑内涵上也和先秦迥然不同,除车马外,还出现了水禽、百戏、文官等新类型,结合汉景帝阳陵陪葬坑的内涵[8],我们认为这些陪葬坑是对皇帝专制下中央集权郡县制、中央政府政权机构的模拟,统称为“外藏系统”[9]。将秦始皇最大的政治遗产以物化的形式持久地保留下来,是对王国时期分封制的一种彻底否定。
除外藏系统外,最能彰显皇帝至尊理念的是高大的封土、封土内的高台建筑以及深埋其下的地宫。从封土北侧秦代地面看,由夯土构建的覆斗形秦陵封土高55米。
黄河流域高等级贵族陵墓的封土形式看来是从长江流域向北传播来的,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经过淮河流域到山东半岛,然后又从黄河下游向中游影响、发展,秦国最后才受到影响;到战国中晚期,东方六国的封土体量远远超过秦国,而埋葬有宣太后、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等秦始皇近祖的东陵,陵墓封土也仅有二三米高,规模在战国晚期列国中是比较小的。秦帝国建立后,秦始皇陵封土即使没有最后建成,但其设计高度、现存高度也一跃成为古代中国陵墓封土之最,这其中有秦帝国文化求高、求大风格上的原因,也受昆仑崇拜升仙的影响。据文献记载,秦始皇陵封土高达116米多[10](P1954),之所以实际高度与文献记载相差50余米,是因为地面以上的封土,是自“预作寿陵”制度之后,下葬死者才开始建造的,而封土没有最后完工就暴发了农民起义[11](P62)。
秦陵封土并非由一层层夯土筑就[12](P97)。新世纪初,我们通过物探和考古勘探相结合的方式[13](P38)发现秦陵封土内竟然还有一组高出地面30米的庞然大物。这组呈矩形的夯土建筑环绕墓圹周边,顶部高出地表30米左右,呈九级台阶式墙状夯土台结构,东西夯土台的中间各留有一处缺口与墓道重合,夯土台围的内部即地宫上部以粗夯土填充。台阶式墙状夯土台顶部内侧东西长124米,南北宽107米;外侧东西长168米,南北宽142米;南墙顶宽16米,北墙顶宽19米,东西墙顶宽22米[14]。各级夯土台上还有以瓦铺设屋面的木构建筑。这是古代陵墓封土中唯一见到的现象,此建筑供皇帝灵魂出游时登高望远使用,亦即《汉书·贾山传》中所说的“中成观游”[11](P2327-2328)。
除外藏系统、陵墓封土以及封土内的高台建筑、陵园内外城东门之间的三出阙外,在“非壮丽无以重威”的帝国理念影响下,能体现皇帝专制体制思想的还有原大兵马俑群体、陵园内外城之间西北处九进院落的礼制建筑等[4]。
二、秦陵地宫结构
秦陵地宫展示的是皇帝在阴间的世界,《史记》说秦陵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学者们推断,地宫顶部摹写着四神二十八星宿的天文图像,地下以水银表现帝国疆域的水系,天地之间是秦始皇。这是对帝国阶段天圆地方、阴阳、五行、水德与人间相互关系的摹写。
按照“事亡如事存”的理念,地宫作为秦始皇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卧室,不仅仅是容纳皇帝棺椁与个人地位生活相关随葬品的场所,更是皇帝本人思考宇宙、帝国治理、精神理想的场所。20世纪初,经过物探和考古勘探,我们知道地宫位于封土之下,距地表深30米;底部呈长方形,东西长80米、南北宽50米。墓室四周、顶部、东墓道顶部均为石质结构,地宫的空间高度为15米,没有坍塌,没有进水[15](P38)。这说明司马迁的相关描述并不虚妄。
拱券技术是来自西亚、地中海一带的发明创造,已发现中国古代最早应用拱券技术的是西汉晚期张安世妻子的墓葬[16]。勘探中可知地宫顶部是用石板构建的,那么,100多年前的秦代,采取什么技术,才解决了高15米、南北50米、东西80米这类大跨度问题的?我们推断,那个时代只有拱券技术才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其形态有可能是拱形顶或穹隆顶,这样才有可能在墓室顶部摹绘天文星象图,从发展的顺序上看,秦陵地宫是最早以砖石建材解决大跨度并绘制天文星象图的陵墓。
墓葬中开始出现天文星象图,与墓葬形制的变革——由椁墓到室墓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正因为这一变化,使得自战国以来形成的天地、阴阳宇宙观得以在墓室结构上体现出来,而传统的木椁墓却很难做到,也没有发现实例。受秦始皇陵地宫设计理念的影响,自西汉中晚期开始,以砖石为材料,以拱券技术解决跨度的方法获得广泛地应用,改变了古代陵墓墓室的形态,多墓道竖穴土圹木椁墓逐渐被单墓道南向砖石室墓所取代。此后,拱形墓以及穹庐顶、叠涩顶的结构很快地在帝国疆域得到普及,一直影响到了东汉诸侯王陵、曹魏时期的高等级墓葬[17]。这种覆盖在矩形空间上方的半球体圆顶的墓室结构,有意遵照和体现出了天圆地方的理念[18](P150)。
自秦陵开创在墓室顶部摹绘天象图以后,这一做法纷纷被后代模仿。西汉前期惟一一处诸侯王级的巨幅天文星象图彩色壁画墓,是汉武帝时期河南永城梁孝王的石室墓,墓室顶部制有近30平方米的“四神云气图”,壁画以青龙、白虎、朱雀为主题图案[19](P115-119);之后洛阳卜千秋砖室墓壁画[20],绘有日月星云仙人、伏羲女娲以及四神、乘凤升仙等,此墓的整体图像程序与司马迁描写的三维宇宙图景极为类似[21](P15)。再晚的是西安交大校园内西汉晚期砖室墓中[22],墓室顶部内绘一幅完整的四象二十八宿环绕日、月的彩色天象图,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四象二十八宿星图,由此推测,自西汉晚期开始,帝王陵墓的天象图设计理念慢慢地在中下层社会流行起来[23]。
科学测试证明,秦陵地宫确实存在有大量的水银,在陵墓封土的中心区域有一个约1.2万平方米的强汞异常区[24],并且封土中心部位强度较高且连片分布,这种分布局限在地宫开挖的范围之内,呈西北弱、北东侧最强、南侧次强的分布规律,这种分布,令人自然想到秦帝国疆域内水系的分布状况,他们之间有着高度的重合性,这佐证了“以水银为江河湖海”的记载,呈现的是帝国疆域内的河湖江海水系,即“下具地理”,也就是以水银为材料,将秦帝国大地上的山川、地貌、水系等摹写在地宫内。研究表明,秦陵地宫中的水银仅仅是作为摹写帝国版图来使用的,并不具有炼丹、防盗、防尸腐等功能,也不具备财富的象征,因为此阶段人们对水银及朱砂的认知仅限于颜料、鎏金银和中药方面[25](P249-262)。
将帝国版图再现在墓室中的创意,在古代中国陵墓中属于空前的创新措施,这是秦始皇将帝国最辉煌的历史以物化的形式载录下来,表现的不仅仅是皇帝个人史诗般的英雄经历,更体现着对国家未来的深深挂牵;它是秦始皇心系天下的表征,也承载着一个帝国皇帝的企盼[26](P26-29)。
三、秦陵地宫所见宇宙观
秦陵地宫是对战国中晚期以来形成的阴阳、五行宇宙观的展现。
这里不仅将秦始皇对帝国的牵挂描述下来,还“上具天文”,将盖天说理论下天地之中的“择中”理念摹写在陵墓中,更将秦代确立的为皇帝专制社会治理体系提供支撑的天、地、人相互关联的天地、阴阳、五行宇宙观也摹写在陵墓中。高大雄伟的夯土以及九层台建筑,是天、阳的体现。地宫顶部的“上具天文”是对天极及周边星象的再现;地宫中江河湖海是大地、阴的体现;以水银制作帝国地理版图是秦人“水德”的象征;秦始皇就躺在天地之中,又是择中理念的体现。
以墓葬结构模拟宇宙模式的做法,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就已成为高规格墓葬中重要的礼制形式。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濮阳西水坡45号大墓中,就出现了此种礼制形式[27]。这座墓以南圆北方的平面结构来表现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并配有蚌壳摆塑的龙虎和斗勺图案,构成中国古代恒星观测体系的雏形,显示出北斗二十八宿四象天官体系的初始框架。殷商时期商王级别的“亚”字形大墓,可能与宗庙明堂建筑平面所象征的宇宙有关,是一种对宇宙模式(中心四方宇宙观)的模拟[28](P315)。
秦始皇陵园是这种宇宙观理念的集大成者,地宫形态及内容是帝国时期宇宙观的体现;其目的是通过对这种宇宙观的摹写,为帝国中央集权体制的合法性与秦始皇本人执政的合理性提供论证,这一理念直至汉唐也一直存在。
宇宙观是不同时期人们对天、地、人相互关系的总体认识[29](P2),它将天地人纳入一个有机的序列中[30](P218-219)。中国古代宇宙观依次发生过三次相续的变化,即颛顼之前的人人通天观、颛顼至商周时期的四方中心观以及战国晚期至近代的阴阳五行观[31]。古代中国人认为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并由此构成中国文明最显著的特征要素。它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转提供合理性、合法性的支撑。
秦始皇陵的封土是天、阳的象征。《周易·系辞》讲“天一,地二”,古人把一、三、五、七、九称之为阳数、天数,十以内的偶数则为阴数、地数。 “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32](P448),“九”代表了最高的范畴,秦始皇陵封土下有一座规模巨大的“九层之台”,奇数“九”作为天、阳数之极的象征,它象征着最高王权。数字信仰,在古代王权政治中具有独特的结构意义,数字崇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屡见不鲜,“九五之尊”“一言九鼎”等一系列相关的成语深藏着一个由数字构成的数理文化体系,是传统中国宇宙观的体现。
秦陵地宫是阴阳、五行宇宙观的集中体现。阴阳是相互对立、转化的力量,它们通过上升和下降交替的运动,促成了事物发展、衰落、再发展的永恒周期,也成为了自然界和社会运转的基本秩序。正所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33](P228)。阴阳与五行属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阴阳的内容通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象反映出来,五行属于阴阳的存在形式。天地阴阳观念是秦陵地宫设计理念的来源——地宫顶部象征天,底部象征大地。
中国古代先后有三种宇宙观,即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盖天说历史最悠久、影响也最深远。红山文化[34]、良渚文化的祭坛[35]以及史前社会象征天圆地方概念的玉琮等都表明,盖天说在中国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即使到西汉中期、更科学的浑天说产生后,盖天说依然深层次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其实,几何形的天圆地方观念在春秋晚期就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已经超越具体形态,开始在哲学层面和宇宙运行法则——道的层面上讨论了。在古代,天、上帝、帝是一回事,是宇宙的主宰。北极是上帝的宫室,又是天的象征;秦始皇陵墓室顶部绘制着以北极为中心的四神二十八星宿图像,是天、上帝的所在地,这是天地阴阳理念下盖天说天圆地方中“天圆”的象征。
中国文明的进程中,源于观象授时活动的“地中”观念也随之产生,“北极之下天地之中”是盖天说理论的自然推论,成为世俗生活中一处神圣的地点——在此可以聆听天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6](P460),因 “择中而立”观念的不断普及,各酋邦纷纷通过“择中”活动以体现号令天下的做法就成为必然。人们认为只有在天地之间的“地中”,才能实现和上帝的无障碍沟通,也才能代表上帝在人世间行事,“君权神授”观念就产生于此,伴随“地中”观念的产生,就必然会有“择中”而居以及“居中”而治理天下的理念。黄河中游区域的“地中”是依据《周礼》中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说测量出来的[36](P2005),《周髀算经》中地中为一尺五寸理论可能是长城地带的地中理论。秦陵地宫地面以水银象征江河湖海,展示的是帝国的版图,是“地方”的象征;秦始皇帝的棺柩躺在天地之中的“地中”, 表示的是天圆地方理念下居中而治,也是皇权来自上帝即“君权神授”的标志。
战国中期之前,关于历史演变、社会发展、朝代更替等,一直没有合适的理论来阐释,战国晚期邹衍五行相克学说产生,很快地风靡社会。五行观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生成的,他们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后来又发展出将五行对应五德的理论,认为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都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当此理论运用到历史变迁时,认为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受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某个元素的庇护,当轮到下一个元素占支配地位时,就以五行相克说作为改朝换代理论合法性的依据。秦始皇是五行序列和力量的信奉者[37](P75)。因为水银和水之间相似的流动性,那么地宫中以水银象征水,则有体现水德观的意味,以水银来模拟江河湖海,是向普天下的芸芸众生宣布,秦灭周是以水德代替火德,此乃天意,宣示了秦帝国建立的合法性和秦始皇执政的合理性。
从王国体制帝国体制,5000年间的国家治理形态演变告诉我们,任何时期为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统治阶层需要创造出一套能反映主要社会成员意志、具有相当约束力,且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经历了战国开始至王莽新朝的450年,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完成了从古国到王国再到帝国的演变以及相应的帝国体制、理念完全确立的变化。为使这套治理体系得到神圣性的论证,需要形成一套时人认可的宇宙观体系来为之提供坚强的支持。阴阳五行相克宇宙观就是在王朝更替、皇权神授的层面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宇宙观不仅能为社会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还能深刻影响人们的行为处事方式,因之也就能为某一文明阶段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核心价值观的支撑,有了这种人与人如何相处的最大共识,社会运转体系才能安全、和谐地得以运行。
[1] 段清波.论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J].中原文化研究,2018,(1).
[2] 段清波.皇帝理念下的秦始皇帝陵―秦始皇帝陵园设计理念研究[J].历史文物,2007,(6).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5] 段清波,张颖岚.秦始皇陵的外藏系统[J].考古,2003,(11).
[6]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秦东陵第四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3,(3).
[8] 焦南峰.汉阳陵从葬坑初探[J].文物,2006,(7).
[9]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的外藏系统[J].考古,2003,(11).
[10]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2]刘士毅.秦始皇帝陵地宫地球物理探测成果与技术[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5.
[13]段清波.秦始皇陵封土建筑探讨-兼释“中成观游”[J].考古,2006,(5).
[1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 年度秦始皇帝陵园礼制建筑遗址考古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2).
[15]刘士毅,等.秦始皇帝陵地宫地球物理探测成果与技术[J].北京:地质出版社,2005.
[16]丁岩.西汉一代重臣张安世家族墓揽胜[J].大众考古,2014,(12).
[17]刘庆柱.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J].中原文物,2010,(4).
[18]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3.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20]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J].考古,1965,(2).
[21]巫鸿.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0.
[22]呼林贵.西安交大西汉墓二十八宿星图与《史记·天官书》[J].人文杂志,1989,(2).
[23]赵超.穹隆顶墓室与覆斗形墓志:兼谈古代墓葬中“象天地”思想[J].文物,1999,(5).
[24]常勇,李同.秦始皇帝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J].考古,1983,(7).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秦陵地宫水银及相关问题的研究[M]∥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6]刘士毅.秦始皇帝陵地宫地球物理探测成果与技术[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5.
[27]孙德萓,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8,(3).
[28]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1999.
[29]王爱河.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0]杰西卡·罗森.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1.
[31]段清波.先秦时期宇宙观与政治实践[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7-25(005).
[32]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3]牛兵占,等.黄帝内经[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34]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J].文物,1986,(8).
[3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诸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8,(1).
[36]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
[37]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