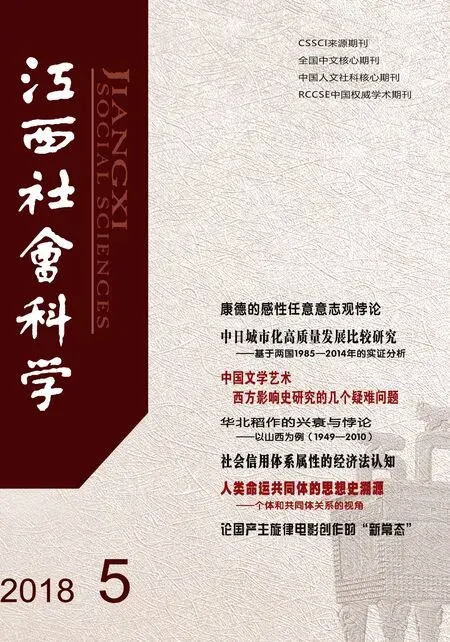论国产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新常态”
2018-02-11
当前国内电影创作空前繁荣,国产电影所倡导的精神价值取向也日益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而作为体现主导意识形态意图的文化产品,“主旋律”电影在其艺术创作过程中更是担负着社会责任和文化重任,需要在创作生产过程中自觉贯彻弘扬“时代最强音”的思想内涵,这也是“主旋律”电影存在价值与存在意义的重要体现。“主旋律”电影以鲜明的导向性介入大众的社会生活,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里所涌现出的新问题新困惑,为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所遭遇的各种复杂矛盾进行艺术化的文本阐释。
在以往的当代“主旋律”电影创作过程中,这种独特的非类型化的“电影类型”经历了“教化优先”“轻视电影性”“背离艺术原则”“忽略接受规律”等不正常状态。近年来,伴随国家电影产业的逐步完善,以电影艺术的方式构建并传播主导意识形态,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建构与国家“硬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软实力”等逐渐成为我们这个迅速崛起的电影大国一种自觉而迫切的文化使命。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在经历了历史与现实的“否定之否定”后,当前国产“主旋律”电影创作以丰富的作品系列和实在的市场业绩逐渐步入艺术创作的“新常态”。“新常态”说明在总结国产“主旋律”电影创作与传播的正反面经验基础上,无论是电影创作者、电影市场经营者,还是电影行政主管部门等都对“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观念、美学意识、叙事策略、传播规律、市场价值等都有更贴近事物本质与规律的新认识。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香港与内地在电影工业领域更加紧密的文化与商业合作的充分实践,使得当前对于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各种新认识与新经验有了更为切实可行的释放与提升。“内地与香港电影业的合作成功扩大了中国电影在海外的影响,展示了中国电影的魅力,促进了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加深了世界对中国的理解。”[1](P9-10)
一、“主题先行”让位于“故事本位”
“主旋律”电影作为意识形态色彩显著的媒介文化现象,在大众传播领域自觉承担起舆论导向与价值传递的媒介功能。也就是说,“主旋律”电影从传播行为的开始到传播行为的终止,整个过程都置身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所预制的框架内。
而在这个“预制框架”内,首要的规制要素就是“题材甄别”与“主题预设”。因此,曾经的非正常状态下的“主旋律”电影创作,常常把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成无生命的符号,在人性的空间里没有栖身之所,其人性的审美价值湮灭于种种“题材与主题”窠臼中。例如:身边琐事少表现;人际关系要单纯;男女爱情要回避;时弊矛盾要淡化;阶级立场要分明,等等。“主旋律”电影对“典型意义”的强调,往往就是认为对题材与主题的监督阐释直接关系到电影作品的基本立场和导向,是不可撼动的第一准则。然而,无论是历史现象,还是社会生活;无论是家国情怀,还是红尘俗世,都是纷繁复杂的。“主旋律”电影也必须告别以“主题先行”为特点的创作上的本末倒置,回归到以“讲好电影故事”为本位的创作基点上来。一切需要经由电影艺术来凝聚和传播的国家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念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既要满足精神层面的“理想尺度”的要求,更要与主流的、通俗的、符合当代电影本体要求的“故事情境”达成“化合”与“互动”的创作共识。
2012年的影片《听风者》,就题材而言,是大众熟悉的革命历史题材。新中国创建伊始,我党领导下的国家情报部门与国民党特务分子展开隐蔽战线的殊死较量。在以往的创作状态中,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主旋律”作品,在创作上往往必然追求的是某种关于革命与历史的“宏大叙事”,而“主旋律”电影创作者也时常被主题所累,在甄别题材大小和主题深浅上耗费精力,创作的手脚始终放不开。这其实正是“为了主旋律而主旋律”的表现,主题的表达过于急切,反而局限了“主旋律”精神内涵的开掘和电影艺术空间的展现。
《听风者》导演是香港电影人麦兆辉与庄文强。他们在2002年合作完成影片《无间道》,从此成为在华语电影界备受瞩目的“麦庄组合”。客观来讲,《无间道》这种“警匪”与“黑帮”式套路娴熟完美的类型片,只要在讲述类型故事的创意与技巧上稍作调整便会焕发出令人惊艳的艺术效果。而“麦庄组合”无疑是能够被市场高度认可的出色的电影故事演绎者。于是,在《听风者》这部堪称是港片导演“红色试水”之作的影片中,“麦庄组合”把一个似曾相识的“革命历史故事”经由对人物情感的细腻刻画,成功地转换成男主人公“何兵”和两位女性“张学宁”与“沈静”的情感戏。影片在凸显战斗于隐蔽战线上的革命者的人性美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讲述了关于一个男人的精神成长的动人故事。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影片关注的是情报人员的执着信念与战斗精神;而从人情人性的角度来看,影片分明讲述的是一个“街头混混”如何在两个女性的精神与情感抚慰下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渐成长成熟的故事。这个大时代风云里男女欲爱不能的故事的确有“去历史化”的通俗解读之嫌,但也正是这样一种“避实就虚”的谍战片类型尝试,把香港电影的通俗叙事与“主旋律”的历史情结很好地缝合在一起,令观众在注目于小人物爱恨情仇的银幕故事之时,对献身于情报战场上的“无名者们”所书写的英雄传奇致以深深的敬意。
“传统的内地电影创作链和香港电影的创作链正好相反,往往是由意念而故事,再由故事而细节,意念是最重要的,而能体现出娱乐价值的细节则是最次要的。因此内地的影片虽在整体叙事上很到位,但在具体细节上平平淡淡,缺乏一定的观赏价值。”[2](P227)2016年票房与口碑双丰收的影片《湄公河行动》绝对够得上体现国家意志的“主旋律”作品。信仰高过生命,坚贞战胜恐惧,理想超越死亡。尤为难得的是,影片叙事精细考究,环环相扣,绵密跌宕,扣人心弦,一气呵成。主题暂时被搁置,思想暂时被隐退,讲一个精彩好看吸引人的故事被放在首位。因此,《湄公河行动》就剧情而言,虽并无多少创新之处,甚至影片的若干“动情点”与“抖包袱”也实在是在观众的意料之中。但观众在轻松惬意之中品尝的却是血腥的拷打折磨,观众在一个曾经的“人民警察尽忠职守,智勇破大案要案”的经典题材里读解到的却是一个令人欲罢不能的好故事,故事里充满了良知、责任、智慧、信念与卑鄙、凶残、苟且、懦弱的较量。
2018年香港导演林超贤继《湄公河行动》之后完成的又一力作《红海行动》,在保持了与《湄公河行动》大体一致的情节路数的同时,更以战争场面之大,特效制作之精,中国海军人物群像之新锐,再度实现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影片开篇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与索马里海盗的激烈较量,迅速将观众带入当下蔚蓝海洋的波诡云谲与英雄叙事的冲动之中。接下来中国海军“蛟龙小分队”成员在伊维亚共和国撤侨与解救被恐怖分子绑架的人质的战斗中,展现出英朗帅气的当代军人风姿与他们彼此之间的“团队情”“战友情”。影片中蛟龙突击队队长杨锐的一句“我是中国海军,我带你们回家”,这份素朴又热烈的“军人情怀”,为一种成熟老练的商业大片情节模式注入难能可贵的“主旋律”价值。毫无疑问,《红海行动》的最大成功依然是高频率借用了“港产类型片”积淀下的视听技巧与叙事规则,又多了几分来自政治与人文层面的磨砺与钻探,使得影片所承担的军旅情怀与主流意识形态喷薄而出。由此可见,《红海行动》的创作思路与制作创意,再次体现了当前在“主旋律”电影文化新常态背景下,某种可以复制的主流类型电影范式。
二、“刻板程式”升级成“修辞策略”
由于以往的“主旋律”电影创作有意无意把电影作品的意识形态性凌驾于艺术性之上,并且在电影作品的传播策略上也忽略电影的消费性,这种看似比较“严谨而正统”的程式化创作趋向,却实际上导致“主旋律”电影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畸形而别扭。因此电影的艺术感染和社会宣传效果并不理想。
电影之所以是一门独立有尊严的艺术,是因为电影有自己的语言,而电影语言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电影的文本建构与文本传播具有独特的一整套修辞技巧。当“主旋律”电影创作步入创作新常态的时候,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主旋律”电影开始告别以往主要由意识形态性支配的“刻板程式”,转而重视更符合电影本性的“电影修辞策略”。这也是当“主旋律”电影无可回避大众文化话语普遍强势、泛娱乐化和消费主义盛行时代的现实考验之际,所必须把握的转型之道。
《智取威虎山》是中国大陆几乎人尽皆知的一部“红色经典戏剧”,它的“经典性”一方面来自于“革命文化”对主流历史的书写,但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因为“革命文化”的权力话语而精心营构的某种“刻板程式”上。这种高度程式化、样板化的文本既保证了作为某种故事样态的“智取威虎山”的稳定感、权威感和安全感,但也同时使这样的电影文本陷入低层次重复创作的现实窠臼中。因此徐克版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在旧有的题材空间里如何找到新的叙事可能性,是一个关键问题。徐克解决此问题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重新包装这个“红色故事”,使用能够与当下的电影观众重启审美对话的新的电影叙事修辞。
从修辞层面来看,导演徐克首先以流畅的镜头语言(包括画面构图、景别、摄影机角度、摄影机运动、灯光照明等元素)、细腻鲜明的蒙太奇叙事节奏以及特效技术大幅度改写了这个电影故事的叙事结构、情节设计与观赏效果。其次电影《智取威虎山》打破了此类红色经典题材电影对“英雄人物”的一般性的“镜语处理”与“情节建构”,徐克通过对人物外在形象与人物内心语言进行类型电影的修辞包装,将英雄人物的“神话特色”与平凡人物的个性化融合于一个更加情理交织的性格世界,借助“深入虎穴”“身手不凡”“儿女深情”等修辞性极强的电影故事场景的自由组合和自由延展,成功讲述一个平凡人物如何成为孤胆英雄,并最终惩治敌人,获得理解和赞誉的现代传奇。
电影《智取威虎山》是一次对传统常态“主旋律”电影的成功超越,是对新常态“主旋律”电影的积极而有效的探索,它不仅熟悉各种“主旋律”电影叙事手段的运用,也深谙受众的接受心理机制。“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诸如经济、规律、对称、秩序等经典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暴露出大部分激动人心的故事是通过一整套叙事手法展现出来的。观众从这些叙事规律中得到快乐,同时增强了娱乐体验。”[3](P38)影片《智取威虎山》在争取受众方面,既善于从技巧层面,提取相似题材类型片中的各种成熟而有效的视听语汇之精华并重新加以组合利用。同时,它也注重对人物关系和情感纠葛的充分铺陈与演绎,始终坚持在“情”与“理”的矛盾冲突中开掘出扣人心弦的戏剧性,这种强烈的戏剧性无疑构成电影文本中的“召唤结构”,这种“召唤结构”与受众内心的审美趣味相契合。我们看多了有意义的影片,但仍然看不够“好玩”的电影。电影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拒绝“好看”“好玩”这个标准,因为电影既可以是小众的匠心独运,更应是大众的“集体娱乐”。徐克版《智取威虎山》首先是做一个有娱乐精神的好看的电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智取威虎山》的成功既是电影商业的成功,也是步入新常态的“主旋律”电影回归电影本性的成功。
同样,《湄公河行动》以时尚动感的银幕动作语言把无论是常规枪战场景,还是飙车追车的特效场景或是直捣虎穴、商场激战、丛林大战、快艇追击等极富视觉冲击力的警匪交战场面都一一真切细致地呈现于银幕上,娴熟的蒙太奇节奏让人目不暇接,悬念丛生。正是这样一种“电影性”的充分书写,使《湄公河行动》打破受众对于“主旋律”电影既有的审美定势,培养拓展受众新的审美期待视野。同样在林超贤导演的《红海行动》中,一种丝毫不逊色于好莱坞大片的战争电影修辞令观众的观影心理更趋紧张与黏合,几场在伊维亚共和国境内城镇的激烈巷战、与恐怖分子狙击手的针尖对麦芒式的斗智斗勇、一系列最新的军事设备展示、高速摄影技术对战斗细节场面的锁定与描摹等,都远远超越了传统“主旋律”电影在同类题材展演过程中视听语言表现上的点到为止或是力不从心,这种经过高度渲染的电影修辞策略极好地烘托出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充满想象性的战争图景的真实环境,而这种环境表现得越真实越激烈,人们对于“反战”的思索,对于“和平”的解读则更加真实而直观。
三、“国家形象”着眼于“以人为本”
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个现实意义考量的背景下,“主旋律”电影的创制与传播成为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而直接的载体。2004年以来国内电影票房一路走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这样的发展态势也使得“主旋律”电影在承担塑造并传播国家形象使命的时候,必须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与时俱进的创作观念。
以往传统常态“主旋律”电影由于普遍强调并突出意识形态性,以至于“主旋律”电影的叙事形态往往高度概念化、脸谱化、肤浅化、平面化。因此,“主旋律”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表现得生硬直接,实际传播效果也就大打折扣。如果说当前的“主旋律”电影已经在故事讲述和电影修辞方面逐步摆脱了“唯宣教论”的束缚,在电影表现形式上开始表现得灵活不拘,那么在充分发挥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功能方面,“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新常态开始表现为以人为本,不违常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新常态下的“主旋律”电影在具体创作实践中逐步回归到一个基本共识,即艺术的基本价值依旧在于情感、人性与价值观。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湄公河行动》讲述了多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突遭袭击,全部遇难;中国政府为遇难同胞讨回清白与公道,派出中国警队精英组成特别行动小组,潜入金三角地区,经过大智大勇的激烈较量,最终成功缉拿幕后毒枭的故事。
电影题材与电影故事的主体决定了这样一部电影必须在对真实案件做 “传奇化”处理的同时,塑造出若干可以成功承担起主流思想意识宣传和教化功能的英雄人物。而这也恰恰是传统常态下的“主旋律”电影最难以拿捏的关键处,在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宣教功能论等因素的联合作用下,“主旋律”电影常常失去对电影人物细节的考究,对人性和人情的细描,英雄人物在审美层次上常常沦为平面化、脸谱化和过度理想化的附庸,难以引发审美共鸣与情感互动,传播效果并不理想。
深谙商业类型片故事经营之道的导演林超贤在突出主要人物的同时,又不刻意固化、美化、神化这些主要英雄人物,而是依据观众对于警匪类型电影的一般接受心理,借助若隐若现的爱情线与亲情线的埋设与延展,从情感细节处追索英雄人物的“常人”和“常情”状态,并丝丝入扣地将这种“常态”展现于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的案件侦办过程中。中国警方“湄公河行动”特别小组的核心人物高刚与中国警方潜伏于金三角地区的情报员方新武,他们作为影片的主要英雄人物,其银幕魅力的来源并非只是赤胆忠心的国家使命感和技高人胆大的英雄行迹,更重要的魅力来源则是回归人性人情的艺术刻画。高刚与方新武,这两个人物在形象与气质上就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的中规中矩的人物,在具体的破案行动中,他们都是标准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在传统常态“主旋律”电影中,“国家”“集体”与“个人”在美学处理上常常是不平等、不和谐的,具体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国家理性”凌驾于“人物个性”之上,形成传统常态“主旋律”电影的中庸化风格,这种所谓的“风格”安全妥帖但灵性全无,人物形象单薄平庸,表现为电影美学上的毫无魅力和吸引力可言。
2017年由香港导演刘伟强执导的《建军大业》与之前同类题材电影作品相比,一个重要创作突破就是紧扣住商业片的核心法则之一“个人英雄主义”,影片大量起用年轻的影视当红明星,以还原历史现场的“青春英雄”为诉求,成功刻画出包括青年毛泽东、青年周恩来、青年叶挺、青年林彪、青年粟裕、壮年朱德等人物在内的一系列创建人民军队的一代元勋形象。“在历史中,人生仍是一出伟大的现实主义戏剧,充斥着各种悬念和冲突、伟大与苦痛、希望与幻觉、活力与激情。然而,人们不仅感受而且直观这出戏剧。当我们仍然生活在我们那充满情感和激情的经验世界中时,在历史之镜中看到这些场面后,我们就感受到一种清晰感和冷静感,获得一种内在反省的清澈宁静。”[4](P168)对于新常态的“主旋律”电影创作而言,“个人英雄主义”非但不与“国家形象”建构相抵触,而恰恰成为建基于“以人为本”观念上的“家国一体”,从而实现电影叙事层面的“执法精英”与“道德人伦”的自然融合,个体价值与国家意志的兼容互现,不拘于成例又不悖于人之常情,平和理性又铿锵有力地彰显出英雄人物的人间情怀与儿女情长,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使之感同身受,情满于怀。这无疑符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新常态对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即“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吃透生活底蕴,书写生动情节、动人形象,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艺术精品,讴歌时代和人民,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5](P61)。
林超贤导演的《红海行动》没有如同《战狼2》那样,在银幕上刻意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超级个人英雄”,而是以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队员的团队群像的方式来凸显“军人”的职业气质与英雄主义。但即便是一个战斗团队,在影片《红海行动》中唯一的女战士佟莉与战友“石头”之间看似不经意的“爱情”借助于“糖果”“防弹衣”以及憨直的“石头”从大家的合影照片中剪下的自己与佟莉在一起的“合照”等精准细节,传达出军旅生涯里作为年轻人的佟莉与“石头”之间的人性人情之美,这条感情线被导演处理得若有似无,极好地呼应了作为中国海军的特种作战部队成员,他们既担负着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也有着与你我一样的对于爱与被爱的铁汉柔情。
作为主导文化的重要表现媒介,“主旋律”电影担负着书写家国正史、凝聚民族共识的艺术使命。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大中华”电影圈进一步融合巩固。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电影人在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心理认同等方面本就有着天然的亲近性。长期历练于商业电影传统深厚的环境中,香港电影人熟稔商业电影的娱乐秘密,他们为“主旋律”电影创作带来了新的艺术观念和操作模式,在既有的题材领域不断结合各自的艺术与商业优势,创新电影语言,拓展讲故事方式,乃至在思想意识层面输入更具“全球化”特质的人文理念。
国家层面始终对电影提出“真实”和“主流”表达的冲动,中国香港作为华语文化圈的重要基地之一,其娴熟灵动又历史悠久的华语文化传播经验系统正为这种“国家冲动”提供了重要而有效的参考与扶助。而香港电影在这一过程中“不再执着于探寻香港身份,构建别样历史,也开始了主旋律式的宏大叙事”[6](P197),这种双向调节互动的“主旋律”电影创作尝试与探索,为当代中国的文艺“新常态”提供了在华语电影层面“国家所需、香港所长”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的经验。当然这种将香港电影人普遍尤为擅长的“类型电影观念与策略”全面移植到当代“主旋律电影”创作生产领域中,在带来了热烈的市场反响,并且对传统“主旋律”电影的种种不足给予必要的革新的同时,是否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与不足”,这也许是对于当下已经步入文艺“新常态”的“主旋律电影”创作做进一步理论思考的一种辩证可能,对此值得继续观察和讨论。
[1]赵卫防.香港电影史(1897—2006)[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2]朱虹.中国广播影视发言人答问录[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3](美)约翰·贝尔顿.美国电影美国文化[M].米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5]徐伟新.中国新常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6]杨远婴.电影学笔记[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