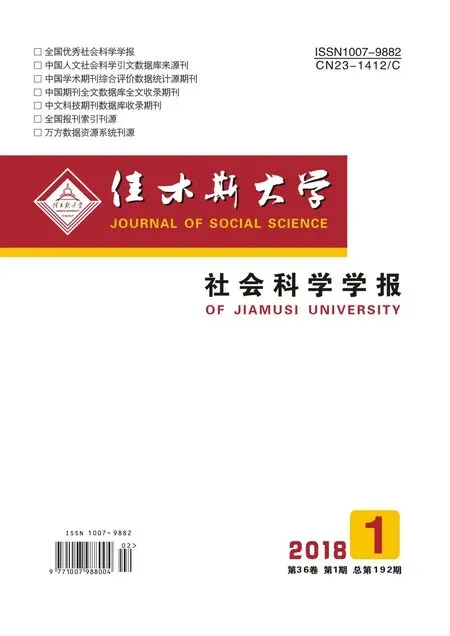色彩标注的人间世态*
——从《晚饭花》看汪曾祺小说色彩的表意策略
2018-02-11迟晓旭
迟晓旭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330031)
汪曾祺对色彩的感觉与记忆来源于儿时大自然丰富的色彩启示,以及童年学画经历中积累的丰富色彩知识。他的小说遵循中国古代诗画同源的美学理念,其中充盈着丰富的色彩感觉,而且民族民间化的色彩概念成为最具个性化的视觉形式,由此成为他叙述旧日故乡文化空间的重要表意策略。作为一位小说家,运用色彩写景写人,以基本的色调对比来烘托人物的心理氛围,并且造成象征的艺术效果,是他重要的表意手法。《晚饭花》是汪曾祺的一篇杰作,三个短篇小说形成对比,讲述了三种旧式女性的不同命运。不同风格的色彩点染强调了主题的倾向,晶莹奢华的珠子灯象征着固守贞操理念的闺阁女子寂寞、了无生气的生存处境;艳丽纷乱寻常的晚饭花隐喻着小家碧玉浅薄的虚荣与短暂的青春;古老的小贩之家中喧闹喜乐的三姐妹,层层渲染出市民女子勤劳朴素生活中绚丽多彩人生风貌。汪曾祺以三种色彩基调表达了对女性三种命运不同的审美倾向:疏离、惋惜与欣赏。
一
中西方的色彩艺术家在艺术创造和时代发展的共同驱动下,构成了内涵丰富的色彩系统,但由于东西方人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种族文化基因等因素,在各自长时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中,他们都独立形成了带着不同民族特色的色彩形式和色彩观念。[1]尚塞以一个画家的身份向我们揭示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即色彩具有一种观念的真实和理性的逻辑,一切的人类活动——历史、心理都会隐藏或融合在色彩之中。[2]中国画家注重色彩表意,南北朝时期的画家就讲究赋彩制形,独立创新,宗炳《画山水序》在山水画反应自然面貌的意象造型中提出“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主张,汪曾祺的小说《晚饭花》就浸透了这样的色彩奥秘。
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这里气候温和,景色宜人,物产众多,资源丰富,历来被称为鱼米之乡,是大运河畔的一颗明珠。高邮湖碧波荡漾,湖上的蓝天因时而变,在黄昏时也会渐渐变成浅黄,枯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城内河港纵横交错,丰富的水力资源给高邮带来了独有的双黄咸鸭蛋以及青虾、银鱼、螃蟹等著名水产。良好的生态环境养育着各种水生植物、鸟类和鱼类,丰富的光与色也早早开启了童年汪曾祺对色彩的独特感知。儒商之家的文化习得也影响了他的审美趣味,祖父汪嘉勋是末科拔贡,重视文化,不惜重金收藏古董字画,存有一套商代的彝鼎,明代的大花瓶,四幅宋代著名画家马远的小条屏,他还珍藏着一方蕉叶大白端砚等稀世珍宝,闲暇时把玩欣赏。他亲自指导汪曾祺读书做文,送她砚台一类书画用品。父亲汪菊生是有名的小城才子,多才多艺、心灵手巧,在体育、音乐之外尤其痴迷于绘画,使得汪曾祺经常有机会观摩父亲作画。“霁红”的花瓶,“大白”的端砚,色彩缤纷的书画作品伴随着汪曾祺的童年生活,可以说汪曾祺在自然与艺术的双重色彩映射中完成心灵的成长。受祖、父两辈的影响,汪曾祺在小学就以绘画、书法名,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期,把绘画的修养带入文学的创作。这一时期,他在传统绘画的家学之外,又接触到了西方现代主义美术,逐渐找到融汇古今中外的艺术基点,最直接地表现在对色彩运用的大胆尝试,表现在他作品中丰富的场景构图与以色彩为标记的表意策略。
二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绘画是从自然中抽调出来的二度或三度色彩,绘画是一种以二度空间为自己行为对象和物质内容的艺术,换句话说,绘画是一个对平面进行加工制作的艺术过程和这个过程的完结及凝固化。作为二度空间艺术,它所能依赖的东西只能是线条、形状和色彩。到十九世纪的后半叶人们发现,在绘画平面的后面的确存在着某种精神的空间,而线条、形状和色彩也确实可以表现出人的某种追求。[2]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在探索色彩的奥秘,直到十七世纪后半叶,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才揭开了色彩的奥秘,在试验中从科学的意义上,证实了阳光是由美丽的七种颜色组成的。因此,西方近世的色彩概念,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具有高度的分解性。中国传统绘画对于色彩的命名方式则是直观的,具有整体的效果。汪曾祺早年的文章最体现他对色彩的敏感,年老后,手法接近白描,但对色彩仍然情有独钟。著有《颜色的世界》,按照色排列各种民族化的色彩概念。比如,他将天色分为鱼肚白、珍珠母、珠灰和葡萄灰;红色则分为牡丹红、玫瑰红、胭脂红、水红、单杉杏子红、霁红以及豇豆红等;蓝色系分为天竺、湖蓝、春水碧于蓝、鸭蛋青等;绿色系分为葱绿、鹦哥绿、孔雀绿和松耳石等几种颜色。这种色系的分类显然是外来美术的理念,而具体的概念则是传统美术的命名方式,每一种颜色都有一个具体形象概念的定语,并且以自然物为修辞限定,形象生动地提示着色彩的质感。由此可见,中西美术的不同理念完美地融合在他的色彩感知中。对色彩的命名方式来源于对生活的观察,也取法传统绘画的色彩分类,体现着中国文化“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命名方式。
三
“书画同源”、“书画相通”在美学研究中已成定论,汪曾祺是用一个画家的眼睛从事文学创作,兼容新旧的绘画理念,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叙事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色彩新的表意手法。许多论者认为汪曾祺的小说有风俗画的特点,所谓风俗,主要是指仪式和节日,仪式即“礼”,包括婚礼和丧礼等。仪式必与场景相关,而在传统的礼仪中,色彩具有文化语义的隐喻与象征功能,所谓观念色是在特定场合中具有提示主题意味的标记。汪曾祺显然深谙个中奥秘,在自己的作品中充分地运用了这样的仪式与色彩关系的文化规范。
他的小说《晚饭花》由三个短篇小说构成,分别讲述了三个不同阶层旧式女子的命运,展现了不同的文化色彩表意。三个女人的故事都是以婚礼为中心铺陈展开,第一个短篇《珠子灯》刻画的是孙家大小姐孙淑芸出嫁一年后娘家送灯这一盛大场面。“一堂灯一般是六盏,其中珠子灯最为华丽,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灯体是八扇玻璃,其余部分都是珠子,下缀珠子的流苏。”[3]67到了“灯节”的晚上,屋里点了灯,珠子灯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水,显得异常安静。元宵的灯光扩散着祥和、华贵、朦胧和暧昧的希望。在中国传统色彩的五色体系中,红、黄、青(绿、蓝)、白、黑被视为正色。绿色的色彩表意为生命及生命的状态,象征着生机和希望。珠子灯灯体上绿色的玻璃珠子以及淡绿的光,无不表现出娘家对出嫁女儿幸福的祝祷。尽管华丽的珠子灯和象征美好的“红”、“绿”两种艳丽的色彩都寄托了吉祥的表意,晶莹剔透、艳丽的珠子灯象征着孙小姐高贵、优雅的气质。可是好景不长,孙小姐在丈夫死后,一心守节,固守空房,毫无生气的了此一生,就像那散了线的珠子灯,最终孤独寂寞地慢慢死去。色彩在艺术上的效应,总是同人物的意识、社会心理乃至民族的风俗习惯密切关联着。因此,在人物的塑造中,色彩的运筹便构成重要的作用。[4]雍容奢华的珠子灯纵然拥有最耀目的色彩,也难以拉近作家与之情感上的距离。而且,它吉祥华贵的色彩表意和孙小姐的命运构成了反讽的修辞语用,反衬出主人公的不幸。
汪曾祺注重用简洁的文字勾勒自己的人物,由于自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民族文化的熏染在潜意识中影响了他对色彩的选择和运用。《晚饭花》中刻画王玉英这一人物形象时,仅仅用了“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这一句简单的话语。就黑白两色而言,黑色在中国古代色彩观念中,承袭最原始的色彩感知,与白构成色彩感知的基础。[5]王玉英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黑白两种色彩的鲜明对比,将王玉英健康、纯净的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样一个看似健康的女性,在与钱老五结婚后,便只留下了一个孤单落寞的背影。汪曾祺在刻画这一女性形象时,将“黑”“白”这样的单调色彩置于晚饭花纷乱的“红”与“绿”的背景中中,为读者点燃出王玉英小家碧玉的生活形态,她的生活是单调的,缺乏色彩的,每天过着重复的生活。她向往爱情,却又不能主导爱情,最终画地为牢。她的命运就像晚饭花那样,纵使发疯一样地使劲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也显得普通寻常,那浓绿的叶子和殷红的花朵也在热闹中显出几分凄清,在盛开的晚饭花中只留下汪曾祺无尽的惋惜。
《三姊妹出嫁》中的三姐妹与孙小姐和王玉英都有所不同,她们出生在热闹喧嚣的市井,在充满爱的家庭氛围中成长,是典型的劳动阶层的女儿。她们身上没有浓重的脂粉气息,也没有任何艳丽华贵的色彩辅饰,有的只是普通劳动者的普通生活,是一种平凡的自然,就像明矾澄过的清水一般朴实无华。三姐妹对各自的生活充满了希望,世俗生活分工明确,将家里打扫的清清爽爽。对于爱情,敢于追求幸福,婚礼充满了喧闹喜乐。三姐妹都拥有平凡的快乐,这样简单的幸福可以投射出更加丰富的色彩。他们勤劳朴素、乐观向上的生活画面,恰恰寄托了汪曾祺的审美理想。他总是有意无意地用色彩强化自己笔下的人物,使人物的生活际遇和性格形成和谐的色调。
四
民族性色彩概念在汪曾祺的色彩选择中体现为独特语词的标记性提示作用。
中国民间绘画多采用象征性色彩,红色在我国古代的有色系列中占有重要地位,山东潍坊杨家埠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大面积的用色都为红色,年节之时象征喜庆,同时也反应出门神的威严。还有很多红墙、红衣、红旗甚至以红色染食品,都可以说明红色是象征吉祥喜庆的色彩。汪曾祺深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对红色这一色彩也是情有独钟。珠子灯的送灯队伍中,女佣人都要穿了干净的衣服,头梳得光光的,戴着双喜字大红绒花,灯体是八扇玻璃,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到了“灯节”的晚上,这些灯里就插了红蜡烛。红色的渲染既烘托出送灯的热闹氛围也暗示了珠子灯的喜庆吉祥。除红色外,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是祥瑞之兆。“凤,神鸟也,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晚饭花》中汪曾祺三次提到凤,第一次描写珠子灯时写道:“顶盖的描写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凤嘴里衔着珠子的小幡,下缀珠子的流苏”;其次,三姐妹的名字都包含一个“凤”字;第三次在描写三姐妹时写道:“两个姐姐绣得全身都是花。这些花里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凤。”不论珠子灯上的凤头、小凤绣在各处的凤还是名字中的“凤”字,都蕴含着吉祥之意。“红”和“凤”都是中国自古以来吉祥的象征,都是风韵独特的民族色彩。
与以不同的色调提示差异性生活文化空间的相适应的,是以时代性色彩差异标注传统的在更续中的变异。《三姊妹出嫁》中父一代与女一代、父一代与子一代都存在着明显的色彩差异。父与女一代的色彩差异主要表现在秦老吉和他的三个女儿身上。三姐妹的父亲秦老吉是个挑担子卖馄饨的普通市民,“他的担子非常特别,是楠木的,雕着花,细巧玲珑,很好看。”楠木为中亚热带常绿乔木,价格昂贵,它的色泽不闹不喧,以暖黄色为主,黄里又带着一点冷的绿色,含而不漏,蕴藉内敛着典雅的气息。秦老吉的楠木扁担又“好像是《东京梦华录》时期的东西,李嵩笔下画出来的玩意儿。”《东京梦华录》是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是一本可以追述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貌的著作。由此可见,这副扁担承载了历史的厚重感,历时性的文化属性显而易见。除扁担外,秦老吉拌馅用的深口大盘也别具一格,是雍正青花。标准的雍正青花呈纯蓝色,纹饰清新淡雅,这一时期的青花瓷,无论造型和装饰,都可以用一个“秀”字来概括,展现出柔媚、俊秀的风格。这一副卖馄饨的家什呈冷色调,在历史的积淀下显得端庄浑融,典雅大方。与之对应的是小凤绣出的艳丽花朵,她把两个姐姐绣得全身都是花。围裙上、鞋尖上、手帕上、包头布上,都是花。小凤绣的花朵大小不一,颜色鲜艳多彩,每一朵花都带有生命的灵性,各色各样的花朵呈暖色调,显得热闹非凡。父一代与女一代在色调的选择上一冷一暖,在色彩的搭配上一雅一俗,生动地展现两代人之间的色彩差异。
父一代与子一代的色彩差异主要表现在石福海和他的大福子身上的“古”与“新”。时福海是一个吹鼓手。人家办丧事,“‘六七’开吊,在‘初献’、‘亚献’之后,有‘进曲’这个项目。赞礼的礼生喝道“进——曲!”时福海就拿了一面荸荠鼓,由两个鼓手双笛伴奏,唱一段比昆曲还要古的曲词,内容是“神仙道化”,感叹人生无常,有《薤露》、《蒿里》遗意,很可能是元代的散曲。”[3]时福海还开了一爿剃头店,字号也就是“时福海记”,随着时代的变迁,剃光头的人少了,剃头店的生意日渐衰败。他的儿子“大福子很能赶潮流。他把逐渐暗淡下去的“时福海记”重新装修了一下,门窗柱壁,油漆一新,全都是奶油色,添了三面四尺高、二尺宽的大玻璃镜子。三面大镜之间挂了两个狭长的镜框,里面嵌了磁青砑银的蜡笺对联,他还置办了“夜巴黎”的香水,“司丹康”的发蜡。”[3]73奶油色显然是西方文化的提示,也是近现代中国域外文化的观念色,奶油微黄的色调与古老农耕民族极为推崇的观念色土黄形成文化史的拼接,提示着时代的变革潮流。父与子的色彩对比中,父一代的特点是古色古香,子一代的特点是时尚且色彩鲜明。时福海在“进曲”时唱的曲子时代久远,就像秦老吉的楠木担子一样,它们都承载着文化史的民族印记,因时间的积淀而古雅庄重。即使子一代用鲜明的色彩,新颖的外在表现形式取代了父一代古旧、单一的色彩表意,那些看似古旧的东西仍会作为一种精致的市民文化保留下来。而色彩丰富艳丽的三姐妹与三个不同色彩搭配的女婿的婚配,也隐喻着市民传统的延续与变通。
汪曾祺的小说多描写小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语言平淡冲和,经常婉转地传达自己对人物的喜好,《晚饭花》这三个短篇小说就描写了三类女性的不同命运,通过色彩差异与女性命运的对比,表达了独特的审美倾向,同时,也为文学情感的表达寻找到了新意义的出口。
[1]李广元,李黎.中西色彩比较[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1.
[2]黄浩.文学色彩学[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
[3]汪曾祺.受戒[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8:67.
[4]孙中田.色彩的语像空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07.
[5]李广元.色彩艺术学[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