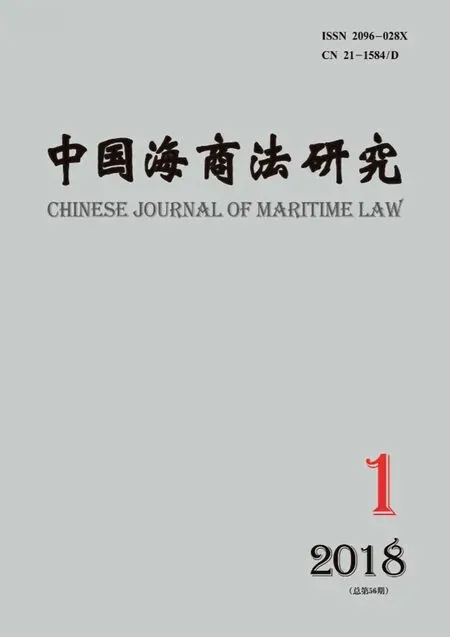公海保护区能否拘束第三方?①
2018-02-10段文
段文
(乌特勒支大学海洋法研究所,荷兰乌特勒支3512HT)
一、问题的引出
自20世纪末以来,受海洋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快速退化的影响,包括公海在内的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养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1]在此背景下,在公海建立和管理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s,MPA)作为一种新的保护公海环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方式应运而生。随着公海保护区划定数量的增加和划定范围的扩张,相应的国际法律问题也逐渐显现并成为了海洋环境法领域的讨论焦点之一。笔者将在归纳公海保护区概念的基础上,着重对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一)概念
关于“海洋保护区”的概念,一方面,其被视为基于海洋生物和海洋环境的目的而受到保护的区域;但另一方面,不同海洋保护区的特定目标是不尽相同的,例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历史和文化特征的保护纳入到了海洋保护区的保护范畴之中,而奥斯陆巴黎委员会的定义则强调对于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此外,我们可以发现,海洋保护区的概念存在于不同的法律层面中,全球层面如《生物多样性公约》,区域层面如奥斯陆巴黎委员会以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因此,海洋保护区可以被视作一个涵盖性术语,涵盖了各种出于保护海洋环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目的,在不同的法律基础上所建立的针对不同具体保护目标的海洋管理或养护区域。[2]
海洋保护区根据其设立位置和范围的不同分为国家管辖范围内海洋保护区和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公海海洋保护区(High Seas Marine Protected Areas,简称公海保护区)则是指在地理位置上位于国家管辖范围外上覆水体的这一类海洋保护区。
(二)主要法律问题及其意义
迈入21世纪后,公海保护区的实践逐渐产生并快速发展。2002年,法国、意大利、摩纳哥在《巴塞罗那公约》及其《特别保护区协定》的体系下通过缔结协议的方式在公海建立了“派拉格斯海洋保护区”(Pelagos Sanctuary);2008年,南极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CCAMLR)在南极海域设立了“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海域保护区”;2010年奥斯陆巴黎委员会在《东北大西洋环境保护公约》体系下通过部长会议做出决定的方式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公海保护区网络”。
随着公海保护区划定数量和面积的扩张,相应的国际法律问题也逐渐显现并成为了海洋环境法领域的讨论焦点之一,其问题既有涉及到如何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建立公海保护区的程序性问题,也有涉及到国家在公海保护区中具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等实体性问题①相关问题的分析可参见Tullio Scovazzi,Marine Protected Areas on the High Seas:Some Legal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2004,19(1),pp.1-17;亦可参见Erik J.Molenaar&Alex G.Oude Elferink,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The Pioneering Efforts under the OSPAR Convention,Utrecht Law Review,2009,5(1),pp.6-20。。囿于篇幅所限,笔者将把讨论重点放在公海保护区的设立及其相应管理措施是否对第三方具有法律效力这一问题上。因为该问题涉及到了公海保护区及其相应管理措施与国家所享有的公海自由、公海权利之间的关系,且对该问题的回答与对条约法有关“条约不能为第三方创设权利和义务”这一原则的理解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此外对该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指导国家有关公海保护区的实践并对未来公海保护区的发展做出预测,因而亦具有比较重要的实践意义。
而公海保护区第三方效力问题的实质,在于公海保护区与公海自由以及国家据此所享有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是一些国家通过条约或国际组织所建立的公海保护区及其相应的管理措施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拘束这些国家或国际组织之外的其他国家(即第三国)管辖下的公海活动并限制其所享有的公海自由。据此,笔者将在归纳公海保护区国际法律依据的基础上,尝试从两个层面对此问题进行回答,一是从条约法的角度来回答条约的第三方效力问题,二是从海洋法视角下公海国际法律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以判断公海保护区能否通过习惯国际法拘束第三方。最后笔者将结合公海保护区国际法编纂的新进展,展望公海保护区第三方效力问题未来可能的发展。
二、公海保护区的设立及其管理措施能否拘束第三方
公海保护区的设立及相应的管理措施涉及对公海自由及权利的限制,例如南极南奥克尼公海保护区在特定海域实施了全面性的禁渔措施,这直接影响到了各国在该海域的捕鱼自由,而《预防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及其附件在部分公海海域设立的“特别区域”对船舶石油和有害物质的排放活动进行了限制。那么公海保护区所涉及的限制性措施,能否对建立起保护区的条约/国际组织之外的第三国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呢?这问题实际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从条约与第三方关系的一般国际法理论的角度,因为目前公海保护区的划定和管理基本上还是依据区域性的条约机制来进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实质在于条约能否产生第三方效力。二是从海洋法视角下公海国际法律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来探究是否存在相应的习惯法依据从而使得第三方在行使其公海权利/自由时需要受到他国所设立的公海保护区的约束。这两个角度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一个侧面的答案同时也是对另一个侧面的启示。最后笔者将从既有的公海保护区实践中,挑出可能产生第三方效力的实例,分析其第三方效力的法理依据和该实践所带来的法律启示和影响,并就此归纳出相应结论。
(一)条约与第三方关系的一般国际法原理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简称《条约法公约》)第34条的规定,条约不能为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除非经该第三国的同意。这一“条约不能为第三方创设权利或义务”(pacta tertiis nec nocent nec prosunt)的规则同时也被认为是一项条约法上的习惯国际法规则,该规则源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平等原则。[3-4]因此基于条约的或条约机制所设立的公海保护区及其相应措施一般不能为第三国创设遵守或履行的义务,除非经过第三国的同意。因此,能否产生第三方效力,在于该第三方的国家意志(will of states)。上述规则同时也意味着,经过了第三国的同意,条约是可以为第三方创设权利或义务的,但第三国的“同意”对“创设义务”和“创设权利”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条件。
《条约法公约》第35条规定了条约为第三国创设义务的条件,即条约之某项规定有意为第三方规定义务且该第三方以书面明示接受。如果第三方没有以书面的方式明确地接受,则该项规定不能创设拘束该第三方的义务。即便是与接受义务相一致的行为,按照一般的条约法理论,该行为本身也不能产生拘束该第三方的义务。[5]257与此同时《条约法公约》第36条规定了为第三国创设权利的条件,与创设义务不同,为第三方创设权利的条款采取默示接受的原则,即当某项条约条款有意为第三方创设权利时,若该第三国没有表示反对,则推定其对该项创设的权利表示同意。
根据上述规则,在判断依据条约机制所建立的公海保护区能否对第三方产生拘束力,也就是说能否为第三方创设权利和义务时,需要以该公海保护区所依据的条约所创设的义务是否为第三方书面同意,以及所创设的权利是否未被第三方所否认为前提。
考虑到目前依托区域性环境或渔业条约所开展的公海保护区的有关实践,在建立和管理程序上都遵循多边的协商和集体决议机制,而非赋予成员国亦或第三国单方面划定或管理公海保护区的权利,如在《巴塞罗那公约》下,具有地中海重要意义的特别保护区的设立和管理措施的确定须经过相邻各国的协商,科学评估以及全体成员国的协商一致才能通过①参见Protocol Concerning Specially Protected Areas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the Mediterranean,Date of Signature:10 June 1995,Entry into Force:12 December 1999(replaced Protocol concerning Mediterranean Specially Protected Areas 1982),Article 9。。此外东北大西洋公海保护区网络以及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措施亦要经过类似的程序才能得到通过。因此,既有的公海保护区所依托的法律机制并没有赋予一国单方面建立和管理海洋保护区的权利。
因为公海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实际上更侧重于为在特定受保护的公海区域内活动的当事方施加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东北大西洋渔业组织设立封闭区域以禁止拖网捕鱼,[6]《南极条约》机制下的南极特别保护区则禁止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②参见CCAMLR,Conservation Measures 91-02:Protection of the Values of Antarctic Specially Managed and Protected Areas,adopted in 2012。。而这本质上是为第三国创设义务的效力问题。从目前公海保护区的既有实践来看,不论是地中海的派拉格斯海洋保护区,还是东北大西洋的公海保护区网络,亦或是南极的海洋保护区或南极特别保护区/特别管理区,都没有第三国以书面的方式明文对这些公海保护区所依托的法律文件予以同意。
因此,从条约法的一般国际法原理的角度来看,这些公海保护区的建立及相应的管理措施无法通过协定国际法或条约机制对第三方产生拘束力。不过,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区域性法律机制的地位得到了全球性条约的承认,从而使得区域性的海洋养护和管理制度通过国际条约对区域机制之外的第三方产生间接的法律效力。《鱼类种群协定》对区域渔业组织权限的界定就是一个范例,笔者将在实例分析部分以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为例对这一情形进行分析。
另外,由于条约的规则有可能会通过作为或发展为习惯国际法规则从而对第三方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③参见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dates of conclusion:May 23rd 1969,entry into force:January 27th 1980,1155 UNTS 332,Article 38。。[5]260因此并不能排除公海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所涉及的规则有可能因为构成习惯国际法而对第三方产生拘束力。
(二)条约或习惯国际法下公海保护区与第三方的关系
从条约法的角度来看,公海保护区所依托的区域性条约机制一般情况下无法产生第三方效力,但公海国际法律制度有其特殊性,一方面,规定了公海法律制度的《海洋法公约》是全球性的国际公约,目前包括欧盟在内已有166个缔约方,[7]囊括了除美国外的主要海洋国家,本身已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效力,另一方面,公海国际法律制度中的部分规则和原则也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亦能拘束美国等非缔约国,例如国家保护海洋环境、进行国际合作以及适当注意的一般性义务。那么设立和管理公海保护区的区域性条约机制能否以这些国际法义务为由,来要求第三国遵守其公海保护区制度呢?
首先,所有的国家都有一般性的义务以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不能损害国家管辖范围外地区的海洋环境,这是海洋法和国际环境法下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不仅仅体现在《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中,也被视为是一项习惯国际法。[8]5该项义务既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也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公海。因此,如果一些国家基于区域性的条约或国际组织划定了公海保护区并采纳了相应的管理措施,本身可以视作是履行这一义务的体现,与国际法的要求是相一致的。同时,如果在该海洋保护区所实施的管理或限制性措施(例如禁止排放污染和有害物质、禁止拖网式捕鱼、限制航行或进入)对于保护和养护该地区的海洋生态环境是必要的,而违反这些措施的要求会对该区域的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的话,那么第三国可能会因未遵守该公海保护区相应的管理规则而违反保护海洋环境的一般性义务。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国家依据条约或国际组织所建立的公海保护区是有可能借助公约或习惯国际法下的一般性义务而产生第三方效力的。然而,对于这一一般性义务的法律意义,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就认为该保护海洋环境的一般性义务由于其内容比较空泛,不够具体,因此不能为国家创设具体的权利和义务。[9]按照这一看法,是不能单以保护海洋环境的一般性义务为由去限制他国依据航行自由、捕鱼自由等相应海洋权利所进行的公海活动的,也不能单以此项一般性义务要求一国遵守其他国家所建立的公海保护区及相应管理措施的。笔者对此的理解是,对于一项义务的关注点应在于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而非其是具体的还是宽泛的,如果其已被纳入协定国际法亦或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那么在法律上对国家而言就是有拘束力的,不能以其仅仅是一般性规定为由认为其无法对国家的权利或自由进行法律上的限制。当然一般性的义务可能带来实施或执行上的问题,毕竟义务的内容和违反义务的标准因为缺乏具体的规定而显得难以判断和把握,这又会进而产生谁来判断和谁来把握的问题,最后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有关当事国自说自话,从而使得保护海洋环境的一般性义务如同处在云端之上楼阁一般,触碰不到国际社会的现实。具体到公海海洋保护区的背景下,一些国家或许可以基于区域性法律机制或组织建立公海保护区并规定相应的保护和管理措施,甚至可以以保护海洋环境的一般性义务为由要求第三国予以遵守,但那又如何?问题比比皆是,相应的管理措施对于保护相应区域的海洋环境来说是必要的吗?一国不遵守他国制定的相关管理措施就会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吗?就是对《海洋法公约》和习惯国际法的违反吗?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性义务回答不了这些问题,第三国也可以轻易地找到不遵守他国建立的公海保护区及相应管理措施的理由。因此,从书本上的法律这一角度来看,保护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可以作为公海保护区拘束第三国的一个法律上的理由,但从实践中的法律来看,上述一般性义务不足以为公海保护区的第三方效力提供一个坚实的法律基础。
其次,基于《海洋法公约》和习惯国际法的要求,国家还有参与国际合作的义务以保护海洋环境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①参见ITLOS,The MOX Plant Case(Ireland v.UK),Order of 3rd December 2001,para.82;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10 Dec.1982,21 ILM(1982)1261,Article 117-118,197。。该项义务存在着同保护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相类似的问题,即原则性/宽泛性地规定能否产生具体义务以约束国家管辖下的公海行为和活动。对此有学者以“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为例,认为这一合作义务是有其具体法律意义的,基于公约第300条规定的善意原则,它给所有国家施加了一项秉持善意参与国际协商并达成有关协定的一项的义务,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单方面地坚持己方立场而不作任何修改的话,不能称之为履行了这项义务,因此在海洋环境领域,各国具有法律上的义务以善意的方式进行协商以应对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所面临的威胁和风险。[8]6不过,该原则本身并不足以为公海保护区的建立和管理乃至第三方效力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相反,如果一个国家不经协商自己单方面建立公海海洋保护区,非但不能拘束第三方,这一行为自身也是违反国际合作义务的表现。[10]但是,如果这一义务能够作为一国行使其公海自由或权利的前提条件,则能够为公海保护区的第三方效力提供一个坚实的法律基础,例如如果一国恶意不参与区域性环境法律机制的协商会导致其不享有该区域的特定权利和自由,那么基于该区域机制所建立的公海保护区就能够对该第三国的公海活动予以限制。1995年缔结的《鱼类种群执行协定》就是上述假设的一个例证,基于该协定海洋保护区有可能产生间接的第三方效力,笔者将在下一个部分对这一情形进行详细分析。
此外,一国在行使其公海权利时,还要受到适当顾及他国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的义务的限制①参见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10 Dec.1982,21 ILM(1982)1261,Article 87(2)。。这里面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他国为了保护海洋环境及生态系统所建立的公海保护区及相应的管理措施是否属于应当被适当顾及的“公海自由的利益”范围内,如果“适当顾及”的规则意味着第三国在行使其公海自由时有义务顾及这些与公海保护区相关的管理措施,那么在这一背景下,适当顾及的义务就能够导致公海保护区制度的第三方效力。当然,这只是笔者所作的一个工作假设,尚无理论研究和实践支撑来证明这一假定;相反,“查戈斯仲裁案”的裁决还以英国没有适当顾及毛里求斯的权利/义务为由认定英国单方面所建立的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不符合国际法②参见PCA Press Release,Chagos Marine Protected Arbitration:The Arbitral Tribunal Renders its Award,The Hague,19 March 2015。,可见适当注意的义务对于公海保护区的第三方效力而言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可以看出,公海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能够在《海洋法公约》和习惯国际法所确立的公海国际法律制度中找到依据,这些依据也确实对公海自由构成了一定的限制。但这些依据基本上是较为宽泛地一般性原则,在现有的公海国际法律制度和船旗国专属管辖制度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动的情况下,无法为公海保护区的第三方法律效力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这是因为国家具有保护海洋环境、参与国际合作等国际法上的义务本身并不等于否定其所享有的公海权利和自由,在实践中公海保护区所依托的区域性法律机制也很难以这些一般性的义务为由,来禁止或限制第三国在保护区内行使包括航行、捕鱼等具体权利在内的公海自由,除非这些一般性的义务被赋予了具体的后果,例如《鱼类种群执行协定》所规定的若不履行参与区域性渔业合作的义务就不在该区域享有针对特定种群的捕鱼权。
综上所述,根据条约法的一般国际法原理以及公海保护区所赖以建立的国际法律依据,公海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一般情况下不能拘束第三方的活动和行为。但存在两类例外,一类是区域性的公海保护区实践可能会通过构成习惯国际法而拘束第三方,另一类是区域性的条约机制可能会通过全球性条约而对第三方产生间接的拘束力。而这两类例外情形必须结合公海保护区的具体实例加以分析,无法一概而论。
(三)具有第三方效力的公海保护区实践
针对上文提到的公海保护区可能产生第三方效力的两种情形,下文将分别结合南极公海保护区的实例和东北大西洋公海保护区的实例予以分析。以考察既有的公海保护区中是否存在具有第三方效力的实践。
1.基于习惯法的第三方效力
尽管基于区域性的环境法律机制所建立的公海保护区及实施的相应管理措施一般不具第三方效力,但这并不排除相应的法律和实践因构成习惯国际法而使得第三方需要受到该公海保护区约束的可能。那么习惯国际法是否可能为公海保护区的第三方效力提供法律上的基础?根据受到较广泛承认的国际法理论,构成习惯国际法的前提是一般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③构成习惯法的前提条件在学界有一定的争议,例如郑斌(Bin Cheng)教授认为法律确信是决定性的要素,一般国家实践并非是不可或缺的。由于笔者的讨论重点不在于习惯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因此采用Akehurst的理论作为标准,原因在于Akehurst的理论相较于前者受到了更为广泛的肯定和承认。参见Michael Akehurst,Customs as a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Law,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47,1976,pp.1-53。。在一般层面上,由于公海保护区的国家实践非常有限且不成体系,因此很难主张公海保护区能够依据习惯国际法获得普遍性的第三方效力。但在更具体的层面上,例如在南极的国际法律框架下所建立的公海保护区,习惯法有可能为第三方效力提供法律上的依据。迄今为止《南极条约》共有53个缔约国,囊括了大部分与南极具有科考或渔业利益关联的国家,其中29个已在南极开展科考或渔业活动的国家同时也是协商会议的成员,能够参与协商会议的决策机制,而其他成员则没有这项权利,此外,所有的这29个协商会议的成员同时也加入了公约下的《环境保护协定》,大多数协商会议的成员(仅有两国不是)同时也是南极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成员。[11]尽管这些法律机制的参与国,在绝对数量上并不构成大部分国家,但“一般国家实践”并不意味着大多数国家的实践,仅仅是利益受到特别影响的国家的实践同样足以创设习惯国际法,这一点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得到了国际法院的认可,例如具备太空探索能力的国家在数量上很少,但它们也能够创设与太空活动有关的习惯国际法,而有核国家的实践同样可能在数量很少的情况下创设与核武器使用和削减有关的习惯国际法①参见ICJ,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Judgment,I.C.J.Reports 1969,p.3;另参见Malcolm N.Shaw,International Law,sixth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79。。考虑到国家对《南极条约》和《南极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加入作为国家对规则的声明和接受,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国家实践,且目前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划定及相应管理措施(不论是《南极条约》框架下特别管理区、特别保护区还是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框架下的公海保护区)都需要经过南极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一致同意,而同意本身亦可表明利益相关国对相应规则的法律态度,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南极科考和渔业利益的相关国通过《南极条约》以及南极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机制所设立的南极海洋保护区及相应的管理规定有可能因构成习惯国际法而对机制外的第三国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
不确定性因素在于有关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国家实践是否是一贯的、一致的。目前仅有的反馈是南奥克尼公海保护区有关渔业的限制措施自2010年建立以来得到了较好的遵守,该保护区也未再受到渔业活动的干扰。除此之外,还没有其他的报告反映南极海洋保护区管理规定的执行和实施状况。[12]因此,鉴于相关资料和信息的匮乏,笔者目前还无法对南极海洋保护的建设和管理是否已经构成习惯国际法从而拘束第三方做出准确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南极公海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措施存在通过习惯国际法而对第三方产生法律效力的可能性。
2.基于全球性国际条约的间接第三方效力
《渔业种群协定》第8条将履行国际合作的义务作为一国捕捞公海特定物种渔业资源的前置条件,要求国家在特定的公海海域捕捞高度洄游鱼类以及跨界鱼类之前,有义务参与区域性的区域管理组织或遵守区域性的渔业管理机制,否则便不能捕捞上述鱼类种群。而区域性的渔业组织基于养护上述鱼类种群的目的,可以建立“封闭区域”(closure areas)并在区域内实施诸如禁止拖网捕鱼的限制性措施。因此,这意味着区域性的渔业组织如果在其划定的封闭区域内基于养护特定鱼类种群的目的采取了有关渔业的限制性措施,是可以通过《鱼类种群协定》第8条的规定拘束该区域性渔业组织/渔业机制之外的第三国的。东北大西洋渔业组织便是区域性渔业组织中在公海采纳和实施这一措施的典型代表,为了与奥斯陆巴黎委员会协调和共同促进东北大西洋公海保护区网络的海洋生态系统养护,该渔业组织在公海保护区网络内划定了五块完全或部分重合的封闭区域,并禁止在该区域内进行拖网捕鱼等活动。[6]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第三方效力是建立在该第三方是《鱼类种群协定》的缔约方的基础上的,且仅限于该协定所规定的鱼类种群(即高度洄游鱼类和跨界鱼类种群),因此这种第三方效力是限于特定范围的间接的第三方效力(封闭区域→区域性渔业机制→《鱼类种群执行协定》→区域渔业机制外的第三方)。因此,对于高度洄游鱼类和跨界鱼类种群的养护和管理,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在公海保护区内所设立的封闭区域及实施的养护措施可以通过《鱼类种群协定》产生间接的第三方效力,但这一效力并不能涵盖其他鱼类种群。
三、结语
综合笔者的分析,可以认为,海洋法的“公海自由”,以及条约法的“不得为第三方创设义务”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公海保护区的建立和管理,这使得公海保护区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够获得针对第三方的国际法律效力。但这一结论并不妨碍公海保护区在两种特殊的情况下对第三方产生国际法律效力的可能。
第一,公海保护区可能会依据全球性的国际条约获得间接的第三方效力,例如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就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所建立的封闭区域(closure areas)就可以通过《鱼类种群执行协定》而间接地拘束第三方。
第二,公海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措施存在通过习惯国际法而对第三方产生法律效力的可能性。尽管在全球层面上还未形成相应的习惯国际法从而使公海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都能够获得普遍性的第三方效力,但有些区域性的公海保护区实践可能会通过形成习惯国际法从而拘束第三方,这一可能性可以通过笔者对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分析而得到证明,只是这种情形的第三方效力要根据公海保护区的具体实例进行个案分析。
同时,基于联合国特设工作组的建议,联合国大会行将开展针对国家管辖外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国际协定的谈判,该拟谈判的协定被视为未来的“海洋法公约第三执行协定”,[13]其中公海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将是重要内容之一,有关这一国际协定的谈判成果很可能决定未来公海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的走向以及对公海保护区第三方效力问题的认识,目前一种可能的方案是仿照《鱼类种群执行协定》,将公海保护区的建立和管理职责更多地赋予区域性的环境组织,赋予其间接拘束第三方的效力,以达到养护公海生物多样性的目的。但具体谈判会如何展开,会达成怎样的成果,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可以肯定的是,公海保护区的进一步设立以及加强对保护区内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未来也会有更多的国家实践加入到这一趋势和潮流中来,公海保护区对第三方的法律效力问题会不会因为这一趋势的发展而产生新的答案,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KIMBALL L A.The international legal regime of the high seas and the seabed beyo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and options for coope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beyo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CBD:technical series No.19)[M].Montreal: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2005:iii.
[2] WOLF S,BISCHOFF J.Marine protected areas[EB/OL].[2015-09-15].http://opil.ouplaw.com/view/10.1093/law:epil/9780199231690/law-9780199231690-e2029?rskey=jE0lQD&result=1&prd=EPIL.
[3] 马尔科姆·N·肖.国际法[M].6版.白桂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30-731.
[4] 白桂梅.国际法[M].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93.
[5] AUST A.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6] OSPAR Commission.2016 status report on the OSPAR network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EB/OL].[2017-09-03].https://www.ospar.org/documents?v=37521.
[7] UN 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Status of the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as at 10 Oct 2014)[EB/OL].(2014-10-10)[2017-09-02].http://www.un.org/Depts/los/reference_files/status2010.pdf.
[8] SCOVAZZI T.Marine protected areas on the high seas:some legal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2004,19(1).
[9] LAGONI R.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M]//KIRCHNER A.Inter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Law:Institutions,Implementation and Innovations.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3:157-168.
[10] TUERK H.Reflec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law of the sea[M].Leide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12:169.
[11] Parties[EB/OL].[2016-03-02].http://www.ats.aq/devAS/ats_parties.aspx?lang=e.
[12] 范晓婷.公海保护区的法律与实践[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118.
[13] CHURCHILL R.The LOSC regime for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fi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RAYFUSE R.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Law.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