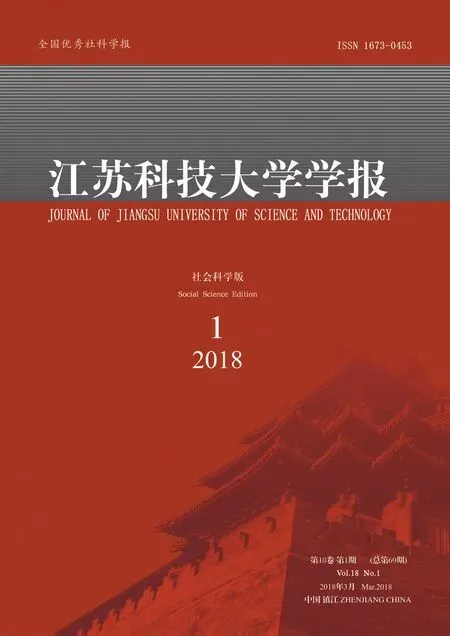地理学视角下的网络热点事件分析与策应
2018-02-10张艳
张 艳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当前,基础设施的完善、移动技术的进步、利好政策的出台、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互联网+”思维的渗透,共同促进了网民规模和网络使用深度的增长,并决定了现代舆论中心的虚拟化。自媒体时代,舆论去中心化显著,网络热点事件本身成为新的舆论“中心”。笔者在对网络热点事件的长期观察中发现,地理活动与舆论传播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地理学中的某些概念和模型能够为热点事件在网络中的发酵和传播提供新的视角和解释。
一、 互联网地理学概念与现状
(一) 互联网地理学
冯文(1999)首次提出互联网地理学的概念,并指出其有两个含义:一是用互联网促进对地理学的认识,另一层是对互联网世界地形方面的一种考察[1]。他认为互联网世界有其独特的地理结构,互联网中的距离是以两点之间中途站的数目以及传送速度组合而成的一种主观的距离感觉,互联网地理学可以向传统地理学借用概念。汪明峰(2012)在第六届人文地理学沙龙上总结了互联网地理学的四个方面:一是虚拟空间的地理学研究,二是有关互联网本身的地理学问题,三是互联网效应的地理学分析,四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展开地理学研究[2]。
目前,在虚拟空间的地理学方面,对社交网络中的人类社会关系、交互行为、时间空间特征等问题的研究已成为网络社会学、行为地理学、人类行为动力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在互联网效应的地理学研究中,人文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都有很大进展;在以互联网为工具的地理学研究中,其主要集中于空间可视化、导航搜索、区域开发与规划、借助大数据对海量地理信息进行挖掘的“计量革命”等。但在第二个层面,即对互联网本身的地理学研究则相对停滞。笔者正是针对第二个层面内容,以网络热点事件为剖面,对其进行尝试性的理论研究。
(二) 网络空间
“网络空间”最早由美国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于1984年在其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提出,原指将人的大脑接通电极就能进入的虚拟空间,现指一个由计算机连接和生成的多维全球网络或虚拟实在。Shiode (2000)对网络空间进行了分层,将其由实体到虚拟分为了真实空间、互联网、网站空间、虚拟城市[3]。Batty(1997)的观点与其相似[4]。Cai等(1999)将网络空间分为四个层面,分别是物理层、网络层、应用层、知识与行为[5]。目前,对物理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光缆及服务器的发展、域名的增长、网民的使用状况等方面;在网络层上,主要是对于网络社区的研究,当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微博,国外则集中于Facebook 和 Twitter。社交网络,是指以一定的社会关系或共同兴趣为纽带,为在线聚合的网民提供沟通、交互服务的Web2.0应用,其横跨网络层、应用层和知识与行为三个层面。在文本内容上,社交网络的研究有市场战略分析、舆论情绪、情感表达、热点预测、信息冗余处理等;在网络结构上,有网民结构、网络联结等。1967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Stanley Milgram通过著名的“追踪美国社交网络中的最短路径”实验发现了“六度分离”。此外,李德毅(2009)提出用物理学的粒子性和波动性来研究社交网络中的动力学行为。
应用层的另一个热点在于网络空间安全和网络空间治理。王世伟(2015)认为网络空间安全已经成为与陆、海、空、太空并列的全球五大空间安全问题之一[6]。在全球层面上,由于不同国家之间资源与能力的不对称,数据主权竞争已成为国家竞争的前沿阵地。在国家层面上,网络空间冲击传统中美关系,并引发博弈与竞争。在社会层面上,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网络空间犯罪行为的刑法回应、网络空间中的言论边界和政策建构、虚拟网络空间内人类社会关系与交互空间的特征等。
(三) 网络热点事件
网络热点事件,又称“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互联网上发生的有较多网民参与讨论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由于互联网传播隐蔽和快捷,此类事件常常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产生巨大影响。唐芳贵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心理机制是事件信息与网民心理的双螺旋演化以及信息流与意识流的共振共生,它往往由公众心理信息爆点引发,如敏感、女性、暴力、权贵等;同时,网络群体性事件也极易引发网络语言暴力、“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行为*参见唐芳贵《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学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目前对网络热点事件的研究多集中于传播机制、舆情监督与引导、热点挖掘与情感分析、话语权变化等。
二、 网络热点事件的特征与问题
(一) 新事件层出不穷,阴影并未消除
依据“知微事见”(http://ef.zhiweidata.com/)数据库记录,2016年共有1 012件热点大事件被记录,平均每日新增2.77件。其中,社会热点322件,占比最高达31.8%;其次为人物事件、娱乐事件和谣言事件,占比分别为17.2%、13.9%、12.8%。数据库使用全平台影响力指数量化事件影响力,其数值是根据事件在网媒、微博、微信三个平台的传播效果对其进行综合、加权、归一化而得出的百分制指数。2016年网络事件排序前三分别为:“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93.6)、“习主席中东三国行”(93.5)、“多地启动楼市限购”(92.4)。这类数值较高的事件,除了本身的重大影响外,也与此类事件较长的持续时间有关。2016年几则突发性爆炸事件,如“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影响力指数为81.3,“魏则西事件”为83.8,“三星爆炸事件”为85.2,“罗一笑白血病事件”为83.3。这些事件一经发生和发酵,立即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和传播。
经过空前的大讨论之后,民众焦点迅速被新热点取代,原有热点事件的后续信息并未得到应有关注。事件后续信息关注与传播乏力,使得事件在传播过程中引发的恐慌等负面情绪并未得到有效疏散和消除,而是隐性地残留在公众潜意识中。当下一个热点事件稍微触动神经,就会引发公众本不该有的过激反应。
(二) 舆论风向转变快,群众疲于追逐
网络热点事件的另一个特征是舆论风向转变迅猛。一个大智大勇、大忠大义之人,在新资料、新动态、新判断介入之后,瞬间就会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罄竹难书之徒。而职业水军、粉丝心态、公关营销等因素的目的性风向引导,使风向拉锯和反转的频次和力度大大增加。由此,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全面性、有效性大打折扣。在海量信息的掩护下,公众无暇检验信息的真实性。受限于时间和精力成本,公众在对现有信息的归纳与总结上也会面临困难。在多而杂乱、真假难辨的信息狂潮中,公众只能寄希望于专业以及一线人士的解读与分析。舆论背后复杂且惊人的经济利益纠缠以及互联网中的“马太效应”,导致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的往往是披着各色“马甲”的“热心网友”。而真正的专业或一线信息,早已被更迭迅猛的信息浪潮吞没。
(三) 谣言四起,辟谣被忽视
除了事件中的虚假谣言,谣言本身也能引发社会的广泛恐惧。在“知微事见”数据库中,2016年谣言类事件130件,占比12.8%。全平台影响力指数较低甚至为零的事件,均为并未得到广泛传播的谣言。比如“低钠盐是送命盐”,因为辟谣及时以及谣言水平低劣,信息在第一时间就被中止传播。
然而,也有一些谣言因为触及了公众的敏感神经而引发大量关注。“年收入12万属于高收入”是钱袋子的问题,“药店公交车变身失联儿童守护站”是儿童安全问题,“安徽一男子手术后右肾失踪”是人身安全问题,“撕不烂的塑料紫菜”“肉松是棉花做的”则是食品安全问题。这些本应是稍有科学素养以及态度严谨的人就能分辨的谣言,却在社交网络中甚嚣尘上。这类谣言相较于曲折复杂、变化迅速且难以验证的事件中的虚假信息,官方及权威辟谣难度较低,辟谣反应敏捷。而公众即使在了解真相后,仍然会在下一次的类似谣言中迷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精准击中了公众的痛点。
三、 地理学视角解读
(一) 作为“地方”的网络热点事件
Relph(1976)提出“地方”(place)有三个标志性特点,即物理环境、人类活动以及心理意义。Tuan(1977)指出“地方”的主要功能在于促使人们产生归属感和依恋感,不同的地方会使人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Breakwell也认为“地方”是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的共同产物。在权威定义中,异质性、可达性和地方认同是“地方”的核心特质。对于判定对象而言,场所感是关键所在,它的影响因素有可识别性、可达性、多样性、活力、文化脉络等。网络热点事件的场所感,完全经得起以上各个影响因素的考验。观察者对热点事件的关注和参与构成了此类“地方”的人地关系。
网络热点事件作为“地方”,唯一可能存疑的地点在于物质基础。然而,“地方”这个概念并非从未被延伸过,海洋、沙漠、密林相对于人类原始的集聚区是一种延伸,新大陆被旧大陆熟知是一种延伸,虚拟事件作为地点也是一种延伸。只是这一次是在信息时代中的延伸,是一种走向虚拟的跨越式延伸。在虚拟网络中,热点事件具备称为“地方”的先决条件。为与实体地方进行区分,可称其为“i地点”。
两个“i地点”的关系,就是“i距离”,“i距离”的大小决定“i地点”进入观察者视野的难易程度,影响因素有时间、路径和活跃度。由于虚拟网络的记录属性,时间不再被空间孤悬在外,观察者的介入时间会对“i地点”的可达性和呈现面貌产生重大影响。观察者所选择的路径对到达“i地点”的便捷程度也非常关键。热点事件的活跃度决定其在服务器中的优先级,也即通往“i地点”路况的好坏程度。
(二) 网络热点事件中的“时空压缩”
空间,Sack(1997)认为是一种矢量的精确表达。网络空间的概念相对成熟,学界观点有:协商一致的幻觉,计算机数据库在人类系统中的图像表达;平行宇宙;一个新的空间,对人类的感官而言是无形的,是一个比物理空间更重要的分布于其上、其内、其间的空间;一个多人冲突、共鸣和震撼的隐喻。檀有志(2013)认为,网络空间除虚拟性、匿名性外,还拥有空间规模无限化、空间活动立体化、空间效应蝴蝶化、空间属性高政治化等特征。从这些特征来看,网络热点事件作为虚拟空间中的次级空间,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为了与实体空间区别,也可将其称为“i空间”。
戴维·哈维(David Harrey)的时空压缩理论认为,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技术的进步使时间飞快加速,社会发展不再是线性均值,而是呈内卷化趋势,无限延伸的均质时间消逝,时间因为海量信息而爆炸,均质的空间被时间征服,空间场所复活于文化意义上[7]。网络热点事件将这种抽象、晦涩的时空压缩现象以简单而具体的微观表现形式展示出来。在网络热点事件的发酵和传播过程中,观察者并非按照严格的时间或空间顺序接收信息。事实上,信息是以一种坍缩状态的时空综合体被捕获的。这正是时空压缩理论中所指的“空间场所复活于文化意义上”。换言之,空间场所复活于网络热点事件上。
实体空间的矢量表达依托于地理位置和物质形式。“i空间”的位置可参见“i地点”,“i空间”大小的矢量表达为数据量。网络热点事件的数据量越大,空间体积就越大,就越容易被更多的观察者发现。
(三) 网络热点事件的地理学特征
威尔逊旋回,是地理学中板块构造学说的重要理论之一。Wilson(1974)在研究大陆裂解与大洋开闭的全过程后,将大洋形成与构造演化归纳为六个阶段,被称为威尔逊旋回。这六个阶段分别为:胚胎期,地壳上拱,岩石圈破裂,形成大陆裂谷;幼年期,地幔物质上涌、溢出,岩石圈进一步破裂,并开始出现洋中脊和狭长海盆;成年期,洋盆扩大,洋中脊形成,出现成熟的大洋盆地;衰退期,海底扩张,洋盆侧出现海沟,俯冲消减作用开始,洋盆缩小,边缘发育沟弧体系;终了期,随着俯冲消减作用的进行,两侧大陆靠近,发生碰撞,边缘发育年轻造山带,其间残留狭窄海盆;遗痕期,两侧大陆直接碰撞拼合,海域完全消失,形成年轻造山带。这一旋回被认为指导着地球表层的构造活动和演化全局。
网络热点事件层出不穷,其类周期性过程中也存在类似旋回。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潜伏阶段、发酵阶段、扩散阶段、漩涡阶段和消亡阶段。其中,威尔逊旋回中胚胎期和幼年期对应的网络热点事件的相应阶段因区分度低、缺乏明显判断标志而被合并为潜伏阶段。在潜伏阶段,公众负面情绪缓慢积累,尚未形成爆点;在发酵阶段,信息本身的特性是关键,包括易引发情绪共振的内核、媒体化包装、匹配的社会背景等;在扩散阶段,多线路“大V”传播产生共振,事件的扩散是时间和机遇问题;在漩涡阶段,二次发酵与扩散,并伴随着情绪与意识的递进性转变;在消亡阶段,有效信息减少,广告出露,负面情绪下沉。准确把握时间的发展阶段,才能采取准确的管理措施。比如,官方信息最晚要在第四阶段开始之前介入,第四阶段完全是情绪泛滥的时期,公众不再关注真相,即使有官方信息,也不会被信任。
热点事件集中爆发,实际上是公众长期关注以及担忧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公众情绪在被突发事件引爆后急速释放的过程。在地理学中,火山爆发、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现象以及地幔地壳运动、水热运输过程都与此相似。在网络空间管理中,对热点事件本身的监督和引导是有效的,却也是被动的。而对人们在长期生活中积累的压力和负面情绪给予关注和疏导,及时解决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安全、公平问题,才是排查潜在问题和隐患的关键。
四、 实证分析——以“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为例
中国互联网平台显示,2017年上半年,在网站统计总量指标中,新浪微博总榜排名第16位,为社交网站之首。而前15位均为各大资讯门户、搜索引擎、网上购物、视频网站、安全卫士、电子支付等类型的硬性需求网站。《第40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中最新统计显示,至2017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有7.24亿,网民移动上网占比96.3%。而在移动客户端统计指标中,社交应用前三位分别为微信朋友圈、QQ 空间和微博。前两者作为即时通信工具所衍生的社交服务,先天条件决定了它们是以熟人社交为主。即使产品在定位和运营中不断汇入弱关系社交,其在信息传播上的媒体属性仍然较弱。而微博则是以社交关系为基础进行信息传播的平台,媒体和社区属性兼备。微博主打陌生人社交,并建立起复杂的传播和社交网络,使其更能代表在充分可达的情况下热点事件在网络空间中的发酵与扩散过程。
基于本研究是对网络热点事件全周期过程进行的微观的追踪与分析,笔者将选取微博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于微博上引起舆论关注,并在微博中有较为完整的周期过程,且在短时间内引起非常广泛的社会讨论,非常适合作为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样本。
2016年4月5日,微博网友爆料了一段自己在如家旗下的和颐酒店发生的惊魂经历。此事在微博平台上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两个相关话题的累计阅读量超过31亿次,创造了中国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大规模的网络传播事件。以下从微观层面剖析事件的整个过程。*数据来源于新浪微舆情(http://wyq.sina.com/login.shtml)、知微事见博物馆(http://ef.zhiweidata.com/index.html)和新浪微博网站(http://weibo.com)。
(一) 发酵阶段
2016年4月5日00∶06,昵称“弯弯-2016”的新浪微博账号发微博并在优酷土豆上传了一个视频,00∶12再次发博,带上话题“和颐酒店女生遇袭”。由于发博时间是在凌晨,传播力相当微弱。08∶01至08∶44,该账号又连发八条微博并关联四个“大V”账号,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恐惧情绪。博文中强故事性、代入感、感染力的词汇众多,第二条 “事发至今超过24个小时,酒店经理关机消失,派出所录完笔录无下文,携程投诉无果”则直接戳中了大众对责任不明晰、处处推诿现状不满的情绪点。第三、四、五条属于强细节还原,除了强大的代入感,它们还点出社会长期关注的三个爆点:一,男子长期徘徊无人管,说明酒店管理不善,安全工作不到位,甚至有暗中勾结的嫌疑;二,因为像两口子吵架而无人帮助,最后遭遇侵害,这一类事件已被广为诟病,有长期的预热基础;三,女性在公共场所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第六、七条重点突出酒店安保和善后非常差,而且不知情、不关心。最后一条则把事件引向“不可知”“阴谋论”等极易引发广泛讨论的方向。
在初中音乐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因为其教学方式的缺乏,导致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对音乐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认知发生偏移。导致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跟随应试教育的脚步,对音乐框架及知识进行呆板教育。这种教育模式忽略了学生对音乐的喜爱性及主观性,使学生对课堂所学知识无法进行深入思考及总结,使整体教学过程偏向呆板化。
15∶00,该账号又发布三条微博,表达了对派出所与酒店方面对此事冷处理的不满,同时也反映出热心网友和记者朋友的参与。20∶10,该账号发布了一条整理性长文,细节详尽,图文并茂,易于传播。同时,又加上另外一个引爆性话题“卖淫窝点案底酒店”。在这条微博发布之前,前十三条微博都未引起足够关注。
在发酵阶段,信息本身的特性成为关键。在该事件的基因里,同时包含女性、暴力、公权、安全感等关注点,这些都是极易触发群体情绪共振的关键点。因此,作为热点事件,它具备广泛传播的先天条件。引发情绪共振的事件内核,加上经过更具吸引力和传播力的媒体化包装,因而它具备了成为爆发式传播事件的先决条件。
(二) 扩散阶段
至4月5日12∶31,经第七位转发者“正经星人”中转,5分钟后有20万粉丝的“布小什大师” 转发。下午,“老卒过河”转发后,有143万粉丝的“纯良大叔”接力转发。这是一条可能引起广泛关注的传播链,但未能成功引起链式爆炸性传播。
20∶10,第十四条微博发布,在4个小时内,引发93.7万次转发、28.3万条评论和1.68亿次阅读。21∶36,昵称为“所长别开枪是我”的账号转发并评论该微博,这条转发又被二次转发6.5万次。这个账号的认证信息是知名网络评论人、新浪微博社区委员会专家委员、微博签约自媒体,是一个擅长以有趣的方式讲述趣闻的“大V”。这一类微博“大V”的粉丝属于活跃度非常高的群体,当时有粉丝556万。
尔后,又有18个粉丝过百万的“大V”开始转发。其中,有粉丝409万的“牛文文”、粉丝518万的“我的厕所读物”、粉丝112万的“葛天-PANDA”、粉丝292万的“赵子琪”,粉丝累计超5 500多万。期间,产生了多条传播力非常强的传播链,比如从“所长别开枪是我”到“休闲璐”,经“囤货君”至“夏目家的小诗哥”等。经过这一轮接力传播,该事件达到网络舆情监控阈值。
至此,“大V”群体开启事件爆炸传播模式。6日凌晨,白举纲、Angelababy、海清、马苏、舒淇等明星纷纷加入评论转发大军。次日上午,姚晨、张俪、吴亦凡、贾乃亮、范冰冰的微博账号还在跟进,明星粉丝再次接力转发评论。由此,事件开始进入刷屏模式,大小媒体集体发声。
在扩散阶段,多线路“大V”传播共振对引发大规模传播起了决定性作用。上文中所说的第一条传播链是有可能成功的,但由于第一条微博的传播性差于第十四条,所以第十四条能够更快地传播。“所长别开枪是我”成为关键点,在“休闲璐”转发后,经三条“大V”间的传播路径,由此带来了真正的大规模信息蔓延。在“大V”传播链共振后,拥有更强大粉丝群体的明星账号加入转发队伍,公共媒体集体发声,事件传播规模进一步扩大。因此,事件的扩散是时间和机遇问题。
(三) 漩涡阶段
事件完全进入大众视线后,公众纷纷加入关注和讨论大军,事件再度发酵和扩散,并引发更多人赶赴网络热战现场。在最初了解到事件后,群体开始进入无意识的情绪表达状态,理性分析和判断力缺失。由于不同群体进入现场的时间不同,后来者缺乏对事件的充分了解,极易盲目跟风。此时的舆论关键词集中于“恐怖”“气愤”“可怕”等负面情绪词汇。经过一定时间的缓冲后,一部分人开始了理性思考,并进行有意识的表达。比如,对事情真相的质疑、对相关人员和机构的追问、对当事人的保护、对此类情况的应对措施等。
随后,事件相关的各机构和责任人主动或被动地站出来发表意见。这些新的物料一经投入,迅速引发更广泛的讨论。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权威声音,公众获得的权威信息比较少,为谣言滋生提供了土壤。于是,谣言迅速蔓延,阴谋论盛行。
4月6日11∶01,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布微博称,“警方正在彻查,请您继续关注”。然而,由于信任缺失以及发声太晚等原因,评论多持嘲讽态度。4月8日 09∶20,“平安北京”再次发博通报情况,涉案男子已于4月7日二十一时抓获。4月9日18∶37,“平安北京”通报后续情况,“女子酒店被袭案5名涉案人员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这些官方结论公布后,声讨大军开始偃旗息鼓,聚集的网民开始散去。
在漩涡阶段,事件进行了第二次发酵与扩散,并伴随着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情绪表达到理性表达的转变过程。这一阶段,更多的人加入网络热战现场,立足于各角度的分析、应对、质疑、讽刺大量涌出,并形成意见集团。同时,由于真相缺失,谣言滋生并迅速蔓延,阴谋论盛行。其后的官方信息因公信力走弱,发声太晚,评论多持负面态度。因此,相关职能机关应健全反应机制,及时辟谣,快速介入,并将相关信息处理方案尽早公开。
(四) 消亡阶段
在嫌疑人被捕之后,仍有大量网民关注事件并主动带话题以维护话题热度。4月11日,“和颐酒店女生遇袭”退出热门话题。但公众关注仍在继续, 4月12日至15日,话题仍有1千万阅读量和1.6万讨论量。然而此时话题下几乎没有有效信息,而是被广告信息攻占,其中夹杂着极少数询问后续结果的声音。至4月22日,话题下已经完全没有有效信息,只有随手带话题的执着者。
10月21日近9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北京朝阳法院”通报事件后续,“和颐酒店女子遇袭事件涉事男子李某某因涉嫌介绍卖淫罪被朝阳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北京朝阳法院已于10月17日正式受理此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然而,这条信息到12月底只被转发了1 628次。这与话题的阅读量相比,微乎其微。
11月4日,“北京朝阳法院”再次发博通报案件审理结果,“涉事男子李某某因介绍卖淫罪今日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五千”。同时法院给出司法建议,“要求酒店查找安全管理漏洞、提高员工职业素养、制定整改措施、杜绝安全隐患”。而这一条信息的转发量只有75次。审理结果通报后,也有不少媒体发布相关信息,但并未产生显著的传播效应。
在消亡阶段,关注人数减少,话题热度降低。由于有效信息减少,广告蜂涌而出。部分人群的不满、挫折感、相对剥夺感、怨恨并没有消失,只是暂时退潮,并会沉淀到下一次事件中。而相关的后续报道和辟谣并没有得到网民的足够关注,这给网友造成了一种事件被搁置的负面印象。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在辟谣和公示结果时,选择更多的渠道和方式。
(五) 讨论
从事件分析的微观层面来看,在时间维度上,网络空间中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发酵阶段、扩散阶段、漩涡阶段和消亡阶段。而网络热点事件的潜伏阶段,是热点事件发生前舆论环境中公众情绪长期积累的过程。它并非以超高关注和海量数据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而是处于一种可感知却无法确证的状态。然而,即使在实证分析中无法微观记录,这一阶段的存在却是客观事实,甚至还是热点事件爆发时策应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网络空间中群体性事件的潜在原因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积累的压力和不满情绪没有出口。关注和解决潜在的问题和隐患才是关键。对本案例而言,在“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发生之前,网络上已经长期流传关于单身女性在公共场所的安全隐患问题。网友在各自的圈子里传来传去,并没有形成集群表达。如此,虽未能引起舆论监督的足够重视,却在网民意识中种下了恐慌和不满的种子。本案例的发生,迅速点燃了网民长期积累的怨气,在全网引起轰动。因此,对此类问题要及时发现,尽早解决关键隐疾。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威尔逊旋回对网络热点事件有很强的类比性,在网络热点事件策应中可以借鉴。
五、 小结与展望
网络热点事件的舆论传播,与自然地理现象的活动机制有高度相似性。将网络热点事件地理化,可以使网络舆论更易于被精确柔性地监测、引导和疏解。类似于对自然现象的监督、观测和防范,对网络热点事件也可以采用指标化监控、危险因素排查、突发状况紧急制动等措施。此外,还可以引入地理学分支学科理论与模型(如计量地理学),对网络热点事件进行预防和预测。
互联网的核心功能是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在信息载体下,营销处处可见。网络热点事件早已成为舆论营销、价值讨论、文化输出的战场。危机公关、抢占至高点、价值观辩论、“带节奏”、“蹭热度”等各种较量层出不穷。网络热点事件数量增长的初期一定会面临秩序问题。由于网民素质良莠不齐、立场观点千差万别、匿名带来的隐藏属性、积累情绪的肆意宣泄等原因,网络舆论环境时常会陷入混乱状态,极易引发大规模的恐慌、愤怒等负面情绪共振,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良性发展。
当然,热点事件的网络传播与现实处置,又有一定的相互独立性。两者固然相互影响,但现实处置仍有其“客观性”。如刑事案件从案发到侦破,必然有其自身特有的客观过程。同时,因为网络环境的共情和宣泄属性,热点事件的呈现往往有一定程度的夸张和变形。这就需要在实践过程中适当考虑网络空间与客观现实的非完全一致性。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在挑战传统的学术概念。网络空间、网络地址就是从地理学中借鉴的互联网概念。人类活动的土地已经不再局限于脚下,还应该包括互联网中的虚拟“土地”。互联网虽然缺乏传统地理特征,但也具备相应的替代维度,比如时间、活跃度、联结度、数据量等。 “关系”的确定性是高于“存在”的。当不再拘泥于实体之后,地理学可以在互联网信息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倘若认同信息在互联网中的主体地位,那么网络空间将不再拘泥于“虚拟空间”“网络社区”,它还可以是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个概念,可称之为“i空间”。同样地,“地点”也可以延伸到以信息为核心的“i地点”。空间和地点概念的信息化,将为网络信息内容研究提供惊人的可能性。
[ 1 ] 冯文.互联网地理学[J].书城,1999(2):21-21.
[ 2 ] 汪明峰.破坏性创新抑或维持性创新?——互联网地理学的兴起与研究进展[C]//朱竑.地理学评论(第4辑)——第六届人文地理学沙龙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79-82.
[ 3 ] SHIODE N.Urban plann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yberspace[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00(2):105-126.
[ 4 ] BATTY M. Virtual geography[J]. Futures,1997(4/5):337-352.
[ 5 ] CAI G, SOCHATS K, WILLIAMS J, Mapping and analysis of pennsylvania′s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J]. Proceedings of ESRI User Conference,1999(6):26-30.
[ 6 ] 王世伟.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5(2):72-84.
[ 7 ] 韩梅.论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