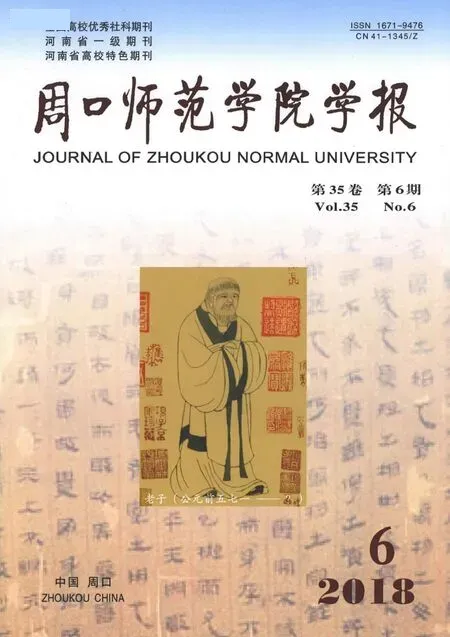论孙方友小说人物形象的地域性
2018-02-09慕德芳
慕德芳
(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文学中的地域包含三个层面:山川、植被、气候等人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人情、风俗、礼仪、语言等构成的文化制度以及心理情感、精神价值、思维观念等人文精神。地域性指的就是这三个层面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稳定的总体文化特征。文学作品中,最能体现地域性的是人物形象。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人物不能体现出地域性特征,其思想和行为就缺乏历史依据和现实根基,形象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将大打折扣。
终其一生,孙方友以小小说构筑起“陈州”这个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表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农业时代的陈州(本文特指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县)曾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平原的一望无垠养成了陈州人豁达开朗的性格,伏羲在此画八卦、定姓氏、别婚嫁使陈州成为中华文化源头之一,孔子、曹植与陈州的历史关联又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文化自豪感。除此之外,离陈州不远的商水、太康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大起义的发起者陈胜、吴广的家乡,那种血性、豪爽恰是本地的文化性格特征之一。陈州灿烂古老的文化影响到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的生活、行为和思想。孙方友在他的数百篇小小说中以地域文化为底蕴,为这些普普通通的陈州人建构了一座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长廊。
一、孙方友小说人物的文化性格
尽管文化源远流长,但陈州的自然环境不尽如人意。地处豫东南平原地带,气候干燥,交通不便,有雨水灾,无雨干旱。自春秋战国之后,陈州的中心地位渐渐衰落。尤其是近代以来,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陈州明显跟不上现代工业社会的步伐。改名为淮阳,陈州及其曾经有的辉煌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千百年来,陈州人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平原地带的开阔养成陈州人幽默达观的心态,历史悠久的文化教化赋予陈州人善良朴实的本性,因资源匮乏造成的生存竞争又培养了陈州人狡黠精明的人生智慧。
孙方友小小说中的人物大都表现了人性善良的一面,像《展氏菜行》中的展家主人、《银元》中的吴三大等,是至善的化身。展氏菜行位于陈州东关,因为贮存黄花菜有方,外地客商多与他们来往。安徽有位大客商,货款充足,与展家做了几年生意,无波无折。有一年,黄花菜还未下来,客商就汇来银票,展家如往常一样为客商收菜、晒菜、贮菜。但一直到腊月二十也不见客商的影子。由于担心黄花菜霉烂,展家主人便自作主张将菜卖掉。此后三年,年年都是如此。三年过后,展家为客商赚了不少银钱,客商仍是杳无音信。于是展家主人便决定亲自到安徽去看个究竟。找到客商的住所,却听说客商已死去三年,展家主人一时愕然,后向仆人说明原委。仆人一听,出主意要与展家主人暗暗分了这笔巨财。
展家主人望了那家人一眼,讥讽道:“我若想昧财,哪还会有你的份儿?”[1]54
事情最后的发展出人意料,客商其实未死,只是以假死的方式试探展家的人品,而展家也以自己的仗义和浑朴赢得客商的信任。自此以后,“那客商便包下了展家的所有库房,每到菜季,展家就为那大客商收菜贮菜。只是那客商仍是不来陈州,一切全由展家主人做主”[1]54。展家主人这种朴实的风格既是生意场上的基本原则,更体现出金钱诱惑下人性的良善。《银元》中吴三大被一老汉所骗,用真银圆换取了老汉的假银圆,于是有了个“好人”的绰号。好人吴三大一直不能提拔,闲暇之余,时时把玩带在身上的假银圆,反思为何好人没有好报。一次在战场上中了一弹,竟然无事,原来是那块假银圆救了他一命。如果不是吴三大心地善良,那也许这一枪就送了性命。他最后能以98岁高龄而寿终正寝,也算是“善有善报”。
“善有善报”是传统文学的主题,体现出文学的教化功能。孙方友在弘扬这一文学功能基础之上,还有超越的一面。在他的小说中,即使那些作恶之人,如《瘫匪》中拦路抢劫的瘫子、《女票》中绑票的土匪头、《匪婆》中的匪首等,在关键的地方也散发出善良的光辉,寄托了孙方友对人性自我救赎的希望和信心。
从生存的角度而言,智慧是一种不依赖道德而具有独立价值的人性品质。人依靠自身的智慧在与自然和同类的竞争共存中生存下来,故而智慧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精明、算计、聪明等。在生存苦难中过日子的陈州人将智慧转化为一种人生的狡黠——一种不损人但却利己的人生智慧。《陈州饭庄》中“一品斋”的老板叫金聚泰,幼年父母双亡,后以厨师为业,在邻人帮助下,在陈州开了一家名为“一品斋”的饭庄。由于经营得当,金聚泰就此财运不断。发财之后的金聚泰为人“敦厚谦逊,而且爱做善事。每日歇业之时,他均要把当天收下来的残羹剩菜再掺些米饭加以调和烩煮,热腾腾、香喷喷地供给数十名乞讨者,让他们也暖暖饥腹,安度宵夜”。金聚泰的义举换得回报,乞丐们也讲义气,喝了金老板的热汤,就自动轮班为“一品斋”护夜。虽然金聚泰小心经营,但“一品斋”慢慢竟有垮台的趋势。原来当地豪门权贵、政府衙门吃饭不给现钱而是记账,时间一长就资金周转困难。金聚泰是外地人又不敢得罪权贵,要账极为困难。一日要账回来极晚,等候已久的乞丐围上来要讨饭吃,金聚泰就对众乞丐说了实情。乞丐们也仗义,愿为金聚泰讨账出一份力。听乞丐们如此一说,金聚泰想出一计,他请众乞丐饱餐一顿,其中两名乞丐故作撑死。老乞丐不愿意,带领乞丐在“一品斋”门前闹事,要求金聚泰厚葬死者,包赔大洋,如若不给,那就告官。“万般无奈,金聚泰只得求助于债户。听说出了人命,各债户再不好意思赖账,不到一天,‘一品斋’的外欠账就基本还清了。”[2]如此讨账的手法,确实是闻之未闻,却又在常理之中。欠债还钱,本属正常。但处于弱势地位的金聚泰却无力要回自己应得的钱,可又不能一放了之——不说饭庄开下去开不下去,单是对众乞丐行善好施就难以为继。金聚泰想出“诈死”的方法讨债,既顺利要回了欠款保住了“一品斋”,又可以继续行善接济他人,最主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还避免了与债主的种种冲突,这就是生存智慧的体现。
还有一种智慧无关生存,却关乎生命,这种智慧也因此具有了道德意识。《怪医》中,刘公子得了怪病,身为御医的父亲竟然无计可施,只好让刘公子回老家等死。路过陈州听戏时,遇到一老翁。此老翁姓孔,在陈州一带很有名气,专治疑难杂症,施手相救刘公子。孔老先生前后连施两计,在刘公子的一急一气中病体痊愈。整个过程中,药不是主要的,完全是病人自身机理紊乱所致。孔老先生不露声色,以种种方法刺激病人,最后取得所要的效果。这是人生经验智慧的表现,而最后刘公子的父亲能够参悟孔老先生的良苦用心,配合一番,治好儿子的怪病,则同样是智慧的体现。
但如果在生存中发挥了智慧,却又有伤道德,那就是一种小智慧,或者说是小聪明,换句话说就是精明。《张三水饺》中的张家饺子名闻遐迩,袁世凯回乡葬母吃了一顿后,赐了“张三水饺,天下第一”8个大字。这8个字当时写在县衙,张三并不知情。于是陈州知县找张三索要一万大洋,要将此字卖给他作匾。张三一听太贵就拒绝了。这幅题字后来被县衙张师爷买走,并开了一家店,挂起袁世凯的题字。生意红火,在周口、汴京都开了连锁店。逼走了真张三之后,张师爷索性辞职,一心做生意,连县太爷也羡慕之余后悔不已。也许从生存的角度而言,张师爷如此做法无可厚非。但无论是巧得题字,还是压制张三,张师爷都表现出机巧之心,这就不是智慧的本然使用。当然他最后能接济穷困潦倒的县太爷,也算是道德的一种补偿。
《雅盗》中的赵仲一日行窃,因看一幅名画入迷而被堵在屋中。他急中生智,为主家大讲特讲《灞桥风雪图》的妙处而脱身。不仅如此,在脱离危险后,他又对作为人质被他押解的主人说他怀中所抱的名画是一幅赝品,真品藏在自己家中,而自己之所以外出行窃就是因为不愿将真品出售。主人听他一说将画轴扔出,赵仲则捡起画幅而逃。在脱身、得画这一过程中,赵仲表现得非常精明,尽管他有“雅盗”的美称,对艺术品也有非常高的鉴别欣赏能力,只是所作所为实在是有碍道德伦理的要求。
二、孙方友小说人物的道德意识
事实上,在孙方友的小说中像张师爷、赵仲这样依靠“巧取”的方式达到目的,从而出现道德瑕疵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物体现出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忠孝节义、民族情怀、扶弱济贫、舍生取义、疾恶如仇……读孙方友的小说总让人有精神上的升华,这与人物体现出的充沛的道德意识密不可分。
在孙方友的小说中,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一方父母官,忠孝节义已经化为他们行为处事的基本道德准则。《生脉散》中,金复然宁愿让女儿改变容颜,也不将她许配金人,体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棋魂》中的老者不仅棋艺高超,而且思想境界高出常人。与出征的将军对弈,故意输棋,以激励将军保家卫国,被将军尊称为“棋圣”。《贾知县》中的贾鲁在陈州任知县,抓住了作恶多端的于姓恶霸,却不想因此被免职。后变卖弟弟田产重到陈州做官,首先处决了于姓恶霸。贾鲁这种舍生取义的做法是其侠义精神的体现,就好像小说中的说法:“贾鲁生于牡丹之乡,很有牡丹之秉性。”[3]《余金亭》中的余金亭被同乡所逼参加抢劫,认出了名角盖三省。自己与盖三省同为梨园中人,又曾同台唱戏。于是就故意暴露出自己,让官府抓了劫匪。余金亭的侠义行为感动了心胸狭窄的盖三省,最后两人竟然成了好朋友。
如果说历史上的那些陈州人多具有侠义古风,那么处于战争期间尤其是抗战期间的陈州人更有一种民族情怀,虽然多是小人物的小作为,在历史长河中甚至激不出一朵浪花,但在个体意义上,却显现出普通人的家国情怀。
《陶都树》中的龙大是个盗墓贼,偶然间得到稀世珍宝陶都树。此消息很快被日本指挥官川原一弘获悉,派人四处打听龙大的下落。陈州文物商们听说此事,找到龙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龙大能以国家为重,不可将国宝交给日本人。龙大虽然是个盗墓贼,却也知道如果日本人夺走了陶都树,自己将成为千古罪人。最终想方设法,未让日本人得逞。
如果说龙大的爱国意识是经过文物商们的一番教导方才醒悟,那么知识分子在异族入侵、国土沦丧情势下的爱国则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茗香楼主人李云灿一生购书3万卷,且多孤本,就想在陈州开家图书馆,既可会友,又可为家乡文化做贡献。但计划尚未开始,陈州即为日本人攻占。为了能让李云灿投降,日本人以取走茗香楼全部孤本相要挟李云灿。这些孤本是李云灿的“灵魂”,但与日本人合作则是出卖人格、国格。经过一夜的思索,他决定自焚茗香楼,自己为陪葬。焚楼之前,茗香楼全楼挂白,李云灿也一身重孝。面对进逼的日本人的不解,李云灿平静地说:“想我李某,一介书生,一不能保家,二不能卫国,平生也就这么点嗜好,为我们大汉民族收藏点书籍。可惜,现在也保不住了。为不让国宝落入你们这群倭寇手中,我只好亲自送它们上西天!”[4]说完之后,从容赴死。李云灿固然爱书,但他更爱国。在更大的、集体的道义前,李云灿选择了后者。集体价值始终在个体价值之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一般性倾向。作为知识分子的李云灿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的所作所为是中国传统文人爱国情怀的再现。
这种高尚的民族气节同样充溢于《赛酒》中。陈州沦陷,日军常到进贡京都的封家御酒馆喝酒,并与酒馆的相公赛酒量:
封家酒馆的相公大多海量,赛酒必胜。日本人气不过,每每失败,便凶恶地抽出战刀,把胜利的相公捅死。血酒相涌,一片恐怖。
可封家相公仍要冒死夺魁。
日本人越赛越恶,封家相公越来越少……
如果说这些普通的相公可歌可泣,那么封家酒馆的老板封甲冲更是义薄云天。他以一敌五,与日军展开了一场喝酒大赛:
……一气喝了几十盅……
……一气喝了二十五碗……
……搬起五坛酒,一字摆开,然后开喝……
……扬眉吐气地喝光了五坛酒,最后,他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多喝了三海碗……[5]
酒场如战场。喝光尿净的封甲冲最后坦然划着火柴,烧毁了日军指挥部。封甲冲以喝酒的方式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精神品格上摧毁了日军的意志。作为普通老百姓,他们只有以自身力所能及的方式表达对日军的愤恨。
孙方友小说中的人物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都有一种潜意识的道德操守;也无论顺境逆境,都不对其有丝毫违背。《天职》讲的即是一个医生将人救活又将其杀死的故事。故事听上去颇有些悖论,但读完之后,却又觉在情理之中。何伏山于民国元年在陈州创办博爱医院,医术高明,尤其擅长外科手术,豫东闻名。1942年的某一天,何伏山被日本人绑架,为受重伤的藤木治病。尽管陈州众人皆知藤木无恶不作,何伏山也知藤木是被八路军武工队所伤,但何伏山还是穿上白大褂上了手术台,取出子弹,之后又认真护理、医治一个多月。藤木伤口愈合,已能下床走动。在准备离开敌营的时候,何伏山又提出为藤木做一次全面检查。在检查中掐死了藤木。这让日军队长小野大怒,责问何伏山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何伏山说,作为医生,不希望手术做失败。小野再次质问何伏山为何救活藤木又杀死他,何伏山说:为了我的祖国!不救藤木,显然有违职业道德;救了藤木,更失民族大义。先救活后杀死,也许是解决二者之间矛盾纠结的最好方式——既恪守了职业道德,又诠释了民族大义,何伏山的形象一下子升华起来。
当然,小说的结尾还以一个日本医生川中一郎枪杀何伏山再次提升了“天职”的内涵。川中一郎是日军军医,平时非常敬重何伏山的医术。何伏山被绑在手术台上,小野命令川中一郎活活解剖何伏山。在医术和军令之间,川中一郎也是非常矛盾。最后他以开枪打死何伏山的方式了结了这种纠结。
小野让川中一郎活活解剖何伏山,显然是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所使,但更是对何伏山所信仰的“天职”尊严的挑衅和侮辱。川中一郎和何伏山也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何伏山望向手术刀时,也就是在提醒强化川中一郎的“天职”意识,这也是川中一郎用手枪打死何伏山的原因所在。尽管川中一郎和何伏山分属不同阵营,但医生的身份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川中一郎的行为一方面体现了“天职”的强烈的道德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性的幽微复杂。这是《天职》在家国情怀之外引发出的一个值得思索的地方,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方友小说现代性的一面。
三、孙方友小说人物的人性表现
文学是人学,写人性是文学的基本准则,也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宗旨。古往今来,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以其深刻的人性表现穿越时空,打动不同时代、阶级、种族、性别的读者而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孙方友的小说写了好多奇人奇事,在奇人奇事的背后隐含着的是复杂的人性。奇人奇事和复杂人性的结合,既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也使读者读完之后对自我及他人有所思索。孙方友说:“我不能要求别人怎么看我的作品,或者怎样对我们的作品做什么样的评价,但我清楚我的写作是以人性为基点,表达我对社会的看法的,正是永恒不变的人性将历史与当下联系起来。”[6]因此,读孙方友的小说不仅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新体验,更是对自我存在的深刻反思。
人性分善恶,孙方友也从这两方面展开人物形象的塑造。除前文所述,其他还有对狱卒贺老二(《狱卒》)的肯定,也有对土匪杀害孕妇残忍行为的否定(《血祭》)。在《蚊刑》《鳖厨》等小说里面,孙方友还写出了县太爷、姚二嫂等人难以用善恶来衡量的人性的复杂。
但孙方友更多的时候表现的是一种具有“血性”的人性:刚强果敢、热诚正直、重信践诺、无畏邪恶。这是人性的非常态,却也最深刻地诠释了人性的复杂和伟大。《血灯》中的吴公干小的时候就读书好学,后来因为家境困顿,就主动退学而让家里专供哥哥吴公锦。14岁那年学铁匠,不仅学成了一手好手艺,也养成了勇敢刚强的性格。在陈州,他古道热肠、反对权势,有着很高的威信。后加入同盟会,受革命思想影响,以推翻清朝统治为己任,斗志极高。可就在准备发动起义时,因人告密而致使兄弟二人一起被抓。在敌人审讯时,吴公干没有一丝害怕,痛斥敌人,一意求死。对这种死都不怕的人,敌人想出毒计,让兄弟二人互残,谁先杀掉对方便可活命。在可以活命的机会面前,兄弟俩仰天大笑,共同慨然赴死,“兄弟俩的鲜血交叉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很大的红色‘十’字架”[7]。几千年的儒家道德文化和道家无为思想在塑造出温柔敦厚的国民性格的同时,也禁锢了那种与生俱来的原始血性。我们的文化只有“顺从”而缺乏“反抗”的因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抗”更能代表生命的崇高意旨,是人性的本真追求。即使是求死,也是生命意志的自我实现。就像吴公干兄弟一样,在死亡面前,将那种与生俱来的原始血性痛快地发挥出来,超越了人性的庸常。像吴氏兄弟这样有血性的人在陈州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一群。他们视生命如草芥的血性精神令人振奋之时,不免有一种悲壮沧桑之感。
《血碑》中的土匪方瞎子抗日不是因为民族大义,而是因为日本人侵占了他的地盘。日本人决心要消灭这支土匪队伍,但并非易事:“因为方瞎子打仗极有种,他的弟兄也个个英勇,听见枪声就忘了命。他们又都会些武功,抡起大刀来如同车轮。若是你刺中了他,他临死也要拉响‘飞尸弹’。”所谓“飞尸弹”就是在腰间绑两颗手榴弹,临死前一拉导火索便与敌人同归于尽。有一天,方瞎子与他的弟兄被日军围在一个村子。日军首领藤木让方瞎子走出,没想到土匪们全都走了出来,只是“全部畅怀露腹,个个腰里别着‘飞尸弹’”。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不相干的村民“个个怀里都绑了‘飞尸弹’”。方瞎子在日本兵放走老百姓准备撤离时被一个日本兵抱住:
……“飞尸弹”炸响,一片火光。
日本人的机枪叫了起来,土匪们扭头冲锋,全部倒在血泊里……
这时候,村上的老百姓突然从背后围拢而来,他们冲进日寇群中,毅然拉响了“飞尸弹”……一片火海!
因为这众多村民的壮举,这个村子后改名为“血庄”:
解放后,政府为捐躯的村民们立了一块碑。碑是用白色的大理石制成。每逢这一天,四乡的村民都来祭奠抗日英雄,他们用红水或血水朝碑上泼洒,故称血碑[8]。
孙方友放大和夸张了人性中的那种原始血性,在表达民族情怀与大众理想时,为当下人性的孱弱注入了解救的希望。
不仅仅是男性,即使是那些弱不禁风的女子也常常有一定程度的血性表现。“陈州笔记”系列中的《仙乐青灯》以专写女性为主。《女票》中被绑票的女人在被匪首枪指着头的情况下毫无惧色,一枪未中,竟要求再补一枪。《女保镖》中的柳娘以一介女子身份随人当保镖已属不易,在雇主于公子调戏民女时敢出手打伤于公子更见出其非凡本色。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孙方友总是赋予他们一些更原始的生命力,这也许是孙方友在表现人情道德之余的一种对生命自由自在境界的向往和追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