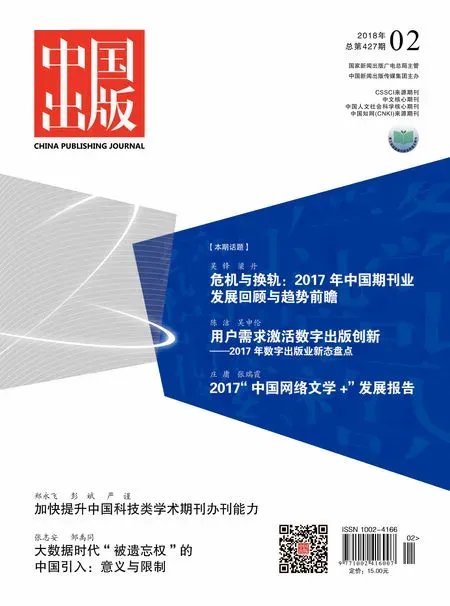死亡与涅槃:电视本体的重构*
——兼与战迪教授商榷
2018-02-08□文│陶冶
□文│陶 冶
大约在21世纪初,美国学术界中电视“死亡论”开始出现萌芽,尽管在当时YouTube还只是一个很难清晰看出盈利模式的新生事物。而当时的中国电视界还在惊叹“超级女声”这样现象级的电视节目横空出世,并对选秀节目和真人秀节目展开补偿性的研究。而到了今天,随着所有卫视广告收入的负增长,中国电视界对“电视死亡论”的认同度却又远高于美国,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认同甚至是带有“恐慌性”和“踩踏性”的。
诚然,这种恐慌有着特定的中国本土背景,例如中国庞大的地市级台面临着垮塌式的经营压力,但是更大程度上恰恰在于,中国电视业的发展历程几乎是将发达国家80年的历史压缩到一半的时间来走,因而频道的扩容与数字化改造在我国成了平行推进的“两条腿”,导致数字有线电视的多频道盈利模式缺乏必要的前期调研。海量的频道出现不仅使得中国观众缺乏准备,更关键的地方还在于美国观众是在广泛接受了海量有线电视频道后面对互联网的,而此二者在中国的共时性发生对中国受众而言恐怕就不仅仅是缺乏准备那么简单的问题了。
也正由于此,《中国出版》对电视的未来展开探讨,毫无疑问,大家对电视未来均持一种理性乐观的态度,并对其如何进行自我演进进行了“画像”。其中,深圳大学战迪教授等所作《仪式感的重建与情感共同体的凝聚:电视文化未来想象》一文多处引用了笔者所译、密歇根大学教授阿曼达·洛茨所著《电视即将被革命》一书的观点,并用以支持其“仪式感的重建与情感共同体的凝聚”的论点,但个别之处有所曲解,故在本文中兼与商榷。
一、能指与所指:无处不在的“电视”
如果今天有人问我们“电视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家里挂在客厅沙发对面墙上的那个黑色的盒子?通过这个盒子我们了解世界,我们投射情感,我们像土豆一样蜷缩在这个盒子对面的沙发里。那么当我们捧着手机或者平板电脑聚精会神地追剧的时候,我们又到底“在看什么”?看手机?看手机上视频客户端里提供给我们的电视剧?不,绝大多数的我们会脱口而出,“我们在看电视”。换言之,“电视”这一指向在语言学意义上已经发生了偏移,“电视”一词的能指与所指已然不再指向同一事物,“看电视”也不再指向统一的行为模式。于是我们只能以逆向研究的方式来层层剥离原有语言学意义上“看电视”究竟在看些什么。此时,我们发现传统“看电视”的行为有两个特定属性即“固定时空”和“线性观看”,因此,基于前者,正如战迪教授在其文中不断强调的“文化的壁炉”“看世界的窗口”等传统电视理论应运而生;而基于后者,电视台的节目编排往往成为了特别具有技术性的工作,以至于传统的电视编播中能够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诞生“标王”。
显然,今天的“电视”,或者说“看电视”这一行为与这两个特定属性发生了彻底的背离。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随时随地看电视即阿曼达·洛茨所谓的“电视无处不在”[1]已经成为了生活中的日常行为。尽管存在着诸多争议,却在努力为“电视无处不在”扫除着最后的障碍。然而,这一技术上的革命不仅仅是从时空概念上解放了电视,更是直接将“电视”从传统电视理论的家庭属性解放出来;也不仅仅使“看电视”裂变成为一种个体行为,更是带来了背后融资模式、盈利模式乃至整个电视经济体系的重构。这些情况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我们不再需要迁就家人的偏好,而被迫与其一同观看自己未必特别想看的节目;我们还可以一边陪家人看着电视,一边用手机或平板电脑看自己真正热爱的节目;我们可以为自己想看的单个节目买单,而不必守在电视机前等候它的到来并被迫观看与之捆绑的广告——传媒经济学中“二次销售”的理论因此被颠覆。
在明确了语言学指向意义上的重构之后,我们反观战迪教授等所作文章,便能清晰地发现,作者依然用传统观念来界定“电视”并使之与“新媒体”对立,而罔顾我们拿着手机“看电视”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以此框定的电视本体在其文中具备了语言学上无可动摇的合法性,从而也就具备了天然的不可解构性,而将“文化的壁炉”与“看世界的窗口”推向极致,于是本来十分日常的行为——看电视——在其笔下成为了一种仪式。另一方面,当我们用其他屏幕“看电视”的时候,“电视”本身也因为这些载体的改变而不断地演化,Netflix制作的电视剧《纸牌屋》,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其实应该是一部“网剧”,而2015年的国产电视剧《蜀山传》也宣告了电视剧发行“先网后台”模式的诞生。电视的本体随着盈利模式的改变而改变,这本来便是一种带有“物尽天择,适者生存”之进化论意义的改变,换言之,今天的电视某种程度上已然成为了这种“自我创造机会”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死守着传统电视而苦苦探寻其出路,恐怕无异于死守着剑齿虎而担心其一旦灭绝虎类将不复存在一样可笑。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预言,传统看电视的方式,在未来有可能会被当作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保护起来,届时其必将更具仪式感。
二、利基与窄播:“高价值内容”生产
极具颠覆性意义的问题也一样出在传统电视上,因为我们国家的频道扩容基本上始于1993年的卫星加密和全国有线电视网的铺设,随着轰轰烈烈的省级卫视上星运动在上世纪末结束,紧随而来的便是全国范围内有线电视数字化的十年时间表,无论是当时的佛山模式、青岛模式抑或是稍晚一点的杭州模式,无不在标榜自己提供了海量信息和频道扩容——这就带来一个副产品——调查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突破2亿户,有线电视数字化程度为80.45%,举行过有线数字电视收视维护费价格听证会的城市中数字电视频道均数为63.89个,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均费为23.53元。[2]这就意味着就有线电视基本层(Basic Package)而言,美国观众只能看到10-12个频道(19.99美元),我国免费有线电视频道数量是美国的5-6倍!免费的60多个频道一起瓜分全国观众的份额,我们恐怕很难再说电视是一个大众传播媒体,或者再称之为广播电视(Broadcasting Television),同样,主持人对着摄像机脱口而出的“广大观众朋友”也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其表述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2014年的尼尔森报告说,“美国的家庭电视现在平均能收到189个电视频道”,但真正常看的,“则平均只有17个频道”,[3]我们相信,中国观众常看的频道数量也应该差不多,因而如何成为每一个人常看的那17个频道就尤为重要了。于是在美国,每一个频道想方设法圈定自己的固定人群就变得无比重要,利基媒介理论的提出使得美国电视频道的细分化建构有了营销学基础,这种理论强调细分市场中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小生境”,以至于自己在这一细分人群中具有统治力。具体的频道所针对的特定人群亦反向建构了频道本身,使得频道的内容生产亦成为“小生境”中不可或缺的生态环,而生物学上的“小生境”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生物在其进化过程中,一般总是与自己相同的物种生活在一起,频道与观众成为了相互指证的彼此。[4]
因此,与传统的广播(Broadcasting)媒体相反,基于利基媒介理论的窄播(Narrowcast)成为了美国电视频道建构的共识。基于利基和窄播,以及我们前述的“电视无处不在”的现实,洛茨提出的“高价值内容”应运而生。由于电视的经济模式发生改变,粉丝愿意为喜欢的内容直接买单,故而“高价值内容”绝然是一种用户的主观判断,比如《小时代》之于郭敬明的粉丝就是无可争议的“高价值内容”,但若其在CCTV-6这样的广播(Broadcasting)平台上播出的话,收视率可想而知。
这种“高价值内容”和利基窄播的特性,用我国“互联网+”的话语来说最为接近的表述应该就是“人格化消费”,但是战迪教授在其文中却将其曲解为“时下流行的《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奔跑吧兄弟》等真人秀节目,一反传统电视文艺高高在上的精英传播观……暗合了当代普罗大众草根意识的觉醒”,[5]殊不知真正“高价值内容”的目标受众根本就不是“普罗大众”——这意味着战迪教授又一次陷入了电视即广播电视(Broadcasting Television)的先验陷阱,并进一步将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这样的真人秀节目视为一种“仪式”。真正的“高价值内容”不在于其高昂的投入与精良的制作,而恰恰在于符合某一特定用户的共享价值观认同,那么这种价值观的细分在我们今天看来应该是电视频道利基化建构的基础,[6]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谓的频道也包括在视频网站上自我设立的“频道”。
三、窗口与壁炉:“仪式”共同体陷落
我们的学术界在思考电视未来的时候其实往往会忽视另一个因素——家电生产商,他们对电视未来的判断或许更基于消费者的直接反馈。毫无疑问,智能手机屏幕的大小在经过十余年的消费者实验后基本确定5~6英寸可以达到用户各项体验的平衡;而平板电脑也基本在7~10英寸之间取得了市场的共识,毕竟尺寸再大的话其便携性将受到考问;而近年来的电视机却在屏幕尺寸上屡屡突破,如果说十年前42~47英寸是主流产品的话,那么目前的55~60英寸的电视机成为了市场主力。由于高清内容(包括4K和高清3D)传输的硬件问题得到解决,观看大尺寸屏幕不再成为一件会带来眩晕的痛苦事,也使得家电生产商意识到进一步拉开与便携式屏幕之间的差距是保留这块屏幕的唯一选择。于是,基于这种趋势我们可以判断家电生产商对传统电视的未来是进一步强调其“固定时空”特征,但是对于“线性观看”却彻底扬弃,尤以乐视TV和小米TV为代表。
家电生产商的所作所为,似乎为战迪教授“仪式论”的观点提供了支撑,但成为仪式的关键不在于屏幕尺寸,而在于仪式的参与者对仪式的认同,就以其热衷举例的《春节联欢晚会》为例,家中的老人以一种仪式感的心态观看,旁边的青少年则触动着手中的另一块屏,看着自己心爱的二次元或是综艺节目,那么此时所显示的收视率代表的又是多少人呢?这种被中国式家长利用家族威权而制造的强制观看行为就是战迪教授所期望重建的仪式?那么这种仪式的可持续性又有多久呢?因此,我们以为在未来,传统看电视的方式下,能够形成所谓“仪式”的只有一种情况——“高价值内容”,正如今天的球迷朋友约三五好友包宾馆熬夜看球一样,那场比赛对他们来说便是“高价值内容”,观看比赛的行为具备了仪式的神圣性,但是“宾馆房间”这个场域又恰恰解构了传统电视理论“家庭性”的根基。
当然,为了进一步捍卫“文化的壁炉”“看世界的窗口”理论,战迪教授还平行地强调了传统观看电视是一种“情感共同体的凝聚”的行为。[7]而在我们看来,“情感共同体的凝聚”与“仪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换言之,没有情感共同体的凝聚,“仪式”只是一种被迫行为。在这个深度垂直细分的碎片化社会结构中,真正能够实现情感共同体凝聚的只有一种东西——价值观。由不同价值观形成的颗粒化微小圈层,每一个小圈层又共享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而彼此之间称为“同好”,为某一特定的“高价值内容”而举行具有仪式感的观看活动。比如几个孩子聚集在一起观看“初音”的演唱会并为这个非人类的偶像痴狂与呐喊,这在这个圈层之外的任何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此时我们不禁要问,哪一个传统的广播电视(Broadcasting Television)频道会播放这一内容?而这又是谁的或者哪家人的“文化壁炉”?凝聚了哪些人的共同情感?显然,破门而入的家长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文化闯入者”,而这几个孩子共享的价值观建构了自己的“门禁社区”。
既然内容是否具有高价值完全基于个人的主观判断,而今天的电视观众不再是“被传播者”,而成为了“内容的选取者”,且不论今天能被称为“现象级”的电视节目或电视剧收视率也不会超过10%的事实——尽管这个数据不真实早已是路人皆知的秘密——就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内容的提取者”能力的不断加强,便已然彻底杜绝了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万人空巷地观看《渴望》这样情景发生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以提取公因式的方式来寻找所有人的“共同价值”或“情感共同体的凝聚”,则未来传统观看电视的行为作为一种“仪式”更加成为“必然”。届时只会是遇到国家重大事件而由各单位组织所有人出现在电视机屏幕前,此时电视不过是仪式的载体,而不是仪式本身。正如家庭影院取代不了电影院的社交功能一样,与“同好”相约观看“高价值内容”成为了社交的需要,而满足了马斯洛的第三需求层次,家庭性的“仪式”共同体在这种功能面前彻底陷落。
四、结语
战迪教授在其文的结尾处做出了“关于电视媒体未来发展的想象基础在于电视在居室中央的位置并未迁移,任何将电视缩小化、移动化、绝对双向互动化的构想都不再是关于电视本体的思考,而是对未来复杂媒体分工的简单化臆测”[8]的呐喊,毕竟我们全文试图重构的电视本体在其看来根本不是电视,而我们驳斥“电视死亡论”的依据恰恰是这种基于本体重构而发生的“涅槃”。但是战迪教授拒斥了我们跳出电视看电视的视角,而将自己牢牢捆绑在沙发上专注于客厅中央的电视,并认为这才是电视的本体,那么我们还是想问,透过这块屏幕,我们在看什么?
相较于美国,我国传统电视受到互联网的挑战更加剧烈,面对互联网视频播出平台的竞争,美国各大电视网的表现令我们中国人特别不解。直到今天,福克斯电视网依然不愿意把《美国偶像》这样的当家节目放到视频点播平台上,美其名曰“保护现场竞赛的纯粹性”,即便有,也至多只是放上前一个星期的节目,而无法像Netflix那样,让观众一口气看一整季的节目。[9]当美国的电视网和有线电视服务商都无法确定具有“内容提取权”的观众,在自家电视机屏幕上播出的内容是什么的时候,中国客厅里的电视屏幕上又在播出什么?
如果说美国传统电视业对版权近乎偏执的保护是美国电视没有被互联网逼上绝境的重要原因,那么版权保护困难重重并造就了“字幕组”这种“非盈利性组织”的中国,显然比美国人更彻底地拥抱着这个互联网时代,也许我们在“共享经济”这一“互联网思维”上走得比美国远得多,也许这使得我们客厅墙上的那个盒子里可以充斥着更多精彩纷呈的内容,那么如果我们这块屏幕上播出内容的全都不是“电视节目”了,我们看的还是电视吗?
如果电视的本体不允许被重新建构,那么传统的电视未来只有一种生存状态——漫无边际播出的线性内容,是一种对陪伴、消遣或娱乐的渴望,换言之,观众的注意力未见得集中在内容上,它可能就是你正在为出门上班做准备的时候播出的晨间谈话节目,也可能是你正在准备晚餐时播出的晚间新闻节目,而这还是凝聚情感共同体的仪式吗?
注释:
[1][美]阿曼达·洛茨著.电视即将被革命[M].陶冶,译.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3
[2]数据源自格兰研究《2015中国机顶盒白皮书》,格兰研究内部数据。
[3]数据来源 :Nielsen Media Research: “Changing Channels: Americans View Just 17 Channels Despite Record Number to Choose From,” 6 May 2014, http://www.nielsen.com/us/en/ newswire/2014/changing-channels-americans-view-just-17-channels-despiterecord-number-to-choose-from.html
[4][6]陶冶.试谈中国电视频道“利基”化建构之可能[J].现代传播,2017(3)
[5][7][8]战迪,李凯山:仪式感的重建与情感共同体的凝聚:电视文化未来想象[J].中国出版,2016(14)
[9]陶冶.直面阻碍的一股无法阻碍的力量——美国电视数字化播出史略[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