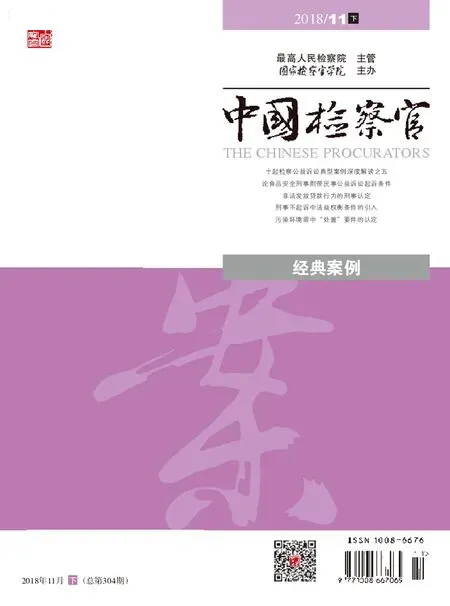累犯条款失效问题研究
2018-02-08文◎王胜*
文◎王 胜*
为了惩戒屡教不改的罪犯,世界各国成文刑法一般均对加重处罚累犯加以规定。我国《刑法》第65条、第66条也设置了一般累犯、特别累犯制度,同时第74条、第81条在刑罚执行上对累犯规定了不适用缓刑、不得假释等限制措施。除了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过失犯罪这二种情形外,累犯条款应当毫无例外地适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所有罪犯。但近年来,累犯条款选择性适用的问题愈发严重,重要原因在于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司法机关为了解决行政与刑事处罚之间的衔接空缺问题,对刑法条文过度诠释,出台了不少将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作为定罪评价标准的司法解释及相关规定,适用的罪名也呈不断扩大态势。尽管刑法理论界对是否将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作为定罪标准长期存在争论,但实务界实际上已经按照“两高”解释来操作定罪事宜。伴随而来的是,一旦将接受过刑事处罚作为定罪标准评价(或升刑格条件),对同时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能否认定为累犯存在争议。否定的观点认为,将刑事前科列为定罪标准评价后,再次以累犯的量刑情节评价,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而众所周知的是,禁止对同一行为重复评价(俗称一事不再理,以下简称禁止重复评价)是最基本的刑法原则,即罪前行为一般是不会成为本罪成立的依据。肯定的观点认为,此种情形如果不认定累犯,则刑法总则的累犯条款在部分具体罪名中名存实亡。事实上,司法机关通过解释的形式终止了立法机关所制定的刑法效力,使得累犯条款失去作用,从而导致部分罪名在某种意义上不再有累犯,严重侵犯了立法权。笔者将当下累犯条款适用所引起的争论归纳总结为“累犯条款失效问题”,主张在反对简单、机械套用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同时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权益。
一、问题的提出
累犯条款失效问题在非法行医罪的认定中表现的最早也最为典型。2008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非法行医解释》)规定,“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应认定为“情节严重”,以非法行医罪定罪处罚。该规定出台之初,便引起理论界的广泛争议,即行政处罚后再次作为刑法评价,是否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反对者认为这显然属重复评价,“行政处罚是一种政府公权力对违法行为的评价,不能再次进行同样是政府公权力的刑法性评价,该规定不存在正当性”。[1]较为流行并被司法实践部门所接受的观点认为,“行政法规与刑法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不同的法律对同一行为不同性质的评价,因此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而且“我国刑法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立法模式决定了刑法与其他法律对同一事实会重复做出评价,但是这个重复评价并未违反刑法中的禁止评价原则”。[2]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实务部门当然要执行,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非法行医刚被刑事处罚后再次 (第四次)非法行医的,能否再次直接入罪?上海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同直接入罪。但也有意见认为,对于曾因非法行医被刑事处罚后再次非法行医的,前面的刑事判决已经生效且执行,在后续刑罚的量刑中可以参照,但不能作为定罪的事实,应按照《非法行医解释》所规定的犯罪标准重新认定。严格来说,第四次非法行医后直接入罪的,实际上对前二次行政处罚又进行了第二次评价,所谓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在非法行医罪认定中已荡然无存。
给司法机关提出的最棘手问题是,对于曾因非法行医被刑事处罚后再次非法行医的,符合《刑法》第65条规定的能否认定累犯并从重处罚?从笔者检索的全国非法行医判决来看,各地做法不一,有直接认定为累犯,也有不再认定为累犯的。其中,细察上海青浦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观点,也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例如,2015年该法院判决生效的纪某某非法行医案中,纪某某于2014年因非法行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满释放后于2015年5月因再次非法行医被抓获,法院以其构成非法行医罪且系累犯从重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9个月。而2016年该法院在王某非法行医案、姚某某非法行医案、薛某某非法行医案判决中,则又纠正了2015年的观点,对有期刑满刚释放再次非法行医的都不再认定为累犯。毫无疑问的是,青浦区法院2016年判决的转变更加符合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但在行政处罚的二次评价上,仍然落入再评价的陷阱。
前述累犯条款适用问题并非局限于非法行医罪,现今较为热门的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及容留卖淫等常见罪名上,司法部门也纷纷将前科劣迹作为刑法条款中“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具体内容。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7项对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留出了一个“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的兜底条款。2014年上海出台《关于本市适用“两高”寻衅滋事刑事案件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工作意见》,对该兜底条款进行了详尽规定,将“因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抢夺、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妨害公务等违法犯罪曾受过刑事处罚,又实施随意殴打他人行为”致一人以上轻微伤的,列为上述“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按照该意见,犯故意杀人罪等暴力犯罪的前科可以被作为寻衅滋事罪的定罪标准使用。如笔者办理的叶某某寻衅滋事案中,2013年叶某某曾因故意伤害罪受过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2017年又在公众场所随意殴打他人致轻微伤,检察院以叶某某构成寻衅滋事罪且系累犯提起公诉,但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前科已评价为由,不再对叶某某认定为累犯,对此检法分歧较大。聚众斗殴罪也有类似规定,2013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 《关于办理聚众斗殴犯罪案件的若干意见》将“因故意杀人、伤害、抢劫、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暴力违法犯罪曾受过刑事处罚,又聚众斗殴的”,直接作为聚众斗殴罪定罪标准。
二、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累犯的观点
前科成为入罪标准后,慎用累犯条款似乎逐渐成为司法实践共识,而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却在盗窃罪累犯认定中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意见。历史上,最高人民法院在盗窃罪认定中对盗窃前科评价、累犯如何认定等问题上始终态度含糊。早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规定,盗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起点,如果是累犯,就可以分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而提高刑格。该规定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反对意见认为,“将刑事前科升刑格处罚后还要按照刑法总则累犯再次加重处罚,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归根究底,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在于其解释内容是否在法律授权范围之内,最高法院的上述解释没有正当性,应当予以废除”。[3]对于量刑升格后是否能继续适用累犯问题,最高法院彼时并未表态,而其近年对前科作为定罪条件后累犯适用问题的态度,让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项规定,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盗窃公私财物的,“数额较大”标准可以按照定罪数额的百分之五十确定。盗窃前科已经被作为定罪标准所使用后,量刑情节上是否还可以以该前科为依据,认定其累犯?否定说认为此为重复评价,不应再认定犯罪嫌疑人是累犯。肯定说认为,应遵循法教义学和立法本意,认定其累犯情节。最高人民法院持肯定说,“本条是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对盗窃‘数额较大’明确的另一个具体认定标准,故对根据本条已构成盗窃罪的行为人,如同时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依法从重处罚,并不存在双重从重问题”。[4]显然,寥寥数语反映出最高法对定罪标准与量刑情节作了区分,认为两者并不重复,而且要求依照刑法总则中累犯规定依法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及观点是否正确、合理,笔者将在后文进行评论。2017年青浦区检察院办理的张某某盗窃案中,就严格依照上述司法观点,认为被告人张某某2017年6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刑满释放后不久即实施盗窃,虽然金额未达(上海市)1千元的“数额较大”标准,但根据有盗窃前科人员数额减半的解释,认定其已构成盗窃罪的同时,认定其已构成累犯,法院也判决认可。但实践中也有不同意见,如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蔡某某盗窃案判决中就不认同最高人民法院观点,直接认为“盗窃前科作为定罪条件后再作为量刑情节,有违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不能再认定为累犯”[5]。
最高人民法院观点也影响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的累犯认定。如,2013年上海出台的 《关于本市办理部分刑事犯罪案件标准的意见》明确,曾因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公文行为被刑事处罚或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或者二年内因上述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再次非法实施该行为的,均定罪处罚。2017年,青浦区检察院在办理李某伪造身份证件案中,认定李某于2016年因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17年再次伪造身份证二张被抓获(上海市规定三张以上定罪处罚),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在盗窃罪中的观点,认定李某曾因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刑事处罚,本次又伪造身份证件,其行为已构成伪造身份证件罪,同时符合累犯条件,从重处罚。法院此后也采纳了公诉机关意见,判决已生效。
三、禁止重复评价与累犯关系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盗窃罪累犯认定问题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但解释的理由是狭隘的。典型的重复评价,包括定罪上的重复评价和量刑上的重复评价。早就有学者指出,“刑法上的禁止重复评价,是指在定罪、量刑时,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予以两次或者两次以上的重复评价”。[6]“重复评价是对犯罪构成事实的重复评价,虽然表面上,禁止重复评价多数会出现在量刑情节上,但必须明确的是,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既是量刑原则,更是定罪原则”。[7]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包含的内容有:“1.禁止将己经被刑法评价的不利定罪情节再次作为定罪情节进行刑法上的评价;2.禁止将己经被刑法评价的不利定罪情节作为量刑情节进行刑法上的评价;3.禁止将己经被刑法评价的不利量刑情节再次作为量刑情节进行刑法上的评价。第一种情形就是定罪上的禁止重复评价,第二和第三种情形就量刑上的禁止重复评价。”[8]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将前科看作数额较大(或情节恶劣)的“另一种具体定罪标准,不涉及到量刑情节,不存在双重从重”,因此不妨碍累犯条款适用的理由,在法理上无法站得住脚。严格来说,前科一旦作为定罪认定后,量刑上的任何评价均是再评价的一种形式。故而,最高人民法院既然已经将前科评价为入罪的标准,入罪后再行进行累犯的量刑考量,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重复评价。
前文所述的累犯适用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归结到一点,就是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能否使得累犯条款失效?笔者认为,累犯条款不能因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而失效,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累犯不仅仅是一种定罪,也是量刑情节,不能顾此失彼。在司法实践中,对有前科的人员,为了强化惩戒屡教不改者的社会效果,无论是再犯或者累犯均应当从重处罚。再犯是酌定从重情节,累犯是法定从重情节,后者的加重幅度要明显高于前者。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而言,累犯是一种特殊的量刑情节。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更是扩大特殊累犯的主体范围,增加了对判处死缓的累犯限制适用减刑及累犯不得适用缓刑、不得适用假释等特殊规定。累犯不仅是定罪、量刑情节,更肩负了从重打击危害性极大的犯罪及指导刑罚如何执行的任务,仅因为累犯是定罪、量刑情节而不适用,系将累犯等同于再犯,与立法原意不符。
第二,累犯是《刑法》总则第65条、第66条所明确定义的法律概念,严格说属于立法解释的权限范围。刑法理论学界始终认为,刑法分则中大量出现以“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作为定罪标准的认定,不应包括行为人犯前表现、犯后态度以及是否为前科、累犯,不能因司法机关作出具体罪名定罪标准的解释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就以刑法总则累犯条款的选择性失效来纠正,否则就侵犯了立法权。
第三,累犯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再评价机制,不能再次机械套用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如在毒品再犯问题上,是否适用累犯就引起过极大争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曾认为既然认定了毒品再犯,就不再适用累犯。但对累犯不适用引起很多不利的处罚后果,如丧失了缓刑、假释等刑罚执行限制等等。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转变态度,明确对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从重处罚。另外,作为定罪中的犯罪构成要素,显然在量刑中不能完全排斥重复评价。所有以行政处罚或前科作为定罪标准的罪名,都存在认定过程中使用了已评价的前科劣迹情节,而后又为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主动回避的问题,此观点前后矛盾,逻辑也不能自洽。
第四,禁止重复评价原则适用应当统一、规范。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现代刑法意义上的累犯,更多地强调犯罪人的人身特征,累犯是一种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特殊犯罪类型。首先,将前科劣迹作为定罪标准,主要是将行为人再犯时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纳入评价内容,并非再次评价前行为。其次,将前科作为定罪的因素,处罚的是现行行为,而非前科行为和累犯的前行为,不会造成二次处罚,也与重复评价无关。最后,如果仅仅因“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而导致累犯条款从常见罪名中彻底失效了,这也意味着此类案件不再有累犯,实属荒谬至极。
四、结语
因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理论研究上的薄弱及受最高人民法院观点的影响,司法实务中累犯条款选择性失效问题愈发严重,极大影响了刑事司法的权威性、公平性。司法机关为了社会稳定的需要,随意在司法解释中运用法律拟制,把前科劣迹作为定罪标准,造成司法权的肆意扩张,不利于对犯罪人权益的保障,进而导致刑罚权的滥用。笔者认为,考虑到累犯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重复评价机制,刑法总则中所建立的累犯制度除了法律的特殊规定外,应当适用于所有罪名。司法机关通过解释的形式将前科劣迹纳入“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定罪标准,实则对过去已经被刑事法律评价的行为再次进行刑事评价,侵犯了立法权,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应当逐步取消并禁止。
注释:
[1]吴婉璐:《行政处罚事实作为非法行医定罪条件的正当性研究》,载《铁道警察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2]李高宁:《禁止重复评价在刑行交叉案件中的适用》,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3]胡乾辉、明新春:《盗窃犯罪累犯不宜加重处罚》,载《人民司法》2006 年 4 月(上)。
[4]胡云腾、周加海、周海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15期。
[5]肖福林:《前科作为定罪条件后不能再作为量刑情节》,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2期。
[6]于志刚:《刑法总则的扩张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
[7]周光权:《论量刑上的禁止不利评价原则》,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1期。
[8]谭轶城:《论刑法评价中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