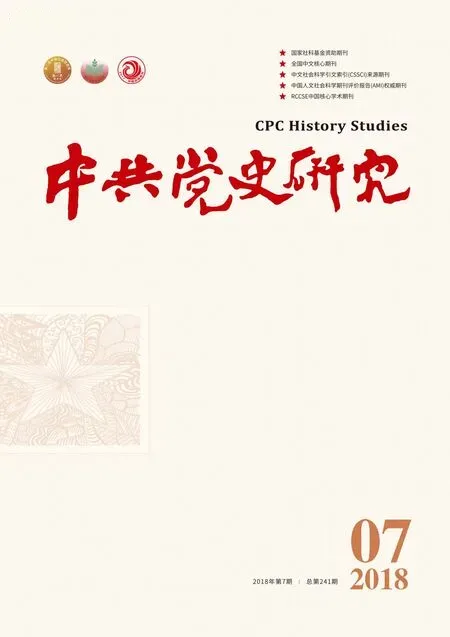对中共六大的再思考
——基于理论视角和档案文献的考察
2018-02-07李佳金
李 佳 金
1928年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一次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条件下召开的重要会议。现有研究范围已经比较全面,譬如开会地点、代表人数的考证,还有相关人物研究等;对于中共六大的评价也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结论;每逢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也都会掀起新一轮的研究热潮。总体来说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如何评价中共六大的不足,始终是中共六大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研究焦点又聚集在“指导机关工人化”和“乡村中心”道路,以及中间阶级政策、富农政策等问题上。本文尝试通过研究近年出版的档案材料并从理论演进的视角,说明中共六大的观点也是诸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对中共六大作出客观的评价。
一、中共自身对六大的评价演变及其历史情境
中共对六大的评价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中共自身对六大的评价*关于中共历史上对中共六大评价的研究,参见杨德山:《中共六大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以中共自身认识史为角度的考察》,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等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研究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最早见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批判“立三路线”的同时对中共六大作出评价:“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并未肃清,六次大会后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之不正确的分析,联合富农及在黄色工会中的错误策略,对改组派的不正确的估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对六大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而且将中共六大和“立三路线”联系在一起,将中共六大的错误定为路线错误。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对六大的批评,特别是“联合富农”这点,并不符合六大的史实。中共六大没有照搬俄国革命公式,相反,认为俄国解决土地问题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并主张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富农政策。在《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这里有一个细节,中共六大农民土地问题报告的起草者可能并非李立三,而是另有其人。李立三在《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中说:“决议草案是由外国同志用外文书写的,其中含有很复杂的东西。翻译的也不是很好,所以有许多地方可能同志们难于理解。”这表明中共六大土地报告并非李立三所写。具体由何人所写,仍有待考证。不过可能是布哈林所写,或者是布哈林的译稿。根据为:首先,布哈林在苏共党内对列宁主义的诠释比较灵活,相比于理论公式,他更加重视列宁策略上的灵活性。如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一文中,布哈林在强调列宁主义的灵活性时说:“再也没有什么比把列宁主义变成教条更使列宁讨厌的事了”。参见《布哈林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第154、155页。其次,布哈林在富农问题上比较宽容,他在1925年《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口号,提出应当重视农民经济发展速度。因此,中共六大农民土地问题报告的起草者有可能是布哈林。中,李立三在讨论中国土地关系的发展前景时说:“我们不能根据耕种土地的数量来划分富农和贫农,因为在中国,土地质量大不相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416页。这样一来,俄国经验中的地主、贫农、富农划分标准就不适用了。李立三强调了中俄两国土地问题的差别:“在俄国,这种斗争采取了小农反对地主的形式。在俄国,富农是自由农民,是资本主义分子……因而在俄国,这个过程是以小土地占有者反对大封建土地占有者的斗争形式进行的。而在中国,是存在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反对土地垄断者,反对垄断性的土地占有者阶级的斗争形式。”*《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第421页。因此李立三说,俄国的革命道路在中国“很难行得通”*中共中央在1926年到1928年的文件中,也很少使用“富农”这一概念,而一般用“小地主”代替,或将“富农”“小地主”并用。在1928年中共中央致江西省委信中,即直言“自耕农问题即你们所谓的富农问题”。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说明中共当时对于“富农”概念尚缺乏明确界定,往往与自耕农、小地主相混淆。。李立三主张在中国针对南北方提出两种不同的富农政策:“南方富农已转到反革命方面,而北方富农还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那么对待富农中的反革命部分,我们当然应该进行斗争,而对待支持革命的部分,也就是还同中农和贫农一起行动的那一部分,我们应该坚持统一战线”。李立三甚至对列宁的革命公式提出质疑:“这与列宁提出的论点有所不同……但我们不能按照刻板公式提出不能同富农搞统一战线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第424页。可以看出,中共六大在对待富农政策上,并不是像六届四中全会所说的那样“联合富农”*对于中共六大“联合富农”的批评最早见于1926年6月7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信。,而是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不同政策的。
中共对六大的评价在延安时期发生转变,形成了一分为二、以肯定为主的评价,这得益于周恩来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毛泽东的《学习和时局》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对中共六大作了深刻的评价:“‘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对于中共六大的不足,周恩来总结了几点:“一、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二、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没有把策略观点着重放在争取中间阶级上。三、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没有重视农村工作与建党工作,虽然当时还不可能产生乡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四、没有更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武装的重要,以武装建党、建政、做群众工作。”周恩来研究中共六大有合乎实际的历史眼光,对于其功绩给予了肯定,对于其不足也能持较宽容的态度,指出“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对于之后的“立三路线”也“不能负直接责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5页。尤其是在中共六大受批评最多的乡村中心问题上,周恩来给予历史主义的理解:“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77页。总体来说,周恩来的评价在两方面具有意义。首先是形成了正面评价为主、一分为二的评价方法,此后中共对六大作过多次评价,虽然不同时期在具体内容上有所调整,但大框架和结论基本延续了周恩来的研究。其次是周恩来强调对于中共六大的不足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即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理论水平,这对于宽容看待历史是有深远价值的。
1944年4月毛泽东《学习和时局》的讲话,以及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共六大的评价与周恩来的评价基本相同,但在一些细节上有所差异。首先,对中共六大成就的肯定与周恩来的评价是一致的,如毛泽东认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这些都是正确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9页。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的讲话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中共六大的不足集中到几个问题上进行言说,如“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8页。等,而对于周恩来所重点关注的“指导机关工人化”和知识分子干部问题,以及工运政策、对其他党派政策等,都没有提及。此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评价,毛泽东与周恩来有所不同,例如对于中共六大提出的十大纲领,毛泽东持肯定意见,但周恩来认为在没收外国资本、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等问题上,“作为策略任务来看,有些就不妥当”*《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62页。,相较更加务实。
总体来说,《学习和时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评价方法和基本结论上与周恩来的研究是一致的,但从篇幅上看,周恩来近两万字的研究更加全面,在具体问题上也说得更详细。以这三份文件为基础,对中共六大的评价基本定型。
近40年来,随着学术研究不断走向客观公正,以及新材料的运用,对中共六大的研究也有了长足进展。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以及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以下简称“《一卷》”)是代表之作。《七十年》对于中共六大成就的评价没有太大变化,对其不足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乡村道路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问题上。但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点,第一是它增加了对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批评;第二是它对中共六大的不足也抱有历史主义的宽容态度,指出“中国共产党处于历史大变动的年代,面对着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要在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初期就对所有这些问题一下子作出准确的判断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7—88页。。《一卷》在研究视野上有所放宽,关注了中共六大的筹备过程、共产国际派驻代表制的改变,以及留守中央的工作等。此外,一些结论的更新也反映了学术研究的进步,例如《一卷》对中共六大的富农政策予以基本肯定,认为六大能够“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332页。,而此前的几次评价都没有提出富农政策问题,周恩来也只是说对“富农没有进一步分析”*《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65页。,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再如对于中共六大的不足之处,《一卷》认为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尤其是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应该负主要责任,这是之前几次评价中所没有的,这和中共党史研究中对斯大林、共产国际的评价转变有关。相比于延安时期中共对六大的评价,《七十年》和《一卷》都特别关注了“指导机关工人化”问题,但这两部书的具体指向有细微差别。《七十年》更关注中共六大干部选拔中的工人化倾向,而《一卷》则增加了对普通党员成分的关注,尤其重点强调了要在“不断扩大群众基础”的同时“解决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336页。。
应该看到,不同时代作出的结论,是带有当时历史特点的。例如,周恩来在评价中共六大的土地政策时认为:“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要经过一个长期摸索过程的,而且要有许多具体的办法,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就是很好的办法。如果根据‘六大’的原则,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只分给贫苦的农民,那就必然发展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或驱逐地主出苏区。这样对斗争是不利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81页。周恩来认为中共六大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偏于激进,但应该看到,1944年是中共在延安探索“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时候,此时中共对地主的政策是党史上比较特殊的宽容时期。而作为反封建任务的基本内涵,没收地主土地是中共的既定政策。此后学界对中共六大的土地政策进行评价时,也不再对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进行批评。
此外,对“指导机关工人化”的批评显示出双重指向。周恩来的研究、《七十年》对这一问题的批评,主要指向是党的干部队伍问题。周恩来认为它容易造成“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互对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80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延安时期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磨合过程的反映,如丁玲所写的“骑马的首长”和“艺术家的首长”问题。而《七十年》对“指导机关工人化”问题提出批评的背景是,1980年邓小平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时提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98页。,对知识分子干部逐渐重用。事实上,中共六大除强调“指导机关工人化”以外,同时还强调普通党员成分的工人化,这一问题直到2002年出版的《一卷》才予以重点关注:“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后,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此基础上,《一卷》更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在“不断扩大群众基础”的同时“解决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335、336页。对这一命题的言说,体现了进入新世纪后中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入党与保持党的先进性关系的思考。
总之,中共自身对六大的几次评价不断向客观、宽容的方向进步,同时也不断开辟着新的研究焦点,如中共六大的筹备过程等。但应该看到,不同时期中共对六大的评价,往往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许多结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周恩来所说,“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58页。,意识到既有结论的时代背景,有助于避免在研究中共六大的过程中固守旧论、“苛求于前人”*不苛求于前人的说法,参见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
二、“指导机关工人化”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探源
“指导机关工人化”和轻视知识分子是中共六大受到批评的主要问题之一。最早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认为:“关于领导机关工人化的问题,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79—80页。《七十年》和《一卷》都谈到了这一问题。2008年,在纪念中共六大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也有学者认为中共六大“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工人化’”*刘学礼:《纪念中共六大召开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对于这一问题需要历史地看待:党的干部队伍从建党初期强调知识分子化到中共六大上“指导机关工人化”的显著变化,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小资产阶级理论的调整有关,而中共六大对工人成分的强调是对这一变化的反映。
中共在建党初期一度强调要从学生中选拔党的干部。1923年7月,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施存统发表《中国的青年运动究竟应该怎样?》一文,强调“未来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服务的人才,须从现在的学生中养成”,将学生作为党的干部队伍的重点培养对象。施存统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微弱,对无产阶级“组织和教育的工作,非籍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来担任和非靠他们帮助不可……无论在掌握政权、运用政权、发达产业、普及思想上……大部分必由现在学生中造成”*存统:《中国的青年运动究竟应该怎样?》,《先驱》第22号,1923年7月1日。。施存统提倡的中共干部队伍知识分子化,是当时中共思想的一种反映,它建立在对工人阶级发展不成熟的判断基础上,主张知识分子应承担组织、教育工人的任务。
1928年之前历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五大时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知识分子占据多数,工人家庭出身或者工人职业的委员比例并不高。例如,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9名执行委员中,有火车司机出身的朱少连、铁路钳工出身的王荷波2人;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10名委员中,项英有纺织厂学徒的经历(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六人,也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7—36页。。总体来看,1928年前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知识分子占主体,工人出身的中执委委员(或政治局常委)比例不高。
但1928年中共六大上提出“指导机关工人化”,并对知识分子干部提出批评。据周恩来回忆,中共六大召开时,“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82页。。在基层,工人对于知识分子干部也表现出不满情绪。如中共六大在讨论政治报告时,满洲的工人代表唐宏经说,知识分子干部“天天穿好的,食好的,过贵族官僚生活”,“工人与他开会时还要穿好的衣服,否则与他不配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555页。。又如大会代表陈海清在讨论政治报告时与人发生争吵,“知识分子他总会说漂亮话的,把事实辩得一点也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第569页。。再如大会代表胡建三在讨论政治报告时说:“机会主义不是发生于工农阶级中。中国以前的中央委员,多半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中国机会主义的深远的社会根源。”*《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第504页。
从无产阶级的组织者、教育者,到中共六大时受到上下层一致的批评,知识分子在中共革命话语中地位明显下降(需要说明的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小资产阶级”概念内涵的解释,向来是囊括知识分子的,因此这里将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表述)。对于这种变化的原因,观念史研究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与“小资产阶级”词汇从一种“针对外部世界的社会分析概念”转变为“针对内心世界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有关*李志毓:《中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1924—1928)》,《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小资产阶级理论的调整有关。1927年中共五大提出“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7页。,并将国民党武汉临时政府当作这一政权的雏形。“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理论的一个重要预设,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关系将维持至民主革命结束。例如,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当时认为,“现时革命的国民政府就包含着民权独裁制的原素”,并认为“汪精卫同志亦曾到会……小资产阶级必与无产阶级同向社会主义的方面前进”*《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338页。,将汪精卫看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独裁”中的小资产阶级。而且,罗易认为小资产阶级将支持中共的革命主张,“小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力量”,“愿意和无产阶级一起走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60页。。但中共五大关于小资产阶级将支持中共的理论,在汪精卫“分共”后陷入被动: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小资产阶级就已经反共。为了解释这一理论悖论,共产国际作出调整:不再统一表述小资产阶级概念,而是将小资产阶级一分为二,把汪精卫解释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将传统意义上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主体*这涉及另外一个理论问题,即自中共二大起,“工农小资产阶级”表述中的“农”一般都指代贫苦农民,而非列宁意义上的“整体农民”。这是中共早期阶级分析方法形成过程中对“工农专政”的误读。因此,“工农”概念中的“农”在不是指小资产阶级时,“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表述才能成立。。1927年7月,斯大林在《时事问题简评》中提出了革命“三阶段”理论,划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界线: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的同盟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第二阶段,同盟变成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三阶段,无产阶级的同盟只剩下农民和城市贫民,认为汪精卫的“分共”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日益发展的土地革命的恐惧”*《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65页。。
受这一理论变动的影响,中共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组合概念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并成为一个专指动摇者、背叛者的负面词汇,如1933年《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中提到,“在革命中将有更多的困难,和更多的叛徒与变节。而变节中的大多数正是那些混在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譬如“自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之武汉时期被拉进工人运动里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1页。可见1927年小资产阶级理论调整的长期影响。处于这段历史时期中的中共六大也不能摆脱这一反智的理论背景*1927年苏共内部党争对这一理论调整起到了“倒逼”的作用。托洛茨基提出应该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斯大林关于武汉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分析,认为“‘武汉的国民党’根本就不是革命的国民党”。参见〔俄〕托洛茨基著,施用勤译:《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7页。托洛茨基还同季诺维也夫上书联共中央,在工会大厦公开批评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上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斯大林以列宁继承者的身份,主张“工农民主专政”,与托洛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抗,只能将汪精卫的“分共”解释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更加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源流尤其是列宁那里,“对知识分子的指责与嘲讽远远超过肯定与赞扬”*杨凤城:《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述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这或许构成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对知识分子态度的理论底色。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最早的辩论中,马尔托夫曾主张一种相对松散的党组织形式:凡是在党的某一组织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每一个党组织都有权承认凡是在它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是党员。列宁批评马尔托夫这样宽松的政策会“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列宁将马尔托夫论点的思想源头归结为知识分子自由散漫的天性,“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的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而列宁主张“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2、471页。从传播史的角度尚未看到列宁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对中共造成的直接影响,但召开于莫斯科、由斯大林和布哈林亲自指导的中共六大所具有的列宁理论底色是毋庸置疑的。
总之,从工人的组织者、教育者,到“混在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形象在早期中共认识中发生了比较显著的改变,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小资产阶级理论的调整是这一改变过程的重要节点。中共六大对知识分子干部的批判、对干部工人成分的强调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被动体现。
三、中共六大不可能产生“乡村中心”观点
没有认识到“乡村中心”的革命道路,是中共六大评价中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如1944年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认为,中共六大“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9页。。后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都有所提及。现有研究也基本认为中共六大主张城市中心,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地位缺乏必要的正确认识。
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乡村道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革命以城市还是以乡村为中心,而且涉及党的农民化与先锋队作用等诸多理论问题。近年出版的有关中共六大的档案显示,中共六大批判乡村道路主要是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进行的。从理论层面来说,乡村道路不符合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建党理论,这表现在很多人都担忧的“农民党”问题上;从实际层面来看,当时的“乡村中心”道路,和后来中共带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并不一样,它在土地改革等方面未能发挥作用,反而因为游击和暴动损害了中共在农民群众中的形象。这二者是中共六大批判乡村道路的真正指向,也是“乡村中心”观念不能产生的原因。
从建党理论方面来看,对农民的大量吸收有可能使中共变成农民党,这不符合列宁建党理论中职业革命化目标以及党和阶级分开的原则。布哈林在大会报告中提到:“想另找一个某种特别的革命阶级作党的基础,就是离开无产阶级而走向农民方面去”,“发生一种意见,以为党内农民的代表应当比无产阶级代表多一点,因为农民比工人更革命些”,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都是有害的倾向”*《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第251、252页。。项英在讨论政治报告时说:“在目前时期,工人还处于低落的情绪中,而农民运动却在不断高涨,我们无疑面临着工人党变成农民党的危险。”*《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第518页。周恩来也对“游击战争充分表现农民意识,到处烧毁城市”*《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第621页。表示担忧。中共六大召开时的党员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全国党员共130194人,其中农民为99830人,占76.6%*《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第214页。。虽然周恩来在组织报告中说这个数字是“没有法子保证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第402页。,但这个数字起码可以说明中共在农民中取得了巨大发展。
在列宁的建党理论中,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成为先锋队去领导大众,而不能沦为群众的尾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党的职业革命化。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依靠“那些丝毫不能‘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工人”,而应该依靠“聪明人”,即“需要有职业革命家”*《列宁选集》第1卷,第391页。。党要职业革命化,要少而精,阶级虽然要团结在党的周围,却不能成为党,这是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所作的进一步说明。而中共六大前出现的“农民化”问题,因为混淆了党和阶级的差别正中其矢。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中共六大的《农民运动决议案》力图去农民化,并在《决议案》最后用着重号强调:“过去以党代替农协代替苏维埃以容纳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倾向,应极力纠正。党只能经过党团的作用影响农协和苏维埃”*《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第881页。。中共六大对党的农民化趋势的纠正,表明这一时期中共力图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将党和阶级分开,重新强调党的职业革命化和先锋队作用。当然,中共六大这一认识是有时代局限的。后来周恩来在总结延安时期的建党经验时说:“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77页。即农民化并不构成妨碍党的无产阶级化的充分条件,这种认识是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在1928年很难有这样的认识。
除建党理论的因素之外,乡村革命未能与土地革命结合,是中共六大批评乡村道路的实际原因。土地革命是列宁民主革命理论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共产国际执委会从1926年末第七次扩大全会到1928年2月第九次扩大全会,也始终在强调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布哈林在中共六大的报告中也将土地革命定为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目前的两大任务”*《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第235页。。
但中共这一时期的乡村革命,大多由暴动转入游击,很少能发展到土地革命。192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南、湖北省委,谈及农村革命时指示:“在乡村中大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东西”;而谈及如何进行土地革命时,则指示:“积极发展土地革命,目前主要的争斗方法为实行与扩大游击战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22、525—526页。基层虽然能够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但难以改变。1927年11月26日湖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认为这一时期“农村之游击战争形成很多错误,汉阳在城市组织工人去乡村行动,所以结果流为流寇之行动,这种以此地之人去杀彼地之土劣且抢劫,结果只有使农民认为土匪之行动”*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32年)》(乙种本),1985年,第4页。。1927年9月江苏省委制定的农运计划中,提到“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但是在制定的具体计划中,并没有涉及土地所有权的变更,而是将主要工作放在减租、暴动上。同时又强调,“某个区域暴动失败后,当设法保持所有的武装潜伏本地或转至他处作游击式的扰乱”*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6月—12月)》(省委文件),1984年,第94页。。192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在答复江苏省委关于乡村暴动的问题时,亦曾总结近期的农运情况:“乡村斗争虽曾经过宜兴无锡常州的先后暴动,然因为发动以后形成了军事投机局势,以致一经失败便溃散无余,土地革命始终未能深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45页。这说明至少在江苏、两湖地区,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式是游击战争。由于1928年年初中共中央已在考虑召开六大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4页。,这种现象短期内没有发生变化。
基层农运参与者的描述更为直接。如中共六大河南代表李鸣在大会上的发言,基本能够呈现当时基层农民运动的样貌。“农军数十人及五六百农民一齐到刘店东李广化之女婿家,把他的东西拿分了,房屋烧掉了。”但除此之外,对于“土地问题,亦未曾注意”。他最后自白道:“此时我们对于民众并没加以注意,以游击战争而竟当作暴动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第806、809、807页。两湖地区情况也基本相同。湖北代表任旭在讨论政治报告时说:“国共分家后,农民认为没收土地不可能,杀豪绅地主,为群众接受。”*《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第588页。直隶的代表王子清说:“北方的抢烧杀比南方更甚……房子是烧掉了几十个村庄,十几里路之外都可以望到黑烟。”*《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第701页。当然,能够推行土地改革的例子也有,比如湖南醴陵,在地主田产上实行了“共耕”制度*“共耕”是一种十几人共同耕种地主的田产,分享耕牛、农具等的制度。参见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31年)》(乙种本),1984年,第69页。,但笔者目之所及,大部分其他地区还是以游击暴动为主。可见,当时农民运动的方式,离土地革命相去甚远,而且游击式的暴动除陷入“盲动主义”之外,还正中“军事投机”的概念,在理论上很难获得认可,在实践中也会产生负面作用。
总之,从当时的理论状态和乡村革命实际两方面来看,中共六大很难提出“乡村中心”道路。在建党理论方面,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担心对农民的大量吸收可能导致党的农民化,进而影响党的职业革命化和先锋队角色。从实际来看,后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与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时的乡村革命是不同的。如果说后来中共通过土改所实现的政治动员、经济资源是走向胜利的关键,那么1928年前后的乡村运动,正如中共自身认识到的,“目前主要的争斗方法为实行与扩大游击战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25—526页。,在游击式的暴动过程中,土地革命难以实现,有些地方甚至让农民误以为是土匪而逃入山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第540页。。因此,中共六大并不是批判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乡村革命,而是批判盲动、游击主义和烧杀抢掠,这对于当时的中共来说确实是切肤之弊。中共对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索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很难预料十年内中共的城市工作会遭遇挫折,转而在乡村革命中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用后来成功的经验要求中共六大,是有失公允的。
四、结 论
中共六大距今已90年,各方面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每个时代对中共六大的评价都有当时的历史情境,在研究中意识到这些结论的时代性,不完全受其限制,是客观评价中共六大的前提。从成就方面看,中共六大是中共从1927年4月开始的理论混乱之后首次进行的全面整理,它厘清了革命性质、革命形势和策略等诸多复杂的问题,是中共列宁主义化、布尔什维克化的一个里程碑。对于中共六大的不足,通过考察当时的理论状态、革命实际情况会发现,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小资产阶级理论的调整,是知识分子在中共的革命话语中从无产阶级组织者、教育者到变节者形象转变的重要节点,而这一转变过程在中共六大上的体现,就是对知识分子干部的批评和“指导机关工人化”口号的提出。此外,中共的“乡村中心”道路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以1928年前后中共在建党理论上的认识,不可能像延安时期那样认识到农民也能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当时只能将党员成分农民化看成是需要纠正的错误。加之这一时期的乡村革命,往往经暴动转入游击,理论上强调的土地革命很少能够实行,因此中共六大很难产生“乡村中心”的思想。
中共六大既是历史的主动改造者,也是历史进程的被动体现者。它在革命性质、形势、策略等理论问题上廓清了一系列模糊的认识,这是其功绩。但在党员干部工人化以及乡村道路等问题上,中共六大以当时的理论状态和实际情况很难作出改变,它只是宏观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小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六大是被动的。在这些问题上应该宽容一些,避免造成对中共六大的“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