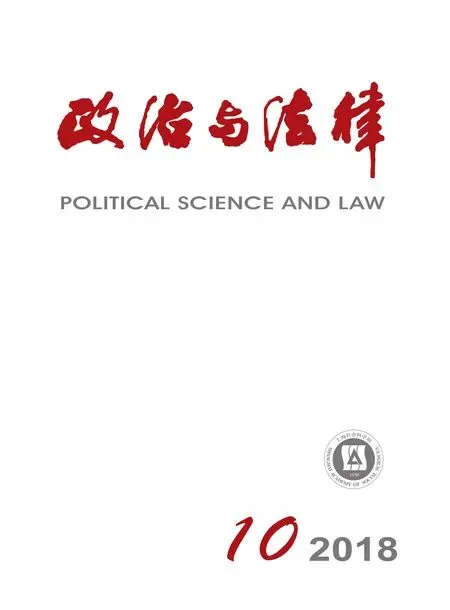故意概念的再定位*
——中国语境下“盖然性说”的展开
2018-02-07李世阳
李世阳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08)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了故意犯罪的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一般认为所谓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①张明楷:《刑法学(上)》(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51页。从这一定义出发,一般认为故意由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组成,并且“知”与“欲”这两个因素必须同时存在,才能证明故意的成立。此外,根据意志因素的强弱,研究者将故意区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然而,故意归根结底是作为犯罪成立的主观要件,一方面,在认定故意时,“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现实地摆在司法实务人员面前;另一方面,在解释学上,围绕故意的本质,形成了认识说与意志说这两大学说阵营的争论。此外,伴随着德国与日本刑法解释学被大量介绍到我国,其对我国传统的刑法知识体系产生强烈冲击,甚至已经融入我国刑法理论,成为我国刑法解释学的主体内容。在故意认定的问题上,德国与日本固然存在诸多学说,然而,这些学说的基本构造与基础是什么,其在司法实务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值得追问。对于司法实务而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已经合法获得的证据认定故意的存在,对于学说而言,核心的问题则在于对故意的成立要件进行定义。那么,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故意的认定,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在逻辑上具有怎样的关联性。在学理上所确立的故意概念对于司法实践在认定故意时能否提供一个具有操作性的定义,或者说实体意义上的故意概念是否已经融合了程序上的考虑因素。对此,需要以故意概念的发展历史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对各项理论主张进行检验,发现其中的问题,提出对故意认定的判断结构。
一、间接故意概念的产生
(一)卡普佐夫创立间接故意概念
在结果加重犯这一概念产生之前,德国刑法学的奠基人卡普佐夫(Carpzov)针对杀人故意提出了一个具有实务价值的问题:对于以高度危险的方式攻击他人者,如果他并非以杀人为目的,但是却又因该行为的危险性造成了被害人死亡时,是否能够以故意杀人论处?对于该问题,卡普佐夫将故意杀人区分为直接与间接意志两种类型,而不论哪一种类型,行为人的意志趋向都是朝着杀害他人的方向迈进(in actum homicidii),据此,卡普佐夫认为两者都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这里所谓的“间接”的方式,是指在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在未有其他外在因素介入的条件下,因行为而径直导致这一死亡结果,这是一种间接而且是透过事件的流程(indirecte er per accidens)所确定的意志。②参见Benedict Carpzov,Practicae novae imperialis saxonicae rerum criminalium parsⅠ,uebersetzt von Oehler,2000,Qu.1.Mr,28,S.31f。转引自徐育安:《故意认定之理论与实务——以杀人与伤害故意之区分难题为核心》,《“中研院”法学期刊》(台北)2013年第10期,第87页以下。据此,间接故意概念得以诞生,从这一论述来看,间接故意的概念着眼于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在此因果流程中介入了其他重要因素,否则当伤害行为本身直接导致死亡结果发生时,就可将死亡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即由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支配了这一因果流程。这样的话,间接故意就获得与直接故意同等的地位,一方面减少证明达到直接故意之程度的困难性,另一方面开启了故意的客观化之先河,同时也建构了主观归属论的基本结构。
(二)来自费尔巴哈的批判
间接故意这一概念遭到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的强烈反对。他认为,故意的成立必须是以具有实现犯罪结果之目的为前提,而这一点正是间接故意案例所欠缺的,在此种案例类型中,行为人在进行一项故意的犯罪行为时,对于此行为附带造成的重大结果,事前有所预见或者有预见的可能性,行为人对于其行为部分具有故意,而对后者之结果部分则有过失。据此,费尔巴哈将这种责任形态称为被故意所决定的过失(durch dolus bestimmte culpa),与故意及过失相并列,成为第三种责任形态。③参见[日]内田浩:《结果加重犯的构造》,信山社2005年日文版,第75页以下。由此可见,费尔巴哈反对理由的出发点是将故意严格限定在直接故意之上,间接故意归根结底是被故意行为所决定的过失,据此当然会得出废弃间接故意概念的结论。不过,从上述理由来看,费尔巴哈另辟蹊径,为结果加重犯这一概念搭建了基本的框架,即“故意的基本犯+过失致人死亡”。然而,应当如何证明这种与主观意志紧密关联的故意之存在,成为一大难题,对于该问题的解决,费尔巴哈又转而主张对故意进行推定。具体而言,要判断什么种类的责任(Verschulden)存在于杀人的基础之中,行为本身的性质,尤其是被使用的武器之性质、伤害的性质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问题。在怀着某种目的而实行的行为在一般经验上应当直接且必然地引起死亡的情形中,就容易推定杀人的意图。与此相对,如果侵害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关系是不同的、间接的或者偶然的,与此相比,非意图杀人的理由就比较充分。④参见[德]安塞尔姆·里特尔·冯·费尔巴哈:《德国刑法教科书(第14版)》,徐久生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以下。
(三)小结
由此可见,故意这一概念本来是被限定于“积极希望结果发生”这一意义上使用的,而这种主观意志态度在很多情况下只能通过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承认才能被证明。这与中世纪的欧洲所普遍采用的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是相吻合的。在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之下,被告人沦为诉讼客体,成为刑讯的对象,刑讯成为一种合法的暴行。⑤参见[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以下。然而,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人权保障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反映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人权保障观念导致了刑事诉讼的理念与构造产生根本性变革,被告人不再被纯粹作为诉讼客体、被纠问的对象,获得了作为当事人的地位,在未经最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因此,被告人不再负有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相反,作为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官承担通过法定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在此背景下,如果继续将故意理解为积极追求某种结果发生的主观意志或态度的话,一方面,故意的成立范围将过于狭隘,另一方面,故意的认定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被告人可以轻易地否定自己不追求结果的发生。
然而,即使是否定间接故意概念的费尔巴哈,在故意的认定上,也不得不采用推定的方式,这本身足以表明费尔巴哈对于间接故意概念的批判以失败告终。间接故意作为故意的一种形态,已经获得普遍承认,与此同时,也开启了故意的客观化进程。反映在实体法上,故意在犯罪论体系上的地位也发生了转变,可以说这一转变过程就是一部犯罪论体系的演变史。⑥参见付立庆:《主观违法要素理论——以目的犯为中心的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以下。基于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功能与故意规制功能,一般认为在构成要件阶段就必须判断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存在构成要件故意,这里的故意仅仅停留于对于行为、结果、因果关系、行为状况等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当具备这种认识时,就能够推定构成要件故意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当存在为违法性提供基础的事实的认识时,就能推定责任故意的存在,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故意概念。当然,这种推定是一种可被推翻的推定,当行为人主观上的认识与客观上发生的事实并不一致即发生认识错误时,是否还可以将客观存在的事实归属于行为人的认识,值得讨论。
此外,我国《刑法》第15条规定了过于自信的过失与疏忽大意的过失,根据认识的有无,前者是一种有认识的过失,而后者是一种无认识的过失。从间接故意的概念产生以来,这一概念与有认识的过失之间的区分就成为认定故意时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在故意的认定上,自其产生以来一直存在认识说与意志说的对立,这两种学说又产生出诸多理论变种。
二、意志说及其理论变种
意志说是指,在认识的基础上或者在行为人的认识程度较低的情形中,作为填补其不足部分的要素是容忍结果发生,更精确地说,有必要伴随着以“积极的意欲”或者“消极的容忍”这一形态肯定结果发生的感情因素。⑦参见[日]杉本一敏:《故意应当在什么程度上被客观化》,载高桥则夫、杉本一敏、仲道祐树:《理论刑法学入门——刑法理论的玩味之处》,日本评论社2014年日文版,第161页以下。如果将故意仅仅限定于直接故意,意志说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但如前所述,间接故意已经成为与直接故意相并列的、作为故意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如果要保持该学说的解释力,势必对于主观“欲求”的感情因素做缓和性理解。据此,意志说又产生出诸多理论变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容忍说、决定说、动机说、类型说、实现意思说。
(一)作为我国通说的容忍说
从我国《刑法》第14条所规定的“放任”这一表述来看,可以说我国刑法所采用的就是容忍说的立场。该学说认为,行为人虽然不具有像希望或者意欲那种程度的侵害法益的积极态度,但只要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结果“不介意”“完全不关心”,就足以成立故意,即消极的容忍就是故意。⑧参见前注①,张明楷书,第253页。由此可见,容忍是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即对于因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的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持一种漠视的态度,当行为所造成的不被法所允许的危险最终在构成要件结果中实现时,就可以将这种结果归属于行为人这种漠视的态度上。例如,在“王新生等放火案”中,被告人王新生为骗取保险金与被告人赵红钦合谋,由赵将王承包的一辆客车烧毁,事后支付酬金。于是赵携带汽油来到汽车站,将王停放的客车烧毁,当时车站内停有其他车辆十余辆,燃烧地点距家属楼16米,距加油站25米,距气象站7米。对于该案件,河南省篙县人民法院认为,判断行为人的放火行为是否足以危及公共安全,就要结合放火的地点以及放火时周围的具体环境等因素来分析。该案中,教唆他人放火的被告人王新生、实施放火的被告人赵红钦,共同实行放火行为的地点是车站,放火时周围停有十多辆其他汽车,与其邻近的是家属楼、加油站等,且两被告人对此是明知的。两被告人的共同放火行为,客观上足以危及公共安全,主观上明知放火行为会危及公共安全,为实现骗取保险金的目的,仍放任这种危险的发生,符合放火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构成放火罪。⑨参见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主编:《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以下。
在该案中,被告人王新生与赵红钦的放火行为到底仅仅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还是构成放火罪,成为争论的焦点,行为人是否具有对于其行为已经威胁到了公共安全的认识又成为判断的核心,这一点的判断必须求诸于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状况。由此可见,容忍说是通过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来决定是否成立故意,虽然承认必须通过客观存在的事实状况来推定主观意志,但起决定作用的在于行为人在认识到自己实施的实行行为及其性质之后所采取的态度。这样的话,容忍这一要素就与违法性认识的内容几乎一致。与此同时,可以说只有将故意仅仅理解为责任要素才能为容忍说提供理论基础。这是因为,如果单纯地根据行为人的表象就认为比过失的违法性更大,就会导致将没有与外部表象相关联的心情作为违法要素,这无疑混同了违法与责任。⑩参见[日]高山佳奈子:《故意与违法性意识》,有斐阁1999年日文版,第142页以下。
(二)决定说在实务中的运用及其难题
德国学者Hassemer从故意犯受到比过失犯更重的处罚这一点出发认为,在故意的内涵中必须包含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因素,而只有将故意理解为一种“决定”,才能实现这一点。具体而言,故意是一种侵害法益的“决定”(Entscheidung),这样的话,故意犯就比过失犯对于事件的因果流程具有更高的控制可能性,其参与不法事件的程度也比较重,相应的刑罚当然也重于过失犯。这其中的意图性因素是指,行为人不但了解到了法益受到威胁的相关信息,而且明示或默示地接受,并将其作为行为的基础,即对于该危险的“意欲”(Wollen)。W infried Hassemer,Kennzeichen des Vorsatzes,in:Gedaechtnisschrift fuer A rmin Kaufmann,1989,S.294ff.然而,Hassemer并未单纯停留于实体法上的概念论证,他还从程序法的角度为行为人作出故意这一“决定”的判断提供一套综合性的判断指标。也就是说,在Hassemer看来,故意的存在与否并无法事先判定,因为它存在于行为人的内心领域中,经常摇摆不定,不可捉摸,在实施一个行为时,既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不是故意的,两者同时存在。然而,这种不可确定的状态通过行为人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就结束,对是否可以说行为人已经做出了决定,需要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观察。
据此,Hassemer列出了一份与认识及意志的判断相关联的判断因子,并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检验,首先,必须先确认外在的危险,这一点取决于行为所使用的侵害方式与工具;其次,对于认识的部分,行为人是否预见了危险,可以通过事件的可预见程度以及行为人的预见能力这两方面进行判断;最后,关于意欲因素的判断,必须借助诸如有无预防结果发生的行为、自我侵害的可能性、特殊职业养成、过去处于类似状况的反应以及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判断。W infried Hassemer,Kennzeichen des Vorsatzes,in:Gedaechtnisschrift fuer A rmin Kaufmann,1989,S.301f,304f.
如果根据决定说,对于以下这样的案件,应如何认定被告人的主观态度,值得探讨。被告人晏某某与被害人刘某某系情人关系,刘某某因怀疑晏某某与其微信好友余某有不正当关系,便来到晏某某的租住房,用晏某某的手机对余某进行辱骂,并与晏某某发生争吵和抓扯。后经人劝说,二人来到楼下公路边,刘某某再次用晏某某的电话和余某吵骂,晏某某夺回自己的手机,随后启动停靠在公路边的中型客车欲返回彭水县城。刘某某上前用后背抵在车前,阻止晏某某离开。晏某某明知刘某某在车前,仍然驾车推着刘某某往前行驶。车辆行驶二三十米距离后,晏某某未见刘某某,但并未停车查看,仍继续行驶,导致刘某某被客车碾压致死。案发后,晏某某主动拨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并到润溪乡卫生院找医生对刘某某进行抢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渝高法刑终字第52号刑事判决书。
在该案中,首先,作为确认外在危险的因素,可以考虑的主要是“晏某某驾车推着刘某某往前行驶”“刘某某被客车碾压致死”;其次,作为确定行为人是否预见到危险的因素,可以考虑的有“晏某某明知刘某某在车前”、晏某某是具有丰富驾驶经验的司机;最后,作为确定“意欲”因素的情节,值得考虑的有被告人晏某某与被害人刘某某是情人关系、两人发生争吵与抓扯、晏某某并未停车查看而仍继续行驶。第一个步骤是对于实行行为的判断,第二个步骤是对于认识因素的判断,第三个步骤是对于意志因素的判断,但这三个步骤的判断是独立进行的,处于平行关系,相互间并没有递进式的推定关系。于是,例如,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一个高度危险的行为,也完全能够认识到这种危险的存在,但却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并不追求结果发生,或者,行为人虽然积极追求结果发生,但所实施的行为并不具有足够的危险性或者对该危险性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在这种情形中,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做出了故意这一“决定”,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最后还是必须根据具体案情,由法官自由心证来确定。
(三)动机说的问题
动机说认为,在预见到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是确实的情形中,就存在确定的故意,但虽确实地认识到结果可能会发生,却仅仅停留于思想状态而未将其作为行为的动机时,也可以说是意识到了结果,因此可以肯定作为故意责任的非难,因为意图是指结果的发生是行为的主要动机之情形。根据动机说,才能将两者统摄于一个故意概念之中。参见[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Ⅰ》,有斐阁1972年日文版,第188页以下。然而,该学说在表述上就极其容易招致误解,因为该学说归根结底并不要求存在行为动机才能认定故意,而只要认识到结果确实可能发生即为足够。因此,有学者对该学说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先应当认识到结果发生的盖然性,在此基础上,行为人并未形成对于该认识的反对动机。参见[日]西田典之:《刑法总论》(第二版),弘文堂2010年日文版,第219页。因此,动机说重视的是行为人的认识对于行为的动机形成过程的影响。不难看出,采用动机说的论者几乎都站在将故意与过失等主观要素仅仅作为责任要素的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上,因此上述对于容忍说的批判也基本适用于动机说。此外,故意犯并不当然地就是动机犯或者目的犯,因为在故意的要件中,并不包含该当于犯罪构成要件之事实以外的事实的认识或容忍,例如故意杀人罪中的故意仅仅以对于杀人的实行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为足够,并不需要具备除此之外“报复”“情杀”等感情因素。这种动机或目的等因素在事实认定的层面上,最多只被作为认定故意的一种情况证据而已。因此动机说并不妥当。
(四)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可否相互补强
德国学者许内曼试图利用类型学的观念说明故意的内部构造,他认为,决定行为支配的认知因素具有层级性,即具有程度高低之分,对于结果发生概率的认知,从最高的确定有把握一直到最低的不一定可能。与此相对,侵害法益的敌对意志也同样具有强度上的差异性。因此,认识与意志两个因素都可以用程度高低的方式予以分析,这样的话,两者所结合而成的故意概念也当然具有这种区分强度的性质,因此故意的内部结构是具有弹性的,属于一种类型思维。参见[德]许内曼:《由语言学到类型学的故意概念》,载许玉秀、陈志辉主编:《不疑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乃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6年版,第459页以下。我国学者杜宇认为,刑法适用的核心不在于概念式的涵摄,而在于归类式的比较。在这一比较式的操作中,隐含着刑法解释的一种新思路。也就是说,对规范意义的探寻,应回溯至作为规范基础之类型,对超出类型轮廓的行为,则应予以排除。合类型性刑法解释的功能优势主要表现在解释的实质化、具体化、结构化与区分化。参见杜宇:《基于类型思维的刑法解释的实践功能》,《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据此,许内曼认为对于故意的解释不能从概念出发进行涵摄,因为故意是一个由认识与意志的强弱关系决定的类型,而且这两者呈现出互补的关系,当认识程度低而意志程度高,或者认识程度高而意志程度低时,仍然可以肯定故意的成立。该学说首先承认应当从认识与意志这两个维度来确定故意;其次认为认识与意志都是具有弹性的概念,而且相互之间具有互补关系,因此故意这一概念也具有伸缩性;最后主张应当以类型的思维来认定故意。在方法论上,其具有独到之处,但认识与意志这两者可以相互补强的根据是什么,作为下位基准,如何确定认识与意志的强弱程度,仍然存在疑问,尤其是,如果承认认识程度的薄弱可以通过意志因素来补强的话,很容易导致主观入罪的局面。
(五)实现意思说的具体适用
实现意思说认为,有必要将故意的认识要素与意志要素放在构成要件故意(违法故意)的层面上进行考虑,在这种意义上,当存在指向结果发生而操纵行为的实现意思时,就肯定故意。参见[日]高桥则夫:《刑法总论》(第三版),成文堂2016年日文版,第179页以下。这里的实现意思是指,指向结果的发生而预见因果关系,实现所意图的结果,并为回避没有意图的附随结果而采取适当手段的、控制行为的意思。作为实现意思的下位基准,可以考虑以下因素:认识事实的实现可能性的程度;是否存在实现计划的意思及其程度;是否存在将结果纳入计算范围的意思及其程度;是否存在回避结果的意思及其程度;是否存在结果回避措施及其程度。参见同上注,高桥则夫书,第180页以下。
该学说将故意作为一种构成要件要素,而不仅仅作为责任要素,因此将故意把握为控制由行为导向结果之因果流程的意思,但这一意思归根结底必须综合能够表明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客观外在的情况证据才能认定,可以将该学说归入上述的决定说的阵营中。这是比较务实的、与刑事诉讼中关于故意的认定相契合的观点。然而,这也不得不成为一种开放性的判断,考虑哪些因素以及不考虑哪些因素,只能取决于具体的案情,最后不得不泛化为“具体案件具体分析”这样的标准。
例如,被告人程伏康案发前暂住在浙江省慈溪市龙山镇山下村,并在当地供电所担任电工(临时工)。其间,被告人程伏康多次私设电网进行捕猎活动。2013年12月31日下午,被告人程伏康在徐某甲种植的桔园内,使用竹棒、铁丝等工具私自架设了电网准备捕兔。当日18时许,被告人程伏康携带逆变器、电瓶等工具至上述地点,将电网通电并在附近守候,但未设立警示标志。当日19时许,被害人毕某等人行至该桔子园捕鸟时,毕某触碰上述电网遭电击倒地,被人送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甬刑一初字第98号刑事判决书。在该案中,被告人在主观上是间接故意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成为争论的焦点,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架设电网捕猎,其主观上虽没有致死他人的直接故意,但存在放任的间接故意。其具体理由是:被告人程伏康系电工,其应当比一般人具有更多的电力常识,其所用的电瓶经逆变器放电后,放大电压,据其供述该电压可达到约80伏至100伏,该电压已超越可致人死亡的范围。经检验,实际该最大开路电压可达到6.566千伏,足以致人死亡。因此被告人程伏康辩称不知道会造成他人死亡后果,是不能成立的。另外,案发当天,被告人布线时,现场确有他人在劳作出入,该现场紧邻329国道,属开放现场,被告人也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未设置警示装置,因此其主观上有放任的间接故意。
应当说,这一裁判理由充分结合了上述作为判断实现计划的意思的五个下位基准,其中,对于故意的认定起关键作用的是行为具有高度的致人死亡的危险性以及行为人并未采取任何回避措施这两个因素,前者确定了认识因素的范围,后者确定了意志因素的程度。然而,从该学说的下位基准来看,判断的对象都指向对于结果发生可能性的认识。据此,该学说其实与认识说无异。
(六)小结——恣意的意志说
尽管在意志说的内部出现诸多理论变种,但在将行为人对于事件发生,尤其是构成要件结果“欲求”态度纳入故意的考量范围之内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出发点在于是否同时要求“认识”因素,以及意志是否建立在认识的基础上。如果将故意仅仅作为一种责任要素,并将责任的本质理解为道义责任论,则在故意的认定上,必然会重视行为人的主观意志,认识的因素最多作为其辅助性的判断因素而已。例如,可以说上述的容忍说与动机说都是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学说,因此得到结果无价值论者的支持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自从德国学者贝林创设构成要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这一古典的犯罪论体系以来,开启了构成要件实质化的进程,尤其是伴随着心理责任论向规范责任论的过渡,故意也开始走向客观化与规范化。与此相对应,构成要件故意这一概念也得以稳固确立,但这仅仅是指对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它就像一只眼睛,负责照看构成要件范围内的客观要素。这样的话,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也承担证明构成要件故意存在的证明责任,但这一证明过程就可以通过实行行为的危险性、结果的发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是否在现场等客观因素的存在来推定。然而,在责任阶段中,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责任故意概念,这是指行为人虽然认识到了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及其性质,预见到了行为的规范违反性,仍然决意通过行为的实施去触犯这一规范的反规范态度,正是这一点为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提供了基础。
由此可见,意志说并不是铁板一块,甚至可以说其内部存在重大分歧。此外,即使将故意的本质理解为一种主观意志的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行为人的主观欲求难以证明,只能根据客观的情况证据来推定。也就是说,例如,当某个行为人在认识到其行为可能产生致死的作用而仍然发动该因果经过时,就可以将其作为故意犯处罚。在这一意义上,故意的客观化成为必然,但有疑问的是应当被客观化到什么程度。认识说在对意志说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观点。
三、认识说的总评
如前所述,故意的客观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其内在的推动力就在于对责任本质的理解从心理责任论走向规范责任论,从此,“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这一金科玉律遭受重大挑战。例如,作为规范责任论奠基人的弗兰克(Frank)认为,没有哪一位论者打算将意欲因素逐出刑法,他们只是认为,意欲因素可以透过行为充分地展现出来,因此,无需在定义故意时将意欲因素纳入考虑,而应着眼于行为在认定责任上的意义,这也正是找出认定意欲是否存在的一个审查标准。参见[德]弗兰克:《论责任概念的构造》,冯军译,载冯军主编:《比较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以下。据此,弗兰克也奠定了认识论的基调:故意的本质在于行为人对于结果的认识,意欲因素可以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没有必要将其特别地作为故意的要件。认识说受到诸多学者的青睐,但其出发点也不尽相同。
(一)规范的故意论在实务中的运用
雅各布斯认为,行为人在认识到构成要件之实现的情形下行事,他可能是为了实现构成要件本身,也可能只是为了实现构成要件的结果,而想(“欲”)这样行事。不管怎样,在这个范围内,对于构成要件之实现的预见就足以成为行为的充分条件。这是主要结果(Hauptfolgen)的领域。进而,行为人在对构成要件之实现有认识的情况下行事,而这种认识并不一定就也要成为“欲”的内容。人们可以将这种认识视为是依赖于“欲”的,但是,实现“欲”并非行为的缘由。这是附随结果(Nebenfolgen)的领域。因而,主要结果是“知”的内容,就像“欲”的内容那样。附随结果也是“知”的内容,并且可以看作是依赖于“欲”。结合避免令人失望的举止这一规范目的,这也就意味着,在主要结果领域,行为人没有从意志和认识上避免结果的发生;在伴随结果的领域,他只是没有从认识上避免,至于意志方面则不需要了。所以,将故意定义成实现构成要件的“知”和“欲”这种通行的说法自始就是不合适的;如果人们需要用“欲”来指称某个举止的驱动力上的某种积极的东西时,使用任何其他的语词所遮蔽的东西反而比它揭示的东西更多。那么,在附随结果那里,“欲”就不成立了。必须这样来修正这个公式,该公式应是:故意是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是知道了如果采取其所“欲”的行为过程的话,会导致构成要件的实现。这种认识可能也并不想(“欲”)实现构成要件。简言之,故意是对行为及其结果的认识。参见[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第六版),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页译者注。在此基础上,雅各布斯对故意进行了以下定义:行为当时的行为人如果是法所期待的具有理性的人,就会感知或预见到被认为应该停止该行为之程度的犯罪事实,而且判断该犯罪结果的发生并非盖然的,即具有发生犯罪结果的盖然性,尽管如此,却并未停止该行为。Guenther Jakobs,Strafrecht AT,2Aufl.,1993,8.Abschn,Rn.23.
这是一个具有高度规范性的定义,该定义包含了以下三层含义:第一,行为人应当预见由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某一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事实;第二,该事实在社会一般人看来是无法容忍的;第三,行为人并未停止该行为。由此可见,该故意概念虽然重视行为人的认识因素,但该认识的对象既包括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也包括对于违法性的预判,这样可能会导致区分不法与罪责的阶层性犯罪论体系崩溃。然而,如果将社会一般人对于该事实的容忍程度作为衡量行为人所认识的结果发生的盖然性程度的话,则可能彻底颠覆了明确区分故意与过失的传统认识,而将这两者的判断纳入统一框架之中。
例如,2014年10月15日,被告人陈某在大冶市刘仁八镇从事卖淫时,被大冶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出HIV-l抗体呈阳性(艾滋病毒携带者),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将检测结果及平时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告知了被告人陈某。事后,被告人陈某继续从事卖淫,并与嫖客郑某、殷某、石某等人发生性关系。经大冶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郑某、殷某的HIV-l抗体呈阳性(即艾滋病患者)。参见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2015)鄂大冶刑初字第00383号刑事判决书。
在该案中,将被害人郑某、殷某感染了艾滋病毒这一结果在客观上归属于与艾滋病毒携带者的被告人陈某发生性关系,应该不存在疑问,即使与艾滋病患者发生性关系并不必然导致病毒的传播,但这也是一种主要传播途径,可以肯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合乎法则的条件关系。然而,能否认定这一因果流程是在被告人主观故意的支配下完成的,则存有疑问。根据上述雅各布斯关于故意的定义,首先,行为人必须具备对于“因性交而导致艾滋病毒传播给对方”这一事实的认识;其次,“艾滋病携带者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这一点是被社会一般人所无法容忍的;最后,行为人并未阻止本应该且可以阻止的性行为。结合该案的案情来看,被告人已经明确地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并且被疾病防控中心工作人员告知了注意事项,因此,对于“因性交而导致艾滋病毒传播给对方”这一点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以上的盖然性。有学者认为,这里的程度虽然无法精准地确定百分之几,但至少应当达到值得对其施加比过失更重的故意责任之程度,即“如果具有以如此高的概率导致结果发生的认识,就可以要求其变更自己的态度,尽管如此,如果胆敢实施该行为的话,就值得对其施加较重的责任非难”。同前注⑦,杉本一敏文,第169页。简而言之,从社会一般人的视角来看,行为人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如果认识到了这种结果发生的高度可能性,就完全足以改变其决意实施该行为的态度,但行为人却没有停止实施。此时,即可将最后导致的构成要件结果在主观上归属于行为人的故意。
这样的话,故意的本质就与过失一样,都是违反结果回避义务。围绕过失的本质,存在旧过失论与新过失论的对立,旧过失论将过失理解为从属于故意的责任要素,其本质在于违反预见义务;与此相对,新过失论将过失理解为与故意相并列的违法要素,其本质在于违反结果回避义务。参见[日]藤木英雄:《关于过失犯的构造》,载《司法研修所论集》1971年第1号,第59页以下。然而,该结果回避义务的发动是以具有某种程度的预见可能性为前提的,正是因为故意的预见可能性程度相比过失而言更大,所以才对其施加更重的责任非难。问题是,大到什么程度就变成故意了。
(二)客观归属论视角的故意危险理论
德国学者普珀(Puppe)在对意志说展开全面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故意危险”(Vorsatzgefahr)理论。具体而言,在普珀看来,德国学说与实务中对于意欲因素的检验,不但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将故意的成立与否求诸于行为人的恣意性决定,以行为人自身的主观感受为审查基准,不得不说是忽视了法律判断在评价上本来应有的客观性立场。Ingeborg Puppe,Der Vorstellungsinhalt des dolus eventualis,ZStW 103(1991),S.1.据此,普珀提出一套根据风险的层级来区分故意与过失的体系:先根据经验区分危险的种类,如果某一行为具有适合造成结果发生的危险则为故意危险,反之则为过失危险,当行为人在行为当时认识到其行为具有故意危险,只要该危险最后在构成要件结果中实现,即可将其归属于行为人的故意,至于行为人在心理上对于结果的发生抱何种态度,是欢迎、接受、希望、还是痛苦,在所不问。Ingeborg Puppe,Vorsatz und Zurechnung,1992,S.39.简言之,如果某个决定是和法秩序的风险原则不相容,那么此时的行事就是故意的举止。这里的故意危险是指对某种风险的设想,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创设该种风险即可引发结果,因而,如果谁有意地设置这种风险,那么人们就只能认为他做出了侵犯法益之决定的表示。参见[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第六版),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
由此可见,普珀的核心观点在于利用已经较为成熟的客观归属理论来理解主观故意的内容,因为根据责任原则,行为与故意必须同时存在,因此,当可以将某个构成要件结果归属于某个实行行为,如果行为人认识到该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通常危险性时,就是有意支配了这一因果流程,因此可以对其进行主观归属。然而,一开始就区分故意危险与过失危险,不得不说有先入为主之嫌疑,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危险的有无及其大小与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并无任何关系,过失行为与故意行为在实行行为危险性的认定上可以作同样的理解,都体现在对法益造成急迫的危险性,甚至在一些重大责任事故中,过失行为的危险性更甚于故意行为。不过,该学说将客观归属论的判断框架引入对故意的认定上,从而以归属这一动态的思维来理解故意,是富有创见的。如果对危险做客观化理解,并将行为人对于该危险的认识可能性高低的认定引入到该判断框架中,也许更具有说服力。
例如,被告人高宇在倒车过程中将在人行道上摆地摊卖货的郑某某撞倒并卷至车下。在围观群众告知其撞人的情况下,高宇下车查看。后高宇不顾围观群众阻拦,上车继续向北倒车,再次碾压郑某某后逃逸,致被害人郑某某因多发性骨折、出血而死亡。在该案中,被告人高宇提出了上诉,其主要理由是在主观上并没有杀人的故意。关于这一点,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有多位现场目击证人证实,上诉人高宇得知被害人被其碾压于车下后曾下车查看,后不顾众人阻拦倒车再次碾压被害人逃离现场。司法鉴定意见书亦证实,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多部位损伤一次碾轧难以形成,符合多次外力作用所致。高宇明知被害人已被其碾压至车下,为逃离现场又倒车对被害人进行二次碾压,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具有杀人的间接故意。在该案中,被告人无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是持希望还是放任态度,其目的是为了逃离现场还是避免围观群众的纠缠,都不在认定故意所考虑的范围之内,应该考虑的仅仅是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具有导致死亡的通常危险性,以及行为人对该危险性的认识程度。从案情出发,开车从人身上碾过这一点,在社会一般人看来当然具有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通常危险性,而行为人是在认识到被害人在自己的车底下这一点的基础上实施该危险行为的,因此当死亡结果最终实现时,即可认为行为人是在故意的支配下完成该因果流程的。
(三)从可能性说到盖然性说
几乎所有的持认识论观点的人都承认,在认定故意时,之所以不需要考虑行为人主观上的意志因素,是因为行为人认识到了其行为具有导致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当这种可能性达到某种程度时,即视为故意。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认定这里的可能性程度。关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故意是犯罪事实在主观层面上的反映,据此对于认识的可能性程度做了如下分级处理:其一,当犯罪事实本来就没有在脑中闪过时,在脑海中就没有描绘相应的“画面”,犯罪事实不具有在主观层面上的反映,因此,该情形是无认识的过失;其二,当犯罪事实虽然在脑中闪现,但立马打消该念头时,就是将不成为犯罪事实的“画面”代替了犯罪事实的“画面”,该情形可以视为有认识的过失;其三,当犯罪事实在脑中闪现,行为人并没有细想怎么办而实施行为时,就描绘了犯罪事实与非犯罪事实的两幅“画面”,因此可以肯定未必的故意;其四,当犯罪事实经过了大脑,仅仅将该“画面”在心理上描述时,就可认为存在确定的故意。同前注⑩,高山佳奈子书,第148页以下。
然而,这一观点不得不面临以下批判:第一,按照这种观点,无认识的过失就丧失了可罚性,但过失的本质并不在于认识可能性,而在于虽然在抽象程度上预见到了结果发生却没有采取相应的结果回避措施;第二,这一观点将故意视为客观情状在主观上的反映,是一种心理状态,但根本无法确定行为人脑中是否描绘了犯罪事实的画面,这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事实认定问题,也是一个规范评价问题;第三,关于间接故意的认定更是完全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因此,这一可能性的分级理论并未成功,反而使故意与过失的认定标准更加模糊。据此,有学者对于故意提出了更高的认识可能性之要求,从而产生了盖然性说。换言之,如果认识到了结果发生的盖然性而仍然实施该行为,即可肯定其主观上的故意,反之,如果没有认识到结果发生的盖然性,就欠缺故意犯的违法性意识可能性,最多只不过对其施加过失犯的非难而已。参见[日]前田雅英:《刑法讲义总论》(第六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15年日文版,第160页。
然而,这里的盖然性仍然无法通过精确的百分比来呈现。例如,在著名的“林森浩故意杀人案”中,关于故意的认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了以下事实:林森浩于2011年与他人用二甲基亚硝胺做过大鼠肝纤维化实验,二甲基亚硝胺是肝毒性物质,会造成大鼠急性肝功能衰竭死亡。林森浩到案后直至二审庭审均稳定供述,其向饮水机中投入的二甲基亚硝胺已超过致死量。据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林森浩具备医学专业知识,明知二甲基亚硝胺系剧毒物品,会造成人和动物肝脏损伤并可导致死亡,仍故意将明显超过致死量的该毒物投入饮水机中,致使黄某饮用后中毒死亡。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沪高刑终字第31号刑事判决书。也就是说,被告人林森浩显然认识到了二甲基亚硝胺具有致人死亡的高度危险性,仍然往饮水机里投入超过致死量的该种剧毒化学物质,即可认定其主观上的故意,当被害人最终喝下饮水机里的水并死亡时,即可对其追究故意杀人罪的责任。至于被告人的杀人动机如何,是积极希望还是放任被害人的死亡,并不是故意的成立要件,最多作为一种量刑情节来考虑。
(四)认识才是故意的本质要素
从理论上的内在推动力而言,规范责任论的建立必然推动故意的客观化,再加上“二战”之后对于行为人刑法、主观主义刑法的反思,在故意的认定上,仅仅关注行为人是否认识或预见到行为的危险性以及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认识说逐渐成为有力的学说。这一立场一直以来都遭受诸如以下的批判:第一,故意与过失仅仅在对于结果发生的认识程度不同,是量上的区别,容易混淆了故意与过失的界限;第二,对于结果发生可能性的判断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然而,不得不说,这些批判都没有对认识说构成根本性的挑战,这是因为,如果从预见可能性的角度而言,对故意所要求的对结果的预见程度当然比过失更高,当具备这种高度预见可能性时,社会一般人在面临这种情形时,一般足以让其抑制自己的行动,但行为人却越过了这一道规范障碍,继续实施该行为,正是基于这一点,可以对故意犯施加更重的责任非难。此外,关于认识可能性的判断,也完全可以通过客观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下位基准来实现。因此,笔者于本文中立足于认识说的基本立场,即认识才是故意的本质要素,展开以下具体论说。
四、笔者观点的展开
(一)故意论的理论功能
1.故意是一个兼具实体与程序的概念
通过上述围绕故意的本质与认定而展开的各种学说的批判性考察可以清楚发现,故意是一个刑事实体法上的基本概念,因此故意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心理事实,而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明确指出,故意并不会像是找到凶手一般被“发现”,而是经过事实之审查后作出的一个规范性判断,评价行为人具有高度的可非难性。参见前注②,徐育安文。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将故意与为故意的判断提供基础的事实这两者区分开来。这一点从心理责任论的崩溃与规范责任论的兴起即可清楚地看到。然而,故意终究还是一种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其本身无法证明自己,只能通过实行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客观存在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推定,在这个意义上,故意概念不得不被程序化。
2.故意的客观化是一种必然
3.应当以归属论的视角看待故意的认定问题
故意归属,或者被统称为主观归责,是以故意认定与客观归属为前提,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行为人在行为开始即有故意,并且最终的危害结果可以归属于行为人的实行行为时,判断最终结果是否可以归属于行为人在行为开始时就存在的故意。参见欧阳本祺:《具体的打击错误:从故意认定到故意归责》,《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客观归属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行为人所制造的不被法所允许的风险是否在构成要件的射程范围内实现,因此这里的故意就是指对于自己的行为制造了侵犯法益之危险的认识,其认识程度必须达到能够预见到这种危险不被法所允许。这样的话,既能为故意的认定提供一个客观化的标准,又对其客观化程度进行了规范性限定。
如前所述,关于这一点,可能面临的最大批判就是将会导致故意与过失只存在量上的区分,没有本质性差异,两者的界限势必变得模糊。然而,在间接故意与有认识的过失之间的区分上,至今为止的学说也没有提出一个足够清晰的判断标准。我国的通说认为应从意志因素区分这两者,对结果的发生持放任、无所谓的态度时就是间接故意,没有这一意志因素的就是过失。然而,这一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最终不得不由法官进行自由心证。据此,我国有学者在反思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模糊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的界限,将其视为“复合罪过”,以减轻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从而提高办案效率。参见储槐植、杨书文:《复合罪过形式探析——刑法理论对现行刑法内含的新法律现象之解读》,《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也有学者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认为,对于罪过之性状本来就模糊不清的疑难案件,只能退而求其次将之认定为过失犯罪,并在相应刑罚幅度内适当从重处罚。惟此,才能够做到既切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又依据排除合理怀疑之证明标准裁断案件。参见冯亚东:《间接故意不明时的过失推定》,《法学》2013年第4期。还有学者从解释论的进路出发,将故意与过失视为一种层级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参见张明楷:《论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笔者认为,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事实,而是一个需要被规范性评价的实体概念,而为这种评价提供基础的事实其实是一样的,即都是实行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不同的是对这种基础事实的认识程度。对于过失犯而言,只要对于结果的发生具备抽象程度的预见可能性,即对法益具有抽象意义上的危险程度,即足以发动结果回避义务,如果行为人懈怠了该义务,则应当承担作为过失犯的责任。这是主张将抽象的预见可能性说与法益相关联的观点,可以说是对“危惧感说”的修正,最近在日本刑法学界中逐渐得到支持。参见前注,高桥则夫书,第217页以下。与之相对,如果行为人对于结果的发生具有具体程度的预见可能性,即结果的发生具有盖然性,这种盖然性表现为从社会一般人的视角出发,并结合行为人自身的特殊认识能力,足以认为由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通常危险性,此时,即可认定行为人是有意地发动该行为,当这种法益侵害的高度盖然性最后在构成要件结果中实现时,即可将这种结果归属于行为时的故意,从而对行为人追究作为故意既遂犯的责任。因此,并没有必要固守故意与过失的绝对区分,事实上也不可能划定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4.意志要素不是故意概念的构成要素
通过以上的考察,笔者认为故意的本质特征在于认识到由其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高度盖然性,而意志因素主要表现为行为人对于结果发生的主观欲求与倾向,这是根据行为人在认识到结果发生的高度盖然性之后所采取的措施表现出来的。因此,可以说意志要素是在认定认识要素过程中所派生出的产品,其本身并不是故意的构成因素,但仍然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影响量刑的情节。例如,当行为人拿尖刀捅了对方的心脏,致其当场死亡时,综合考虑尖刀的锐利程度、长度、刺伤的部位、捅刺的力度、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事件发生的起因等客观因素,即可判断该行为的危险程度及其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据此得出行为人具备故意的结论,至于行为人对于被害人死亡的态度完全不影响故意的认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国《刑法》第14条所规定的“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只是一种注意规定而已,其目的在于,一方面是有助于司法实践中是对故意的认定,另一方面是对于故意犯罪的量刑做分级处理。律师在涉及故意犯罪案件的辩护中经常会提出被告人在主观上是间接故意而非直接故意,就体现了这一点。
(二)基本结论
于此,笔者将本文的基本结论概括如下:故意的认定仅仅需要考虑认识因素,并不需要考虑意志因素,意志因素以认识要素的具备为基础,并由认识因素推定,其本身只是一种量刑情节。故意的认识对象是实行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故意的认识程度需要达到具体的预见可能性,即认识到了实行行为侵犯法益的危险性以及因果关系的基本部分,而过失犯仅需要具备抽象的预见可能性,可以从这一角度出发区分故意与过失。在故意的认定上,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行为人认识到危险及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这三点组成了基本的判断结构。关于行为的危险性判断,应当以使用的工具、打击部位、力度、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实力对比状况等客观资料为素材,从社会一般人的立场出发进行事前判断。关于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判断,应当从包括行为人在内的社会一般人的视角出发,判断从行为人的行为导向构成要件结果是否具有相当性。关于行为人的认识可能性判断,应当以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能力为基点并结合行为人的特殊认识能力进行判断。
(三)观点的检验
可以把笔者于本文中提出的上述观点归入盖然性说的阵营中,而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在故意的认定上应当同时考虑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意志因素是区分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的关键因素。在大部分案件中,适用笔者的观点与通说的观点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为了凸显笔者观点在适用于司法实务中的优势,笔者试图以网络犯罪中共犯的认定、认识错误问题的处理、不作为犯中故意的认定、被害人自陷风险责任归属等富有争议的问题为例检验笔者的观点。
在动态MCS场景下,将AdaCode与RainbowRate[3]进行了比较.RainbowRate是针对长距离无线链路设计的速率选择算法,优于其它适用于短距离链路的速率选择算法.
1.网络犯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
随着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犯罪不断升级演化,呈现出新型化、精细化、专业化、组织化等特点。一方面,除了利用互联网实施传统犯罪,危害网络和信息安全行为也越来越公开化、规模化。形成了各类黑色或灰色产业链,成为寄生于电子商务乃至整个互联网的毒瘤,尤以恶意注册、虚假认证、虚假交易三大灰色或黑色产业为甚。在背后不断支撑这些犯罪和产业行为的是互联网技术灰色或黑色产业。各种恶意硬件软件开发和买卖为互联网犯罪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支持。非法信息、数据买卖、恶意聊天群组和平台网站运营是各类犯罪和黑色或灰色产业行为滋生的土壤。伪基站、恶意注册、盗号软件、炒信平台、身份证、手机卡、银行卡买卖、各类恶意聊天群组肆意活动和发展,已成为互联网犯罪的帮凶。
由此可见,在互联网犯罪中,最底层的互联网犯罪形式就是传统犯罪的网络化,但这只是一种不纯正的互联网犯罪方式,其背后还存在一系列的、一环紧扣一环的互联网犯罪环节。从根源上来说,账号与数据信息是从事互联网交易行为的基础,但技术才是互联网犯罪的支撑,当通过恶意软件盗取账号与信息时,就从源头上扰乱了互联网秩序。获取这些账号与数据后,卖家与买家就需要交易的场所,对于互联网犯罪而言则是以平台的形式出现。于是,互联网犯罪呈现出了一环扣一环的无缝对接的违法犯罪模式,然而各个环节的参与人之间经常是在线上完成交易的,按照传统的对于共同犯罪之成立条件的“共同故意”之理解,是否能应对互联网犯罪中的共同犯罪现象,存在疑问。
例如,从2014年开始,湖北籍男子胡某从马某等人处购买社工库数据——数百万条账密对(手机号、密码),并伙同王某在湖北鄂州通过“某云”等盗号软件批量扫号获取支付宝的账号及登录密码,再批量销售获利。胡某对上述部分支付宝账密通过全国最大的黑卡手机验证码平台即爱玛平台换绑支付宝绑定黑卡手机,以达到控制支付宝账户的目的。初步查明,胡某等人通过批量售号非法获利数万元。2015年,河南籍犯罪嫌疑人马某、白某等人以每个几元不等的价格从胡某、王某处购得大量支付宝账户及密码,并在焦作市某网吧内通过代理IP登录受害者支付宝、创建虚拟商品订单支付交易的形式盗窃支付宝内资金,再将虚拟商品的卡号、卡密销赃至黑龙江籍犯罪嫌疑人陈某处套现获利。初步查明马某等人盗窃支付宝账户3000余个,金额6万余元;陈某收赃金额一千余万元。该案中,湖南籍男子张某、叶某、杨某等人在长沙成立“某云工作室”开发34款盗号软件,该软件由另一犯罪嫌疑人马某甲负责销售,约定销售获利五五分成。初步查明,张某等人通过销售盗号软件非法获利二百余万元。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刑终43号刑事判决书。
可以将该案的作案流程归纳为数据获取和提供层次、软件和黑卡提供层次、扫号获取密码层次、使用账号盗窃资金层次、收赃层次等五个环节。这五个环节一环紧扣一环,缺少其中一个环节,都将导致下一个环节无法进行。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在处理互联网犯罪案件时,一般没有以整体的眼光来审视所有的这些环节,往往只关注第四个环节的“使用层次”以及第五个环节的“收赃层次”。例如在著名的“徐玉玉案件”中,仅仅将直接实施电信诈骗行为的犯罪嫌疑人逮捕并起诉,但在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如果没有掌握被害人徐玉玉的个人信息,不可能实施精准的诈骗行为;如果没有在网上或群组公开传授犯罪方法,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娴熟掌握犯罪技巧;如果没有开发并大量贩卖盗取数据库的软件,公民的个人信息就不会被大量盗取。然而,这些高智商的犯罪产业链却一直存在,在背后源源不断地为前端犯罪提供技术上的支撑。因此,如果仅仅打击实际实施盗窃、诈骗等行为的行为人,而不根治互联网中的黑色或灰色产业链,则不得不说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策略而已。
如果要根治互联网中的黑色或灰色产业链,从刑法的角度而言,先应当在不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从解释学的视角出发对现有刑法条文进行解释,当穷尽语义最大范围边界仍然无法以现有刑法条文进行规制时,再求诸于立法。很显然,如果线上的黑色或灰色产业链与线下的犯罪行为构成共同犯罪的话,就能打击线上的黑色或灰色产业链。然而,在解释共同犯罪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论证素未谋面的行为人之间存在“共同故意”。如果遵从传统观点对于故意的理解,则共同故意的成立需要行为人之间具备“共同的认识要素”与“共同的意志要素”,因此这种共同性就体现为完全的犯罪共同说的立场。按照该观点,在上述案例中,张某等人虽然将其所开发的盗号软件贩卖给胡某,但对胡某会将该软件用于何种犯罪行为这一点并不知情,更谈不上与胡某共同希望或放任犯罪结果发生。至于胡某将支付宝账号及密码贩卖给马某等人,以及马某后续实施的盗取支付宝账户里的资金以及销赃等行为,更是一无所知。因此,从传统的关于共同故意的理解出发,必然得出不构成共同犯罪的结论。
然而,从笔者的前述观点出发,意志要素并不是故意的构成要素,因此作为共同犯罪之成立要件的“共同故意”,仅需要具备共同的认识即为足够,即共同认识或预见到了结果发生的高度盖然性。据此,张某作为盗号软件的开发者,当然清楚地认识到买家购买了该款软件之后将主要从事盗号活动。关于这一点,可能有反对的观点会提出技术的中立性,即贩卖盗号软件是一种中立帮助行为,关于中立的帮助行为,参见[日]山中敬一:《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关西大学法学》第56卷第1号,第34页以下。但不得不说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盗号软件的“恶意性”,即仅仅只能用于盗号,除此之外别无它用。这样的话,张某就完全能够预见到购买了盗号软件的胡某从事盗号、洗号、卖号行为的高度可能性,据此就容易肯定张某与胡某之间具备共同故意。在客观上,张某所提供的盗号软件对于胡某犯罪行为的完成也确实起到了物理意义上的帮助作用,从因果共犯论的角度出发,共犯之所以受处罚,是因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对于最终的法益侵害结果具有因果性贡献。参见[日]西田典之:《共犯理论的展开》,成文堂2010年日文版,第189页以下。因此,根据笔者的观点,肯定张某与胡某构成共同犯罪并不存在障碍。同理可证,胡某、王某与马某、白某等人也构成共同犯罪。
2.认识错误问题的处理
如前所述,故意是指对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主观上所认识的内容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之间未必是一致的,当出现不一致的情形时,在刑法上将其称为认识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错误是故意的反面,因此,认识错误问题的处理也是检验故意理论的最好试金石。
当存在认识错误时,就出现了两个构成要件,一个是行为人基于行为当时的故意而设定的A构成要件,另一个是在客观上被实现的B构成要件,于是,错误论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对基于事前判断的A构成要件与基于事后判断的B构成要件进行比较与取舍之后,是否可以将其内容归属于行为人的认识。因此,A构成要件中的故意是存在于行为当时的完整的故意,而B构成要件的故意是行为当时存在的、结果能否向行为进行主观归属的这一作为“主观归属”意义上的故意。在客观归属论的框架下,派生出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即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的对应原则,也就是说,在所有具有刑法归属意义的事后判断中,以事前判断为前提,根据事前判断,设定事后判断展开的范围,不允许事后判断超越事前判断所设定的框架。参见前注,高桥则夫书,第67页以下。可以将该对应原则适用于错误论领域,从反面探讨故意的归属问题。以下笔者以因果关系错误以及方法错误为例进行检验。
(1)因果关系错误问题的处理
当发生因果关系错误时,意味着行为人所设想的因果流程与实际发生的因果流程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例如,在被作为教学案例而列举的“桥墩案”中,行为人所设想的因果流程是将被害人推入水中溺死,但实际发生的因果流程是被害人被桥墩撞死。因此,对于主观归属而言,所关注的问题是:被害人被桥墩撞死是否可以评价在行为人实施推人行为的当时所存在的对于“结果发生的盖然性”认识的范围内。因此,判断行为人所认识的“危险的现实化”与客观存在的“危险的现实化”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本质性差异才是解决因果关系错误问题的关键。参见[日]高桥则夫:《犯罪论中的“构成要件重合”的规范性、机能性分析》,载山口厚等编:《西田典之现实献呈论文集》,有斐阁2017年日文版,第9页以下。当存在本质性差异时,就不能将实际发生的结果归属于行为人在行为当时的故意,反之,如果不存在本质性差异,则可以进行主观归属。关于是否存在本质性差异的判断,取决于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导致其所设想的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盖然性与导致实际结果发生的盖然性的大小比较,当这两种盖然性差异并未超出包括行为人在内的社会一般人的预期时,则可以将实际发生的危险的现实化归属于行为时的故意。
(2)打击错误问题的处理
打击错误又称为方法错误,一般是指结果并未发生在行为人的行为所指向的对象,而是发生在其他的对象上。例如,被告人王某与肖某某因为拉货问题发生争执,后王某在用大理石块砸向肖某某时,将坐在一旁的保安杜志家砸成二级轻伤。参见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2015)周刑初字第333号刑事判决书。对于该案件,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扔石块故意伤害肖某某时误伤杜志家,系打击错误,虽然行为对象与预期不符,但侵犯的法益相同,即侵犯了他人的身体健康权,都在同一犯罪构成要件范围之内,其行为同样构成故意伤害罪。显然,该法院以法定符合说肯定了故意伤害罪的成立。如果从上述的对应原则出发考察故意的归属,则可以做如下考虑:不管石头砸到肖某某还是砸到杜志家,都同样侵犯了“禁止伤害他人”这个行为规范,因此,即使石头最终砸到了杜志家,也可以说“禁止伤害他人”这一行为规范与“结果发生的盖然性认识”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说伤害肖某某的认识这个行为规范故意包含了伤害杜志家这个制裁规范故意,据此就可以肯定后者在前者的范围之内这一对应原则。关于行为规范故意与制裁规范故意的关系,参见前注,高桥则夫文。第10页以下。
然而,必须说这是“数故意犯说”的归结,但事实上,被告人王某并不同时存在伤害肖某某与杜志家的两个伤害故意。根据笔者的上述观点,如果将透过认识因素而被推定的意志因素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的话,虽然无法阻却打击错误中的故意,但将其刑罚的限度控制在过失犯的范围内,则值得考虑。日本学者中野次雄教授提出了所谓的“对故意犯的过失责任”。参见[日]中野次雄:《方法错误与所谓的故意的个数》,载《团藤重光博士古稀祝贺论文集》(第二卷),有斐阁1984年日文版,第217页以下。高桥则夫教授从规范论的视角对该观点做了如下解读:从行为规范的视点出发,成立复数的故意犯,在违法阶段基于制裁规范的发动而奠定了成立数个故意犯的基础,但在责任阶段,因为只存在杀害或伤害一个人的意思,所以作为非难可能性的规范责任就减少了。并且,作为刑法目的的可罚责任(制裁规范的发动)也减少了,因此故意责任的量在整体上就减少了。据此,对“构成要件故意”做出“责任过失”的评价也是可能的。笔者赞成将这一观点适用于解释打击错误的情形。刘明祥教授关于打击错误问题的处理,明确主张应当适用具体符合说,而不应当适用法定符合说。参见刘明祥:《论具体的打击错误》,《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此外,从归属论的角度考察打击错误问题的,参见柏浪涛:《打击错误与故意归责的实现》,《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前注,欧阳本祺文。
3.不作为犯中故意的认定
目前为止,刑法学界关于不作为犯的讨论,基本都围绕着不真正不作为犯展开,而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认定中,几乎把所有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或者保证人地位上。似乎只要肯定了这一点,不作为犯就自然成立,但是作为义务的肯定最多充足了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如何认定不作为犯的主观故意或者过失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根据笔者的观点,基于等置性原则的要求,成立不作为犯的前提是不作为的举止与作为的方式在对于法益的危险程度上符合比例性原则的要求,因此,不作为犯同样具有自身独特的实行行为,但这种实行行为表现为处于保证人地位的行为人支配既有的危险,并将其导向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该不作为者将导向结果的因果流程控制于自己掌中。关于排他性支配理论,参见前注,西田典之书,第178页以下。如果以客观归属论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的话,则可以做如下表述:负有消除既有危险之义务的行为人在可能履行该义务的前提下却没有采取相应的结果回避措施或降低风险措施,由此导致既有危险在构成要件结果中现实化。对于主观归属而言,行为人是否认识到了既有的危险状况、危险程度、自己所处的地位、对于危险现实化之可能性的预测等因素为行为人对于结果发生之可能性的判断提供基础性事实,当综合这些因素可以推定行为人认识到了结果发生的盖然性时,则可以将构成要件结果归属于行为人在行为时的这种认识,即故意;反之,如果认识的程度尚未达到盖然性,则只能评价为过失。
例如,2014年7月30日,被告人詹桥驾车将情人秦某某带到水库岸边,在车内秦某某追问被告人詹桥是否在前天去武汉会见另外一个情人时,遭到詹桥的否认。秦某某趁詹桥到河边洗脸之机偷看詹桥手机信息,见詹桥当天中午与武汉情人有通话记录后,非常生气,并与被告人詹桥发生争吵。气急之下,秦某某从被告人詹桥的车上下来并脱掉身上的衣服和鞋子往水库里走。当秦某某往水中走了大约十几米远时,詹桥追上从后面拉住秦某某右手上臂,但被其挣脱。随后,詹桥又到秦某某前面阻拦。在阻拦过程中,詹桥因失去平衡倒在水中,其间用脚踹了秦某某一下。当詹桥浮出水面时未见到秦某某踪影,便独自游回岸边。尔后,詹桥既未积极寻救秦某某,又未呼救和报警,而是慌忙驾车逃离现场,致使秦某某因无人及时救助而溺水死亡。案发后,被告人詹桥向秦某某的亲属及相关人员隐瞒秦某某溺水一事。参见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2015)鄂红安刑初字第00030号刑事判决书。
该案中,被害人秦某某的死亡结果可否归属于被告人詹桥的不救助行为,是客观归属层面上的问题,在综合考虑“走向水库的危险程度、被害人的自救能力、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情人关系、水库周边是否其他可以施救的人、被告人在发现被害人沉入水库后的举动”等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可以认为被告人在认识到既有危险的前提下,并未采取积极的措施消除或减少该危险,以致最后该危险在死亡结果中现实化,因此可以肯定该死亡结果是不作为这一实行行为的“作品”。与此相对,这一死亡结果可否归属于行为人对于死亡结果发生之盖然性的认识这一问题则是主观归属的领域,当从既有危险导向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这一因果流程都在被告人的认识范围之内时,即可肯定故意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