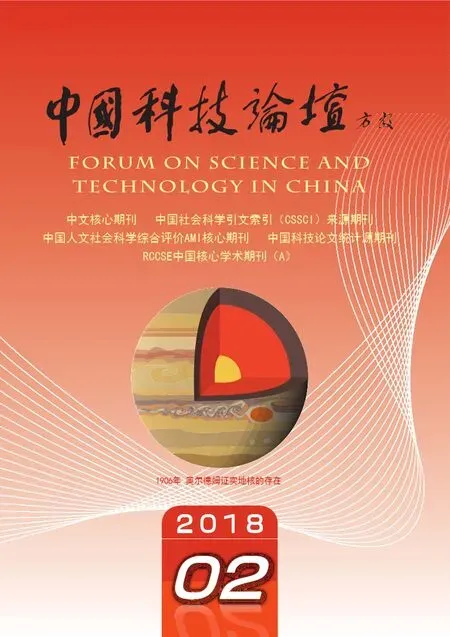技术标准的三重属性
——兼论技术标准与法学研究的关系
2018-02-06王庆廷
王庆廷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0 前言
所谓技术标准,是指对标准化领域中需要协调统一的技术事项所制定的标准,主要包括基础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工艺标准、检测试验方法标准,及安全、卫生、环保标准等类别[1]。我们吃的食品、穿的衣服、住的房子,以及开的汽车都伴有系列技术标准,就连呼吸的空气都有标准——近年来PM2.5日渐引人关注,催生了空气质量指数(Air Quality Index)的出台。如果离开了技术标准的保驾护航,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寸步难行,时刻处于危险之境。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技术标准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体现。如果一个国家的技术标准能够成为国际标准,在很多方面就有了话语权,甚至可以领导世界。反之就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中国出口经常遭遇的贸易壁垒就是例证。人们常说“三流企业卖苦力,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技术,超一流企业卖标准”,把“企业”置换为“国家”同样适用。反观现实,技术标准领域存在以下或轻或重的问题,亟待予以重视和解决:科学程度欠缺,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们需求;政出多门,充斥着利益分割与行业保护,标准之间矛盾冲突,让人无所适从;制发程序混乱,修订不够及时,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民众参与程度低,无法有效监督,利益难以保障;规制方式粗暴,缺乏配套机制,许多标准游离管控之外,等等。
面对如此重要且问题多多的技术标准,相关研究却呈现出两点不足:一是涉足学科趋于偏狭,多集中于科学学、管理学、经济学、标准学以及相关的理工类学科,法学、哲学、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类领域涉猎甚少;二是标准研究落入细微,多集中于某一或某类技术标准的具体应用类研究,抽象层面的理论统摄研究偏少偏弱。对于技术标准而言,无论是理论层面的研究,还是实践层面的应用,如此现状都是有待改善的。而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症结就是对技术标准的属性认识有所偏差。长久以来,囿于“科学主义”的影响和“专业知识”的迷信,人们对技术标准已经习惯和偏重于科学视角下的认识,而生疏和忽略于其他视角下的解读。其实,技术标准是一个综合性的存在,具有多重属性,除了科学的属性之外,还有人文的属性,以及法律的属性。基此,本文即以技术标准的属性为题,尝试对其做一多重视角下的解读,并兼及论述技术标准与法学研究的关系。
1 属性之一:科学的内核
毫无疑问,技术标准属于科学的疆域,其内核是科学而非其他。与大多数词语一样,“科学”的含义也是不断处于流变之中,有不同的层次和方面[2]。狭义的科学一般仅指自然科学,主要涉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即运用观察试验的客观手段和逻辑严密的数学方法研究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其结论只能通过“发现”而非“创制”来获取,可以被证伪;广义的“科学”是指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主要涉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艺术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虽然有自洽的逻辑标准和成熟的理论模型,但是结论的客观性远逊于自然科学,难以摆脱人为“创制”的色彩;更加广义上的“科学”则可以理解为“方法”,“它表明了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一种思路或一种规范[3]”。以此作为参照,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技术标准的“科学性”是比较强的,可以归为自然科学领域,具体表现为三大方面:
1.1 技术标准拥有较强的专业属性
专业属性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技术标准属于专业领域,远离日常生活,普通民众难以接触。比如工程建设领域行业标准《地下管线电磁法探测规程》(YB/T 9027—1994(2009))、饲料国家标准《饲料中卡巴氧、乙酰甲喹、喹烯酮和喹乙醇的测定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农业部2086号公告-5—2014)、放射卫生防护领域国家标准《高纯锗γ能谱分析通用方法》(GBT 11713—2015)、危险废物鉴别方法标准《固体废物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HJ 77.3—2008)等,可能大多数人都闻所未闻。前述标准都是从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标委”)官方网站(http://www.sac.gov.cn/)中随机选取的,都是属于比较生僻的专业领域,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接触到,更遑论知悉了。二是技术标准有自己的专业术语体系,溢出日常话语和感官知觉,普通民众难以知悉。很多技术标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就是日常生活的标准,比如大气环保标准、食品卫生标准、汽车行业标准等。对于这些技术标准,大多数民众的了解要么知其名不知其实,要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之所以如此,盖因技术标准的本质是一种“分解方法+术语表达”:在分解上主要有三类方式,要么化简为繁——将简单的事物分解为繁杂的事物,要么化大为小——将宏大的事物分解为细微的事物,要么化暗为明——将模糊的事物分解为明晰的事物。分解的结果就是远远超出人的感官知觉能力所及,必须借助科学仪器;在表达上有一套精准的专业术语体系,与日常生活中的零散话语相去甚远。以汽车内部装饰用的地毯为例,一般人的了解也就仅限于其大小、形状、气味、硬度等感官能够感知的范围,关心的主要是地毯是否结实和舒服等因素。而在行业标准《汽车用地毯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QC/T 216—1996(2009))中,对于地毯是否结实,就被分解为“断裂强力(N)”、“断裂伸长率(%)”、“梯形法撕破强力(N)”、“耐磨耗试验(失重 mg)”、“燃烧特性(级)”、“耐磨色牢度(级)”、“耐水色牢度(级)”等若干专业术语指标,并详细规定了数值区间和试验方法。
1.2 技术标准拥有过硬的科学支持
在国标委2014年发布的《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GB/T 20000.1—2014)中明确指出:“标准宜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作为标准家族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标准,自然更是以科学为基础:一是有科学的理论支撑。就以我们常见的交通信号灯为例,之所以用了红黄绿三种颜色,而非其他的颜色。虽然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还是有科学原理支撑的。根据光学原理,人的眼睛是根据所看见的光的波长来识别颜色的,而波长与传播距离成正比。红色光波长在可视光线中是最长的,容易发生衍射现象,穿透空气的能力强,在雨天和雾天可以传得更远,适合作为禁行信号。黄色光波长和穿透能力次之,适合作为慎行信号。绿色与红色的区别最大,都属于原色——色彩中不能再分解的基本色,易于辨认,而且穿透能力也较好,适合作为通行信号[4]。二是有科学的实践支撑。与人文社科领域的思辨和冥想的方法不同,自然科学的最大特点就是用事实讲话,其结论系运用观察和试验的方法得出并予以验证,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客观性,超脱于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不会因人而异。与之对应,技术标准的数据指标大多系根据观察和试验得出,有充足的实践支撑,而非思辨和冥想的产物。比如,国家标准《商用车辆和挂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GB 12676—2014)中规定了制动距离、响应时间、衬片材料等制动方面的技术标准。在该标准起草过程中,就进行了大量的试验,不仅有汽车试验场和检测中心提供的试验条件和试验技术支持,“(商用车制动标准修订)工作组的整车生产企业都提供了本企业典型车型的制动试验报告”。此外,工作组还进行了一次实车验证试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与WABCO(业界最大的制动系统供应商)于2010年6月1日至10日,在北京通县汽车试验场共同组织了EBS(电控制动系统)评价试验[5]”。
1.3 技术标准受制于现实的技术水平
从应然层面讲,任何一项技术标准均非随心所欲的产物,都须立基于现实的技术实践,超越于技术实践的标准难以施行,落后于技术实践的标准没有必要。同一时期的技术实践往往参差不齐,有先进的技术,也有落后的技术,但是技术标准并不必然立基于最先进的技术。因为除了技术先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该技术必须具有可推广性,或曰经济性。如果推广成本过高,条件不够成熟,即使该项技术足够先进也难以成为技术标准的现实依据。以食品保质期为例,在冰箱大规模普及之前,食品的保质期一般是指常温贮存下的保质期,而在冰箱大规模普及之后,很多食品可以在低温条件下贮存(冷藏贮存或冷冻贮存),保质期得到大大延长。如果说科学理论的应然程度决定了技术标准理论上的可能性,是丰满的理想,那么技术实践的实然水平则决定了技术标准现实中的可能性,是骨感的现实。
2 属性之二:人文的底色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技术标准是关于人的需要的技术化投影,具有浓郁的人文底色和相当的伦理意蕴。如果说科技需以人为本的话,那么技术标准同样需以人为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技术标准表面上呈现的是技术要求,实质上暗含的则是人的需要。无论技术标准的起草、修改还是废止,归根结底都是源于人的需要。技术标准不仅是一个由公式符号和数据指标组成的冰冷概念,更是一个蕴含人文价值和世俗关怀的鲜活生物。离开了人的需要,技术标准将成为无源之水,毫无意义;不积极关注人的需要,技术标准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成为一纸具文。粗略浏览各类技术标准,就会发现都是为了服务人的各种需要,既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需要(如服装标准),也包括特定时空内的特殊需要(如医疗标准),既包括以人为对象的直接需要(如食品标准),也包括以物为对象的间接需要(如饲料标准)。“服务人的需要”是技术标准的人文底色,具体可以分解为三点:
2.1 这里的“人”是有侧重的
一是侧重“抽象的人”而非“具体的人”。即模糊具体的人的差别,进行一定程度的“一刀切”。比如具体的人高矮胖瘦各不相同,但是常见的男士衣服尺码标准却只有五个:S码(对应身高165cm胸围90cm),M码(对应身高170cm胸围95cm),L码(对应身高175cm胸围100cm),XL码(对应身高180cm胸围105cm),XXL码(对应身高185cm胸围110cm)。易言之,将千差万别数以亿计的具体男士予以抽象,划分为五个“标准人”。二是侧重“整体的人”而非“个体的人”。即淡化人的个体性,关注人的群体性,比如地域、行业、年龄、性别、企业等。正因如此,依地域划分,技术标准可以分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地区标准。依行业划分,可以将工业标准分为工程建设领域行业标准、安全生产领域行业标准、原材料工业行业标准、装备工业行业标准、消费品工业行业标准、电子信息行业标准、软件服务业行业标准、机械行业标准等。根据具体行业,还可以再分。比如消费品工业行业标准又可细分为轻工行业、食品行业、纺织行业、包装行业等。三是侧重“一般的人”而非“特殊的人”。即主要以生活中的普通人为依据,重点关注普通人的一般需求。以空调噪音标准为例,到底多少分贝合适,制定依据是普通人的忍受限值。在日常生活中,有的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有的人对声音特别麻木,但这些人的特殊情况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2.2 这里的“服务”是中性的
它既可以是正面的满足,也可以是反面的节制。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有的需要是理性的,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益于人类整体利益。有的需要是非理性的,可能阻滞经济社会发展,无益于人类整体利益。前者如希望穿的衣服更加舒适和美观,希望吃的食品更加安全和健康;后者如为了经济的一时发展而鲁莽短视不惜污染绿水蓝天,为了飞驰电掣的快感而不顾安全因素将汽车的速度研制得超过飞机。因此,为了人类的长远发展和整体考虑,技术标准对于各类需求不能一味迁就,刻意逢迎,而是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满足理性需要,节制非理性需要。
2.3 这里的“需要”是有层次的
人的需要多种多样,大多数种类的需要都有一定层次,由低到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低级层次、中级层次、高级层次。以住房需要为例,抛去其他因素,单以面积划分,“一居室”属于低级层次,“大三居”属于中级层次,独栋别墅属于高级层次。与之对应,技术标准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底线标准,以人的低限度生存为目的;中等标准,以人的适度发展为目的;高级标准,以人的高层次享受为目的。以食品标准为例,腐败变质、霉变生虫、致命病菌、农药残留等卫生指标属于底线标准,因为直接关乎人的生命健康;食品添加剂标准属于中等标准,因为它们的主要用途是改善食品的外观、风味、组织结构或贮存性质,对人身无害但也没有营养;营养成分及其数据指标属于高级标准,直接表明食品营养价值的高低优劣,体现食品之于人类的最终价值。当前,中国很多技术标准低于国际标准以及发达国家的标准,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巨大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正如回顾中国的食品标准演进史,就会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的食品标准整体上比较落后,“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首先考虑到的是吃饱饭,对于吃的东西是否符合卫生标准,相对来说就考虑得少了一些[6]”。
3 属性之三:法律的品性
通常而言,法律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7]。对比而言,技术标准显然不属于传统的法律范畴,既没有明显的法律外观,亦缺乏显著的法律效力。纵然如此,技术标准也是社会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权力化的技术规制,对于社会和个人都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此观之,技术标准与法律又有相当的家族类似特征,具有相当程度的法律品性,依品性色彩由淡到浓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
3.1 形式上的规范性
依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ISO/IEC导则》,标准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依照国标委《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GB/T 20000.1—2014),标准是“通过标准化活动,按照规定的程序经协商一致制定,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指南或特性,供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文件”。可见,技术标准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规范性文件,拥有一套包含术语表达、编写规则和发布程序等特定内容的规范体系。这些在国标委发布的《标准化工作指南》《标准化工作导则》《标准编写规则》《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科技平台标准化工作指南》《综合标准化工作指南》等系列标准化指导文件,以及《标准化法》《标准化实施条例》《地方标准管理办法》《行业标准管理办法》《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等系列标准化法律法规规章中有详细规定。比如,以制定程序为例,大致可以划分为预研、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出版、复审和废止等若干阶段。
3.2 内容上的调控性
知识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并运用其来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内容类知识,即关于“是什么”的知识;二是原理类知识,即关于“为什么”的知识;三是方法类知识,即关于“怎么做”的知识;四是规则类知识,即关于“谁能做、谁不能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的知识[8]。以此观之,技术属于方法类知识,标准属于规则类知识,而技术标准就是给技术领域有关事项厘定规则的知识。法律规范无疑是典型的规则类知识,在内容上有典型的逻辑构成,包含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个部分。其中,行为模式是对法律主体做出的行为指示,大致有四种模式,即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不得做什么;法律后果是国家对法律主体行为选择的评价,主要有两类态度,一是肯定评价,包括承认行为合法、有效、给予保护、进行奖励等,二是否定评价,包括认定行为非法、无效、科以责任、给予制裁等。与法律规范相比,标准规范也有典型的行为模式内容,主要表现为使用“应”“宜”“可”等字眼。其中“应”即应当,表示的是强制性要求(“不应”则表示禁止性要求),“宜”即适宜,表示建议性、推荐性要求,“可”即可以,表示的是允许性、选择性要求[9]。进一步与法律规范对比,就会发现标准规范中欠缺了明确的后果评价及其处置条款。以此观之,技术标准的规则性似乎要大打折扣,其实不然。因为与法律规范一样,技术标准的目的也是规制调控,化乱为齐。作为社会调控手段,技术标准的本质是一种权力化的技术,不仅是一种事实描述,更是一种价值判断。易言之,后果评价已经内含于技术标准的字眼之中,符合标准即意味着正面评价,表示“合格”“良好”“优秀”“先进”等,不符合标准即意味着负面评价,表示“低劣”“淘汰”“危险”“落后”等。
3.3 效力上的约束性
根据名与实的关系,大致可以将法律分为“硬法”和“软法”。前者是名实相符的法律,即不仅形式上具备法律外观,而且实际上具有法律约束力;后者是名实分离的法律,即虽然形式上欠缺法律外观,但实际上具有法律约束力。以此观之,很多技术标准可以归入“软法”范畴,甚至有些可以归入“硬法”范畴。特别是在行业法制日渐发达的今天,技术标准的法律色彩日渐浓厚,“从理论上讲,每一行业都必然应当存在一个法律体系,它的法律形式(法的渊源)可以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规章,甚至可以是行业自治性规则、行业标准、行业习惯等等[10]”。如前所述,虽然技术标准有一定程度的形式规范性和内容调控性,但是与完整的法律外观相比,还是相差较大。比如,以名称为例,法律会冠以“法”“决定”“条例”“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定后缀,而技术标准则没有类似的严格后缀。可以说,“通过求诸形式意义上的诸种判断标准,可以得出技术标准不具有法律规范外观的结论[11]。”尽管如此,技术标准还是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的,而且很多情况下,这里的约束力不是道德义务性质的软约束力,而是具有法律义务性质的硬约束力。依据《标准化法》,中国的技术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其中强制性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具有当然的法律约束力。中国的强制性标准相当于世界贸易组织(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中的技术法规,在强制执行力上是一致的、相当的,都要求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12]。推荐性标准虽然是推荐使用的标准,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具有约束力:第一,该标准被国家法律法规援引,这是法定约束力;第二,该标准被当事各方签订的合同协议援引,这是约定约束力;第三,该标准被经营者宣称其产品符合,这是声明约束力。技术标准的约束力范围及于相关各方:一是及于标准规制者,即受技术标准规制的个人和单位。很多技术标准是针对生产经营活动过程提出程序规范和技术要求,以及对调整对象规定了项目清单和目标阈值,表面上规制的是“技术”,实际上规制的是“人”,为个人和单位设定了直接或间接的法律义务,产生了溢出“技术”的外部法律效果;二是及于行政执法者。技术标准是行政机关开展执法调查,进行事实认定,做出行政处理的判断基准;三是及于司法裁判者。“在中国审判实践中,法院尽管在判决正文中没有引用技术标准,但是在专业技术领域,作为判断事实认定构成要件的基准,技术标准在事实上发挥着法院审查基准的功能[13]”,成为“隐形的法律”。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增强约束力,技术标准往往和法律联合作战,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全盘吸纳模式。技术标准“被逐字并入法律或其附件中,成为法律条款的主要部分,并成为强制性法律规则[14]”,再辅以设置明确的法律权利、义务和责任,成为典型的法律样态——“技术法规”;二是明确援引模式。技术标准游离于法律之外,没有纳入法律及其附件,但通过法律条款的明确援引,可以落实到某一技术标准的特定或若干版本,进而发挥其约束力;三是模糊参考模式。在法律条款中没有明确提及具体的技术标准,而是笼统规定遵守“一般认可的技术准则”,考虑“科学和技术状况”,及应用“最可行技术”等模糊术语或“通用条款”[15],实践中可能也没有具体的技术标准与之对应。在三种模式中,立法权的集中性渐趋弱化,各种标准化组织可以一定程度上分享立法权,随之而来的是立法成本逐步降低,修订起来更加容易和便利;技术标准的明确性逐步弱化,法律色彩亦随之淡化;相应的,法律适用中自由裁量权愈发增强,对行政执法者和司法裁判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技术标准与法学研究的关系
技术标准理应纳入法学研究的视野,从浅层原因来看,主要是关于技术标准的法治实践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就立法而言,存在介入状态游离,管控思想僵化,立法供给粗劣,施行效果低下等问题。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88年12月29 日通过,自1989年4月1日施行)为例,已经施行了28年,从未进行修订,从形式到内容再到效力,均已严重落后于实际需要,几成一纸具文,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部法律。就司法而言,实践中对技术标准及依其制作的鉴定意见的审查状况并不尽如人意,或疏于审查,或怯于审查,或拙于审查。如此一来,基于技术标准及其鉴定意见在定罪量刑、侵权赔偿等司法实践中的特殊意义,就间接造成了法院审判权的主动性旁落——鉴定机构的“事实审判”——鉴定机构成了事实上的审判机关,鉴定意见书成了事实上的判决书[16]。就执法和守法而言,由于技术标准出台的仓促等原因,很多因素考虑不周,致使出现诸多执法尺度不一和守法无所适从的情况。以2009年发布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GB/T 24158—2009)为例,该技术标准将车重40公斤以上、时速20公里以上的电动自行车划入机动车范畴。虽然国标委发布《关于电动摩托车相关标准实施事项的通知》(国标委工一[2009]98号),明确前述标准暂缓实施,但实际中仍然有执法部门按照前述标准执法,更有一些地方将前述标准变相列为强制性的地方标准。正是前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实践中的种种问题,使得技术标准亟须引起法学研究的高度关注,而法学研究关注技术标准亦是理所应当。因为法学是实践导向强烈的学科,法学研究直接而主要的关注对象就是法治实践——关注法治实践问题,分析法治实践原因,提出法治实践对策。
从深层原因来看,法学研究之所以要关注技术标准,与技术标准的三重属性有着由远及近的内在关联,进而法学研究的重点也各有差异。就技术标准的科学属性而言,科学与法律有显著区别:一是客观性与合法性的区别。科学尊崇客观性,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理解和说明世界,运用的方法主要是数理逻辑和观察实验。法律尊崇合法性,秉持合法性优于客观性的立场,重视法律真实胜过客观真实,运用的方法包括法律解释和自由裁量等。二是创新性与保守性的区别。科学的本性在于创新,即不断地怀疑、批判、突破和创新以达至真理;法律的本性是保守,立法上的规则预设和司法上的遵循前例是保证法律统一的基本原则。三是无穷性与终结性的区别。与科学为发现真理可反复试错、纠错、无穷探究相比,法律最直接的目的是解决纠纷,而纠纷必须在当下一定时间内予以终结,不能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17]。基于以上区别,可以说科学与法律是游离关系,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各守其道,互不干涉的。法律对科学属性下的技术标准应该秉持一种消极的尊重立场,保持法律克制,尊重科技边界。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即是框定法律与技术标准的各自边界,坚持法律的归法律,科技的归科技,对于技术标准的问题如果能在科技范围内解决的话,法律不能主动介入。当然,并不排斥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在主动或被动的越界情况下,法律对科技也会起到制约作用,比如技术标准的滥用需要接受法律的规制。就技术标准的人文属性而言,技术标准与法律具有显著的互通性:一是价值立场的倾向性。不同于技术标准科学属性的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技术标准的人文属性要求必须秉持一定的价值立场,比如节约资源的环保性考虑、公众安全的公益性考虑、注重效益的经济性考虑等。而任何法律的出台都必然体现一定的价值导向,比如秩序、安全、效益、自由、正义等。二是关注对象的交叉性。人文属性要求技术标准关注人的需要,理性对待人的需要,注重人的需要与科技水平的匹配,与时空条件的协调。法律的使命是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等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中人的需要是各种关系的核心所在,如何平衡不同层次、种类、时空的人的需要是法律的重点关注对象。三是追求内容的确定性。人的需求是五花八门甚至杂乱无章的,技术标准的任务就是将这些需求由零散变为统一,由模糊变为明白,由概括变为确定。法律的任务与之异曲同工,即为千差万别的个人设置统一、明白、确定的行为模式。基于以上联系,可以说人文属性下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有相当程度的交叉关系,两者价值共享,任务相通。因而,法律对人文下的技术标准要予以适度的介入,协力应对人的需要。在此期间,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即是厘定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的需要的理性范围,将人的需要裁剪转换为人的理性需要,在此基础上尽量确保技术标准理性应对人的理性需要,提升技术标准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就技术标准的法律属性而言,技术标准和法律具有较高程度的重叠,如果采用广义的法律角度,甚至可以将技术标准纳入法律范畴易言之,技术标准包含于广义的法律之中。前已述及,技术标准与法律均属于社会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形式上的规范性、内容上的调控性、效力上的约束性等诸方面分享家族类似的特征,对于社会和个人都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而,法律对法律属性下的技术标准应该而且可以予以积极的规制。在此期间,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即是研究法律对技术标准的程序规制,涉及技术标准的考量因素、参与主体、制定程序、位阶次序、效力层级、司法审查、版权保护[18]等各个方面。
因此,对于技术标准,无论就浅层的法治实践而言,还是就深层的本质属性来说,法学研究都不应刻意绕避,使其沦为法学“荒漠”,而要积极关注,使其成为一方生机勃勃的法学“绿洲”。
[1]GB/T 15497—2003.企业标准体系——技术标准体系[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4:5.
[2]马晓彤.中国古代有科学吗?——兼论广义与狭义两种科学观[J].科学学研究,2006(6):817-822.
[3]胡玉鸿.法学是一门科学吗[J].江苏社会科学,2003(4):167.
[4]冷宇.交通信号灯为何是红黄绿[N].京华时报,2014-03-20(C05).
[5]标准起草小组.商用车辆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编制说明[EB/OL].http://www.caam.org.cn/Files/file/biaozhunfile/1111/zhengqiuyijian-sc11-21-bzsm.pdf,2015-11-05.
[6]人民日报评论员.认真贯彻执行《食品卫生法》[N].人民日报,1983-07-01(4).
[7]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76-78.
[8]刘钢.关于“标准”的探讨[D].南京:东南大学,2005:8.
[9]王世川,马艳霞.小议我国标准与法律的关系[J].标准科学,2012(3):19.
[10]孙笑侠.论行业法[J].中国法学,2013(1):48.
[11]宋华琳.论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从行政法规范体系角度的定位[J].行政法学研究,2008(3):39.
[12]上海市标准化研究院培训中心.如何理解“强制性标准”和“标准的强制性”——我国标准化法律法规体系特色之解读[J].质量与标准化,2011(5):44.
[13]宋华琳.论行政规则对司法的规范效应——以技术标准为中心的初步观察[J].中国法学,2006(6):126.
[14]廖丽,程虹.法律与标准的契合模式研究——基于硬法与软法的视角及中国实践[J].中国软科学,2013(7):170.
[15]克努特·布林德.标准经济学——理论、证据与政策[M].杜邢晔,牟俊霖,李青吉,王晶,译.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68.
[16]王庆廷.审判权的主动性旁落——以估价鉴定为例谈法官的不作为[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9(1):249-256.
[17]孙莉.在法律和科学技术之间[J].科学学研究,2007(4):592-597.
[18]王渊,熊伟红.“技术标准”版权性问题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7(3):8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