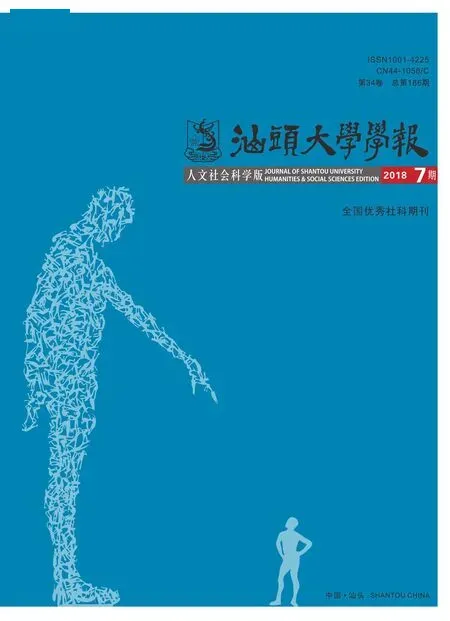论《诗经·陈风》创作及编选意图
2018-02-01程建
程 建
(桂林理工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教学部,广西 桂林 541004)
《诗经·陈风》为何只收《宛丘》《东门之枌》《衡门》《东门之池》《东门之杨》《墓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十首,是个值得考究的问题。诗人希望通过它们反映陈国社会变迁,编选者则希望通过它们“微言大义”。而揭示创作及编选意图,正是《诗经》学的一个方向。从胡公满受封于陈(前1045年)到陈闵公去世(前478年)共计567年间,陈国在“国际舞台”上一直表现“低调”,以致于学术界都不太愿关注它。《诗经》学领域也不例外,既有《陈风》研究,或止步于个案研究,或在巫风问题上纠缠不清。可喜的是,有学者尝试从文字学、文学、文化学角度解读《陈风》。遗憾的是,它们也只是对《陈风》中某一类型诗作作了相对系统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巫风、婚恋、情思、忠臣四个维度,解密《陈风》传递出的社会信息,以及它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一、巫舞成风
陈国本是太昊之墟,地处黄河以南,颍水中游,淮水之北,辖地相当于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亳州。周武王灭商后,封舜后人妫满于陈,是为胡公。为拉拢陈胡公,周武王又将大女儿大姬嫁给了他。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陈国巫舞成风,正与这位大姬有密切的关系:
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吴季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后二十三世为楚所灭。[1]1653
在班固看来,大姬以君夫人之尊,热衷祭祀,重用史巫,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民众积极仿效,陈地巫风盛行,流荡不返,以至亡国。此说对后世影响巨大,解《诗》者亦多从之。只是,将陈国巫风盛行这个社会罪责全推给一个女人,终究有些不“地道”。
即便没有大姬出现,陈国也摆脱不了巫风的影响。陈国是在伏羲、太昊之墟上建起来的,殷商时此为虞遂封地,后来妫满封陈,此地不能不继承了殷商“尚鬼”的风俗。至西周,武王分封诸侯,陈国北则商的后裔宋,西则淮夷,南则荆楚,全是喜欢“装神弄鬼”的国家。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陈国身处其间,耳濡目染,也免不了沾染上巫觋歌舞的习气。只是到了妫满受封于陈,大姬以君夫人身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一天早些来临罢了。
大姬因何“好祭祀,用史巫”?有学者认为,有政治的考虑,“所谓‘好祭祀,用史巫’,是大姬任用史巫,因利乘便,借史巫在陈国当地的威望达到控制陈国国政的目的”[2]57,而“《宛丘》、《东门之扮》二诗是在陈立国之初大姬“专政”的情形下产生的”[2]59。此说应是受了班固《汉书·地理志》季札“国亡主,岂能久乎”、颜师古注“言政由妇人,不以君为主也”[1]1654的启发。照此说法,大姬于周则为功臣,于陈则为罪人。然而,关于大姬专政,无论是地上文献,还是地下考古,都没有直接的证据。且胡公、大姬生活的时代,商纣甫亡,天下观望,周天子也不大可能怂恿大姬控制陈国;而通过《宛丘》《东门之枌》,也看不出陈国“政由妇人”的迹象。可见,“大姬专政说”纯属臆测,而《宛丘》《东门之枌》不必为大姬专政下的产物。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大姬为求子而“好祭祀”:“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诗云:‘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1]3336与先前的政治说相比,此说更胜一筹。毕竟,在我国古代,尤其是贵族家庭里,迫于男尊女卑、母以子贵的残酷现实,女性向神灵祷告求子的例子有很多。
无论如何,巫觋歌舞很快在陈国大地蔚然成风。而透过《诗经·陈风》中《宛丘》《东门之枌》这两首诗,我们仿佛看到当年陈国巫觋歌舞如何盛极一时。先看《宛丘》诗:
子之荡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这是首刺时诗,揭露的是陈国贵族对巫觋歌舞的如痴如醉。关于此诗旨意及创作背景,《毛序》云:“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诗作讲“淫荒昏乱,游荡无度”,诚然;只是将它坐实为刺陈幽公,却有些牵强附会。存世文献中,并没有陈幽公痴迷巫觋歌舞的记载。但诗作既云“子之荡兮”,想必它是针对陈国贵族的了。众所周知,我国春秋以前,只有贵族们可称“子”。试看诗中的这位陈国贵族,他对巫觋歌舞何其投入:忽而在宛丘上,忽而在宛丘下,时而击打着鼓,时而敲打着缶,不分季节,挥舞着羽毛,早忘了尊贵的身份。倘若此种情况当时只是个别现象,也不曾造成社会影响,诗人估计也不会堂而皇之地吟咏它。既然有人煞有介事将它写了下来,说明巫觋歌舞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程度了。
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陈国贵族的积极示范下,越来越多的陈国民众加入到巫觋歌舞的狂欢中来。在欢欣与狂热的氛围中,很容易擦出爱情的火花。且看《东门之枌》:
先是在宛丘纵情歌舞“东门之枌,宛丘之栩”。领舞的是子仲家的孩子,“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后来,贵族们厌倦了,就决定选个好日子,到南方之“原”跳舞。他们打算先在集市会合,女孩子们忙着跳舞,竟忘了纺织,“不绩其麻,市也婆娑”。巫歌唱开了青年男女的芳心,巫舞勾起了青年男女的情欲。有学者即说:“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舞由娱神而转为娱人,其中的性感意味却有增无减。因此舞能刺激人的春心,使人产生对异性的思慕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3]206于是在去南方之原的路上,他们眉目传情、互赠情物,“穀旦于逝,越以鬷迈。视尔如荍,贻我握椒”。通过《宛丘》这首诗,我们看到了陈国的大人君子们一改往日的高高在上,在鬼神面前载歌载舞,不时扭捏身姿的“丑陋”,“洵有情兮,而无望兮”;而通过《东门之枌》这首诗,我们看到陈国贵族巧借祭祀之名,而行放纵情欲之实的“可爱”,“视尔如荍,贻我握椒”。贵族青年们的这些躲躲闪闪的爱情,就像初春时节在旷野里草尖上刚刚钻出来的一丝绿意,等待它的必将是芳草碧连天的春意盎然。
《宛丘》及《东门之枌》作者,只是希望通过它们记录下陈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诗经》编选者则不止于此,他们更想表达的是,陈国巫风盛行,说到底是“乱自上作”。
二、婚恋自主
陈国巫觋歌舞一旦成了气候,就像决堤的洪水,席卷一切障碍。而首当其冲的,正是维系家庭基础与社会秩序的婚姻。《东门之池》这首诗,讲的正是陈人“焕然一新”的婚恋观:
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
东门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与晤言。
这位陈国男子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姑娘:她在东门外的池子里沤麻,辛勤劳作却又无怨无悔;她容貌美丽,又端庄贤淑;当然,她的歌也唱得不错。今天,在我国民族地区,还流行着对歌的习俗:郎和妹在山野对歌,郎把妹唱乐了,她就作了他的新娘。这首诗既讲“晤歌”、“晤语”、“晤言”,又关注她的勤劳,“沤麻”、“沤纻”、“沤菅”,想必是将她当准新娘看待了。关于此诗创作意图,有人说它是为了刺时,如《毛序》:“刺时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贤女子以配君子。”照此说法,作者是陈国一位忠臣,他看到君主终日花天酒地、胡作非为,就琢磨着为他找位端庄贤淑、知书达理的夫人,由她来规劝、约束他。请后宫佳丽来扮演“致君尧舜”重要角色,多少有些异想天开。而“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也更像是当事人语气,而非代作者口吻。如此深情对歌,到头来,却忍心让她作别人的新娘,这种傻瓜世间少有!沤麻、沤纻、沤菅,绝不是贵族的工作,可见与《衡门》不同的是,这首诗的主人公是平民而非贵族。但青年男女甜美的恋情,注定不会被时代埋没。到了南宋朱熹,他便干脆抛开《毛序》的解释,大胆写下“此亦男女会遇之词”[4]82评语,默认了诗中男子的“一往情深”。
在骚动的青春面前,传统婚姻渐趋破碎。《东门之杨》,反映的正是“爽约”的社会问题:
双方约定,黄昏时分,东门杨树下,不见不散。但是等到星星都在天上眨眼睛了,也没等到对方出现,其郁闷可想而知。诗中约会者为谁?是贵族还是平民?等人者是男是女?究竟为何爽约?后来结果如何?诸如此类,诗人全都不讲,他似乎只想突出“爽约”主题。《毛序》作者认为,此诗讲女方撕毁婚约,云“刺时也。婚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郑玄追究女方不至原因,认为是留恋他人,“昏以为期,明星煌煌”《郑笺》即云:“亲迎之礼,以昏时。女留他色,不肯时行,乃至大星煌煌然。”朱熹则认为,此诗并未触及婚姻问题,它只是讲青年男女的一次约会,“此亦男女期会而有负约不至者”[4]82。这看似是稳妥的解读,毕竟,诗文触及婚姻的,也只有“昏以为期”一句(古时婚礼在晚上进行)。问题在于:在作诗的年代,谈情说爱有没有如此肆无忌惮;如果只是普通的约会,诗人有没有必要将它写下来,编《诗》者有没有必要将它收进来。然而青年男女间的一次司空见惯的约会,其中一方爽约,诗人有什么必要“大写特写”呢?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讲,“亲迎而女犹不至”的说法似乎更胜一筹。考虑到在我国古代,婚姻于家、于国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亲迎而女犹不至”,确实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而此诗存在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三、情思跌宕
情思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想关上它可就不容易了。如果说《东门之枌》中的“视尔如荍,贻我握椒”,勾画的是贵族男女之间羞羞答答,那么到了《月出》《株林》《泽陂》,则见证了陈国民众在悠悠爱河中的无法自拔。陈国虽地方狭小,却不乏绝色佳人。她像皎洁的月光,光彩照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陈风·月出》),像出水的芙蓉,清新可爱,“彼泽之陂,有蒲与蕳。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她的一笑一颦,举手投足,美到令人忧伤,“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陈风·月出》)。爱慕他的人,常常夜不能寐,流泪到天亮,“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寤寐无为,中心悁悁”“寤寐无为,辗转伏枕”(《陈风·泽陂》)。以上两首诗中的主人公究竟为谁?他们是贵族还是平民?文献不足,不得而知。但陈国大地春意盎然、情思跌宕的景象,通过以上两首诗,却可以深切感知。而如此大胆讴歌女性的美,肆无忌惮诉说心中的情,在先秦典籍中极为罕见,也难怪封建卫道者要为《陈风》贴上个“淫声放荡,无所畏忌”(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国无主,岂能久乎”杜预注)[5]1125的标签。
陈国“淫声放荡,无所畏忌”,说到底是“乱自上作”。有学者即说:“因为有大姬热衷于此道在前,君主荒淫在后,上层贵族也深受文化熏染,而民间本就有浓厚的巫风和较为开放的婚恋习俗,于是上行下效,自由浪漫之风弥于整个陈国。”[6]199《毛序》说《东门之枌》疾“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说《月出》刺“在位者不好德,而说美色焉”,说《泽陂》刺“陈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悦,忧恩感伤”,其太过征实的做法固不可取,但是将斗争矛头对准陈国的统治者,却没有搞错对象。从《东门之枌》中纨绔子弟含情脉脉,“视尔如荍,贻我握椒”,到《泽陂》中贵族男子为情所困,“寤寐无为,涕泗滂沱”,注定顺理成章。何况,在其中起表率作用的,还有陈国的一位国君,此即陈灵公。在陈灵公的生命里,恰恰出了一位尤物,此即夏姬。她的美不仅致命,害死了三夫(夏御叔、连尹襄老、屈巫)、一子(夏南)、一君(陈灵公),走两大夫(孔宁、仪行父),而且倾国倾城,将陈国推向灭亡。《株林》这首诗,讲的正是陈灵公对她的痴迷: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
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
该诗大意为:陈灵公整天疯狂地想着寡居的夏姬,总是变着法去她家;但是陈灵公身为一国之君,总要注意影响,所以他去株林找夏姬寻欢,不说找夏姬,而说找夏姬的儿子夏南,一路上还要“乔装打扮”,掩人耳目。后来,灵公被夏南射杀,陈国差点儿成了楚国的县。当然,在陈国二十五世国君中,陈灵公这般“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毕竟是个案。但是他的表率作用,却为陈国跌宕的情思加进了一剂催化剂。建国之初,大姬以君夫人身份为巫觋歌舞率先垂范,而今陈灵公君臣为纵欲之风推波助澜,陈国大地自然要“淫声放荡,无所畏忌”了。
四、中流砥柱
陈国国运萎靡不振,风俗破败如此,却两次亡而复兴,延续645年之久,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晋、楚等大国需要它作缓冲;其二是陈国有一批国之干城。这些国之干城既包括“有所不为的”狷介之士,也包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卿大夫。且看《衡门》这首诗: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翻译成现在的话,即:横木为门,可以栖身长住。泌水流淌,可以玩乐以忘饥。吃鱼,不必吃黄河里的鲂鱼、鲤鱼。娶妻,不必娶齐国、宋国的姑娘。其恬淡自然,令经纶世务者窥之忘返!吃得起黄河里的鲂鱼、鲤鱼,有希望娶宋国、齐国的姑娘,可见诗中的这位男子是个贵族。吃黄河里的鲤鱼、鲂鱼,娶宋国、齐国的姑娘,本是贵族特权。现在,诗中的这位贵族男子却要打破这些条条框框。《毛序》认为,这首诗是劝诱君主的,“诱僖公也。愿而无立志,故作是诗以诱掖其君也”。这却犯了穿凿附会的大忌。由谥法“愿而无立志曰僖”,演绎出陈僖公“愿而无立志”,正是《毛序》的一贯套路。而以栖身衡门之下,吃鱼不必鲂、鲤,娶妻不必齐、宋劝诱君主,也不伦不类。所以,清代的方玉润反驳《毛序》说:“夫僖公,君临万民者也,纵愿而无立志,诱之以政焉而进以道也可,奈何以无求于世之志劝之?岂非所诱非其所望乎?”[7]284南宋的朱熹倒是抛开了“诱僖公”的成见,将诗旨归结到隐居,“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4]82。诚然,“自乐”,是诗人最想强调的;但是将这位男子视为无欲无求的隐士,却是理解过了头。诗中男子若是已经“无欲无求”,为何还要念叨着娶妻呢?可见,《衡门》中的主人公并非想隐遁山林,做个“孤家寡人”,他不过是不再执着于吃黄河鲤鱼,娶名门闺秀罢了。然而,在巫风横行,举国如狂的紧要关口,他们却可以抛弃高门广屋、美味佳肴、名门闺秀,而追求高远的东西,“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水洋洋,可以乐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这种“举世混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生态度,在迷醉状态的陈国弥足珍贵,此诗“可谓中流砥柱,挽狂澜于既倒,有关世道人心之作”[7]284。从此以后,“衡门作为诗人择取的与深门大户两相对照的浅陋之地,其简单却自由无羁的特征,成了众多文人安贫乐道、淡泊自守的精神家园”[8]35。
仅凭这些狷介之士的“有所不为”,陈国还不足以六百余年危而不倒,它同样需要“有所为”者。在《墓门》和《防有雀巢》中,我们见识到陈国的国之干城。眼见国运日下,举国若狂,这些忠臣无比心痛。即便君主只当耳边风,他们仍不厌其烦进谏。且看《墓门》:
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
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
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
这显然是首政治讽喻诗,据《毛序》“《墓门》,刺陈佗也。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的说法,它对应的是陈佗杀太子免的史事:陈文公死后,长子鲍继位,是为桓公;公元前707年,桓公病重,文公次子陈佗杀桓公太子免;桓公去世,佗自立为君,于是陈乱。说此诗与陈佗杀太子有关,学术界并无异议。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是,这首诗针对的是陈佗,还是陈桓公。而“夫也不良”这句诗,也就成了揭开谜底的关键。《毛序》指出,陈佗没有好老师教导,才走上了犯上作乱的不归路。《郑笺》顺承《毛序》,解“夫也不良,国人知之”为“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将陈佗的罪恶完全推给师傅,肯定不是作者的本意;为陈桓公、陈佗开脱,也不公平。毕竟,在这桩历史公案中,陈桓公没有提前防范,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而“知而不已,谁昔然矣”、“讯予不顾,颠倒思予”,也更像是忠臣的抱怨之词,抱怨桓公未采纳他的建议,防患于未然。北宋苏辙即说:“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9]386至此,《墓门》作者的、《诗经》编选者掩埋两千年的的苦心重见天日,乱臣贼子始难逃公论。
即便君主没有听进自己的金玉良言,最终吃了大苦头,这些忠臣也不会与朝廷离心离德。在他们看来,君主很容易被蒙蔽,应该谴责的是“君侧”的奸佞之人。且看《防有雀巢》诗:
大意是说:鹊于河堤筑巢,苕于土丘生长,庭院里瓦铺道,土丘上长绶草,全是无稽之谈,心上人反信而不疑。是谁挑拨了我的心上人?我心里愁苦、害怕,又烦恼。有学者认为这是首刺时诗,如《毛序》:“忧谗贼也。宣公多信谗,居子忧惧焉。”对《毛序》此说,汉唐学者无异议。至南宋朱熹,抛弃《毛序》不用,认为此诗不关时事,只是“男女有私而忧或间之之词”[4]83。此说不能说不稳妥,但是未必符合诗旨。如果只是担心心上人误听谗言离间,何须“心焉惕惕”,惶恐不安呢?而如果它只讲儿女私情,诗人何必堂而皇之写出来呢?《诗经》编选者又何必小心谨慎将这首诗收录进来了?即便如此,在我国古诗文中,以男女之情比君臣关系不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吗?仅凭“谁侜予美”,即说它只讲私情,显然难以服众。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毛序》所云并非无根之谈,此诗完全有可能指斥进谗及信谗。只不过,在创作背景上,我们不应太过计较,不必将它与陈宣公捆绑在一起。
结 语
通过以上对《陈风》十首的剖析,我们对陈国的社会变迁应该有所认识:在包括大姬在内的上流人士的“积极”引领下,巫觋歌舞很快蔚然成风;民众对巫觋歌舞的热情参与,尤其是青年女子的大量加入,不仅冲击到这个国家的纺织业,而且由于巫觋歌舞甘作谈情说爱的温床,必然冲击到国民的婚姻基础;在欢歌笑语声中,幽闭的情欲被释放了出来;至陈灵公君臣公开宣淫,陈地遂“淫声放荡,无所畏忌”;幸亏有“有所不为”的狷介之士,忧国忧民的忠贞之士,这个国家才得以在大国夹缝中苟延残喘。由此可见,《陈风》中各篇均有所寄托,不仅有创作者的寄托,希望通过它反映社会现实,而且有编选者的寓意,希望通过这十首诗,为从政者敲响警钟,警告他们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呼吁他们重视“修齐治平”。
诚然,《诗》无达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种对《诗经》的理解。从这层意义上讲,对前人传注,我们不必苛求。只是,我们前边“两千年的《诗》学家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它的真相全给这一辈人弄糊涂了。譬如一座高碑,矗立在野里,日子久了,蔓草和葛藤盘满了。在蔓草和葛藤的感觉里,只知道它是一件可以附着蔓延的东西,决不知道是一座碑”[10]309。所以,本着对诗人、《诗经》编选者的尊重,却必须痛下决心,将这些藤蔓一一斩除。说到斩除的工具,虽然锈迹斑斑,却极其锋利,这就是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