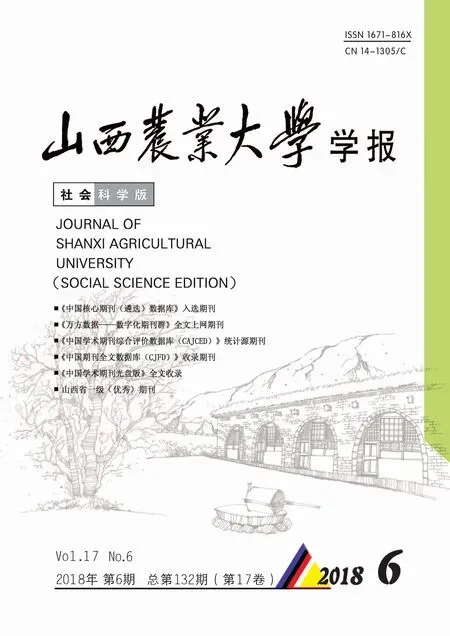传统“年例”与农民闲暇生活
——基于粤西庵里村调查分析
2018-01-31刘勤余柳娟
刘勤, 余柳娟
(1.广东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广东 湛江; 2.广东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秉持“年例大过年”的观念,粤西农民在“年例”期间走亲访友,游神娱神,互动往来,满足了自身的心理诉求,在仪式中实现了神圣和世俗融合共生。本文基于粤西东简镇庵里村的田野,通过文献法、访谈法和观察法获得了相关资料,调查探究年例的闲暇价值。
一、研究缘起
受限于地理区位和人文历史积淀的限制,粤西在相当长的时期属于开拓之地,地域话语权薄弱。史料记载的年例最早在宋代《雷祖志》中略有表述,直到明清时期在高州、雷州等地方方志中才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年例的起端,与当地民众面临频繁的自然和人为灾害时的生存应对诉求密切相关。面对天灾人祸的威胁,年例是民众驱赶邪灵的祈福行为[1]。诸神信仰满足了地方民众群体性的心理及社会需要[2]。
与其他民间仪式活动的经历相似,粤西年例也经历了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和市场化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粤西农民就自发地恢复了年例活动。地方政府推选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保护、传承和弘扬。地方媒体和城乡居民不时报道、分享这一地域特色活动。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研究者对此表达了浓厚兴趣,有了初步的研究积累。
田野调查记叙了年例活动的流程,描述了年例活动的准备、经过、结束三个阶段,呈现了做年例、吃年例、睇年例的内容[3]。直观上看年例活动,研究者认为它以仪式的宏大场面突显了村落的宗族认同, 是宗族的一次盛宴,强化了村落宗族认同[4]。它的兴办是村落社会自组织的结果,涉及到经费筹集、组织者尽责、人员配置、组织管理等,其实施对象、交往互动、规则运用等远远超出了血缘地缘的村落范畴。粤西宝村的调查发现,年例作为仪式公共生活,建构和强化了区域社会,成为维系与整合社会的重要途径[5]。
与粤西农民年例生活的繁盛热闹相比,年例研究成果数量与之不相匹配。利用中国知网文献库,以年例为篇名进行的文献检索,发现从1990年至今,文献库中共有57篇,其中期刊37篇(含报刊11篇),学位论文20篇。
从发表时间看,粤西年例的成果集中在最近5年,且分散在不同学科。就相关文献的主旨看,除去前文所述的年例缘起、年例流程等,还包括年例活动的价值和功能。作为地方性文化活动的年例,具有缩小人际距离、承载多元艺术、丰富村落的文化生活[6]、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价值[7]。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年例具有粤西——岭南文化的品格,在仪式狂欢中实现个人、群体和社会的稳定平衡[8]。田野调查发现年例具有社会认同、娱乐休闲、心理慰藉等社会功能[9]。这些成果或偏好空疏化的宏大叙事,或偏好狭窄的宗族叙事,有待基于厚重经验的“深描”进行论证。
功能主义理论正是通过个人的需要和社会的稳定解释社会现象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年例在当下得以维系和传承的个人和社会需求何在。基于前人功能主义的解释,利用参与式观察方法,调查者进入到农民生活世界,处境化的理解和阐释年例,进而论证年例是粤西农民闲暇生活方式。
二、调研点的基本情况
调查点是粤西东简镇庵里自然村。东简镇位于海岛东部,常住人口有4.3万,东海中线公路横穿全境。庵里村是个革命老区村庄,是东简镇下辖的七个行政村之一。庵里村委会下辖6个自然村,分别是庵里上、庵里下、衔口山、潭水塘、水洋、极角、河沟七个村民小组。庵里上和庵里下是一个自然村落,原名为夏山村,后改为当地人惯称的庵里村(自然村)。
庵里村拥有10800人口,共2700户,皆为余姓,是当地余姓家族中人口最多的自然村。该村面朝大海,水产资源非常丰富,有耕地4850亩,滩涂和海水养殖面积1700余亩。村民传统的生计以水稻、花生、香蕉种植,对虾等海产养殖为主,以培育虾苗、珍珠等闻名。近年来随着东海岛开发区工业发展,村民开始了兼业生存。年轻人到附近企业或市区务工,老年人留守务工,年人均收入5600元左右。
村庄迄今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延续着华南农村神灵信仰的地方性特点,庵里村民信奉的主神是“炎帝鄧天君”(即神话故事中的托塔天王李靖),神像尖嘴脸部黑白相间,脚踩一只麒麟。庵里村民口头相传,这是“炎帝鄧天君”为了收海中的麒麟为坐骑,日夜守在海边,不停吸海水以便擒获麒麟,结果吸成了尖嘴巴,终于擒住了一只麒麟。除了庵里村外,“炎帝鄧天君”也是水洋、衔口山、潭水几个自然中余姓村民供奉的神灵。临岸而居,以海为生,地方神灵就具有了一些海洋气息。
庵里村的年例起源已是个无从追究的谜,最初的年例活动与取悦这位神灵有关。每年农历十月初一,村里举行“扒佛头”活动,在余姓男子中选出一位新“佛头”。这一角色由时间充裕、灵活利索、热心公益的村民担任。次年农历正月十六进行新旧佛头交接,被定为庵里村的年例时间。告知神灵和祖先后,新佛头进行正式上任,负责处理庙内事务,侍奉“炎帝鄧天君”。
作为传统习俗的庵里村年例延续到建国后,和大多数民俗的遭遇相似而遭禁绝。20世纪80年代初期,庵里村恢复了年例习俗。经过数年活动后,村民发现旧历时间不合时宜。年例活动的组织者们——佛头、房长、村干部们(实为村民小组的几个主要负责人)聚在庙里,请神问神后确定正年例日改为正月初四。这个时间降低了村民的经济压力,便于春节前低价采购的物资能够充分使用,也考虑了村内青年农民春节后外出务工和亲朋好友假期结束后工作时间的限制,还避免镇域内的年例扎堆,方便村落间的相互走动。
三、年例中乡村社会的闲暇消费
仪式是一个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概念,它包含着神圣象征和集体世俗。仪式的兴办,需要一定的人群参与,伴随一定的消费。仪式离不开消费,同时一些消费活动本身就是仪式性的。仪式消费就有了神圣和世俗融合共生的层面。年例是宗教与世俗并存的聚集活动,期间提供了特定商品频繁交换的时机,也就出现了伴随年例而来的小型商品集散贸易。这种贸易时间较短,随不同村庄的年例期而流动,又在特定时间相对集中。
每逢年例活动,生活物资消费比较集中,对蔬菜、鸡鸭、鱼肉、虾蟹等总体需求量比较大。生活物资用于祭祀消费和宴请酒席消费。正年例之前,各家户的女性负责张罗准备请神敬神用的三牲和水果。三牲主要是全鸡、猪肉和整鱼。年例活动中,祭祀的食物及分享行为,有着特定的象征意义。三牲显示了祭祀消费较低的等级性和差序性。
宴请酒席的消费量较大。村里各户都要估算客人数量,酒席规模等。普通家庭在庭院和房中摆上3~5桌酒席,每桌8~12个菜品。近年来,价格昂贵的食材也都上了酒席。除了少部分蔬菜自家提供外,大多数食材和物品需要采购。
年例前的消费活动带来了庵里村的市场繁荣,春节和年例的叠加加大了节日消费。虽然生活水平已有较大的改善,日常生活中的村民还是节俭持家为本。但年例仪式的铺张,某种程度的“夸富宴”,是村民求得社会地位认同的表现。
生活物质消费支撑了村内商户经营,一次性碗筷、饮料、烟酒等快速消费品的销售,也带动了碗碟、桌椅、帐篷等物品的租赁业务。就连原本是淡季的餐饮行业,也针对性的提供厨师或包揽酒席的业务。开发区和镇里的超市甚至摆出了年例购物一条街。周围的流动摊贩们在年例期在进村道路两旁摆摊设档,绵延数公里。
服务和文化消费也是年例活动生成的闲暇。年例中请神、迎神和游神环节,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2016年的大巡游比较隆重,参加巡游表演的除了外村本地队伍外,还请了吴川、雷州等地的表演队伍。整个巡游队伍达到1千余人,绵延2公里。村民参加巡游,不太在意能拿多少报酬,认为“能够给神服务是种荣幸”。巡游队伍的扩大还需要向外请人,村里还会宴请一些重要的客人,由此可以看出年例活动的消费已经由个体家庭消费转向了作为共享观念集体消费了。
这些消费的采购和分享过程,“有能力影响我们的信仰,指导我们的行为,能够自我展示,引申出责权关系并带给人快乐”[10]。年例活动引发的各类消费准备不是一次性的体验,需要村民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往返于住宅和市场。村民们相邀一起逛市场,尤其是居家的村妇。她们一起比较各类物资的性价,在选择中感受消费的乐趣;满市场寻找物美价廉的合适物品,和商贩们认真的讨价还价,在节省中获得消费的成就;享受物质丰裕的感官,体验喧闹的场景,在闲暇中获得消费的满足。
因此,村民们安排好家庭的闲暇时间,消费商品和服务。年例消费既是生存所需,也是娱乐所需、慰藉所需。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村消费能力迅速提升,虽未成为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但在节庆和仪式生活中正在形成新的支配权力[11]。年例伴随着消费,这本身就是消闲的一种方式。
四、年例中乡村社会的交往互动
社会交往是人与人之间互动往来,进行物质、精神交流的社会活动。当下的农民社会交往,其范围较少超出血缘地缘关系的交往圈,其形式建立在半耕半工的兼业基础上,其价值以休憩与延续为主。年例引发的社会交往是农民闲暇的时间分配、对象选择和具体内容的填充。
“食年例”是年例活动的重要内容,在食的过程中建立和维系着家庭和村落的社会交往。日常生活中,村民忙于生计,探亲访友缺少时间和机会,而利用年例之期,均可实现。年例活动前,村民通过各种方式邀请自己的村外亲友参加年例活动。90年代以前,邀请的宾客以血缘亲戚居多,数量稳定。如今,邀请的宾客以朋友为主,数量越来越多。同窗聚会也借着年例流行起来,村里年青一代也在建立和维系着自己的小圈子。
正年例的前一天,当地人称之为起年例,进行年例准备的意思。家中妇女准备好拜神用的三牲、酒、香、纸钱、鞭炮等。住得近的亲友,通常是女性,空闲时就会过来帮忙。正年例日,各家带着祭品在指定地点跪拜神灵,祈福平安、道心愿、求吉利。拜神结束后,村民带回祭祀的食物,准备家宴。
据统计,庵里村中等家庭一次食年例的支出预算要3000元左右。而年例的支出又很难从客人送的礼金中实现收支平衡。客人送的“利是”,通常是象征性的,不足以抵消支出,年例给一些平困家庭带来了经济压力,但从长远看,食年例又是互惠互利的,村民做年例,村外的亲戚朋友送了人情,而当村外亲友做年例时,他又去还人情。食年例为亲疏远近的亲友提供了探访机会,巩固了村民的社会网络。
参加食年例的客人数量和酒宴规模,体现出村民的村外关系范围和支持强度。亲友互动往来,在日常生活里分散,在年例活动中相对集中,展现了村民村外社会交往。客人数量越多,体现家庭的社会关系越发达;酒宴规模越大,体现出家庭的经济实力越强。因此,食年例有着身份重构和阶层认可的社会意义。不同层级的村民适应各自的阶层位序,在年例中有着各自的行为表征。
村中富裕阶层财富充足,年例花费数万元是很正常的现象。他们广邀亲朋,借此建立、维系各种社会关系。这一阶层不在乎所获礼金的多少,看重的是年例活动所体现出的村庄身份、实力和社会地位等,这对贫穷的亲友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村庄中间级阶层的农户面临的压力最大。年例活动,他们必须得办,既不能像困难层级那样小办,也不能向村中富裕层级那样大办。降低年例的档次,在大家看来是件寒酸的事情,与村中地位不符。强大的舆论压力,中间阶层的农户家庭就要置办数桌酒席,宴请至亲挚友来祝贺。
村庄底层的农户经济条件较差,实在花费不起就只好放弃。放弃的结果是这些贫困者的社会关系网越来越狭窄,社会交往的能力越来越弱,以至于在其人生的许多重要环节得不到帮助。
年例过程中,村民们的仪式消费关联着社会交往,也形成了阶层认同与阶层间区隔。不同层级交往不仅体现了其经济实力,也体现了他们的文化认同和自我塑造。同一层级的村民家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某种消费、社会交往等投射到对应的阶层中,大家维持基本相似的水平。在仪式消费、社会交往塑造某种层级认同时,村民也借助这类符号表现和传播这种认同。
五、年例中乡村社会的娱神狂欢
年例的娱神狂欢活动带有原始宗教的表征,已历经数百年。村民举办相关的娱乐活动实现人和神灵的交流,获得感官的满足,宣泄生活的不满,表达愿望和诉求,奉送感恩的心灵。
年例中的游神是个庄重神圣的重要活动,有大小之别。大游神是庵里、水洋、啣口山、潭水塘四个自然村(余氏宗亲)联合组织的游神。从9点至14点,千余人沿着四个自然村的大街小巷巡游,历时约5小时。小游神是庵里村单独组织的游神。历时2小时左右,两百余人在村庙请出神灵,绕村内各庙堂宗祠、街巷村道巡游。
正年例日,游神依时出行。游神队伍前有仪仗鼓乐开道,后有各色表演。90年代的游神队伍主要是醒狮、轿队、彩旗队、锣鼓队四部分组成,余姓子孙为主,仪式阵容较为简单。现今,游神队伍逐渐壮大,有豪车组成的轿车队、彩车队、娘子军队、旗手队、令旗队、俊马队、宫灯队、锣鼓队、管乐队、高桩舞狮队、舞龙队,以及邀请而来的吴川飘色、高跷舞龙队和武术表演等。巡游队伍还抬着余氏祖先,随着游神形式多样化,除了余姓子孙外,还邀请了其他姓氏族人。
正年例日早上,村民们在自家门前放张圆桌,摆满祭品。当游神队伍抬着神公经过时,村民燃放鞭炮、跪拜祈福。这个过程即是“摆醮”。他们相信迎神能够祈福驱邪,规避灾害,保佑平安和美、事业有成等。游神队伍经过时,村民还会送红包,数额依各家经济状况和个人意愿而定,红包交给“佛头”,维持神庙的日常运作。
作为地域性、周期性的仪式活动,年例伴随着格尔茨所说的“文化表演”。如果从经济和环境层面看,无疑是浪费和污染环境的非理性行为,但却有着地方性的社会诉求,村内不同阶层的村民积极参与娱神活动,娱神过程中,村民得到放松、充满安全感、心灵得到慰藉。
正年例日的晚上主要以粤剧、雷剧、歌舞表演为主。庵里村的方言是黎话,戏曲多选择雷剧。开演之前,有专人给神公上香、放鞭炮,寓意请神公一同看戏。一些研究常称之为“酬神戏”。这类表演看似用来娱神的,实际已经自然延伸附带产生了娱人的功能。
请神、游神、迎神、送神和晚间的表演活动等,营造了乡村生活的热闹场景。这一过程中,人群喧嚣、活动展开,与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形成了鲜明对比。热闹场景中,村民们暂时摆脱了日常的忙碌,寻找到各自的乐趣,得到身心的愉悦。周期性的年例,不断的强化着族群的集体欢腾和集体记忆。年例在娱神的同时有了娱人的功能,成为受村民欢迎的娱乐活动。
六、结语
粤西年例作为民众社会生活的组成,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别样的闲暇。在消费迈向没有内涵,没有特色,没有个性,缺乏内容的虚无外部实践中[12],年例仪式消费带来了频繁的社会互动和交往沟通,带来了消费的愉悦,它是单调的村民生活的调节。年例活动提供了跨社区交往的机会,展现了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和行为方式,既塑造了阶层分化与区隔,又维系了分化中的社区整合和认同。年例在娱神中提供了娱人的内容,建立起从私人到族群的欢腾记忆。总之,年例活动已充分融入到粤西农民生活之中,成为其闲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着农村社区生活的合理性。
参 考 文 献
[1]吴汉林.谈年例的渊源与展望[J].南方论刊,2010(9):98.
[2]刘岚,张文江.川年例祭祀活动调查报告[J].民俗研究,2002(3):52-64.
[3]蒋明智,吕玉东.乡村社会的人情盛会:以粤西高州的年例为例[J].民俗研究,2008(1):84-99.
[4]周大鸣,潘争艳.“年例”习俗与宗族认同:以粤西电白县潭村为中心的研究[J].文化遗产,2008(1):61-70.
[5]刘勤.公共生活中的自我认同与社会整合:粤西“年例”解读[J].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1(2):26-30.
[6]何火权.关注传统民俗 丰富多元文化:从茂名年例风俗谈起[J].南方论刊,2011(2):92-94.
[7]陈泽豪.浅谈“年例”的表现形态与重要价值[J].神州民俗,2011(4):141-143.
[8]罗远玲.仪式叙事中粤西年例的变迁与当代意义:以广东省茂名市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22-25.
[9]周大鸣,潘争艳.年例仪式与社会功能:以粤西电白县潭村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5-9.
[10]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M].张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9.
[11]陈昕.消费与救赎: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13.
[12]张敦福.迈向“虚无之物”的日常生活消费实践[J].社会,2006(2):159-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