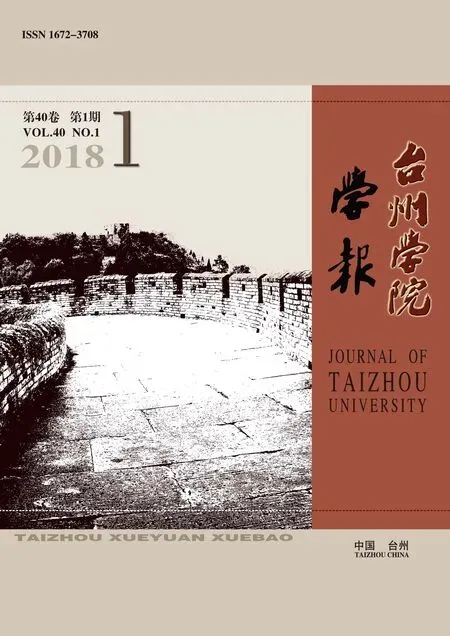《克里特岛的女人》的暴力主题*
2018-01-28赵学峰
赵学峰
(台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二战结束后的第三年,美国诗人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1887-1962)携妻去到梦寐已久的爱尔兰。不料,一旦离开安静悠闲的卡梅尔(Carmel),放下夜可仰望星辰,日可面朝大海的隐逸生活,杰弗斯便觉得非常不适,以至于病倒在旅途中。正是在都柏林住院期间,他开始写作《克里特岛的女人》(The Cretan Woman),该剧改编自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而在此之前的1946年,杰弗斯改编了欧里庇得斯的同名悲剧《美狄亚》。《美狄亚》在百老汇的成功上演可谓是杰弗斯继续改编的动力。1954年,在为诗集《饥饿之地及其它诗歌》(Hungerfield and Other Poems)做出版准备时,杰弗斯又重新修订了《克里特岛的女人》,最终一起出版。
在创作《美狄亚》和《克里特岛的女人》时,战争阴云盘桓在杰弗斯心中,挥之不去。杰弗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这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生活,并促使他建构起“非人本主义”理念。因为一战之故,原本准备定居欧洲的计划被迫夭折,与妻子来到荒蛮原始的卡梅尔,躲避战争,同时躲避喧嚣的人群。然而,一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消散,二战的序幕已经拉开,这场在更长时间、更广地域的人类浩劫刷新了人类伤亡的历史记录。仅仅是五年之后,美国又卷入了朝鲜战争,到《饥饿之地及其它诗歌》出版的1954年,杰弗斯感慨“苦涩徒劳的战争,这场战争什么也没有改变,南北双方还是在同样的边境线上对峙,装满弹药的枪炮随时准备开火”[1]109,此后美国又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到杰弗斯去世的时候越战还未结束。在《血海汪洋》一诗中,他曾写下“两场战争,他们又在孕育第三场。此刻正守卫海滩,警惕北方/怀疑拂晓,探测每一片云朵/积蓄力量。然而美国的要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要矗立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就像是拜赞廷/至于我自己,我同意你,嘲笑我吧。遥望未来并朝它尖叫是一桩愚蠢的事/一个人就应该只看不说……这么多的血海汪洋,我们总是掉进去。”[2]一场比一场更具杀伤力的战争,越来越多的暴力带来重大的伤亡,促使杰弗斯不停地追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弗洛伊德曾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写到,人类普遍具有“除了保存生物并使它加入更大的单位的本能外,一定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相反的本能,这一本能试图分解这些单位,并且把它们带回到它们的原始的,无机的状态。这就是说,不仅存在着爱神厄洛斯,还存在着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一部分死亡本能转向外部世界,以进攻本能和破坏本能的面貌出现。”[3]65-66人有爱和恨两种本能,正如宇宙有“引力”和“斥力”两种力量,二者共同构成并且支配世间万物的运动。“引力”和“斥力”是宇宙的两种本能,爱和恨、建设和破坏,是宇宙中的“引力”和“斥力”在人身上的投影[4]309。死亡本能会表现出侵犯或者自毁,当它转向外部时,导致对他人的攻击、仇恨、谋杀,甚至会派生出民族国家之间的侵略、屠杀或战争等一系列毁灭性行为。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人性的反思似乎有着与杰弗斯不谋而合之处。
在《克里特岛的女人》中杰弗斯虽然凸显了在情欲挣扎中的费德拉的形象(仅从杰弗斯把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更名为《克里特岛的女人》便可了解),但对希波吕托斯和忒休斯的塑造则着重在于表现暴力主题,两人之间上演了最为惨烈的人伦悲剧,借此,杰弗斯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对战争暴力的鞭笞。
一、施暴于自然的狩猎
狩猎和战争都是暴力,前者针对自然,后者针对人类自己,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两种活动或人类行为都需要男性体内一团自由游离的攻击性能量(男性荷尔蒙)来完成”[4]182。雅典国王忒休斯的儿子希波吕托斯一向被视为是贞洁的代表,不近女色,不敬作为爱神的阿弗洛狄忒。爱神最引以为豪的是“我让果树开花,结出甜蜜果实,我让快乐的鸟儿在枝头双栖,我让男子倾心于女子……我让潮水跟随着月亮升落,我让群星彼此相恋,爱上大地。如果没有我存续的力量,它们将在夜的恐惧中分崩离析。”[5]177阿弗洛狄忒不无骄傲的独白恰好注解了弗洛伊德定义的爱之本能——“终生奋力以求和产生的则是生命的复苏”[6]34。爱之本能和性本能,性本能和爱欲其实都一样。“我们的性本能的力比多就以这种方式和诗人们及哲学家们的爱欲都一致起来了,爱欲把一切有生命的事物聚合在一起”[6]38。爱之本能无疑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是生成并延续生命的力量。而贞洁的希波吕托斯不但有意疏远爱神,还嘲笑每棵灌木的背后都藏着偷情的“繁殖狂,令人作呕。至于我,我宁愿把我的热情用在野熊和野马上”[5]178。那些追求爱欲的恋人们,为年轻的王子所不齿。希波吕托斯更愿意把力量用于破坏而非建设。眼见如此一个翩翩少年,不去花前月下浪漫却整日在林间追逐奔跑,阿弗洛狄忒不由地抱怨道,希波吕托斯只在乎跑马,训犬和打猎,耽于与年轻男子的兄弟情深。
如果说希波吕托斯拒绝爱神,是因为他的爱之本能尚未苏醒,那么他的死亡本能则是非常活跃,施暴于自然的狩猎成为他进攻和破坏本能的出口。希波吕托斯一看到他的年轻朋友艾扬就问道,“重箭带来吗?”艾扬回答,“射熊的重箭和射鸟的轻箭都带了,还有箭筒”[5]177。可见,希波吕托斯并非一般消遣性地打猎,打鸟儿或兔子这些小动物,他钟情于射杀猛兽,因为唯有射杀猛兽才能彰显他的男子气概,更能宣泄“自由游离的攻击性能量”[4]182。于是,继母费德拉在引诱希波吕托斯时有意把自己比作为他的猎物,说:“来追我吧,你是伟大的猎手,打猎就是你的生活……你知道小鹿在山间的秘密通道,你知道狼奔向何处,你知道在潮湿的森林里,在暗流深处的岩石上有带斑点的猞猁凝视,她玉石般充满野性的眼睛,像在绿色暮光中燃烧的双子火焰,期待着热血沸腾。”[5]181
如果说,原始初民打猎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是生存的必须,而非逸乐,那人类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为什么还要继续打猎?在欧洲很多国家,狩猎被戴上王室贵族运动的光环,构成了贵族传统的一部分。譬如,在英国,贵族的猎狐行为由来已久,而且得到法律的许可,直到2005年在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压力之下,英国国会通过猎狐禁令才予以禁止。但是,2017年5月英国首相特丽莎·梅,为了满足部分贵族对猎狐的需求,有意讨论终止猎狐禁令的提案,引发大部分英国民众的抗议,首相不得不尴尬地收回提议并且道歉[7]。可见,无论是古代还是21世纪,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总有一些人需要在狩猎中让“自由游离的攻击性能量”释放出来,这个强大而原生的力量需要一个出口,它时而左躲右闪,时而卷土重来。令人可喜的是,即便人类给狩猎冠以无数冠冕堂皇的理由,谴责狩猎动物的暴力行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二、施暴于人类的战争
人们的攻击和破坏本能需要释放,相较于施暴自然,在战场中释放似乎显得更加理直气壮,有时候不但不会被追责所造成的破坏力,还有可能因此得到权力和物质的嘉奖。
雅典国王忒休斯素以骁勇善战而闻名。最早使得忒休斯获得声誉的是在去雅典的路上,还是少年的他勇杀了一队强盗,后来为了获得王位,又杀死了威胁其王位继承权的叔父的50个儿子,此后,他还杀了半人半兽的米诺陶,一路走来,忒休斯双手沾满了鲜血,他用宝剑给自己劈开一条道路,又用宝剑铸就了这个国家。一个好战的国王带给国家的只能是一片凋敝。在《克里特岛的女人》第一幕开场的时候,借王宫外面游荡着的三个女丐(她们随时准备捡拾王宫里施舍出来的东西),可以得知,因为国王忒休斯常年在外征战,国内的民众民不聊生。
内忧外患之际,王宫内也不平静,当王后费得拉引诱希波吕托斯不成,转而向国王忒休斯反咬一口,诬陷希波吕托斯玷污了她的床榻。此时,费德拉只想借忒休斯之手为自己报仇,保留自己的颜面。于是,她不断地挑唆忒休斯:“你这一生杀了多少人,三百人吗?都是亲手杀的吗?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把你当作英雄,把你当成伟人,杀,杀,杀,他们为你树起了塑像。而你却放过了自己的儿子。”[5]192忒休斯禁不住这样的激将,把儿子叫来对质,但未等儿子把话说完,忒休斯血脉偾张,他“缓慢而暗暗地”靠近希波吕托斯,“熟练迅速地抽出剑,从胸骨下方向上挑起”[5]198,希波吕托斯就这样倒在了自己父亲的剑鞘下。
在欧里庇得斯的原作中,忒休斯并没有亲手杀死希波吕托斯,他把儿子赶出王宫,借助海神波塞冬的力量使其殒命。杰弗斯的改编无疑加强了戏剧性,他让忒休斯直接动手,并且让费得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指控嗜杀成性的忒休斯,“以前你杀别人家的儿子,现在终于轮到了自己的儿子”[5]199。和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发动者一样,作为一国之君的忒休斯总能给战争冠以种种辉煌的名义,而其实质都是引发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杀戮,最终嗜杀成性的英雄自己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手刃亲子,而这恰恰是忒休斯未曾预料到的必然。
忒休斯和希波吕托斯父子二人都崇拜暴力,儿子沉迷于打猎,父亲嗜好战争,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是:嗜好打猎的儿子死于嗜好战争的父亲之手,父子相残是人类最可怕的毁灭方式。杰弗斯以此提出警示:人类终将走上自我毁灭之路,这就是战争的最终结果,是人类的可悲之处。
二战后的美国,战争的胜利让上至罗斯福总统下至普通百姓无不欢喜雀跃,而远在卡梅尔的杰弗斯只是冷眼相看,他与胜利的喜悦氛围格格不入,他的悲观来自于对人性的洞悉,那人性中无法剔除的进攻和破坏本能,这种本能会不断寻找突破口,所以战争无所谓胜利或失败,总有下一场战争就在不远的前方。历史上战争的胜利比比皆是,无非是“将军夸宝剑,功在杀人多”,愚蠢的人啊,何喜之有,何乐之有?
三、结 语
欧里庇得斯当年在创作这两部戏剧时和杰弗斯面临同样的问题。《希波吕托斯》和《美狄亚》分别写于公元前428年和公元前431年。彼时正值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欧里庇得斯曾在青壮年时期目睹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晚年时又经历了雅典与斯巴达长达27年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BC.431-BC.404),“他注视着战争的发展,而他能从光荣的假象看到它背后隐藏着的罪恶。”[8]246既看到过得胜后的雅典骄纵狂妄,致力于扩张为帝国,凶狠、残忍、无所不用其极,也遥望到了被打败的雅典众叛亲离,失意落寞,如一个巨人缓缓地倒下。美国作家罗宾逊·杰弗斯继承了欧里庇得斯“永远在审视,永远在质疑的精神”[8]249,以《克里特岛的女人》展现人类在死亡本能的驱使下,对于自然的暴力、人类相互之间的残杀,最终对于人类的延续以及未来表现出极大的忧虑。
参考文献:
[1]Karman,James.ed.,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Robinson Jeffers with Selected Letters to Una Jeffers[C].Stanford:Stanford UP,2009.
[2]Jeffers,Robinson.So ManyBlood-Lakes.[EB/OL].[2018-01-18].https://www.poetrysoup.com/famous/poem/so_many_blood-lakes_4687.
[3]西·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M].傅雅芳,郝冬瑾,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4]赵鑫珊.战争背后的男性荷尔蒙[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5]Jeffers,Robinson.The Cretan Woman[C]//Hungerfield and Other Poems.New York:Random House,1954.
[6]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自我与本我[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7]Fox Hunting:Theresa May Has Pledged to Hold a Vote on Repealing the Ban.[EB/OL].(2017-05-10)[2018-01-16].https://www.peta.org.uk/blog/fox-hunting-theresa-may-has-pledged-tohold-a-vote-on-repealing-the-ban/.
[8]汉密尔顿.希腊精神[M].葛海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