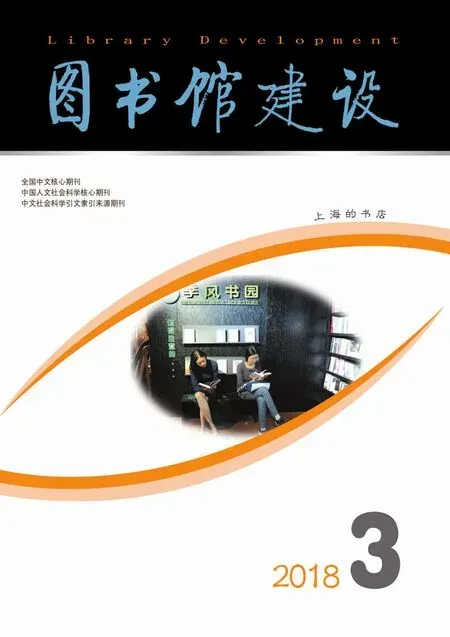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进展*
2018-01-26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浙江杭州310053
田 蓉 (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浙江 杭州 310053)
唐 义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大学数字图书馆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2)
1 研究背景
在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背景下,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导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政府改革浪潮席卷全球。与此同时,除政府以外的第二、第三部门在资金、技术、管理、服务等方面蕴含的极大能力及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逐步凸显,这为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新视角。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是将文化资源以数字化的形式加工、存储,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使用的产品和服务,它是信息环境下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形式。政府管理下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与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以充分发挥后者在数字资源建设、信息技术支撑、营销与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满足社会公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维护公共权益,促进文化繁荣。
从政府治理相关理论的提出,到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财政部、新闻广电总局、体育总局起草的《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内外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不断丰富,其中也包括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研究。本文聚焦于除政府以外的第二、第三部门,如企业、行业协会、基金会、学校、科研机构、非营利性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研究进展,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策略、供给模式、参与途径、支撑理论等进行系统梳理,以期对后续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概况
本文运用文献调研的方法,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含SCIE、SSCI、A&HCI、CPCI数据库)与CNKI数据库为数据源进行主题词组配检索,主题词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合作”“information service*”“public /private”,剔除无关数据共得到相关检索结果62条。笔者在文献调研中发现,论述国内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项目,如世界数字图书馆(World Digital Library)、欧洲数字图书馆(Europeana)、澳大利亚(Trove)检索等的文献中同样也包含社会力量参与的研究,因此,再次在数据库中重新检索得到其他相关主题文献19篇。
笔者对论文进行详细阅读分析后发现,国外较早开始了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的相关研究。1982年,美国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简称NCLIS)就针对公共与私营部门在信息服务中的角色定位展开了调研[1]。从研究主题看,国外文献较多从数字文化遗产项目建设实际出发,论述社会力量与政府机构合作共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方法与途径。21世纪初,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市场准入与社会化协作机制,如王远均、赵媛探讨了数字图书馆产业的市场准入原则与制度[2]。随着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社会化问题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2015—2016年,该主题的研究达到高峰,研究的问题逐步细化,如肖希明和完颜邓邓分析了国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多种社会参与模式[3]。此外,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理论支撑、参与途径、问题与改进策略也得到了广泛关注。
3 研究主题分析
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涉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的理论基础、必要性、供给模式、参与途径、问题及策略等方面。
3.1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理论基础
3.1.1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治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主张引入竞争机制,对公共部门进行市场化改革,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提供了理论根基[4]。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导下,政府作为行政手段的掌控者仍然居于公共文化事业管理的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随着公民意识的崛起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弊端的暴露,治理理论逐渐兴起。莱斯特·M·萨拉蒙认为,现代公共问题需要高度的协作,政府应该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新政府治理”[5]。吴理财等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以“政府治理”代替“政府管理”体现了“文化治理”理念,文化发展应依靠公共部门跟私营机构、自愿与非营利团体组成的复杂网络[6]。肖希明、完颜邓邓认为,治理理论主张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提供了理论支撑[3]。
3.1.2 多中心理论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公共文化服务的多中心主义是传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分野。张金岭调查分析了法国行政管理去中心化和具有地方分权特色的多层次、多中心的公共文化制度体系[7]。黄粤参考了Rose Richard提出的“社会总福利应是家庭、市场和国家提供的福利混合”[8]这一理念,并以公共文化福利的概念诠释了公共文化需求的社会供给,认为公共文化福利作为社会福利之一,不应该由政府唯一提供并支配,应由民间社会共同参与[9]。多中心理论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表明,传统的政府“单中心”管理模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
3.1.3 资源依赖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资金、技术、人力、物力等多种资源的依托。正如资源依赖理论所说的,每个组织都需要通过与外部合作,从而获得自身不具备的资源,以支持其核心业务的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通过社会力量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工作效率,这与社会资本理论有着良好的契合性。完颜邓邓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分析了政府与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文化资源建设、技术资金、服务覆盖、活动宣传等方面的不足,指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要求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突破自身条件的局限,通过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外部环境进行互补性资源与能力的交换,实现互利与双赢[10]。陶国根探讨了社会资本理论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契合性。社会资本理论包含的社会普遍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3大核心要素,能够促使社会资本的优化整合,推动现代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11]。
3.2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必要性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受社会环境因素与自身发展需求双重影响,目前研究文献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分析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必要性。
3.2.1 有效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
公共数字文化产品在政府或者市场支配条件下,往往因他们各自活动方式的特点或任务的复杂性致使公共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和公共文化资源的浪费。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由于处于垄断地位和其庞大的科层体系,使得服务成本损耗大而服务效率不高;市场又因其追求绝对利润无法弥补政府在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中的功能缺失[4]。政府与市场的双失灵导致公共文化产品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配置不均[10],造成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供需矛盾。社会力量以其灵活、高效和公益性的特点,作为政府与市场间的新参与主体,能够有效弥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不足。
3.2.2 社会力量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孟令国、高飞分析了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动因,认为内驱动力是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事业的主要动力。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的责任意识和参与精神不断增强,会根据自身能力自发地提供文化产品[12]。莱斯特·M·萨拉蒙将非营利性组织、基金会、社区公共文化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定义为“职业公民”,他们接受专业培训,有意愿和义务为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工作[5]。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维系自身发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必然选择。
3.2.3 实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益最大化
柯平指出,传统的公共文化机构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社会组织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拥有资金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营销优势,更了解用户需求,与传统的公共文化机构可以形成优势互补[13]。“政府出钱办、群众围着看”的政府垄断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用户需求相差甚远。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引入竞争机制,将具备实践能力与操作资质的社会主体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大循环”,能够加强良性竞争,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益[4]。
3.3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国内外研究学者将目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供给模式主要分为3种:政府主导型供给模式、社会力量主导型供给模式与合作共建型供给模式。
3.3.1 政府主导型供给模式
张金岭调查研究了法国的公共文化社会治理模式:法国在公共文化治理中不断进行制度改革、倡导多元协作,但是政府始终坚持其主导地位,这与法国政府的国家责任意识较强和法国政府作为国家集体利益的监护者这一社会普遍价值取向有关[7]。徐昌义、李洁对成都市公共文化创新服务实践进行了研究:成都市建成了政府主导下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格局,形成了“政府+企业”“政府+社会组织”“政府采购+市场化运作”“政府+志愿者个体”等社会化参与模式[14]。肖希明、张芳源探讨了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合作存储模式,并认为以传统文化服务机构主导,企业、信息研究所等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的“主导—参与”模式是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合作存储的主流模式之一[15]。
3.3.2 社会力量主导型供给模式
美国、德国由于没有强势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因此形成了社会力量主导型的供给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主要以政策法规鼓励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企业、个人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营造良好的公共文化生态[4]。企业等营利性组织提供有偿服务,社团、协会等非营利性组织参与无偿服务。不同参与主体也会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不同的服务范畴,如专业化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社团举办公共数字文化活动、公民个人根据不同的能力与职业背景进行文化事务管理与建设[16]。
3.3.3 合作共建型供给模式
合作共建型供给模式通常是在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通过半官方的组织进行沟通协调。郑丽萍介绍了以英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政府与民间共建的“分权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文化艺术基金管理组织,如英国的博物馆委员会、美术馆委员会、大不列颠艺术理事会等承担了文化资源分配与管理等职能[4]。吴理财等认为,合作共建的政府与民间“分权”管理模式可以划分为垂直和水平两种“分权”维度;“分权”模式促进了文化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公共文化服务管理权限向地方和民间组织的扩展[6]。
3.4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途径国内外关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案例研究的文献中均论述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多样化途径,笔者认为可以划分成以下4种。
3.4.1 提供资金支持
肖希明、杨蕾分析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项目的资金保障制度,并指出政府拨款在项目建设中并不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基金会、企业、组织机构、个人等的赞助与捐款是资金来源的重要方面[17]。曾琴、蒋文昕以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和新媒体中心(CHNM)为例,总结了社会记忆数字化项目构建的经验。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斯隆基金会(Alfred P.Sloan Foundation)、卡瑞斯基金会(Samuel H.Kress Foundation)等机构对该项目提供了经费赞助[18]。英国区域性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Sense of Place South East(SoPSE)聘请了专业的融资专家对项目发展进行长远规划,努力通过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从而获得充足的资金保障[19]。可见,社会力量提供资金支持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3.4.2 组织文化活动
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四部委起草的《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将组织与承办文化活动列入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相较于政府机构而言,社会组织更了解社会公众的需求,在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活动中能够用多样化的形式促进数字文化资源的建设与传播。李晓秋介绍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内蒙古分中心联合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举办的“感受数字文化,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数字文化资源推广活动的情况[20]。在“美国记忆”项目建设之初,美国国会图书馆也与美国科技公司合作开展了“全国数字图书馆竞赛”,鼓励社会公众贡献更加丰富的数字文化资源[21]。
3.4.3 开展商业合作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引入市场机制的途径包括业务外包、特许经营等。政府可以灵活应用多种政策工具,如贷款、担保、合同、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税收优惠、代金券等,与社会机构形成合作关系[5]。杨松认为,在我国当前政策背景下,应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模式,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应尽快在项目设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责权利分解、项目合作方式、特许合约文本等方面进行规范[22]。WeseniTemesgen A.等运用软系统方法,分析了公私伙伴关系PPP模型的软性因素,为埃塞俄比亚地区构建更高效的公共信息服务传播机制提供了参考[23]。案例研究同样表明国内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项目已经开始了市场化运作模式。杜洁芳介绍了国家数字文化网项目与中国文化传媒网在互联网硬件设备托管、软件系统开发设计、网站建设中开展的全方位合作[24]。王艳翠调查了澳大利亚Trove检索项目的社会合作情况,Trove与Gale和RMIT两大数据库商开展的数据资源访问合作,大大扩展了社会大众能够访问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规模[25]。
3.4.4 共建数字资源
政府与传统的公共文化机构只有与社会力量合作共建数字资源才能真正提高资源建设的广度与深度。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可以广泛调动用户的力量,利用社交媒体工具为用户建立互动交流和贡献内容的平台,促进资源发现与共享[3]。世界数字图书馆(World Digital Library,简称WDL)、欧洲数字图书馆(Europeana)、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简称DPLA)等项目都直接从社会组织和机构获取资源[10]。欧洲数字图书馆(Europeana)与谷歌公司合作,将60万卷历史书籍数字化并提供获取[26],大大提高了资源建设的效率。参与数字资源建设同样有利于社会力量自身的发展。Elizabeth M.Celi和Richard E.Moore Jr.指出,鼓励公私伙伴关系(即PPP)和社会青年力量参与制作欧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纪录片和数字操作手册,不仅有利于人类文化的长远开发与保存,而且能够提高社会青年就业率和促进公私伙伴关系的发展[27]。
3.5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对策
社会力量与传统的文化机构合作进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时必然会遇到一些新问题,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发展策略。
3.5.1 健全政策保障机制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首先需要法律政策的推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完善的国家税法、公共文化机构的专门法律、行业协会的战略规划、公共文化机构的政策,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提供了多层次的保障。我国近年来颁布了一些宏观政策,未来需要对行业和文化机构层面的微观政策进行细化[3]。
除了法律政策体系保障以外,政府还应健全社会力量参与的财政税收管理体系。采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以奖代补等多种投入方式[17]。周宜开认为,应给予民营中小文化机构与转企改制的国有经营性事业单位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28]。梁立新认为,应设立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公共文化发展基金;同时采取信贷优惠政策,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实行差别化等利率政策,提高信贷业务工作效率和服务层次[29]。
3.5.2 支持社会力量自身发展
培育文化类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能力是提高社会力量自身“造血”能力的保障。柯平认为,应该加强对文化类社会组织的培训,提高社会组织自身竞争力[13]。冯雨晴认为,应加强人事管理,积极招募优秀的专业化人才,提高社会力量的专业化水平[30]。徐昌义、李洁提出应重视文化志愿者队伍的发展,加强高校和军队的文化志愿者队伍素质,借鉴国外经验,形成稳定和可持续的文化志愿服务队伍[14]。在鼓励社会力量自身发展的同时,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将其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纳入政府采购范畴,并且通过评选奖励、土地优惠等激励措施满足其发展需求[4]。
3.5.3 做好绩效评价与监督管理
绩效评估与监督管理是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蔡秀云、张晓丽指出,建立科学的供给效应识别机制能够更好地把握政府对文化类社会组织扶持的方向、重点,是实施有效的财政激励的重要依据[31]。在进行社会文化机构的管理时,应当建立有效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对信誉好、绩效高的优秀社会组织给予表扬与优惠支持,对存在问题的社会组织也要提出整改要求,实现规范化管理[13]。
4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研究特点
4.1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日益受到关注,研究主题不断细化与深入。
国外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的探讨开始较早,而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2010年以后。2010年以前,国内更多地聚焦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必要性、公私合作的基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的重大意义等主题的研究探讨。201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颁布后,该领域的研究日益增多。学界在探究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支撑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各类社会主体的参与途径,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的供给模式和未来发展策略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4.2 研究主题呈现跨学科的特点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社会组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问题,与公共管理学科相关,主要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公共事业管理的社会参与机制、公共财务管理等方面;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则与图书情报学相关,包括数字资源建设、信息系统构建、信息组织与服务等方面。目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的论题综合运用了这两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进行跨学科研究。
4.3 注重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效率
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效率既是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出发点,也是新政府治理的目标。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支撑理论研究是基础;对社会组织参与方式和社会化供给模式的研究有利于扩大数字文化资源建设的规模,提高资源建设的技术水平;对社会化发展对策的研究能够明确未来社会化参与的导向,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效率。
5 未来研究的方向
5.1 把握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建设特点进行深入研究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虽然有一些单独论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的文献,但是许多关于社会力量参与主体、参与途径、供给模式的研究仍然是在公共文化服务这一大主题下开展,没有凸显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收集、数字平台建设与维护、数字资源服务与推广的特点。未来研究应该在公共文化服务这一大框架下对数字文化服务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调查与分析,从而指导实践的创新与发展。
5.2 注重国外理论研究成果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
国外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的研究开始较早,治理理论、多中心理论等在国外也有了较为成熟的经验。相较于美、德等国而言,我国在公共数字文化的建设中仍以政府为主导,各种政策工具的使用也正处于摸索阶段,因此要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力量的发展规模、专业技术水平、社会大众的数字文化需求等实际情况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的研究,提出推动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策略。
5.3 开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体化研究
目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研究主要分为理论性研究和实践案例研究。关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社会化的支撑理论和必要性研究大多以宏观性的论述为主,而关于参与途径、供给模式的实践案例研究大多停留在阐述现象的本身,鲜有对国内外发展现状的系统调研及一般规律总结的文献。我国在宏观政策的推动下,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探索刚刚起步,应该加强从实践到理论的规律性研究,以期对实践提供指导。
[1]Hernon P.Public Section/Private Sector Interaction in Providing Information Services[R].Washington,D.C.:ERIC Clearinghouse,1982.
[2]王远均,赵 媛.数字图书馆产业市场准入的意义、原则和制度[J].图书馆杂志,2004(3):12-18.
[3]肖希明,完颜邓邓.国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社会参与模式及其启示[J].图书馆,2016(7):26-30,48.
[4]郑丽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2:8.
[5]萨拉蒙.新政府治理与公共行为的工具: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09(11):100-106.
[6]吴理财,贾晓芬,刘 磊.以文化治理理念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85-91.
[7]张金岭.社会治理视域下的法国公共文化服务[J].学术论坛,2016(11):156-162.
[8]Richard R.Common Goals but Different Roles: The State's Contribution to the Welfare Mix[J].The Welfare State: East and West,1986:13-39.
[9]黄 粤.吴川市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4:6.
[10]完颜邓邓.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社会合作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6(3):55-60.
[11]陶国根.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5(40):55-60.
[12]孟令国,高 飞.公共文化发展的社会推动力研究:以浙东南地区为例[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944-949.
[13]柯 平.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机制[J].图书馆杂志,2015(11):13-15.
[14]徐昌义,李 洁.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力量参与研究:以成都市创新实践为例[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5(6):63-66.
[15]肖希明,张芳源.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合作保存模式研究[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4(2):37-44.
[16]肖希明,完颜邓邓.治理理论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社会参与[J].图书馆论坛,2016(7):18-23.
[17]肖希明,杨 蕾.国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宏观管理及其启示[J].图书与情报,2015(1):2-8.
[18]曾 琴,蒋文昕.社会记忆视角下的数字档案馆建设:以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和新媒体中心为例[J].浙江档案,2016(8):15-17.
[19]Yeates R,Guy D.Collaborative Working for Large Digitization Projects[J].Program:Electron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s,2006(2):137-156.
[20]李晓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谱写社会和谐曲[J].图书馆建设,2008(2):103-105.
[21]American Memory.Mission and History[EB/OL].[2017-07-20].http://memory.loc.gov/ammem/about/index.html.
[22]杨 松.积极探索和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式)——关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图书馆)服务专题访谈[J].图书馆杂志,2015(11):9-11.
[23]Weseni T A,Watson R T,Anteneh S.A Review of Soft Factors for Adapti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o Deliver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Ethiopia:A Conceptual Framework[G].Addis Ababa:IEEE,2015.
[24]杜洁芳.增强互动效应促进合作共建:国家数字文化网建设服务工作迈上新台阶[EB/OL].[2017-07-20] http://www.ccdy.cn/xinwen/gongong/xinwen/201512/t20151202_1167963.htm.
[25]王艳翠.资源共享在澳大利亚之Trove范围扩展:澳大利亚图书馆界的电子资源共享[J].图书馆杂志,2013(7):68-74.
[26]国家图书馆研究院.欧罗巴那数字图书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与谷歌公司合作推进欧洲文化遗产向公众开放[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4(6):76.
[27]Celi E M,MooreR E.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Youth Employment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G].Granada:IEEE,2015.
[28]周宜开.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J].前进论坛,2011(10):28-29.
[29]梁立新.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价值体现与机制创新[J].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3):88-92.
[30]冯雨晴.关于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研究[J].法制与经济,2014(4):126-127.
[31]蔡秀云,张晓丽.社会组织供给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激励研究:基于因子方法的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15(3):8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