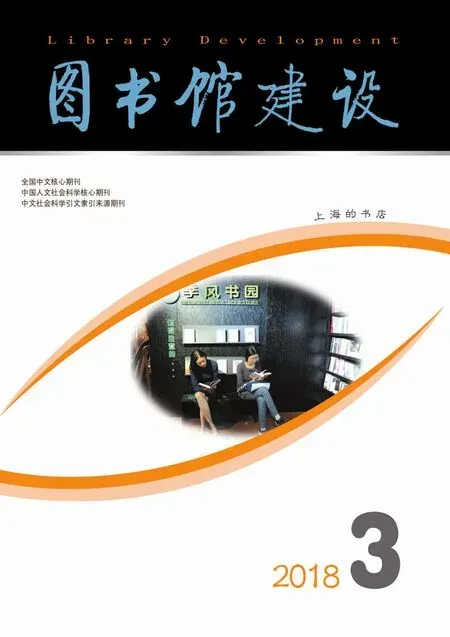嬗变与复归:图书馆智慧与服务研究探析*
2018-01-26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四川南充637009
郎 筠 韩 亮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 四川 南充 637009)
1 引 言
近百年来,智慧与服务一直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早在20世纪初,韦棣华创办文华图专时,就将它作为校训,赋予了学校崭新的时代精神和永恒的灵魂。此后,以智慧与服务(Wisdom & Service)为代表的文华精神历经沈祖荣等几代图书馆人发扬光大,成为留给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宝贵财富。
文华肇始,意在以图书与知识开启民智,用聪明才智为社会服务,在沈祖荣的主持下确立了“研究图书馆学,服务社会”[1]的宗旨。可见,文华校训立足于启迪民智的文化机构,服务民众的社会事业的定位,有着深刻的立意和明确的所指。步入21世纪,在各种新理念、新技术的冲击下,图书馆智慧与服务研究快速蜕变。既有学者如程焕文等坚定秉持文华校训,为此奔走呼号,力图重塑以智慧与服务为核心的图书馆精神[2],又有学人在知识服务研究背景下,将智慧与服务合二为一,生成智慧服务概念,如梁光德提出要将知识服务升级为智慧服务[3];傅荣贤主张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转向智慧之学[4];黄幼菲认为公共智慧服务是图书馆知识服务的高级阶段[5-9]。智慧图书馆研究兴起后,学人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提出智慧化服务新体系,如严栋认为智慧图书馆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智慧化服务和管理的新模式[10];董晓霞等主张智慧图书馆是感知智慧化和服务智慧化的综合[11];乌恩提出智慧图书馆是以智慧化设备为手段为用户提供智慧化服务[12];王世伟则指出互联、高效、便利的智慧图书馆可以带来更高的服务质量,培养更多的智慧公众[13-16]。
不难看出,不同时期的不同研究者依据不同的研究背景与发展环境,不断转换研究重点,提出各种新思考,影响着图书馆学人的观念,塑造着新时代图书馆的服务与管理理念。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华校训的本来面目却逐渐模糊。如果说基于智慧与服务本体的研究带有浓厚的原教旨主义色彩①,那么基于知识服务升级的智慧服务与基于新兴信息技术的智慧图书馆研究,经过概念衍生已偏离智慧与服务的本义。这反映出在信息环境影响下,图书馆服务从稳定化常态向多样化动态的演变历程。但这种演变是否必然导致图书馆核心价值发生变化?不同阶段智慧与服务的研究基点存在哪些异同?新环境下文华校训是否价值依旧?本文以“智慧与服务”“智慧”“服务”“智慧图书馆”“智能图书馆”等检索词,通过CNKI梳理了1990年1月至2017年7月的相关文献,分别以本原、解构、异变3种范式予以总结,以期为新时期智慧与服务研究及实践获得有益启示。
2 智慧与服务研究的嬗变
2.1 期望与憧憬:智慧与服务的本原
现时学人论及智慧与服务,多将之视为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精神传统。然而考镜源流,这一精神却并非源自中国传统的藏书文化,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舶来品。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的藏书楼重藏轻用,图书仅为特权精英阶层独占,鲜有民众能获其益。近代意义的中国图书馆是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其中,文华公书林创始人韦棣华女士的贡献值得一书。
1899年,韦棣华女士初临中国,面对社会破败、民智未开的现状萌发救济之意。为实现匡济民生、启迪民智的宏愿,她引入西方图书馆的先进开放思想,着力创办文华公书林。“公书林者,民众化之公开的图书馆也”[1],即通过图书的共享与阅读满足民众对知识的渴求,以此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为了持续、广泛地发展图书馆事业,韦棣华将人才养成视为重中之重,培养了一批专业图书馆人才,开启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先河,被黎元洪誉为“中国图书馆运动的王后”[2]。
在韦棣华影响下,沈祖荣毅然投身文华公书林,践行以图书馆事业实现教育救国与教育强国的理想。他认为,国难当头图书馆应当担负起“前方将士精神粮食的供给”“受伤将士休闲教育的顾及”“难民的教育”和“一般民众的教育”职责[17]。受强烈爱国精神驱使,沈祖荣将基督教理念融入图书馆事业,凝练出“智慧与服务”作为文华图专校训,“以求唤起爱校观念及求学精神,使知有所趋向”[18],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中极具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事件。在文华精神鼓舞下,经过沈祖荣30余年不懈耕耘,培养出大批图书馆学专门人才,其中多数不仅常年从事图书馆工作,更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毛坤曾感慨道:“图书馆事业至为繁苦,自朝至暮,饮食而外,无休息之时。且在今日图书馆员者,地位低微,报酬亦啬。见异思迁之士,鲜有能忍受之者。而文华图书科诸同学,安之若泰,且益发奋,其忠于所学,为何如哉?”[17]可以说,如果没有以智慧与服务为代表的文华精神的强大感召,无法想象有多少后学愿意踏入冷僻的图书馆学,更无法预期裘开明会因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默默无闻的工作而饱受赞誉。
从文华系创业开拓的经历不难发现,虽然大的时代背景略有不同,但无论是创办人韦棣华还是后继者沈祖荣等,均将启迪民智视作图书馆事业的目标,并以馆员的聪明才智于潜移默化中服务社会、教化民众,实现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从这个角度讲,文华校训中智慧所指有两个基点,一是作为客体的民众智慧,二是作为主体的馆员智慧,而将两者串联,实施主体对客体教育功能的则是图书馆服务。完美的闭合设计体现了那一代图书馆人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未来发展的美好期望与憧憬,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
日后,程焕文在阐释文华校训时,认为智慧是《圣经》中世人孜孜以求的美好事物,与沈祖荣倡导的图书馆精神高度契合;图书馆作为文化教育服务机构,本质属性在于服务[19]。服务是馆员的天职,馆员的智慧决定了服务的优劣。“如果图书馆员不以服务为本,图书馆的一切建筑、藏书、设备、技术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图书馆员没有足够的智慧,图书馆的一切服务也就没有多大的社会价值。”[19]以此为基础,他进一步构建了图书馆精神的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呼吁扭转因精神缺失导致的图书馆发展“整体非理性”状态[20]。
或许是程焕文的系列论述精深缜密,对智慧与服务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阐述,尤其是将“智慧与服务”作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训后,业界美誉度颇高,一时间持异议者甚少,且无人能出其右,故而曲高和寡;亦或是智慧与服务这样一个带有浓郁哲学色彩的话题阻滞了后续研究持续跟进,21世纪以来,真正从智慧与服务本体展开的研究并不多见。但得益于程焕文将智慧与服务升华为图书馆精神的高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王凌云从该角度切入,响应重塑图书馆精神的呼吁,确立了提高馆员素质、丰富智慧、优化服务3项重点[21];沈俏梅从倡导图书馆精神,树立职业意识、服务观念,掌握科学方法入手,提出有智慧的服务[22];王雪玲从馆员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出发,论述了做智慧型女馆员的必要性[23];阴月华从知性智慧、理性智慧、情感智慧、实践智慧4个维度探讨了馆员智慧的生成途径[24];齐凤艳将国学经典与馆员的智慧、精神作了一一映射[25];张玉文主张转变馆员服务观念是实现智慧服务的前提[26]。
以上研究多从职业精神、价值理念视角强调馆员智慧这个基点的重要性,注重馆员人文精神、心灵智慧的塑造,提倡以馆员智慧提高服务的内在品质,在服务中体现馆员智慧的魅力。王杉[27]、张延贤[28]、王梅[29]将之归纳为理念性人文智慧,但纯粹基于人文理性对智慧的概念、价值展开分析论证,从而得出“拥有智慧,才能发挥智慧”[22]的结论,未免流于表面。加之由于缺少实证研究,更多意义上是一种精神、理念的呼吁,也增加了论点落地的难度。
值得一提的是,燕辉等人[30]及刘秋让等人[31]从价值论和学科服务视角对智慧与服务作了全新解读。新解读融入技术维度,对智慧与服务价值链进行重构,指出馆员能力增长、信息技术应用、用户智慧增进三者共同构成图书馆智慧,化解了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长期存在的对峙问题,并结合学科服务的发展瓶颈,提出构建基于馆员智慧的学科服务能力。这既是对文华校训的精益继承和发展,也凸显出实体服务场景支撑下研究的应用价值。
2.2 衍生与虚化:智慧与服务的解构
如果说倡导重塑图书馆精神是忠于文华校训的本义,那么试图改变智慧与服务宽泛的理念性认知,在知识服务基础上衍生出的智慧服务则是对智慧与服务本义的虚化。或许在早期的一些论述中也体现了智慧服务的理念,但首先将其提炼出来作为独立概念展开研究的应属刘志勇。2004年,他提出智慧服务是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环境下形成的新型服务理念,馆员的文化素养、知识组织、信息管理、网络导航、智能重组能力是其主要内涵[32]。该文虽然主张将智力资源纳入图书馆管理,却短于提出可行性方案,立论与同期馆员能力建设相关论点大同小异,目的是为图书馆确立知识管理模式、开展信息增值服务奠定理论基础,因而整体并没有跳出知识管理的范畴。随后,梁光德、黄幼菲以此为核心,从概念、特征、本质、内容等方面将智慧服务与知识服务展开对比[3],提出公共智慧服务是知识服务的高级阶段、是知识服务的扬弃和飞跃,转知成慧应取代知识服务作为图书馆核心价值等系列论点[5-9]。期间,有学人意犹未尽,深觉仅从服务角度谈论智慧远不足以提升图书馆学的学科价值与社会地位,进而主张图书馆学应从知识之学走向智慧之学[4],建立面向与通往智慧的图书馆学科体系[33],实现智慧修养观的学科转进与职业突破[34]。由此形成了馆员智慧—图书馆智慧—图书馆学智慧的递进升级,完成了对智慧与服务本义的解构。
然而,这种解构却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概念厘定模糊不清。梁光德为了将知识服务引向智慧服务,在概念界定上使用“一般性”和“创造性”[3]来加以区分,剥离各种修饰性词语后作者所谓的智慧服务即创造性知识服务。该定义不仅本体并未脱离知识服务,在本质上更看不出与知识服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从黄幼菲“公共智慧服务就是对知识的本质及知识之间的关系进行有序的揭示,防治信息污染、信息虚假”[6]的描述中,不仅看不出所谓公共智慧服务与知识服务的区别,就连文献服务也难以从中区分开来。但作者却以此为基础,结合知识“已沦为力量和金钱的奴隶”[7]的物化论,梳理知识服务研究流派的观点,尤其是王宗义[35]、王均林等[36]、段小虎[37]对知识服务的批驳意见,认为知识服务存在视野狭隘、无法普惠大众、理念冲突严重、无法实现人的终极关怀等缺陷[38],反映出图书馆核心价值分散、含混、浅薄,未能揭示图书馆的智慧本体属性[8],推导出以转知成慧为核心价值的公共智慧服务是知识服务进化的必然,试图实现上位概念对下位概念的包容,以此回避知识服务研究中的诸多争议。
其次,论证推导松散失范。虽然梁光德也从知识服务与智慧服务的关系、特征、内容上展开深入分析,但在论证时把前者定位于基础的知识组织、共享与传递,而将后者拔高为知识的生产、开发与创造 ;基础知识归于前者,专业知识则归于后者[3]。且不论这种拔高是否科学,归类是否简单粗暴,也不论这种划分是否割裂了完整的知识服务链,更不论知识服务是否只具备单向度的工具理性,智慧服务是否必然提供价值理性,单从先抑后扬的论证方法看,其结论着实难以令人信服。为了论证公共智慧服务进化的合理性,黄幼菲认为十数年来知识服务研究的量变积累必将引发公共智慧服务质的飞跃[6]。作者甚至在本人都对转知成慧能否引领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心存疑虑之时,转而信心满满地提出只要“图书馆确立转知成慧的核心价值,就能满足人类对自由、知识、智慧的追求”[8]。在缺乏科学规范演绎过程的前提下,这无疑是对量变与质变原理,应然、实然与必然关系误读下的穿凿附会。
再次,移植套用外来理论。长期以来,学界对图书馆学本质的探索经久不息。为了构建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展开相应的跨界研究,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成果中汲取新观点的立论依据本无可厚非,但智慧服务的相关研究首先预设了一个新型图书馆,为了将之与传统图书馆显著区分,便赋予它一个终极的价值使命——转知成慧,为了确保核心价值得以实现,又将其实现手段——公共智慧服务视为新型图书馆的本质,为了展现该本质的践行路径,于是移植了融界方法论、柔性逻辑论、广义计算语言论、科学语言本体论、全信息微计算技术、超级高等智能工程、超循环知识生态工程等大量外来理论[33]。这一思路完全是从研究主体的主观价值想象出发,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价值导向问题。但在价值想象与客观现实的对立中探究理想的服务模式与学科发展路径,不仅使引入的理论水土不服、表意不精,导致研究泛哲学化、泛学科化,同时缺乏真实场景分析的虚化研究也加剧了理论与现实的分离。为了稍作挽回,黄幼菲[6]给出了与现有嵌入式学科服务几无二致的应用方案,熊伟等则“呼吁尽快开发图书馆专业技术平台系统”[34],开展公共智慧服务,但无论哪种预设都不得不面对理论空谈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尴尬。可以说该观点最大的问题就是悬浮,理论—方法—结论都似乎是空降,无视学科差距,盲目移植外来理论与概念内涵。
程焕文曾痛陈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沉迷于学科体系及其组成结构与概念要素的不断解构与重构之害[39],遗憾的是智慧服务研究依然没能跳出窠臼。尽管它意图将文华校训启迪智慧的理念精髓进一步升华至转知成慧的新高度,但纯文本的理论演绎呈现得很局部、很刻意,始于能力建设,却落于理念纷争,终有坐而论道制造焦点与热点之嫌。这不免让人深思:为何立意高远的学科本质研究,在大量外来理论充实下,反倒无法给现实一个科学可行的指导方案?相较之下,10余年的学术研究,竟不如知乎等知识分享服务平台所取得的成效和影响力,图书馆智慧服务的价值从何得以体现和验证?仔细探查,不难发现既有研究多对图书馆消亡论持十足戒心,生怕缺失内涵、缺乏远见、无力创新、没有高级面向的学科体系的图书馆会在某天灰飞烟灭。在自卑与焦躁心态作祟下急于改变现状,将图书馆设定为人类智慧中心,将馆员视为近乎全知的知识生产者,提出“裁衣论”,为用户提供知识精品[7],包办知识、智慧生产与创新,热衷于为一个弱势行业和学科张贴各种力不能及的标签,用纯粹的高位甚至玄奥理论提升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和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如此不切实际的预设,不仅有违独立个体基于自身知识结构、价值取向,从点滴知识积累中获取智慧的文华校训精髓,也势必会抹杀图书馆的特质,动摇图书馆存在的基础。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在评论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时曾说:“社会的尊重不在于我们是什么级别,而在于我们是否做得好。”[40]这句话放在图书馆领域同样适用。其实,初景利等早在图书馆新消亡论的辨析中就提出了基于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应对策略[41]。这说明只有沉下心来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基于问题找寻解决方案才是攻坚克难的良药,而一味痴心于更迭高位理论,无视知行断裂,终究得不偿失。
2.3 移用与扩张:智慧与服务的异变
如今,学界多认为智慧图书馆是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已从基础理论、应用技术、服务模式等角度展开全面研究,成为践行智慧与服务理念新的落脚点。如果说智慧与服务是理念驱动型研究,智慧图书馆则是技术驱动型研究。由于对技术的过分强调与依赖,使得智慧图书馆研究在移用智慧与服务本体过程中产生新的异变。同时,基于应用技术的扩张研究,也导致图书馆作为研究主体被淡化。
2.3.1 智慧概念的移用
王世伟指出智慧图书馆有别于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的主要特征在于互联、高效和便利[15],后两者是图书馆发展中解决文献存储与服务的局部方案,前者则是创新发展的全局方案[16]。不过王世伟[15-16]、郭玲[42]、余丹[43]、吴吉玲[44]的比较研究,多是从静态视角观察数字图书馆。过去20余年,数字图书馆已在资源建设、技术应用、读者服务,乃至组织变革、运营管理、理念更新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面对当今多元、泛在的新环境,还将继续向智能化、语义化、知识化、模块化和自助化方向发展[45]。因此,动态地看,智慧图书馆的研究并没有揭示其与数字图书馆的显著区别,却在表述上充斥着各种语义混搭,意图移用文华校训的“智慧”概念,建立Wisdom与Smart的映射关系,解决“智能”与Smart的不匹配现象,使得看上去热闹的学术研究在细节上把握得很不严谨。
从国外研究看,无论是加拿大渥太华的首都地区Sm@rtLibrary跨馆一站式检索平台[46],还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图书馆的Smart Library Network Programs[47],亦或是芬兰奥卢大学基于位置感知的Smart Library移动服务[48],以及Mark C.Miller基于SQE(Software Quality Engineering)的Smart Library软件设计[49],乃至Marshall Breeding对影响Smart Library的6大技术潮流的系统介绍[50],无不是从技术应用出发,拓宽图书馆服务场景。因此,Markus Aittola等认为,Smart Library是彻底基于软件的解决方案[48],意即智能图书馆。国内智能图书馆(Intelligent Library)研究早见于吴继周等人设计的CXQ系统[51];后有张洁等人[52]及陈鸿鹄[53]从智能建筑角度作出探讨;张厚生等[54]将RFID引入图书馆研究后掀起热潮,一度成为智能图书馆代名词。同期,台湾则将基于RFID的Intelligent Library实践称为智慧图书馆[55-57],是为该词源起。IBM抛出Smarter Planet概念后,智慧地球等各类“智慧”表述迅即火爆。随后,国内引入Smart Library研究,便移用“智慧”表意,以示与Intelligent Library的区别。遗憾的是,学界术语使用严重失当。既有同作者在同主题研究中随便切换智能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语义[11,58],也有不加分辨地将Intelligent Library、Smart Library与Smarter Library视作同义语,甚至逆向开发出Wisdom Library[59],更有如“智能化智慧信息服务”[60]、“智慧文献服务、智慧知识服务、智慧集群服务”[61]等赘疣。尽管近年仍有少数学人坚持使用规范术语,审慎地提出图书馆4.0时代是智能图书馆[62],但此类发声始终难敌智慧图书馆的热词效应,被迅速湮没。
黄长著对学界术语似是而非地随意使用曾颇有微词[63],但智慧图书馆研究仍受此遗风影响去拿现成外来成果,既无视国外纯粹基于技术背景的研究旨趣,又漠视两岸术语使用习惯的巨大差异,也忽略了智慧地球开放性商业概念背后的营销炒作,强行赋予其独特的人文智慧[64],将特定语境下的术语理解为“能够满足各种需要、幸福没有烦恼的图书馆”[65],意图使Smart与Wisdom等义齐观,无疑是语境抽离后的概念误置。学术研究选用合适词语是提升研究准确性的第一步,最忌以偏概全[66]。而智慧图书馆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基本特征看,远未超离智能范畴,却以过强的概念形式感与新名词的拼接包装模糊了智慧与服务的研究实质,以致夹在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摇移不定,被批为根基不稳、价值偏离、急功近利[67]。
2.3.2 应用技术的扩张
2011年,一篇《2050年高校图书馆尸检报告》引发学界关注。尽管程焕文、范并思都推出博文予以反驳,但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下,学人无不感受到图书馆被日益边缘化的压力。吊诡的是,看似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颠覆了图书馆存在的理由,却也推动它更加努力地接纳与应用新兴技术,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演变并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王世伟认为,智慧图书馆注重的是信息技术支撑基础上的整合集群、协同管理、泛在便捷和跨越时空的读者服务[13]。的确,自从严栋给出智慧图书馆=图书馆+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化设备[10]的定义模式后,各种累加式定义层出不穷,有所区别的只是应用技术方案不同,或技术外延有大有小[68-70]。目前,相关研究已包罗了市面可见的RFID、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ICT、VR/AR、SAAS、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二维码、数据可视化、3D虚拟、可穿戴技术、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等众多技术热点[71-72]。与此同时,智慧服务研究也不再囿于纯理性思辨,而在技术跃进的驱动下就实施方法、模式构建等具体问题展开探讨,如陈远等整合智能场馆层、智能感知层、泛在网络层、大数据处理层、智慧应用服务层建设,提出了泛在智慧服务的构想[73]。具体实践上高校图书馆先行一步,上海大学图书馆基于感知层、计算层、交互层的技术应用[74],推出了移动借阅、自助选座、自助借还、机构知识库等新型服务[75]。南京大学图书馆进一步融合移动服务与知识发现,生成了Find+、Mobi+、Book+、Pad+、Subject+、Paper+等系列聚合应用[76]。重庆大学图书馆则在文献元数据仓储上重构管理系统,实现了资源的精细化揭示,开拓了个性化、专业化学科服务新模式[77]。
客观地说,新兴技术的追踪与应用为图书馆建设提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开拓了研究视野,使研究充满活力。但各类技术通过层层加持的不断扩张,逐渐异化为研究主体,图书馆作为技术的应用场,人文属性被淡化甚至隐匿,沦为附庸。尽管王世伟反复强调智慧图书馆超越了技术层面,应克服把注意力局限于服务平台和业务流程的智能化,停留在数字网络技能和娱乐互动享受上[14],但大量研究仍不可避免地陷入技术决定论下的伪实证主义研究,如主张智慧图书馆的核心就是图书馆服务和管理都无需人工干预达到智慧状态[78];认为缺乏云数据存储、分析、计算中心是图书馆智慧化程度低的主要原因[79],依托物联网标识的图书馆则会产生人类身体器官延伸的智慧效果,实现用户智慧化改造[80]。此类比附大多泛泛而谈,还停留在自动感知、自助服务、数据采集、信息推送等局部层面,只是基于算法对基础体力劳动的节约与替代,充其量算得上弱人工智能(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连能够深度学习的强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超人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都不算,更遑论意识与情感合二为一的人类智慧。
冷静分析技术的扩张,学界追热词、造热点的研究惯性以及学人的浮躁心态难辞其咎。自Smart Library流行伊始,学人就将之视为风口,在捡拾国外技术成果的同时迅速完成学术前沿的抢滩[81]。然而,铺大饼、拼图式的研究忽略了我国各地区、各系统、各层级图书馆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过分夸大技术的作用,将目的与手段混作一谈,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反而削弱了图书馆服务。仅凭蜻蜓点水般的问题描述、技术讲解与方法介绍进行研究,深度不足且欠缺普遍意义,对实践的指导价值能有多大?以致服务研究呈现简单替代与理论空想两极分化,实践中乱象丛生,在智慧**风潮席卷下项目上马轰轰烈烈,设备闲置凄凄凉凉[82],造成浪费实在难称“智慧”。面对价值选择困境,程焕文以“火车论”[39]表达出对技术扩张的不满与失望,也有学人提出需要锻造新一代价值理念,实现智与德的共生[83]。此时蓦然回首,智慧与服务理念却已蒙尘良久。
3 智慧与服务研究的复归
智慧与服务作为图书馆的重要价值理念,昭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势。尽管嬗变中本原、解构、异变交织,但只要立足图书馆主体,区别研究对象与工具,破除简单虚化、移用、扩张的思维定式,避免不可理解的错抄与不可接受的误读,其价值终将实现复归。尤其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兴起背景下,以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机为代表的技术融合,日渐模糊了数字、物理与生物世界间的界限,也加速了传统图书馆隐退,触发了新型图书馆的诞生。伴随注重人的需求、可接近性、开放性、生态环境、资源融合的“第三代图书馆”的萌发[84],现有馆藏格局、业务分布、馆员能力与发展规划受到巨大挑战。面对剧烈变革,重新审视图书馆是什么,充分发掘智慧与服务理念在时代变迁中新的价值内涵,以用户需求为驱动,通过技术革新、能力提升、管理创新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显得十分必要。
3.1 面向用户需求
人和客观知识是图书馆活动必须同时面向的两个方面[85],而增进用户智慧才是图书馆服务的最终目的。理念驱动型的智慧与服务研究在张扬主观价值想象的同时极易脱离图书馆具体现实,成为一厢情愿的幻想[86]。特别是在传统馆藏中心观的束缚下,复杂繁琐的分类、编目体系与图书馆能够拿得出手、有价值的服务内容形成了鲜明反差,即便是引以为重的学科服务、参考咨询,也因能力不足多半流于形式而饱受质疑[87]。面对互联网去中心化的冲击,黎瑞刚在为传统媒体破局时指出,只有用户的行为变化能给我们划出一条清晰的主线[88]。新时代已经来临,旧思维不适合指引未来,图书馆曾经所谓的中心地位,已被数据库、知乎、豆瓣、公众号等知识运营商渐次瓦解,继续抱残守缺、忽视用户所思所想,将使图书馆零落成“一地鸡毛”。2007年,美国第13届大学与研究型图书馆会议上提出“未来10大假设”,其中的伴随用户需求与期望变化改进服务备受关注[89]。目前,广州图书馆已从基本服务分化出主题和对象服务,搭建了分面布局、分众服务的创新框架[90]。可见,以用户需求为驱动重塑图书馆业务布局与服务体系,在规范化服务基础上实现多元、细化、专深的差异化服务,既是实现转型的题中之义也是必经之路。
3.2 融入信息技术
随着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广泛渗透,我国信息消费步入快速增长阶段,规模不断扩大。数字原住民逐渐崛起为社会主流,整个社会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的环境与方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信息服务中介机构,图书馆的功能实现与形态演变越来越仰仗技术进步,尤其在化解信息过载与用户有效利用间的矛盾上,技术效能有目共睹。面对无序泛滥、多维关联、动态发展的信息内容,传统以库为单位的整序体系已经无力揭示知识对象间的复杂关联,而用户对问题特征模糊、结构变化复杂、需要探索解构的“弱信息”[91]需求的迫切性已经压倒问题指向明确、辨识特征明显、易于检索获取的“强信息”[91]需求。前者不拘泥于具体问题,更侧重宏观知识结构的搭建,这恰是辨别未来趋势与方向,促进用户学习创新与智慧生成的关键。因此,基于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实现资源揭示粒度的精细化、语义化、可视化,突破半结构与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瓶颈,达到关联知识的可追踪、可利用、可分析,并不是“是否”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不过考虑到我国图书馆行业发展不平衡与技术应用中普遍存在的标准多样、迭代加速、资金匮乏等问题,如何透过“虚胖”的数据繁荣,关注真正的颠覆性趋势,将技术、数据优势转化为能力优势,需要作出深入理性的考量,绝非受技术变革的恐慌驱使做毫无目的的布朗运动②。
3.3 提升馆员素养
技术进步带来的图书馆跨越式发展使人产生技术无往不利的错误幸福感。美国学者兰开斯特曾质疑在技术的渗透和统治下图书馆正变得非专业化、非人性化[92],过于强调技术路径容易导致专业知识弱化,价值理念迷失进一步加剧行业边缘化危机。事实上,NTSB(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事件调查中采用计算机反复模拟也很难再现机长萨伦伯格的壮举,最终结论是:只有出色的飞行员才是应对威胁的利器[93]。同样,图书馆的种种变革无不通过服务得以展现,正是馆员把个人素质带入图书馆,才使服务具有了活力。对此阮冈纳赞指出,馆员的独创性和学识水平是图书馆得到充分利用的钥匙,这种学识即判断力、教养、科学作风和好学精神[94]。过去学界在研究IT的时候把焦点放在了T端(技术),忽略了I端(个人),但没有智慧的馆员,技术也没有价值。因此,当技术重构图书馆服务时必须重新思考人的价值。无论是伊安·约翰逊等主张的培养具备卓越洞察力和执着献身精神的智慧馆员[95],还是王世伟提出的弘扬智慧工匠精神[96],在匹配用户高纬度信息服务的刚需面前,馆员必须跨越积极性鸿沟,锻造对用户需求的洞见与知识发现、分析能力,形成服务的专业基础。如此,智慧与服务将不再是空泛的宣传口号或观念教育,而是脚踏实地的具体行动。
3.4 创新管理机制
在新环境、新需求倒逼下,新能力的开发与利用需要新机制加以保障。一个行业的兴衰不在于某个技术环节的突破与创新,而在于有没有形成一套科学且行之有效的管理范式。传统依托行政隶属、以馆藏为中心的运作管理机制已成为整体发展战略的短板。既然图书馆的智力内涵与能力水准再也无法以馆藏量标定,馆员能力已成为图书馆智慧与服务水平上限的决定因素,那么打破旧有思维边界,以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为总抓手,从基于直觉与经验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基于数据分析、事实驱动的管理机制就成为必然选择。首先要以组织结构的动态调整整合观念更新、任务分配与流程梳理,推动简单技能岗向专业服务岗迁移,以优化的资源配置确保新布局与用户需求发展的适配度。其次要坚持不懈地推动学习型组织建设,确立人才队伍发展规划,明确馆员能力发展目标,以层级化、制度化的培训促进克服怠惰心理,加强创新能力开发。尽管新的发展路径尚无成熟经验可循,但不意味着局部的变革成为没有内在联系的各种支离破碎的工作集合,遇到问题就停摆。技术、服务、管理创新应该像咬合的齿轮一样有机地相互推动,一旦运转起来就会形成越转越快的“飞轮效应”。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管理文化才具备更强的导向力、凝聚力和竞争力。
3.5 激发交流活力
图书馆是社会文化交流链上的一个环节,受制于传统由信息源到受众的板结化线性传播模式,服务内容追不上技术变化,空心化危机愈演愈烈。当技术不断进步,沟通和交流的障碍随之减少,知识的分享与传播方式更具参与性、对话性和创意性,绝不是图书馆随便做点什么都会有人买账。智慧与服务的焦点在于用户智慧的增益,但智慧并非与生俱来,它是人生经验的综合与生活理性的沉淀。图书馆应该在交流互动中传达对未知的求知欲,促进个体知识社会化与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结合,这是人们通过自己擅长的知识与世界连接的一种新方式。领域不同、兴趣相同的人以这种方式连接在一起,不仅能够从各自专业角度提供有价值的内容,通过吸收、批判,形成互相补充、纠错、印证、延伸的,具有自清功能的结构性知识,避免“灯下黑”现象,甚至可以具备设置议题的能力,相较于以拥有为目标和以喜好来过滤的知识服务,在讨论与思考中突破隐性知识无法以语言清晰表达的限制,打破认知固化、扩展认知边界、重构认知体系的服务格局更大、包容性更强、更易于产生创新思维的共振。国家科学图书馆支持开放、合作、交互的智慧中心服务实践[97-98]已经证明,授人以渔远比被动提供图书馆服务更能体现智慧与服务的理念精髓。
4 结 语
面对我国图书馆的百年发展,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它背后的生长逻辑。尽管新技术是图书馆创新的杠杆,但很明显智慧与服务才是保持事业发展活力的基因。图书馆只有在汹涌袭来的社会发展潮流中,坚守启迪智慧、服务大众的社会责任,才能保持强劲的生命力。智慧与服务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哲理论证有多么充分、完美,而在于以日拱一卒的实证研究克服现实困难从而彰显光芒。开放的新环境在延续智慧与服务理念的同时,也使其概念体系变得更丰富、更包容,不主观、不绝对、不固执、不自以为是的态度则是确保研究主体不再迷失、研究目的不再错位的关键。
注 释:
①原教旨主义,本意指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基督教新教中率先出现的一种观念形式,具体表现为在神学中自我意识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此处将立足于传统图书馆本体研究的智慧与服务比作原教旨主义,而将经过概念衍生与技术解构后的各种新解释比作现代主义。
②布朗运动,原指被分子撞击的悬浮微粒做无规则运动的物理学现象。此处比喻个别图书馆学研究与实践在技术的强力冲击下脱离本体漫无目的地四处发散。
[1]周黎明“.智慧与服务”[J].图书情报知识,2010(1):2.
[2]程焕文,刘继维.文华精神——在纪念文华图专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演[J].图书馆建设,2001(6):101-102.
[3]梁光德.智慧服务——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服务新理念[J].图书馆学研究,2011(11):88-92.
[4]傅荣贤.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说”的反思——从知识之学走向智慧之学的取向[J].情报资料工作,2009(1):6-10.
[5]黄幼菲.公共智慧服务、知识自由与转知成慧[J].图书与情报,2012(1):10-13,82.
[6]黄幼菲.公共智慧服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高级阶段[J].情报资料工作,2012(5):83-88.
[7]黄幼菲.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扬弃和“飞跃”:公共智慧服务[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36(2):26-30.
[8]黄幼菲.基于“转知成慧”的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兼议知识服务作为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缺失[J].图书馆研究,2015,45(4):1-5.
[9]黄幼菲“.转知成慧”:当代图书馆核心价值的重新定位[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7):13-17.
[10]严 栋.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图书馆[J].图书馆学刊,2010,32(7):8-10.
[11]董晓霞,龚向阳,张若林,等.智慧图书馆的定义、设计以及实现[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1(2):76-80.
[12]乌 恩.智慧图书馆及其服务模式的构建[J].情报资料工作,2012(5):102-104.
[13]王世伟.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智慧图书馆[J].图书馆建设,2011(12):1-5.
[14]王世伟.再论智慧图书馆[J].图书馆杂志,2012,31(11):2-7.
[15]王世伟.论智慧图书馆的三大特点[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38(6):22-28.
[16]王世伟.略论智慧图书馆的五大关系[J].图书馆杂志,2017(4):4-10.
[17]程焕文.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三位一体”与“三维一体”的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6):65-69.
[18]程焕文.一代宗师 千秋彪炳——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J].图书馆,1990(6):64-67.
[19]新世纪中国大学图书馆发展之我见——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访谈录[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1(6):2-5,13.
[20]程焕文,周旭毓.图书馆精神——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J].图书馆,2005(2):3-9.
[21]王凌云.重塑图书馆精神——关于“智慧与服务”的思考[J].晋图学刊,2003(6):12-13,55.
[22]沈俏梅.论图书馆“有智慧的服务”[J].前沿,2002(3):86-87.
[23]王雪玲.做“智慧型”女馆员[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4(1):70-72.
[24]阴月华.图书馆工作者服务智慧探析[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09,11(1):123-125,128.
[25]齐凤艳.也论图书馆人的智慧——国学经典的启迪[J].河北科技图苑,2011,24(4):15-18.
[26]张玉文.智慧与服务——从转变图书馆人的服务观念谈起[J].图书馆学刊,2011,33(11):111-112.
[27]王 杉.对图书馆智慧服务三种形态的分析与评价[J].新世纪图书馆,2013(4):13-18.
[28]张延贤,王 梅.图书馆智慧服务的概念、内涵与分析[J].现代情报,2013,33(4):34-38.
[29]王 梅.图书馆智慧服务体系中的人文智慧解析[J].新世纪图书馆,2013(7):3-7.
[30]燕 辉,魏小盈,杨 华.学科服务背景下“智慧与服务”新解读[J].图书与情报,2014(1):122-127.
[31]刘秋让,燕 辉,白君礼,等.价值论视角下“智慧与服务”新解读[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5(2):5-9.
[32]刘志勇.智慧服务——网络时代图书馆员的崭新职业理念[J].现代情报,2004(2):140-141.
[33]熊 伟.建立面向与通往“智慧”的普通图书馆学科体系[J].图书与情报,2012(1):4-9.
[34]熊 伟,杨 艳.公共智慧服务何以可能:馆员专业修养与图书馆公共智慧服务——2012年陕西图书情报界第3期主题学术沙龙纪要[J].当代图书馆,2012(4):72-74.
[35]王宗义.图书馆“核心能力”建设的思考——“新世纪图书馆管理变革的散思”之三[J].图书馆建设,2003(3):1-4.
[36]王均林,岑少起.知识服务与图书馆的核心能力——与张晓林先生商榷[J].图书情报工作,2002(12):115-119.
[37]段小虎.图书馆核心能力:信息服务格局变化中的认识冲突与分析[J].图书馆杂志,2010,29(9):2-4,8.
[38]黄幼菲.图书馆核心价值的思考——“转知成慧”[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5(4):5-9.
[39]刘锦山,程焕文.程焕文:用理念引领发展[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2,32(6):7-11.
[40]南开大学校长:高校取消行政级别是一定要落实的[EB/OL].[2017-11-23].http://www.sohu.com/a/128640520_105067.
[41]初景利,杨志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图书馆新消亡论论辩[J].图书情报工作,2012,56(11):5-11.
[42]郭 玲.从数字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发展探要[J].图书馆学刊,2013,35(9):1-3.
[43]余 丹.从数字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的发展探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6(7):238-240.
[44]吴吉玲.数字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比较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15(2):43-45.
[45]周 杰,苏 静,曾建勋.下一代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思考[J].图书情报工作,2013,57(8):35-39.
[46]What is SmartLibrary?[EB/OL].[2017-08-08].http://smartlibbibliogen.ca/en.
[47]Smart Libraries Build Smart Communities:Future Directions of the State Library of Queensland [EB/OL].[2017-08-08].http://www.slq.qld.gov.au/__data/assets/file/0016/3157/smart_libraries.pdf.
[48]Aittola M,Ryhänen T,Ojala T.SmartLibrary-Location-Aware Mobile Library Service[EB/OL].[2017-08-08].http://www.mediateam.oulu.fi/publications/pdf/442.pdf.
[49]Miller M C,Reus J F,Matzke R P.Smart Libraries: Best SQE Practices for Libraries with an Emphasis on Scientific Computing[EB/OL].[2017-08-08].http://e-reports-ext.llnl.gov/pdf/314914.pdf.
[50]Breeding M.Smarter Libraries Through Technology[EB/OL].[2017-08-08].http://journals.ala.org/index.php/sln/issue/viewIssue/320/82.
[51]吴继周,陶 毅,刘 全.一个智能图书馆系统(CXQ)[J].大庆石油学院学报,1992(2):73-76.
[52]张 洁,李 瑾.智能图书馆[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0(6):12-13,31.
[53]陈鸿鹄.智能图书馆设计思想及结构初探[J].现代情报,2006(1):116-118.
[54]张厚生,王启云.图书馆服务的无线技术——RFID的应用[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4(1):56-59.
[55]郭斌达.台北市立图书馆智慧图书馆读者使用行为之研究[D].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2008:4.
[56]Shih-chang H.Assessment of the Benefits of Taipei Public Library Intelligent Librariesand ''FastBook'' Automatic Book Lending Stations[EB/OL].[2017-08-08].http://library.ifla.org/901/7/203-horng-en.pdf.
[57]杜宜谙.北市最大福德智慧图书馆启用[EB/OL].[2017-08-08].http://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20140614002202-260405.
[58]董晓霞,龚向阳,张若林,等.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图书馆设计与实现[J].图书馆杂志,2011,30(3):65-68.
[59]郑怿昕,包 平.智慧图书馆环境下馆员核心能力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7(1):7-11.
[60]谭春霞,佟成涛.基于智慧图书馆理念的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J].兰台世界,2014(32):122-123.
[61]邓蓉敬.试论中国智慧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及构建路径[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4,26(5):179-182.
[62]董曦京.从“工业4.0”计划展望“图书馆4.0”时代[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6,25(4):36-42.
[63]黄长著.关于建立情报学一级学科的考虑[J].情报杂志,2017,36(5):6-8.
[64]李凯旋.人文视角下“智慧图书馆”定义的再思考[J].图书馆界,2013(6):14-16.
[65]刘宝瑞,马院利.基于智慧理念的智慧图书馆空间样貌探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5(11):26-29.
[66]邱五芳.提升研究准确性应注意的若干问题——图书馆学理论联系实际之我见[J].图书馆,2009(3):10-12,15.
[67]李燕波.国内智慧图书馆研究中的“不智慧”[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4,23(1):63-68.
[68]邱庆东.大数据时代智慧图书馆建设探析[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5(6):12-15.
[69]李 婴.基于互联网+的智慧图书馆模式及特征分析[J].情报探索,2016(3):116-121.
[70]储节旺,李 安.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及其对技术和馆员的要求[J].图书情报工作,2015,59(15):27-34.
[71]王黎娟.国内智慧图书馆研究综述[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4,34(7):90-93.
[72]刘 岩.基于共词分析的国内智慧图书馆研究探析[J].图书馆学研究,2015(18):9-14.
[73]陈 远,许 亮.面向用户泛在智慧服务的智慧图书馆构建[J].图书馆杂志,2015,34(8):4-9.
[74]康晓丹.构建第三代图书馆的技术思考:以上海大学图书馆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32(1):78-82.
[75]郑春汛.智慧图书馆提升服务能级——上海大学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与探索[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4(6):37-39.
[76]沈奎林,邵 波.智慧图书馆的研究与实践:以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J].新世纪图书馆,2015(7):24-28.
[77]张 洁,袁 辉.智慧图书馆系统支撑下的学科服务实践[J].图书馆论坛,2017,37(7):27-32.
[78]金敏婕.智慧图书馆——构建智慧城市之思考[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4):17-20.
[79]黄 辉.试论智慧图书馆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及改进策略[J].新世纪图书馆,2014(8):12-15.
[80]黄 辉.基于物联网标识体系的智慧图书馆建设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8):41-44.
[81]王子舟.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11(1):4-12,35.
[82]付真卿.成都街头千余智能信息亭被闲置 造价数万1个[EB/OL].[2017-08-08].http://cd.qq.com/a/20150422/011594.htm.
[83]刘亚玲.智与德的共生:智慧图书馆发展愿景[J].图书馆论坛,2016,36(1):31-35.
[84]吴建中.走向第三代图书馆[J].图书馆杂志,2016,35(6):4-9.
[85]蒋永福,张红艳.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哲学四定律[J].图书馆建设,2002(5):20-23,26.
[86]傅荣贤.对图书馆学研究中两个基本范式的反思[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35(1):42-46,85.
[87]程焕文.关于改变图书馆学研究立场的思考——从“用户永远都是正确的”说起[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3):89-93,102.
[88]罗振宇、马 东、吴晓波到李笑来,这些“行走的IP”背后的知识消费浪潮[EB/OL].[2017-11-23].http://www.sohu.com/a/127442051_116132.
[89]ACRL Announces the Top Ten Assumptions for the Futureof Academic Libraries[EB/OL].[2017-08-08].http://www.ala.org/Template.cfm?Section=news&template=/ContentManagement/ContentDisplay.cfm&ContentID=154350.
[90]方家忠.广州图书馆新馆开放服务后的若干启示[J].图书馆杂志,2014,33(2):4-9.
[91]Palmer C L.Research Practice and Research Libraries:Working Toward High-Impact Information Services[EB/OL].[2017-08-08].http://www.ideals.illinois.edu/bitstream/handle/2142/9742/researchpracticieslibraries.ppt.pdf.
[92]兰开斯特,梁奋东.对“无纸社会”的再思考[J].公共图书馆,2009(1):75-78.
[93]空中浩劫S10E05:全美航空1549次班机《最高职责》[EB/OL].[2017-08-08].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4036267/.
[94]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M].夏 云,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8:43.
[95]约翰逊,陈旭炎.智慧城市、智慧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员[J].图书馆杂志,2013,32(1):4-7.
[96]王世伟.图书馆应当弘扬“智慧工匠精神”[J].图书馆论坛,2017,37(3):51-56.
[97]王保成,孙九胜,莫晓霞,等.支持开放、合作和交互的国家科学图书馆智慧中心服务实践[J].图书情报工作,2013,57(18):11-15.
[98]李一平,徐 迎,邓 玉,等.图书馆作为开放智慧服务中心的模式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3,57(15):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