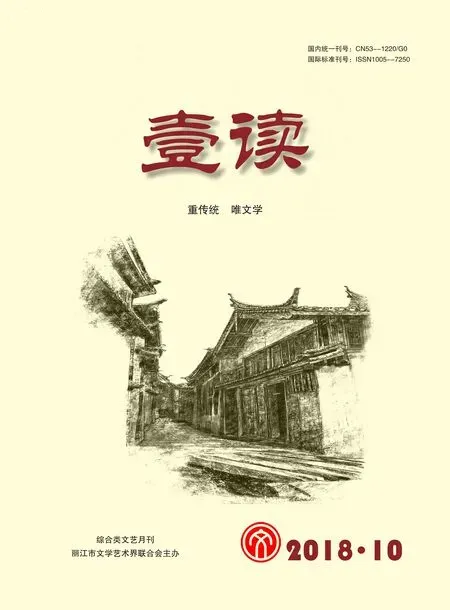狮子山下(组诗)
2018-01-25李志宏
李志宏
五花石巷
岩上,五彩光晕里熟睡的花瓣
是马匹遗落半道干涸的魂魄
是石头留给阳光的另一个出口
剖开运气和经验的传说
在天光普照缝隙里打坐的蝉
是一个指点迷津的支点
凭借他撬下来叫做天机不可泄露的秘密
铺成风霜四通八达的吆喝
挑夫脚步惊醒的鸡鸣
从东到西畅通无阻
马匹铃声击碎的灯火
由北向南滚落一地
石巷,五花石巷铺就的喧嚣混迹市井
滴水穿石坚而韧的结局
像一句掷地有声的成语
让以柔克刚找到借口
天南地北汇集到一起的方言和手势
在比酒还悠长的巷子里
互致问候,打探消息
草鞋、布鞋和靴子从巷子里一走
各路神仙就鱼目混珠了
轿子、肃静和回避往巷子里一抬
就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石巷,五花石巷里慢慢长成的手艺
有的在树荫下凝成夏天的冰粉和凉粉
与纸扇一起风和日丽
有的在二胡马尾上流淌成思念的眼泪
白酒和炒熟的蚕豆才能安抚
对着一条五花石巷打开的门
吱呀一响,走出来的
不是书生就是马锅头
他们有的着风一样飘逸的长衫
沿着巷子走向文字不可理喻的深处
有的穿马甲,随驮队和茶走向
音讯全无的北方
只有从门里走出的妇道人家
把星辰和手艺当本分卖给客商
循着暮色沿巷子匆匆返回
点燃松明孤独的夜晚
穿针引线缝衣纳鞋独守空房
五花石巷寂寥
那潜行在石头里缅怀时间的花瓣和
上面四散开来如行云流水的
脚步和马蹄声
随日渐丰茂的故事和长长久久的等待
和风徐徐,恣意绽放
狮子山下
是狮子山自己
承受了全部自然的磨难
在一条古老的南北轴线上
安抚阳光
狮子山不高
连太阳爬到坡头
都想栖息在古柏
比绸还温润的香里
蜜言死了,誓言活得滋润
炸雷死了,耳朵活得舒坦
古柏老了,全身张开占卜的嘴巴
也比不上不知为谁见风使舵的风铃
在一种预想的香脂里
我回了一趟自己的西域
羊群正在啃食烈日的黄金
丽江马匹走过的地方
落日殷红的布帛怎么看
都像四方街抵御时光的羊披
左右为难的狮子山下
飘荡了几千年的炊烟
不知道能否在桃花、水井和照壁之间
找到一块情歌的土壤
试图在古道上火中取栗的人们
你不在乎坚守妇道和手艺的女人
也该为瓦屋上开出的雪莲
忘掉途中冷了千年的火塘
在庆云苑小区河边看翠鸟捕鱼
一只翠鸟
将影子斜插在午后
运送经文阳光的枝桠上
将好听的歌子从嘴边卸下
寄存在隐隐绰绰的阴谋中间
遮蔽同样好看的外表和绸一样
脆生生的名字
留一双碧绿的眼睛在世外
透过穿越诗歌的流水
开始琢磨放生的好处
一尾用鳍思想的鲤鱼
被慈悲用旧了的木桶
赎回真身以后
像放生者一样开始快活
开始肆意向下游消费人类的业障
在庆云苑小区那段小河里
梦一样显露了红色尊贵的鳞片
和鳞片上一闪即逝的火光
可上浮或下潜都无法藏匿的基因
在这一刻还是出卖了
红鲤鱼无与伦比的身份
也败露了放生者置身世外的初衷
饥肠辘辘的翠鸟
不想让一句隔着千山万水的咒语
困住无所不能的利爪
困住内心的闪电
在抵达水负载的无为时左右为难
翠鸟从柳低垂的春光
与河岸上比名字好听的花朵旁边
在一朵玉的涟漪中央
叼起躲不开的劫数
在我眼前轻描淡写地
将适者生存又一次喂饱
从一截木头开始老旧
爬满春夏秋冬的一截红椿
在牡丹、荷花、青松和腊梅间
被刊刻、被模仿、被利用
给岁月留下余地 否定
这是主人和木匠的密谋
阳光的旨意
从遥远的驿站
递折子那样传递过来
它不拘泥隔扇是否被绵纸糊上
也不因窗棂的繁复和简洁
动摇窥探
柴虫,为木头活着的昆虫
潜伏于正在缴械的年轮
亢奋时,什么人家的木头都敢啃
都敢拿来锤炼牙齿后
当旗帜抗议不通情达理
一间屋,一座城无一例外地
从一截木头开始 背叛
老旧
时光也往往在秦砖与丽江土坯
谁更强大的纷争中
剥离掉混迹民间的风雅和风光
有时候,一截木头的韧性
远比不上一张蛛网可靠
比耐心衰减更快的
一定是竭力想挽回颓势的
年代表面的刻木记事
一截沉重的木头和一截
雕龙画凤的木头
不论高贵还是卑贱
最后都逃不掉
被柴虫掏空的命运
老旧
从一截木头开始
从成年柴虫的运筹帷幄中
步步为营
不易觉察,不留情面
干脆,彻底地
退出
一位土司苦心经营的强权
失去始作俑者的威严和尊贵
而后,也是慢慢地
木已成舟那样
在柴虫武力示威中
化腐朽为神奇
巴吾
纳西话把银器走路的声音
用近似歌唱的语气
重复一遍时在舌尖上遇见的巴吾
玉米把路途寂寞用阳光的成色
描述黄金的向日葵时提及的田野
赞颂了诗歌的高贵以后开始平庸的流水
穿行在田野青蛙们示好异性的歌声之间
而后,以清者自清沾沾自喜
巴吾
与雪山众神相拥而眠时
以多有打搅的慈悲心怀
生怕在日出日落之间弄出点响动来
卑微惯了的巴吾
年成好时叫丰收
叫男人奢侈的白酒
偶尔也叫醉和迷惑
叫女人用麦芽糖点化的
戒指般精致的幸福
孩子含在无忌的口里叫乖巧
老人用松明火把熏熟以后
用来医治人间百日咳
叫一剂石破天惊的中药
巴吾
下弦月里蟋蟀用二胡上
那滴颤栗的磷火抚慰哀和愁的村庄
祖先开疆拓土的阵阵呼喊
促使铁匠学会了铸造
从此,土地不光盛产粮食
还懂得歌吟耕牛和赞美犁头了
丰收的马车从形似盆地的民谣里
沿着洒满金桂
不可言说体香的村道缓缓而来时
把几亩薄田视为比书中那座黄金屋
更像宿命的才子
舌苔柔下来时
你就是寨子里吟诗的高人
巴吾
我们一再用黄铜密码标识的门扉
被铁栅栏重重困在历史足音之中
纵然怀旧的泪腺
滴落无家可归的文字中间
也难阻止那匹下弦月般的钥匙
成为锁最后的祭物
巴吾
曾经坠满翡翠的天空下
从未走错过迁徙路途的燕子
能否找寻得到三坊一照壁的屋檐下
一年用舌苔修补一次爱情
就一劳永逸的那只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