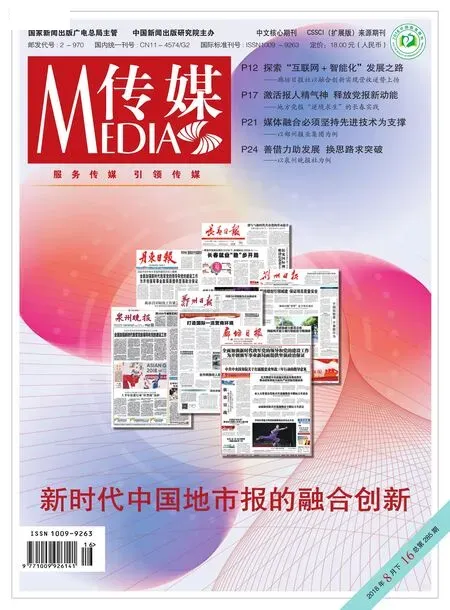多重媒介传播中的医生形象误构研究
2018-01-25徐晨霞
文/徐晨霞
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突出,暴力袭医事件频现报端,在此背景下,医生的舆论形象发生了诸多变化,从2003年“非典”时期受人尊崇、舍身救人的“白衣战士”变成了现在“乱收红包、乱开药、无医德、无耐心、冷漠”的形象。建构主义认为,人类对社会的所有感知都是某种建构的结果,媒介建构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公众对医生的负面刻板印象是由媒介建构的,新闻媒体、医疗剧、出版物、社交媒体等媒介对医生形象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误构。
一、多重媒介对医生形象的误构表现
(一)新闻媒体:歪曲化、树立“完美”典型
1.歪曲化报道。从2005年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到2010年后的缝肛门事件、八毛门事件、保温箱烤死婴儿事件、丢肾门事件等,都是影响较大的涉医新闻。这些事件经调查之后,大部分存在虚假报道或歪曲报道,记者在报道中或是对新闻素材进行了选择性使用,并非事件的原生状态,或是过早将事件定性,造成了舆论的首因效应,或是对诊疗方式先入为主,将医生标签化传播,导致医生形象在舆论中处于被动地位。
2.树立“完美”典型。2018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微信客户端文章《急诊送进国外医院,才发现我们欠中国医生一句道歉》引用了几个案例,如医生持续2小时15000多次心外按压救回患者、多位医生累瘫在手术室或病倒在手术台等。类似的新闻还有《医生腰椎犯病,坐轮椅绑护具做8台手术》《父亲心梗紧急抢救,医生儿子在隔壁为其他病人做手术》等。此外2013年媒体树立的北京卫生系统先进典型——北京儿童医院B超神探贾立群医生的形象是:24小时随叫随到、废寝忘食、艰苦朴素等等。这种医生“救命奇迹”“累倒术台”“带病救人”“舍亲救人”“不名一文”的无私形象报道显得极端化,导演出了畸形的医生形象。如果患者遇到的医生与媒体报道的有差距,就很容易产生失望情绪和医患冲突,甚至暴力袭医。又如,《含泪送别!8毛钱治好高烧的“不打针爷爷”,这才是医者仁心》这则新闻引发了不少医生质疑,医生认为以治疗费用高低和是否打针作为衡量医德的标准的不严谨表述,这类报道抬高了医生的道德标准,如果诊疗方式与新闻中的不符,医生就相当于背负了道德十字架。而疾病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岂是“8毛钱”和“不打针”都能解决的?这样的报道催生了公众对医生的不合理期望值,一旦医疗结果没有达到患者预期,医生就会遭到舆论挞伐。
(二)医疗剧:道德神化式、娱乐化传播
1.道德神化式传播。近几年来影视剧以过度苛求的奉献精神来展现医生职业形象,以对冲中国当下严重的医患冲突和公众对医生的刻板印象。如在电视剧《心术》中,刘晨曦为抢救病人,立即离开正在医院透析的女儿,其叙事逻辑是医生须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具有崇高的职业精神,舍弃母女亲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人生理想和现代医护“白衣天使”的光荣称号投射出人们的崇医心理,剧作将医生塑造成道德完人迎合了中国观众对该职业的想象。但这种叙事手法过度强调医疗伦理,未真实呈现医疗领域的现实矛盾,变成了一种虚假的道德神话和对医生的压力。
2.娱乐化传播。医疗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发挥抚慰、麻醉、娱乐、宣泄和协调等功能,不论什么题材的影视剧一旦被搬上荧屏,都注定了其文化商品属性,要争取收视率。例如在电视剧《柳叶刀》中,医学知识和技术被隐没起来,更多地展示人物恩怨——姐姐认定妹妹被谋杀,要替妹妹报仇;医药集团的药被迫下架,要报复;丈夫被小三争抢,妻子起杀机等。医疗剧本应充满医学专业性和现实冲突性,但其作为媒介文化难以摆脱消遣娱乐性,明星阵营、情感纠葛、个人恩怨往往使其变成披着医疗剧外衣的情感剧、悬疑剧。
(三)出版物:偏激化传播
2018年6月2日,医疗微信公号“三甲传真”中《小学教辅书如此描黑医生,岂能不管?!》一文曝出,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语文五年级下册教辅材料的一道看拼音填空题为:“有些医院总是打着专业的旗号,但是从医生的素质、从业经验等方面来看,破zh à n( )比比ji ē( )是,所以患者一定要注意。”不可否认医疗行业中确实存在一些医院和医生专业经验不足的现象,但不可忽略医生对国民健康作出的巨大贡献。教辅材料的这句话以偏概全,将局部和个别问题放大至“比比皆是”,并且提醒小学生要“注意”防备医生,这抹黑了医生形象。部分出版物以充满成见和偏激化传播方式直接对医院和医生开火,在幼小学生心里种下对医生不信任的种子,降低了医生职业美誉度,这可能导致近年来报考医学专业的学生逐年减少的现状更加严重。更有甚者可能对医患冲突起到思想催化剂作用,滋生出中小学生厌医、仇医的思想,青少年暴力袭医的极端行为就曾见诸媒体,如在2014年齐齐哈尔医生遇袭案中,嫌疑人是一名未满19岁的高三学生。
(四)社交媒体:舆论标签化、极化传播
1.舆论标签化。“术中要价”新闻近年来不时出现,社交网络舆论对医院的坑蒙拐骗、高价宰客行为唏嘘不已。实际上涉事医院多为莆田系民营医院,网络舆论忽略了新闻背后的逻辑,将医生集体标签化,对莆田系医院的集体斥责却要正规公立医院一起承担。
2.舆论极化。中青舆情监测室曾对2013年1-10月“伤害医生”事件进行舆情监测,共收集相关信息319755条,其中微博讨论最为活跃,信息量达312818条。在随机抽样的2000条舆情信息中,对医护人员的褒义信息比重仅为5.0%,中性信息占11.0%,贬义信息超过八成,形成舆论的极化。凯斯·桑斯坦认为,这种大多数人对某一人群或事件形成一致观点的现象称为群体极化。社交网络作为人们释放压力、表达情感、宣泄情绪的平台,加上表达的自由性、匿名性,导致舆论表达易走向极化。
二、媒介对医生形象误构的原因与影响
1.医生形象偏差是媒介建构的结果。李普曼认为,人们的直接经验十分有限,需借助媒介建构的中介即“拟态环境”来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吉登斯认为,媒介很难做到客观地反映现实,一定程度上是在虚构、塑造现实和生产着现实。在多起医患矛盾事件中,媒体的最初报道形成首因效应,等到事件真相调查清楚,网络舆情已退至低谷,受众对医生的负面刻板印象已形成;部分医疗剧或迎合观众对医生的职业道德期待,或激发观众发泄医患矛盾下积攒的不满情绪;部分出版物以偏概全,对医生全盘否定,引导公众对医生的戒备心理。媒介根据自己的认知和立场以“十面埋伏”之势建构医生形象,导致公众对医生充满成见。
2.医生形象误构是话语权力的结果。在媒介话语权力生产过程中,话语权拥有者不仅主导“他者”身份建构,还通过自我身份建构,在潜移默化中诱导大众认同话语权拥有者所持的政治观念、价值判断、利益诉求,以实现对媒介话语客体的控制。在医生形象媒介生产的第一阶段,媒介以选择信息来源、组合拼接细节、忽略背景信息等手法,实现话语权力关系的运作,对医生塑造一个“他者化”镜像。在第二阶段,社交媒体用户将“他者化”镜像进行解码和再次编码,在网络空间中延续这一议题,形成网络舆论。在媒介的“十面埋伏”下,医生的声音显得微弱无力,医生被误构的形象是多种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共构而成的“他者化”表征。在这种共构过程中,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
3.公众对医生的误解损害医患双方利益。英国《柳叶刀》杂志一篇题为《中国医生处于威胁中》(Chinese Doctors Are Under Threat)的文章认为,在中国医生从昔日的道德楷模变成今天一副破落户的潦倒形象和医患关系紧张上中国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报纸、电视与互联网有关医生欺骗患者的报道铺天盖地,负面报道比例彻底压倒了正面报道……对于缝肛门事件,很难说媒体的错误报道是因其缺乏医学知识、还是为追求轰动效果。不过,公众对于医疗职业的误解肯定最终损害了医患双方的利益。传播者习惯在冲突性的医患关系中寻找新闻、故事、话题,于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关系被媒介建构成冲突性关系,受众被引导于天价医疗费事件、缝肛门等事件中去思考医患关系,一种医患间水火不融,兵戎相见的社会氛围逐渐被营造出来。
4.医患互不信任阻碍医疗技术进步。医患间剑拔弩张的关系不断侵蚀着社会资本,造成医患互不信任,不信任情绪弥漫社会,又进一步削减社会资本,导致恶性循环。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由公民间的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构成的有机整体。福山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副产品。近几十年来人们对政府机构、医学界等的信任水平都在下降。科尔曼认为,信任本质上是出于对自我利益保护的需要,是一种在做出行动前进行的风险考量。可见,当一个人在选择是否信任他人时,必然要预估他人是否做出回报。对此,深圳录音门事件可见一斑,患儿家属对医院不信任,为对可能发生的纠纷做好“取证工作”便对医生的话进行“句句录音”,医生感到“压力很大”,为确保自身的合法权益,以让患者“步步签字”针锋相对,如此你来我往间的最终结局是导致医患双方“双重失灵”,阻碍医疗技术进步。
三、重构医生媒介形象对策
(一)传媒提高专业度与责任感
1.树立社会责任意识。新闻专业主义强调传媒的功能、责任、信念,以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伦理,超越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精神及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媒介在涉医传播中应遵循新闻专业主义,以公正、公开、公平为目标取向,树立媒介的社会责任。
2.发挥议程设置和把关人功能。医生典型形象传播选择适当的“度”,避免极端化和畸形化。引导读者正视医生的社会角色,传递正确的生命观念,弥合当前愈演愈烈的医患矛盾。
3.改变单一价值观,采用合乎情理的叙事逻辑。深刻反思造成医患矛盾的医疗体制问题,重视医学常识的准确表达,重视社会效应而非市场效应。正确树立医生媒介形象,强化医生媒介形象的传播力度。
(二)医生积极争取话语权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介为传播精英所控制,医生在媒介近用权上一直处于绝对弱势状态。传播者素质参差不齐和对医学专业知识的匮乏,进一步导致医生形象传播偏差。因此,医生应积极争夺话语权,进行自我形象建构,对负面刻板印象纠偏。2016年10月,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指导,依托中国医师协会等发起组建的“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汇聚了不同类型的微信公号,包括个人类、政府等机构类、医疗机构类盟员单位2079家左右,总粉丝近2亿人,其宗旨是搭建医、患、媒沟通平台,传播医学健康知识,及时准确科学发声,打击涉医谣言,树立医疗行业和医生形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助力深化医改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近年来其个人类微信公号如“雨林在线”,政府机构类如“广东卫生信息”,医疗机构类如“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在社交媒体中为自己发声,对医生形象正确传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受众提高媒介素养
在媒介化社会中,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人们对媒介的了解程度、分析与处理媒介信息的能力处于不平衡状态,因此在知识结构上补充媒介素养知识尤为重要。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之父约翰·彭金特(John Pungente)提出媒介素养的八大理念:1.媒介是建构的产物。2.媒介建构了所谓的“真实”。3.受众“协商”着理解媒介。4.媒介暗含商业因素。5.媒介包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6.媒介掺杂了社会和政治因素。7.不同媒介在报道同一事件时存在差异。8.每一种媒介都独特的美学形式。此外,加拿大媒介素养中心还注重五个方面的引导:1.谁创造了信息?2.媒体运用了什么技术?3.人们对不同讯息的理解差异有多大?4.价值观念、态度是怎样在媒介中呈现的?故意忽略了哪些信息?5.为什么要报道这条新闻?对于医生形象的媒介误构和非理性网络舆论,受众应提高媒介素养,正确地理解媒介信息,批判性地解读媒介信息。
(四)传受双方提高医学素养
目前媒体对口卫生系统的记者大多不是医学专业出身,欠缺一定的医学素养,在报道时又未就相关问题咨询医学专家,常常写出偏离科学常识的报道,导演出助产士“缝扎”产妇肛门、八毛钱能“治愈”巨结肠病、保温箱能“烤死”婴儿的闹剧。同时,网友也因欠缺相应的医学素养,让原本清晰的事情变得扑朔迷离。在从众心理的影像下借助网络传播非理性舆论,发泄对所谓“误诊”医生的愤怒情绪,将其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对医生造成了极大的误解和伤害。传受双方如果具备一定的医学专业知识,可能会避免出现传谣、信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