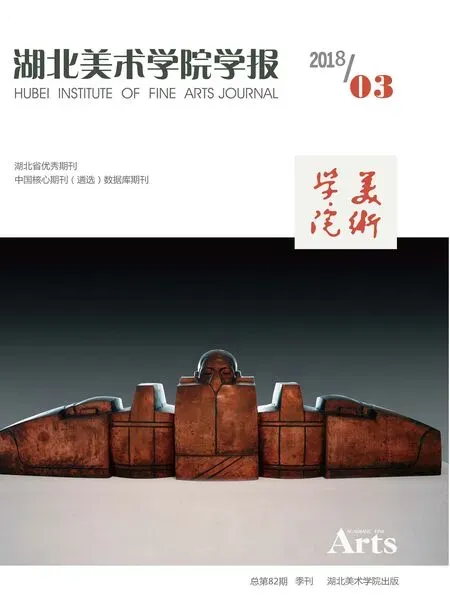武陵山区土家族织锦传承源流考
2018-01-25
在湘鄂交界的湖北来凤和湖南龙山土家人中,一直以来流传着一句民谚:“养女不织花,好比没养她。”所谓“织花”,是千百年来流传于土家族女性中的传统织造手艺。因在斜式腰机上,以麻、棉、丝等五彩线为原材料,采用通经断纬、反面挑织的方式手工织造花布,故称“织花”。又因在织造过程中,织女们用重达五六斤的大“布刀”来拍打纬线,使其紧实,故又叫“打花”。不管是“织花”,抑或是“打花”,都是土家人对该门手艺的习惯性叫法。晚清同治年间的贡生彭勇行,曾做竹枝词云:“山村处处柳絮斜,闺女生来会打花。四十八勾花并蒂,不知将送予谁家。”“打花铺盖”,是土家人对这门千年手艺的通称。在土家语中,人们把这种织造物称为“西兰卡普”。所谓“西兰”,有“铺盖”之意,“卡普”则为“花”的意思。此外,还有“土花铺盖”的说法,学界亦将其称为“土锦”或“土家织锦”。
一、土家之源与流布范围
数千年来,土家族世代聚居在湘、鄂、黔、渝四省(市)毗邻的武陵山区。土家织锦是土家女子自幼便开始学习的女红手艺,至今仍流传于沅江和酉水流域一带。著名美术史论家阮璞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经实地调研后认为:“从清代中叶到末叶的文献上看,湖南的龙山、永顺是主要的产地。根据现存彩织艺术遗产来看,这些文献记载是不无根据的。龙山的苗市、坡脚、靛房三个公社,土花铺盖的传统尤其保存得比较完整,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研究资料。其他如湘西的古丈、保靖、鄂西的来风等地,过去也有些土花铺盖的出产。”[1]半个多世纪已过去,目前土家织锦传承较好的依然是湖南的龙山、永顺、花垣,以及湖北的来凤地区。
千百年来,土家人繁衍生息于鄂、湘、渝、黔诸省毗连的武陵山下和酉水河畔,故又被称为“武陵土家”。春秋战国时期,此地属古巴国南疆。在土家语中,土家人自称为“毕兹卡”,或同音的“密基卡”、“贝锦卡”等,意为“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先民在历史上被侮称为“蛮”或“夷”。《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2]故巴人崇虎,时至今日土家人亦以虎为图腾。秦灭巴以后,一部分巴人流入武陵山,与当地族群融合。在两宋以前,一直都被侮称为“巴郡南郡蛮”、“武陵蛮”、“廉君蛮”、“五溪蛮”等;宋代以后,土家族就单独被称为“土丁”、“土人”、“土民”或“土蛮”等[3]。关于土家族的起源,有多种说法,诸如巴人说、賨人说和孳人说等,其中尤以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的“巴人说”影响较大,他认为土家族祖先为古代巴人后裔[4]。吉首大学彭秀模先生在《孳考》中认为秦襄王时射杀白虎的“板楯蛮”(“白虎复夷”)即为“孳”,简称“孳夷”;并得出“孳”即“賨人”自称的结论[5]。正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所云:“近年来,土家族多元来源说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即以古代巴人的两支——廪君蛮和板楯蛮为主源,融合当地土著和进入该地区的汉人、濮人、楚人、乌蛮等族群共同构成。可以断定,大约自唐末五代以后,土家族这一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开始逐渐形成为单一民族。”[6]
如前文所述,在宋代以后土家族名称相对固定,以“土”称之,接近现代称谓;宋代以前则被称为“蛮”或“夷”。清代文献将土家织锦的前身上溯至先秦时期的巴蜀“賨布”和两汉时期哀牢夷的“兰干细布”,阮璞先生在考证时认为“说‘阑干细布’就是近代土家族彩织的前身,似乎不甚可信”,因“哀牢夷所居地区与土家族相去甚远”。但是,他又根据南宋末年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认为宋代娘子布源于汉代阑干细布,且“阑干”为湘西蛮族獠言的说法,以及他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土家族地区调研时看到土家人把织造出来的条状或格状图案纹样仍然称为“阑干”的情形,似乎又认同了土家织锦的前身为“阑干细布”的说法:“可能这不全是出于一种巧合吧!”[1]
不过,在阮璞先生实地调研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一些文献资料陆续被发现,传承数千年的土家织锦源流脉络大致可以如此勾勒。
二、从先秦时期的賨布到魏晋时期的阑干细布
先秦时期属于巴国之境的武陵山区即产桑麻,织造业发达。如《华阳国志·巴志》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皆纳贡之”,“会诸候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7]。秦灭巴后置巴郡。《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载:“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2]2831这是关于巴人以“賨布”作为岁赋纳贡于秦的最早记载。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賨”字作了解释:“賨,南蛮赋也。幏,南郡蛮夷賨布。”在许慎的解释中,賨布作为一种贡赋,其真实名称是“幏”。唐代杜佑在《通典》卷一百八十七“南蛮上”中亦云:“巴人呼赋为賨,谓之賨人焉,代号为賨人夷。”[8]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賨者,南蛮赋也。《文选·魏都赋》注引《风俗通》曰:‘盘瓠之后,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廪君之巴氏,出幏布八丈(《后汉书》云八丈二尺)。’幏亦賨也。故统谓之賨布。”[9]
賨(幏)布是目前为止最早见诸史料的土家人织物,亦可能为土锦的早期雏形。随着原料和工艺的发展,又出现了较賨(幏)布更精细的阑干细布。据《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载:“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阑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2]2849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之“南中志”中将“阑干”解释为:“獠言紵也,织成文如绫锦。”“紵”即现在的苎麻。南宋朱辅在《溪蛮丛笑》中亦有所云:“娘子布,《汉传》载阑干。阑干,獠言纻,合有续织细白苎麻,以旬月而成,名娘子布。”[10]他认为宋代的“娘子布”源于汉代的阑干。所谓“阑干”,即由细白苎麻织成的布;其工艺复杂,织造进度较慢,需“旬月而成”,与现在的土家织锦一天织15厘米左右的速度差不多。
三、从隋唐到两宋时期的斑布
在麻成为土锦的最初原料之后,随着木棉从异域引入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棉纱逐渐被用于土锦织造中。宋代李昉在《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之“布帛部七”中引用三国时期万震所著《南州异物志》云:“五色班(斑)布,以(似)丝布,古(吉)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毳,中有核如珠句,细过丝绵。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绩,在意小抽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班(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11]此处的“古贝”应为梵语音译“吉贝(木棉)”之误。当时人们已将形似鹅绒、细过丝绵的棉花用于织造五色斑布,且对棉花的去籽、纺纱,以及将棉线染色和织布的工艺流程,都已相当娴熟。从五色斑布精细如丝织布来看,当时的织造工艺已较为精湛。
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和之后,土家先民在隋唐时期聚居于武陵山脉的湘鄂川黔四省边区,并逐步形成单一民族,且将斑布用于服饰中。据唐魏征《隋书》之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地理下”载:“南郡、夷陵、沅陵、清江……诸郡,多杂蛮左……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班(斑)布为饰。”[12]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被泛称为“九溪十八峒”,该时期的土家族先民亦被称为“五溪蛮”(即“酉、辰、雄、樠、潕”五溪)。故土家人所织之布被称为“溪布”或“溪峒布”,并成为岁赋贡品。据《宋史》卷八《真宗本纪》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是岁,溪峒蛮来贡。……三月丁未,峒酋田仕琼等贡溪布”[13]。苏轼《内制集》云:“元祐二年五月,溪峒蛮人彭允宗等进奉端午布。”[14]《宋史》卷十七“哲宗本纪”亦载:元祐四年(1087)“十一月庚午,……溪峒彭儒武等进溪峒布”[13]329。《宋史》卷四百九十四“南蛮二”载:乾道元年(1165)“辰之诸蛮与羁縻保静(靖)、南渭、永顺三州接壤,其蛮酋岁贡溪布”[13]14192。诸如此类的记载,反映了当时武陵山区的土家首领携峒布进京纳贡的历史事实。
朱辅在《溪蛮丛笑》中介绍了用蚕丝所织顺水斑布的情况:“顺水班(斑):蚕事少桑多柘,茧薄小不可缲(缫)。可缉为紬,或以五色间染布为伪,名顺水班(斑)。”[10]意为在溪蛮(指“五溪蛮”,包括武陵山区的酉溪、辰溪、雄溪、樠溪、潕溪等五溪流域)地区因桑树少而柘树多,所养蚕茧质低丝少,但可将其搓成丝线,染色后织成斑布。朱辅还在该书中提到了“不阑”一词,他认为“不阑者,斑也”,所谓“斑布”,即由此意而来。1992年,考古人员在来凤县百福司镇酉水河畔的卯洞发掘170米绝壁上的“仙人洞”时,发现有宋代晚期的织物,其纹饰清晰、色泽可辨,疑为土锦(斑布)。
四、繁盛于明清时期的土锦
由元入明清,随着棉纱、蚕丝等原料在土家人聚居的武陵山区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被称为“斑布”的土锦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大元一统志》(辑本卷四)载:“常德路风俗形势”为“居民务本,勤于耕织,自崇观以来制锦绣为业,其色鲜明,不在成都锦官下”[15]。地处湘西北、与湖北交界的常德地区织锦业盛行,且色彩艳丽,名气不输成都蜀锦。在随后各朝的官修方志中,对土锦有了更为详细的描述。明代李贤撰《明一统志》之“卷六十六”载:“永顺军民宣慰使司,古蛮夷地,春秋国之境,秦属黔中郡,汉以后为武陵郡,宋为永顺州及上中下溪三州,本朝洪武二年置施溶州。风俗……身服五色斑衣。”[16]至明代中叶,彭士麒《永顺宣慰司志》云:“(土人)喜斑斓服色。”其后的《湖广通志》之“卷七十六”亦沿用此说:“永顺府,《通典》溪州土地与辰州同,《明一统志》土民服五色斑衣。”[17]上述所云“斑衣”,即为“斑布”所做衣物。
至清代,各种(地方)文献典籍对斑布、土锦(布)的描绘记录颇为详实,对该织物的名称叫法亦多样。在民族名称尚未确定时,亦有称为苗锦的。如做过施南府同知的清乾隆时期著名诗人商盘,曾在一首颂咏来凤原大旺司所产织锦中将其称为“苗锦”:“冉䮾遗种语侏离,大旺当年有旧司。苗锦如云成五色,胜他蕃褐紫驼尼。”又有《溪州竹枝词》云:“溪州女儿最聪敏,丝挑苗锦旧有名。‘凤采牡丹’不为巧,‘八团芍药’花盈盈。”溪州,即现在的永顺及周边地区。再如,由符为霖主修、刘沛编纂,成书于清同治年间、增纂刊刻于光绪年间的《龙山县志》亦云:“苗锦,绩五色线为之,色彩斑斓可爱。俗用以为被,或作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巾。”[1]56不过,出现最多的字眼还是“土锦”。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戏曲家顾彩受容美土司之邀游历鄂西南土家人聚居区之后,在《容美纪游》中对当地特产——土锦赞不绝口:“峒被如锦,土丝所织,贵者与段(缎)同价,龙凤金碧,堪为被褥。”说明当时土锦原料不仅有麻、棉,还有蚕丝,因工艺精湛、材料金贵,故价格不菲(与缎同价),多用作被面。不久,画家谢遂绘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6)早期的中外民俗画卷《皇清职贡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中,绘有本土以及四方藩属境内各民族人物形象,对民族风俗服饰尤为考究。画卷中除了描绘土人身着民族服饰的劳作形象外,亦有题文云:土人“妇勤于纺绩土绫、土布,民间亦多资之”。清代皇家称其为“土绫、土布”。前文所述“斑布”究竟为何物?在张天如主修、顾奎光编纂,刊刻于清乾隆年间的《永顺府志》(1763年)之“物产志”中给出了答案:“斑布,即土锦。”所谓“土锦”,即在织“布”基础上,以通经断纬的方式挑织诸多色彩的断纬线,最后形成梭线和彩线两种纬线分别穿过三到两组经线,从而织出各种纹饰,将素色“布”变为华丽“锦”[18]。《永顺府志》对土锦描述较多:“土妇颇善纺织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用细牛角挑花,遂成五色”,又“峒锦、峒被、峒巾作鹤、凤、花、鸟之状”等,寥寥数语,描述了当时土锦的原料、工艺、图案色彩和纹饰。清代永顺府所辖范围为现在的永顺、龙山、桑植和保靖等湘西4县,与鄂西南的来凤、鹤峰等地接壤。在清代,武陵山区土家人用蚕丝织锦成为普遍现象。
从清代湖南龙山和湖北来凤两县各版县志可以看出当时武陵土家族地区织锦繁盛的景象。由缴继祖主修、洪际清编纂,刊刻于清嘉庆年间的《龙山县志》(1818年)载:“土妇善织锦、裙、被,或经纬皆丝,或丝经棉纬,挑制花纹,斑斓五色。”继之,由符为霖主修、刘沛编纂,成书于清同治年间、增纂刊刻于光绪年间的《龙山县志》亦云:“土、苗妇女善织锦裙、被,或丝线为之,或间纬以棉,纹陆离有古致。其丝并家出,树桑饲蚕皆有术。又织土布、土绢,皆细致可观。机床低小,布绢幅阔不逾尺。”由此观之,该时期的土家人在织锦时,有的是经纬线全部用丝,有的以丝为经、以棉为纬,且纹饰“陆离有古致”,极大地提高了土锦的质地和装饰艺术效果。
在清代恩施和来凤的方志中,对当地的织造业亦有较多记录。如清道光版《施南府志》载:“妇女居城市者娴女工针黹,居乡者纺绩室中。”由李勖主修、何远鉴和张钧清编纂,刊刻于同治五年(1866)的《来凤县志》,对当时来凤县境内植桑养蚕、缫丝织锦的现状作了较多描述。如志中所云,为发展养蚕织锦业,提高土锦品质,来凤知县丁周曾于清代道光十年(1830年)贴出布告,号召土民植桑养蚕:“丝,亦坚韧,但养蚕者甚少。道光年间,邑侯丁公曾刊示其法,教民蚕桑。”志载:“女勤于织,户有机声”,“城乡四时,纺声不绝。村市皆有机坊,布皆机工为之”。又“妇女多事纺绩,以供衣服”,且“花布,染各色棉纱为经纬,斑然可爱”。当时,来凤地区把土家称为“花布”,应与民间将织锦手艺称为“织花”有关。当地独特着装习俗也促进了织锦业的发展,如志中所云:“男女垂髻,短衣跣足,以布勒额,喜斑斓服色。”相邻于来凤、龙山的重庆酉阳秀山县在晚清时亦有此俗,据清光绪《秀山县志》载:“前史称荆州、沅陵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故章服多以斑布为饰”,“今邑梅、石耶二洞之人并喜裁斑布以为衣,则亦地近习渐,故转相慕效,以成风俗也”,“惟人好佩长刀,喜捕猎,家织斑布,散卖诸落,以为恒业”等。相传,自清早期开始,在酉水流域的诸多土家人就以织锦为“恒业”,一些集镇形成以棉、麻、丝及其制品为主要交易对象的“花纱”集散地。正如同治版《来凤县志》所云:“每逢场期,远近妇女,携纱易棉者,肩相摩踵相接也。”此时的土锦在逐渐兴起的集市墟场中成为交易商品。
纵观土锦自先秦到明清时期的流变,其原料由最初的麻到后来的丝和棉,因其工艺日渐精湛而价与缎同。特别是清雍正四年至十三年(1726年—1735年)“改土归流”之后,政治上、经济和文化上的变化使土锦织造得到了极大地繁荣与发展,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时期。在此背景下,外部族群得以进入土家人世居的武陵山区,加深了土家族和汉族在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交流与融合。统治者政策的转变,以及汉人带入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优良的棉桑蚕品种,使土家人聚居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带动织造等传统手工业的技术革新和行业兴盛,社会需要的亢进也促进了土家织锦在生产数量和质量上的提高等。
五、20世纪几经起落的土家织锦
历经清代中晚期的繁盛之后,绚丽多姿的土锦开始走出武陵大山,名声远播并走出国门。据民国版《龙山县志》(1939年)载:土锦“近有征往长沙、南京及东西各国备品列者,惜千数百年来不知改进……”这种“千数百年来不知改进”的缺憾,加之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各种战乱,致使已具千年历史的土锦逐渐走向衰落。至1940年代末,湖北来凤、湖南龙山和永顺等传统织锦地域的织户已不多,湖北来凤县仅有20余户,西兰卡普的产量亦较少。
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和完成,土家织锦的发展状况有所好转。1953年底,龙山土家织锦被选送参加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首次亮相全国性展览,便获得业内专家学者和织锦同行的关注。由此,土家织锦这朵在武陵大山中落寞绽放千余年的绚烂山花不再孤芳自赏,迎来发展的好时期,各地对织女们的培训亦逐步开始。1957年,湖南省和湖北省分别举行美术作品展览会,龙山和来凤的土家织锦分别参加各省展览。当时有湖南媒体如此报道:“当你踏进民间工艺美术陈列室时,你会感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土家族的打花铺盖,其花纹结构的完整性和色彩的富丽,会使你感到惊讶。”来凤选送的两件土家织锦在“湖北省首届美术作品展览会”会上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1958年至1959年,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编写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史的指示精神,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委托武汉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武汉分院(今中南民族大学前身)和湖北艺术学院(今湖北美术学院前身)组成“土家族文艺调查队”,在鄂西南和湘西北土家族聚居地区展开为期近半年的田野调查,搜集并整理了一批珍贵资料。1959年,调查队完成《土家族文学艺术史》初稿的撰写①该书稿曾拟于1959年向建国十周年献礼,但终因受到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而未能出版。书稿中“土家族工艺美术部分”被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所,于1982年收录至《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之湘西土家族的文学艺术》。1989 年,阮璞先生在此基础上写成了独立的《土家族美术史》,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土家族美术的专著。,书中土家族美术史部分由湖北艺术学院的阮璞先生承担,对土家织锦有较多记录。调研期间,阮璞先生跋山涉水遍访织锦老艺人,获得口头史料,并结合方志史料,从历史源流、名称演绎、民俗内涵、编织技艺,以及材料、色彩、图案和审美等方面对土家织锦作了较为详实的论述。这是我国学术界第一次对土家织锦展开深入研究。调查队美术组其他人员也专门搜了集当时被称为“土花铺盖”的土家织锦图案资料,共搜集有60余种,经整理后挑选出33种在题材、纹样和色彩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最后做成8开精装全彩活页装的《土家族彩织图案集》,1959年9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所知,全国范围内最早对土家织锦展开调查研究并出版研究成果的学术研究活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历经千年传承的土家织锦传统工艺被列为“四旧”,遭到限制与破坏。有些织锦合作社被解散,集镇上的“花纱”交易被取消,从业人员纷纷改行。一些织女即使在家偷偷织一点以换取油盐,亦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割掉。大量的木制织机被劈掉当柴烧,只有少数土家山寨、大队将织锦作为副业,组织少量织女生产。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和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施行,工艺美术得到扶持与发展,并成为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在此背景下,土家织锦得到逐步恢复与发展,织女们开始重操旧业。在湖北来凤、湖南龙山和永顺等土家织锦曾经盛行的地方,一些国营和乡镇土家织锦企业相继开办起来,共计10余家,从业织女数百人。湖南龙山县轻工局也于1984年开办了龙山民族织锦工艺厂,聘请龙山苗儿滩的传奇织女叶玉翠作为终身技术顾问。叶玉翠生于1908年,一生坎坷,命运多舛,手艺精湛,为土家织锦在特殊时期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作品不仅多次参展,还被国家轻工业部一次性收藏62件。1988年在叶玉翠从艺70年时,国家轻工业部授予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这是我国对传统工艺美术从业者所授予的最高荣誉。龙山县为其举办“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玉翠从艺70周年和80寿辰暨土家织锦开发研讨会”。叶玉翠成为土家织锦的第一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是土家织女的典型代表。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工艺美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轻工和文化等部门对土家织锦的发展和研究也倾注了较多精力,土家织锦行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湖南省工艺美术和群众文化系统多次派人赴龙山调研,辅导民间艺人,促进技术革新,并编撰《湖湘织锦》一书。此外,湘西永顺的织锦艺人还改进织机,将幅宽50厘米左右的斜腰机改造成150~200厘米左右的宽织机。在1986年湖北省文化厅和省群众艺术馆举办的“湖北民间美术作品展览”中,来凤县文化馆收集并选送了25件土家织锦作品参展。1987年,该批作品又赴京在中国美术馆参加“首届中国艺术节·湖北民间美术作品展览”。此后,该批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展览,声名广播海内外。1995年,龙山县苗儿滩镇被湖南省文化厅命名为“土家织锦之乡”。上述种种举措,均促进了土家织锦的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纯手工、低效率为特征的传统工艺美术逐渐走入低谷。土家织锦未能幸免,湖南湖北各地曾经红火的土家织锦厂相继倒闭,从业人员散落四方。尽管我国于1997年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但在工艺美术行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收效甚微。
六、21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土家织锦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的逐步重视,特别是自2005年我国全面掀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以来,土家织锦与其他传统手工艺技艺一样,迎来新的春天,并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2006年以湘西自治州作为保护单位的“土家织锦技艺”,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年,龙山县被国家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授予“中国土家织锦之乡”。2008年,龙山县苗儿滩镇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土家织锦之乡”。
2007年,我国首位土家织锦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玉翠的徒弟和侄孙女叶水云,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同一宗族、同一山寨、师徒二人均获得国家级大师称号,在我国目前的443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实为罕见。相对于其他土家织女而言,出生在龙山县苗儿滩叶家寨、现为湘西民族职业学院教师的叶水云,受过相对完整的美术专业学历(中专和大专)教育,她将现代美术知识融入传统织锦工艺中,并在传统土家织锦的挑织工艺、造型和色彩方面有过诸多创造性的改进和发展,成为新时期土家织锦的领军人物。2009年,叶水云与同是龙山苗儿滩的刘代娥,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家族织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同一门手艺,同一个乡镇,有两个人被同时命名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在全国亦不多见。
2009年,来凤土家织锦技艺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0年,来凤织锦艺人刘未香被命名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家族织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11年,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代娥创办的龙山苗儿滩镇捞车河村土家织锦技艺传习所,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3年,来凤土家织锦村被湖北省文化厅列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同年,龙山县技工学校开办了全国首个全日制中级土家织锦工艺班,以学校教育方式来传承土家织锦。秘书处设在龙山的中国少数民族用品协会土家织锦专业委员会,还专门为此编撰了《土家织锦工艺教程》(上下册)。土家织锦是纯手工制品,每个织女的手法都不一样,为了统一质量标准,2015年,湖南省相关部门在龙山发布《土家织锦湖南省地方标准》。
七、结语
传承千年且一度中落的打花铺盖是土家族女子自幼跟女性长辈习得的女红手艺,纹饰高度抽象、色彩斑斓绚丽的土家织锦是土家族文化的象征。从先秦时期的賨布到魏晋时期的阑干细布,到隋唐两宋时期的斑布,再到繁盛于明清时期的土锦,直至土家织锦在20世纪的起起落落,以及在21世纪的传承保护与复兴。名称的变化,反映的不仅是土家织锦工艺不断革新的过程,也见证土家织锦源远流长的演进历史。土家织锦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承载的不仅是武陵山区土家族的历史文化,其数千年的传承流变也是我国诸多传统工艺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