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班组的进化轨迹看产业工人地位之变
2018-01-25

工业革命前的田园生活文 | 国共慧
在一个国家的现代文明进程中,身穿蓝色卡其工装的“产业工人”曾是一个令人引以为豪的职业形象。进入 21 世纪,如火如荼的工业 4.0 进程中,一般创造性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工人将何去何从,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 “回归”呢?通过班组这一工业细胞的进化历程,便可窥得。
班组起源与初进化
班组起源于工业革命前的近现代工厂中。此后,它分别受到工业革命、科学管理思想以及人力资本思想的影响而逐步进化。在工业时代末期演化成以电气化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以精细分工协作为生产模式,以严格的质量管理和生产标准为控制手段的班组团队。我们把这段时期的班组称为工业时代的班组。
班组是在对传统手工工场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并在一座座新建的工厂中迅速蔓延。所以,在诞生之初,班组产生于劳动分工,服务于生产效率,是初步具备制度保障的工人团队。此时的班组特征也十分鲜明:工人大都从事简单生产任务,依靠体力贡献价值,因此个体生理优势(体力)占据主导地位。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诞生大大突破了人类的体力极限,此后,“技术”就成为班组形式和班组建设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
严格意义上的班组出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我们将其定义为班组 1.0。这一时期,工人已经开始从事简单的机器操作,不过由于机器的不完备性,工人的体力优势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机器运转效率和动能。此时的工人配合机器动力开展工作,称为班组 2.0。2.0时代,班组成员开始分类,有些工人开始操作复杂的机器。当然,仍有一部分工人还在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在这个时代的班组中,综合生理优势(体力 + 智力)占据了主导地位。
技术在快速迭代之后,进入了长期的蓄力期,这也迫使工厂主不得不思考,如何利用技术外的因素来提高生产效率。这使得影响班组和组织进化的第二个因素——管理,直接进入人们的视线。
19 世纪末,很多工厂主为了解决生产效率低、雇员数量臃肿、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曾尝试引入计件工资制,然而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泰勒进行了科学管理的最初实践。在米德维尔钢铁厂,泰勒逐渐建立了“任务管理系统”,先是做了工时研究,然后又重新定义了绩效标准,并重新进行了工作设计和人员配置优化,这些班组劳动时间和工作方法的研究,就是《科学管理原理》的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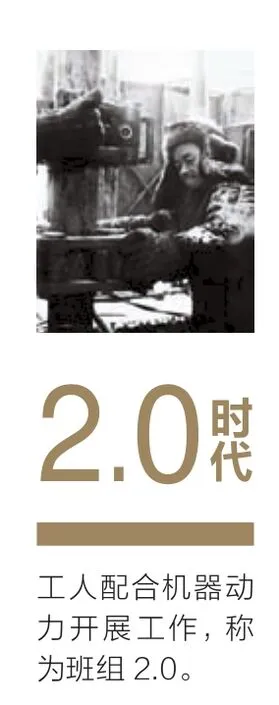

管理因素影响下的班组 2.0 时代,内部也开始进一步优化,班组分工更加明确和精细,工人之间的绩效差异也开始凸显。然而,由于工厂主依然不够尊重工人,也导致了劳资双方矛盾频发。
矛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在一次次的劳资冲突中,工厂主开始意识到,工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劳动者。促成这样观念改革的原因之中,尤其以梅奥的“霍桑试验”为著。
1923 年到 1932 年,梅奥在霍桑工厂开展了长期的试验研究,结果发现工人的“人际关系、工作态度、情感和感觉”对于生产效率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并由此提出了“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假设是关注班组内人性特征,它反映了工人在感情方面的特点和需求,倡导管理者不仅要用规章制度来管理,还要使管理人性化,使班组更加具备活力。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平和发展开始成为世界的主旋律,而“人”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生产要素,开始发挥出它的无限潜能。
班组进化的“螺旋上升”
在工业时代,班组分别历经“技术”“管理”“人的认知”的驱动之后,开始了新一轮的螺旋式进化历程,班组进化进入3.0时代。
随着互联网的勃兴,信息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班组与企业之间、班组与班组之间、班组内部的沟通有效性。
在班组3.0时代,工程师逐步走上班组舞台,工人与工程师同时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同步创造价值,使得班组定义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将这一时代的班组定义为自动化生产条件下,与机器协同开展工作的工人和工程师团队。
信息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全球化。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强,随着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资本和生产越来越集中在大型企业之中,商业社会的主要矛盾变成了规模经济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者日益多样化需求之间的不匹配。
如果说,“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垂直型组织形式、刚性生产、生产者决定论和垄断型市场结构特征”的福特主义代表上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那么此后,“大规模定制、水平型组织形式、消费者主权论、弹性生产、竞合型市场结构”的后福特主义思潮,则直接促使柔性生产、倒三角、前端拉动后端等组织管理方式的出现。
在后福特主义指导下的班组 3.0,开启了面向客户需求的组织运行方式再造之路。在定制化生产条件下,体力劳动基本上被工程师取代,这种组织运行方式,能够快速响应客户,有效满足客户需求,直接提高了班组客户价值创造的能力,因此备受推崇。
在人力资本理论影响下的班组 3.0,依旧在探索如何利用定制化技术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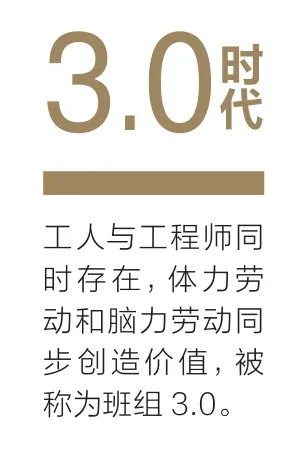
科技变革推动班组进化为“生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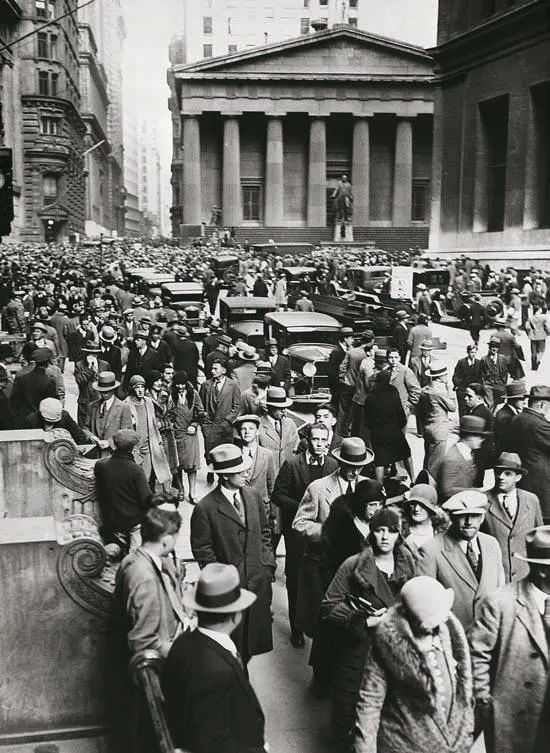
当今,班组正处于信息时代和智慧时代之交。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班组的规模经济与定制化成本,总是无法获得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借着班组进化的逻辑,管理者重新开始思考,如何利用技术的手段,来实现成本和需求的完美结合。这将为班组打开智慧时代的大门。
还好有3D打印,还好有“大云物移”,工业4.0的推进,实现了过去“无人工厂”的畅想。过去成千上万人的流水线,现在只需要几十个工程师就可以搞定,而且成本更低。
在工业智能推动下的班组4.0,内部已经由智能化生产条件下的工程师和技师组成,纯粹的操作性工人没有了用武之地。在4.0时代,班组由过去单一功能的执行单元,变成了兼具决策功能的单元,成为价值创造单元,同时因为“大云物移”技术的加持,班组也开始具备了自我驱动、价值创造、智慧分析、资源响应等特点,从某种抽象的意义上讲,已经可以用“生命体”的概念来解释班组4.0的独特特征了。
随着员工的多能协同和技术的推进,班组的价值创造能力也越来越强,传统指令型的组织管控方式显然无法有效释放班组的潜能。部分优秀的企业,逐步开始升级管理方式,以有效应对技术和员工能力提升带来的生产力。比如,华为的前端铁三角——中端重装旅——后端大平台;海尔的创客小微;国家电网的生命体班组建设等,都在探索“大平台 + 小前端”的运作方式,以期通过管理机制的提升,来配合班组生产力的提升。
诚然,平台型组织尚无明确共识,所以,我们以自组织的方式来指引班组在4.0 时代优化管理机制,通过多中心、分布式、去权威的组织方式激发班组活力。在多中心的自组织运行机制背后,如何释放人性、激活人性,突破员工潜能来释放宇宙能量,以人的能力的提升来配合技术手段的提升和管理机制的优化,成为班组建设的重要课题。
使用人、激励人、发展人,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手段,不同的目的,会带来不同的效果。如果仅仅把员工当作班组实现目标的手段和工具,那班组就无法与员工真正地形成生命共同体。所以,唯有转变观念,把“人”当目的,而非手段,才能在“人”的目的和班组的目的之间找到平衡契合点,使双方为了共同的“目的”去努力、奋斗。

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不断突破自己生理和心理缺陷的历史。在人工智能起步的今天,人类的生理极限,已经远远滞后于技术和机器,如何利用技术升级来突破人类极限,使得班组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确实令人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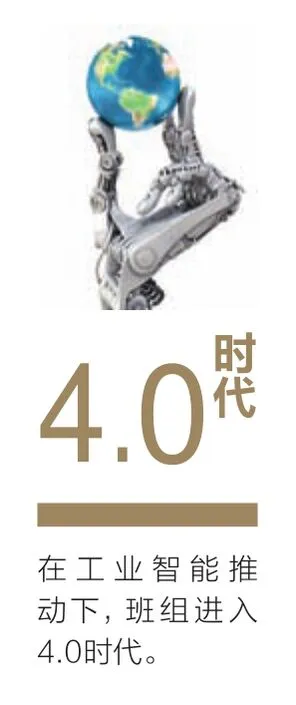
远方的远方到底是何方?
人工智能,使得组织具备了“智慧化”特征,这种智慧化班组,我们称为班组5.0。在这个时代,智能机器开始大量替代班组成员,随着决策下放和多中心权威,各个中心和班组有着各自的独特诉求,协同性和一致性大大降低。自组织的方式,虽然可以激发价值班组的创造活力,但也会使组织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受到一定的掣肘。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沟通将变得无差异、无延迟、无歧义,各种前端信息可以完全保真地呈现在平台上,平台的管理决策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可以实现“绝对理性”,平台的指令,由于控制系统的完备,可以使得前端完全执行。在这样的假设之下,企业将成为超级平台型组织,而班组则成为企业中的超级执行单元。超级平台型组织下的班组内部充满了人机交互与融合的工程师团队,人工智能开始大量取代人类,失去工作的人类社会开始分层为脑力科学家、一般工作者和一般人。脑力科学家创造了智慧的地球,智慧的世界,而人工智能的思维觉醒,也不断地激发人类战胜人工智能的欲望。
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对超人工智能忧心忡忡,比尔·盖茨也认为人工智能会成为人类社会的大麻烦。但这无须多虑,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人类由采集时代进入农业时代,再进入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工业时代是人成为机器的时代,智能时代是机器成为“人”的时代,人类将何去何从?
在脑力科学家的帮助下,人类将进化为超人类,全面发展自身,开发自己的潜能。目前人的大脑只开发了 5%,这个时代脑力科学家将帮助人类将闲置的 95% 都开发出来。超人类具备了人工智能的物理机能和人类的生理机能,是优于一般人类和人工智能的物种。
超人类的出现,使得班组中的主导权重新回到了人类手中,班组也成为超人类主导下的人机协作体。此时的班组,具备了超级生命体的特征,而这目前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未来的智慧班组,就让未来去定义吧,我们甚至不确定在未来“智慧”这个词是否还恰当。我们确实想象不到,远方的远方到底是何方?
人类进入采集时代,大约经过了百万年级的漫长历程,由采集时代进入农业时代,大约经过了万年级的时光,由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大约经过了千年级的光景,工业时代才走过两三百年的路程,就即将迈入智能时代,由此推演下来,由智能时代进入超人类时代,应该不会超过百年光阴。
站在变革的时代节点下,班组还将遵循着“科技——管理——人”的主线螺旋式上升。我们不禁会问,作为班组主体因素的产业工人该何去何从?是坐等时代变革,被机器智能所替代,成为“一般的人”?还是抓住时代机遇,发扬传统的拼搏精神为社会创造价值?选择权掌握在产业工人自己手里,而社会发展也一定会为每个人留下相应的位置。

(更多有关班组进化的知识,请移步《班组进化论》,该书已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