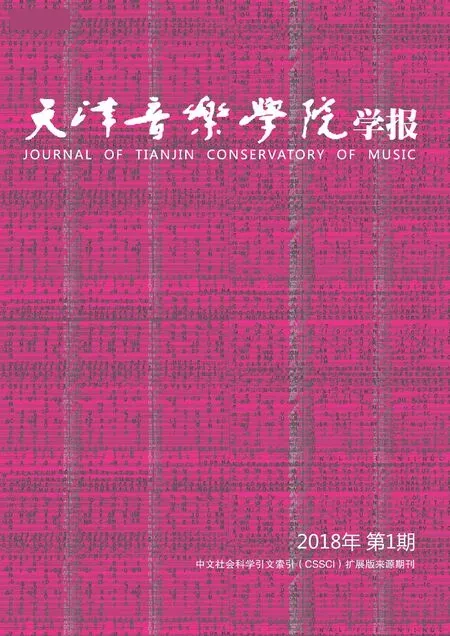中国古代音乐史视域下高句丽音乐研究的得与失
2018-01-24王希丹
王希丹
高句丽音乐研究是中、朝、韩、日等多国学者共同关注的学术议题,其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集安高句丽壁画墓的发现。本文着重分析中国古代音乐史视域下的高句丽音乐研究现状,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学者对其研究的得与失。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中的高句丽音乐研究现状
自公元前37年开始,高句丽成为独立存在的政权,于公元668年覆国,因此在中国历史的时间脉络中,高句丽具有自己的存在生命,历时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高句丽705年的历史发展持续不断,并与周边地区、国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交往关系。因此,探讨高句丽的音乐发展必然需要依托于高句丽自身政权独立的发展历史,当然也不可忽略不同时期的周边音乐文化对其的影响。然而当今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内容中,高句丽音乐的身影虽时有闪现,却尚未体现出其音乐发展的独立性与连续性。
自叶伯和《中国音乐史》开始,郑觐文、许之衡、王光祈、杨荫浏等诸位先生均有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问世,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音乐史著作继续增多,如吴钊、刘东升先生《中国音乐史略》、黄翔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刘再生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郑祖襄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等,其中以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为代表性的丰碑之作。此外,冯文慈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亦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专著中对特定领域着力颇深的难得之作。诚然,大部分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书籍中均对高句丽音乐的文献记载进行了阐述,即在谈及隋唐宫廷俗乐乐部时提及高丽乐①笔者注:据魏存成先生考证指出,约在公元5世纪高句丽改称高丽(参见魏存成:《中原、南方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及高句丽改称高丽时间考》,《史学集刊》2004年第1期,第73-79页),因此目前所见文献中,传入隋唐宫廷燕乐部的高句丽音乐称为“高丽乐”。,然而着墨不多,探讨相对充分的代表性著作便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和《中外音乐交流史》。
(一)《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的高句丽音乐研究
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②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简称“史稿”)在秦汉部分的论述中已经涉及到了集安高句丽壁画墓的乐器图像。在该书第五章中论述阮咸的历史时提及“辽宁辑安古墓壁画中的汉琵琶”,并附图③同注释,第131页,附图见该书图55。。经过分析我们可知,“史稿”所说的“辽宁辑安古墓”即是吉林集安高句丽壁画墓,这幅图是五盔坟5号墓天井第二重顶石西北端所见弹阮咸仙人图④王希丹:《集安高句丽墓壁画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绪论,第ⅩⅩⅤⅢ页。。可能由于材料掌握的缺乏,“史稿”虽然在此处引用了这幅伎乐仙人图,却并未对其所归属的墓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亦未将其与后文中的“高丽乐”研究联系起来。其后,当“史稿”中再次提到高句丽音乐之时,便已将它归入“外国音乐”的行列,在第六章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中,“史稿”谈到了“各族音乐文化的大融合”问题,其中指出公元436年左右,少数民族音乐疏勒乐、外国音乐安国乐、高丽乐传入中原⑤同注释,第161页。。在第九章、第十章隋唐俗乐的探讨中,高句丽音乐内容再次出现。在对隋唐俗乐部的性质进行分析中,“史稿”指出,安国乐、天竺乐、扶南乐和高丽乐均为外国音乐,并指出,西凉乐与高丽乐均受到了龟兹乐的影响⑥同注释,第 215页、第 254-256页。。由此可知,在“史稿”第六章、第九章、第十章所提到的高句丽音乐均指传入中原、在宫廷中流传的宫廷乐部“高丽乐”,并已经将其定位为外国音乐了。
“史稿”作为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中的集大成之作,最为全面、丰富的展现了中国古代音乐历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其中对高句丽音乐的研究在通史著作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尽管该书卷帙浩繁,然而限于多重原因,其对以集安高句丽墓音乐壁画为代表的高句丽音乐资料的使用及研究显得较为薄弱。一方面,尽管高句丽壁画墓的发现、研究在20世纪初已经开始,然而考古、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并未较快地在以“史稿”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著作中得以吸收,这体现于“史稿”中集安高句丽墓音乐壁画与魏晋隋唐时期的高丽乐的内容没有联系起来看待;另一方面,对隋唐俗乐乐部高丽乐的性质直接归于外国音乐也有待商榷。高句丽在历史上定都四次,最初都城为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县附近),公元18年移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附近),公元427年移都平壤(今朝鲜平壤附近)⑦魏存成:《高句丽遗迹》,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公元586年移都长安城(今朝鲜平壤附近)⑧《三国史记·高句丽》载:“(高句丽)自朱蒙立都纥升骨城,历四十年,孺留王二十二年(前18),移都国内城,……都国内,历四百二十五年;长寿王十年(427),移都平壤,历一百五十六年;平原王二十八年(586),移都长安城,历八十三年。宝臧王二十七年(668)而灭。”[高丽]金富轼撰、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高句丽》,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3页。。其中直到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之前,高句丽都是一个建立、发展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国内的音乐文化与中原地区、周边相邻地区交流频繁,此一时期其音乐属于少数民族音乐的范畴;自公元5世纪上半叶高句丽迁都朝鲜半岛北部的平壤,正式成为横跨今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国家,其后的高句丽音乐文化发展除了继续与中原地区交流、触碰之外,增多了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乃至日本的文化交流机会,此一时期其音乐属于外国音乐的范畴。对于以上两个时期音乐性质的划分主要取决于其政权性质的变化,并不一定说明两个时期的音乐发展发生了断裂式的剧变。然而通过集安高句丽墓音乐壁画与朝鲜半岛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墓葬音乐壁画的内容对比我们可知,迁都平壤前后的高句丽国内音乐的确可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此本文指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入北朝的高丽乐仍然属于少数民族音乐,而隋唐时期的俗乐乐部高丽乐,则可以理解为外国音乐了。
(二)《中外音乐交流史》中的高句丽音乐研究
冯文慈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⑨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先秦—清末》,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称“交流史”)是一部专门探讨中国与历史上其他地区、国家音乐交流历史的专著,该书中对西域乐伎的传入、与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乃至东南亚地区的音乐交流均有分述,是首次对中原地区与高句丽的音乐交流进行单篇论述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
在该书第二章“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中谈到了汉时玄菟郡下设高句骊县的音乐风俗,并将汉武帝赐高句丽鼓吹伎人的文献记载与朝鲜半岛安岳3号墓所见的行列图联系起来讨论,指出该壁画反映了汉代鼓吹乐对高句骊的影响⑩同注释,第23页。。在谈到卧箜篌乐器发展之时,“交流史”引用了集安高句丽第17号古坟所见的弹卧箜篌图,并以此说明“根据为数不少的古代朝鲜壁画等可知,卧箜篌在古代朝鲜是相当流行的。”⑪同注释,第 26-27 页。
“交流史”的第四章“繁花似锦的胡乐根植中原”中谈到,隋朝建国初期的宫廷七部乐中有三部外国乐伎,“西域的安国伎、天竺伎和东方邻国的高丽伎”⑫同注释,第56页。。该书在隋唐宫廷乐部七部乐、九部乐和十部乐列表部分亦有相似表述⑬同注释,第64页。。“交流史”第五章“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鼎盛辉煌”的第一节专门探讨了中国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音乐交流,其中的“中国和高句丽的音乐文化交流”部分,便是专门对中国与高句丽的音乐交流问题进行了探讨⑭同注释,第 107-108页。。文中运用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隋书·乐志》等中国史籍中的高句丽使用乐器记载;朝鲜半岛史籍《三国史记》中的《黄鸟歌》、玄琴制造传说记载等;考古资料方面主要是援引了朝鲜学者全畴农文章中对集安高句丽壁画墓、朝鲜半岛安岳3号墓等所见图像所做的乐器研究结论⑮[朝]全畴农撰、奚传续译:《关于高句丽古坟壁画上乐器的研究(续)》,《音乐研究》1959年第3-4期,第85-104页,第87-91页。,但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
由此可知,“交流史”是国内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中首次较为充分的对高句丽音乐资料加以综合分析的著作,其对文献、考古资料均给予了一定重视,并注意了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吸收。然而由于“交流史”写作的特点,该书并非试图单独梳理高句丽音乐史,因此在资料的拣择上多为承袭既有观点。一方面,“交流史”虽然在第二章对汉时的高句骊县音乐风俗有所描述,但是并未说明其与后世高句丽国之间的关系,而在其后的章节中,均将高丽乐的性质定位于外国音乐了;另一方面,在考古资料的使用上,对集安高句丽壁画墓的墓葬情况引用不甚清晰、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与公元4至7世纪朝鲜半岛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壁画墓之间的关系也并未加以厘清,从文中观点可知这一部分的材料和观点主要承袭自朝鲜学者全畴农先生、日本学者林谦三先生的相关文章和著作,因此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
综上所述,尽管高句丽壁画墓的发现与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展开,在历史与考古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然而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中的吸收是较为缓慢的。一方面,受到20世纪50年代将高句丽作为古代朝鲜历史的观点影响⑯马大正:《中国学者的高句丽归属研究评析》,《东北史地》2004年第1期,第6页。,高句丽音乐被直接以“外国音乐”的身份进行探讨;另一方面,早期译成中文的朝鲜学者、日本学者在音乐领域的研究对中国古代音乐史视域下的高句丽音乐研究具有一定影响。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高句丽墓音乐壁画研究可知,直到1980年,考古学者方起东先生开始了对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乐舞图的分析,随后,以集安高句丽墓音乐壁画为代表的高句丽音乐研究逐渐获得了考古、历史、音乐史学等领域专家、学者的更多关注。
二、中国学者高句丽音乐研究的得与失
高句丽是发源于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民族,它建立的同名政权“高句丽”在7个世纪的时间里雄踞中国东北,在公元4至7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身影。如前文所述,高句丽音乐研究从对集安高句丽墓音乐壁画的研究开始。目前所见的最早文章为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发表的《鸭绿江に河畔の高句丽遗迹壁画上い见える歌舞音乐资料》⑰[日]岸边成雄:《鸭绿江に河畔の高句丽遗迹壁画上い见える歌舞音乐资料》,《东洋音乐研究》1937年第1期,第74页。,其后朝鲜学者宋锡夏发表论文《辑安高句丽古坟和乐器》⑱[朝]宋锡夏:《辑安高句丽古坟和乐器》,《春秋》第2卷,1941年,第439-442页。。中国学者中最早对高句丽音乐进行展开性研究的学者是方起东先生,他于1980年发表《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的舞乐》⑲方起东:《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的舞乐》,《文物》1980年第7期,第33-38页。。回首三十余年,中国的高句丽音乐研究有所收获,亦有所缺失,存在着进一步的研究空间。
(一)中国高句丽音乐研究之所得
中国的高句丽音乐研究虽然起步较日本、朝鲜半岛国家为晚,但是在最初的研究过程中便注重开启多国研究视野、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在乐舞研究方面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展开,近年来随着高句丽考古、历史研究的整体发展,高句丽音乐研究也在多方面、多层次的展开,具备了深入研究的基础。总结来说,中国高句丽音乐研究之所得,可以从如下三方面进行论述:
1.较早的注重多国学术视野
虽然中国学者对高句丽音乐进行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方起东先生的《集安高句丽壁画中的舞乐》,然而在日本、朝韩学者的高句丽音乐研究开展之初,中国学界便较早地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既具备了开阔的多国学术视野,又获得了通畅的学术讯息。1959年,《音乐研究》创刊伊始便翻译发表了朝鲜学者全畴农的文章《关于高句丽古坟壁画上乐器的研究》(续)⑳[朝]全畴农撰、奚传续译:《关于高句丽古坟壁画上乐器的研究》(续),《音乐研究》1959年第3-4期,第85-104页,第87-91页。。全文分为“序论”“提供音乐资料的壁画的种类及其性质”“乐器类别论”“乐器的编制和它的年代”“从音乐资料看高句丽音乐的源流”五部分,并在“乐器类别论”部分重点探讨了玄琴、琵琶、角、长笛、横笛、箫、螺贝、建鼓、齐鼓、悬鼓、腰鼓等多种乐器。该文中提到的高句丽墓葬共计11个,包括吉林省集安地区的舞踊墓、三室墓、通沟十七号墓(即五盔坟5号墓)和四神墓,朝鲜半岛地区的安岳1号墓、安岳3号墓、平壤车站前古坟、台城里古坟、双楹塚、龛神塚和江西大墓,涉及乐器图像约70余幅。全氏一文最初发表于朝鲜《文化遗产》1957年第1期,该文篇幅较长、内容丰富,《音乐研究》于1959年分两期连载。中国历史研究内容丰富,高句丽音乐研究虽未成为持续被关注的热点,但是在研究中一直具有一席之地,境外有关高句丽音乐研究的成果也不断被介绍到中国学界。1990年,高洁翻译的《高句丽的音乐、舞蹈和杂技》㉑高洁译:《高句丽的音乐、舞蹈和杂技》,《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0年第1期,第30-38页。一文发表于《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该文译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高句丽文化》的日文版第六章,文中主要结合朝鲜地区的安岳三号墓、药水里墓、平壤站前壁画墓、集安地区的舞踊墓壁画和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探讨。2002年,顾学铭翻译的韩国学者宋芳松先生文章《从音乐史上考察长川1号坟——以壁画的乐器为中心》㉒[韩]宋芳松、顾铭学:《从音乐史上考察长川1号坟——以壁画的乐器为中心》,《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第4辑,北方文物杂志社2002年版,第113-127页。发表于《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该文分为五个部分:“前言”“长川1号坟壁画概观”“长川1号坟壁画乐器探讨”“西域乐器的接受”“长川1号坟之音乐史的意义”。宋芳松先生在该文中指出,长川1号墓中所见乐器包括横笛、五弦琵琶、玄琴、大角、阮咸、长箫、筚篥等8种,并将高句丽的乐器发展分为公元5世纪之前、5世纪之后两个时期进行探讨。该文1985年发表于《韩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一书,1991年宋芳松自译的英文版发表于《亚洲音乐》,其观点有所修正,所述乐器增加为10种㉓Song,Bang-song.“Koguryo Instruments in Tomb No.1 at Ch'ang-ch'uan,Manchuria”,Musicaasiatica,1991,6,pp1-17.。该文首次对长川1号墓乐器进行了专门的综合探讨。2004、2005年,宫宏宇翻译的韩国学者李惠求文章《朝鲜安岳第三号坟壁画中的奏乐图》(上、下)㉔[韩]李惠求著、宫宏宇译:《朝鲜安岳第三号坟壁画中的奏乐图》(上、下),《黄钟》2004年第4期、2005年第1期,第 111-114页,第 136-141页。发表,该文对安岳3号墓的前室跽坐乐队、回廊行列图和后室乐舞图分别进行了探讨,其中涉及乐器包括角、排箫、大立鼓、二重鼓、鼓、铎形乐器、琴筝类乐器、阮咸、洞箫等。作者认为,安岳3号墓的前室壁画乐人图来自汉代宫廷宴飨的黄门鼓吹乐;回廊行列图展现的是汉代另一种鼓吹乐,即武舞铙歌鼓吹,乐队中描绘的都是中国乐器;后室东壁的舞乐图中舞者为来自西域的胡人,然而伴奏乐器都不是来自西域。同时作者指出,该墓的奏乐图意义重大。李惠求先生的韩文原文在1962年发表于《震檀学报》,其后1974年由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普罗汶译成英文发表于《韩国杂志》(Korea Journal),宫宏宇先生的中文译本翻译自英文版、并对照韩文原文,其后发表于2004、2005年的《黄钟》。
除此之外,在相关的中国、韩国、东亚音乐译文中,亦有不少高句丽音乐研究内容被介绍到中国学界。如[日]岸边成雄著《唐代音乐史的研究》㉕[日]岸边成雄著,梁在平、黄志炯译:《唐代音乐史的研究》,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版。中有较详尽的对于高丽伎的讨论,以丝绸之路研究视角看待高句丽音乐遗迹的研究如[日]岸边成雄著《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㉖[日]岸边成雄著、王耀华译:《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版。、[日]岸边成雄著、樊一译:《古代朝鲜的乐器》(续)㉗[日]岸边成雄著、樊一译:《古代朝鲜的乐器》(续),《乐器》1989年第1、2期,第27-29页;第28-32页。、[日]林谦三《东亚乐器考》㉘[日]林谦三著,钱稻孙译,曾维德、张思睿校注:《东亚乐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韩国学者张师勋的《韩国音乐史》㉙[韩]张师勋著、朴春妮译:《韩国音乐史(增补)》,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
基于历史、地域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音乐研究是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等国家学者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自中国的高句丽音乐研究开展以来,便已融入到这样的国际视野之中。全畴农、李惠求、宋芳松三位学者关于高句丽音乐研究的论文均颇有分量,代表了一定时期朝鲜半岛地区高句丽音乐研究的发展水平。日本学者岸边成雄、林谦三具有的东亚学术视野亦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思路。因此可以说,中国的高句丽音乐研究从发展的最初
2.较为充分的乐舞研究
在高句丽音乐研究中,中国学者对乐舞的研究较为充分。1980年方起东写作的《集安高句丽壁画中的舞乐》㉚方起东:《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的舞乐》,《文物》1980第7期,第33-38页。是国内学者写作的首篇高句丽音乐研究文章,影响较大。该篇文章中探讨了舞踊墓群舞图、长川1号墓群舞图和独舞图、麻线沟一号墓乐舞图、通沟十二号墓乐舞图,较为充分的展开了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中的乐舞图像材料,作者有意将其与朝鲜族舞蹈进行比较研究,并认为高句丽乐舞壁画体现了高句丽舞蹈的五个特点:其一,古代高句丽民族民间舞蹈极其兴盛;其二,高句丽的专业舞蹈队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其三,高句丽在公元4、5世纪有男子独舞、男子双人舞、男女群舞多种形式;其四,挥舞长袖是高句丽舞蹈一个鲜明的特色;其五,长袖特色影响并生发了高句丽舞蹈的基本形态。方起东先生在文中指出,根据壁画所知的是公元四、五世纪高句丽舞蹈的印象,而《隋书》、《旧唐书》等文献中记载的高句丽伎乐是稍后公元7至9世纪的高句丽伎乐,两者所反映的时代有所不同。1986年,耿铁华的《高句丽民俗概述》㉛耿铁华:《高句丽民俗概述》,《求是学刊》,1986年第5期,第77-81页。一文分六个部分介绍了高句丽民俗,其中在“歌舞习俗”中结合文献和集安舞踊墓群舞图进行了探讨。1987年,方起东《唐高句丽乐舞札记》㉜方起东:《唐高句丽乐舞札记》,《博物馆研究》1987年第1期,第29-32页。一文是作者对中国史籍中高句丽音乐相关史料的梳理。作者指出高句丽音乐记载的史料主要见于正史高丽乐记载、李白诗歌和杨再思便关注到了多国的学术发展状况,获得了较高的起点。传中。在对《旧唐书》、《新唐书》、《通典》中的高句丽音乐记载分析中作者指出,史料中的高丽乐乐队庞大、具有较强表现力;乐队使用乐器多为中原或西域乐器;隋代高丽乐应有专门为舞蹈伴奏的舞曲;舞人有自己的独特妆扮;高丽乐的节目非常丰富。在对李白诗歌《高句骊》的考释中作者指出,“白马小迟回”中的“马”当为“舄”之误,因此该诗句形容的是舞者的舞蹈脚步。关于《旧唐书》等材料记载的杨再思跳高丽舞一事,作者分析认为其舞容可能与现代朝鲜族农乐舞中的舞“象毛”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方起东先生的两篇关于高句丽舞蹈的研究文章是中国学者研究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乐舞图、高句丽舞蹈研究方面的力作。1990年,耿铁华发表《高句丽民族的长袖舞》㉝耿铁华:《高句丽民族的长袖舞》,载《古民俗研究》第1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137页。一文,以集安四座高句丽墓壁画为主要材料进行高句丽民族长袖舞的研究,该文探讨了壁画墓的分期、高句丽长袖舞的特点和高句丽长袖舞的发展阶段。杨育《谈高句丽壁画中的舞蹈》㉞杨育:《谈高句丽壁画中的舞蹈》,载《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286页。一文从“高句丽壁画中舞蹈的产生与发展”、“社会特征”和“艺术特征”三个方面探讨了高句丽乐舞。该文在集安四座壁画墓基础上加入了安岳3号墓的探讨。王丽萍《浅析高句丽舞乐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㉟王丽萍:《浅析高句丽舞乐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6期,第273-274页。一文探讨了高句丽舞乐的历史地位、对高句丽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和在历史上的作用。赵霞《高句丽乐舞与吴越文化的渊源窥探》㊱赵霞:《高句丽乐舞与吴越文化的渊源窥探》,《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31-35页。一文对高句丽乐舞“极长其袖”的特点与汉代长袖舞进行了比较分析,作者认为高句丽乐舞受到了吴越“白纻舞”的影响。孙作东、李树林《论“高丽乐舞”产生的历史条件》㊲孙作东、李树林:《论“高丽乐舞”产生的历史条件》,《音乐创作》2013年第8期,第150-152页。一文探讨了高句丽乐舞产生历史因素的文献学分析和考古学依据。该文指出绘有高句丽乐舞的壁画墓包括舞踊墓、通沟十二号墓、三室墓、长川1号墓、麻线沟一号墓和五盔坟4号墓。李晓燕《高句丽宫廷舞蹈的历史文化》㊳李晓燕:《高句丽宫廷舞蹈的历史文化》,《乐府新声》2015年第2期,第132-135页。一文中指出,高句丽的宫廷舞蹈包括长袖舞、胡旋舞和舞象帽三种。王希丹《论集安高句丽墓乐舞图中的舞姿》㊴王希丹:《论集安高句丽墓乐舞图中的舞姿》,《乐舞研究》第2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6年版,第60-74页。一文分为集安高句丽墓乐舞图概述、舞姿分类、文献记载中的高句丽舞姿和结论四个部分,该文将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中所见乐舞图的舞姿分为六式,并探讨了舞姿之间的关系及在壁画中的组合方式。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高句丽音乐研究中的高句丽乐舞研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注,以方起东先生为代表。一方面,方先生的文章首次对集安高句丽墓中的音乐壁画进行了统合分析,其对壁画材料与文献材料进行时代区分的方式亦是较为严谨合理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方先生的《唐高丽乐舞札记》一文亦对涉及高句丽音乐的主要史料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其对“白马小迟回”诗句的考证是中国高句丽音乐研究中史料考证的亮点,这一见解对分析高句丽舞姿形态尤为重要。在其后的高句丽乐舞研究中,集安高句丽壁画墓成为研究中的主要材料,中国学者对壁画墓的分期、高句丽舞蹈的艺术特点、历史地位和作用、与其他文化的渊源等方面均进行了探索。随着近年来研究的细化与展开,出现了对高句丽乐舞中特定类别的探讨(如宫廷舞),同时亦有部分学者在文章中引入了朝鲜半岛地区壁画墓的材料,在舞姿的进一步探讨中,对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乐舞图中的舞姿进行分式及组合形式探讨突破了以往文字描述的界限,获得了进一步的规范与量化,为与其他乐舞图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
3.近年来逐步展开的多视角多层次研究
尽管在高句丽音乐研究开展之初,中国的音乐学者、考古学者均有所关注,但是多视角、多层次研究的逐步展开是近年来的事情,特别是自2004年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后,更有力地促进了高句丽相关研究成果的问世,其中音乐方面的研究也逐年增加。除前述乐舞研究之外,在壁画内容综合研究、乐器研究、比较研究、价值与意义研究等方面均有新的进展。第一,高句丽音乐综合研究。田小书的《高句丽乐刍议》㊵田小书:《高句丽乐刍议》,《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22-26页。梳理并分析了高句丽墓中的音乐壁画和文献中的高丽乐记载,其中提到了朝鲜半岛高山洞10号墓的舞蹈壁画;王希丹《集安高句丽音乐文化研究》㊶王希丹:《集安高句丽音乐文化研究》,《乐府新声》2014年第1期,第197-201页。一文从舞蹈、乐器、伎乐天人图三个方面对集安地区的高句丽墓音乐壁画进行了探讨。第二,乐器研究。武家昌《冬寿墓壁画中的乐器及相关问题》㊷武家昌:《冬寿墓壁画中的乐器及相关问题》,《博物馆研究》2006年第1期,第41-52页。试图对冬寿墓中所出现的乐器做专门的考释,作者指出冬寿墓(即安岳3号墓)中涉及的乐器包括鼓、钟、笛、铙、瑟、阮咸、排箫、胡角等多种;王放歌《高句丽古墓壁画中的乐器》㊸王放歌:《高句丽古墓壁画中的乐器》,《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6期,第269-270页。中探讨了文献所载的高句丽乐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的高句丽乐器及高句丽乐器的源流和影响;宋娟《长白山鼓吹乐初探——以高句丽鼓吹乐为中心》㊹宋娟:《长白山鼓吹乐初探——以高句丽鼓吹乐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第1期,第80-84页。是在鼓吹乐这一单一乐种发展历史的背景之下,结合文献与考古的高句丽鼓吹乐资料进行的研究;王希丹《论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的细腰鼓》一文从“高句丽使用细腰鼓类乐器名称考辩”和“从4至10世纪周边细腰鼓实物、图像看其在高句丽的流传”两方面入手,探讨了高句丽使用细腰鼓类乐器的名称、形制和传入时间㊺王希丹:《论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的细腰鼓》,《音乐研究》2016年第2期,第44-56页。。第三,壁画内容比较研究。李殿福《唐代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与高句丽壁画比较研究》㊻李殿福:《唐代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与高句丽壁画比较研究》,《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2期,第38-42页。一文中谈到了壁画中乐器的比较,该文指出,渤海贞孝公主墓所见的乐器与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中所见具有较大不同。第四,研究意义及价值研究。包括徐杰《高句丽音乐研究及其价值》㊼徐杰:《高句丽音乐研究及其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26-28页。、田小书《长川一号墓壁画在高句丽音乐史上的价值》㊽田小书:《长川一号墓壁画在高句丽音乐史上的价值》,《交响》2015年第4期,第40-43页。等。
综上所述,中国的高句丽音乐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后予以展开,最初便具备了宽阔的多国学术视野,在乐舞方面研究较为充分,近年来在多层次、多视角的高句丽音乐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二)中国高句丽音乐研究之缺失
在前文中我们指出,中国音乐史学论著中的高句丽音乐研究仍较为薄弱,从研究阵营来说,历史、考古学者与中国音乐史学者在此课题方面的沟通也显得不足。本文认为,中国的高句丽音乐研究目前所见的不足之处主要由于对其研究资料整理不足、分析不清所致,高句丽音乐研究资料主要见于文献资料和壁画图像两方面,均可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分析。由此,本文指出中国高句丽音乐研究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高句丽音乐文献整理、辨析不足
以目前的研究所见,并未发现高句丽使用自己的语言,也并未发现留存的高句丽自有文献资料,因此记载高句丽的音乐文献多来自于中国史籍记载和朝鲜半岛、日本的后世史籍之中。其中,中国史籍中对高句丽音乐的记载首见于《三国志》,其后有《后汉书》、《梁书》、《魏书》等,自《隋书》开始有俗乐高丽伎的记载,《旧唐书》中始有杨再思跳高丽舞的记载,《乐府诗集》中收有王褒、李白关于高句丽歌舞的诗作,后世类书中也多有关于高句丽音乐的记载;朝鲜半岛史籍所载高句丽音乐内容主要见于《三国史记》、《高丽史》之中,《三国史记》中主要包括高句丽琉璃明王《黄鸟歌》、鼓角自鸣神话、玄琴来源等方面的记写,《高丽史》中记载了留存于王氏高丽时期的三国俗乐中高句丽乐的曲名与解题;日本古籍中记载了高句丽乐师在日本的活动情况。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留下了关于高句丽音乐的相关记载,其中涉及音乐风俗、使用乐器、诗歌、歌词、乐曲名称、舞蹈服饰、乐器来源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系统整理与分析,可以获得对不同时期高句丽音乐的多方面认识。
2.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与朝鲜半岛壁画墓音乐图像关系不清
在以往的高句丽音乐研究中,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与朝鲜半岛壁画墓的关系问题并未引起太多关注。随着高句丽考古、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发展,中、韩、朝部分学者对朝鲜半岛“高句丽壁画墓”概念提出了质疑,并根据墓葬形制、墓室壁画、出土文物等方面特点对公元4至7世纪朝鲜半岛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壁画墓进行了文化归属分析,中国学者赵俊杰指出,在这些壁画墓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汉人墓葬,或者汉化的高句丽人墓葬㊾赵俊杰、梁建军: 《朝鲜境内高句丽壁画墓的分布、形制与壁画主题》,《边疆考古研究》2013 年第13 期,第227-254 页。。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是高句丽政治文化迁移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权力集团与自治领,即使在高句丽迁都之后,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文化也并非在短时间内趋同,亦经过了逐渐交融的过程。因此本文认为,集安高句丽壁画墓是较为明确的高句丽墓葬,其墓葬形制、壁画内容、出土文物反映了高句丽人的世俗生活与精神信仰意识,公元4至7世纪朝鲜半岛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壁画墓中存在高句丽壁画墓,但是也有不属于高句丽壁画墓的墓葬类型,因此不可笼统地将集安高句丽墓音乐壁画与朝鲜半岛壁画墓的音乐内容放在一起,全部当做高句丽墓音乐壁画进行讨论。
例如,在以往高句丽音乐研究讨论中经常出现的安岳3号墓便是汉人墓葬,因此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其中描绘的行列图、乐舞图与集安高句丽壁画墓所见内容迥异;再如德兴里壁画墓,亦为有墨书题记可寻的汉人墓葬;安岳3号墓与德兴里壁画墓均产生于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之前,可以说反映了公元4世纪中叶至公元5世纪初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汉人移民可能存在的音乐文化生活内容,而并非该时期的高句丽音乐生活情态。公元5世纪中叶以降,朝鲜半岛壁画墓经历了逐渐高句丽化的过程,其中出现了与集安高句丽墓相近的音乐壁画,比如玉桃里壁画墓群舞图、高山洞10号墓舞蹈图、江西大墓伎乐仙人图等,这些公元5世纪晚期至公元7世纪初的音乐壁画体现了朝鲜半岛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壁画墓内容与集
赵俊杰、梁建军:《朝鲜境内高句丽壁画墓的分布、形制与壁画主题》,《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第13期,第227-254页。安高句丽壁画墓内容的趋同性,而集安高句丽墓的音乐壁画作为较为典型的高句丽音乐图像,成为解析朝鲜半岛壁画墓音乐图像的重要标尺,也是研究朝鲜半岛壁画墓音乐图像的基础与前提。两者关系的厘清,有助于对高句丽音乐全史、公元4至7世纪朝鲜半岛音乐历史研究的推进。
3.集安高句丽壁画墓音乐图像分类不明
中国的高句丽音乐研究中对集安高句丽壁画墓的材料尤为重视,研究亦多以此为基础。在前述学者的研究中,集安壁画墓乐舞图的研究可谓较为充分。截止2017年6月,目前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所见,绘有舞蹈图像的集安高句丽壁画墓包括舞踊墓、麻线沟一号墓、通沟十二号墓和长川1号墓,对这4座墓葬舞蹈图像的描述和研究自方起东先生的《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的舞乐》一文便已展开。然而集安高句丽墓中的音乐壁画并不止舞蹈场景,而是包括乐舞图和伎乐仙人图两类,乐舞图反映了高句丽的世俗音乐生活,其中出现了舞蹈的伴奏乐器,反映了高句丽人的舞姿、舞者组合形式等内容,集安壁画墓中绘有乐舞图的墓葬产生年代整体上较绘有伎乐仙人图的墓葬为早,且该类乐舞图具有较为独特的高句丽民族风格;伎乐仙人图中描绘的使用乐器包括吹奏乐器、弹拨乐器和打击乐器三大类,涉及墓葬包括舞踊墓、三室墓、长川1号墓、五盔坟4号墓和五盔坟5号墓,共计5座墓葬,以往的研究中多将这些乐器与乐舞图中所见乐器、文献所见乐器混为一处进行探讨,本文认为,伎乐仙人使用乐器可能为高句丽实用乐器,但作为代表信仰世界的音乐图像,需要与代表世俗世界的乐舞图像分开进行探讨,在两类乐器图像进行分别探讨之后,再将其共同归于一处、进行高句丽使用乐器的解析。
此外,集安高句丽墓音乐壁画的分类探讨亦有助于对朝鲜半岛墓葬音乐壁画的进一步研究。集安高句丽壁画墓是目前所知最为典型的高句丽墓葬,其中的音乐图像分为乐舞图、伎乐仙人图两类。朝鲜半岛壁画墓中的音乐图像包括乐舞图、百戏奏乐图、伎乐仙人图和大量的行列图,这与集安高句丽壁画墓所见的音乐图像有较大差距,可知两者可能存在文化归属的差异性㊿王希丹:《集安高句丽墓壁画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5-46页。。由此可知,对集安高句丽墓音乐壁画进行明晰的分类研究,是其壁画材料得以获得充分解析的前提。
4.从音乐文献、音乐图像到音乐史的距离
如前所述,在以往的高句丽使用乐器研究中,曾经出现将文献记载、图像(乐舞和伎乐仙人图)所见的乐器进行叠加、之后进行重新分类的研究方式。通过分析我们可知,文献、图像的资料既分别指向着高句丽音乐发展的不同时期,同时又带有着原有史料的视角与意义功能。从这些文献、音乐图像到音乐史,还需要用审慎的分析建立起一道桥梁。
以文献为例,高句丽音乐记写主要出现于中国正史中的风俗记写和隋唐俗乐的记载之中,风俗记写中的高句丽音乐记载被一笔带过,较为模糊,但通过对比其他东夷民族的风俗记载,又可知其言简意赅、并非言之无物;隋唐俗乐中的高丽乐是从南朝、北朝流入隋唐宫廷,是经过了历次加工和润色的“宫廷”高丽乐,因此在使用乐器上更多的体现了隋唐宫廷俗乐的乐器编配,方起东先生曾指出高丽乐使用乐器多为中原或西域乐器[51]方起东:《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的舞乐》,《文物》1980年第7期,第38页。,然而通过对高丽乐部与其他俗乐部使用乐器的对比分析可知,其中仍然存在高句丽使用的特色乐器,比如桃皮筚篥、义嘴笛等[52]王希丹:《集安高句丽墓壁画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79页。,这些乐器的使用讯息又是风俗记写和音乐图像中所没有出现的内容。
以壁画为例,通过考古学界对集安高句丽壁画墓的研究可知,该地区公开发表的资料中包含音乐壁画的七座高句丽墓主要产生于公元4至7世纪之间,由此可知这些音乐内容所反映的讯息主要集中于公元4至7世纪的四百年间。从反映的题材来说,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中的内容布局具有整体上的功能性,音乐图像作为其中的内容之一必然承担着一定的功能性意义,因为其中的音乐图像并不是为了反映高句丽的音乐历史而描绘,而是首先服务于丧葬文化的意义与内涵。由此可知,音乐图像也与文献同样具有着自己的视角和功能意义。目前所知的高句丽音乐研究材料中尚未发现乐谱或者活态音乐留存,因此所知的文献、音乐图像材料便是了解高句丽音乐的主要方式,从这些材料的分析到高句丽音乐史的辨识,其中需要经历许多谨慎的分析才能架起通向高句丽音乐历史的桥梁、解开高句丽音乐的谜之面纱。
综上所述,中国的高句丽音乐研究起步较日本、朝鲜半岛国家为晚,但最初便具备了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其中对以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为主的高句丽乐舞研究展开得较为充分。近年来高句丽音乐研究逐步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在以往的研究中,相关高句丽音乐记载的文献可以进一步进行整理和分析,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与公元4至7世纪朝鲜半岛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壁画墓的关系尚需厘清,集安高句丽壁画墓的音乐图像亦需进行重新的分类研究,在对这些材料进行汇总的基础上,高句丽音乐研究还有许多进一步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