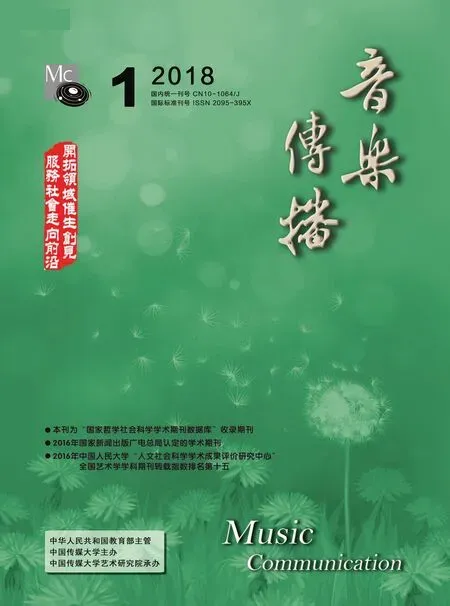音乐选秀网络综艺热播的冷思考
2018-01-24王东昇
■王东昇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
2017年是音乐选秀类节目重归中国电视观众视野的一年,网络视频平台自制的一些相关节目更是争相出现。“Freestyle”“Diss”等一些充满后现代文化色彩的舶来词汇开始随之广泛流行,并引起了一些道德上的争议;许多新人歌手诸如PGOne、欧阳靖、毛不易、魏巡等的某些歌词和生活中的一些表现也成了众多网民持续讨论的热门话题,以至引起了管理部门的密切关注。爱奇艺自制的《中国有嘻哈》(第二季已改名为《中国新说唱》,下文暂用原名)资金投入巨大、创作团队据说也是经验丰富,因此上线不久便引起轰动,成为所谓“现象级”节目。而由企鹅影视、哇唧唧哇和新浪微博联合出品的被宣传为“音乐偶像养成节目”的《明日之子》,也成了近年来网络直播综艺节目中少有的“爆款”之一。应该说,这些“竞秀”机制颇有后现代色彩的音乐选秀类网络综艺,与过往的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相比,无论是模式还是风格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同时其自身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值得关注与研究。
(一)竞秀形式的十足“网感”与过度娱乐化
一般而言,传统的电视音乐选秀节目有着较为充足的制作经费和相对稳定的收视保障,所以与网络音乐选秀节目相比,视听品质更为精致,市场开发也更有保证。尤其是《中国新歌声》、《歌手》等一批“综N代”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凭借开头几季的精良制作,早已积累了较为庞大的观众群,理应是视听消费市场的首选。但遗憾的是,这些“综N代”节目普遍呈现了较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有将原有模式奉为圭臬的趋向。创新性的总体匮乏导致其颓势越发明显,关注度和讨论热度不断下滑。当传统电视音乐选秀节目转移到网络平台播出后,观众的收看方式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对节目的创作理念具有很强的引导性和约束性。老套的、被动的节目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选项更为丰富的网络播放平台,因此创作者必须针对这种新的传受模式对节目进行一定的改造,使得节目更具“网感”。笔者认为,音乐选秀类网络综艺(后文将“网络综艺”简称为“网综”)的独特“网感”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互动广泛音乐选秀网综的互动性不仅体现在节目对讨论话题的设置上,更体现在节目提供给观众互动的多维方式上。互联网带来了传受双方的频繁互动传播,被动接受信息的“沉默的大多数”正转变为拥有更多选择权、主动权和话语权的“清晰的个体”。以“综艺+直播”形态出现的网综节目,借助众多播出平台与社交平台,延展出十分广阔的讨论空间,交流与互动的方式也较传统媒体有了巨大的变化,观众能够在观看节目的同时讨论、“点赞”、打分、评级,甚至是做实时的弹幕交流,极大地调动了参与积极性。《中国有嘻哈》和《明日之子》两档节目都在不同程度上引入了直播的元素。《明日之子》在前三期新手对战后采用了全直播形式,直播赛的在线观看人数最高突破3000万,而《中国有嘻哈》的总决赛通过“尖叫之夜”的预热在“奇秀直播”共迎来5200万人观看,并收到超过600万张选票。这种直播的、实时的播出形式,会让观众产生一种类似于现场观看的紧张感,因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节目的互动之中。此外,这两档节目也都借助微博来带动观众的讨论与参与,《中国有嘻哈》来自微博的投票占总票额的10%,而《明日之子》中,拥有最多选票的选手还会获得5%的投票加权。这样的赛制模式,与节目的运营传播是深入地、广泛地结合到一起的。
评判多元所谓多元评判,就是指选秀节目中的评委和观众对不同类型选手的自身价值在予以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多角度的评审。互联网的兴盛为人们自由表达的愿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网上的多元话语表达为人们搭建了一个人较为理想的抒发己见、沟通交流的场域。尤其是“网生一代”,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梦想和追求更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传统音乐选秀中相对单一的评判规则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今时代与个体发展模式的多元化趋势。所以说,一档音乐选秀节目想要被更多年轻人所接受,对传统的单一评审赛制进行改造就几乎是必然的。作为纯网综的《明日之子》在竞秀策划上就进行了更为大胆的突破与创新:在竞选渠道上,它抛弃了以地域为标准的赛区划分,采用了更符合网络特性的“盛世美颜”、“盛世独秀”、“盛世魔音”三大“赛道”的制度;在评选机制上,它颠覆了以往选秀节目中评委做主、观众追星的模式,将传统的专业评审与大众评审改为“星推”和“粉推”两种形式,在“星推”评审中又划分出“首席”、“实力”和“才华”三种标准。在一档节目之中让三种不同的选拔标准共存,不仅体现了节目创作者对互联网平台节目制作理念的深入发掘,也体现出节目组倡导的多元评判取向,即给选手和评委更为广阔的自我表达空间。
语态年轻在视听传媒领域中,“语态”是一个外围的概念,指视觉、听觉、语境以及风格呈现等多方面的综合样态。它不仅传递着节目架构的基本形式,也承载着极为个性化、风格化的艺术特色。音乐选秀网综中的网感呈现,与“语态”和观众的心理共鸣同样是密不可分的。网综节目的受众以年轻人为主,尤其是“网生代”用户,正不断成长并逐渐成为网综节目最大的受众群体。据说,《明日之子》的受众群中12至24岁的占约60%,因此节目的整体风格必须满足年轻网民的更多期待,并在节目的内容与形式中注入一定的新鲜与“前卫”元素,在此基础上再努力超越他们的审美期待视野。“星推、粉推”的赛制与具体流程,也都体现出该节目明显的年轻化创作倾向,杨幂、薛之谦、华晨宇三位“星推官”以及张大大、好妹妹乐队、苏运莹等嘉宾的话语和形象风格也都带有很强的时尚感,“二次元”选手荷兹的加入更是引起了评论上的分化。
娱乐过度娱乐是人类生命本能的一种自然显现。音乐选秀网综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其中的娱乐元素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娱乐性压倒观赏性、艺术性、思想性,成为一档节目的主导时,就会带来各种问题,比如音乐品质的低下、社会意识的淡薄、文化本真的疏离、艺术精神的空洞等,这些已经被不少评论者乃至普通观众所诟病。比如某档以方言和流行音乐的结合为特色的音乐网综,仅从策划角度看,它的表现形式十分有价值,但它在具体的创作中却有步入误区的嫌疑,时常展现出某种媚俗之态,让人觉得节目更想追求的是商业利益的实现。很明显,这种创作理念和制作方法是不太可取的。从推广方言歌曲到后来的糟蹋传统,过度娱乐化的创作倾向、对流行音乐过于随意的利用心理,应是出现这种滑坡的主要原因。
(二)音乐内容类型多元与质量把控缺位
音乐选秀类网综在音乐内容的选择范围上有明显的拓宽,其创新路径至少可以总结为以下两条。
一是拓宽曲风,挖掘小众领域。爵士乐、布鲁斯、雷鬼、嘻哈等各种在中国较为小众的音乐类型逐渐受到创作者的注意,并被转化为节目策划的基本创意源。比如嘻哈是当今西方流行乐坛较为主流的类型之一,起源于黑人音乐并在不少国家广泛流行。在中国,嘻哈音乐及其延展出的嘻哈文化一直处于带有“小众”与“地下”的隐秘标签,从而只在小范围内传播的状态,主流媒体对其的介绍十分罕见。因争议而受到规制的《中国有嘻哈》即是当下音乐选秀节目市场细分化的产物,其创新突破点正是对准了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嘻哈音乐,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激烈的竞秀。尽管某些选手的歌词和精神面貌是否值得广泛传播引发了议论,并由此导致了节目发展的一些波折,但仅就这种体裁本身而言,直白且富有力量感的情感表达依然是年轻人所喜爱和追捧的。因此,我们要追求的应该是将其尽可能引导到“正能量”的方向上去。
二是将本土传统元素与流行音乐相结合。例如,由爱奇艺、尚众传播联合出品,光启传媒制作的方言音乐综艺节目《十三亿分贝》就大胆尝试以“方言+音乐”作为创新的突破口,在北京、沈阳、长沙、西安、杭州、广州、成都等七座城市集结80组方言音乐人争夺全国大奖。这档节目的整体风格轻松诙谐,其文化元素的组合方式也颇有新鲜感。
但是,与传统电视音乐竞秀节目《中国好声音》、《歌手》等相比,2017年热播的“现象级”音乐选秀网综有不少都暴露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那就是作为本该以音乐为内核的选秀节目,展露出了对市场的过多妥协、对音乐品质追求的逐渐忽视。以最为火爆的《中国有嘻哈》为例,这档节目的确开创了一个小小的先河,挖掘了许多有潜质的歌手,也有助于嘻哈音乐通过交流和碰撞开始与主流音乐文化的无形的融合过程,节目的总冠军更是登上了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的舞台,但实际上许多观众依然看重的是这个节目的“噱头”而不是节目本身的内容价值。在该节目中亮相的众多音乐作品,能被称为精品、被观众广泛认可和传播的依然太少。中英文混杂、强押韵脚、大量的翻唱改编、西方色彩严重等现象都反映出中国嘻哈音乐远未成熟,作品中即便是“本真”的人生感悟也难免略显苍白,对社会的议论也略显浅薄,于是就更难奢求艺术性与思想性了。我们也能从这点中看出,节目组把太多的精力聚集在了赛制流程、市场运作与宣传方面,而在音乐制作水准的把控上则有相对明显的不足。
(三)此类节目的延续性问题与未来转型
前面已经提到,热门综艺节目的第二季、第三季等被称为“综N代”的节目,在当下综艺节目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综N代”节目往往延续旧有的节目模型,仅根据当下热点和特殊情况进行微调,虽然形成了一种体系化的制作模式,塑造了自己的节目品牌,但一味固守已经取得成绩的节目模式也很容易导致缺乏创新动力,进而丧失新鲜感与趣味性,不再具有超越观众的审美期待视野的能力,于是观众的忠实度与收视黏度也会随之下降。回望处于“综N代”阶段的《中国新歌声》,它刚进入市场时,也曾凭借其独特的策划与竞秀机制取得了轰动效应和相关的商业回报,但目前似乎已经开始被一些“喜新厌旧”的观众所逐渐远离。
老牌音乐选秀《超级女声》的“后代”《2016超级女声》转移到网络平台播出后,其前期宣传的确引起了受众的短暂关注,但播出期间的表现也不尽人意,关注度、讨论度和话题度看来都没有达到策划者的预期。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这档节目对原有节目模式的依赖性不可能不强,于是没有针对互联网综艺在创作与传播上的特点对节目的策划进行足够充分的改造。同时,我们也看到《2017快乐男声》吸取了教训,既以高度知名的《快乐男声》为品牌基础,又尝试了更具新意的竞秀策划。在选拔机制上,《2017快乐男声》取消了传统电视音乐选秀惯用的短信投票、专业评委、媒体评委表决等方式,采用了视频与直播结合的投票评选模式,大大提升了观众的直接参与度。在城市赛制中,节目还设立了由200位风格迥异的少女观众组成的所谓“挑食少女团”,由他们决定选手的去留,这一创意至少会令许多男女青年观众相当感兴趣。
与此同时,《中国有嘻哈》即便不考虑音乐体裁引起的争议,也面临着选手缺乏与模式难以改动的双重难题,节目的延续性问题不容忽视。毕竟在中国喜欢和制作嘻哈音乐的人群还属于少数,而节目已经将华人嘻哈圈里水平较为上乘的人请了个遍。所以,其后续节目的策划可以结合中国嘻哈音乐与网络传播的特性打造视角异于前季但又有深层连续性的新节目,比如进行中外嘻哈音乐交流对抗之类,让“养成类”、跨界类、原创音乐类的节目类型元素交融进来,为这类原本出身于“地下”的音乐的正规化、健康化发展提供创作阵地与宣传平台。
毫无疑问,网络平台正在成为视听消费最直接的渠道和最重要的内容供给者之一,这一变局必将影响音乐选秀节目的生产与传播模式。因此,在剔除病症的前提下,创作者理应在坚持和秉承年轻化、多元化、互动化、时尚化、专业化的互联网精神中把握节目的创作要素,使得音乐选秀节目在网络播放平台上取得内容的多元化创新、形式和赛制的多样化呈现。更重为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娱乐化形式与艺术内容表达之间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讲的,“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音乐选秀网综更加注重文化内涵与艺术精神的呈现,推出更多充满时代精神并富有趣味,亦能被年轻一代广泛接受与认同的作品,是此间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