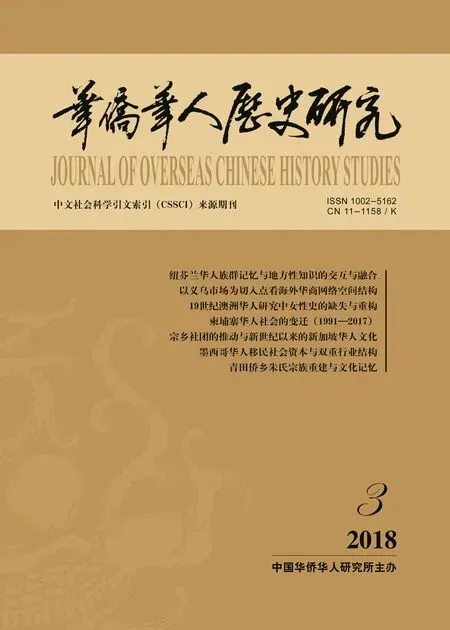论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华人学者的红学研究
2018-01-23武迪
武 迪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北京 100081)
一、美国红学研究现状及问题
从清末以来,《红楼梦》及红学研究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海外红学的兴起,一是得益于《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红楼梦》首先是在中华文化所波及、影响的周边国度流传开来的①胡文彬在《〈红楼梦〉在国外》一书中指出:“据日本学者的研究,《红楼梦》一书是于1793年(日本宽政五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从浙江的乍浦传入日本的。”同书指出“《红楼梦》传入朝鲜的时间最迟不会在道光朝以后”,另据19世纪初的朝鲜学者的著述已有关于《红楼梦》记载的情况看,大约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已有《红楼梦》传入朝鲜。《红楼梦》传入泰国的时间大约在拉玛二世时期,最晚不晚于1825年。道光十年(1830),沙皇俄国东正教使团访华,其中有一名大学生库尔梁德采夫携带了一部抄本《石头记》回国。此抄本于1964年在列宁格勒亚洲人民研究所分所被发现,后简称为“列藏本”。,在海外影响的扩大同时还得力于外文译本、译介文字的出现和传播。②1830年,英国人戴维斯翻译了《红楼梦》的部分章回,并发表在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杂志第2期上;《红楼梦》的英译本最早出现在1842年前后,由罗伯特·汤姆(R·Thom)翻译并发表在《中国话》(The Chinese Speaker)上。约五十年后,乔利(H·Bencraft·Joly)翻译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红楼梦》英译本。此外,19世纪以来《红楼梦》还出现过日文本、德文本、法文本等。二是国外研究者对《红楼梦》青睐有加,发表、出版了诸多有关《红楼梦》的论著,推动《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③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Giles)曾在“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一书中介绍曹雪芹的相关信息,并认为他是《红楼梦》的作者。他在另一部名为“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书中用了两万字的篇幅介绍了《红楼梦》的相关情况。参见Giles Herbert, 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London,1898;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London,1901.另外,赛珍珠在1938年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发言“The Chinese Novel”(《中国小说》)也评价了《红楼梦》。参见Buck Pearl S, The Chinese Novel,London,1939.美国学者浦安迪(Andrew H.Plaks)在20世纪70年代的博士论文也以《红楼梦》为对象的。参见Plaks.Andrew H. , 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像浦安迪一样专心于中国古典小说和《红楼梦》研究的汉学家还有苏联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英国霍克思(David Hawkes)和闵福德(John Minford)等。三是世界各国的华人学者和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对红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产生了一批丰富的成果。应该说,海外红学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海外华人学者的贡献。夏志清(C.T.Hsia)、周策纵(Zhou Cezong)、余英时(Ying-shih Yu)、赵冈、唐德刚(Te-Kong Tong)、余国藩(Anthony C. Yu)、黄卫总(Martin. W.Huang)、陈庆浩、叶嘉莹等一批华人学者在中国文学和红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对红学的壮大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一个极富特色的的异域文化现象。
《红楼梦》传入美国的时间较晚,但美国红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海外他国难望其项背,并直接推动了红学专业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到来。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二战的结束,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对人才有着巨大吸引力。美国出于国家战略需要,鼓励国内各大高校、科研机构从事有关中国、苏联等“敌国”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教学。在这种机缘的策动下,汉学研究在美国逐步发展起来。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汉学”演变为“中国学”,以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国学”的特征是以近现代中国研究为主;在研究方法上注意采用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之理论方法;注重实用性。参见张惠:《红楼梦在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81页。美国国内许多高校,如后来在红学研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普林斯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等都筹办了东方系(东方语言文学系)或扩建其规模,并引进了大量来自中国(主要是港台地区)的留学生和专业人才,为美国红学研究的突进打下了坚实基础。⑤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国防教育法”,鼓励美国青年学习外国语言。之所以与国防有关,无非是知己知彼的意思,因为在法律中规定要修习的外国语,当时,大部分是与美国为“敌国”的语言,如中、苏与东欧,还有一些远东、近东以及非洲的语言。政府在各大学广设奖学金,成立研究中心,以招揽学生,学习西欧以外的语言。参见柳无忌:《柳无忌散文选—古稀旧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129页。另一方面,美国在1943年和1965年先后废止排华法案,调整移民政策限制,为华人移民提供了入美学习、交流、工作、定居的机会。如今所知的曾活跃于美国学界并涉足红学的著名华人学者,如周策纵、唐德刚、夏志清、赵冈、余英时、余国藩等都是在此前后抵美求学的。①周策纵1948年留美,后获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夏志清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留美,后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唐德刚1948年留美,195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赵冈1962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余英时1956年留美,后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余国藩1956年至美国霍顿学院学习历史、英语文学,后至富勒神学院攻读神学,196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与此同时,对美国红学极有影响的胡适、张爱玲等人也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旅寓或定居美国。他们的红学研究不仅对美国汉学研究有所裨益,更拨动了中国红学研究者的敏感神经,获得了中国红学界的诸多反馈——这些可贵的建议和意见,最终都将反哺中国的红学研究。
旅美华人在海外红学研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值得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当前涉及此领域的论著较少,代表性的有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书中第十三章谈及美国的红学研究,侧重《红楼梦》在美国的传播和美国学者的研究,较少涉及华人学者。高淮生的海外学人红学研究综述系列文章,分别谈及美国华人学者周策纵、余英时、余国藩等人,偏重对红学的探讨和对海外学人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较少从华人学者的身份、教育、文化背景加以审视。张惠《红楼梦在美国》是目前所见对美国红学研究总结、归纳、分析最深入的,涉及1960年以来的美国红学研究的整体情况,着重分析了美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浦安迪(Andrew H. Plaks),华人学者夏志清、余英时、余国藩、黄卫总等人的红学研究以及美国社会、文化和各方面影响因素,对华人研究者的整体性关照较少。
通过对美国华人学者之红学研究的整体审视,发现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如美国华人学者的身份、教育、文化背景对他们的红学研究有哪些影响?他们的红学研究对海外红学、汉学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又是通过哪些方式推动这种发展的?等等。本文着力于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二、华人学者的身份背景与跨学科研究范式
美国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教育科研等诸多背景与中国颇多不同,故其红学研究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面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红学研究以版本、曹学及文本研究为主,而美国的红学研究则呈现出更为活跃、自由的状态——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统计学等多个学科的方法及学理思路被应用于红学研究中。
在红学研究中,华人研究者别具一些优势:他们早年接受过系统的中式教育,谙熟中国的语言、文化,胜于国外学者。同时,他们又接受了西式教育,吸收、借鉴了西方思想和文化成果,其知识体系和理论化程度领先同时的中国学者。加之,美国国家政策鼓励学者从事外国语言、文学、政治、社会等领域的研究。旅美学者不仅享受一定的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撑,还在多元文化氛围中不断汲养,并利用在美高校任教、交流、访问的机会,将所获得的红学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推而广之,并与海外汉学家一争高下。②美国福特基金会在1960—1962年期间为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等15所大学提供了十年期和五年期的用于非西方研究的总计达2650万美元的捐助款项。参见韩铁:《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9~142页。据统计,1959—1970年,联邦政府对中国研究的拨款总额达到了1504万美元,高校对中国研究的投入近1500万美元。相比于1928年全美高校选修中国课程的学生人数不超过6000人,1960年,全美高校选修中国课程的本科生已超过17000人。高校中增设了为数不少的教学研究职位,1960年担任中国课程教学的专职教师达到480位,1969年增加到500~600位。参见张惠:《红楼梦在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83页。
(一)心理学时域下的红学研究
夏志清作为早期美国红学研究者,自觉承担起在美国传播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化责任。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在《批评》上发表了《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1],1968年又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此书代表了他在《红楼梦》研究上的主要范式——心理学研究方法,其目的在于向西方普通读者宣讲中国优秀的古典小说。西方读者缺乏汉语基础和阅读经验,在阅读中国古典小说时需要引导和阐释。夏志清说:“我无意于去评说当今红学研究中所有的争论和猜测,因为这对一般的读者无甚帮助。”[2]这直接影响了他在红学研究上的偏向,即重视运用西方理论解读《红楼梦》和读者的阅读感悟。因此,夏志清给予薛宝钗以客观公允的评价,提出了与大陆学者相左的学术见解——扬钗抑黛。事实证明,夏志清许多在当时看似不合时宜的观点,在日后海内外红学研究中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夏氏在从事红学研究时,习惯将西方理论融入红学研究。他采用基督教的“圣爱论”阐释《红楼梦》,重视爱与怜悯在《红楼梦》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要解读蕴藏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哲学元素,不能忽视心理学方法的应用。《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悲剧书写的巅峰之作,同样是一部关乎“心理现实主义”的伟大创作。[3]夏氏借助西方心理学研究方法,把当时中国学者由外向内、由社会到人心的研究范式,调整为一种通过开掘人物内心世界,把握人物心理动态,使人物带有独立的人格,进而再探究其形象及叙事作用的研究范式。如果说王国维将人生痛苦归结为欲望使然,那么夏志清对痛苦根源的理解则不尽相同。他认为贾宝玉要真正达到个人的解脱,关键并非放弃欲望,而是放弃爱与怜悯,只有将对美和芳龄女子的执念抛之脑后,才能真正了却尘缘,实现自我解脱。[4]
“扬钗抑黛”说是夏志清红学研究的另一创见。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分析薛宝钗和林黛玉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认为“在与宝玉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女性中,宝钗与袭人都是明白事理的人;而跟她们相对的,黛玉和晴雯却是敏感的、神经质的、不切实际的……而今宝钗和袭人被称作封建走狗,尽管他们真正的罪行还是因为夺走了黛玉的婚姻幸福以及生命。”[5]这种对宝钗、袭人的偏见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和民族认知有着密切关系,体现着国人欣赏黛玉之美而对弱势者抱有同情的民族心理。而那些以西方文论、文化解读《红楼梦》的研究者则为宝钗打抱不平。[6]夏氏与当时大陆学者的意见相左,很大程度上是他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理论学习和学术训练,并有意识地将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相融合并加以应用的结果。
(二)华人学者的实证路径
20世纪70年代,美国红学研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陈维昭曾指出“1949年至1976年……海外红学却以另一种姿态迅速兴起,并放射出斑斓的色彩。”[7]华人学者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国汉学家以及青年华裔学者对《红楼梦》版本考证、曹氏家世等实证研究不甚关心。究其原因,一是中美远隔千里,获取相关研究资料实属不易。汉学在美国学术界原属边缘学科,版本、家世研究在美国学术界也处境尴尬。二是两国社会、家庭结构存在着巨大差异。汉学家们对上及远祖,旁及叔伯昆仲的家世研究和中国家族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宗法制度比较陌生。因此,实证研究的重任便落到了华人学者的肩上。
作为美国红学界的早期代表,赵冈、唐德刚等学者面临当时中美交流不畅的困境①赵冈的《红楼梦新探》在1970年由香港文艺书屋出版,周汝昌回忆:“那时还没有实行开放政策,外面的书物,我个人是看不到的,后蒙友人寄赠一部,也被海关卡住,费了周折,才得准许进口。”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探·序》,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5页。,本着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原则,以中国传统实证方法融合跨学科方法开展红学研究,实为可贵。尤其是以实证见长的赵冈,其代表作《红楼梦新探》《红楼梦研究新编》等在美国红学界可谓独树一帜。余英时曾说:“赵冈的基本方向还是考证、版本方面,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最大,在海外的考证派,他是代表性的人物。”[8]这是极为中肯的评价。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红学界正酝酿着一次“红学革命”的风潮——“这个可能建立的新‘典范’是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造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9]。余英时对当时已僵化的“自传说”和过分偏重考证的“外学”嗤之以鼻,引起了极大的学术反响。在这种情况下,赵冈坚持实证研究,实属不易。周汝昌不无赞许地说:“《新探》(赵冈《红楼梦新探》)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特立独行地赞助支持了‘外学’的威风与意气。”[10]作为经济学家的赵冈,文史研究原非其所长,但他能利用经济学、社会学等跨学科方法研究《红楼梦》,如在《红楼梦新探》中谈及康熙与江南双季稻之种植等问题,都表现了他开阔的学术视阈下的研究成果。
与赵氏同侪的唐德刚,作为胡适的入室弟子,也与《红楼梦》有着密切的联系。唐氏看重将“社会科学方法”引入红学之中。①“盖新兴社会科学中诸‘法则’与‘概念’,极多均可引入作研讨新红学之新方向。”唐德刚认为弗洛伊德之唯性论、马恩列斯之阶级分析说、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研究中之种种成果,均可引入红学研究以供思考。参见唐德刚:《史学与红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0页。作为在一个农村中的大家族里长大的青年,唐德刚对“那种有条不紊的宗法结构和错综复杂的人事纠纷,以及表兄妹之间谈情说爱的故事”有着亲身体验,这是域外研究者不具备的先天优势。他了解一个作家成长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对其人的深刻影响,因此他重视文化的冲突,特别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任教时,对中西方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在红学研究中,他特重“满汉文化冲突”问题,认为应该从社会科学层面揭示这一文化冲突的概念。1980年在第一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他将“数十年久积心头之‘社会科学处理方法’以治‘红学’之法螺举例再吹之。”虽然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困难和限制,但这种高屋建瓴的学术见地仍是可供借镜的。
(三)继承汉学精神和应用信息技术
美国红学到了20世纪80年代临近一个拐点。在此之前,欧美裔研究者占较大比重;而在80年代,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是华人学者。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周策纵,他作为国际红楼梦研究会的主席,第一、二届国际红学研讨会的推动者、主持者,在海内外红学界影响巨大。
周策纵在中国考据学的基础上,融合社会科学方法、信息技术进行红学研究,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关联。周氏在旅美求学之前,已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等有了深入了解。1948年留学美国的经历促使他的治学发生变化。在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期间,他对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有了直观感受,从中逐渐摸索出一条适己的治学路径[11]。他是政治学博士出身,社会科学,历史学治学方法与精神主导其资料分析,讲究事实证据,客观史学,始终严格监控着红学界望文生义的凭臆测、空疏的解读。加上他的校勘、训诂、考证的功夫高强,及很客观的史学训练,使他很清醒地看待胡适及后来的学者。应该说,西方汉学精神在周氏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以西方汉学精神,突破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其研究往往出于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其原动力是纯粹趣味。”[12]王润华曾指出“在美国受了当时西方学术思潮与方法的影响,……曹红学研究实际上与目前西方学术主流的文化研究方法与精神是一致的。”②周策纵在1950年提出以“曹红学”来称呼他的《红楼梦》及其作者的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建构从广大的人文社会视野与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他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注重版本、目录、注释、考据的清代朴学的考据传统,同时又加强中国学的方法与态度,企图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多元的观点与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考据训诂结合,应用文字考证训诂和版本校勘,同时也把现代语言学、文学批评、比较文学、计算机科技带进曹红学研究。参见王润华:《周策纵的曹红学:文化研究新典范》,《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6辑。周策纵的不少成果正是这种严谨、精致的汉学精神在现实中的具化操作,他摒弃浮名、穷尽一生心力去专注于小问题的研讨,是值得学习的。
周策纵既提倡学习胡适考证之法,又主张“要用中外文学理论批评和比较文学的方法去分析、接受和评论小说本身”,鼓励各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法的应用,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角度去研究。[13]这种治学方法的总结,一方面是针对“只考证、不阐释”研究方法的反驳。他希望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研究,将红学研究从“为考证”的泥淖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这种治学方法的选择与他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在海外求学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在美国求学的几年中,周氏逐渐体认到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上的缺陷——逻辑不甚严密和认知意识偏弱。因此,他将大量精力放在中西方哲学、政治学方面,并希望这种“认知”的强化有助于促进红学研究的发展。
周策纵、唐德刚等华人学者的学术主张,不仅被贯彻到各自的科研中,还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加以实践。周策纵鼓励学生以发散思维、跨学科的手段处理《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将文本研究与语言学、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的研究融合起来,对红学研究颇有裨益;另一方面,周氏倡导从人文学科中“跳出去”,在信息革命伊始便主张利用计算机和数据统计技术研究《红楼梦》,可谓是一次创举。周氏的学生黄传嘉、陈炳藻先后通过计算机数据统计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和新成果的诞生不能不归功于周策纵的启发。
三、华人学者“还红学以文学”的努力
自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问世,曹雪芹自传说便成为新红学的核心观点,版本、曹学、探佚等开始成为研究主流,文学与艺术层面的研究反而稀见了。这样一来,不仅旧红学、索隐派的影响力被极大削弱,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批评研究也被阻塞了出路。对这种研究内部危机的认知,海外华人学者更为敏感。程步奎指出:“这种考据材料,主要属于史学及版本学范围,基本不涉及《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的艺术成就……更由于过分探索曹雪芹的家世,使‘红学’转为‘曹学’,成了系谱学研究了。”[14]程氏之说与余英时主张的核心观念——红学革命及“两个世界论”—如出一辙。
(一)余英时:红学革命与新典范的建立
余英时作为享誉世界的华人学者,他所倡导的“红学革命”是对新红学内部存在的危机做出的主动回应。余氏学说巧妙地利用了孔恩(Thomas.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到的“典范”(Paradigm)①孔恩认为,广义的“典范”指一门科学研究中的圈套信仰、价值和技术(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fs,values,and techniques),因此又可称为“学科的型范”(disciplinary matrix )。狭义的“典范”则指一门科学在常态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examplars or shared examples)。这个狭义的“典范”也是“学科的型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是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之学,从学理上反思新红学产生以来存在的复杂而根深蒂固的“危机”—原有典范面临着技术的崩溃。
新红学面临的困境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突显在新红学的“典范”过度依赖考证和新材料的发现,“新红学”面临的问题是“过分地追求外证……结果是让边缘问题占据了重心问题的位置”[15],忽视了《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这一典范在1954年批胡(适)、批俞(平伯)运动中得到一定调整,李希凡、蓝翎所提倡的封建社会斗争论和阶级分析法走到台前。但余英时认为“它(李、蓝的研究方法)在‘解决问题’的常态学术工作方面无法起示范的作用”[16],这种研究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机械、生硬地套用在红学研究中的一种借题发挥。余英时对此提出红学研究的新典范,应该是把研究重心放在“小说的创造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鼓励红学研究从专注于考证,转向关注文学和艺术的研究。这种基于学术史及学理的反思—“凡是从小说的观点,根据《红楼梦》本文及脂批来发掘作者的创作意图的论述都可以归之于红学革命的旗帜之下。”[17]在当时的大陆还少有人提。值得注意的是,俞平伯在晚年的反思中与余英时达成了默契。②俞平伯对余英时观点的呼应是在1987年1月7日《中报》第17版上刊发的,比余英时提出“红学革命”的倡议晚了十年。
余英时的“红学革命”和新典范在香港一经刊发,便在海内外产生极大反响,引发考证派的强烈反弹,以周汝昌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以及赵冈等旅美学者都提出了商榷意见。周汝昌说:“奇怪的是采用者把考证版本也看成是‘外学’,而宣称只有研究‘作品本身’才是内学;亦即‘红学革命’之后……真好像红学已经进入了另一‘世界’了!其实这真是(不过是)一种错觉与幻觉。”[18]当然,余英时在提倡“红学革命”和新典范的建立的同时,并未抹杀考证在红学研究中取得的突出成绩。平心而论,余氏反对的并非是考证,而是考证在红学研究中的滥用。他客观、公允地评价了胡适开创的新红学在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诚如余国藩所说:“我希望回应余英时的呼吁,让《红楼梦》取得真正的小说地位。”[19]
(二)文化批评指导下的红学研究
余国藩是早期旅美学人中较年轻的一位,然他学老于年,在美国红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接受了余英时“红学革命”中的主张,同时取法西方宗教学、神学并和比较文学方法结合起来,用文化批评方法阐释《红楼梦》的思想与内涵。
余国藩通过标举阅读、文史作品和《红楼梦》三者共有的“虚构”,解构了胡适主张的“自传说”并讽刺“盖全神索求小说外缘的现象”[20]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反对将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家世和自传上。余氏在《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红楼梦〉〈西游记〉及其他》等著作中反复谈及虚构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书中多次对余英时的“红学革命”和新典范报以掌声,他说“余英时说得好:‘这里确有一个奇异的矛盾形象:即《红楼梦》在普通读者的心目中诚然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小说,然而在百余年来红学研究的主流里却从来没有真正取得小说的地位。’”[21]何况,《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如果抛开文学不谈,一门心思去寻找历史的真相,这不啻为一种莫大的讽刺。余国藩认为这一怪象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整体文化中的历史主义”有很深的关联,以至于在区分“史实”与“虚构”时缺乏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余氏对虚构的把握深刻影响了美国红学后进,黄卫总称赞余氏研究“无疑将成为红楼梦研究的一个经典。”
宗教学、神学、比较文学、史学的学习和研究,对余国藩的红学研究影响很深。学习宗教学和神学,使他擅于从宗教的视角看待《红楼梦》中的情欲等问题,并提出佛教寓意在《红楼梦》中的重要性,这一点是其他研究者所欠缺的。余氏将文化批评的范式巧妙地引入了红学研究中:通过细读文本,从边缘文字向文本核心逐步推进,深入探究《红楼梦》的思想内涵,并利用后经典叙事学的方法解构了索隐派和考证派之间的矛盾。他的《重读石头记》除了传统论述外,也带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德里达和新历史主义者的影响尤重。[22]
(三)华人学者对文艺批评的回应
美国红学进入专业研究时期以来,华人学者主导的文化批评研究范式已成一种潮流。实际上,华人学者在20世纪早期恰与海外红学走上了同一条路——文艺批评。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作为批评派红学的开山之作,力求从悲剧、人生与文学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他将叔本华的悲剧主义、老庄的人生哲学等融汇于一,提出《红楼梦》的主旨在于宣扬人世的痛苦和解脱观,其研究价值在于“使得红学的研究不再沉陷于寻章摘句、深文周纳的狭小格局。”[23]然而,当考证红学蔚然时,王氏所开辟的批评范式为人诟病。周汝昌曾说“王先生的《评论》终归是‘评论’……那些纷纭的红学研讨,真是节外生枝,真是自寻苦恼。”[24]
以王国维为代表的红学批评派在大陆虽遭遇挫折,但在美国却享有盛名。从文学批评或比较文学的观点治红学的人在海外逐渐多了起来诸如夏志清、余英时、余国藩等都曾对王国维的红学研究报以掌声。王国维作为最早以西方理论解读《红楼梦》的评论家,树立了一个可供参考和学习的榜样。夏志清如是说:
王国维作为中国的先驱者之一,把西方理论应运于中国文学研究中,明确指出《红楼梦》所具备的悲剧精神的广度在中国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25]
他称赞王国维是伟大的学者,是中国将西方理论应用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先驱。余国藩也对王国维的红学研究深为叹服,认为王氏之论“另辟蹊径,所见不落前人窠臼,令人不得不叹道:王国维不愧一代文学史家兼批评宗匠。”[26]
从海内外对王国维及其《红楼梦评论》的态度上的差异,不难体会到批评派和考证派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华人学者通过各自著述与几十年前的王国维形成了学术交流与共鸣。究其原因,正在于海外华人学者对当时红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反拨、调整的一番可贵尝试。
四、华人学者对《红楼梦》海外传播的推动
随着《红楼梦》及其译本在全世界的传播、扩散,其文化影响力愈发凸显。华人学者在推动《红楼梦》的海外传播上发挥的作用更有成效。
(一)组社、办刊、教学:海外红学的发展
周策纵、夏志清、余英时、余国藩等华人学者,身处美国多元、开放的文化氛围和较宽松的学术环境中,有意识地利用组社、办刊、教学等方式为《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和经典化助力。
1948年,周策纵初到美国,便与顾献粱、唐德刚等在纽约顾氏公寓里组建了白马社,当时戏称为“纽约红楼”[27],其目的之一便是推动美国红学的发展。胡适曾高度赞扬白马社是“第三文艺中心”[28]。作为红学史上的重要概念“曹学”,最早即由顾献粱提出。[29]
1961年,周策纵、唐德刚等人又在美国创立了《海外论坛》,他们宣称这是一本“留美学人讨论问题发表意见的刊物”[30],旨在推动美国汉学的发展。胡适赞赏这批青年学人并以实际行动给予支持,他在《海外论坛》第二卷上发表了《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迷》[31]。周策纵紧随其后发表了著名的《论关于凤姐的“一从二令三人木”》[32],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教学亦是美国华人学者推广红学的重要手段。当时在美任教、培养学生、推广红学并借此与汉学家一争高下的华人学者当属余国藩和周策纵。余国藩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四十余年,曾在20世纪80年代和李欧梵合开了《红楼梦》课程。其后,穷十年之力,就《红楼梦》的各层面撰文,完成了《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一书。[33]余国藩的学生李奭学、沈安德、周轶群等后来大多在美国、加拿大、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任教,形成了一股推动海外汉学研究的合力。相比之下,周策纵的学生在科研上更集中于研究《红楼梦》,如陈炳藻利用计算机统计了《红楼梦》中20多万语汇的出现频率,并撰写了博士论文《〈红楼梦〉的作者问题:词汇的电脑统计研究》。[34]余定国则受周策纵和余英时的影响,撰写了《〈红楼梦〉的“第三世界”》,并在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提交讨论,对后来国内红学研究很有启发。
(二)专业研究:研究者与研究成果的增长
自美国红学进入专业研究时期以来,从事红学研究的华人学者,不论是人数还是研究成果数量都有较为明显的增长。1960—2000年的40年里,美国华人学生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呈现明显增多的趋势。[35]
另外,全美关于中国四大名著研究的硕、博士论文数量,《红楼梦》研究数量最多,共有41篇,远超过其他三部小说(《水浒传》21篇,《西游记》15篇,《三国演义》24篇)。[36]
(三)华人学者推动红学研究的国际化
红学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1980年6月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当时除《红楼梦》外,还从未为单独一部中国小说举办过国际会议。此次会议规模很大,“正式参加的人数有八十八人……这些人代表的地区,略按人数多少次序,计有美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九个国家和地区。”[37]其中以美国华人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居多。他们的发言、讨论对促进红学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参加并推动国际红学研讨会的举办,美国华人学者还通过学术争鸣、相互辩难来相互促进。香港《明报月刊》曾是海外学人发言的重要阵地。金庸曾说《明报月刊》的“作者几乎包括了海外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各家各派人士……包括了全世界的华人,方面之广,大概已超过了上述那些前辈刊物,所介绍和讨论的问题之广泛,大概也已超过了。”[38]《明报月刊》创办以来发表了55篇来自美国及中国大陆与港台学者的红学代表性文章,其中美国华人学者论文有16篇之多,如果算上有旅美经历的宋淇等人的文章,则数量达到总数的一半。从这一数据不难看出,正因有了如此之多热衷红学研究的华人学者,《红楼梦》在美国的传播远才比其他中国古代小说更为广泛。
五、结语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登上学术舞台的美国华人学者——夏志清、周策纵、唐德刚、赵冈、余英时、余国藩及他们各自的学生、亲朋胡适、顾献粱、张爱玲、宋淇、潘重规、陈炳藻、余定国、黄卫总、李奭学等人在美国及中国两岸三地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人数众多的红学研究圈。
华人学者因其特殊的身份,常立志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并希冀与西方汉学家一争高下。诚如余英时所说:“我想一个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大的人谈《红楼梦》,倒也不一定非得借西方的理论来壮胆色不可吧!”[39]余国藩回忆早年在去往美国的轮船上看到西方报刊介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时的情状,“记得当时的我也曾反躬自省,很想知道自己能否从反方向来从事研究——也就是精通西方的人文学科——和这位年轻教授一较长短,甚至超越之。……多年后才了解这次‘仓促立志’对我的影响,因为我往后的思想与专业发展都缘此而来。”[40]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领悟和对西方理论的吸收借鉴,华人学者在红学研究上所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们采用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提出了“红学革命”和新典范,力求将红学研究重心放在文本研究上;他们通过组社、办刊、教学、办会推动红学研究的国际化交流,在促进《红楼梦》在美国的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1] C.T.Hisa,“Love and Compassion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Criticism,V(1963),pp.261-271.
[2][美]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
[3] C.T.Hsia,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246.
[4] C.T.Hsia,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287.
[5][美]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9~280页。
[6] 张惠:《当代美国红学界右钗右黛之文化思辨》,《中国文化研究》(冬之卷),2013年。
[7] 陈维昭:《20世纪的海外红学》,《人民政协报》2013年10月28日。
[8] 胡文彬、周雷:《红学世界》,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52~53页。
[9] [美]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第15页。
[10] 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7页。
[11][12]王润华:《周策纵的曹红学:文化研究新典范》,《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6辑。
[13][美]周策纵:《红楼梦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14]程步奎:《〈红楼梦〉与社会史——兼评张毕来〈漫说红楼〉》,香港《抖擞》,1979年第34期。
[15][美]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第16页。
[16][美]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第13页。
[17][美]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第21页。
[18]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7页。
[19] Anthony.C.Yu,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20.
[20]张惠:《红楼梦在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21][美]余国藩著,李奭学编译:《〈红楼梦〉〈西游记〉及其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1页。
[22]王岗:《余国藩(1938—2015)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学术理念》,《世纪宗教研究》2015年第4期。
[23] 俞晓红:《一个世纪的关照——写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一百周年之际》,《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1辑。
[24]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25]C.T.Hsia,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p.287,246.
[26] [美]余国藩著,李奭学编译:《〈红楼梦〉〈西游记〉及其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1页。
[27]王润华:《周策纵的曹红学:文化研究新典范》,《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6辑。
[28]王润华:《被遗忘的五四:周策纵的号外新诗运动》,《文与哲》2007年第10期。
[29]顾献粱:《曹学创建初议——研究曹霑和石头记的学问》,《作品》1963年第1期。
[30][美]周策纵:《红楼梦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31]胡适:《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迷》,《海外论坛》1961年第2卷第1期。
[32][美]周策纵:《论关于凤姐的“一从二令三人木”》,《海外论坛》1961年第2卷第11期。
[33]李奭学:《误入桃花源:敬悼先师余国藩教授》,《南方周末》2015年8月7日。
[34] Bing-Cho Chan,The authorship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Computerized Statistical Study of its Vocabulary, Thesis(Ph.D.)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80.
[35] 参见张惠:《红楼楚研究在美国》附录《美国红学研究论文论著(1960—2006)》。
[36] 参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数据索引(2013年)。
[37] [美]周策纵:《红楼梦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38]金庸:《群星灿烂月华明(总序)》,《四海红楼》,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39][美])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第6页。
[40] [美]余国藩著,李奭学编译:《〈红楼梦〉〈西游记〉及其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