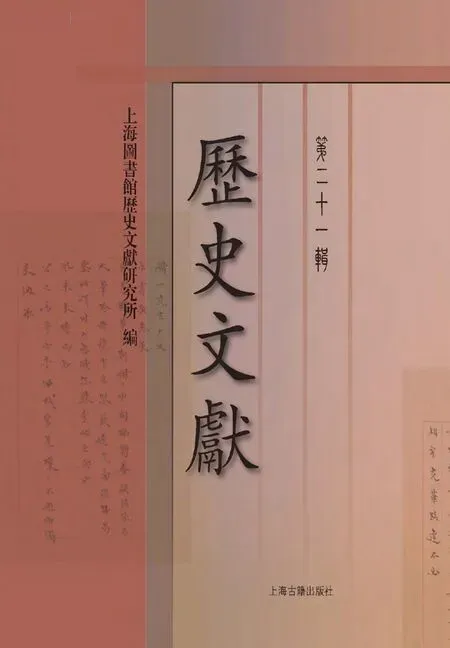《震旦雜誌》: 中西文化與教育交流的見證
2018-01-23周仁偉
□ 周仁偉
自從英人以堅船利炮轟開中華帝國的大門,西方文明與古老的東方文明以一種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方式展開了全新的對話,前所未有的文化的衝撞與交匯由此發端。廣袤寧静的華夏大地,在種種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鮮事物和理念的衝擊下,開始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民族的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了世界之廣闊,意識到了瞭解西方文明的必要性,而西人的殖民思想也原本就含有文化輸出的内容。雖然最初的戰爭可以説是由貿易糾紛而起,西人在華的擴張也終以政治經濟的利益爲核心,但文化教育領域的交流也在雙方的合力下悄然生長。中國近代教育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産生了最早出現的新式學校機構。創立於1903年的震旦大學就是中華大地上較早的新式高等教育機構之一,《震旦雜誌》是震旦大學長期發行的一份刊物,既見證了一所高等學府的風雨變遷,又展示了在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留下的一個個堅實的足跡。
一、震旦大學概況
震旦大學是一所以法國耶穌會爲背景的高等學府,是舊中國建立的最早的新式教育機構之一,也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不可忽視的一座豐碑。
耶穌會歷來重視在傳教過程中與當地文化的深入交流,法國耶穌會自1840年代重返上海徐家匯之後,一直都有興辦學校的打算。早在1850年就創辦了徐匯公學,爲教會培養人才,馬相伯先生即爲校友之一。戊戌維新之時,梁啓超即提議請馬相伯負責在北京成立一翻譯學院,馬相伯則建議將學校設在上海。當然,這個計畫隨着百日維新的失敗也一並流産了。
1903年初,南洋公學部分師生因與校方發生矛盾憤然離校,造訪馬相伯請另建學校。馬公欣然應允,多方奔走籌措,成立新校,以徐家匯老天文臺爲校舍,定名“震旦學院”。學院邀請耶穌會教士擔任教席,課程以拉丁文和哲學爲主。1905年,耶穌會士南從周(F. Perrin)任總教習,試圖對學校進行變革,激起師生不滿,馬公退出震旦,與部分震旦師生另立復旦公學,即後來的復旦大學。震旦學院一度停辦。同年8月,震旦學院恢復開學,天主教會開始全面控制學校。
1908年學院遷至羅家灣吕班路五十五號(今重慶南路)新落成的校舍,之後隨着學校的擴張,校舍又屢經擴建,爲學校的工科、醫科提供了充足的實驗和教研設施。1915年還將徐家匯博物院移設學院内,30年代改稱“震旦博物院”。
學院最初分預科和高等科,高等科後分爲文學法政、算術工學和博物醫學,此後逐漸發展成擁有法學、工科、醫科,尤其以醫科著稱的綜合性高等學府。1932年學院正式向民國政府注册,改名爲震旦大學,政府指派1908年畢業於震旦學院的校友胡文耀擔任校長,但實際上學校的控制權仍在教會手中。
上海解放後,學校由人民政府接管,天主教會退出學校。1952年,在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震旦大學被撤銷,震旦大學醫學院與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合并,在羅家灣的震旦大學原址成立了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現已成爲交通大學醫學院。
二、雜 誌 概 況
《震旦雜誌》是震旦學院内部發行的一份期刊,創刊於1909年,至1949年停刊,歷經40年,從形式到内容都發生過很大的改變。根據雜誌的出版形式和卷期號的演變,可以將其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09—1919年上半年,共出19期。大部分年份爲一年兩期,個别年份爲一年一期。這個階段,尤其是最初幾年,可以説這還是一份相當簡單的學院内部刊物,排版設計顯得相對簡陋,甚至連封面上的卷期號都不止一次出現印刷錯誤。而且在這個最初階段,這份刊物可以説並没有一個正式的、統一的書刊題名。最初的刊物,在中文封面上印的題名爲“震旦學院”,法文封面爲“Université l’Aurore”,從第十一期(1913年)開始,中文題名變爲“震旦大學院雜誌”,法文不變。後來又有幾期的題名爲“震旦大學院課選”,因爲這幾期雜誌的内容全部爲課選,没有校務方面的資訊和其他内容。
雜誌最初主要以中文編寫,内容主要包括學校章程、大事記、教職員名録、同學録、學生成績和課選,其中課選是指學生作業與作文之類的選登。部分科目的課選爲法文。由於雜誌中同時有中文和法文的内容,所以將兩種語言的内容分别以不同方式排版,用不同的頁碼,從書的兩頭向中間編頁裝訂。中文内容依照中文書籍的習慣豎排,漢字頁碼,向右翻頁,法文的内容横排,阿拉伯數字頁碼,向左翻頁,書的兩面分别是中文和法文的封面。這是當時中西文雙語刊物或書籍常見的編排方式。
第二階段是1919—1939年。這個階段雜誌發生了重大的轉型。第十九期之後,刊物名稱變爲《震旦大學院文學法政雜誌》,總期號重新從“1”開始,直到1939年,共出了40期,基本上仍是一年兩期,偶有一年一期。同時還出版了《工科雜誌》和《醫科雜誌》,但這兩份衍生出來的雜誌並没有出版很久,據後來雜誌發表的聲明解釋説,因無力支撑這樣的出版形式,在第十二期之後,還是將“文學法政雜誌”改爲了綜合性雜誌。從1926年的第十三期開始,雜誌名稱變爲《震旦大學院雜誌》,法文名稱爲《Bulletin de Université l’Aurore》。從1933年的第二十七期開始,中文名稱改爲《震旦雜誌》,這個最爲人所熟知的名字就是從這時開始的,一直沿用至雜誌終刊。也有一些資料上標明《震旦雜誌》的起始年份是1933年,可能也是以此爲依據。而且雜誌從這時起成爲完全的法文刊物,不再刊登中文文章。1934年的刊物封面下方出現了“内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二七四二號”和“郵政特准挂號認爲新聞紙類”,這可能是《震旦雜誌》從學校内部刊物變爲向政府相關部門登記注册的正式出版物的開端。1932年震旦大學正式向民國政府注册,可能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震旦雜誌》在1933年左右經歷了一種較爲明顯的“正式化”的過程。
這個階段,雜誌的主要内容也從課選變爲了更爲完整的、更具有學術性的各類文章,可以説是完成了從校内通訊向學術性期刊的轉型。雜誌中的中文内容逐年減少,最後改成了和西文一樣的排版,與西文混排,不再有逆向的中文書頁,成爲完全以法語主導的刊物。
第三個階段是1940—1949年。這一階段雜誌出版頻率增加,變爲季刊,十年間共出版40期,卷期編號與之前相比有幾處變化。首先,卷期號之前增加了“Série III”(第三系列)的字樣,1940年的第三系列第一期雜誌中刊登了一篇聲明,將之前兩個階段的雜誌定義爲第一系列和第二系列,解釋了“第三系列”這個説法的由來。然後雜誌按年劃分卷號,以前的雜誌的卷期是以學年來劃分的,標識通常爲“Année scholaire 19xx-19xx”,而“第三系列”的卷期是按西曆年劃分的,以每一年爲一卷,每一卷有四期。期號一開始是每卷獨立的,即每一年的期號都是從一到四,但1948年和1949年兩年改用了總期號,爲第三十三期到第四十期。同一卷内的頁碼是連續編號的,這樣做可能是爲後來編制索引提供方便。
這一階段的雜誌内容維持第二階段已經成型的風格,以大篇幅的學術性文章爲主,内容大大增加,不但出版頻率翻倍,單期的厚度也明顯增加。這時還有一個明顯的進步,即每一卷的最後一期附有一份本年度文章篇目索引。在1949年的最後一期,還做了一份整個第三系列的索引,包括三個部分: 作者名索引、主題分類索引和關鍵字索引,可以説大大提升了雜誌的實用價值。
如前所述,《震旦雜誌》曾在20年代演變爲三種並行的刊物,另兩種衍生出來的刊物也可以視作《震旦雜誌》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雜誌第二系列的第一期(1919—1920學年),刊登了一篇啓事,聲明雜誌進行了改版,不再刊登學生課選,而是改爲發表校友投稿的各類文章。並且根據學校的專業設置,將雜誌拆分爲三種: 《文學法政雜誌》《工科雜誌》和《醫科雜誌》。原雜誌中的校務内容、大事記等保留在《文學法政雜誌》中,於是《文學法政雜誌》可以視爲《震旦雜誌》的主幹,而其餘兩種爲附刊。
雖然自然科學和工科方面在震旦大學的教育體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工科雜誌》似乎並没有得到很好的發展。在徐家匯藏書樓的藏本中,《工科雜誌》衹有1919—1923年的五期,總共發表了約30篇各類論文,内容涉及從數學、物理學到鐵路、船舶、能源等工程學科。《文學法政雜誌》在第十三期(1926年)發表啓事,將雜誌更名爲《震旦大學院雜誌》,内容將覆蓋法學、文學與理工,可以推想《工科雜誌》最晚於此時已壽終正寢。
《醫科雜誌》後來發展成了另一種很有影響力的專業期刊,但在萌芽階段出版的期數可能比《工科雜誌》更少,徐家匯藏書樓的館藏中有1920年的第一期和1929年的第三期雜誌,以及若干没有封面和卷期資訊的殘本,第三期雜誌的中文封面題爲《震旦大學院雜誌醫科附刊》。由此可以大致推斷,《醫科雜誌》在20年代並没有實現連續發行,也不具備相對獨立的地位。後來獨立刊行的《震旦醫刊》(Bulletin Médical),藏書樓所藏最早的有期號的一期爲1932年的第七期,很可能是延續了原《醫科雜誌》的期號。《震旦醫刊》一直出版到1949年,是上海的一種高水準的、有影響力的醫學專業刊物。
《震旦同學録》也是隨《震旦雜誌》的成長而産生的。在最初的時侯,同學録是雜誌中的一個欄目,第一期單獨發行的同學録是1917—1918學年的,此後便成爲了一種連續出版的刊物,最後一期是1949—1950年的第三十八期。
1929年,雜誌還出過一份二十五週年紀念刊,除了校慶活動和演出内容之外,還刊登了一篇震旦二十五年小史,和一份1912—1928年畢業生名録。
三、雜誌的主要内容
在《震旦雜誌》第一系列的時代,即1909—1919年,這份刊物基本上是一份校内通訊,其内容主要是校務和課選。校務包括學校的大事記、教職員名單、學生名單、學生成績、文憑授予情況等等,有時候還會有一些照片,包括師生、校舍等等。
第一期雜誌起首的内容就是馬相伯先生手訂的學校章程,以及後來幾年之中修訂的章程。這是幾份非常有意思的史料,雖然雜誌始創於1909年,但是從這幾份章程當中,也能粗略看出馬公對興辦新式教育的構想和學校早年的一些發展變化的輪廓。
最早的一份章程是1903年馬相伯手訂的。當時明確的宗旨爲“廣延通儒,培成譯才”,①可見是戊戌時翻譯學院的構想的延續。功課以拉丁文爲先,一年學拉丁文,一年學其他國文(英、法、德、意任選一門)。課程分爲文學與質學(即科學)兩科,文學正課包括古文(希臘拉丁)、今文(英、法、德、意)、哲學,附課包括歷史、輿地、政治;質學正課包括物理學、化學、象數學,附課包括動物、植物、地質、農圃、衛生、簿記、圖繪、樂歌、體操。這就是馬相伯先生最早設想的震旦學院的藍圖,培養目標是精熟西方學術、博涉現代科學的人才。1904的續訂章程仍爲馬公手訂,提出的宗旨爲以“格物致知”“輔益區夏成材之士”,②以西方文明培養中華人才的大方向不變,但是去掉了單純的“譯才”的提法。課程進一步細分爲文學、致知、象數、形性、師範。文學仍是古文和今文,以拉丁文爲先,致知分爲原言、原物、原行,是以哲學爲主的内容。象數和形性是把原來的質學進行了進一步細分,師範則包括原來的簿記、圖繪、樂歌、體操等技能型的課程。
1905年重訂章程由南從周等修訂,顯然是在馬公離開之後有了較大的變化。學校宗旨爲:“便益本國學生,不必遠涉重洋留學歐美,而得歐美普通及高等程度之教育,不涉宗教。”③特意拈出“不涉宗教”是頗爲有趣的。課程分爲預科和本科,各兩年。預科爲西國普通學校課程,本科爲中學校與高等學校程度。科目設置與原來大同小異。第一年用中文教學,第三年開始全用法文。這一份章程還提出了將來開設法學、醫藥和工程等高等學科的構想。1908年遷至羅家灣後有一份暫定章程,韓紹康訂。這份章程提出放緩初級課程,變爲四年,成績優秀者升入高級課程。④1909年的新章程,⑤確立了三年預備科、三年高等科的基本學制,之後長期沿用。以後學校的招生章程、學制規則等等有單獨印行的資料,一些重大變化也會在學校大事記中有所記載。
關於震旦校務的最主要的欄目最初叫作“記事珠”,衹有中文。到了第二系列時不再用這個欄目名稱,但還是經常有這個欄目,以中文、法文同時記録校園大事。1933年雜誌改名《震旦雜誌》之後,校園記事就衹有法文没有中文了。這個欄目裏可以看到學校一些重大校務的變更,每年常規的各類學術活動、慶典活動,以及校園裏發生的重大事件,比如名人來訪或紀念活動等等。除了這些與震旦校史相關的資料之外,校園外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通常也會在學校的記事中留下痕跡。比如,1919年的五四運動,因涉及學生運動,這一學期的記事中就對當時校外的背景和校内的學生動向作了比較詳細的報導。⑥1932年“一二八事變”,震旦醫學院的師生組成救護隊參與傷病員的救護,雜誌刊登了學生孫忍德的救護日記的節選。⑦1937年8月,上海抗戰爆發,之後幾個月的記事内容,就不再是以學校爲中心,而是詳細報導了教會下屬的幾所醫院的傷患救護和難民救助工作。
除了大事記之外,雜誌也有專門欄目追蹤震旦的校友。最初衹是簡單的同學録,後來隨着學校的發展和校友隊伍的壯大,雜誌有了校友通信(Courrier des anciens)、校友近況(Nouvelles des anciens)等欄目,爲當時的校友們提供聯絡平臺的同時,也留下了關於學校和校友們的豐富的第一手史料。
在校務之外,最初雜誌的主要内容是課選,就是學生的作業選刊。課選分爲中文和法文兩個部分。早期的中文課選内容非常傳統,就是文言寫作。雜誌發行的頭兩年,時代仍是晚清,雖然科舉已廢,不再寫八股文章,但文章從内容到形式,基本不出唐宋古文的框架。形式均爲散文議論文,題目大致也是傳統義理的闡發或是針對舊史的品鑒人物、議論成敗,例如: 《大學以格物致知爲先論》《信陵拒虞卿論》《鄭子産不毁鄉校論》(1910年第三期),但在這些非常傳統的題目之下,文章内容倒也不是完全刻板守舊的,來自西方的哲學、政治、歷史的理論和觀念已經開始進入文章之中,舊瓶裏逐漸裝入新酒。也會有一些題目論及當時的時事,例如《論春秋列國同盟與今萬國平和會之異同》(1911年第五期)之類的題目,不免讓人眼前一亮。文章末尾一般會有一兩句點評,不過還是傳統塾師的手筆,没有太多新意可言。總之可以看到新文化運動之前的國語教育,即便在西方人開辦的學校中依然是相對保守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確保了學生仍具備紮實的傳統文化根柢,而不是拋棄一切全盤西化。五四之後的大學生連基本典籍都看不懂,則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進入民國之後,新式的文章開始增多,出現了更多着眼於現實的題目如《論全國幣制速籌統一》《論地方自治即當規復》《論强迫教育急宜實行》(1917年第十四期)等等。中文課選中偶爾還會有一些詩歌等文學創作。
法文課選内容比較多樣,因爲除國語以外的所有課程都是以法文教授的。文科有寫作、翻譯,理工的有數學、物理、化學、地理等各類課題的解題、論證等等。但是,由於震旦學院早年還没有高等學科,很多課選衹能達到今天的中學生習題的水準,對後人來説是一種有意思的史料,而在其學科領域則談不上有學術價值。
早期雜誌中比較有分量的文章,是名人的演講。這類文章最早見於1912年第八期,登了兩篇,一篇爲律師休斯(M. Hughes)的英文演説《羅馬律與英律之比較》,另一篇是法國天文學家、當時徐家匯天文臺長蔡尚志司鐸(P. Chevalier)的演説《日球之體度構造及近狀等》。這類名家進校園的演説活動,後來發展到每個月都會舉辦兩三場,成了震旦學院的一種常規活動,參與演説的大多是各領域的科學家、工程師,也會有律師、銀行家等等。這類活動都會在大事記中有記録,其中部分講稿會以中文或原文發表在雜誌上。
雜誌進入第二系列之後,不再刊登課選,代之以學術性更高的一些文章,有些是論文,有些是翻譯。有些文章是同時以中文和法文發表的。作者也不限於學生,有很多是震旦學院的教師或相關機構如天文臺、博物院的專家。翻譯的文章最初有一些國外文章的中譯,後來較多的是漢語文學或經典的西譯。韓愈、柳宗元、蘇軾、王陽明、曾國藩家書都出現過法文翻譯。論文的論題多集中在中國的歷史、地理、法律、經濟等領域。從這裏可以看出,學校雖然是教會主導並全面引入西方的教育體制,但並不單純地是在爲西方或者説爲教會培養人才,學生掌握的是西方的現代知識和學術方法,而研究的方向,至少在文史社科方面,是以中國爲中心的。而且也不祇是單純地學習套用西方人研究中國的方法,也會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用自己的眼光觀察這個社會的變化和成長。比如第八期(1923—1924學年)有兩篇文章論及新文學運動,用法語書寫、署名爲徐象樞的那篇表達了比較支持的態度,而漢語文言寫的那篇則是明確的反對,在同一期雜誌中以兩種語言論戰,也可以看得出雜誌對活躍的學術風氣的支援。
除了著述或翻譯的文章之外,雜誌中還有文摘和書評的欄目。文摘會摘選一些其他雜誌的文章,書評是一些書目的推薦和介紹。從總體上來説,進入第二系列之後的雜誌已經實現了轉型,從校務性質的内部刊物轉變爲了一種學術型的刊物。
由於第二系列開始時,雜誌曾被分科拆爲三種,所以從學科範圍來看,20年代前半段雜誌的内容主要爲文史社科方面的,1926年以後,工科的内容回歸,偶爾也會有醫科的内容,雜誌又成了綜合性的雜誌。事務性的内容並没有被剔除,常見的欄目如校友近況、校友通信、校友會活動、校内的大事記等等,還有學校所屬的震旦博物院和廣慈醫院的動態報導。
雜誌的第三系列,即1940—1949年,可以説是《震旦雜誌》的巔峰期,雜誌内容激增,發行頻率翻倍。在1949年的最後一期,編制了一份十年間雜誌内容的索引,整個雜誌的學術風格和特點可以從這份索引中略窺一二。
索引共分爲三部分: 作者名索引、主題分類索引和關鍵字索引。從作者名索引來看,十年間在雜誌上發表過各類文章的作者近120位,各類文章及書評、書目等近300篇。
經常爲雜誌供稿的多爲耶穌會士及震旦大學的教員或校友。在這份作者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到,有曾擔任震旦校長的胡文耀、才爾孟(G. Germain)、茅若虛(Louis Dumas),法學院的院長彭永年(Andre Bonninchon)、教務長喬典愛(Andre Gaultier)等等;也有來自耶穌會的著名學者,如《利瑪竇神父傳》的作者裴化行(Henri Bernard)、《在華耶穌會士列傳補編》的作者榮振華(Joseph Dehergne)、震旦博物院的主任鄭璧爾(O. Piel)、《江南傳教史》的作者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viere)等等;還有來自校外的專家,如雷士德醫藥研究院的主任伊博恩(Bernard Emms Read)、德籍猶太裔學者羅文達(Rudolf Lowenthal)等等。事實上,從第二系列中期開始,專家學者已經成爲《震旦雜誌》供稿的主力。
主題分類索引將各類文章分爲九個大類: 哲學、宗教、文學、漢學、歷史、地理與中國經濟、法學、自然科學、教育。筆者對每個類别的篇數作了一個簡單的統計如下:
從這個分類索引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震旦雜誌》的課題範圍是以文史爲主,工科和醫科另有刊物,所以在這裏會相對少一些。而其中占據非常重要地位的内容大都是關於中國的研究和介紹,對中國的哲學、歷史、政治、法律、民俗、文學、藝術以及自然環境、科學思想的研究和介紹占據了雜誌的大部分版面。這些文章當中,既有原創的論述,也有直接翻譯的中國著作,翻譯對象包括從老子、莊子到王陽明等的傳統典籍,也涉及當代文學(民國時期),如魯迅、巴金、茅盾、林語堂、曹禺的作品。還有相當數量的書目的整理和推薦。從第二系列時期已經體現出來的對中國學的關注,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更明顯的發展和延伸。這一點可以説在很大程度上既反映了雜誌的趣旨,也折射出震旦大學在教育上的方向和成果。
總體而言,作爲一種連續出版整整40年的期刊,《震旦雜誌》在教育、學術、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是一個相當漫長而重要的歷史時期的見證,其實料價值和學術價值都是不容忽視的。同時這些寶貴的學術資源長期深藏在圖書館的書庫中,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一方面,作爲一種以法語爲主的資料,語言的阻礙使得能夠涉足這一領域的學者比能夠使用漢語、英語資料的人要少得多;另一方面,歷史文獻本身的稀缺性,使得很多有需要的讀者也不能便捷地接觸到這些文獻資料。這次《震旦雜誌》的影印出版,相信能給許多學者和研究人員帶來諸多便利,也會給相關領域的研究開拓出一些新的方向。
① 《震旦學院》第一期,1909年,第13頁。
② 同上書,第17頁。
③ 同上書,第20頁。
④ 同上書,第25頁。
⑤ 同上書,第1頁。
⑥ 《震旦大學院杂志》第十九期,1919年,第3頁。
⑦ 《震旦大學杂志》第二系列第二十五期,1933年,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