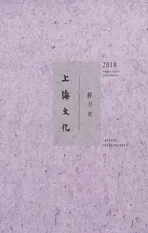以“忠恕”之道行“平等”理想
——简论蔡元培先生的平等观念与实践
2018-01-23高瑞泉
高瑞泉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近18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他们的奋斗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包括观念世界的变革,其中包括今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一的“平等”观念之形成。纵观历史,经过1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作为现代观念谱系中基础性的观念,“平等”已经从严复所说的古代的“消极平等”转变为现代的“积极平等”,①严复曾经用“消极平等”和“积极平等”来区分古代尤其是宗教论域中的平等与现代社会政治论域中的平等,他说:“盖佛固言平等矣,而意指平等于用慈;亦言自由矣,而实明自由于解脱。即使求诸犹太之旧约与夫基督之新约,固言于上帝前诸色人平等,然其平等者,平等于不完全,平等于无可比数。然则宗教之所谓平等者,乃皆消极之平等,而与卢梭民约所标积极之平等,倜乎相远,有必不可强同者矣。”(见《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8页)本文仅仅借用严复的这对概念以明平等观念有古今之别。至于严复本人的平等观念则比较复杂,包括对卢梭平等观念的批判,拙著《平等观念史论略》第4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0-176页)对此有所讨论。它进入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正是这场转变的积极成果之一。在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50周年时,来讨论蔡元培先生的平等观,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笔者以为,从古代“消极平等”,即围绕着人的相同性的理论,主要演变为心性形而上学或者旨在追求解脱的出世观念,经过一场转变,成为现代人讨论什么是平等和如何实现平等时,主要涉及建构社会制度、规范公民和政府的行为那样一种具有强烈实践品格的观念,它是中国社会史变革的一部分,包含了知识精英观念世界的一场飞跃,由此开启了现代性的传统,使古代传统以一种新的形态与当代生活构成了连续体。通常人们比较强调平等观念的“西学东渐”的来源,事实上,中国人接受平等观念还有传统思想作为与之接榫的资源,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开始,不少学人都有意识地运用儒佛道等相关要素去接纳和融摄西方思想,如果说他们属于从传统士大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代的话,蔡元培先生则接近第二代人物。作为前清翰林、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又是“新文化的创始人、教育家、哲学家”,①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9页。冯友兰先生是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学者中少数重视蔡元培哲学的人物之一,在其《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单列第3章,专门论述了蔡元培的哲学思想。蔡元培这种特殊的身份和作为,很可以让我们将其作为观念变迁史亲历者的另类典型,来回顾当时的知识精英在经历这场“飞跃”的过程中,其思想世界所表现出来的丰富性。
一
一般而言,只有现代社会才将平等作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原则。“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和政治的要求,平等是拉开现代社会序幕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的产儿。”②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平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页。这一曲折的过程具有世界普遍性,中国也不能独免。更准确地说,平等观念在中国的进程是与民主革命相因应的。20世纪初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于所谓“排满革命”,参与者中的激进分子曾经提出一种极端的主张:“杀尽一切满人”;蔡元培参加了这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世运所趋,非以多数幸福为目的者,无成立之理;凡少数特权,未有不摧败者。”“夫民权之趋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③蔡元培:《释“仇满”》,聂振斌编:《文明的呼唤:蔡元培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页。满洲贵族独霸政权之所以应被推翻,因为它违背了人民应该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的准则。这个准则意味着所有成年人都具有平等地参与政治意志的构成的权利。不过蔡元培并不赞成“杀尽一切满人”的过激主张。中国的“排满革命”不过是在民主成为世界性潮流的情势下,“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东亚之社会”而已,所以“排满”只是为了结束少数上层满洲贵族独霸中枢的局面,实现平等的理想,而经过两百年的民族融合,满汉不仅在文化上高度相似,而且普通满人在政治上也如同汉人一般,所以绝不能因为民主革命就忽略国内的各民族的平等。不难看到,即使是在其一生中相对激进的时期,蔡元培也持一种较为理性的态度。在其后期,蔡元培依然关心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关系。他赞成戊戌时期的思想家宋恕的议论:
今国内深山穷谷之民多种,世目之曰黎,曰苗,曰猺,曰獠,被以丑名,视若兽类……今宜于官书中,削除回、黎、苗、猺、獠等字样,一律视同汉民。④宋恕:《卑议〈同仁章〉》,转引自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24页。
蔡元培对于社会政治平等的立场是一贯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他赞成“劳工神圣”: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的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①蔡元培:《劳工神圣——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64页。
有些学人认为古训“人皆可以成尧舜”即意味着人人平等,其实这样解释平等,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肯定人有“成圣”的可能性,恰如佛教承认“人人能成佛”一样,依然只是停留在超越的领域,所以严复很正确地指出这只是“消极的平等”。而“劳工神圣”是在劳动为社会生活提供基本的可能和作为人的第一需要的意义上,肯定了社会生活中现实的平等,而不再是平等的形上学。这与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有根本的差别,也与我们一度见过的那种将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抹杀脑力劳动的价值的理论不同。
古代中国有“齐民”的概念,不过“士农工商”并不一律平等。取代“齐民”的是,20世纪初“平民”的概念开始流行。“平民”一词,可谓古已有之,大致是指称在官宦之外的“百姓”。但是古代“平民”之间也并不“平”,因为同为“百姓”,还是有贵贱、贫富的差别。因此,蔡元培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对“平民”作了新的解释:平民并不只是与贵族相对的范畴,“‘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得平等”。有些学者一直以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世袭罔替的贵族,或者因为有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从下而上的社会流动的存在,就否定中国古代实质上是不平等的社会(有些时代甚至是极端不平等的)。事实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文盲率还占人口的90%。如果我们理解“知识就是权力”的知识社会学,那么,蔡元培和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从事“平民教育”,恰恰就是希望从根本上改变由于教育的不平等而带来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不平等。
乔万尼·萨托利说过:“平等首先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抗议性理想,实际上是和自由一样杰出的抗议性理想。平等体现并刺激着人对宿命和命运、对偶然的差异、具体的特权和不公正的权力的反抗。”②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蔡元培的平等主张显然有“抗议性理想”的面相。不过,在研究平等观念的动力学的过程中,也有一种保守主义的理论,他们通常坚持一种怀疑主义的眼光,认为平等意味着社会底层的人们出于“妒忌”,而意欲将社会精英拉低到与自己相同的水平。因而平等不仅和社会正义一样都是一种神话,是一种“卑劣的情感”,而且会因为妨碍“自由”而妨碍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平等的嫉妒心理学解释是否有道理,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在蔡元培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身处社会上层、官居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文化精英,发出的对不平等的抗议和改变此类社会状况的真诚努力,它也许可成为对嫉妒心理学的一种反驳。也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发现,平等观念在蔡元培身上表现出一种高贵的面相。因为真正的高贵恰恰就是能将身份感作“有而无之”的消弭。
蔡元培的平等主张是一以贯之的,这里的“一以贯之”不仅仅是言语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当然,它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在新文化运动中,在部分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中,平等已经不再只是主观的价值诉求,而多少成为其生活实验的一部分。换言之,在这批教育背景、社会身份、经济地位、革新倾向大致相近的知识分子中间,平等观念具备了某种实践性。辛亥以降,平等为成文法所肯定,虽然对于民众来说,它是名存实亡的东西,但是对于知识精英而言,却多少有了精神上的优势和某种程度的保护。就教育平等而言,五四期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女生,最早实现了男女同校。在此背后是现代教育的逐渐普及。除了大的社会环境,变化还涉及知识分子自身的生活方式。譬如《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和主要作者群体之间,就存在过一种比较平等的合作关系。《新青年》最初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他到北京大学后将编辑部迁至北京,陆续吸收了钱玄同、鲁迅等10多人参加编辑部工作。这种同人刊物的办法,决定了他们是自愿的组合,即使有实际的领袖(如陈独秀),同人之间还是平等的,并没有从属关系,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学术同人关系,不要求大家的意见或对具体问题的观点完全一致;相反,刊物只是他们的公共空间,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和展开争论的场所。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其载体正是他们共同编辑的《每周评论》。
这种平等的氛围也进入了北京大学,它与蔡元培先生掌校时实行的改革有关。蔡元培本人无疑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的改革家和教育家,在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实行了许多实际的改革。最具有代表性的事情是,1918年1月学校的25名学生联名给蔡元培写信,说一个门房自学得非常好,蔡元培就把他提升为职员,并且答复说,在学校教员和其他工友之间没有地位的差别,研究五四运动的专家周策纵评论说:“以中国保守的社会等级模式来说,这当然是不同寻常的。”“大学内被灌输以一种平等的精神。以前学生和教授、学生和门房工友之间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①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5页。另一件事也说明了蔡元培如何身体力行平等理念。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上任第一天,校役们照例排列在校门口鞠躬行礼。蔡元培摘下礼帽,鞠躬还礼,使一向受人轻视的校役们大为惊诧。蔡元培平等待人的风范可见一斑。总之,在蔡元培那里,平等是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在生活中的待人接物需要体现出“礼让”的美德,它可以贯穿学术活动的是非之辩和实际生活的利害之争:
苟当讨论学术之时,是非之间,不能异立,又或于履行实事之际,利害之点,必得其是非之所在而后已。然亦宜平心以求学理事理之关系,而不得参以好胜立异之私意。至于日常交际,则他人言说虽与己意不合,何所容其攻诘,如其为之,亦徒彼此忿争,各无所得而已。温良谦恭,薄责于人,此不可不注意者。②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1页。
这样一个以儒家“温良谦恭”为准则的人,却又能勇敢地参与到为平等理想之实现的政治斗争中。在30年代,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和暴政,蔡元培与宋庆龄等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且发表了系统的人权主张:“我等所愿意保障的是人权。我等的对象就是人。既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受保障的普遍人权。”保障人权不仅仅不受党派、国别的局限,针对国民党的滥施暴政,蔡元培强调:
我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区别。未定罪的人,若是冤的,其人权不应受人蹂躏,是当然的事;已定罪的人,若是冤的,亦当然有救济之必要。至于已定罪而并不冤的人,若依照嫉恶如仇的心理,似可不顾一切了;然人的罪过,在犯罪学家之归于生理之缺陷,在社会主义上归于社会的因缘,即在罚当其罪的根际上,本尚有考虑的余地。所以古人有“如得其情,哀矜勿喜”的箴言,又有略迹原情的观察,即使在法律制裁之下,对于当罚之罪,不能不认为当然,而不应在于当然之罚上再有所加——苟有所加,则亦有保障之必要,例如狱中私刑、虐待等是。所以我等对于无罪或有罪之人,亦无所歧视。①蔡元培:《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外记者招待会致词》,《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366-367页。
简言之,蔡元培已经意识到: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一组互相关联的政治上稳定的组合。②罗伯特·道尔:《论政治平等》,张国书译,台北:五原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23页。
二
蔡元培先生一生积极从事社会、政治活动,但是也曾经专注于哲学理论研究和学术著述,除了主张“以美学代宗教”、对美学有独到的研究以外,他在伦理学和伦理学史的研究上,于近现代哲学史上也占据着前驱的位置。他不但著有中国第一部《中国伦理学史》,而且一直不遗余力地提倡道德建设,主张养成国民“完全人格”。需要“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而无所谓骄谄。意志自由,而无所谓侥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是皆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人所当自勉者也”。③蔡元培:《社会改良会宣言》,《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7页。所以,其平等观念的具体特点,在伦理学的论域中也许显现得更为清晰。他曾说过:
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也矣。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毋加诸人。《礼记·大学》曰: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平等之谓也。古者盖谓之恕。自由者,就主观而言之也,然我欲自由,则亦当尊人之自由,故通于客观。平等者,就客观而言之也。然我不以不平等遇人,则亦不容人之以不平等遇我,故通于主观。二者相对而实在相成,要皆由消极一方面言之。苟不进之以积极之道德,则夫吾同胞中,固有以生禀之不齐,境遇之所迫,企自由而不遂,求与人平等而不能者。将一切恝置之,而所谓自由若平等之量,仍不能无缺陷。孟子曰:鳏寡孤独,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张子曰: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伊尹思天下之人,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仁。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源,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①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0-11页。
我们不难发现,蔡元培在论述其平等(和自由)的价值时,处处以原始儒家(孔孟)为参照。在西方观察者看来,西方现代平等观念有其宗教的根源,《圣经》中所谓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教义蕴含着如下的观念:在道德的重要性上,人类是平等的;最没有天赋、最少成就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每个人的幸福和痛苦有着同样的道德重要性。“中国的伦理则仅仅关系既是等级的又是互相补充的关系。”②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增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但是,在蔡元培看来,孔子和孟子已经提供了平等的基本原理。在讨论“德育”问题时,以“人类本平等也”为预设,他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以平等为前提的修身原则之一,并作了中西融合的解释:
子贡问于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乎?”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日,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也欲无加诸人。”举孔子所告,而申言之也。西方哲学家之言曰:“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其义正同。例如我有思想及言论之自由,不欲受人之干涉也,则我亦勿干涉人之思想及言论;我有保卫身体之自由,不欲受人之毁伤也,则我亦勿毁伤人之身体;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不欲受人之窥探也,则我亦慎勿窥人之秘密;推而我不欲受人之欺诈也,则我慎勿欺诈人;我不欲受人之侮慢也,则我亦慎勿侮慢人。使无大小,一以贯之。③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390页。
基于平等的人际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但是一种“消极的戒律”,而且蕴含着“积极的行为”的意向。所谓“消极的戒律”,即意味着我们并不能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直接推论出“以己之所欲施于人”的绝对合理性;所谓“积极的行为”,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立者,立身也;达者,道可行于人也。言所施必以立达为界,言所勿施则以己所不欲概括之,诚终身行之而无弊者也。④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390页。
蔡元培实际上已经将平等与“自由”视为现代价值观念的一套紧密的连锁,它同时又可以从“忠恕”之道中获得其深刻的植根性。或者说,如果人们真正进达“忠恕”之道,就不难实践平等的法则。这样的意思,在其《中国伦理学史》“忠恕”一节中已经有所表述:
孔子谓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非曾子一人之私言也,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礼记·中庸》篇引孔子之言曰:“忠恕违道不远。”皆其证也。孔子之言忠恕,有消极、积极两方面,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消极之忠恕,揭以严格之命令者也。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积极之忠恕,行自由之理想者也。①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9页。
用“忠恕之道”来解释平等自由观念,体现了蔡元培融摄中西,要以本民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准”的基本立场。②在写于1910年的《中国伦理学史》开头,蔡元培就表述:“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顾尚无伦理学史。迩际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槃如烛。几有互相冲突之势。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准,则益将旁皇于歧路。”不过,由于儒家在长达2000年的发展过程中,其义理已经是高度衍化了的,包括后来不但成为意识形态,而且制度化为“礼教”,因而“以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为衡准”,③在写于1910年的《中国伦理学史》开头,蔡元培就表述:“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顾尚无伦理学史。迩际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槃如烛。几有互相冲突之势。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准,则益将旁皇于歧路。”就不能不对传统思想有所抉择,包括不能不正视在20世纪被广泛批评的“三纲五常”。蔡元培的策略是用“对等”(parity)来解释平等(equality),从而与忠恕之道这个道德黄金律统一起来。忠恕之道将“人”与“我”作为对等的关系,包含了某种程度的“非特指的个人”的性质(impersonality),它表示我们的行为与具体的对象无关,因而可以远离我们的偏私。④像蔡元培这样强调传统儒家伦理意味着人伦之间的“parity”关系,后来有著名的梁漱溟所谓“互以对方为重”的论式;而美国哲学家郝大维、安乐哲则认为传统儒家的平等观念可以作社群主义的解释,也是强调“parity”,而非“equality”。拙著《平等观念史论略》的第2章有所讨论。其积极的向度隐含着人应该普遍地得到尊重,因而和现代平等观念所意味的同一社会的人平等地享有人格尊严的要求,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前文曾说及蔡元培在伦理学史的成就,从平等观念史的角度看,蔡元培可能是第一个注意到道光年间儒者俞正燮⑤俞正燮(1775—1840年),字理初,安徽黟县人,属于乾嘉考据学派后期学者之一,著有《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蔡元培之后,鲁迅、周作人等也相继推崇俞正燮对男女平等观念所作出的贡献。蔡元培晚年还说:“自《易经》时代以至清儒朴学时代,都守着男尊女卑的陈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称谓贵重》……等等篇,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我至今还觉得有表彰的必要”。蔡元培:《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550页。伦理思想之价值的人。他坦陈自己“崇拜”俞正燮,首要的原因就是俞正燮能“认识人权”,主张“男女皆人也。而我国习惯,寝床、寝地之诗,从夫、从子之礼,男子不禁再娶,而寡妇以再醮为耻,种种不平,从未有出而纠正之者。俞先生从各方面为下公平之判断”。作为一个传统的儒者,俞正燮的杰出之处,固然在于其出于“嘉孺子而哀妇人”的人道情怀,揭示古代男女不平等的陋习(包括裹足之风俗,妾媵之设;妒在士君子为义德、谓女人妒为恶德;所谓“贞操”专对妇女之而言的礼教,乃至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不合情理,同时又通过考证方式从古代经典中发掘资源,说明传统中亦有尊重女性的文化脉络,因此“是皆从理论说明女权者也”;他广征博引,“无一非以男女平等之立场发言者”。⑥蔡元培:《〈俞理初先生年谱〉跋》,《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71-573页。
俞正燮的论述大多是运用考证之学来批评假道学的伪善或陋儒的僵化,蔡元培在发现俞正燮的同时也引思想家宋恕为同道,认为宋恕能复归孔孟之真精神:
他在《卑议》中说:“儒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强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强’。洛闽讲学,阳儒阴法。”(《贤隐》篇《洛闽章》第七)又说:“洛闽祸世,不在谈理,而在谈理之大远乎公。不在讲学,而在讲学之大远乎实。”他的自叙说:“儒术之亡,极于宋元之际。神州之祸,极于宋元之际。苟宋元阳儒阴法之说一日尚炽,则孔孟忠恕仁义之教一日尚阻。”可见他也是反对宋元烦琐哲学,要在儒学里面做“文艺复兴”的运动。他在《变通》篇《救惨》章说:“赤县极苦之民有四,而乞人不与焉。一曰童养媳,一曰娼,一曰妾,一曰婢。”他说娼的苦:“民之无告于斯为极,而文人乃以宿娼为雅事,道学则斥难妇为淫贱……故宿娼未为丧心,文人之丧心,在以为雅事也。若夫斥为淫贱,则道学之丧心也。”①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123-124页。
在蔡元培看来,真正出于孔孟的忠恕之道,就一定会有一种抑强扶弱的人道主义正义感,其内里则是人的平等观念,因而对于男女不平等的陋习自然而起一种抗议。
蔡元培对俞正燮、宋恕等的表彰并非只停留在著述中,而是用自己的生活实践来体现自己实在与他们是同道。早在他任中西学堂监督期间,妻子病故,“未期,媒者纷集。孑民提出条件,曰:(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媒者无一合格,且以后两条为可骇”。②黄世晖:《蔡孑民先生传略》,蔡元培、陈独秀:《蔡元培自述 实庵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8页。如果我们阅读过《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不难发现蔡元培所奉行的择妻原则与俞正燮、宋恕等的男女平权思想有高度的契合。因此,对于蔡元培本人而言,上述蔡元培对俞正燮、宋恕伦理思想的发明,很大程度上为一个从前清翰林转变为新式知识分子的人物,提供了主张男女平等的心理支持。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史,则提供了一个“异端反为正统”和“边缘进入中心”的重要案例:俞正燮和宋恕都并不为一般学者所重视,更何论普通民众?因此,今天在我们建设公民道德的过程中,如何更深入、广泛地发掘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并进一步作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三
倘若我们深入地考察蔡元培的平等观念,还可以发现它具有更深一层的哲学意蕴:在蔡元培看来,平等应该成为合理地解决认识论的“群己之辩”的前提或价值偏好。如果我们承认追求真理的过程就是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而进达知识的过程,那么首先就必须设定参与讨论的各方是平等的,意见的真理性并不因为主体的身份而改变,因而讨论就成为一种追求合理性的活动。正如普特南所说的那样:“我们关于平等、知识自由和合理性的价值观念深层地相关。”③希拉里·普特南:《理性、历史与真理》,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9页。合理性作为现代性的核心,其在学科建制上最大的体现是现代学院制度。而说到中国的现代学院制度的建设,我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它既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都在北大任教;刘师培、黄侃、辜鸿铭、梁漱溟等也在北大任教。这多半是由于蔡元培的办学宗旨是如此开明: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①蔡元培:《答林琴南的诘难》,《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76页。
体制上“依各国大学通例”,表示新的北京大学应该建立现代学院制度;“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被人们广为称道。不过其内在精神是“学术独立”或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它与王国维所云“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②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本质上是相通的,对于现代大学中人而言,学者以学术研究为自己的职志,应该致力于专精之学,而不在意它是否“有用”。“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③蔡元培:《北京大学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82页。因此它又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内在一致的。
现在我们熟知某个说法:大学之谓大学,不是有大楼,是因为有大师。这话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常常见到的另一种情况是,少数所谓“大师”,其实早已沦为学阀。而学阀意识固然是知识在权力结构中的异化,在认识论的论域则陷入独断论的虚妄。不难发现,“大师”崇拜和蔡元培无缘,他说:
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唯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与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之,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任学生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也。④蔡元培:《大学教育》,《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597页。
在蔡元培看来,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要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有人喜欢讲学术民主,如果“民主”在这里意味着发挥论辩合理性,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充分地对话,自然也有成立的理由,但是“民主”终究要有决断,所以还需要所谓“公共认可”来决定其取舍。在现代社会中,学术研究虽然是在科学知识共同体中进行的,但是不仅人文学科中的创造性工作的主体一般是个体,即使是在自然科学技术领域中那些最有创造性的发现,起决定性作用的多半还是少数杰出的个人。因此,在学术问题上,我们还应该更重视自由讨论和发表,它不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则行事。其实,无论是“民主”还是“自由”,其前提都需要承认从事学术活动的主体是平等的,不因为多数人的意见就否决少数人的意见,不依靠现成的“权威”而限制年轻人的创造性,也不能用“正统”来排斥“异端”。这种认识主体的平等意识,不但表示蔡元培认为人作为理性的主体,有自由创造和理性选择的能力,学术活动就是要培养和促进这种能力。而且后面更蕴含着对人的易错性的深刻认识,即凡是人都可能犯错误,任何观点的提出,最初都只是“意见”,正是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人们可以更接近真理。而任何出色的学术理论,它的有效性都有其限度。自由的发表、平等的对话,不但可以使善于在对话中获益者有所收获,或者改进自己的理论,或者更丰富自己的学说;而且有利于养成良好的学术生态,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它是社会团结的重要表征。
以平等作为认识论的“群己之辩”的预设或价值偏好,同时也就意味着反对单一“学科的傲慢”。蔡元培批评在学院制度内部,专业主义造成的学科之间的隔阂:
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牵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科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①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1、451-452、450页。
针对“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的倾向,蔡元培又说: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②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1、451-452、450页。
从根本上说,蔡元培的办学理念,是要建设一个师生研究学术的共同体,来推动知识创新:“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③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1、451-452、450页。《北京大学月刊》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这一方针之实施,对于“高深之学问”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历史学家吕思勉后来说:“北京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种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幡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的研究,才不为众所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后生小子,也知道专讲肤浅的记诵,混饭吃的技术,不足以语以学术,而慨然有志于上进了。这真是孑民先生不朽的功绩。”④转引自张晓唯:《蔡元培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71页。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一定不会忘记,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不仅为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提供了最好舞台,也为在当时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学人保留了从事专业研究的阵地。正是在北京大学,没有多少正规学历、更没有留洋经历的梁漱溟、熊十力等开创了现代新儒家哲学,今天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讲儒学已经成为潮流所趋,就忘记其最初实在不能脱离蔡元培先生所创造的不同学术派别平等对话的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