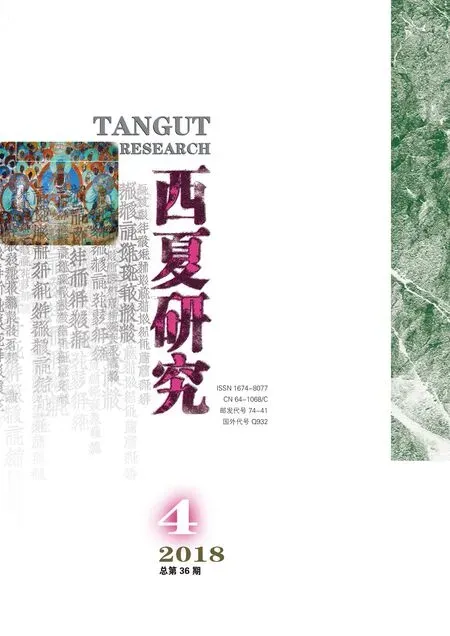四十年来黑水城汉文经济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18-01-23陈瑞青
□陈瑞青
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数量可观、内容丰富,涉及宋夏金元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社会等诸多方面。目前黑水城汉文文献已基本公布完毕,总数在5000件以上①。黑水城汉文经济类文献主要集中在西夏和元代,其中西夏经济类汉文文献56件,包括“俄藏”34件、“英藏”18件、“中国藏”4件,涉及榷场文书、借贷文书、马料文书和各类账目等内容。黑水城元代经济类文献的数量更大,约为860件,其中“中国藏”最多,达到700余件,内容涵盖户籍赋税、农田水利、提调农桑、官用钱粮、军用钱粮、官员俸禄、诸王妃子分例、契约票据等方面。此外,还有一些遗漏未收的元代经济类文书,包括“俄藏”43件、英藏97件和混入《俄藏敦煌文献》的20件。总体来看,黑水城汉文经济文献的总数在900件以上,对于研究西夏、元代经济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十年来,黑水城汉文经济类文献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总结相关研究经验、分析不足并展望未来,必将对进一步推动黑水城文献研究大有裨益。
一、黑水城西夏汉文经济文献研究
西夏经济类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夏契约、账簿、马料和榷场使文书等方面。
西夏契约研究。在黑水城西夏汉文契约中,比较重要的有《西夏天庆年间裴松寿处典麦契》、《西夏天盛十五年王受贷钱契》和《西夏光定十二年李春狗等扑买饼房契》三份。1980年,陈国灿先生利用《敦煌学资料》中误收的英藏黑水城西夏借贷契约,运用文献学方法复原了《西夏天庆典当残契》[1],这是敦煌学研究方法在黑水城文献研究领域的一次有益尝试。其后,陈炳应先生从民族问题、经济问题、契约格式和文书年代等方面对西夏契约进行了研究[2]。王元林对《西夏光定未年借谷物契》进行了考证,分析了该件契约的内容和格式,并与《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和俄藏《天庆年间典麦契》作了比较[3]。孙继民、许会玲不仅探讨了文书中所反映的西夏借贷利率,而且通过《西夏天盛十五年王受贷钱契》研究了西夏的双国王爵制度[4]。陈静对俄藏、英藏中的西夏典麦契进行了综合研究,探究了西夏典出粮食品种的变化、典当抵押品的种类和西夏高利贷的畸形发展等情况[5]。杜建录重点探讨了俄藏西夏典粮文契中所反映的文契格式、贷粮利率、偿还期限、违约处罚等问题[6]。李华瑞对《光定十二年赁租饼房契》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份文书既可看作房屋租赁文契,也可视为一份经济合同,但不具有承包合同的性质[7]。乜小红对《光定十二年赁租饼房契》进行了考证,认为这是一件西夏时期短期承包式租赁契约。该契约既承袭了唐五代契约的书写传统,也存在一些微小变化[8]。韩伟从民间法视角研究了西夏黑水城卖地契中的亲族权利、官私转贷、违约责任和证人等问题,并就其特色与汉文契约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尽管西夏文契约与汉文契约存在一定差别,但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类似点更多,因此与中国传统契约文化一脉相承[9]。
西夏账簿研究。杜建录对《西夏乾祐二年材料文书》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材植账、漫土账和胶泥账,指出这些文书是西夏工程建设与材料储运的原始资料,并对文书中出现的地名、人名进行了考释[10]。张多勇等对《西夏乾祐二年(1171)黑水城般驮、脚户运输文契》中出现的“合同”、“一般驮”等重要名词进行了考释,探讨了西夏的运输和交通问题[11]。孙继民对《西夏乾祐二年材料文书》中材植账、漫土账和胶泥账等入库账簿进行了复原,形成了以年度为单位逐月逐日逐人逐组登记驮数并押印为记的入库账书式,推断其性质为西夏的年度专项物资入库账[12]。同时,孙继民指出入库账书式,丰富了我们对西夏文书种类特别是汉文文书种类的认识和了解,对研究西夏文书制度,尤其是汉文文书制度具有原始史料的文献意义。账簿文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脚户的组织方式和运营规模,是反映西夏交通运输史的珍贵资料,为研究西夏库藏史的第一手资料。
西夏马料文书研究。杜建录对英藏4件西夏马料文书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印证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向公务人员提供粮饷草料的相关规定[13]。陈瑞青对西夏马料文书进行了重新整理,纠正了其中存在的错简,并通过比较宋、夏、元军事制度指出文书中所涉及的马匹为政务用马,马主身份可能是西夏时期的站户[14]。
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研究。黑水城共出土西夏“南边榷场使” 文书17件,其中俄藏15件、英藏2件,内容均为南边榷场使向银牌安排官汇报榷场税收情况的报告。日本学者佐藤贵保最早对榷场使文书进行系统整理,复原出文书的书式,初步揭示了南边榷场使文书的内涵及其对研究西夏与金代贸易的意义[15]61-76。此后,史金波《西夏社会》一书对榷场使文书的性质、价值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未见西夏设“榷场使”官职,而由“转运司”掌管经济诸事,或许转运司主官转运使是“榷场使”之西夏文称谓。西夏在首都设都转运司,各地又有转运司,其中南院转运司或为南边榷场使司[16]154。杨富学、陈爱峰发表《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场贸易文书研究》一文,对上述文书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指出西夏与金朝贸易货物种类繁多,以丝、毛织品居多,此外还有食品和书写用品等。在西夏与金朝的榷场贸易中,西凉府和镇夷郡是重要的货物供应地。南边榷场使应即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卓啰边中转运使司,兼任榷场货物集散地凉州的“榷货”之职,既负责榷场货物的筹备,同时负责榷来之货物在河西等地的分发。[17]随后,杜建录对《黑城出土西夏榷场文书》进行了考释,在文书释文、交易货物品类解释和地名考释等方面取得了进展[18]。孙继民、许会玲不仅复原了南边榷场使文书的书式,而且指出其性质为榷场使向上级机构汇报榷场收税情况的统计报告,“依例扭算”进口总值。进口总值即应税额,是各种进口商品的具体种类、数量和价值量。同时,该文探讨了南边榷场使汉文文书所反映的西夏官方汉文公文制度、外贸统计制度和扭算制度、外贸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等问题[19]。同时,他们还对榷场使文书中的价值尺度进行了研究,指出西夏一匹合三十五尺,通过商品之间的换算关系推算出当时西夏西凉府所使用的度量衡之间的关系,进而估算出西夏榷场贸易中的税额[20]。孙继民还对榷场使文书中反映的西夏出口商品的边检制度进行了研究[21]。冯金忠探讨了西夏榷场使的制度来源问题,认为榷场虽然明确出现于宋辽金时期,但其历史可追溯到互市,二者之间存在一定渊源关系。宋初与南唐之间设立的榷署(或榷务)是榷场的直接源头,西夏榷场使很可能远承唐代。[22]此外,杜立晖还对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的录文进行了补释与考证[23]。陈瑞青对榷场使文书中反映的西夏榷场住户资质申请制、货物无禁检验制、交易替头代理制和回货扭算报告制进行了探讨[24]。宋坤对榷场使文书中川绢、河北绢之间的换算比例问题进行了分析[25]。冯金忠[26]和陈瑞青[27]分别利用榷场使文书探讨了西夏银牌制度的渊源、西夏公文“头子”的类型和作用。郭坤、陈瑞青通过对夏、金榷场贸易商品进行考察,认为夏、金之间榷场贸易中所出售的川绢、川缬、抄连纸等均来自南宋。这些商品并不直接从南宋获得,而是通过与金的贸易过程辗转进入西夏,这一认识对研究宋、夏、金之间贸易提供了新思路[28]。陈瑞青指出,由于川绢与河北绢的价格波动影响西夏榷场税收,所以西夏在榷场贸易中实行浮动税率,同时创造性地实行川绢、河北绢双系数税收登记体制,体现了西夏榷场管理体制的严密性[29]。杜立晖认为黑水城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中的“替头”并非西夏“住户”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中介或代理人,而是代行南边榷场中相关胥吏的职能[30]。从“替头”的角度来看,南边榷场使文书的主要内容似为南边榷场使向银牌安排官所上的呈文,汇报“替头”发送回货到各处的具体情况,而非旨在汇报榷场的税收问题。
二、黑水城元代汉文经济文献研究
黑水城元代经济类文献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丰富,对于元代经济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目前,学术界重点关注农业、畜牧业、仓储、水利、钱粮、税收、契约等问题。
农业经济研究。马彩霞认为,元代亦集乃路农作物产量很低,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服务于畜牧业[31]。杜建录对黑水地区西夏至元代的农业、畜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涉及水利灌溉、农产品种类、农户户口、土地买卖、畜牧业种类和数量等问题[32]463-468。徐悦研究了黑水城出土提调农桑文书,认为其反映出元政府对种桑养蚕的重视,并对亦集乃路推行区田法和桑粮间作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33]。刘广瑞对这件提调农桑文卷进行了再研究,认为其很可能是元代地方官以《救荒活民类要》为底本,参考《至正条格》后撰拟而成的地方版本[34]。此后,徐悦还据此探讨了亦集乃路的屯田面积、户数、屯田类型、屯田户的构成和屯田的管理机构等问题,认为其具有屯田类型齐全、屯田户种类繁多和民族成分复杂的特点[35]。吴超认为元代的司农司、劝农司、监察机构、地方官吏和社均有劝农职责,其中监察机构和地方官吏兼管农事是元代农业管理的一大特色[36]。同时,吴超还从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知识、规范田制与鼓励栽桑、推行区种和桑粮间作、扶持贫困农户等方面探讨了元代亦集乃路农业技术推广问题[37]。此外,吴超还探讨了亦集乃路土地开发问题,认为元代亦集乃路土地开发面积虽然达到一定规模,农业也有长足发展,但依然是一个农牧兼营的地区[38]。周思成探讨了元代亦集乃路的土地占有与租佃关系,认为以屯田户为主体的小农经济在亦集乃路可能仍然占主要地位[39]。孔德翊探讨了元代亦集乃路自然灾害问题,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与气候变化关系密切,元代西北屯田开发、农业生产技术应用不当是造成自然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亦集乃路自然灾害表现出多样性、频发性、关联性特征[40]。
农作物与粮食供给研究。徐悦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药材三个方面对亦集乃路农作物种类进行了考述[41]。刘洋利用黑水城出土文献,证明元代亦集乃路可以种植水稻[42]。丛海平利用黑水城出土《大德四年军粮文卷》,对海都之乱时亦集乃路的位置、为元军筹措转运军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阐明了作为西北兵站之一的亦集乃路在元代北方军粮后勤供给体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43]。张重艳通过分析黑水城出土的一批元代军粮文书,认为阔端赤是元代基层军队中负责管理马政的人员,其军粮及其他开支由地方供应,在军队中的地位和正军相似[44]。朱建路在对英藏黑水城出土两件元代军政文书重新释录、整理的基础上,指出元代亦集乃路的粮食来源具有多元化特征,除甘州、宁夏府路外,河东宣慰司也是其来源地之一[45]。
水利研究。吴宏岐利用黑城出土文书研究元代亦集乃路灌溉河渠情况,对各渠道的名称进行了考证。通过新考订的7条渠道,考察了各渠的户口数量与元代亦集乃地区的人口规模[46]129-145。王艳梅利用《黑城出土文书》中的大量材料,在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亦集乃路的渠社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47]。李艳、谢继忠认为元代亦集乃路作为甘肃行省的北部重镇,军民所依赖的农业生产全靠黑河水灌溉,由于人口、耕地、气候、民户负担等多种因素,当地水利灌溉管理严格,针对纠纷时常发生的现实,官府有相应的纠纷处理方式和方法[48]。霍红霞指出亦集乃路的水利管理机关为司农司、河渠司、兵工房和社,亦集乃路采用西北地区通行的自下而上的用水法则,当地政府有调解水利纠纷的职能[49]。
仓储研究。刘广瑞对亦集乃路广积仓中的“白帖”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广积仓出具的税粮凭据。关于白帖文书未加盖政府印章的情况,除纳税人没有缴纳税契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纳税粮户未交齐税粮[50]。高仁、杜建录探讨元代亦集乃路粮仓的设置及其作用,认为粮仓不仅是囤积粮食的仓房,还是地方政府的粮食征收与放支机构,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1]。
畜牧业与酿酒业研究。吴超认为亦集乃路的生产经营方式是农牧兼营,当地既有一定数量的民营畜牧业,也有相当数量的官营畜牧业,其牲畜饲养主要采取夏秋散放和冬春圈养的形式[52]。牲畜饲养分工更加细致,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地畜牧业较为发达。刘秋根、杨小敏认为元代亦集乃路官府自用非商品酒的生产由官府集中生产转变为官府管理下的分散酿造,体现了封建官府变相多样的求利手段和国家宏观、有效控制酿酒业能力的不断完善[53]。杨印民认为元代为保障驿站对过往使臣的酒品祗应,甘肃行省省府对酒务槽房的生产和各项开支进行严格监督与审查,甘肃行省执行的酒禁政策严重冲击了槽房酒业生产[54]。刘永刚认为元代亦集乃路尚酒之风浓厚,酒的官方消费、商业消费均较活跃,下层甚至存在嗜酒之风。元代所实行的榷酒政策既对酒类酿造、出酒率有不同规定和要求,同时又表现出酒课征收的灵活性[55]。
税收研究。潘洁、陈朝辉利用黑水城出土的税粮账册,分析了亦集乃路税粮的种类、税额等基本情况,并与俄藏西夏赋税文书进行比较,揭示了亦集乃路税粮征收的基本规律和农业种植的特殊情况[56]。此外,潘洁还探讨了黑水城文书中所反映的元代亦集乃路税粮、抽分、酒醋课、契本税等赋税征收的相关情况,弥补了黑水城赋税研究的不足[57]。在此基础上,潘洁还对黑水城元代税票中所反映的税票格式、税额差异、地税征收方式、征税时间、发放机构、监管人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58]。吴超对《黑城出土文书》(汉文卷)中涉及地税、抽分羊马、酒醋课和商税等内容的文献进行了研究,认为亦集乃路税务管理遵循一定规则,这种管理同当时的社会条件相适应[59]。杜立晖对元代亦集乃路税使司呈解课程程序、管理体制、收税人员等问题进行了研究[60]。陈瑞青对黑水城元代酒醋课程文书进行了研究,认为文书内容反映出实行“散办法”后,地方酒醋课的征收推行由上等户认办的包税制,酒醋课时限改由按季征收。酒醋课作为国家税收的一部分,亦集乃路总管府虽作为本府酒醋课的具体主管部门,却无支配权。文书中反映的这一系列情况,集中体现了元代酒醋课征收制度的新动向。[61]张淮智对黑水城出土元代《大德十一年税粮文卷》中的两号文书残片进行了缀合,将其复原为一件文书[62]。
钱粮、俸禄研究。陈瑞青对元代亦集乃路钱粮房《照验状》进行了考证,认为其中出现的三个元帅府和两翼军人实际上是征公元帅府统属下的几支驻防亦集乃路的外地部队。这几支外地驻军的后勤给养由亦集乃路总管府钱粮房负责筹办,反映出元代后勤供给的地方化现象[63]。潘洁《黑水城出土钱粮文书专题研究》一书对黑水城文书中的提调钱粮、钱粮储运、口粮文书、军用钱粮、官用钱粮、钱粮物账等文书进行了系统考证,为了解元代亦集乃路钱粮收支、地方经济特色提供多角度思考[64]。杜立晖利用黑水城文书对元代钱粮考较的时间、程序、内容、责任、奖惩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钱粮房为亦集乃路钱粮考较的实际组织者[65]。潘洁、陈朝辉对黑水城文书中钱粮物的该支、实支、正支、折支、添支五种放支形式进行了归纳,探讨了各种形式形成的原因[66]。潘洁将黑水城元代文书中的勘合文书分为抽分、军粮、俸禄、祭祀、分例、其他钱粮物勘合六小类,认为元代勘合的使用比较广泛,对于研究元代勘合制度与勘合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67]。杜立晖在确认黑水城元代勘合文书原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元代勘合文书的形态、特征和运作流程[68]。潘洁、陈朝辉对桑哥失里大王分例羊酒文书和卜鲁罕妃子分例米面文书进行了部分复原,并对文书中的地方支出经济、纪年文化、机构设置等问题展开研究[69]。杜立晖对元代俸禄文书进行了研究,认为元代俸禄制度中存在请俸程序,请俸呈文具备一定的特征与书式,元代俸禄的放支时限以月为基本单位,但在实际运行中又有灵活性和因地制宜的特点[70]。张国旺利用黑水城文书分别探讨了蒙古教授、司狱司官吏、路级吏员和地方官员俸额的变化,探讨了元代俸禄制度执行的具体情况[71]。
钞库、钞本、票据研究。陈瑞青对黑水城出土元代 F116: W12 号文书进行了考释,认为这是甘肃行省丰备库下发亦集乃路总管府的牒文。该件文书对于研究元代财政制度的运作、万亿宝源库的职能和地方财政支出来源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72]。高仁对黑水城文书中的支持库进行了考证,认为这是亦集乃路总管府所设钞库。支持库承担亦集乃路所有财政开支,放支形式通常为纸钞,在元末通货膨胀时也放支充当货币的粮食。亦集乃路的课程不入支持库,支持库钱钞全部由甘肃行省丰备库下拨[73]。庞文秀对黑城出土的盐引、盐券、茶引、钞本、契本等有价证券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些有价证券曾在一个时期代替法定货币进入流通领域,除当局或明或暗的鼓励和倡导外,也由这些有价证券自身所具有的条件和职能所决定[74]。此外,姚朔民对黑城出土元代钞币进行了介绍[75]。周祥对黑城出土编号F1:W38、F123:1、F192:W2等几件文书进行了考证,结合结论探讨了元代钞本行用制度[76]。李春园认为元代亦集乃路地区的货币以中统钞和小麦为主,中统钞是政府支付手段,小麦则充当当地中小额市场交易的媒介。元代中期,中统钞与小麦的比价为40—80 两/石。亦集乃路的借贷一部分为无息,有息贷款的月利率均为10%。与汉地相比,亦集乃路的牲畜、纺织品、粮食等商品价格表现出地区性特点。[77]
契约研究。杨选第利用《黑城出土文书》收录的13件借贷契约,研究了元代借贷契约的特点和亦集乃路居民经济生活概况[78]。叶新民对黑城出土元代文书中的合同婚书以及有关借贷、雇佣、买卖、租赁等方面的契约文书进行了考辨[79]。孟繁清利用黑城出土的几件契本残页,结合其他史料记载,研究了元代契本文书使用的基本情况[80]。许伟伟对比了西夏、元时期的谷物借贷文书契约,考察了西夏、元契约文书的各自特征和黑城地区谷物种类等问题,揭示出黑水城地区西夏、元时期的一些经济活动特点和社会面貌[81]。杨淑红从法学角度将元代保人担保分为留住保证和履行保证两类,若保证事项未实现,保人需承担代偿责任。在履行保证过程中,按照保人代偿责任的范围可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元代汉文借贷契约履行保证的兴起,反映了债权保障趋于严密、担保制度逐步完善的发展方向。[82]杜建录对中国藏黑水城出土文书中6件元代钱钞借贷契约进行了整理,研究了元代借钱契的格式、借贷利率等问题[83]。杜建录、邓文韬对黑水城汉文文献中的6件合伙契约进行了研究,重点探讨了文契所反映的合伙方式、盈利分配、风险责任等问题[84]。同时,他们还对黑水城文献中的元代租地契、赁房契进行了分析,指出元代黑水城租佃契数量较少的原因,与流行于该地区的农奴制生产关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封建租佃制的发展有关[85]。张重艳对元代契约参与人的称谓进行了分析,认为元代契约双方当事人称为立文字人和立契人,契约的第三方包括见证人、牙人、保人、代书人,契约当事人和第三方的签押都有一定顺序[86]。梁君对两件元代婚姻契约进行了研究,重点探讨了婚姻关系中的婚嫁权归属问题[87]。杜建录对黑水城西夏、元时期契约文书进行了系统介绍,认为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元契约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同时,自身也在发展变化,元代契约的内容、格式和西夏多有不同[88]。
三、黑水城汉文经济文献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学界对于黑水城汉文经济文书的研究虽然取得长足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本分析不够,限制了文书价值的探讨。在以往的研究论著中,或多或少存在文本分析不足的现象,引用文书时不能很好地吸收学术界黑水城文献整理的最新成果。如孙继民带领的团队对黑水城汉文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先后推出《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2012年)、《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2015年)、《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016年)、《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献(佛经除外)整理》(2018年)。杜建录先后推出《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2015年)和《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2017年),后者采用图录本形式整理黑水城汉文文献,极大地方便了学界使用。在上述整理成果出版之前,一些论著引用文书时因无法核对图版而造成录文错误。大批整理成果出版后,一些研究论著仍使用早期文书录文,无视最新研究成果,严重限制了文书价值的发掘。另外,由于部分学者缺乏古文书学知识,文书分析存在简单化处理倾向,仅根据文书中的关键词进行归纳总结,造成研究结论似是而非。
第二,文书研究手段单一,缺乏多学科交叉。文书研究的基础在于文献学整理,除文献学外,还需要历史学对文书进行价值分析。文献学和历史学是文书研究者应当具备的两项基本功,要求学者不仅要有文献校勘整理能力,还要有历史综合分析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在实际研究中,一些论著或多或少地在这两方面存在缺陷,文书研究者不熟悉历史学背景、历史学者不懂文书的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度的存在,造成一些研究论著就文书谈文书、文书与传世文献脱节、文书研究游离于学术前沿的不利局面。即使在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已达到相当水平的今天,利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对黑水城汉文文献进行解读的佳作也依然屈指可数。
第三,文书研究以个案为主,缺乏关联和贯通。从目前的研究论著来看,以个案研究为主,既缺乏黑水城文书的内部关联,也缺乏与黑水城文献上下时代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之间的贯通。所谓内部关联,主要指汉文文书之间的关联和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文书的关联。后者需要文书研究者突破西夏文、蒙古文、八思巴字、藏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障碍,对相关文书进行关联研究。目前学界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很不够,黑水城出土的双语文书至今尚未得到很好地整理和研究,能将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文书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并能做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论著还不多。黑水城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宋、夏、金、元诸部断代史的内部系统,没有打破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徽州文书之间的壁垒,更好地发挥黑水城文献在古文书学中的承上启下作用。
黑水城汉文经济类文献研究已经走过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学界在文献整理和研究两个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虽然这些成果和敦煌学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一定会迎头赶上,因而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文本是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基础,要重视文本在文书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运用文献学、古文书学的研究手段校勘文书、定性文书、分析文书,以准确无误的文书文本为前提开展学术研究。尤其在黑水城文书研究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今天,从文本出发对文书进行再研究、再探讨已成为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的必由之路。
第二,积极借鉴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手段,多视角、多维度地开展黑水城文献研究。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首先要克服语言障碍,将汉文与西夏文、蒙古文等少数民族文字文书相结合,全面推动黑水城文献研究向纵深发展。同时,积极探索文书与文献、学术前沿问题相结合的路径,以“问题”为出发点和切入点,凸显文书在宋、夏、金、元史研究中的独特作用和价值,真正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推动学术界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层次探讨。
第三,积极发挥黑水城文献在中国古代纸质文书史上的链条作用,做好上勾下连,深入探讨黑水城文献与敦煌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中古文书作为整体序列展开综合研究。分析同性质的文书在不同时期的前后演变规律,是突破黑水城研究瓶颈的有益尝试。只有打通文书,一些尚未进入研究视野、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黑水城经济类文献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利用黑水城经济类文献探究西夏、元代经济史中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学界热点。可以预见,随着黑水城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类文献必将在史学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取得更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注释:
①统计文献包括《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