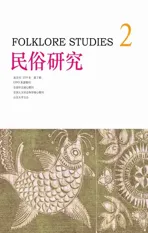19-20世纪江南田野景观变迁与文化生态
2018-01-23王建革
王建革
景观是一种叠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空间系统,具有制度性、社会性与文化性。一个民族的景观是世世代代形成的,具有时代性。杰克逊关于美国乡村景观的分类有三种:中世纪的景观,具有适应能力;近代的景观,产生边界的可视化;现代的景观,暂时性强。*[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发现乡土景观》,俞孔坚、陈义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译序第2页。中国传统时代的田野景观具有生态稳定性,地表建筑和乡村的道路都高度可循环。江南的景观是国家体制下的小农景观,具有高度权力的运河和自由分散的小农田块的密切结合,未规划的乡村小路和大小不同的乡村聚落形态,农田的各季颜色,形成古典田园诗歌的审美意境,这既是农夫的,也是士人的。农夫有本能的农田景观的欣赏,农田和耕牛会给他们带来自然的愉悦,他们有深厚的土地感情。刘邦父亲住进长安后想念家乡的景观,近代农民也依然如此。赛珍珠在《大地》中有这样的描述:“除了他的吃喝和他的土地,他再也不想什么新的事情。但是他只想土地本身,他不再想地里的收成怎样,也不再想该播什么种子或别的事情。他有时弯下身,从地里抓些土放在手里。他手里攥着土坐着,仿佛他手指间的泥土充满了生命。”*[美]赛珍珠:《大地》,王逢振、韩邦凯、沈培锠等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319页。这是许多小农的终极关怀。士人也有一系列的景观体验并形成为诗画,宋代的江南田园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19世纪以后,西人对田野有相对客观地评价,这为我们分析江南景观的多重视角提供了帮助。集体化以后,乡村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统一化水网与农田体系代替了传统的疏林断岸。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以后,小农经济的恢复并没有实现传统景观的恢复,而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现在的这种状态。在这其中,二百多年来一系列价值观念与审美观念的变化对景观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文化生态的影响。本文通过各种人士的视角,分析这种景观变迁的过程和隐含其中的动力。
一、19世纪田野景观的中西对比
清代的江南景观与唐宋时代的江南有较大的差异。经历了几千年的集约化开发之后,景观质量大大衰退。宋时田园诗大兴,景观质量甚佳,但此后随着人口进一步增长,散乱的水网系统和小农化的田块增多,使田野景观的质量呈下降之势。尽管如此,田野之美仍是诗歌的主题。祝允明《暮春山行》诗曰:“小艇出横塘,西山晓气苍。水车辛苦妇,山轿冶游郎。麦响家家碓,茶提处处筐。吴中好风景,最好是农桑。”*(清)钱谦益撰集:《列朝诗集》丙集第九,许逸民、林淑敏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3337页。与范成大和陆游的时代相比,祝允明所见的田野景观已经衰退了许多。明代时期利玛窦在对各地物产做评价时,景观评价较少,反而注意到的是各地的花草:
花草之丰盛确实令人不能再有什么奢求了,中国人有很多种花是我们从不知道的,它深深打动人们的美感,并显示出造物者慷慨的恩赐。中国人似乎对于花的形状和颜色要比香味更为喜欢,在他们开始与欧洲人贸易往来之前,他们实际上并不知从花草里提取香精的学术。*[意]利玛窦、[意]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11页。
传教士的视野集中在新奇物种方面,难有景观评价。受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徐光启对田野的评价多了些士人少有的科学描述。他这样讲冈身区可种甘薯的沙地:“吾东南边海高乡,多有横塘纵浦。潮沙淤塞,岁有开濬,所开之土,积于两崖,一遇霖雨,复归河身,淤积更易。若城濠之上,积土成丘,是未见敌而代筑距堙也。此等高地,既不堪种稻,若种吉贝,亦久旱生虫。种豆则利薄,种蓝则本重。若将冈身脊摊入下塍,又嫌损坏花稻熟田。惟有种藷,则每年耕地一遍,皆能将高仰之土,翻入平田。平田不堪种稻,并用种藷,亦胜稻田十倍。是不数年间,邱阜将化为平畴也,况新起之土,皆是潮沙,土性虚浮,于藷最宜,特异常土地。”而低乡的景观,他则如是说:“在低下水乡,亦有宅地园圃高仰之处,平时作场种蔬者,悉将种藷,亦可救水灾也。”*(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之二十七《树艺》,朱维铮、李天纲:《徐光启全集》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60-2561页。
18世纪末,马戛尔尼在浙江感受到农业的密集。“浙江省多湖泊,像江南一样江河和运河交错,但除了稻米外,出产极不相同,主要产丝,为喂养吐丝的蚕,山岭之间肥沃、美丽的河谷,乃至平原都种植了桑树。”*[英]乔治·马戛尔尼、[英]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9页。他谈到美丽的山谷和依然保持着长期美丽的山地,他也看到许多破败和贫穷,他认为中国的园林风格是征服自然,西方人的园林风格是改进自然。这一点恰与许多中国学者的中西观念相反。
他们的目的是改变发现的一切,破除旧的创作风格,在各处引进新的。如果是一片荒地,就种上树;如果是干旱的沙漠,就开河灌溉,或者凿湖蓄水;如果是一马平川,就用种种方法使它花样翻新。他们让地面波浪起伏,山峦堆叠,将它们挖成溪谷,用岩石将它变得崎岖。他们夷平凹凸,将欢乐带到荒野,要么赋予沉寂的大地以生机,造大片森林与之为伍。*[英]乔治·马戛尔尼、[英]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9页。
这种改造田野的做法,更是指中国的园林经营。与他同行的斯当东也说:“中国人布置园艺,没有一定规格,也不按科学原则,但随手拈来自成风趣,又简单又美丽。”*[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38页。农人经营田园与池塘的水平,与园林经营类似。中国农业就是一种园艺化的精耕细作,因此西人称赞中国农民是园艺者。江南的园林经营也多与农业经营有类似之处。清代高士奇讲自己家乡平湖的江村草堂是“因自然之园圃,不加缔构”*(清)高士奇:《江村草堂记》,陈从周、蒋启霆选编:《园综》,赵厚均注释,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9页。。乡村田野中的美景,稍加整治,即成园林。总之,经营园林与经营农业有太多的一致性。斯当东认为中国人种植不太讲究行列,这应当是与欧洲农田相比较的观感。他和马戛尔尼都对江南的桑树有深刻印象。在苏州运河两岸,他关注到大片桑树和乌柏。*[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38、429、451、457页。马戛尔尼团队的轮船副船长看到河流接着河流,景物变幻无常。“这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地方的耕作实况:掘土、施肥和耕田,不同的操作法我在沿河两岸的田地上能看得清楚,虽然中国农民生产着与在欧洲我们所见的同样良好的谷物,但这一情况说明,在这里是全靠坚持不懈的劳动得来的,因为他们的农具看样子是十分粗笨的,是一种不轻便的机械。”他看到大量的围观他们的人群和水牛。“聚集来观看我们启程的观众是如此之多,让人难以置信。除了步行而来的以外,还有很多人骑在水牛背上,或者站在水牛车上;这些水牛与我国的牡牛是同样的驯良而易于驾驭。这类水牛在这个国家内大量用来做拖运工作,主要是用在农田和耕作方面。”船长看到了精耕细作下的中国农业在农业机械方面的不足,更认为中国人在一些区域的努力,使田野的风光更加美丽。“江的四周仍旧是山岭起伏,风景绝美,居民之善于耕作和装饰更加强了其美观程度。当我们沿江上溯,一路上大面积的乌臼树园和桑园相间出现;这使时刻变化了的山川景色,增添了不少风光。”*[英]爱尼斯·安德逊:《在大清帝国的航行:英国人眼中的乾隆盛世》,费振东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182、188页。轮船长发现了山川景色和桑基农业之美。马戛尔尼对苏州到杭州一带的桑树也有深刻印象:“运河两岸,一望无边的土地上,种植桑树。桑树有两个不同的品种:一是普通的桑,morus nigra;另一种叶子小得多,平滑和呈心形,结白色果实,约田野草莓大小。后者更具有灌木特性,但两者的树枝都不让长成结实的木材,因为要时时剪枝让树干每年长出幼芽,其叶据认为比老枝的更细嫩。”“浙江省多湖泊,像江南一样江河和运河交错,但除了稻米以外,出产极不相同,主要产丝,为喂养吐丝的蚕,山岭之间肥沃、美丽的河谷,乃至平原都种植桑树。”对山水交错地带的河谷景观,有很美好的印象。“苏州府以西是连绵的山岭,以我们迄今看见的要高,其下是一个大湖(太湖),在中国以其如画美景和盛产鱼类而闻名。我们有意到这个可爱的地方游玩。”西湖的美,一直为各族和各阶层的人所认同,西人也不例外。“这个湖的天然和人工美景,胜过我们至今有机会在中国看见的任何景色。四周山峦高耸,变化成各种形状,山谷里生长着稠密的各种树木,其中三种不仅因本身美丽,也因明显不同于其他树木,特别引人注意。”*[英]乔治·马戛尔尼、[英]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22、450页。其实,由于他们刚来中国,对中国的印象,仍然以稀有物种为中心。乌桕树是嘉湖地区传统景观中的林木,马戛尔尼的使团曾对这种树有特别的关注。斯当东亦看到大片的桑林中间间隔着一些产蜡油的乌桕树。*[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38、451页。
总之,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来中国的西人,对江南田野的评价与欣赏程度并不甚高,但长期以来的风景区,与国人有相当的审美认同。当时的江南文人,尽管继承着宋代以后田园诗的农业审美,对山水景观的审美关注多,农业景观的审美关注少。钱载是18世纪嘉兴本地的诗人,他对太湖和周边的溪山多有诗句,农田诗不多。讲到田野时,更是一种兴味,不是景观。“倒眠紫草田,横拉红蔷架。堕池钓童抱,攀桑蚕妾骂”,这种紫草田是绿肥。他说:“吴俗,春田之不种油菜、蚕豆、大小麦者,撒草子于中,俟其生,绿叶纤茎,开紫白间小花,曰‘荷花紫草’,取以胶河泥,资培壅。”这种紫草田,用草和泥向稻田施肥。紫花草种植在单独的畦中:“撒子出茸茸,畦分菜麦中。低低花紫白,簇簇露深浓。寒食罱泥膠,嘉禾膏雨同。几翻勤灌溉,常足壮培壅。”菜花开放时,文人可以敏感地观察到油菜花形成的景观。蚕豆的绿色与油菜菜花的黄色也相配:“篱门开阖野田香,杨树湾东近汉塘。晓露满畦蚕豆绿,晚风连顷菜花黄。年光只有春来好,日景谁知老去长。”嘉兴田野的稻、草、麦、菜分别与桑树搭配成色调。春天有梅花与杏花:“西舍不遥东舍近,梅花初落杏花开。罱泥担粪看齐出,葱本桑秧买旋栽。将及春分前夜雪,早过惊蛰一声雷。”*(清)钱载:《萚石齊诗集》卷七《倪翁村居録壁閒旧句感述》、卷四十九《九丰堂·篱门》、卷五十《荷花紫草田》,丁小明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4、831、856页。这些景观是普遍存在的,西人关注也不多。马戛尔尼等人的江南景观,与清代文人的描述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他的大副安德逊也关注到青山绿水,眼光与士人一样,只是更有科学化的特点。安德逊这样描述绍兴一带的绿水:“这一部分江面虽阔,但水深达二三英尺之外很少,没有一处超过四英尺深的。江水呈绿色,江底为砂砾,江边则砂石相混。”*[英]爱尼斯·安德逊:《在大清帝国的航行:英国人眼中的乾隆盛世》,费振东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187页。
中国文人的审美比西人更敏感一些。西人对江南的看法,受他们的家乡,即欧洲田野景观的影响。欧洲乡村景观的整齐度远高于中国,中世纪以后,西方的田野就保持了庄园式的经营,各类景观整齐划一的程度远高于小农经济的中国,中西景观差异,使斯当东和马戛尔尼不对农田景观有什么赞美,而对山水景观多有欣赏。与英国不同,中国是山地国家,他们欣赏山水。在中国文人的景观视野中,少有大视野景观整齐度高的环境,明清时期诗词的乡村描述,多是小桥流水、树木花草和庄稼颜色。事实表明,中西方知识分子对江南的田野印象有共通之处。
19世纪的江南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战争,农业恢复后,景观开始恢复。这一恢复被1868年来华的李希霍芬所关注,他在钱塘江两岸看到荒凉的景观:“当年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就是经过这条水路进京的。如果他们的舰船大炮再来到这里,一定会发现此时这里变得荒凉了。”*[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著、[德]E.蒂森选编:《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李岩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51-252页。作为一个国际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视野丰富,又有非常好的科学分析。他认为宁波一带的山林景观像日本,属于保护得比较好的区域景观。江南一带的森林,除了少数风景地点外,已经在长期破坏下衰退。在宁国一带,他注意到民众对树木的破坏性砍伐。“这里的景色尽管不及岭以南地区,但也十分秀美。山上是美丽的针叶林带,大部分都有20年到30年的树龄了。但我也看到个别被伐倒的树木,树龄都在50年到60年之间。然而树木的生长状况很糟糕。森林被砍伐得厉害,特别是树龄不高的树木被绑作木筏状顺流而下。人们在伐木的时候根本不懂得经济,通常紧缺的粗大漂亮的树木却被劈成柴火。”*[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著、[德]E.蒂森选编:《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李岩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89页。内藤湖南认为在中国或欧洲那些森林早已毁坏殆尽的国家,若不去遥远偏僻之地,无法看到天然林的美丽景色。*[日]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62页。清初的叶梦珠描述过松江府的林木状况:“薪樵而爨,比户必需。吾乡无山陵林麓,惟藉水滨萑苇与田中种植落实所取之材,而煮海为盐,亦全赖此。”*(清)叶梦珠:《阅世编》,来新夏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180页。赵翼论江南的泥炭时,捎带着谈到江南田岸的树木:“江南惟沿村有树,河港之在野者罕所植,间有之,亦必取作器,小则伐为薪,其孰肯砍而弃诸河?意必洪荒以来,两岸本多树,随山刊木时,始伐而投之,历千万年成此耳。”*(清)赵翼:《簷曝杂记》,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第80页。山地的林木破坏,归因于山林的公地性质,由于中国小农经济的发达,乡村公共管理难以支持山地森林的恢复,越是集约化的农业区,山地的森林景观越是难以恢复,因为这样的地区人口密度甚高,对燃料的需要也更大。清末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指出,因没有公共地制度,国家与农民任山地处于破坏状态。“渭河沿岸的庄稼地里分散着大量枝叶繁茂的树木,严重影响了庄稼的生长,而两三英里以外的山上却是光秃秃的。人们宁肯在自家的庄稼地里种树,也不愿在不宜庄稼的山上种植草木。这是因为在没有公共管理的条件下,山地不属于任何人,上面的任何东西都会遭到破坏和抢劫。”在四川,他发现农村地区杂草丛生。“农民进行园林式的耕作。虽然到处都种植稻米、大豆、白菜、玉米和蚕豆这些维持生命的必要之物,却没有草坪、葡萄园、桔子树!路过农舍,一眼就会看见脏兮兮的一丝不挂的婴儿,无精打采的小脚女人,破烂的地板、被烟熏黑的墙、黑暗的房间、当地猪、脱毛狗、吃草的驴子等等。”*[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公茂虹、张皓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第18、276页。李希霍芬对江南田野的评价也不高,他认为江南人多用粪肥田而破坏了美观:
当然,不甚美观的地方也和日本有相似之处。早上我从船中出来看到的第一幕,就是一群男人挑着一桶桶大粪到田里去。在村子里每家每户的门前都摆着或大或小的木桶或石桶,里面盛着在当地人看来宝贵的肥料。在街道尽头的小屋子里,过路人还能用自己的排泄物为这里的老百姓祈祷获得好收成!这种状况不比日本差多少;农业和国民经济最高程度的完美循环,但是完全无视一切美好的感觉,尤其是嗅觉。*[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著、[德]E.蒂森选编:《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李岩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1-32页。
科学的记录与描述,使他对一些相对风景的描述不像中国文人那样,文人集中于说好,那种好也大多是客观的存在,随着景观的衰退,描述便不断减少。他们不在诗歌里赞美田野景观时,景观往往经历着衰退和破败。江南整体的景观,被宋人大量描述,越到后期,描述越少。绍兴一带的东湖是风景区,李希霍芬的描述相对科学真实:
第二天早上我在湖面上绕了一个大圈。这是一个人工湖,由一座长15米,高5米的大坝拦截而成。湖水大概深两米,混浊死寂,如同小池塘里的水质,且长满了水草,看来湖里有不少鱼。湖岸有些起伏的地方,湖水冲到山间的一些湖湾里。大概有45-50平方公里那么大(根据我的草图测算)。西南边远处可见大概达到1200米高的群山。*[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著、[德]E.蒂森选编:《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李岩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3页。
据他的描述看,嘉湖与绍兴的一般水塘并不洁净,活水流动与塘水更新差,这也符合明清时的水流状态。在太湖周边地区,他对村庄与田野的景观作了描述,且与欧洲作了对比:
(12月9日)太湖呈椭圆形,东南端距西北端40公里,西南至东北25-30公里,深度大概不会超过1.5米。岸边地势平坦,长满了芦苇,尤其是东南边。湖上散落几座岛屿,岛上多山。看起来上面都有人住,即使是最小的岛上也建有房屋。除了渔业外,当地还有很多人从事纺织业。房屋都是石头的,屋顶铺着黑色的砖。也许在房刚刚建成的时候曾经粉刷过白灰,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根本就看不出来了。整个村子呈现灰暗的色调,如同废墟一般。这般景不由让人想到了意大利。相似性不止如此,村外的景色也假曾相似,到处种满了桑树,形成一道道树墙,狭窄的小路就从树底下穿来穿去。树下还种着很多蔬菜和豆类植物。但是没有玉米和葡萄,如果有的话,那么这里的景色和伦巴第很相似。*[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著、[德]E.蒂森选编:《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李岩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9页。
太湖美景和沿岸桑基农业,李希霍芬给出了西式科学描述。村庄景观不美,但他仍说这里的景观像意大利,以现代的眼光看,可能很美。只是他的审美,也受到了当时盛行的欧洲科学审美观的影响。自然科学大兴后,人们对田野的赞美不再集中于自然化和人文艺术化,更赞美科学设计下的园林和田野,李希霍芬对中国景观的评价不高,多源于此。但是,李希霍芬也不否认中国局部景观的文化特色,对一些特色景观,特别是小石桥,仍给予了高度地评价。中国特色的园林化景观被这位西方科学家欣赏:“连河道上那些美丽的石桥都是花岗岩造的,石块被打磨得非常光滑,大概有三四米长,形成完美的弧度。”*[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著、[德]E.蒂森选编:《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李岩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0-51页。
中国文人看到景观不佳处,往往不描述。当时整体的景观衰退,因此文人才没有更多的田园诗。以江湜为例,他在临平关注到河中的水生植物,这是少有的水面美丽景观。“水市菱初老,霜畦麦又生。来因迎使节,默自动乡情”,这只能算是中性的景观评价。在松江城外有闲地,他在这里散步,也感叹家乡苏州城的拥挤。他认为当时的苏州城“尺土借人百金赎”,这是寸土寸金的描述。在这里,“无隙能栽半竿竹”。长期以来,传教士和外国考察者也这样描述人口拥挤的苏州城。在山水之间,往往有树木和水面,这样的地区是山水画中的景观,被古人讴歌,也被近代诗人赞美。在宜兴,江湜提到了这样的农田。“我闻阳羡山,其下多良田。田多须水溉,此水余清涟。单锷知其利,乃不知其妍。我观上流平,瑩瑩玻璃然。树影忽倒落,写入波中天。有如皎月色,布满寒林前。”*(清)江湜:《伏敔堂诗录》卷八《松郡城南地甚闲旷,可散步》《宜兴道中观水有作》、卷十五《临平道中》,左鹏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5-146、154、298页。
中国文人很少描述荒草与聚落的景观状态。徐兆玮曾提到常熟荒地。“兵燹之前,本有老荒;兵燹之后,又增新荒。以予所知,昭邑除张、吴、归、何诸市木棉地全熟外,每图各占荒田十分之二三。”*(清)徐兆玮:《徐兆玮日记》“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三十九日(9月3日)”,李向东等标点,黄山书社,2013年,第104页。李希霍芬在西湖附近看到了衰退的野生景观与荒凉的村落,对乡村在战乱后的破败和杂草群落对村落的侵占,描述得非常清晰:“我回到河边,沿着河岸有一个长长的村子,在村子和山坡之间是居民的耗时地和田园。看得出来以前被耗时种的地方现在大部分都荒废了,杂草丛生,甚至延伸到村落中。村子里大部分房屋都成了废墟。”*[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著、[德]E.蒂森选编:《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李岩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56页。这是一种战后的荒凉,农业活动以零星的集约化方式开始,很少出现技术的中间形态,没有像西方或中国早期的那种休耕形态。李希霍芬在江南发现了农业技术体系在周期性衰退与重建过程中的技术稳定性。正是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使中国农田景观塑造没有农业技术的中间类型。人们重新恢复农业时,只耕种少量田地。
究其原因,除了在太平天国时期遭到破坏外,此地人口众多,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却就这样白白荒着,可能由于这里的人只被允许开垦指定的土地,不能自由耕种土地。另外还可能在受到工具和耕作方式落后影响而导致的劳动力低下。当然缺少肥料也是重要的原因。情况常常是这样的,人口因为战争或是疾病减少后,需要人工施肥的那些作物自然跟着减少,相应的耕地的数量也减少。如果当地减少一半的人口,那么耕地的面积也跟着减少一半。南北方相比较,南方出现上述情况的可能性更大。*[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著、[德]E.蒂森选编:《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李岩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56页。
中国农业对肥料的依赖,决定了农民在开荒初期,由于人口较少,只耕作较少的耕地,其他地荒废,呈荒野状态。周期性动乱发生后,杂草丛生。随着人口增加,田野被辟为农田,部分为荒地。完全垦殖后,又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多而形成更多的小块农田。田野的周期,只是一块块集约化农业斑块迭加的过程。中国农业在近代人口增长的周期下,不是边际效益增加或递减的周期,是肥力决定下的生产恢复的周期,这是由生态循环和几千年以来精耕细作技术水平所决定的。李希霍芬认为,尽管中国农业是一种发达农业,却没有达到土地利用应有的水平。他发现太湖周边的山丘没有被利用,长满了野草,没有种葡萄,更没有羊,认为这是一种遗憾。他认为林牧业需要提高,而中国人在生活上没有那么多的需求,稍事耕作就能不依靠外部力量吃饭穿衣。如果欧洲人利用欧式农业经营技术,荒废的山岭和草原会被用来发展畜牧业,“得到的产品将成倍地增加”*[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著、[德]E.蒂森选编:《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李岩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9-50、257页。。偏向种植业的中国集约化农业技术,是人口压力较高下的一种状态,但是,这种技术没有应有的弹性,以至在人口较少时土地利用不充分。他更受当时的资本化思维的影响,看农业景观,不再是一种风景欣赏,而是一种资本价值的评估。在欧洲,当时的许多草原被圈成牧场,一部分农田也被牧场化。但是,中世纪的敞地景观依然在一些地区存在。*[法]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余中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0-263页。在乡村,许多共同地被保护下来,乡村人有着共同放牧权,这种公共地,有着公共的景观,不像中国的小农经济下的景观农业化和小型化。
英国历史学家西博姆习惯于从古纸堆中寻找长期以来在其祖国的土地上被抹却的共同地役制,1885年他十分惊奇地看到现实社会中畜群在博斯的留茬地上游荡。法制对强制轮作的废止在第一帝国时期激起一片遗憾声。实际上它长期存在着,几乎同过去一样蛮横不可一世。在长型田块区,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强制决定于土地的形式,甚至还有道德束缚的因素。在洛林高原,在阿尔萨斯或勃艮第的平原,到了春天,三圃制的三部分以其各异的颜色争奇斗艳。只是在以往用来休闲的田块上,新的作物代替了稀少的荒草。*[法]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余中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2页。
中世纪的三圃制一定程度的存在,是农业技术的中间形态。在中国,小农占主导地位,景观随意化,即使种植同样的作物,也有一定的混乱度。
中国小农群体有一定的园艺审美水平,破烂状态是在一定道德、制度和人口的压力下,整个小农群体对景观的放弃。但是,国人原有的园艺素质又可以随时恢复田野的生机。在适合自己的土地上,小农会经营自己的田野空间。由于政治对乡村社会的压迫,基层社会的管理能力才出现大幅度地下降,许多小农放弃了庭院和田野空间的管理。罗斯对中国的田野经营没有什么好的评价,他看到的中国田野只有农作物: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的确被开发成“花园”式了,因为每块石头都被砸碎了,各种杂草都被除去了,各种作物都像婴儿一样得到了精心的照料。一种粮食作物即将收割时,另一种已准备下种了;新的作物经常种植在还未收割的成熟作物的行间。“花园”一词本应使人产生美感并感到愉快,而在中国不会有此感觉。在任何一个乡村里,人们都找不到被留下来用作娱乐场所的空地。没有绿地,没有草坪,没有鲜花,也没有点缀生活的树木、公园和乘凉的地方。*[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公茂虹、张皓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第80-81页。
明清以来,中国乡村审美基本限于田野,没有公共绿地和空间。农民的庭院和士人的园林是私有的,外人无权欣赏,田野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公共空间了。士人消失的时代,也是审美空间大衰退的时代。这时的中国小农,在经济衰退中尽力维持着田野的生产力。他们维系着农业的可持续性,供养了大量的人口。
李希霍芬及一些西方人士对江南的评价,有真实与科学的一面,尽管中国人也有涉猎,却没有西人详细。到20世纪,从卜凯到日本学者和满铁的调查专家,都以科学认知为前提研究江南农业。他们对人均地亩数、劳动力投入等技术性指标过于敏感,相对忽略地理景观和技术形态。天野元之助对松江的调查涉及到聚落形态和人文景观,这种调查的景观呈现,并不是有意为之,是日本调查的那种面面俱到的特色所致。大部分调查没有李希霍芬的景观视野。*[日]南满州铁路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40年。许多西人仍然没有忽视田野之美。英国画家利德乐看到西湖周边农田中的水牛与水田时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叹:“早餐后我到岸上散步,没走多远就见到一幅典型的乡村图景。水牛在水田里耕作,为播种作准备。‘啊!’我想道,‘无需浪费时间’,决定画下这个画面。”他不但肯定传统江南农业的田野,也对中国的传统农业持肯定的态度,当时的大部分西人却不是这样。“人们正在田间辛勤耕作。有的锄地除草,有的抬着一桶液状物,往土里施。气味随风飘来。在中国什么都不浪费。但外国人对这种用恶臭的粪肥浇灌作物的方式不太赞同。他们要求大家当心自己吃的蔬菜,经常还强制人们彻底放弃蔬菜,特别是沙拉和生蔬。”*[英]托马斯·霍奇森·利德尔:《帝国丽影》,[美]陆瑾、欧阳少春译,李国庆校订,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54、70-71页。清末有一位真正的农业专家,他对景观和中国传统技术的评价一直影响到现在,这就是美国专家F.H.金。
二、F.H.金与中国传统
美国土壤学家F.H.金在1909年对中国的考察,不单用现代科学揭示了中国有机农业的持续性问题,而且对江南细微处的景观作了细致地观察和理解。他的《四千年的农民——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是一本伟大的学术专著,出发点是解决世界性农业问题。他在研究技术形态的同时,也对江南田野的景观有详细地记载和研究。*[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东方出版社,2011年。他的观点与中国古代农学家不谋而合,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农学思想。
金用照片见证了吴淞江两岸狭长而陡的山坡地上的光秃景象,这种景观也是罗斯所描述的那种景观,他看得更为仔细,也知道江南发生的强人口压力与燃料危机。“那里的树木沿着山坡呈带状分布,树龄在2-10年之间。它们与垂直边界地区不同年龄的树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特别狭长的地方还不足两根木棒宽,其中一个地方的树木最近被砍伐光了,我们沿着这儿走了很长一段跑离,看见周围的松树生长状况非常好。在一片30×6平方英尺的土地上,树木多达18棵。在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东西都被砍光了,连树桩和粗大的树根都被挖起来用作燃料。”这种砍伐使古代的森林更加减少。近代上海的兴起与人口聚集引起的燃料需求大规模增加,林地破坏普遍存在,虽然当时也有植树造林和林地的维系更新。在上海吴淞江西岸的山丘上,他看到,“许多人挑着扁担将一捆捆的树枝运下山去。我们就山坡地的造林计划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树根能回收利用使广泛地挖掘树根成为必然,树根被挖起后,新的树苗便能够迅速成长。因此这儿并不需要大面积地种植树木”。一般家庭有培育松树苗的苗圃,苗圃处的树苗生长,异常迅速。*[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87-89页。他的描述似乎在纠正李希霍芬的陈述,想说明虽然中国的山林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人们也正试图恢复这种山林生态,他的目的是想说明东亚的农民更具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金发现东方的田野时空是一种拥挤的时空。这包括一年四季集约化耕作,田野的自然景观在农业集约化下产生的复杂度。正是这种集约化空间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经营,西方大农场那种整体景观没有出现。华北有间作与套种,江南有各种各样的灌溉河道与小水塘,地面上有各种积肥设置,秧田与插秧田景观各有特色。他在浙江看到一块刚刚整理好的稻田,准备插秧。田被整理过,挖出的泥土被弄成了粉末,然后与泥浆混合在一起。这种挖土填土的过程,对一个中国人而言再平常不过,金却视为一种独特的农业经营。有序的插秧人群,也成了他关注的对象。水车灌溉,运河旁的水车棚,也都是他欣赏的对象。*[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160-188页。古代文人也对这样的稻田与人群进行过赞美,小农经济与江南地貎结合,孕育出陆游和范成大的田园诗歌。当时的江南田野,生态未遭大规模地破坏,适合士人审美。南宋的楼璹在临安做於潜县令时,访问田夫蚕妇,制成耕图二十一幅,织图十二四幅*王毓瑚编著:《中国农学书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88-89页。,此为《耕织图》。《耕织图》本身说明了农村一般农民的审美关注,与此同时,《耕织图》中的景观,特别是农夫、田埂、稻田、秧苗以及家庭内的织机,也是士大夫的审美对象。农夫在有风格的田野上耕作有一种中国特色的朴拙之美,这种美为中国各阶层所共通,也为西人所欣赏。
田野中的积肥景观是江南集约有机循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农业的生态系统维持中,积肥不可或缺,但这部分景观被传统的中国文人抹去,因粪屋与便缸景观不雅。不过江南古代农书的作者们却重视这类设施。陈恒力对南宋陈尃《农书》中所讲农居之侧的粪屋有所复原。《补农书》讲调了肥壅的重要性,记了“粪窖”和“粪潭”等设施。尽管如此,陈恒力认为古人并不重视积肥设置,北方的粪堆积于屋外,南方的粪缸露天放置,会受到雨冲日晒的损失。陈认为西方人更重视这类设施:“我曾听去过比利时的同志说:比利时人口众多,已耕地少,农家特别重视积肥设备,做成大粪池,用水泥抹墙,上也有盖,不使人粪尿一点损失,又讲究保肥料的质量。”*陈恒力编著:《补农书研究》,王达参校,农业出版社,1958年,第132-134页。其实,中西方常常相互误解,金与西方农学家就对中国古代的粪便处理有很高的评价。金描述的这一部分景观,不是批判的眼光,而是欣赏的眼光。这一部分景观,连士人都视为不雅,西方人士却认为中国的粪便处理有益于公共卫生。金引斯坦力博士1899年的讲话说明中国经验:“从中华民族诞生以来的3000或者4000年间,中国的出生率一直都显著地超过死亡率,且中国的卫生情况比中世纪的英国要好得多。家庭卫生的主要问题是每天打扫房子,假如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又能获得一些额外的利益那就更好了。极富文明的西方人焚烧垃圾,将污水排入大海,中国人则是将两者都用作肥料。中国人不浪费任何东西,并且总是将神圣的农业职责铭记于心。对细菌的研究工作表明,处理人粪尿和生活垃圾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它们埋在干净的土壤中自然净化。”斯坦力博士认为上海没有什么必要建设西方式的卫生系统,中国传统处理方法即可。*[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116-117页。
金的价值判断往往也与江南乡下人一样,松江与上海的农民可以辨析土地粪力。同光年间的《吴下谚联》有言:“粪,所以美土疆。清者力薄,浓者力厚,此自然之势。何松江之一清水者,反胜于上海之浓厚,以铁搭坌取者乎?盖上海土高宜麦,与华、娄产稻之乡异。松江人每嘲为东乡吃麦饭,故其粪无力。松江人心思尖锐,不似上海人直遂,上洋人每嘲松江人从肚肠中刮出脂油,故粪虽清薄而有力。”*(清)王有光:《吴下谚联》,石继昌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第66页。作为20世纪的美国农业土壤学家,金对人们的施肥和耕作有特别的观察。中国古代的农书和农谚中都有对农民施泥肥重要性的阐述,金也详细地记载了昆山和嘉兴一带农民挖河泥并堆叠到稻田或桑基上的情景。他观察到河边田地每英亩的淤泥堆积量达70吨。淤泥堆于河边,形成有坡度的田块。一些地区的淤泥堆于路边。上海附近,他看到人们利用退潮和涨潮之间的空隙从苏州河里挖淤泥。“农民还告诉我们每两年这些淤泥就会被更新一次,要是能够获得一些其他更便宜的肥料,更新的周期就会更长。”在嘉兴南部,“淤泥在田地的表面形成了一个2英寸厚的松散保护层,下雨的时候淤泥在雨水的冲击下会变得更加坚实。雨水会携带一些泥土而来,这些泥土在地面堆积的厚度不超过一英寸。因此,每英亩桑园土地的重量可能都超过120吨”。游历上海、嘉兴和杭州时,他发现:“这些土壤是从农田周边的沟渠里挖出来的,之后它们被堆放在河床沿岸。据我们判断,运河里的泥沙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它们可能吸收了石灰、磷酸以及碳酸钾等水溶性物质。据一些农民判断,它们也可能在水中经历了生长或者发酵等过程。正因为这些变化,人们调换土地的劳动才有了价值。将土壤堆放在河岸上,是为了方便用船将它们运送到桑园中去。”*[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97-100页。为了一点肥力,人们在搬运大量的土壤,土壤景观处于这种不断地被折腾状态。土壤的堆叠,可以快速地影响小地貎环境。徐琪指出:“在圩田地区,除开沟排水外,大量施用河泥,垫高田面,以逐步降低地下水位成为改土的主要措施。根据当地施用泥肥习惯,以每年每亩施用河泥40-50担(约合4000-5000斤)估算,每六七十年即可垫高一个耕作层(20厘米厚),每三百年大致可堆迭成一个1米厚的土剖面。”*徐琪等:《中国太湖地区水稻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4页。
嘉湖地区的桑基农业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这种农业可以塑造美丽的河网、水塘、桑树和采桑女的景观。农民精明地经营着桑基农业的空间。外国考察者经过运河时,只看到桑树景观,没有细致考察农业的形态。金博士对桑树进行了考察,他的研究与中国传统农学家十分相似。明清时期的江南农书讲到的拳桑被金用相机拍到,他看到三排桑树与两边的稻田相间的景观,还看到一些刚刚修剪过的老桑树干和刚刚长出第一季桑叶的桑园相并排。他对桑树的观察是植物学家式的:“树上的长枝是由去年的嫩芽长成的,而且它们上面的桑叶至少已经被采摘过一次了。在长势良好的桑园里,树枝可能长到2-3英尺。”他看到的桑树,大多具有12-15年的树龄,“树枝的末端能不断生长主要是因为每年都会对树枝进行修剪。树底下的土壤上覆盖有一层厚厚的刚绽放的粉色苜蓿,之后会将它们埋进土壤里,它们就会为土壤提供氮和一些有机物质,腐烂之后它们还会释放出一些钾、磷和其他矿物物质作为植物养料”。*[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198-200页。桑树景观经不起战争摧残,桑蚕业需要的积累比较多,战争环境下,养桑的时间较长,投资没有即时效应。愈樾发现他的家乡湖州在太平天国时期难以养桑。“吾湖蚕事,甲于海内。而兵兴以来,受害最酷,菱湖、荻港等处,向称蚕桑渊薮,而村落化为邱墟,人民转于沟壑,几乎靡有孑遗焉。意者积数百年养蚕之孽而发之一旦乎?”在这种情况下,“广种桑树,不如多植木棉”*(清)愈樾著、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403页。,正是这一战争环境,导致了桑地景观的变化。
嘉湖平原的人们挖河引水蓄水,不断地堆叠土壤,扩展桑地面积,地面变得高低不平,这种高低不平有一定的美观度。建房的房基高低不平与挖池后形成的桑竹种植相配合,形成一种美化。“凿池之土,可以培基,基不必高,池必宜深。其余土可以培周池之地,池之西,或池之南,种田之亩数,略如其池之亩数,则取池之水足以灌禾矣。池不可通于沟,通于沟则妨邻田而起争。周池之地必厚;不厚,则妨邻田而丛怨。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之五《别楮》,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122页。种桑竹、培房基和桑基,美化了田园与房屋。陈恒力认为明末清初的旱地和稻田的平整程度比20世纪50年代好得多。他在杨园村发现:“桐乡县杨园村一带的地基比田面一般高六、七尺,低的三、四尺,高的十余尺。事实上从那时就已开始使整个地形复杂化起来,一是使地基高,一是使池塘深,一是使田面小。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设计,在一个小地段内,使田、地、池错综起来,就形成了地面的高低不平。”*陈恒力编著:《补农书研究》,王达参校,农业出版社,1958年,第117-119页。
清代以来,蚕桑大利,农民的培土热情日益加高,桑地扩展,景观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金看到的挖河泥与土地不断地被折腾的状态,是长期以来的一种活动。肥力决定了地表景观的变化。生活于18-19世纪的钱泳曾指出:“增筑隄岸,亦有法焉。必今年筑若干,高取葭菼以蔽之。明年增若干,高插水杨以护之。后年增若干,高取罱泥以益之。三年之后,草木根深,隄岸坚固矣。”在这一过程中,取别处之土以增圩岸。“或于田旁近地,取其圩塞河道之土以筑之,或罱河底之泥以益之。如最低之田,无从取土,则在田中开一塘,挑泥增岸,盖农人每以粪壤为肥禾之用,一年高一年,仍取田土以实之,并无妨于田也。”*(清)钱泳:《履园丛话》,张伟点校,中华书局,第102-103页。挖河泥的过程,伴随着水塘与河港水利设施状态的维持。金看到桑基农业所呈现出来的小规模景观特色,桑基鱼塘是河港末端发展的结果。照片中河道有船,河岸上有成排的桑树。无桑树的区域为蓄水池和水塘,河渠连接着水塘,“它们之间通过表面沟渠和运河相连”。水塘与河港相连,水塘的淤泥可以肥田,他也看到水塘与小路的景观。*[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60-61、100页。
随着土地升值,田园规模减小,大量士子在小生境基础上寻求环境怡情。张履祥提出凿池形成小环境,在小环境基础上精细经营,以此形成士绅的优雅生境。这种小生境也需要很高的成本,池塘边种桑竹,然后筑室。“筑室五间七架者,二进二过,过各二间,前场圃后,竹林旁树。桑池之北,为牧室三小间,圃丁居之。沟之东,旁室穿井。如此规置,置产凿池,约需百金矣。少亦需六、七十金。其作室亦需此数,非力所及也。积渐废产以置产,约略相当,作室则全无措手矣。”*(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之五《别楮》,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122页。这种耕读之境需要士人家庭的长期积累,还需要小农的种植与经营经验。水塘在嘉湖地区是用来抗旱蓄水的,也被农民巧妙地利用到生态循环中,因此农民视小水塘为宝。这种经验一直得到持续。在海宁县袁花公社,集体化时代有“弯弯曲曲的沟渠七高八低的田地;零零星星的田壤;稀稀拉拉的专桑(专业化桑园);七零八落的溇潭;继继落落的河浜;东分西散的住房”之说。1970年代的档案曾这样说:“溇潭多,河港少。田间积水多,地下水位高。小农经济看作‘金饭碗’的溇潭一千四百零八只,面积达一千五百五十九亩三分。”90%以上的渠道是弯的,水乡特色强烈,水网末端非常复杂。明清时期的破碎化与圩田小型化演化,形成了有特殊生态意义的小水潭。*沈文华:《抓大事、促大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情况汇报》,1973年12月12日。桐乡市档案馆农业机械水利局档案,档案号:56-1-8。这种小地貎上的自然生态循环,构成小农的金饭碗,是小农稳定的生态基础。这种小农经济的基础景观与当时集体化时代的制度体系不吻合,致使这种小型的生态景观在集体化时代逐步消失。
田野中泥土小路,是古今中外的审美主题之一。江南的小路与圩岸一体,加上小桥流水及其与周边植物配合,有着非同一般的美。小路的复杂,应该是个体地块产权分散的一种表现。在艺术作品中,士人突出小路的田园风光审美。在修路时,道路的占地,需要得益的小农有共同的认同并且捐出一段路面,“农民为修筑道路而捐出的土地都不会是笔直的,因此,所谓的乡村道路就是逶迤曲折,比两地的直线距离增加了一半的长度”*[美]柏生士:《西山落日:一位美国工程师在晚清帝国勘测铁路见闻录》,余静娴译,李国庆校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明恩溥曾经描述过乡村道路那种缺乏养护的状态。在北方,人们不向道路提供泥土,路面很快低于周边的田地,再加上排水时人们向道路排水,由此道路会成为死水河沟。*[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第29-32页。江南的路多是圩田岸,明显地高于田地,经过较大河流时有优美的拱桥,远比北方乡村更有诗意。麦嘉湖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道路的国家,没有路权,大家都使用时便是公共的。他认为自然的路是最好的。小路弯曲,使人迷惑,是一种防御外人的手段。“大自然不赞成这些正儿八经的大路,于是通过风霜雪雨,通过杂草蒿莱,通过野花和灌木,竭尽全力让它们与周围世界的美协调一致。”小路在雨水时泥泞,是其生态性的一面,于人不便,却是生态的,可持续的。“雨一直在下,小路在那些优雅地弯向路面的低垂的稻穗中间蜿蜒穿过,形成完美地弧度。它只有一英尺宽,即便是在晴好的天气,脚底下也需要相当的稳定性,才能避免滑入那黏糊糊的污泥中。”他认为中国的小路不像西方那样被用于审美目的,他也认为具有审美景观价值的是那些桥。*[英]麦嘉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秦传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253-261页。其实,士人文化有深厚的小路与小桥的审美传统。
三、集体化时期
江南集体化时代的统一化景观的形成,有制度因素,更有19世纪西方和苏联大农场思想的影响。无论在美国还是苏联,景观划一的撼人之感被认为是先进的经营方式。这种统一的景观,其中既有资本权力,也有政治权力,这两种权力都受到科学规划思想的影响,也产生了相关的权力美学。马戛尔尼使团主计员巴罗就认为小田块不经济,他对中西方的大农与小农有过详细的阐述,他讲的是资本的权力景观配置观。“英国大农胜过小农之处,主要在于大农户供给佃户的农具比后者使用的要好,因此耕作起来利于下种。富裕农户在同样面积上的生产常常超过小农。在中国,农民算是小农户,牲口很少(我可以说几百万人完全没有),不能指望全国能达到多高的耕作水平。或许我们可以承认他们在园艺方面的特长,但大规模耕作,他们肯定不能和许多欧洲国家相提并论。”*[英]乔治·马戛尔尼、[英]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48-449页。他认为中国没有大家场,在许多地区没有效率与产量。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家都认为中国小农落后,改造的模式应是美国式大农场或苏联式集体农庄。这种改造在民国时期没有得以落实,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制度条件具备,中国田野发生了几千年没有发生的事情。这种改变甚少在美学上值得反思。整齐一律在美学上只是一种初级阶段的审美,生命的韵律之美,是一种高级形式,中国的田园之美,表现出一种生命的韵律与品味。黑格尔说:“在绘画里,整齐一律和平衡对称也有它们的地位,例如在全体的结构、人物的组合、姿态、动作、衣褶等等方面。但是在绘画里比起在建筑里,心灵的生气更深刻地贯注于外在形象,平衡对称这种抽象的统一所起的作用就较微细,只有在艺术起源时我们才看到严峻的整齐规则,而在较后时期,绘画的基本风格就变为接近有机体的较自由的线形。”*[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17页。
集体化以后,乡村纳入政权体系中,政权力量推动了田野景观的统一化,道路系统和水利系统可以被轻易地改变。官方用群众运动的组织形式对传统地表景观进行整治。挖河泥仍然像金看到的差不多,只是规模非同一般。1958年搞积肥运动。在常熟县,当地推广了干河取泥之法,排水之后动员人力大规模挖河泥。“车大河,带小河,顺带小潭塘。”挑出来的河泥上一层做肥料,中层垫低田,底层作圩岸。最后,全苏州专区都在学习常熟的干河取泥经验,而群众运动的景观也非同传统时代的组织规模。“白天满河人,夜里一片灯,到处是车水声。”许多长期没有动的河道也被清理了,“干的河有的是连江大川,有的是通湖深渠,连前清咸丰三年、乾隆六年和太平天国以前从未开过的河道都翻了身”。*《苏州专区冬春积肥运动情况(资料)》,1958年4月27日,苏州市档案馆,档案号:H37-3-12。新形式的机械排灌改变了传统的田岸大棚车制度。在吴县,“农家遇大水则集秸槔以救之,鸣金击柝以建作息,建瓴滴水以时番休,号大棚车”*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上《风俗一》。。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集体化时代。昆山县石牌乡有7个大圩子,他们的集体排涝叫“车大滨”,他们的圩田都有3-5处车口,“过去的每个车口,因地方狭小只能放3-5部水车”。1954年抗涝时将每个车口扩大了,扩大后的车口叫“大棚基”,可容纳10-30部3人轴的水车一起工作。这么多的水车大概也只有一部抽水机的效率。*江苏省昆山县人民委员会:《抓住圩田特点,采取多种多样的排涝方法:石牌乡基本上取得了防涝斗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第二集),水利出版社,1958年,第525-533页。随着机械排灌的兴起,传统的排水景观消失了。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农田方格化是一种统一规划的产物,这种规划使传统圩田的特色被改变。在吴江低地地区,平整化特色取代了传统景观的高高低低。1959年,“11月30日统计:全县已平整土地,扩大耕地面积2999亩,其中开生荒地745亩,并结合改良土壤28726亩,全县秋播深翻6寸以上土地28万亩,占秋播耕翻面积48万亩的58.3%”。这种平整伴随着土地连片,“土地连片,耕作方便,节省人工,为机械化鸣锣开道”。平望乡幸福大队阉前圩,坟山、土墩、沟潭众多,耕作不便。犁田转弯多,耕麦田脚多,兜的圈子多,每年要浪费230个人工。平整土地以后,种麦时间缩短了2天。北厙公社东风大队禽字圩有685亩,最大的一块只有6亩。当时的人把土地景观与政治挂上钩:“封建田岸千百条,小农经济几分田”,即小块田属封建社会,高级社则大连片。整田以后,都是30-40亩一连片,方向南北,分6墐,呈井字形,“过去牛也难走,现在拖拉机也好开了”。*江苏省苏州专员公署农业局:《吴江县农林局关于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情况报告》,1959年。苏州市档案馆,档案号:H35-3-73。
昆山县城北公社同心大队有13只圩,整地前的地貎状态是:“田形畸形不正,土地高低不平,墩、潭、溇、塘,田块大小不一,水沟另乱无章,弯曲堵塞。”可以看出,传统田块地貎特征有多样性并富有弯曲性,有一定程度的高低不平,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传统园林的美学特色。文件称其有十多,“田岸多、潭塘多、坟墩多、田角多、死角多、荒废多、受涝多、耕田起犁多、灌溉用水多、蒔秧补尖多”。在这十多中,大部分是针对统一化经营的生产方便而言的,田岸多、潭塘多和坟墩多,并不见得不美。文件认为这种景观是小农经济的景观。“这种小农经济时代遗留下的土地利用方式,限制了农业高速度发展。当时正处大跃进时期,人们对农业的高速度发展充满了想象。这个村将原来600多块平均3.8亩左右的田块调整为190多块12亩地块的方正田。减少了田岸400多条,与此同时,填平浅潭10个,荒塘320个,这样的工作基本上使原来参差多态的地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实行了‘五化’,即田块方正化,排灌渠系化,劣土良田化,种植成片化,田间机道化。直看成条,横看成排,岸直似浅,渠道干支纵横,块块能灌;水沟有纲有网,条条通河,旱涝无忧,土地面貎,焕然一新。”*昆山县城北公社同心大队:《昆山县城北公社同心大队破旧立新,大搞平整地土,实现园田化的情况》,1959年11月11日。苏州市档案馆,档案号:H35-3-73。村庄组织重视排灌方便,也欣赏横平竖直的方形田块。
在松江县华阳桥乡,1958年的平整土地被视为是有利于机械化发展的重要举措。1958年的要求是:“在耕作区范围内,地平面差度一般不超过0.5-1市尺,成片地至少在1000亩以上,且要求地形端正,一般呈长方形。”对耕作区的坟墓和台基,官方要求迁移或下埋。耕作区内也填了许多小河浜。“对大涨泾、官绍塘等10大河港需要疏浚以利灌溉和用水;其他支河小港,其对机耕不利而工程较小的,1959年内予以填平,工程较大的,以后逐年填平。”*松江县城东乡委员会:《以联民社为中心发展为集体农庄的规划草案》,1958年7月6日。松江区档案馆,档案号:37-1-58。太仓县的太星大队有海塘,有潮水的感潮,有低地与高地的景观。为防潮水倒灌,有一系列的圩堤。集体化时期整修大、中、小圩堤,建造水闸。这是在传统守堤基础上的建设。1964年暴雨时,“大队支部党员亲临第一线,带领贫下中农,日夜守护圩堤,指挥排涝。”方法为:“严格做到内河与外河,河和田,高田与低田三分开,先排低,后排高,先紧后缓。”*《太仓县西郊公社太星大队一九六四年农业生产持续大幅度增产经验总结》,1955年。太仓市档案馆,档案号:521-4-64。在嘉兴的圩荡田区,那里原来的景观是一个个的圩头,四周环河,外河的水位,常与圩内田面相平或略高于圩心。这种传统的溇港围田,现在已成为文化遗产。1958年以后的整地,破坏了这种形态。集体整修圩埂,打井疏河,打坝并圩。打坝并圩是用打坝方法封堵圩与圩之间的河道,使原来小圩成大圩,规模在1000亩左右。圩与圩之间的河也成了圩内河道。这种作法改变了特有的低洼地带的小圩田景观。*浙江省土壤普查土地规划工作委员会编:《浙江土壤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0页。
海宁县袁花公社的农民将小规模的桑基稻田和水塘视为金饭碗,到集体化时代,这种金饭碗被定义为落后的小农思想。小水面、小桑园、小田漾被全面整治。“全社已有田漾二千零六十五只,二万六千八百一十五亩,规划为六百零五只田漾。三万一千二百零七亩。专桑二千七百零三块,九千八百七十二亩,规划为六百零二块,一万零五百二十亩。旱地二千四百二十五块,规划改成三百七十二块。三千五百八十二亩。”*沈文华:《抓大事、促大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情况汇报》,1973年12月12日。桐乡市档案馆,档案号:56-1-8。随着田块方格化,桑基鱼塘发生了变化。水塘、稻田和桑树被统一规格化了。徐琪的《太湖地区水稻土》一书1979年彩色图片所展示的吴县洞庭公社的桑基鱼塘方方正正,吴兴县苕南公社的稻田与桑基也方方正正。*徐琪等:《中国太湖地区水稻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页。桐乡县提倡小圩并大圩,小田畈并大畈,根据河流、浜与稻田的位置进行合并。小田畈并入大畈以后拆掉田埂,一般田畈3-4亩一块。还要将低田变成高田,在这过程中,田边旱地上的几棵小桑树也要移栽。*《低洼地区水稻生产的调查总结报告》,1958年,桐乡市档案馆,档案号:55-1-46。由于桑蚕业的重要,官方加强了专业桑园建设。桐乡县蚕种场为保护传统的桑园,不使间作作物进入桑园。*《浙江省蚕种场桑园栽培管理操作规程一(初稿)》,1964年。桐乡市档案馆,档案号:55-1-130.
四、结 语
农村改革后的新体制适合了小农的经营规模。这一小规模经营,没有了古代小农的那种田园诗化,田野的森林却因绿色革命的成绩而得到了恢复。但是,乡村景观的建设却仍然延续近代景观混乱化的倾向。河流、田地和植物的田园风光没有恢复,甚至连集体化时代的那种简单化田野的生机都被破坏了。简单工业化和城市化使江南田野的河流、道路与村庄都被大规模地改变,简单的现代化设施使田野处于前所未有的混乱化状态。中国乡村的去传统化、去生态化的大趋势之所以形成,是19世纪西方与苏联的思想影响所致。中国本土的传统审美,一直处于被改造和被取缔的状态。宋代的江南田园风光构成中国江南地区古典古代的生态文明,这一生态文明却在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增长和经营的衰退出现了大衰退。但即使在近代的破败环境下,其景观仍有传统审美的影子,最近60多年来的发展则几乎将这些影子消除殆尽。传统品味与传统景观同时衰落,共同空间的管理机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宋代田园诗的大盛与田园风光的优美是大量存在的。明清时期,野外景观大量丢失破坏,加上传统中央集权下乡村管理能力的缺失,公地悲剧下的景观衰退不可避免。但是,明清士人仍可以在田野中寻求田园风光,而现代的江南田野,则基本上没有传统的审美空间。集体化时期形成的强大景观管理体制,却失之于简单化与权力化。最近三十年的简单城市化影响,更是使传统审美倾向几乎消失殆尽。笔者曾在2005年和2016年对桐乡市杨园村进行过采访。2005年的杨园村尚有传统的桑园和村落形态,而2016年的杨园村已成为城区边缘,农田尚有,农民却居住在楼房式的小区内。农民没有西方种植业的景观理念,也没有杨园先生的传统审美,不是宅旁种竹,而是高楼前面种菜和杂粮,把本为公共空间的绿地种了菜。重建乡村景观须注重传统风格的古典田野景观,这不是单靠西式的设计规划所能成就的事,更需要一种古典生态文明的知识传承和文化传承。值得欣慰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领袖开始对江南小镇与传统田园产生了恢复的欲望,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提高和审美趣味的提升,古典风韵的田园风光建设将为长三角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