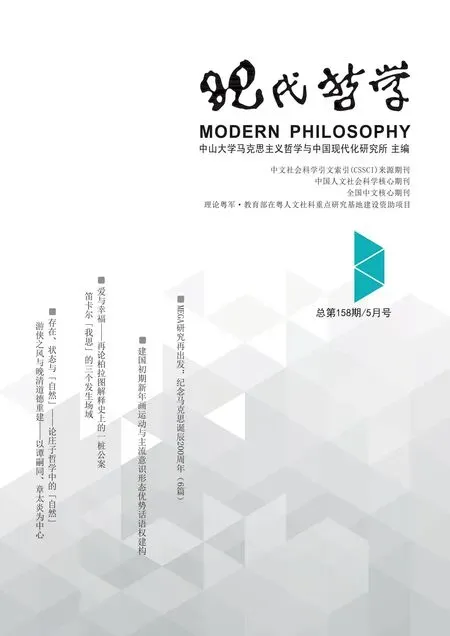论“实在与反阻”的意义
——从狄尔泰与舍勒关于实在性问题的共识与争论出发
2018-01-23王嘉新
王嘉新
自近代哲学以降,实在性问题(Realitätsproblem)就是知识论中最为核心且棘手的问题。用胡塞尔的术语表达,在自然态度下,人们不言自明地默认异己的实物以及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然而,一旦进入哲学的理论反思中,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马上就会变成最为令人疑惑的问题。这一疑难被康德不无夸张地称作“哲学和普遍人类理性的丑闻”*康德说:“唯心论尽可以就形而上学的根本目的而言仍然被看作是无辜的(事实上它并非如此),然而哲学和人类普遍理性的丑闻依然存在,即不得不仅仅在信念上假定在我们之外的物(我们毕竟从他们那里为我们的内感官获得了认识的全部材料)的实在,并且,如果有人忽然想到要怀疑这种实在,我们没有任何足够的证据能够反驳他。”([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B XXXIX ,第27页。译文略有改动。)。不过,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丑闻”的确促使人们持续地对实在性问题进行反思与研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语哲学中,伴随着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的深入,哲学家们不断尝试给这一问题新的哲学解答。*例如,青年时代的海德格尔在1911年曾撰写名为《近现代哲学中的实在性问题》(Das Realitätsproblem in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的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综述。在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引述了哲学家奥斯瓦尔特·屈尔佩(O.Külpe)的话:“实在性问题位于……未来那种哲学的临界处。”([德]海德格尔:《早期著作》,张柯、马小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页。)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狄尔泰对于外部世界实在性的反思。狄尔泰从其生命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以当时最新的生理心理学研究成果为基础,论证了实在性在生命体验中的起源,试图把关于实在性的讨论从笛卡尔主义传统下对理智活动的单一强调中解放出来。更进一步,狄尔泰的这一理论尝试对现象学重新理解实在性的努力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斯·舍勒首先意识到狄尔泰这一工作的巨大意义,并且在其晚期的手稿《唯心论与实在论》中,对狄尔泰的思考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回应。舍勒早年的哲学生涯与狄尔泰密不可分。在1895-1896年间,舍勒在柏林密集地参加了狄尔泰的讲座。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通过对狄尔泰的批评与反思,舍勒才真正获得通达其晚期重要概念“实在”的论述能力。下文将首先展示狄尔泰和舍勒的相同之处与分歧。基于此,舍勒晚期的“实在”概念才能被理解。只有理解了这里的“实在”概念,我们才能有根据地主张,舍勒晚期思考蕴含着一种以实在性理论为内容的“基础存在论”,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舍勒关于实在的学说潜在地构成了海德格尔版本的基础存在论的竞争对手。*赛普指出,一方面舍勒和海德格尔的共同策略是指出过去的“唯心论和实在论”之争背后忽视的问题,另一方面舍勒并不同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他的批评,因而《唯心论与实在论》一文包含着回应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论的意图。根本上说,舍勒的“基础存在论”的核心概念是“生命”,并不预设被遗忘了的“存在问题”,或者说并不预设某种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解释学循环。(H. R. Sepp, Über die Grenze. Prolegomena zu einer Philosophie des Transkulturellen, Nordhausen: Traugott Bautz 2014, S. 209.) 同时参阅:[捷克]汉斯·莱纳·塞普:《阻力与操心——舍勒对海德格尔的回应以及一种新此在现象学可能性》,张柯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一、狄尔泰的立场
狄尔泰关于外部世界实在性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于1890年撰写的长文《如何解决我们对于外部世界实在性的信念的起源及其合理性的问题》中。显而易见,狄尔泰对实在性的讨论并不指向实在性一般,而是明确地把对外部世界实在性的信念作为研究对象。在康德那里,只是诉诸于信念来辩护实在性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理性的某种失败。在狄尔泰这里,解决实在性问题的思路转换为:对外部世界实在性的论证,既无需贬斥信念,也无需寻求信念之外的理性功能,对实在性的辩护恰恰在于寻找这种信念本身的根据。在狄尔泰看来,信念并不意味着非理性的,相反,信念本身有其在人类意识经验中的合理性根据。
在这篇长文中,狄尔泰首先批评了当时的普遍的思维定式,即把“实在和真实仅仅理解为服务于理性功能的概念程式”(die Realität oder Wirklichkeit nur begriffsmäβige Formeln für Verstandesfunktionen)*W. Dilthey, Beiträge zur Lösung der Frage vom Ursprung unseres Glaubens an die Realität der Auβenwelt und seinem Recht, in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V, Teubner: Leipzig/Berlin 1924, S. 92, 94. (以下凡引《狄尔泰全集》,均仅给出该全集的简称“GS ”、卷数和页码。)。这里,狄尔泰的对话者是赫尔曼·冯·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后者认为,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应该被还原为感觉材料之间的某种思想关联(gedanklicher Zusammenhang),并且这种思想关联(Denkzusammenhang)应当从自然科学的经验研究中获得理解。对于赫尔姆霍茨来说,这里的“思想”(Denken)无异于根据因果律(Kausalgesetz)发生的无意识的推导(unbewusste Schlüsse)。这种因果律,作为外部世界实在性的根本保证,在赫尔姆霍茨看来应表现为一种先天给定的超验法则。狄尔泰对赫尔姆霍茨的这一观点并不满意,因为这种超验法则与思想的推导联系在一起,有其自身无法剥离的理智主义预设。在狄尔泰看来,赫尔姆霍茨在晚年偶有提及的意愿冲动(Willensimpuls)才是突破外部世界实在性问题的关键所在。与赫尔姆霍茨相反,狄尔泰不寻求通过建立感觉材料和思想之间的关联,解释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而是试图通过分析感觉材料与意愿的内在联系,揭示我们对外部世界信念的来源。在这点上,狄尔泰面对的首先是笛卡尔主义,或者说理智主义传统的强势地位:“自笛卡尔以来,大多数的解释者认为,意愿既不能压制感觉材料,也不能凸显感觉材料,更不能掌控感觉材料。这些解释者们以感觉材料的这个特点为根据,认定并且在理论上践行了感觉材料并不依赖于意愿这一观点。”*Ibid., S. 95.对此,狄尔泰并未直接予以否定,而是指出:基于对感觉材料不依赖于意愿的坚持,而忽视或者否认感觉材料和意愿的根本性关联,会使人们错失理解实在性信念的根本要素的机会。针对这种理智主义的成见,狄尔泰写到:“我不从思想关联出发,而是从在冲动、意愿和情绪中被给予的生命整体出发,解释人对外部世界的信念。”*Ibid., S. 95.
这里,狄尔泰很明显地展示了他的知识论立场与他对生命整体的研究纲领之间的深刻关联。与理智主义进路纯粹关注作为功能性的思想不同,狄尔泰试图在人的生命的体验(Erleben)中寻找实在性的起源。而且,逻辑与思想本身只有在“在体验中敞开的生命”(das im Erlebnis sich erschlieβenden Leben)中才能得到理解。与此相应,狄尔泰主张必须充分发掘了感觉(Empfindung)的认识论价值,才能恰当解答实在性问题。对于狄尔泰来说,实在性问题不单纯是思想的问题,而是生命本身的问题。*Vgl. H-U. Lessing, Wilhelm Dilthey. Eine Einführung, UTB: Stuttgart 2011, S. 65.
问题是,实在性是如何在体验当中产生的?狄尔泰认为,对于实在性的信念首先必定预设了人的内在(Innensein)和外在(Auβensein)之分。这一区分无需通过意识的某种功能实现的,其本身就是意识的性质。在他看来,对于这一性质的进一步解释要回到人的反阻经验(Widerstandserfahrung)。这种经验产生于意愿的两种不可分割的状态:第一种状态是意识中的意愿的冲动,第二种状态是对这种冲动的抑制(Hemmung)。这两种状态尽管不可分离,但是在狄尔泰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的,而且是间接的。
首先,意愿的冲动是自发从内在而生的,狄尔泰把它称作“意向”(Intention)。狄尔泰认为意愿的冲动可以回溯到冲动的集合(das Bündel von Trieben)中。因此,认识主体就是凭其意愿的冲动驱动意向的个体,而对于这个意愿的抑制随即产生,并且伴随着与之无法分离的情绪体验。在这个机制之下,意愿的两种状态是不对称的依存关系。在狄尔泰看来,对于外部世界实在性的信念,恰好在于通过对意向的抑阻产生的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实在性关联。
其次,意愿的冲动和对意向的抑阻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必须通过感觉材料的中介。狄尔泰认为,“在冲动的意识和对意向的阻碍的意识之间的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存在于按压感觉那里,并且总是在那里。因此,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意识只是经过中介的。人们不应该通过任何夸张的方式试图轻松地解释对于外部世界的信念,诸如诉诸于意愿的直接的反阻经验,或者索性诉诸于对直接给予存在的心理学虚构”*W. Dilthey, GS Bd. V, S. 103. 加黑强调出自笔者。。这里,狄尔泰首先把反阻经验落实在了具体的按压感受(Druckempfindung)上,这与当时经验科学的进展是密不可分的。*狄尔泰积极参与了当时心理学的研究。在关于心理学和人类学讲座中,狄尔泰梳理了当时实验心理学的关于按压感受的研究。(Vgl. W. Dilthey, GS Bd. XXI, S. 211-215.)对于按压感受作为中间环节的强调,目的在于批评那种把外部世界存在当作是直接未经中介的被给予的观点。在狄尔泰看来,这种观点既无法在哲学上得到论证,也无法在经验科学的研究中获得支持。基于对按压感的哲学反思,狄尔泰把反阻经验理解为意识中的可被经验之物。人和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关联,就存在于感觉联结(Empfindungsaggregat)中。这种意识感觉联结就是意愿冲动和反阻体验的联结点。因此,狄尔泰把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直接的实在性信念还原到了意识中的间接的反阻体验上。
二、舍勒对狄尔泰的继承与批评
上文对狄尔泰关于实在性论证的勾勒,为我们提供了进入马克斯·舍勒的实在性理论的基本语境。舍勒早年受狄尔泰生命哲学影响颇深。具体到外部世界实在性的问题,我们更能清楚地发现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思想关联。在舍勒看来,狄尔泰本身置身在一个伟大的丰富的思想传统中,这个传统主张“实在是在反阻的体验当中给出自身的”*M. Scheler, Späte Schriften, Gesamte Werke, Bd. IX, Bouvier: Bonn 1995, S. 210. (以下凡引《马克斯·舍勒全集》,均仅给出该全集的简称“GW”、卷数和页码。)。狄尔泰的巨大贡献在于,他重新使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哲学讨论中复活,并且在生理心理学知识的进展中使之更为丰富。而舍勒晚期著作中对实在性问题的回答,正是建立在对狄尔泰思考的继承与批评之上。舍勒继承了狄尔泰开辟的这一问题的基本论域,以及从反阻体验出发寻找关于外部世界实在性根源的基本路径,但是批评狄尔泰对于反阻体验的哲学解读。正如汉斯-莱纳·赛普的概括,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在反阻体验中经验到的实在物,或者说实在本身,是经由意识而获得原初把握的,还是有其本己的体验路径?”*H. R. Sepp, Über die Grenze. Prolegomena zu einer Philosophie des Transkulturellen, Nordhausen: Traugott Bautz, 2014, S. 204.在舍勒看来,尽管狄尔泰正确地强调了本能型的行为在实在联结产生中的原初作用,但是他却同时把这种行为限制在本能意识(Triebbewusstsein)的范围之内。狄尔泰把实在经验归于意识,总是相对于意识来解释对象的实在性。在《唯心论与实在论》一文中,舍勒正是围绕这一基本点展开对狄尔泰理论的批评。
与狄尔泰一致,舍勒也把“实在”定位在冲动(Impuls)和反阻的关系中,然而舍勒并不接受狄尔泰把这一关系理解为经由“感觉材料”中介的关系,而是力图复活在狄尔泰那里被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的“直接性的反阻经验”。舍勒明确地表示:“这种被狄尔泰拒绝的‘直接的反阻经验’恰恰是持存着的。”*M. Scheler, GW Bd. IX, S. 212.舍勒通过对狄尔泰“按压感觉”(Druckempfindung)概念的批评来阐释直接性的反阻关系。狄尔泰把“按压感觉”看作是位于指尖的一个死的感受。在舍勒看来,如果按压感觉仅仅是在皮肤表面的一个死的感官体验,那么它实际上同狄尔泰想要通过这一按压感觉建立起来的反阻经验是矛盾的。如果我们把按压感觉理解成为和具体的感官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感官感觉,那么按压感中的反阻体验就不可能形成对出于本能系统(Triebsystem)的意向的阻碍。在舍勒看来,与其说反阻体验来自于作为感官感觉的按压感,毋宁说所谓的“按压感”是反阻经验的伴随现象(如果它不是一种错误的概念虚构的话),前者因后者而可能,两者应该严格地加以区分。这里,舍勒当然需要解释为什么反阻体验完全不同于按压感。
舍勒的这一论断依赖于当时最新的生理心理学对负重或者拖拽体验的研究结论。人们发现在负重或者拖拽的行为中,人的用力体验的强度和肌肉的紧张体验的强度并没有严格的相关性。显然,反阻体验关联的是人的力量投入的感受(Krafteinsatz des emfindenen), 而肌肉紧张程度则是感官感觉。舍勒认为,这一经验研究揭示的反阻体验和感官感觉的区别,足以证明狄尔泰把人的反阻体验等同于作为感官感受的按压感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M. Scheler, GW Bd. IX, S. 212.。舍勒批评道:“真正的反阻体验绝不是表面的感官经验,而是居于中心位置的我们的冲动(Drängen)与追求(Streben)的经验。”*Ibid., S. 210-212.因此,舍勒把反阻经验界定为体验中居于核心的一个特别纬度。反阻体验的这种中心性特征,也使得我们不能把它和周围的感官体验混同起来,无论这种感官体验是紧张感还是按压感。在这个意义上,力量投入实际上并不是由按压感所带来的。相反,感觉着的人作为力量投入着的源泉奠基着所有在各种感官中呈现的感觉(Empfindungen)。
上文呈现了舍勒就当时的生理心理学语境对狄尔泰的批评。下面需要从纯粹概念分析的角度再次去审视舍勒对狄尔泰的“按压体验”(Drucksempfindung)的批评。在狄尔泰看来,运动冲动(Bewegungsimpuls)是由意愿或者意志行为驱动的。仅仅有意愿带来的冲动当然不足以产生反阻体验,反阻体验还需要对意愿冲动的阻碍(Hemmung)。狄尔泰认为这个阻碍是我们一种有意识的经验,并且“按压体验的组件”必须作为阻碍意识的前件同时被给予,才能保证冲动和阻碍在体验中一体两面地同时出现。狄尔泰根据不同感官把感觉区分为各种感觉类型,例如皮肤上的触感、皮下组织的感觉、肌肉收缩的感觉、关节处的运动感觉等。狄尔泰把反阻感觉(Widerstandsempfindung)当作这些感觉的高一级概念来使用。反阻体验发生在整个冲动体验的系统中,因而与之相应的类按压体验(Druckhafte)也无差别地在各种感觉类型当中存有。*Vgl. W. Dilthey, GS Bd. V, S. 103-104.在狄尔泰看来,在内关节的部位存在的不仅仅是运动感受,还有按压的感受。
与狄尔泰不同,舍勒想要阐明的是“无中介的反阻体验”。尽管我们看到狄尔泰肯定了反阻体验作为所有感觉类型不可或缺的一个面向,但是在舍勒看来,狄尔泰的反思恰恰遮蔽了真正的无中介的反阻经验。舍勒认为,这种无中介的反阻关联的是力量投入(Kraftseinsatz)。如同负重或者拖拽的例子中所证明的,力量投入并不能定位在任何具体的感受组件中,因而对力量投入的反阻也不包括在四周的感受中。舍勒的核心命题是:在狄尔泰那里反阻经验并不是真正的反阻体验,反阻经验被理解为意识中的属于感觉组件的内容,而这并不是原初绽出的反阻体验。
舍勒观点的革命性在于翻转了反阻与意识的关系。舍勒认为绽出的反阻是意识产生的基础,正是在反阻中的返照(Reflex)使得意识成为可能,而不是相反。因此,想要真正抓住冲动与反阻这一对构成实在(Realsein)的关系,必须把研究从意识概念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相反,在狄尔泰那里,意识不仅作为我们思考实在问题的出发点,还是我们反思实在问题的边界。狄尔泰在《描述与分析的心理学概念》一文中写道:“意识无法反观自身的背后,思想处在[和意识]的关系中,思想从意识中来并且依赖意识,这个关系是我们永远无法丢弃的前提。”*W. Dilthey, GS Bd. V, S. 194.狄尔泰意图在意识中找到外部世界实在性的根据,因为哲学地反思实在性作为思想本身受到意识概念的限制,舍勒则笃定实在性问题的解决一定在意识之外,实在性早在意识的内在经验成形之前就已经起作用了。
舍勒看来,投入(Anstrengend) 、发力(Krafteinsetzend)是从本能的生命中心生发的。从生命中心出发的本能冲动当然不会在意识领域缺席。然而,在舍勒看来,狄尔泰把它错认为意愿(Wollen)。在狄尔泰那里,保证主体外部世界存在的反阻关联的是有意识的意愿。意愿、感觉与冲动构成了生命结构的三重奏。舍勒从根本上质疑狄尔泰的三重生命结构的合理性。舍勒认为这里狄尔泰又犯了一个错误:“狄尔泰把反阻称为意愿的经验,明显他想到的更多是有意识的意愿的中心,后者不是属于我们任意的自发的生命中心的本能冲动,而是来自意识中心的意愿。”*M. Scheler, GW Bd. IX, S. 214.从舍勒的观点看,实在性的要素是从对活跃自发的、完全非任意的生命冲动的反阻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对有意识的意愿的反阻中产生的。*M. Scheler, GW Bd. IX, S. 214.更进一步,狄尔泰认为,意愿关系到的是任意的运动冲动。对外部世界实在性的意识来自于对这种运动冲动的阻碍(Hemmung)。那种对非任意的运动关联到的是本能冲动,对后者的讨论出现在狄尔泰思考的边缘地带。而狄尔泰分析的中心点在于认知主体的实在性经验。在脚注的位置,狄尔泰提到,在生命的初始阶段,运动当然不是任意的。胚胎阶段的生命进行的是某种非任意的活动;在新生儿那里,我们也能看到出于饥渴的非任意的吮吸运动。我们可以说在生命初始阶段的非任意运动中起作用的是一些特殊的本能冲动,后者和有意识的意愿是不同的。遗憾的是,狄尔泰并没有进一步地对这两种本能冲动和意愿冲动做出进一步研究。恰好在这点,舍勒指出,三重生命结构中的冲动和意愿的区别在婴儿的吮吸运动中坍塌了。
舍勒的立场是,本能和意愿的关系应该被颠倒过来。在狄尔泰意义上的,意愿冲动作为驱动力是有问题的。如果说在成熟的意识主体那里,运动意向是从意愿冲动而来,那么毋宁说这种“意愿冲动早已和本能冲动融为一体了”*Ibid., S. 215.。在舍勒看来,精神的意愿来自于对本能冲动的阻碍或者去阻碍。意愿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精神活动的结果,他是通过对本能冲动的否定产生的。因此,作为一种高级的精神性活动,意愿不是永续性的,而是不常有的行为(Seltenheitsakt);与此相反,我们的实在性体验却是持续着的。因此,对于意愿的反阻在舍勒看来是无法理解的。反阻作为实在性体验之锚只能扎在本能冲动和外在世界的环节中。我们最基本的实在信念的根基不在于个人意愿的层面,而在于更深的人的非任意的本能生命的层面。
从整体上说,舍勒认为狄尔泰把实在性问题单面地理解为“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也是不合适的。在舍勒看来,外部世界不能被理解为实在物的总体。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在外部世界中呈现出来的对象都是实在的,外部世界同样包括有许多非实在对象,如彩虹、影子、镜像等。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考虑内在世界的心灵对象问题,不能认为意识中发生过的内容和心灵的存在没有实在性。舍勒关心的“实在”(Realsein)不仅是外在对象的实在性,同时也包含我们心灵世界的实在性。在舍勒看来,“实在”不只关涉到外部环境的实在,而是关于所有可能的存在领域的实在,实在是我们全部经验的根本性纬度。*Ibid., S. 215.因而,舍勒认为,狄尔泰并没有把实在性问题的核心意义揭示出来,具体地说,狄尔泰错失的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整体性的“实在性”。
换句话说,舍勒关心的是实在性的“实在”,而狄尔泰追问的毋宁说是主体的“实-有”(Realität-Haben)问题。在舍勒看来,实有属于一个特别的场域(Sphäre),即在意识中被给予的外部世界;而“实在”无差别地在所有场域以及可能的场域中在,即“实在一般”(Realität überhaupt)。*“场域”概念的分析和整理,参见M. Frings, Life time: Max Scheler’s Philosophy of Time, Springer: Dordrecht/London, 2011, p. 80.后者作为舍勒的根本关注点,显然与狄尔泰通过反阻经验来解释的“实-有”不同。“实在”毋宁说是前意识的直接的生命冲动与世界关联。反阻在舍勒看来是整体性(Totalität)的反阻,是世界的反阻(Weltwiderstand)。*M. Scheler, GW Bd. V, S. 217-18.
三、小结及进一步思考
基于上面对狄尔泰与舍勒关于实在性争论的观察,我们目前可以得到两个阶段性的结论。第一,就实在性问题而言,狄尔泰和舍勒的分歧在于,作为实在性来源的反阻体验如何被理解,它究竟源自处于中心的生命冲动,还是源自经由感觉过程中介的意愿生命。第二,狄尔泰和舍勒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强调实在性来源于人的生命进程,并且都从“冲动”和“反阻”这对概念出发来解释人的实在性信念。无论狄尔泰对外部世界实在性的研究,还是舍勒对实在性一般的强调,其共同立场都是拒绝把实在理解为(康德式的)纯粹理智的设定活动(Setzungstätigkeit)。二者的共同立场可以成为我们反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于实在性问题理解的重要的参照。对狄尔泰和舍勒关于实在性争论的再考察,旨在重新把作为实在性的反阻重新带入到现象学语境中。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我们看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把经验的这一纬度排除在现象学的考察之外。
抛开胡塞尔不谈,舍勒这里提出的“实在”概念,可以被看作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之外定义人的“实际性”(Faktizität)的独立尝试。如果可以被理解为基础存在论,舍勒的实在性理论将是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强劲对手。海德格尔显然没有理解舍勒“作为实在的反阻”对于意识和生命的成在(Werden)的核心意义。海德格尔在1925年的讲课稿《时间概念史导论》中处理了狄尔泰-舍勒对于反阻经验的讨论,然而并不充分。海德格尔并不否认反阻现象本身的经验的一部分,但是认为反阻现象显然不是最原初的生命结构的实际性。他认为,恰恰是在“烦”和“意蕴”中展开的世界的世界性使得反阻成为可能;而舍勒那里的反阻或者说意愿行为,关联的是一种在手物。*M.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Sommersemester 1925), GA 20,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4, S. 302-303.显然在海德格尔的思路里,在手的(Vorhandensein)之所以能够作为在手的凸显出来,是在更原初的上手(Zuhandensein)的在场的基础上,或者说在“烦与意蕴”敞开的世界性中。因此,反阻充其量是个“现象特征(phänomenaler Charakter), 这一特征是以世界为前提的”*Ibid., S. 304.。实在物以及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应当还原到此在在世存在的世界性。后来,在《存在与时间》第§43节海德格尔几乎重复了他在《时间概念史导论》的观点。
就海德格尔的观点,有三点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上手的概念与在手概念的区分,以及海德格尔由此试图建立起来的实践对于理论的优先性,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理论争议。*例如,蒲浩思认为,海德格尔的“上手”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此在的“巡视着的操心”(die umsichtige Besorge)实质上是一种带有实践性质的意向活动,巡视(Umsicht)本身包含着最小的无可逃脱的认识性要素(尽管还不是判断式的认识活动),因此,“上手”概念表达的纯粹的实践性是不可能的。(参见 G. Prauss, Erkennen und Handeln in Heideggers “Sein und Zeit”, Karl Alber: Freiburg/München 1977, S. 27-41.)在本文的论域中,如果上手本身就包含着无可消除的认识要素,那么“上手”又如何能够支持由此而来的对反阻概念拒斥。第二,即便海德格尔是对的,人类此在与世界的关系就其最原初处确实是上手的关系,即一种原初的目的导向的“实践”活动,那么在舍勒的视角下,上手关系也必然地包含着“冲动和反阻”这一最基本层次。舍勒也完全可以同意,我们在工具性的“实践”活动中,“上手”先于由于目的未实现产生(意向未获得充实)的“对象化”活动,先于由此而产生的带有反思性特征的对象意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上手”可以先于反阻。第三,最令人吃惊的是,在海德格尔的眼里,舍勒和狄尔泰的观点并无不同,舍勒用来解释实在性的“反阻”经验是和对象性活动和判断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显然,海德格尔对于我们上文展示的舍勒与狄尔泰的根本分歧缺乏了解。因而,他对狄尔泰和舍勒观点的捆绑式处理很难站得住脚。本文已经充分地展示了,舍勒的“实在”概念试图揭示的是意识中的前意识的世界关联。在实在的基础上,意识才通过反身的关系产生,意识毋宁说是“由世界的反阻的受难的结果”(Das Erleiden des Widerstandes der Welt)*M. Scheler, GW Bd. IX, S. 43. 对这一点的详细阐述,参见M. Frings, Life time: Max Scheler’s Philosophy of Time, Springer: Dordrecht/London 2011, p. 82.。因此,“冲动-反阻”是先于对象性关系(主体-客体关系)的,因而绝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在手”的关系。海德格尔批评舍勒把反阻经验作为原始生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其完全错误的“生物学倾向”(biologische Orientierung)*M.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Sommersemester 1925), GA 20,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4, S. 305.。恐怕这也包含着他对舍勒哲学的深刻误解。舍勒对实在的思考显然是借助生物学研究成果的哲学思考,但不是仰生物学鼻息的。“实在”与“反阻”的关系是生物学无法定义的。正是通过辩护这些生物学无法理解的生命经验,舍勒为一种基于“实在”概念的基础存在论赢得了可能。舍勒对于人类此在“实际性”的界定恢复了费希特对于“实在即反阻”的观点,其讨论的实在高于具体科学对于实在的局部讨论,并且为后者提供了存在论基础;同时这种讨论本身又处于和具体科学(感官生理学)的关联中,无法脱离后者被理解。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