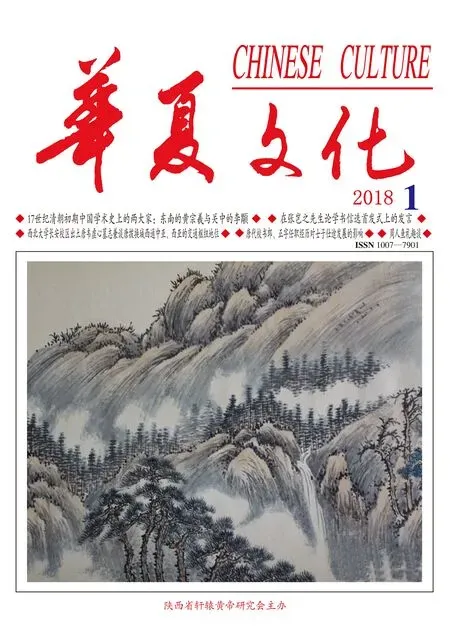跨界结构主义诗学批判
——从《诗经》的戏剧化形式说起
2018-01-23张惠泉
□张惠泉
语言是诗歌的主体,抒情语言即作者诗性人格在作品中的表现,即抒情主人公自我形象塑造的主要媒介。《诗经》作为先秦文化的代表,其诗歌语言具有的叙事性和口语化色彩,使其部分篇目在某种方面有了一定戏剧文学的语言色彩,即在表达一定文化意义与审美意义的同时,具有了现场直观性和艺术表现性。
尽管《诗经》的审美特色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存在上都是诗歌,仍然有其他文学体裁的影子若隐若现,其中之一便是戏剧的特点。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诗经》的部分诗篇借助人物形象的自我表现(主要是对白、旁白与独白)实现艺术观感,从而促成了读者超时代的接受。
一、戏剧形象与诗性人格的互补——诗歌的拟戏剧场景
我们这里所讲的《诗经》指的是其中有现实主义形象化塑造的抒情诗篇目,包括《国风》的大部分和《小雅》中的一部分。作为本文讨论对象的诗歌,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诗歌中有明确的、具象的形象塑造(例如《周南·桃夭》不能计入,因为没有人的形象真正出现)。
(2)必须是有一定外在或内在矛盾冲突的诗篇,而不能是单纯的概念化抒情诗(《大雅》中大部分作品都是这种情况)。
(3)抒情主人公必须在矛盾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不能是代言叙述或者转述形式,更不能符号化(如《陈风·株林》借叙述者之口来表达情感,不能计入)。
满足了矛盾冲突、形象塑造与人的主体三个要素,就满足了戏剧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划分上的基本要求,也就可以证明《诗经》的这些篇目即带有天然的戏剧性。戏剧依赖于感性联系发生,依赖于表演者与观众的情感交流,这一方面,从中国古典诗歌的道统而言也是合理的。
“任何艺术都是艺术创造者的一种‘言说’,从言说的方式上来看,戏剧是史诗的客观叙事性和抒情诗的主观抒情性二者的统一。” (董建、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页)黑格尔就从发生学的角度上肯定了诗歌和戏剧在表现上的相同性,并且认为“戏剧是诗歌较高级的表达方式”,肯定了诗歌中含有戏剧成分的合法性。
但是,过分拔高《诗经》中戏剧性的成分,喧宾夺主,乃至于声称《诗经》有剧本的性质是不妥的。《诗经》不是剧本,也远远没有在形式上达到诗剧的高度,它本质上仍是抒情诗,只能从索隐的角度掏挖其戏剧性的吉光片羽。因而,我们认为,即使是满足上述条件的诗歌,也只有戏剧场景与戏剧精神,并不具备成为戏剧的可能性——我们姑且叫它诗歌化的“拟戏剧场景”。
文学在产生早期文体不清的现象,即抒情诗歌的形象表现和叙事不能很好分离的现象,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然而,这些“残损的剧本”依旧有其美学价值值得探究,这就够了。《诗经》中的诗歌语言以何种方式表现自身的戏剧性,从而建立这种情感交流模式,就是我们接下来必须关注的话题。单纯的理论推导只能证明戏剧与诗歌审美互通的可能性,而文本分析将是解释这一问题行之有效的手段。
二、《诗经》中戏剧化的语言模式
语言是文学的直接构成因素,由于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必然具有的节奏性和抒情性,诗歌语言的形式美在接受心境上的显像,相对于象征美总是第一性的。“人们把抒情诗抄在本子上,是因为其调和优雅的音律和华美秀丽的章句使人着迷,而绝不是因为更深层次的东西(尼古莱·特鲁别茨科伊:《文学论著》,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而戏剧则依赖于语言表现张力和矛盾中的人物塑造,因而,作为“演员”的诗歌抒情主体的语言(借助于对话、旁白、独白等直观形式表现)就成了《诗经》戏剧美学的主要来源。
戏剧的语言主要分三个部分:剧作家的“提示语言”、主体表达的语言和“潜在语言”。多数情况下,《诗经》的语言主要是主体表达的语言,即对话、旁白与独白。
1. 对话结构
《诗经》中的对话多发生在男女恋人之间,大多数有着“女曰某”“士曰某”的结构性语言提示(但也有例外,如《魏风·园有桃》《周南·卷耳》,便是没有明确提示符号的对话体表现)。《诗经》对话体诗歌的主要语言风格是清丽明快的,这既是这些诗歌的共有特点,也是这种对话结构形式的必然倾向。
在现代戏剧理论中,在剧本文学阅读中,“读者主要是通过台词认识形象的”(董建、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因而在具有戏剧性的这部分诗篇中,对话体往往是形象塑造最完整,也是最具戏剧内容观感的。试举《郑风·女曰鸡鸣》《周南·卷耳》为例: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郑风·女曰鸡鸣》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周南·卷耳》
《郑风·女曰鸡鸣》是一个相当典型而且明显的对话体诗歌,前两句分别用“女曰”、“士曰”开头,随后每八个字为一层,成典型的问答式,具有良好的再现性,几乎是文本情感与形象内容的具体化复现。语言表现上,这种夫妇问答的形式,有与戏剧舞台语言相适应的口语化特点,从而使艺术场景高度真实,使其沾染了生活化色彩。惟妙惟肖,妙趣横生,真情实景,如临其境。对话性诗歌普遍表现出对现实的高度复写与强烈关照,牺牲了一定的艺术张力,从而形成了文学性较弱而舞台性强的艺术特色。
直接对话体作品着眼的主题大多是爱情、婚姻等较为轻松简单的个人情感和生活世界。除本例之外,《诗经》中这样的诗篇还有一些。如《郑风·溱洧》直接用白描式语言表现了男女恋爱的甜蜜场景;《魏风·陟岵》通过虚写游子与家人的对话,表达了思念故土亲人的桑梓之情;《齐风·鸡鸣》则完整的再现了妇女唤夫早起的场景。单个场景之中对白的白描式展现——这种戏剧性的表现手法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比较典型化。在审美欣赏中实现代入与共鸣也就比较容易。
《周南·卷耳》事实上是对话体诗歌的一个变体,即取消标志性的对白提示,打破舞台空间二维化和时间线性的限制,从而实现“无所不在”的超验性审美观感。以牺牲部分舞台表现力为代价,以“虚笔”实现更加精妙绝伦的结构美。全诗首章以女子口吻为女子怀夫之笔,后三章以征夫口吻写男子怀妻之状(此处尚有争议,一说后三章所写仍是女子,这里从二分的主流观点,见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两地同情,共入一诗,初看如入七宝楼台,再看则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之意。然而,由于若隐若现的存在于通篇结构的对话体与独白的交错,作品在解决时空隔离问题的同时获得了新的召唤结构。男女主人公超越时空的对话结构本身,恍如隔空呼唤,两地同心,具有着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这是《卷耳》特有的结构美学,国风之中,仅此一篇。
易非再问妈,妈就答不上来,其实妈心里是有答案的,只是她不知道怎么说出口,她的答案就是:除了李倩倩这种缺心眼的女孩,还有谁看得上向南呢?这种缺心眼的女孩提的要求,你还不赶紧一口答应下来,好让他们把婚结了,不然,错过了,向南再去哪儿找个老婆呢?
总体来说,相比于其他结构,对话结构的复刻性与再现性强,更能调动读者的感性审美。其作品主体简单,结构简洁(简单的重章叠句),注重形象刻画,文本明显趋向封闭性——这也是这些作品多用对话体的原因。
2.独白结构
“独白,是由单个戏剧人物讲出的,有较强抒情性的语言”(董建、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在《诗经》中则表现为抒情诗主人公以语言方式表达出情感的外在形式,诗性人格在这里,作为唯一或主要的表现主体向接受者施以直接的浪漫化艺术关注。与严格意义上的戏剧不同的是,《诗经》的“拟戏剧场景”可以把独白而非对话作为舞台表现的主体,唯一的原因就是《诗经》的篇幅较短,它所展现的仅仅是一个片段,而非完整的故事。
独白形式的抒情作品占据了《诗经》中戏剧性作品的主流,这一形式也是《诗经》戏剧场景中主要的抒情表达方式。笔者认为,基于独白的语言特点、抒情方式的不同、写作风格的差异等,可以进一步分为“呼告式独白”与“陈述式独白”两种。
(1)呼告
呼告,即抒情主人公强烈情感的爆发式倾泻。在很多诗歌中,由于矛盾冲突的激烈和创作者内心情感的强烈,作品的抒情自然就变成了呼告。在这里,抒情就是全部,感性压倒一切,它带给人的是狂飙突进的情感体验和形象化的艺术观感。
《诗经》的这部分诗歌往往句式不整,言语粗放,情感没有节度,故多被旧儒学刺为“淫奔之诗”。“呼告体”作品多分布于《国风》中,尤其集中分布于“郑”、“卫”二风中,这与“郑卫风淫”的主题色彩也是分不开的。试举几例:
《召南·行露》:“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女子以质问的口气指责强迫她的无良男子,疾言厉色,掷地有声。《邶风·简兮》:“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直接抒发了女子对舞者的倾心与爱慕。《郑风·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则抒发了女子强烈的悔恨之心……《诗经》这类诗词数量较多,胜在情真。
有必要说明的是,《诗经》中戏剧化的“呼告式旁白”与修辞上的“呼告”是有区别的。诗经中抒情主体的呼告是在场景维度中实现的,它首先要依托一个具体可感的场景,从而使情感的抒发为形象表现服务。故而,单纯、朴素的情感爆发,或者情感与叙事内容脱节(起兴)的并不能算作呼告式戏剧。如《唐风·有杕之杜》: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适我?中心好之,曷饮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来游?中心好之,曷饮食之!
此诗情感强烈,却不能产生戏剧化的美感。首句系起兴,与故事的发生场景无关,而余下的部分纯粹是呼告,没有必要的描写和叙事铺垫,基本上是一往无节的呼号,故而并不具备戏剧观感,只是一个女子思而不得的痛苦呐喊的真实写照。
(2)陈述
以诗性人格外化的抒情诗主人公为叙述主体的直言叙事,往往就带动出陈述式的独白。基本上这种陈述结构上遵循一个比较严谨的线性或者循环结构,冲突并不激烈。呈现出徐徐展开,娓娓道来的风格。此类诗例较多(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小雅74篇中),故不单独做文本分析。
从戏剧本身的理论来看,陈述性的独白艺术性上绝难与呼告式的抒情力度相比拟,而是更多地偏向叙事性的完整。独白的现实关照下,理性便自然地成为了诗性人格主流。在这种独白中,作家的诗性人格“在感性现实的表现中无需更多的支持,因为他在他自己内部就是一个整体”(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选自《席勒美学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
结论
戏剧化的诗歌体系中,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也是诗歌之所以有了戏剧性的核心所在。
戏剧化的《诗经》关照,本质上是以西方文论为蓝本的《诗经》再解读,这种解读根本上隶属于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如果要肯定《诗经》文本在诗歌的结构之外还有延展的空间,那么结构批判无疑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