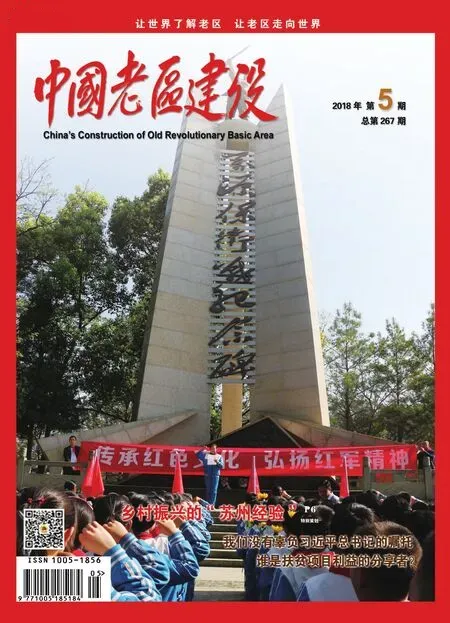谁是扶贫项目利益的分享者?
2018-01-23□何毅
□ 何 毅
笔者在鄂东南大别山南麓一个集老区、山区、库区于一体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调研时,发现在扶贫项目和资源的分配获取过程中,乡村“能人”凭借人际关系,率先得知信息获得扶贫项目,同时通过与权力形成利益共谋关系,共享了扶贫项目的分配收益。
找项目:信息意味着权力
火哥(村里人对其的称呼)是笔者调研的村里有名的致富能人。早年在北京经营装潢和建材生意,县驻京办撤销前一直负责县里干部在北京的接待,因此在当地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他在村里的声望和权威比村主任还高,是农民眼中“能通天的人”。因为待人温厚,不摆架子,村里人对他评价很高。
2017年年底,火哥从县国土局长那里得知,村里100多亩的山林因为承包人资金周转不开想转手。这位局长给他指点迷津,劝他承包下来。“他说山林承包50年,现在大概前后需要十几万元,还说我们村今年可以分到茶树补贴15万元,另外其他的堰塘整治和道路硬化等,都可以走项目(通过项目资金。编者注)。”火哥对笔者说。
火哥心里也算了一笔账,不算承包费用,其他的基础设施如果有项目资金可以做到不亏不赚,路和水电修好后转手也不止这个价钱。而一旦申请到茶树种植补贴,他可以以此为契机尝试茶油生意,反正最后也出不了多少钱。因此他接受了局长的建议
火哥告诉笔者,能够顺利拿到项目,县和乡镇领导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不过现在不同了,必须在圈圈里转,不能越线。一般项目和规定下来后,第一时间他们就会想出招,怎么样可以打擦边球。比如新修堰塘,每亩补贴1万元,水利局验收完才给钱。实际上那个地方满打满算才两亩,不用补那么多。我是把堰的侧边一部分也算了进去。”
火哥新修堰塘主要是为了私人养鱼,并不是为了村庄的水利灌溉。但是在出示的审批手续里,他是以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名义进行申请。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合作社更容易通过审批,特别是可以用带动贫困户的理由,这在拿项目过程中体现更为明显。
拿项目:关系才是关键
年初,一件村民眼中的“好事”让火哥出尽了风头,为他积累了民心,也为他谋划的茶树种植项目奠定了基础。
通往村里的水泥路因为地势低,一下大雨河水就会淹没道路,车和行人无法正常通过。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是迟迟得不到解决。如果从工程实施角度来说并不难,只需要修建一座小型的混凝土桥梁即可。一直未修桥的原因在于拿不到项目,没有上面的项目经费根本无法建设。
架桥通路项目属于基础设施建设,归县交通局主管。火哥和县交通局长曾是牌桌上的牌友,两个人关系不错,加上局长侄儿在北京发展时曾受过他的照顾,所以村主任和驻村工作队就出面请他去运作。
具体怎么操作的,火哥一直闭口不谈。笔者从村民那里得知,批下来后实施工程的“头头”好像是某一位领导家的亲戚。对于这种现象,村民见怪不怪,一村民反而说起火哥的好话:“他能得很,帮老百姓办了一件善事。这么多年一直说架桥都没有动静,他一出手就解决了。村干部还是不中,整天就知道打牌。要我说就应该他来当村干部”。
在村庄内部,农民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都专注于过好自己的生活,对公共事务缺少必要的关心,更不愿意出钱出力。现在,往往只能通过国家资源下乡和转移支付来解决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那些能拉来项目解决公共事务的人便成了村民眼中的“有面子有能力的人”。因此,村庄公共舆论对一些人“拿国家的钱办自己的事”就具有一定的容忍度和接受度。
谈及架桥事宜时,“火哥”脸上并没有骄傲和欣喜。他告诉笔者其实这就是相互利用,如果他不这么做,他自己的事情就办不了。
尽管产业扶贫一直是县和镇里工作的重点,但是因为周期长、见效慢和风险大,在基层干部这里不能形成有效的政治资本。即使基层干部付出巨大努力,一旦产业项目效果不明显甚至失败,很多干部的前途就会受到影响。而架桥这种事情也是群众关心的事,办好了基层干部也积累了民心。因此基层干部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周期短、见效快、政绩直观的基础设施项目。
当然,村庄的现实也决定了基层干部也不是完全出自私心。“火哥”对此也深有感受:“你说天天喊产业扶贫,路都没完全通,怎么扶贫?还有就是手机信号也不好,这些基础设施还没完全建好,你产业扶贫扶得起来?”
基础设施项目是基层干部眼中的“香饽饽”,“火哥”对此了然于胸。因此他便以山林的茶树种植项目和山林道路建设为交换条件,帮忙运作了架桥通路的项目。村两委干部也答应等年后相关款项下来后,优先考虑他承包的山林。在村里“一事一议”会议上群众代表也一致通过了该决定。
审项目:材料过关就行
产业扶贫项目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是私人先行垫资,然后主管部门进行验收,验收合格才能拿到补贴。从制度设计上,上级部门对监督项目的实施具有主动权。但是在现实操作层面,则出现了双重悖论。
一方面,扶贫项目瞄准的目标群体是乡村贫困人群,但是该群体在自身生存发展都需要国家补助的情况下,无力承担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牲畜的饲养。因此基层干部往往倾向于以“大农带动小农”的合作社模式推进产业扶贫。但是产业项目主要由县级政府根据项目属性委托业务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或监督,因此另一方面在验收检查上也会出现“自己人审自己项目”的窘境,对项目实施过程中不规范的“擦边球”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谈及项目审核验收时,“火哥”显得非常轻松:“这么多项目,哪个天天检查去?只要有施工图片、材料齐全就行。晓得你正儿八经在做就能过关。当时建堰塘时,挖掘机一开进去,我就开始拍照片。按说应该全部建完才能拿钱,水利局局长跟我是朋友,看都没看直接签字,我就拿到钱了。”
“火哥”之所以不担心,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他眼中,他自己承包的山林已经组建了茶树种植合作社,新修堰塘的工程确实正在实施,他并非通过拿补贴来赚钱。第二,在运作项目过程中,他给主管单位送了礼。至于怎么应对上面的抽检验收,该准备的材料他事先在镇长的提醒下也都准备周全了。
最后结束访谈时,笔者提及中央大力反腐的制度环境,特别是“老虎苍蝇一起拍”的时候,“火哥”也感叹:“其实现在项目运作蛮难的,因为大家怕出事,除非领导了解你这个人是正经做事才敢帮你。上面各种检查验收,一个环节出问题都麻烦。我这样做也是没办法,你想想这个地方这么偏,还在山区,基础设施如果都是自己搞,那不得亏死?所以上面审的时候只要是你踏实做事,有些环节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评论
湖北省提出2019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2017年年底,省里改革了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在原有资金、项目、管理、责任“四到县”基础上,增加了“招投标”这一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审批权实行“五到县”规定。在“五到县”特别是“扶贫资金大整合”的背景下,贫困县客观上确实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但是,扶贫项目本身也容易因为地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发生变通和异化。本文通过乡村一位“能人”的经历,可以清晰地看到扶贫不同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当以贫困群众为初衷设计的扶贫项目,被“能人”率先知晓时,他们往往会针对项目本身作出变通。如何防范此类失范偏差行为的发生,是各级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何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