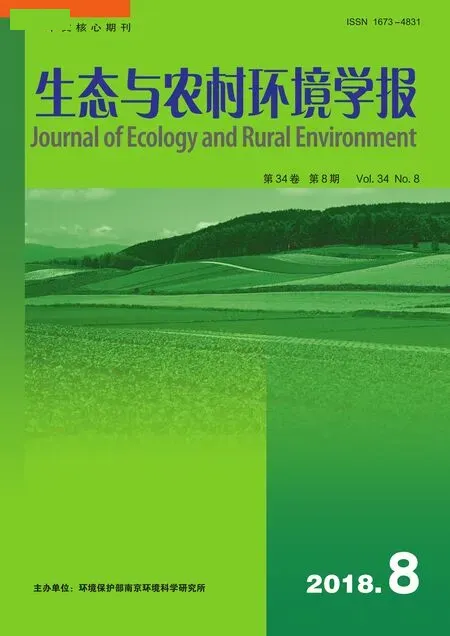生态保护红线区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监管
2018-01-22李海东高媛赟燕守广
李海东, 高媛赟, 燕守广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42)
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重、生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是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有效手段[1]。矿山生态环境损害被认为是影响区域生态安全的第一大诱因。长期以来,矿产资源开发有力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但也产生了严重的矿山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受到威胁[2-4]。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的经济重心和发展活力所在,矿产资源丰富[5]。2017年7月,原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水利部联合印发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开展生态退化区修复”。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生态保护红线不仅是一条空间界线,也是实施严格源头保护的制度设计[6]。目前,政府和学界从概念、类型、管控措施等方面开展了很多有益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成果[5,7-9]。然而,如何以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的要求,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特别是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有效监管,是我国生态环境重大问题决策支持亟待解决的问题[10-11]。污染治理、植被恢复/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是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有效途径。为此,笔者针对当前长江流域整体性保护不足、生态系统破碎化、生态服务功能仍呈退化趋势等问题,在调查与评估矿山生态环境问题、恢复治理监管现状及制约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江苏、安徽、江西、湖北、重庆、四川等省(市)矿山生态环境损害与修复监管的专题调研与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探析了废弃矿山生态环境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典型生态保护红线区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对策。
1 长江经济带矿山生态环境损害现状
1.1 仍有大量废弃矿山分布
长江经济带地跨热带、亚热带和暖温带,地貌类型复杂,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山水林田湖草浑然一体,森林覆盖率达41.3%,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目前,长江经济带共有矿山901座,其中大型矿山120座,中型矿山195座,小型矿山586座。从矿种来看,排名前5位的为磷矿(137座)、铁矿(120座)、≥1 000万t煤矿(111座)、萤石(100座)、铜矿(85座)。
长江经济带共涉及7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14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根据“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2000—2010年)遥感调查评估项目”数据,长江经济带11省(市)共有矿产开发点约1.9万个,矿区面积约1 775 km2;其中,3个水土保持重点生态功能区(大别山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分布有634个矿产开发点;4个生物多样性维护重点生态功能区(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分布有1 749个矿产开发点。长江经济带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矿产开发点主要集中在中上游的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和江西。
1.2 矿山生态环境损害问题突出
长江经济带矿山生态环境损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关键生态空间保护形成新的挑战。大量历史遗留矿山不仅造成大面积的土地损毁,而且矿业活动产生的“点-线-面”开发利用格局会造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和迁徙廊道被破坏,影响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其次,危及流域生态安全。矿山生态破坏包括森林资源、草地资源、耕地资源、水资源、次生地质灾害等造成的实物破坏和生态功能损失[1, 12]。有报道显示,贵州省六盘水市由于采煤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减弱了水土流失抑制效应,造成南部煤矿区土壤侵蚀较严重,尤以分布零散、生态环保措施不力的私营煤矿区为甚[13]。长江经济带上游区生态环境本底脆弱,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如果长期大面积的区域性水土流失得不到及时控制,势必导致流域内河床升高、河道淤积。第三,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矿山环境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固废和土壤污染等造成的实物量破坏和人体健康损失[1, 12]。煤炭、有色金属、磷矿等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其中磷矿采选与磷化工产业快速发展已导致总磷成为长江首要超标污染因子。采选活动产生的大量酸性、碱性、毒性或重金属成分会通过下渗、地表水径流、地下水迁移、大气飘尘和雨水冲刷等方式向下游扩散,影响范围远远超过生产作业的地域和空间。针对湘西花垣县家庭灰尘的研究表明,来源于周边铅锌矿采选、冶炼及道路车辆等的灰尘中重金属的综合潜在生态危害均达到很强水平,2014年以来造成部分村寨的儿童血铅超标。
2 矿山生态修复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矿山生态修复与保护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
从类型来讲,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包括景观型破坏(对地表覆盖的影响)、环境质量型破坏(对水体、大气和土壤的影响)和生物型破坏(对生物群落的严重破坏甚至摧毁)[12]。原国土资源部、原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的职能范围均涉及矿山生态修复与保护,各部门均制定了相关的环境保护技术政策,为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然而,现有的技术政策主要围绕矿业活动导致的地质环境治理、次生灾害防治、植被恢复/土地复垦等,大都停留在“以视觉治理为主,污染物防控则属于事后补救型”的景观型修复阶段,没能实现从末端治理向过程和源头延伸的污染物防控的全生态环境要素修复,尤其在水体、大气和土壤环境修复方面的针对性不强。矿山生态修复应包括环境质量型修复和生物型修复,然而,由于基础理论缺乏、生态修复目标不明确、部门条块切割等方面的管理支撑不足,加之目前的矿山生态修复存在理念、技术和工艺相对落后,现有技术政策和标准规范之间不一致等问题,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存在“被动应对多,主动作为少”的现象,生态功能修复效果大打折扣,无法有效彻底根除矿山生态环境损害问题。
2.2 共抓矿山生态修复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
恢复生态系统功能,不是简单的植被恢复/土地复垦,而要强调已经破坏或者退化生态系统功能的整体提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陆续建立了以生态保护和修复为主导的一系列体制机制,但具体到生态保护红线区修复有些“先天不足”,特别是缺少齐抓共管矿山生态修复的体制机制。多年来,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在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方面的主体责任和主要事权不清晰,始终难以突破“各自为战、以邻为壑”的割裂现象。为减少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造成的矿山地质环境破坏,2009年原国土资源部颁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建立了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然而该保证金仅限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目标要求不高,没有考虑区域生态功能修复。2013年原环境保护部印发HJ 651—2013《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技术规范》),是全面开展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指导性技术要求,然而《技术规范》并没有强制实行,全国仅有山西实施较好。矿山生态修复目标的科学制定,不仅强调自然生态系统修复,还要考虑与区域经济社会系统的匹配问题。从统筹协调层面看,面临的最大问题和难点就是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部门和地方“各扫门前雪”现象依然严重,现有的流域管理机构由于历史定位和部门属性等原因,难以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的“共抓”关键点真正发上力。
2.3 矿山生态修复和经济发展间的矛盾尖锐
201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要求“在2017年底前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要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可以有效禁止在重要生态空间进行矿山开采问题,但无法解决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后,中央和地方强化了思想层面长江经济带的“共保”意识,各级决策部门和社会各界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有了较高的认同和共识。然而,在国家整体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大形势下,“只开发、不保护,重发展、轻保护”的传统惯性依然很大,由于经济较落后,建设和发展资金紧张,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和创造财政收入的心态,“重资源开发、轻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矛盾依旧尖锐。在具体实践和实际操作层面,不明确的矿山生态修复目标、不健全的管理体制和不利的自然条件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生态功能修复。调研表明,有些地方政府在矿产开发招商引资上,仍存在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甚至违反政策和原则,层层开“绿灯”,造成重要生态空间曾发生“无证开采、争抢资源”的现象;在矿山生态修复目标制定方面,大都是强调复绿,基本没有考虑生态系统结构(垂直结构、水平结构和物种多样性)、过程和主导生态功能(水土保持功能、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的有效修复。
3 矿山生态修复监管对策
3.1 建立涵盖生态环境全要素的矿山生态修复评估监管机制
一是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的底线思维,从源头设计,把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摆在突出位置,在思想认识上统一“一条心”,在组织协调上形成“一盘棋”,在实际行动中拧成“一股绳”,以生态环境保护统领生产力要素配置和沿江经济活动。二是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基础,从生态环境全要素的角度,改革现有的管理体制,理顺部门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明确牵头部门和责任边界,统筹建立水、气、土壤、地质、生态等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行动机制,落实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责任。三是在生态环保督察中有针对性地纳入矿山生态修复成效评估专项内容,重点就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植被恢复/土地复垦、水土保持、重金属治理等进行核查,坚决抑制和消除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履行生态环保责任中长期普遍存在的各种“不规范”行为,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环境短板。
3.2 制定生态保护红线区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专项规划
一是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克服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植被恢复/土地复垦、污染防治等传统单一要素的治理模式,制定矿山生态修复目标管理技术体系,明确不同主导生态功能的矿山生态修复目标,做到区域生态功能的整体性修复。二是根据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和原环境保护部印发的《技术规范》等标准文件,基于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水源涵养等主导生态功能,在贵州、江西等省选择典型地区开展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专项调查与评估,研究提出重点生态功能区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模式。三是与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联合,全面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区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严格落实最严格的“谁破坏、谁恢复”制度,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稳定提升与区域经济社会系统的双耦合修复。
3.3 开展矿山生态环境损害评估与功能修复技术研发
一是加强矿山生态修复的基础理论研究,根据主导生态功能,开展区域生态退化诊断与评估,识别矿山生态环境对区域生态功能退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建立基于区域经济社会系统调控与局地生态功能修复技术相结合、有利于区域生态功能提升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矿山生态修复目标管理模式。二是制定矿山生态修复分区方案,实现从总体设计至治理技术的过渡。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区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和恢复治理现状调查结果,评估不同类型矿山生态修复目标制定情况,以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原则,统筹设计好长江经济带“上游修复、中游优化、下游保护”的分区施策和空间管控,构建上中下游协同发展的系统生态安全格局。三是开展矿山生态环境损害与功能修复等方面的技术研发,提升科技支撑水平,重点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区矿山生态环境问题调查、主要生态功能诊断、生物多样性重建、生态廊道构建、区域生态功能提升等关键技术,实现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植被恢复/土地复垦—生物多样性重建—区域生态功能修复的过渡。
3.4 研究制定矿山生态修复国家标准
在《技术规范》的基础上,重点强调矿山生态修复标准的制定,区分金属矿山和非金属矿山,按矿种类型(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重金属、稀土金属、石灰石、萤石、石棉、高岭土等),结合开采方式的差异性,参考《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包括陆生维管植物等11项),以及GB 1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修订为GB 15618—2018《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的形式,进行标准系列化,增强可操作性,制定并发布矿山生态修复国家标准,包括能反映矿种类型差异性,涵盖不同开采方式、不同自然条件下的生态修复目标确定的一系列矿山生态修复标准。同时,在制定并发布矿山生态修复系列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成效评估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