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个体 论王国锋的摄影作品
2018-01-21千叶成夫
千叶成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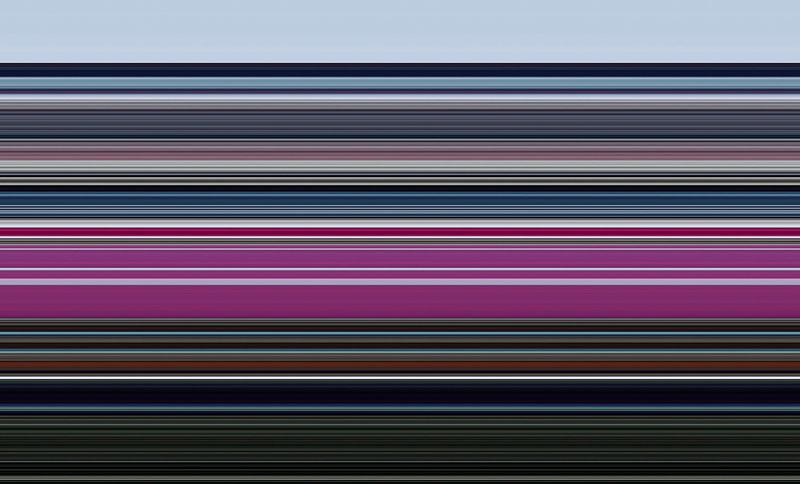


2010年
1 引言(框架)
纵观王国锋整个的艺术实践过程,他的作品除了参加在美术馆或画廊举办的一般意义的展览之外,王国锋也进行了很多其他形態的艺术尝试。比如:他和德国、瑞士或中国的一些戏剧合作创作的一些“舞台装置”作品。其中包括《9,600,OOOcm?》 (2009年),在舞台中央用玫瑰花瓣搭建边长8米,厚15厘米的正方形花床,演员在“床”上或跳舞或躺卧,或把玫瑰花瓣撒到身上。另一个作品名为《无题》(2009年),他将42件日常物品用医用白色纱布包裹起来,然后让演员移动或自由组合这些物品,与表演进行互动等等。这种形式的作品属于并不适宜在画廊或美术馆进行展示的作品。
可以说,王国锋的艺术实践突破了一般艺术或艺术作品的创作形式和成规。即便不是完全脱离,也表现出了极大的不一致。在王国锋的作品中,摄影或视频等作品是适合在美术馆或画廊等空间展示的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或艺术作品。
探讨王国锋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说出“属于(一般意义的)艺术”,或是“不属于(一般意义的)艺术”这样的语言,但归根结底,这是因为王国锋试图创作的作品正是有别于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的艺术”。难道不是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进一步思考:他的摄影及视频作品实际上既不属于“一般意义的影像作品”,又不属于“一般意义的艺术”呢?
2 多义性
王国锋的摄影作品中,最著名最出色的,应该是被称作“社会主义系列”的作品。该系列作品在表象上的特点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或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型建筑作为拍摄对象,并且整个画面里没有一个人物出现。具体而言,首先,王国锋选择了象征“社会主义”的建筑;第二,照片中原本被照上去的人物通过数码技术被删除。有时也只留下身穿中山服的艺术家本人,当然,他的存在也是十分渺小的。
这一系列作品的题目是《理想》,或《乌托邦》。对于国家来说,这样整齐划一的风景就是乌托邦。无论有多少人都要像没有人一样安静。无声的存在,对于国家而言才是一种理想(状态)。当然这不过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相反,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的理想(状态)是:不是人而是国家要像这样整齐划一、沉默、安静。这对于民众才算得上是乌托邦。王国锋这一系列作品的特征就在于这样的“含义的双重性”,或者说“多义性”。
为什么说是“多义性”呢?原因在于这个“双重性”其实并非仅有“双重”。第一,这一系列作品不单单比喻“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人民”,也可以普遍地延展为比喻“人民”与“国家(体制)”;第二,作为该作品的创作背景的中国当代社会及中国人民,这两方的关系很复杂,有丰富的多义性。
因此,王国锋这一系列作品不可以被单纯地解读。诸如“在作品画面中删掉像沙子一样多的人,单纯地表现出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或者“通过删掉人来呈现高大宏伟的建筑,以此来批判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矛盾”等等表述,都是肤浅的说法,无法全面地把握作品所传达出来的思想。
3 天安门广场
每当我看到王国锋的作品,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天安门广场。准确地说不是现在的天安门广场,而是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之前的空旷的广场。在我的想象中,天安门广场一直在冬天里,冷风吹过广袤的空间。如果这里集结军队或者人群的话,那一定是有大事件的。这是我假想的事。事实上的确曾有过红卫兵集结于天安门广场的事情发生。在我的想象(世界)中,不论王国锋拍摄的建筑是什么,都与故宫叠加在一起了。我的幻想虽然只是个人感觉,但这并非与观念和理念无关。
原本是为了人类服务的建筑,因其体形巨大而超越人的时候,也可以说在观念层面上忽视人的时候,就自行其是地展开独立行动了。在这里,只有建筑,人消失了。并不是真的消失了,而是建筑的存在感太强了,没有了人的存在空间,使人无法接近建筑。
在我眼中,这些建筑也广义地象征着所谓的“国家制度”,或“国家权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市里的超高层建筑,本质也是非人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两种建筑是相同的。
在我的眼中,日本的超高层大厦看起来是一种巨大的虚无。而王国锋拍摄的巨大建筑,也不可避免地使我联想到故宫或天安门广场。正因为这样,王国锋镜头下的巨大建筑,同时也应该说相当于资本主义的超高层大厦。为什么?因为问题的核心始终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类”。这也是我所说的多义性。
4 社会性
若用一个词来概括王国锋的创作源泉,那 就是“社会性”。事实上,不仅仅是王国锋,基本上现在对中国的艺术家来说,剔除“社会性”因素就不可能有“艺术”。虽然有一些例外,但在中国当代背景下,把“艺术”创作与“社会”分离开来,纯粹追求“艺术”是很难的。因为在现实中,艺术都不可避免要面对“国家”或“社会”。这种情况就仿佛是“国家”或“社会”一直在“刮风”。一年中一直刮东风的地方长大的树木,不得不偏向西方。无论各个树木的心志如何,所有的树都只能偏向西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生活,但若要在国家和社会里生存,就只有跟着往西偏。要跟随“上层建筑”的导向。这种情况的极致就是:“人类”不再是“个”体,而是归结于“ 上层建筑”,那时,“人类”没有“个”体。
然而有时候,即使逆风,人们也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志生存。这就需要努力偏向东方。即使身体已经倒向西方了,也要努力通过本能、思想或者感觉而偏向东方。这时,“人类”就是个体,是并不一定从属于“上层建筑”的一种存在。
在西欧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中,艺术创作的根据,笼统地说就是从“上层建筑”转移到了“个体存在”。近代以前,“上层建筑”基本是宗教或宗教控制下的国家(地区、或民族)。西欧近代史就是人类取代“上层建筑”的历史。
那么,中国是怎样的情况呢?在当代中国,“人类”是什么?最后的归宿在哪里?
这些就是王国锋的作品里或暗示或鲜明地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的,同时也是普世的。
5 眼睛与大脑
王国锋的《理想》和《乌托邦》等系列作品吸引我的原因是:首先,作品中没有人,整个空间中营造出了“沉寂”的氛围。这种沉寂有着巨大的魅力。空无一人,这是为什么?这份“沉寂”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刚看到他作品的瞬间开始,“人在哪儿?”这个疑问始终占据我的眼睛和大脑。“大脑”开始寻找问题的答案,游走在各种不同的解读之间。尽管有诸多解读,最后我也只能选择一个。
而“眼睛”却仍然迷惘。这并不是因为“眼睛”没有回答的能力,而是作品中本来就没有人。没有就是没有,看到了“没有”的“眼睛”只能去追寻“没有”。而对这个“事实”,具有思考能力和使用语言能力的“大脑”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人。无论如何解释,解释终究无法触碰没有人这个事实。而且,可以说大脑的解释试图在回避“不存在”这个“事实”。而眼睛则比大脑更能直接地去触碰到“不存在”,顺服地接受无人的“事实”。
我被他的作品所吸引,主要是因为我的“眼睛”。“大脑”可以很快找到一个解释,因此无需苦恼。可是,虽然“大脑”给出了解释,“眼睛”却不能完全被说服。由于作品上“空无一人的事实”拥有非凡的魅力,“眼睛”也在“空无一人的事实”和在这个事实中所呈现出来的“沉寂”氛围里感受到了这个作品的最大的魅力。
可以这么说,在这里,“大脑”和“眼睛”的步调是不一致的。并非背道而驰,却也去往不同的方向。前者探求“意义”,而后者关注“作品本身”;“大脑”倾向于作品所要传递的深层思想或故事,而“眼睛”倾向于不解释;前者想超然于作品,而后者却想要摆脱含义;“大脑”以“理性”理解作品,而“眼睛”则以“感觉”去认知;“大脑”试图排除感觉,而“眼睛”试图排除理性。站在王国锋的作品前面,我的“大脑”認为,虽然这里没有人,但本来是有的,那么“没有人”(人没有被表现出来)就有特别的意义。也就是说,“没有人” 是一种表达方式。另一方面,我的“眼睛”感觉到没有人的事实,而且不仅这里没有,也许哪里都没有。即:感觉到这个事实本身就是这个表达方式的核心。眼睛不是想到的,而是感觉到的。
就我本人的喜好而言,艺术表达的核心是“眼睛”和“感觉”,而不是“大脑”或“含义”。这样的说法也许会让人认为我是一个“纯粹艺术派”。但是,艺术表达并非那么简单。
6 感觉的大海
二十世纪中期,在西方国家近代艺术走向终结之前,艺术的表现一直是偏重于意义的。为了超越这段历史,曾经有人尝试把艺术作品的意义排除掉,只做最纯粹的艺术。纯粹抽象绘画就是这种艺术的代表。其中失败的例子是放弃了绘画的“叙事性”,只单纯追求作品的“绘画性”,结果不是仅仅表现出了色彩的美丽,就是仅仅呈现了颜料本身这种物质。前者是“感觉”的探索方向有误区,后者则破坏了“绘画”。沉溺于感觉的大海并不是“绘画”。颜料本身的美和绘画的美是不同的,物质也不是绘画。
成功的例子,我们可以看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或者罗斯科(Mark Rothko),在感觉的海洋中传达出来的既非信息也非叙事的“含义”。超越特定而具体的叙事,把“叙事”溶化在“感觉”的大海中,然后理解从感觉中来讲述的“意义”。“理解这个意义”十分关键。
这种方法与想要表达特定而具体的信息的方法并不相同。因为若仅想表达特定而具体的信息,是可以省略掉把“叙事”先放在“感觉的大海”中这个步骤的。有没有这个步骤,表现出来的结果将大相径庭。“感觉”本身有其固有的“逻辑”,必须要感觉到才行。艺术是在感觉到这个“逻辑”之后才可能开始的一种表现(形式)。
我们称之为“艺术”的这种人类“表达活动”,不管源于什么动机(比如说是为了表现社会问题和矛盾或者为了在造型上实现纯粹的画面等),都是在“感觉”这个漫无边际的汪洋大海中呈现出来的。艺术家自己首先要溶化在这种“感觉”的汪洋大海里。不只是作为超然的旁观者,而是一定要沉潜在“感觉”里面。然后艺术家就会知道这种感觉的渗透力是巨大的,想随意行动是不行的。通常需要一边考虑方向及方法,一边摸索前进。否则根本无法前进。即使创作开始之后,也要一边前进一边不停地思考方向和方法是否正确。考虑这些就需要用到大脑,但考虑得是否正确,就必须用自己的感觉来验证,而不是反过来。
7 间接性
王国锋作品的魅力,并不在于只通过拍摄有象征性的建筑就能明显传达出来“政治体制”或者“人与政治体制”这个主题。我是首先靠眼睛来感知作品的,而不是先探寻接受主题或故事。眼睛首先接受图像本身,这一点对我来说是确定不移的。
我的眼睛首先捕捉到的是被拍摄对象本身的美及其呈现出来的漫无天际的“安静”,这是一种“虚”的感觉。更确切地说,前者并不是现实存在的建筑本身的美(我们并不知道现实中的建筑是否美)。王国锋所拍摄到的“建筑”的美,就是摄影作品的美。因此作品的美也是“被表现出来的虚”,虽然看不到“虚”(但是能确切地感觉到!),却能够真切感觉到美。不仅如此,我的眼睛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美”和“虚”。我一直关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近代艺术的最后阶段,知道如果不加以注意,作品就容易只注重“美”和“虚”,但我感觉王国锋的作品里还有别的东西。
他把建筑拍成照片。而他不是纪录摄影师,所以照片变成了被称为艺术品的“虚构作品”(Fiction)。一般而言,建筑物本身(给视觉)的信息越隐藏于虚构的主题中,作品的美就越能够被显现出来。从西欧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近代艺术的最后阶段来看,“叙事”和“美”在本质上是相互排斥的。但是在王国锋的作品中,在“叙事”存在的情况下,“美”就已经跃然呈现。在“叙事”层面丝毫不减的同时,达到了“美”的层面。这是我的眼睛能够感觉到的。他的作品并非只追求叙事而变成无聊的东西,也完全没有仅仅沉醉于感觉之中无法自拔的迹象。
王国锋作品的“叙事性”不像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那么直接。而是间接地隐喻于作品之中。以“虚”的感觉呈现出来这个事实,但是让观众感觉到的却是由“被删掉的人” 所引发的。这完全依靠他的直觉和感性。他的“感觉”让他决定从照片中删掉人。有时候,留白反而是更好的表达方式。“叙事”从表面消失,隐藏在作品里。隐含的叙事,有时使作品的表现更具冲击力。
8 直接性
当我不能够完全理解王国锋的作品时,我就背过身去。那时,我的肩膀和后背感觉有什么东西掠过,很微妙的感触。于是我转身再看作品,然后,为了确认刚才的感觉,再次背过身去。当然,第二次就没有了这种微妙的“感触”了。但我知道,作品传达给了我类似“气场”的东西,一种“信号”、“眼神”或“愿望”!
这种感触有别于所谓的一般的气场(aura)。气场的实质是“品质”。越优秀的作品,品质越高,气场也就越强大。“气场”是面对作品的时候也能够充分感受到的。可以进一步说,艺术作品的“气场”是“视觉”的概念,只有通过看艺术作品才能存在的。作品的“气场”并不会超出视野之外。但是,从王国锋的作品传达到我肩膀和背后的更像是一种声音,在呼喊着:“欣赏我、感觉我”。虽然看不到“作品上的人” ,我却想去看到和感受到他们。这样的呼声使我感受到作品的“社会性”。当我没有把握住这一点的时候,我背过身,“她”就赶来迫我。另外,作品本身有6到7米的大尺幅也很重要,因为这样可以使很小的声音变成很大的呼声。
虽然王国锋作品的“叙事性”很强,但更为重要的,它的“叙事性”是以绝妙而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样的“间接性”增强了作品的“叙事性”,提高了作品质量。在这里,我将他试图表现“叙事性”的做法,看作是远远超越了艺术史上一些不好的写实主义、社会主义写实主义和主题主义的范例。将王国锋的作品看作是虽然试图追求“社会性”,但却是从“感觉”出发、或以“感觉”作为支点的范例。可能艺术家本人没有察觉到,作为一个表现者,他的出发点不是别的,就是“感觉的大海”。
与上述“绝妙的间接化”相矛盾的是我还在他的作品里感受到了“直接性”。删除人的影像毫无疑问是受“间接化”意图的驱使,从那迷人的“安静”中引出了美丽的“虚”。而且,不得不说他的作品也确实理直气壮地表现出了“直接性”。王国锋从正面拍摄了北京站、北京展览馆、北京饭店等一些特定的宏大的建筑。这些建筑很美,以至于如果有人觉得艺术家只想拍摄建筑本身的美也不足为怪。但这种美并不是因为其作为建筑作品而产生的美,而是作为一种“存在”而美。我的眼睛不停地被这个事实吸引,使得我不得不长时间盯着作品。然后,我感觉到这个呼声并不是从建筑前面的广场发出来的,而是从建筑本身而来,而建筑本身就是人民。
9 “矛盾”是一种可能性
人并不是被删掉了,而是跟建筑一体化了。或者说为了化为建筑而必然地被删掉,而穿中山装的王国锋本人作为人的象征,替代他们站在那里。虽然,在巨大的建筑面前,艺术家显得十分渺小。我们也无从知晓观众是否看到了他,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建筑本身就是人。建筑物或者说体制不是别的,就是人本身。没有什么是比这个更为“直接”的信息了。对于适应了西欧及资本主义国家艺术的我来说,面对如此“直接的”开宗明义,让我有些眩晕。那是因为在一段时期内,我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作品。
在西欧,绘画(艺术表现)也曾经是直接表现“叙事性”的。但受到西方近代艺术巨大洪流的冲击,将所谓的“叙事性”间接化了,甚至选择了离开。于是,从“叙事性”最终向着“造型性”发展下来。发展到二十世纪后半期就走到了死胡同,这是很多人了然于心的共识。在西欧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艺术,基本上也是同样的状况。
王国锋的摄影呈现出了与上面不同的存在方式的可能性。不要误会,他并不是想在艺术表现中简单地恢复“直接性”。而且,也不是说中国当代艺术流派想要完全脱离西方而独辟蹊径。不知道别的艺术家如何,王国锋不是。我认为,他的摄影作品的“直接性”(也是“间接性”)的存在方式与西欧艺术不同。那么,他试图要表现出来的也许是不同于一般“艺术”的某种艺术,是不一样的“作品”。
换句话说,知道建筑就是人类本身,并没有改变建筑的“美”和“虚”的魅力。也就是说,建筑既是人,同时也是建筑本身。王国锋实现了包含双重性的“矛盾”本身。
因此,我在王国锋的作品中所看到和感受到的建筑的“美”和“虚”,并不是他在向“造型性”的发展中产生的。当然,造型性本身的魅力也必然存在,但并不是孤芳自赏封闭在里面的。这点就不同凡响。更准确地说,他的“作品”并非刻意营造出“无”,那种只能通过刻意营造“无”来表达艺术的事情也与他无关。在这种意义上,他的尝试蕴含了此 前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的可能性。不是单纯的“新”,也不是單纯的“可能性”。而是创造出不同形式的“作品”的可能性。这里说的不同形式,是区别于迄今为止我们所理解的“艺术”的。
使王国锋的艺术尝试成为可能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他的个人才能,另一方面是中国当代社会。艺术源于社会,也会超越社会。那么,王国锋将走向哪里?
